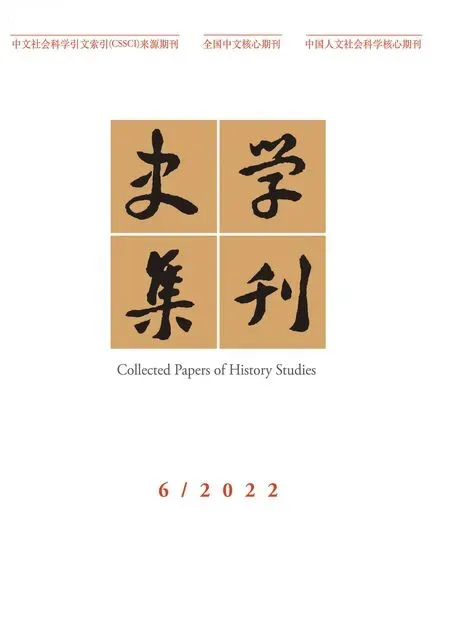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论明代中期“理学名臣”丘濬的佛教观
何孝荣,陈文博
(1.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天津 300350;2.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景泰至成化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明孝宗即位后,丘濬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不久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七年(1494)八月,他升少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廉能有为,两广用兵,他“陈方略数事”,军帅“多其策”。他主国子监,“鼓舞诱掖,以兴士类”。及入阁,丘濬“上二十余事,陈时政之弊,且请访求遗书”,明孝宗“皆嘉纳”。(1)《明孝宗实录》卷九七,弘治八年二月戊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775-1776页。他著有《大学衍义补》,明孝宗褒称“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致治”,(2)《明孝宗实录》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辰条,第135页。又有《朱子学的》《家礼仪节》《世史正纲》《琼台诗文会稿重编》等,(3)参见李焯然:《丘濬著述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99-124页。今人合编为《丘濬集》。作为当时的“理学名臣”、宰辅高官,丘濬视佛教为“异端”,要求抑制佛教势力,同时他也赞扬、信奉佛教,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思想和生活呈现出杂糅矛盾状态。迄今尚无专文探讨丘濬的佛教观,仅个别论文有所提及。(4)学术界目前只有郑朝波《论丘濬的宗教思想》涉及丘濬的佛教观,但未作专门论述。参见郑朝波:《论丘濬的宗教思想》,《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本文试图考察丘濬出入理学与佛教及其杂糅矛盾的佛教观,揭示丘濬以及明代中期的官员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态。
一、尊奉程朱理学,视佛教为“异端”
儒学自汉代为董仲舒改造后被尊为统治思想。魏晋以后,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对儒学主导地位形成一定冲击。北宋程颐、程颢等人进一步改造儒学,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创立了理学。明初,明太祖宣布“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5)(清)陈鼎编:《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4页b。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永乐年间,明成祖编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汇集程朱等人的“四书”“五经”传注以及性理论述,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和科举考试的标准,“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6)(明)胡广等:《性理大全》卷首附明成祖《御制序》,国家图书馆藏明内府抄本,第4页a。这样,程朱理学居于独尊地位。
丘濬出生于明初,通过寒窗苦读,由科举入仕,因此他服膺程朱理学。他以“诚”为世界本原和最高范畴,“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一诚。诚者何?实理也”。(7)(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首《诚意正心之要·审几微·察事几之萌动》,《丘濬集》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丘濬提出“诚”就是“理”,与程朱并无二致。他也认同程朱的天理、人欲之别,“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8)(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首《诚意正心之要(补)》,《丘濬集》第1册,第13页。不过,丘濬并非一位理学理论家,他没有就“理”“气”“性”等理学范畴做更多的论证和探讨,而是遵从程朱之说。(9)参见郑朝波:《丘濬哲学思想辨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他引宋儒真德秀话说:“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复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于朱子而大明。其视曾子、子思、孟子之传,若合符节,岂人之所能为也哉?天也!”(10)(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朱子学的·道统第二十》,《丘濬集》第7册,第3430页。将程朱理学定为儒学正传。他尤其尊奉朱熹,其学“以紫阳为宗,读书穷理,以究极圣贤之精蕴”。(11)(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首附(明)郑廷鹄《刻琼台会稿后序》,《丘濬集》第8册,第3695页。他“汇朱子微言,仿《论语》作《学的》”,(12)(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首附(明)叶向高《丘文庄公集序》,《丘濬集》第8册,第3678页。即辑录朱熹思想论述而编成《朱子学的》,弘扬程朱理学。因此,后人称其为明代“理学名臣”。(13)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一《丘濬》引《理学名臣录》,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三十五辑“史部方志类”第四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a。
儒学与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作为和影响等方面都截然不同,因此前贤往儒斥佛教为“异端”。丘濬尊奉程朱理学,自然也将佛教视为“异端”。但他对佛教为“异端”不再做学理上的重复论证,只是偶尔引述并阐发前人有关言论。如,他在指出佛教与儒学的区别和佛教危害时说:“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谓因果,所谓缘业,彼之深于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僧人出家,“其于世间一切纷华声利、美好端丽之物,视如土苴。虽其君亲眷属有所不顾,头目手足有所不惜”。(14)(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重修杭州石屋寺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8-4289页。他引述宋高宗反对鬻牒度僧之言:“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并进一步阐发道:“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15)(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7-558页。
丘濬经常引述前人关于佛教为“异端”的论述。如,他引述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再引用程朱派学者指后世佛教为“异端”之言:“程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史伯璿曰:……佛氏之学,能弃君父,灭纲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丘濬评论说:“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德无不一,非绝去异端之教不可也。”(16)(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七八《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丘濬集》第3册,第1216-1217页。也就是说,佛教、道教为最大的“异端”。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反复斥责佛教为“异端”。如谈及丧礼,丘濬说:“礼废之后,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乡里中求其知礼者盖鲜”,朝廷须行“古礼”,“而异端自息矣”。(17)(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五一《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家乡之礼(上之下)》,《丘濬集》第2册,第833页。
永乐年间,太子少师姚广孝抄传所著《道余录》,批驳程朱等人“攘斥”佛教之言,“逐条据理,一一剖析”,(18)(明)姚广孝:《逃虚子道余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46页。护持佛教。姚广孝即释道衍,为“靖难”第一功臣,深得明成祖宠信。时朝廷独尊程朱,饶州儒士朱季友“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被明成祖斥为“儒之贼”,“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19)(清)陈鼎编:《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第14页b。但明成祖对姚广孝及《道余录》并未批判和惩罚。至宣德年间官修《明太宗实录》,则斥姚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20)《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073页。指其为官方哲学之敌。(21)参见何孝荣:《论姚广孝与新明朝的建立》,《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丘濬在朝,时有人以《道余录》见示,请“为之分析”。丘濬作诗回复说:“儒生不读佛家书,道本无亏岂有余?请问前朝刘太保,西来作用竟何如?”(22)(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四《王初阳尚书致政家居,以姚少师〈道余录〉见示,意欲予为之分析。书此复之》,《丘濬集》第8册,第3853页。意思是,作为儒生是不读佛家书的,程朱理学之道圆满完备而“无亏”,没有姚广孝可以商榷批驳之处;请问元朝太保刘秉忠(刘秉忠先以僧人辅佐元世祖,而后还俗为官)治国究竟是用佛法好,还是儒学好?丘濬仍是指斥姚广孝《道余录》为“异端”。
二、反对皇帝佞佛,要求抑制佛教势力
魏晋以后,佛教迅速传播,很多民众出家,大肆修建寺院,佛教势力膨胀。对此,丘濬指出,“佛之教行乎中国,中国之人所以崇奉之者无所不至,广其寺宇,严其像设,而又累木石以为浮图”,“下至偏州小邑,无不建之,以为标表焉”。(23)(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延祥寺浮图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7页。僧人冗滥,“今世所谓高者,往往华服用,精饮馔,居则侈屋宇,出则盛骑从,甚至争总摄之位,购住持之檄,终讼以告讦,持梃以相向。至于犯戒律,违规约,则又其日用常行事耳”,不真实修行,乃至逾戒越律,“举世皆然”。(24)(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重修杭州石屋寺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9页。
丘濬赞同禁绝佛教。他高度赞扬后周世宗的禁佛,表示“世宗毁佛像以铸钱,毅然不惑,可谓刚明之主”。(25)(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二七《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铜楮之币(下)》,《丘濬集》第2册,第489页。他引欧阳修提倡的修补儒学以抑制佛教,及韩愈禁绝佛教之论,指出:“其法行乎中国千余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易然者。欧阳氏欲吾修补吾政教之缺废者,诚反本之论”,“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教、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之说,乘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德之教、礼义之俗,顿然复矣”。(26)(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七八《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丘濬集》第3册,第1223页。
不过,丘濬也看到,佛教为民众广泛信奉,历代并不能真正将其去除,因此他提倡切实可行地抑制佛教,避免佛教势力过度膨胀。他说:佛教“已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27)(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7页。为此,他反对皇帝佞佛。他引梁武帝事例说:“古之帝王好佛者无如梁武帝”,“考之史鉴,武帝饿在台城,子孙自相鱼肉,以至于亡”。(28)(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七《论厘革时政奏(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丘濬集》第8册,第3973页。梁武帝“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本欲儌福于己,而反有以致祸于人,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后世人主其鉴之哉”。(29)(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戒滥纵之失》,《丘濬集》第4册,第1761页。丘濬反对僧道入宫。他引述《周礼》注疏“潜服、贼器不入宫”云云,评论说:“成周以宦者掌门禁,其严也如此。我朝禁僧道非朝见由前门,不许入皇城门,及无牌面,并凶服、异服,有持寸铁者,皆不许入禁门,亦周人意也。”(30)(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八《治国平天下之要·严武备·宫禁之卫》,《丘濬集》第4册,第1848-1849页。他抨击元朝皇帝佞佛,“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宫持咒,每岁元正,命所谓佛子者张白伞盖,遍游都城,此何理也!”(31)(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六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秩祭祀·祭告祈祷之礼(下)》,《丘濬集》第3册,第1018页。
丘濬反对皇帝大肆度僧建寺。他批判唐代李德裕等人以度僧为皇帝“资福”之论,指出:“天以好生为德。度民为僧,是阏绝天地生生之仁,岂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矧绝六十万人之生,意其召灾,又何如哉!以是为求福,臣不信也。”(32)(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6-557页。他举宋神宗因钱公辅建议“始卖度牒”,指出“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卖度牒始于此”。他再批判王安石大肆鬻卖度牒而贴补国家财政的做法,说:“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民未为僧,官未卖度牒,未尝无边事,无荒年,未闻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孟负其学,以尧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见也。”(33)(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7页。其实,丘濬并非完全反对鬻卖度牒,而是主张有限度地鬻卖度牒。他引述宋高宗反对鬻买度牒之言后,评论说:
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无违碍,量地方远近,俗尚缓急,俾出关给度牒路费钱,收贮在官,造册缴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祝圣之日,行礼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其教法,当众簪剃毕,然后给牒。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簪剃者,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缺不补。如此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既得其钱,岁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及修造桥梁之用。如此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34)(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8页。
丘濬主张按照明成祖规定的僧人“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35)《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条,第2109页。鬻卖度牒。这样,度僧就不会超过“祖制”定额,既限制了僧团势力的膨胀,国家又可通过鬻牒获得“免丁钱”,贴补财政,获得经济利益。
三国魏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对此,丘濬指出:“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36)(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八八《治国平天下之要·备规制·宫阙之居》,《丘濬集》第3册,第1359-1360页。这也是提醒皇帝,若大肆修建佛寺道观,“则必驯致于亡”。
除了通过评史来表达其反对皇帝佞佛,要求抑制佛教势力的主张以外,丘濬还在弘治五年(1492)四月十日直接给明孝宗上疏,“论厘革时政”,指出“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义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云云。而其“厘革时政”建议的前七条,都是针对皇帝可能受到蛊惑而佞信佛教(包括道教,但为次要者)而言的,包括:(1)“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请折之”;(2)“有言创造寺观以植福田者,请谕之”;(3)“有言印造经忏以求利益者,请谕之”;(4)“有言修斋设醮必须丰盛者,请折之”;(5)“有言诵经持咒可以禳度者,请正之”;(6)“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术者,请谕之”;(7)“有言祀神以求福佑者,请正之”。(37)(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七《论厘革时政奏(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丘濬集》第8册,第3972-3976页。丘濬提醒皇帝不要受臣下及僧道蛊惑而佞佛,应抑制佛教势力的膨胀。
三、强调恢复儒家礼仪,辟除佛教习俗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为各阶层人士接受和崇奉,生活中如婚嫁丧祭、祛病除疫、日常信仰等习俗多受到佛教影响而改变。丘濬视佛教为“异端”,也强调恢复儒家礼仪,呼吁辟除佛教对习俗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婚嫁丧祭习俗。婚嫁丧祭是人生必然经历的大事,其礼仪习俗也最受人重视。魏晋以后,婚嫁丧祭的礼仪风俗逐渐受到佛教影响,中国传统古礼荡然无存。对此,丘濬尤为不满。他引古代颍川太守韩延寿与民众“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之事,指出:“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婚嫁丧祭之无其制”,“民间一遇婚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说之炫惑,遂至破产”,“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蠧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矣”。他说:“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婚丧祭,一依此礼以行。……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38)(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八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广教化以变俗》,《丘濬集》第3册,第1279页。他呼吁民间婚丧嫁娶使用《朱子家礼》,去除佛道风俗。
特别是丧葬礼仪,在宋代以后流行作佛教法事。明初,明太祖多次在首都南京举办佛教法会,“为死者超升,生者解冤”,(39)明太祖:《御制蒋山寺广荐佛会文》,(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三《钟山灵谷寺》,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b-70页a。又下令将全国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其中教寺、教僧专门为民众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法事(名瑜伽僧或赴应僧)。明代中期以后,“教僧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40)龍池淸:「明代の瑜伽教僧」、『東方學報』、1940年第1期。民间法事盛行。(41)参见何孝荣:《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83页。丘濬引述“孔子在卫,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相焉。孔子许之”,然后评论说:“礼废之后,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乡里中求其知礼者盖鲜。必欲古礼之行,必须朝廷为之主,行下有司,令每乡选子弟之谨敏者一人,遣赴学校,依礼演习,散归乡社,俾其自择社学子弟,以为礼生。凡遇人家有丧祭事,使掌其礼。如此则圣朝礼教行于天下,而异端自息矣”。(42)(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五一《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家乡之礼(上之下)》,《丘濬集》第2册,第833页。他又引述司马光“世俗信浮屠诳诱,于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云为死者灭弥天罪恶,必生天堂,受种种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烧舂磨,受无边波咤之苦”云云,指出:“追荐之说,惟浮屠氏有之。……士庶之家,一有丧事,无所根据,因袭而为之,以为当然之礼耳”,“昔宋儒朱熹所著《家礼》,会粹诸家礼,以为一书,而于丧礼尤备。我太宗皇帝命儒臣载入《性理大全》书,颁行天下。臣尝以浅近之言,节出其要,以为《仪注》,刻板已行,在臣家乡,多有用而行者,遂以成俗。盖行古礼,比用浮屠省费数倍。伏望圣明为礼教主,复行古礼,非独可以正民俗、辟异端,而亦可以省民财、厚民生也”。(43)(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五一《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家乡之礼(上之下)》,《丘濬集》第2册,第835-836页。丘濬主张丧祭恢复朱熹《家礼》,去除佛、道法事礼俗。丘濬在为泰州独乐处士王昭作墓志铭时,赞其“尤以孝闻”,“两居丧,一本古礼,不用浮屠法”。(44)(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二三《独乐处士王公墓志铭》,《丘濬集》第9册,第4512页。
丘濬反对焚尸火葬习俗。自古以来,中国尤其是儒家提倡孝亲,主张土葬。但后世民众贫困,亲人去世而无地土安葬,有抛尸野外者,也有受佛教风俗影响而火葬者。丘濬不以为然,他引述宋朝“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并州知州韩琦“为买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他评论说:“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45)(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八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广教化以变俗》,《丘濬集》第3册,第1285页。他从中国传统孝亲观念出发,认为受佛教影响的火葬违背孝亲人伦,要求恢复土葬。

“傩”为古代在腊月举行的驱疫逐鬼仪式。丘濬引述《汉志》所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指出“傩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于《周礼》方相氏,而其事见于《月令》之三时”,“虽以孔子之圣,亦从乡人之所行,盖有此理也”,“汉唐以来,其法犹存。汉以中黄门为之,盖以其出入禁掖为便”。丘濬指出,后世“傩”俗失传,“然宫中邃密,阴气偏盛,不能无影响之疑,于是乎假外道以驱除之。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宫持咒,每岁元正,命所谓佛子者张白伞盖,遍游都城,此何理也”!丘濬提出,“斟酌汉唐之制,俾内臣依古制,以为索室逐疫之法,是亦辟异端、严宫禁之一事也”。(47)(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六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秩祭祀·祭告祈祷之礼(下)》,《丘濬集》第3册,第1017-1018页。
第三,丘濬反对民间师巫打着佛道降神救病旗号,烧香集众,行组织叛乱之实。他引述北宋庆历年间贝州等地“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宣毅军卒王则借此组织发动叛乱之事,然后评论说:“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48)(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三八《治国平天下之要·严武备·遏盗之机(下)》,《丘濬集》第5册,第2139-2140页。丘濬还引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因而发动起义一事,他警告说:“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49)(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三八《治国平天下之要·严武备·遏盗之机(下)》,《丘濬集》第5册,第2149-2150页。
四、赞扬佛教,宣传慧能及广东地区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丘濬在朝议事建言,尤其是在撰呈给皇帝、论述“治国平天下之要”的《大学衍义补》中,表达出鲜明的尊奉程朱理学(儒学),视佛教为“异端”的态度和思想倾向,要求禁绝佛教,强调抑制佛教势力。但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他也赞扬和肯定佛教,与僧人交游。
我们翻阅并以“佛”“释”字对文渊阁《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进行全文检索后,没有发现丘濬撰写过赞颂释迦牟尼的专门诗文。但是,他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观音偈》:“观音菩萨妙观音,两眼睁睁到处寻。不用临风侧双耳,声容言貌总归心。”(50)(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四《观音偈》,《丘濬集》第8册,第3861页。观音为观世音的简称,佛教宣扬其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愿,众生遇难时,只要念其名号,观音菩萨“观其音声”,即前来解救。(51)(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大正藏》第九册第262号,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电子佛典集成”2018年版,第56页。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盛行。丘濬赞扬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不待大众念诵名号,即眼寻并解救众生所受苦难,是“妙观音”。丘濬对观音菩萨的赞扬,反映出他对佛教的赞扬和信奉。
丘濬宣传慧能及广东地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禅宗初祖达摩,南朝梁时从海上来到广州,然后北上,在中国传化。慧能,唐朝贞观年间生于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东),后移居南海(今广州),龙朔年间至黄梅东禅寺修习,不久禅宗五祖弘忍授以衣钵,慧能即逃隐于岭南十余年。仪凤元年(676),慧能至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正式剃发受戒。其后,他行化于广州和韶州(今韶关)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新州国恩寺等地,弘扬南宗禅法门。先天二年(713),慧能圆寂。唐宪宗时,赠谥“大鉴禅师”。其后,南宗禅获得朝廷认可为禅宗正宗,慧能成为禅宗六祖,禅宗为后世中国佛教的主体(其他宗派多衰微难传)。因此,慧能及广东地区在禅宗史、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丘濬对此大力宣传,先后两次为禅宗祖庭南华寺作长诗。第一次所作诗名为《寄题南华寺大鉴禅师》,诗中充满了对佛教东来(“佛法来东旦”)、禅宗初祖达摩在广州进入中国(“禅宗肇岭南”)、慧能在岭南创立南宗禅(“一溪香气水,万缕藕丝衫”)、禅宗分化出五家七宗(“结子花开五,先人枣示三”)、一统中国佛教(“众流归大海,孤月印寒潭”),以及对中国佛教贡献(“蔼蔼花云暖,瀼瀼法露甘”)的赞誉,还表达出他自己“也知祖堂近,无暇一登参”的遗憾。(52)(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四《寄题南华寺大鉴禅师》,《丘濬集》第8册,第3816页。丘濬第二次所作诗名为《题寄南华寺三首》,也表达了与《寄题南华寺大鉴禅师》一致的情感,仍是肯定慧能及广东地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53)(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四《题寄南华寺三首》,《丘濬集》第8册,第3858页。
丘濬还曾为广东南雄延祥寺修建佛塔作记文,其中说:“西竺氏之教,法派相传,凡二十八代,至达摩始至中国,又五传至卢能(慧能俗姓卢,故又称卢能——引者注)而止焉。其始也达摩自南天竺浮海至广州,而北往中国,其终也卢能自黄梅得道归,南至广州祝发,终于曹溪居焉,遂不复传。是则禅教之兴,始终皆在于岭南。而雄都乃岭南往来必由之道,而寺适当其冲,而浮图在于是焉,谓之异人之建,虽不可必要之,不能无意也。”(54)(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延祥寺浮图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7页。从这些文字,也可见丘濬对禅宗及广东地区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的肯定。
五、喜寺院悠闲安静环境,与僧人交游
丘濬也喜欢寺院悠闲安静的环境,经常游览。他为名刹金山寺题诗:“岷江万里下,梵刹半空开。吴树风吹断,淮山水荡回。潮声杂钟磬,波影动楼台。千载张公子,题诗会雨来。”(55)(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三《寄题金山寺》,《丘濬集》第8册,第3796页。他与友人游寺登山,薄于日暮,未及绝顶,遂约次日重游,作诗云:“扰扰世尘间,聊偷一日闲。寻僧因到寺,乘兴偶登山。野色供春赏,钟声送晩还。明朝重有约,蹑屐上孱颜。”(56)(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三《与友人游寺中,遂登山,薄于日暮,未及绝顶,约次日重游》,《丘濬集》第8册,第3791页。他又游一山寺,有诗曰:“暇日来游祇树林,焚香话久落花深。竹光日透成金界,鸟语风传杂梵音。草绣岭头成绀发,月沉潭底印禅心。老僧携卷求诗句,乘兴挥毫试一吟。”(57)(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五《游山寺,寺僧携卷求诗,因次人韵》,《丘濬集》第8册,第3918页。他游览寺院时为空上人方丈题诗曰:“地僻少风尘,僧居即隐沦。烟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长日饭留客,夕阳钟送人。他年如结社,还许醉相亲。”(58)(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三《题空上人方丈》,《丘濬集》第8册,第3798页。他还希望能如东晋名僧慧远与刘遗民等在庐山结社念佛。
丘濬羡慕僧人的悠闲安静生活。他在《送僧还山》一诗中说:“山人慵出山,才出即思还。举世惟僧乐,谁人似汝闲!风花空色界,水月静禅关。了却尘中事,方能出世间。”(59)(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三《送僧还山》,《丘濬集》第8册,第3805页。在《姑苏陈氏佳城十景十首》中,有两首吟诵了寺院的悠闲安静。其一为《海云茶屏》,其二为《寄心修竹》。(60)(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三《姑苏陈氏佳城十景十首(缉熙学士先茔)》,《丘濬集》第8册,第3809页。丘濬在《过峡山飞来寺》一诗中说:“三过飞来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顿悟我曾僧。钟响出幽壑,猿声啼古藤。本无来与去,明日问南能。”(61)(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三《过峡山飞来寺》,《丘濬集》第8册,第3802页。慧能为南宗禅创立者,故又称南能。丘濬艳羡寺院生活,甚至说自己前世为僧人。
丘濬与僧人交游。上引丘濬抒写寺院环境和生活的诗,多是他游览寺院、与僧人交游而作。再如,他在《暇日过僧寺偶书》一诗中云:“僧居暇日偶经过,话到忘机不觉多。夙契自应知我是,任缘无复问谁何。”(62)(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五《暇日过僧寺偶书》,《丘濬集》第8册,第3900页。闲暇之日,丘濬拜访寺僧,相谈甚欢,有“夙契”,由此也透露出他一定程度地信奉佛教。再如,北京僧人惠馨,成化年间云游至杭州,重修圮废的石屋寺(大仁院),后至京,托通政何文璧介绍,请丘濬作修建记文,丘濬“不辞而为之书”。(63)(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重修杭州石屋寺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9页。丘濬交游的最有名僧人为当时的皇亲、左善世周吉祥。吉祥为北直隶昌平(今属北京)周氏子,明英宗贵妃周氏之弟。吉祥幼时好出游,尝出不复归,后出家于京城大觉寺。他日常游行于坊市,夜入报国寺伽蓝殿中歇宿。天顺二年(1458),据说周贵妃、明英宗同时梦感伽蓝神来告,遂令宦官找到并召吉祥入宫。觐见寒暄后,吉祥仍愿为僧,不想还俗封爵,遂复还寺,周贵妃厚赐之。明宪宗继位,周贵妃成为太后,吉祥成为皇帝舅舅。成化二年(1466),明宪宗令改建护国寺为大慈仁寺,又“广度僧众,俾居其中”,(64)明宪宗:《御制大慈仁寺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授吉祥为右阐教。成化十七年(1481)十月,吉祥升右善世。(65)《明宪宗实录》卷二二○,成化十七年十月甲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806页。后吉祥官至左善世,为最高僧官。弘治年间,吉祥成为明孝宗的舅爷爷,孝宗为大慈仁寺立护敕碑,碑载庄田数百顷。弘治二年(1489)四月,吉祥奏请免拆毁私创寺观,礼部弹劾其“故违禁例、阻挠新政”,明孝宗也不得不斥其“辄便奏扰”,(66)《明孝宗实录》卷二五,弘治二年四月丙辰条,第576页。但并未惩治。吉祥“住寺,众尝数百人,禅诵济济”。(67)(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六《吉祥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65-766页。示寂,明孝宗“遣官致祭”。(68)(明)归有光:《震川集》卷一一《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289册第173页。可见,吉祥是“贵戚之为僧者”,(69)《明孝宗实录》卷二五,弘治二年四月丙辰条,第578页。也曾因维护佛教而反对拆毁私建寺观,遭到大臣们弹劾。对僧官周吉祥,丘濬理应保持社交距离,毕竟二人“道不同”。但是,丘濬与他熟络,并为之撰写了一篇像赞:
貌癯而清,行勤而苦,味蔬笋以代膏粱,被裓衣而舍簪组,丛林仰其志之孤高,大众服其心之公溥。拈花鹿苑,契空相于无言;竖拂猊床,敛机锋于不语。飘飘然虚空无碍之闲云,霡霡乎法界有情之甘雨。体道以心,与物无忤。是宜奉纶命而握僧录之印章,震潮音而立禅宗之仪矩。以戚畹近派之贤,为宝刹开山之祖。祝慈寿于万年,演宗风于千古。(70)(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二二《周僧官赞》,《丘濬集》第9册,第4485页。
丘濬把吉祥描绘为一位清瘦刻苦、持戒公正、禅悟空透、管理有方的高僧。是直笔绘写?还是曲笔奉承?或兼而有之吧!
余 论
作为明代中期的“理学名臣”、宰辅高官,丘濬一方面视佛教为“异端”,要求禁绝佛教,强调抑制佛教势力,辟除生活习俗中的佛教影响,另一方面又赞扬、信奉佛教,宣传慧能及广东地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僧人交游。他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其佛教观建立在理学根基和底色之上,因此既有尊奉程朱理学而视佛教为“异端”、希望禁绝佛教的原则坚守和理想追求,又包含鉴于社会现实而提倡抑制佛教的妥协变通,还掺杂了赞扬佛教、信奉佛教的个人信仰真实流露,几个面相既矛盾冲突,又杂糅于一体,颇有特色。那么丘濬何以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有如此杂糅矛盾的佛教观?或者说,形塑“理学名臣”丘濬杂糅矛盾佛教观的社会、个人背景是什么?丘濬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的佛教观又有怎样的典型意义?
首先,明代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是丘濬视佛教为“异端”、要求禁绝佛教、辟除生活习俗中佛教影响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明太祖尊奉程朱理学,明成祖编颁三部“理学大全”,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明代前期、中期,士子们为了科举功名,多埋头苦读程朱著作,学作“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理学家们也多墨守程朱,“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71)《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2页。士子们“读圣贤书,知佛、老为异端”,(72)(明)李贤:《古穰集》卷三○《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4册第790页。因此很多人主张禁绝佛教。如方孝孺“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不惮放言驱斥”。(73)(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四三《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5页。解缙提倡“释老之壮者驱之,俾复于人伦;经咒之妄者火之,俾绝其欺诳”。(74)《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第4116页。正统年间,理学家吴与弼指出:“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难矣。”(75)(明)李贤:《古穰集》卷二九《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4册第785页。在这种严厉的文化专制环境下,丘濬读书、应试,终成“理学名臣”和宰辅高官,他理当接受并带头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尊奉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成为他的思想根基和底色,因此他视佛教为“异端”,要求禁绝佛教,强调去除婚丧嫁娶、祛病除疫等各种生活习俗中的佛教影响。可以说,这是他作为“理学名臣”、宰辅高官而对明朝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的原则坚守和理想追求。
其次,明代统治者提倡和保护佛教,明代中期诸帝极为崇奉佛教,是丘濬容忍佛教,但反对皇帝佞佛,要求抑制佛教势力的主要原因。魏晋以后,佛教为各阶层人士普遍信奉。明太祖崇信佛教,并认识到佛教对劝化民众、维护统治有巨大作用,“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76)明太祖:《御制文集补·释道论》,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78页。明太祖宣扬“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77)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一一《三教论》,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第156页。为此,明太祖制定,后经明成祖完善,明朝确立了既提倡和保护,又整顿和限制的佛教政策。至明代中期,最高统治者“平庸佞佛者多”,“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常常得不到很好的执行”,(78)参见何孝荣:《明代佛教政策述论》,《文史》,2004年第3辑,第49-70页。致使佛教势力膨胀。主要表现有:其一,大肆封授供养藏僧、做斋醮法事。正统年间,京城供养藏僧数百名,朝廷“命启秘密各色坛场”。(79)(明)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赐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第99页。成化年间,京城供奉藏僧1200余人,封法王13位,明宪宗“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赐予骈蕃”。(80)《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条,第1077页。其二,滥发度牒。为了限制佛教势力,永乐年间规定全国僧人总额,且五年一次考试,发放度牒。但正统、景泰年间,均实行三年一度,滥发度牒。明宪宗大肆度僧,成化二年(1466)、成化十二年(1476)、成化二十二年(1486)通过考试和鬻卖,共发放度牒超过37万张,全国僧、道“共该五十余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僧人),(81)(明)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三《陈言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7册第734页。超过永乐定额的10余倍。(82)参见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何孝荣:《论明朝中后期的鬻牒度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其三,广建寺院。明代禁止私建寺院,但各朝皇帝无不带头建寺,并为各地私建寺院赐额,使其披上合法外衣。如明英宗“命役军民万人重修[庆寿寺],费物料巨万”,赐额“大兴隆寺”。(83)《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三,正统十三年二月己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157页。正统年间,甚至出现“两京敕建寺多僧少”的现象。(84)《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丁未条,第564页。景泰帝建大隆福寺,“费用数十万,壮丽甲于在京诸寺”。(85)《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七,景泰四年三月癸未条,第4970页。明宪宗建寺、赐额尤甚,“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复增建,以至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86)《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条,第4392页。明孝宗是明代中期为数不多的清明中兴之主,但也修建了10所寺院。(87)参见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251页;何孝荣等:《明朝宗教》,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7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作为官员还是普通士人,无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阿顺现实和皇帝,对佛教加以容忍。丘濬先后担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主管礼仪、宗教、祭祀等事务,如果坚持程朱理学,视佛教为“异端”而一味要求禁绝之,则其职责窒碍难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兼殿阁大学士,负责章奏票拟等,对皇帝喜好亲疏也必然要一定程度地尊重和阿顺。因此,即使他作为“理学名臣”,其坚持以佛教为“异端”的立场和希望禁绝佛教的想法,终须让位于现实,他只能妥协变通,容忍佛教,允许皇帝信奉佛教,与受宠于皇室的“贵戚”僧官周吉祥等交游。当然,作为清醒的宰辅高官,丘濬又明白必须抑制佛教势力膨胀,为此他反对皇帝佞佛,批评皇帝招藏僧入宫做法事,要求控制僧人和寺院数量。为此,他编纂、进呈《大学衍义补》,“无一而非古先圣贤经书史传之前言往事也,参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88)(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七《进〈大学衍义补〉奏》,《丘濬集》第8册,第3956页。其中他反复宣扬反对皇帝佞佛,要求抑制佛教势力,有鲜明的针对性。
第三,丘濬信奉佛教,热爱乡梓,是他赞扬佛教,宣传慧能及广东地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的重要原因。佛教宣扬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以及因果报应等教义观念,而“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89)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具有相当大的精神慰藉作用和欺骗性,因此佛教在历代为各阶层人士所信奉。明代中期,“释教盛行,满于京师,络于道路,横于郡县,遍于乡村”,(90)《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辛卯条,第5371页。“修盖寺观,遍满京师,男女出家,累千百万”。(9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丁酉条,第3583页。丘濬的家乡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佛教于唐宋时期逐渐传入,明代日益普及,为民众普遍信奉。(92)参阅刘正刚:《宋明海南佛寺与佛教世俗化研究》,《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明代中期以前,琼州府修建了佛寺12所。琼山县弥陀堂,正统年间知府程莹“逐尼罢庵”。但民人信佛,“景泰末,乡人私招尼归复”。(93)正德《琼台志》卷二七《寺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第4页b。正德《琼台志》记载,琼山“民性淳朴,俗敦礼义,尚文公《家礼》,冠丧祭礼多用之,始自进士吴锜。及丘深庵著《家礼仪节》,故家士族益多化之,远及邻邑。间有循俗,丧用浮屠亦少,婚则多越礼度”。(94)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1册,第26页a。可见,在丘濬《家礼仪节》劝化前,琼山民众“俗”有“丧用浮屠”者。丘濬生长于斯,不可避免地信仰佛教。成年后,他“博观群籍,每借诸市肆,虽释老伎术,亦所不废”,(95)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一《人物八·本朝三·丘濬》,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三十五辑“史部方志类”第四册,第 1页a。也读过不少佛教书籍。时代局限和家乡环境影响,使丘濬虽然在朝为官、谏诤言事时尊奉程朱理学,以佛教为“异端”,但退朝居家,在日常个人生活中也表现出佛教信仰。他赞扬观音,肯定佛教,甚至吟出“顿悟我曾僧”的诗句。他热爱乡梓,时琼州府属广东,有御史夏某受命将巡按广东,丘濬作诗送之:“而我岭南人,喜幸倍千百。预为乡人喜,从此得苏息。”(96)(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送广东夏廉宪》,《丘濬集》第8册,第3710页。他宣扬慧能及广东地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是热爱乡梓、弘扬乡梓文化的一个表现。
其实,丘濬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以理学为根基,而又信奉佛教,其杂糅、矛盾的佛教观也是当时官员士人佛教观的缩影。明代中期,除了极少数保守的儒臣士人强烈反佛以外,绝大多数官员士人都一方面尊奉程朱理学,以佛教为“异端”,要求抑制佛教势力,另一方面容忍、信奉佛教。如,天顺至成化初年担任首辅的李贤说,他当年“在学,读圣贤书,知佛老为异端,同类有挂其象者即斥其非,以为名公巨儒决不如此”。正统初年,他任吏部验封司主事,造访吏部尚书某人家宅,“见正寝东严整一室,疑必家庙,问之,则曰佛堂也”,李贤“不觉骇叹”。李贤“又以为文章名世者,必不尔”。但造访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石首先生”)府第,见“庭中高悬一幅,视之,乃观音象也”,李贤“不觉失笑”。这些宰辅高官也都信奉佛教,李贤感叹:“呜呼!人其人,火其书,果谁望邪!”(97)(明)李贤:《古穰集》卷三○《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4册第790页。他们不可能禁绝佛教。再如,理学家吴与弼于正统年间拒绝被荐出仕,表示要等到朝廷去除佛教、不再信用宦官才能应荐,“人皆笑其迂”,(98)(明)李贤:《古穰集》卷二九《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4册第785页。可见众人的态度。弘治年间官至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生于朱子之乡,又自称为程子之裔,故于汉儒、宋儒判如冰炭”,(9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篁墩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1页。亦为“理学名臣”,视佛教为“异端”。但程敏政也肯定佛教“使一世之人皆归于为善而已”,(100)(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九《杂著·对佛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3册第356页。主张儒、佛共存,并与诸多佛教人士结交,信奉佛教。(101)参见孙玲:《论程敏政佛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至于明代中期官员士人反对皇帝佞佛、要求抑制佛教势力膨胀的记载,在《明实录》中屡见不鲜,或者说是当时官员士人们普遍的呼声和反应,诸帝佞佛也正是因为被这些官员士人上疏谏诤揭露而得以记录于《明实录》。当然,丘濬作为“理学名臣”、宰辅高官,对佛教“异端”的看法更为突出,批判也更为着力,因此与一般官员士人相比,丘濬出入儒、释二教的佛教观杂糅矛盾色彩更为显明,也更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或者说,研究丘濬的佛教观,无疑对于解析丘濬以及明代中期官员士人普遍尊奉程朱理学,而又多信奉佛教,出入儒、释的思想和生活状态具有标本意义。到了明代后期,王守仁心学风靡,官员士人崇佛更甚,他们的佛教观则呈现另一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