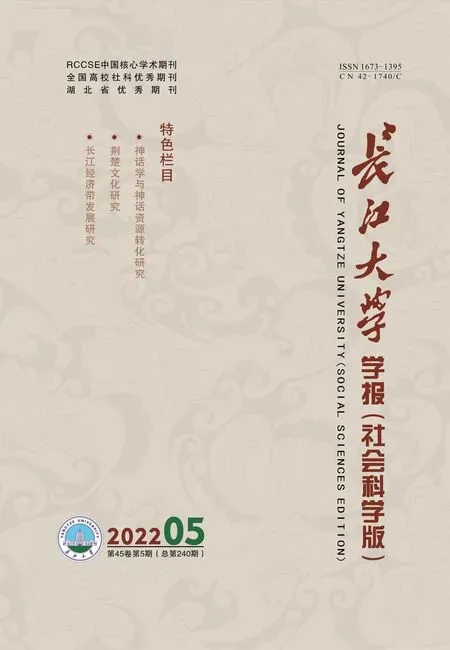当代运动员神化现象研究
——以谷爱凌和苏炳添为中心
熊威 黄欣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问题缘起
由于新冠疫情,原定于2020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暑期进行;半年后,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季奥运会也如期拉开帷幕。夏奥与冬奥之间大大缩短的间隔时间,再加上无时差的便利条件,以及家门口举办盛会的热闹氛围,让大众对奥运会和运动员空前关注。在奥运会举办期间,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几乎都与奥运会相关。在浏览相关新闻和网络言论时,笔者偶然发现,个人,甚至是官方媒体,给予那些处于世界顶级水平的运动员的评价,似乎都已经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将运动员描述为神话般的英雄人物,类似于“神”这类的词汇更是频频出现。比如《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多次将田径运动员苏炳添称为“苏神”;在乒乓球运动员马龙再次夺得男单冠军后,很多网友评论道:“马龙是真的神!”诸如此类的评论还有很多。一位位跨越人类极限、创造历史的运动员是如何在大众的口中逐步由凡人迈向“神坛”的?神化运动员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这是笔者想进一步探寻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凡人成“神”现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往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关注历史人物是如何成“神”的,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1]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来考察关羽是如何从一位武将变为民间的“多面神”的,其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探讨背后的神化方式及原因。二是聚焦于当下的神化现象,现有成果大体关注的是演艺界明星的成“神”现象,例如在明星制造工业环境下,影视作品的神仙人设和粉丝群体的加工共同打造了偶像的神化[2]。对运动领域的体育明星关注度则较低,仅有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以媒介生产和商业需求为基础来探讨体育明星是如何被塑造的。如郭晴《贝克汉姆现象: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偶像崇拜与媒介制造》[3]以贝克汉姆为例,探讨在消费社会里,媒介是如何以“英雄化”“神化”来制造偶像的;刘少华《大众文化时代的体育明星——以姚明为中心》[4]讨论了大众文化时代体育明星的文化内蕴、包装营销等问题。从神话学的角度来分析运动员神化现象的成果则较为缺乏。张晓陆《体育英雄的神话学研究》[5]立足历史的宏观角度来探究塑造体育英雄的几大因素,但未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对于当下正发生的神化运动员现象的讨论略微不足。关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从该现象归纳出将个体塑造为神话人物的模型,这一方式又是延续了古希腊的思维模式[6]。也有学者指出对运动员英雄般的称颂,折射出的是体育运动在团结群体和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7]。
本文将从神话学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下神化运动员的具体现象来梳理运动员迈向“神坛”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及其蕴含的神话意识。由于代表性的运动员较多,本文仅选取苏炳添和谷爱凌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之所以选取二人,首先是因为这两位运动员在热度和关注度上都远高于其他运动员,具备典型性。其次,两位运动员性别为一男一女,所涉及的比赛领域也不同,参加的分别是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但两人却都被称为“神”,这说明两人拥有相同的成“神”特质。笔者选取这两位运动员作为案例,希望能尽可能扩大论述面,归纳出运动员神化的共同因素。
二、神化历程
对凡人的神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背后涉及多方的共同参与。如有学者指出好莱坞电影明星通过角色扮演而放大自己以至于成为超人,这是由制片人、导演和崇拜他们的公众一同打造出来的。[8]滨岛敦俊在总结江南地区土神成神的要素时也指出,主要要素有:义行、灵迹(或显灵)和封爵。[9](P83)综合古今不同凡人化“神”的现象,神化需要来自个人、大众、官方三者的共同推动:首先,成“神”的个人需要有某些特殊行为或具备独特之处;其次,大众对其神化持肯定态度,他们相信,甚至会采取措施来强化这种神化;最后,还需要官方的认可。以谷爱凌和苏炳添为代表的优秀运动员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卓越的竞技成绩,受到大众的推崇,奠定了他们成“神”的基础;怀揣敬仰与崇拜,大众又以多种方式强化他们的神化;来自官方的话语或仪式进一步确认了他们的神圣身份。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运动员最终获得合理性的“神”之身份。
(一)个人特质
“神”字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里均有两大基本含义,既可以指“神灵”,也可以指“特别高超、不平凡、神奇”。从“神”的基本意思来看,成“神”的首要因素就在于个体与众不同、异于常人的突出特质,这也是神化的前提条件。优秀且足以代表国家站在世界竞技舞台上的运动员数量众多,但并不会都被大众称为“神”。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述民众将各类人物神化为英雄并加以崇拜时就提到:“崇拜就是超乎寻常的惊奇,对事物的无限惊奇,就是崇拜。”[10](P10)可见,这些能成“神”的运动员身上必然有着与其他运动员相比更为超乎寻常之处。
作为运动员,他们身上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他们在专业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在体育圈有一个常见的缩略词“Goat”,即“Great of All Time”的缩写,意思是这位运动员是“历史最佳”,即某项目领域的世界顶尖水平,目前暂无能超越他的选手。这部分选手在大众眼中,尤其是对粉丝而言,常常就是被神化的对象。
谷爱凌可以说是近两年才被国人所熟知,但在很早之前,她就在专业领域里大放异彩。在青少年时期,谷爱凌便横扫全美各种赛事冠军,被称为初露光芒的“天才少女”。自2019年起,谷爱凌正式代表中国参赛,为中国取得了19金5银4铜;她还创造了多个纪录:唯一单届奥运会获得三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唯一的女子U槽超级大满贯,两度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11];同时,为实现北京冬奥中国队全面参赛的目标,谷爱凌临危受命,参与了大跳台项目,仅练习一年,就成为奥运赛场上自由式滑雪唯一身兼三项的女性运动员,且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谷爱凌以传奇成绩证明:目前在自由式滑雪领域内,她是当之无愧的顶尖选手,她的成绩和突破是其他选手难以望其项背的。这种一骑绝尘的成就让谷爱凌在大众眼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具备“超人”能力的运动员,进而成为大家口中的“神”。
相较于谷爱凌,苏炳添的战绩似乎远未达到“Goat”的标准,但这为什么丝毫不阻碍大众推崇他为“苏神”呢?从上述谷爱凌的成就来看,她的意义可归结为一种“绝对的统治力”,她在该领域内是“战无不胜”的;但苏炳添的意义却并非在此,他的出现象征“零的突破”。在田径赛场上,黑人运动员具备先天的种族优势,他们在田径项目上的统治历史十分悠久;相反,该项目却少见黄种人的身影。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110米跨栏夺冠令国人振奋不已,正是因为他创造了中国人或是说黄种人在田径赛事上的历史;但此后,新的开始没有被延续下去,这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遗憾。可以说,苏炳添的出现正是打破了平静,再度续写“零的突破”。
苏炳添运动生涯中的多次成绩都是中国田径的新纪录:2012年8月,在伦敦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成功晋级半决赛,成为中国短跑史上第一位晋级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选手;2014年3月,在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飞人大赛中,苏炳添成为第一位晋级世界大赛短跑决赛圈的中国选手;2015年5月,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比赛男子100米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成为在正常风速下真正意义上第一位闯入10秒关口的亚洲选手;2021年8月,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再次刷新了他所创下的亚洲纪录;随后,苏炳添带领中国男子短跑接力队在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以37秒79的成绩收获递补铜牌,这是历届奥运会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最佳成绩。[12]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当晚,苏炳添是起跑线上唯一的黄种人选手,尽管最后未收获奖牌,但舆论大都给予了肯定的态度,认为苏炳添能进入决赛就已经是一种胜利。可以说,苏炳添之所以能够被大众推崇化“神”,无关他的成绩是否为领域内的世界顶尖水平,而在于他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超越与突破。在此处,我们以另一项目跳水进行对比。众所周知,中国在跳水项目上具备长期的领先优势,且持续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跳水运动员。但对于跳水运动员,甚至是蝉联金牌的运动员,大众似乎很少以“神”来称呼他们,比如大众将郭晶晶称为“跳水皇后”;又比如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多次满分的全红婵,也很少人将她称作“神”。在长期占据优势的项目里,金牌、蝉联,或者是满分,都难以赢得大众的惊讶与惊叹,因为在一开始,大众就是以一种“理应如此”的心态来看待比赛成果和参赛运动员的。与此相反,对于还未留下国人足迹的运动项目,任一具备突破性的成绩都能让大众为之惊叹。因此,苏炳添的成绩虽未达到统治般的领先,但他与谷爱凌相似,都为中国取得了零的突破,他所书写的传奇足以让他成“神”。
(二)身份赋予
在运动员个人超乎寻常成绩的基础上,大众开始有意将他们与普通人相区分,以进一步凸显他们的神圣性地位。米尔恰·伊利亚德认为,宗教徒常以再创造和圣化的方式将神圣时间、空间与世俗时间、空间区分开来,这样的神圣时间、空间就具备了非均质的特殊属性。[13](P1~2,P32~33)与此思维相类似,大众对部分优异的运动员进行出身的神化或独特身份的赋予,以合理化他们的神圣身份。
中国古代神话中存在系列感生神话,感生神话最初是原始思维下的特定产物,但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这类神话被统治者借用为宣扬天命的工具,以凸显自身身份的与众不同,实现愚民的政治目的[14](P94~95),比如《史记》里提到刘备的出生是源于刘媪“梦与神遇”[15](P67)。如果说,统治者的感生神话是自身为了维护统治权威的主动神化,那么另一种则是出于民众的推崇心理而实现的被动神化。比如包公以清官形象赢得了民众的尊敬,民众遂将其推崇为“神”进行崇拜。在民间流传的包公传说中,对包公的出身就进行了多处神化,以回应他的“神”身份,这部分神化不仅表现在包公的长相异于常人,还体现在太白星在为包公算命时预言了包公的出色仕途,等等。[16]
运动员在领域内的优异成绩构成了他们神化的前提,怀着崇拜的情感,大众在此基础上将各种身份附加于他们身上。虽然当下的“附加”远未达到古代社会神化的那种奇幻色彩,但是身份的加工也加强了他们身份的尊贵性、神秘性,有意谱写“神系”,合理化他们的“神”之身份。
尽管谷爱凌的出身对大众而言几乎是透明化,但同时又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随着谷爱凌在冬奥期间知名度的迅速提升,关于她的出身、家庭教育等讨论也在网络上热烈展开。有关其母亲谷燕传奇经历的旧时报道[17]还被网友找出,引发全网热议。其父亲的身份从未对外公布过,这丝毫没有阻碍外界的各种猜测。在众多猜测中,提及度最高的就是:谷爱凌的父亲是谷歌5号员工、房地产开发商雷·西德尼(Ray Sidney),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18]尽管这个信息之后又被传是谣言,但是关于谷爱凌父亲的猜测却从未停息,并且这些“父亲”的身份都不同寻常。能力过于常人的家人本就让谷爱凌的天赋与优秀显得与生俱来,大众给予的评价几乎也契合了中国的一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谷爱凌的出身就与普通人相隔开来,是常人难以触及的高度。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又极力渲染谷爱凌的家庭是如何倾注高价来培养这一天才的,多篇报道都不厌其烦地强调:母亲谷燕培养谷爱凌至少花费了上百万美元,谷爱凌因此才能成为冲浪、芭蕾、钢琴、高尔夫、射箭、越野跑、攀岩等十几项全能的天才。在这些报道里,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几乎化为了一个词——金钱,即只有出生于拥有优质基因又优越富裕的家庭里,才能成为超人的运动天才。
与谷爱凌相反,苏炳添的出身并非如此惹人注目。苏炳添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古一村,初中时期开始与短跑结缘,在多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后被田径教师赏识,正式接受系统的专业化训练。苏炳添的出身与成为专业运动员的契机都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平常,没有像谷爱凌那样完美的预设前提。但在2022年8月,一条微博热搜却赋予了苏炳添新的身份——这条微博热搜的名字叫“苏炳添是苏轼后代”。在词条热度持续升高后,有新闻记者去采访了苏炳添祖籍的苏氏祖祠理事会会长,会长声称:根据族谱,苏炳添是苏东坡第29代孙。[19]接着,又有人晒出了苏炳添曾在苏东坡宗祠庙堂前上香的照片,还有人将苏炳添的照片与苏轼的画像进行对比来论证真实性。之后,村委会和相关学者又回应对此不知情或这个论断目前无法证明。[20]苏炳添是否为苏轼后代,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在此对这一新闻的可信度也不予评价。但是,这一突如其来的身份赋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有关谷爱凌的身世讨论。苏轼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符号;苏炳添作为田径赛场上的优秀运动员,向世界证明了中国速度,是足以代表中国的“百米飞人”。一古一今,一文一武,两大“苏神”依凭血缘的联系而汇聚,苏炳添也由平凡的出身升级为文学名家的后代,他的傲人成绩似乎也更为理所应当,是延续了宗族的优秀基因与荣光,与谷爱凌的身世讨论达到了相同的效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人们会为了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21](P6),大众将苏轼、苏炳添两大符号相联系,既延续了苏轼的当代影响力,又为苏炳添附加了尊贵的身世背景,以便让“苏神”这一形象更为合理化。
(三)广告宣传
在运动员的造“神”运动中,广告可谓是不能忽视的一大因素。
运动员作为在世界竞技场上为国争光的形象,他们自身具备着较高的商业价值,因此也颇受广告商的青睐,尤其是领域内代表性的运动员。笔者在查阅谷爱凌和苏炳添两位运动员的广告资料时,发现这些广告都具有相似的特征——有意突出两位运动员的天才形象和超人特质,加上画面、广告词和背景音乐的配合,以塑造他们“神”的形象。

表1 谷爱凌的部分广告

表2 苏炳添的部分广告
罗兰·巴特将神话定义为一种语言、传播的体系,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22](P167)广告就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种典型神话,以叙述的方式构造新的神话。通过以上表格的展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广告首先根据运动员的特性,在画面中反复呈现运动员才能做出的高难度动作,且画面中褪去其他元素,只留下最为纯粹的运动场地和运动员本人,他们矫健的身姿最大化地展演在大众面前,这样的场景让人极易联想到他们在赛场上的突出成就,这让观众清楚看到运动员的卓越之处,认识到自己和他们(运动员)之间的差距。
除了画面,以文字或声音呈现的广告词也进一步强调了运动员超人的能力。谷爱凌的广告中多次提到她的不同身份——集运动员、模特、跑者、演奏者等于一身,又无数次提及她在较小年龄段就取得了傲人成就,将“完美”“伟大”“学霸”等标签反复加之于她身上,而这些都是常人无法匹敌的,她也因此有了令人瞩目的“神”之光环。苏炳添的广告则是多次提到“快”“历史(突破)”“第一个”等字眼,字幕还会对这些内容进行放大处理,有意强调他的传奇性突破和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还以比赛时观众落泪、欢呼的反应再次衬托他的不凡成绩。多角度的刻画共同叙述了两者的神话。
这一系列广告在背景音乐上也有相似之处。广告在一开始往往无背景音乐或是背景音乐较为低沉,此时画面呈现的常常是两人在做着比赛前的准备活动,可以明显感知赛前紧张的氛围。随着广告的推进,当两人开始投入比赛,在画面中呈现高技巧的动作姿态时,背景音乐开始由低沉转为高昂,振奋的旋律伴随着运动员的矫健身姿,呈现理想化、富有感染力的景象,带来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画面、广告词和音乐的相互嵌合,几乎隐去了运动员背后日复一日的努力训练,所呈现的只有他们完美、无懈可击的一面,无形中强化了对运动员的神化。
(四)官方认可
如果说运动员个人和大众为神化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具体途径,那么官方的认可则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上述的几个因素,均是从个人、民间的角度来讨论运动员如何成“神”,然而这一过程最终还需要官方的参与和认可。
在奥运会期间,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对谷爱凌、苏炳添多次进行了宣传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有一张谷爱凌的新闻图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当时也被很多人称赞为“神图”:图片中的谷爱凌戴着比赛专用的护目镜,未露出面容;身着比赛服,衣服的背面印着一条腾飞的金龙;身后所挂着的名牌被风吹起;身旁溢满了被扬起的飞雪。这张图展示的是赛程中的谷爱凌,不管是她身上的比赛装备还是身旁的飞雪,都传达了比赛过程的紧张感;同时这张新闻图的一大亮点便是身后的那条金龙。龙形象可谓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龙文化经历了图腾崇拜、神灵崇拜、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等几个阶段[23],尽管当今华夏儿女都可以自称“龙的传人”,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封建帝王被称作“真龙天子”,“龙”暗含一种权威和专指,将至高无上的帝王与普通民众划分开来。之后,龙逐渐成为西方认知中国的象征性符号,即中国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服饰作为附于身体之上的装饰物,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文化的表达。特伦斯·特纳提出“社会皮肤”(social skin)概念,他认为, “身体的修饰是一种中介……身体的外观代表了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边界,服饰和其他形式的身体装饰成为表达文化认同的话语。”[24]官方媒体所发布的谷爱凌身着亮眼的金龙战服,既有意突出了中国文化元素,将谷爱凌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展示国家形象;同时,龙形象又赋予了谷爱凌独特的身份彰显,在空中飞跃旋转的她正如腾飞的金龙,具备异于常人的“神”之特质。在后来的系列报道里,官方媒体还在谷爱凌的身旁配上了颇具豪情壮志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官方媒体的报道,再加上极高的点赞、评论和转发量,都让谷爱凌的这一身份和形象被广泛传播开来,无意间也强化了谷爱凌的“神”身份,让大众肯定或者接受了这样的标签。
除了官方媒体的宣传认可,国家层面还举行了系列的表彰仪式来再次肯定两人所取得的成绩。2021年9月,前往西安出席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大会堂会见了体育界的代表。在会面中,习近平总书记特意走向苏炳添,勉励他:“你虽然没有拿牌,但是含金量绝不次于一块金牌,你打破了亚洲人百米极限。”[25]之后,这个场景的图片和视频便被广泛传播,这都在无形中再次强调,尽管没有取得奖牌,但苏炳添已经为国人创造了田径赛场上的神话。同一时段,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授予获得奥运金牌的杨倩等45名运动员,以及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苏炳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让苏炳添与金牌获得者共获奖章,打破了传统惯例,让取得历史性突破的运动员与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享受同等待遇,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和重要的示范价值。[26]这一官方颁布的具有权威性的奖章,可以说重申强调了苏炳添所书写的传奇。2022年4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场设置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中央是庄严的国徽,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会场气氛庄重热烈。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的优异表现;在欢快的乐曲中,亲手为突出贡献集体和个人颁奖并合影留念。谷爱凌就位列于表彰名单之上[27],她在会场上还获得了极大关注,这也标志着她在官方仪式层面再次获得认可。国家举办的系列仪式以盛大的氛围和重复的展演重述两人的传奇英雄成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符号或价值通过仪式活动的‘程序公正’被提升到一种认知的高度”[28](P79),两人的神化在官方话语的肯定和推广下,最终被广泛认知并接受。
三、神化之因
乌丙安提到圣人崇拜的形成依据在于这些人“表现了人德、人智、人勇,其文治武功利于民,为世人景仰、敬慕”[29](P222)。在和平年代,运动赛事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一)大众的尊崇情感
以谷爱凌、苏炳添为代表的优秀运动员得以成“神”的最重要动力源于大众的尊敬与崇拜之情。从开幕式、比赛期间再到闭幕式,分配给各国家队的志愿者们都会高举国家旗帜,运动员们会身着印着国旗的统一队服,领奖台上冉冉升起的国旗配上响起的国歌……这一切都在表明:赛场上的运动员们早已隐去了他们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而化为国家、民族的代表,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自尊与荣誉。
有学者指出,体育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强化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体育可以展示国家的优越地位,运动赛事的精彩表现往往能提高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声望;其次,体育也是寻求认同与合法性的手段,同意国家间的竞赛意味着相互承认,拒绝体育竞赛则表示否认他国的独立主权;最后,体育能有效激发民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团结感,尤其是一些具有可观赏性的团体比赛。[30]可以说,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实际上是一种仪式的对抗,赛场上的竞技就是国家间的力量角逐。作为体育运动赛事的主角,运动员往往会成为其中的焦点,运动员在赛场上呈现的竞技能力和心理素质,不仅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性因素,也彰显了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力量。
在体育赛事和集体认同感紧密相联的背景下,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推崇与优待。在古希腊奥运会中,代表城邦或部落的优胜者会获得众多荣誉与奖赏。在奖牌未出现的时代,优胜者会获得橄榄枝桂冠,而橄榄树在古希腊神话里是来自智慧与和平女神雅典娜的礼物,也是生长在宙斯神庙旁边的“圣树”。所以,橄榄枝桂冠代表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除了官方授予的荣誉,待优胜者返回家乡时,民众会怀着自豪之心为其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做诗歌以赞美或演唱;他们还会获得一系列的奖赏:终身由国家供养、免除纳税、在剧院获得最好的位置,等等。[31](P15)
同样的心态也延续到了现代奥运会中。以谷爱凌、苏炳添为代表的优秀运动员在世界舞台上奋勇竞技,他们首先以自身的高素质展现了民族的精神与风采。当苏炳添站在百米决赛起跑线的那一刻,无论最终成绩如何,他都已经创造了历史——打破了田径赛场上的种族血统论,书写了中国人或是黄种人的新历史,有力证明了民族的潜在实力,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其次,他们取得的奖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多次发布的谷爱凌身披国旗领奖的微博,点赞量都过万,评论中也频繁出现“为你自豪”“骄傲”等言论。他们的这些独特属性,会让大众心生崇拜,自然愿意将其称为“神”。
(二)广告的宣传需求
如上文第二部分所述,以两位运动员为主角的广告,也存在着造“神”的行为,将运动员与普通人分隔,有意显现他们不同常人的能力与成绩。这样的神化在无形中也造成了一种割裂感:一方面,作为优秀的运动员,他们是伟大的;另一方面,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平凡的,似乎命中注定般无法达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割裂感看似矛盾,实际上正是广告的必要之处。何为广告?广告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引导消费,产品销售量是否提升正是判断一支广告好坏的标准。
运动员,尤其是优秀的运动员,具备无可替代的商业价值。一方面,这些运动员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粉丝群或群众基础,他们可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将运动员所面对的观众转换为产品潜在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广告商可以将他们身上本就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能力,进一步放大和神化,达到成“神”的效果。这样的效果在一开始会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矛盾和割裂感,但在这之后,往往会激发受众的羡慕与渴望——“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样优秀、具备超能力的人”。这样的感情就会将观众引向产品本身,最终实现“变现”或“转换”,满足广告商的宣传需求。
这样的割裂感在牛奶品牌伊利的广告中最为明显。今年5月,伊利力邀苏炳添和单板滑雪运动员苏翊鸣共同拍摄了一条广告。在广告的开篇,两人就共同说出了“别人都叫我们苏神,其实我们一点也不神”这句广告词;接着,画面又展示了两人训练的场景,配上“你会摔倒,摔倒了就笑着爬起来”“困难越冷酷,热爱越发烫”“永远地重复着”此类表达坚持与热爱的励志性广告词,似乎都在极力证明——苏炳添和苏翊鸣并不是完美的“神”,他们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与失败,唯有热爱和坚持,他们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但这就是一则完全“祛魅”的广告吗?并不是。尽管广告的初衷似乎是为苏炳添、苏翊鸣卸下“苏神”的标签,但值得注意的是,伊利品牌的官方微博在发布此则广告时,所带的话题就是“大小苏神的青春宣言”,也就是说,品牌在一开始还是以“苏神”的身份标签来吸引大众点开视频进行观看,在广告开始前,观众在心中已有了预设——他们是肯定“苏神”这一身份的。广告又不断呈现苏炳添冲刺时风驰电掣的画面、苏翊鸣脚踏滑板腾空飞速旋转的场景,与此同时,字幕还醒目标注了两人创造历史的成绩:“9.83秒”“1980度”,画外音则配上了奥运会时情绪激昂的实时解说:“苏炳添创造了历史!”“苏翊鸣一鸣惊人!”即便广告旨在否认“苏神”标签,但无论是前期宣传还是具体内容,又在反复渲染他们超越极限的超常实力,是再次肯定“苏神”的一种表达。
这样的矛盾或者割裂实际上就源自广告的需求,广告首先需要借助这些运动员身上的超常特质,为品牌吸引关注和流量,又借用这一特质将自身品牌的特性也进行神化,打造品牌的神话[32];同时,又不能将产品完全置于高高在上的神圣位置,反而要传达一种普通人也能触及的可能性。只有这样,广告才能充分发挥出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成功实现“变现”。
(三)国家形象的彰显要求
在上个世纪,由于鸦片的侵害和列强的侵略,中国积贫积弱,还被冠上“东亚病夫”这一蔑视性的称呼。李小龙在电影《精武门》里不仅踢碎了“东亚病夫”的牌匾,更是表达了国人渴望重证自身的强烈意志。从1949年至今,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风雨。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巨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有了巨大提升,更不用说国人体质的增强和体育事业的腾飞。
为洗刷“东亚病夫”的屈辱过去,向世界展现崭新的国家形象,中国的脚步始终未曾停歇。自1991年起,中国就开始申办奥运会,第一次申办惜败后又在1999年再次申办,最终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成功的消息一经传开,就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狂欢,这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2015年,北京又成功申办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经过了14年的时间,中国再次迎来奥运盛会,而北京也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座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中国申奥虽历经波折,但也成为了国家力量和形象的有力彰显。
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举行正值疫情后的两年,曾有人质疑:在疫情时代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赛事,是否是劳民伤财之举?这样的担心显然在奥运会之后得到了否定答案。与其说奥运会是为运动员提供了竞技赛场的舞台,不如说是为国家形象提供了展演平台。《记忆之场》一书提到,环法自行车赛事有意打造英雄化的事业,赛事“真切地创造或假定有一个神话空间,呈现作为榜样的人物”,颂扬那些冠军为“英雄”,甚至为之树立纪念碑,而环法自行车赛本身又展示着法兰西的记忆、功绩和当下。[33](P248~251)2008年奥运会至今已过去了14年,中国再次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节点,中国已经从追赶者变为迅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参与者和领跑者,迅速崛起的中国需要书写新的神话以重塑国家形象,再次主办作为世界级运动盛事的奥运会便提供了良好的重新书写的机会。除了在赛程期间以各项优质的服务对外进行展示,赛场上的国家运动员也是民族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优异的表现是中国体育全面发展的缩影和国家崛起神话的生动呈现。尤其是相比于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在中国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一直较低,中国队在往年冬季奥运会上的成绩也不够亮眼。官方宣传的“三亿人上冰雪”口号在动员大众以外,也要在比赛结果中有所呈现。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官方就曾归化部分优秀运动员,谷爱凌的华裔身份优势,再加上官方的主动倾向,让谷爱凌最终顺利代表中国参赛。她在滑雪项目上的优异表现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在该项目上的空白,既实现了中国全面参赛的目标,也助力了书写国家崛起的新神话的需求,因此,她也同样被神化,以满足国家民族身份彰显的需要。
奥运会在原初就体现着对健美人体的崇拜。黑格尔认为希腊的艺术源自人们对身体的修饰。[34](P287)在古希腊的奥运会中,所有人均是裸体参加竞技,在比赛中展现着他们原始、自然、健康的身躯;同时,古希腊众多神的雕塑都拥有完美的身躯,这也是他们将人体加以理想化的结果。新冠疫情给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疫情直接危害着大众的安全健康。自疫情爆发后,官方除了极力提倡必要的防护措施及宣传接种疫苗的必要性之外,最为主要的手段便是鼓励大众积极运动健身,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以抵抗病毒的侵害或是将侵害降至最低。那么,在赛场上展示健美身躯和出色运动能力的运动员便成为了宣传全民运动的不二选择。在媒体平台的图片和视频中,所呈现的几乎都是在比赛过程中的精彩瞬间、他们身上的健硕肌肉和脸上的自信表情,这无疑是古希腊奥运会推崇健美人体初衷的延续。自然身体又是一种象征,道格拉斯就将身体视作整体社会的隐喻,并将其细分为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35](P16)。运动员的健硕躯体最初是物理身体的呈现,这样的躯体又展示着病毒难以入侵的“铁人”姿态,传递出运动的有益效果,是当前社会推崇强壮体魄的象征符号,他们的物理身体也因此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将他们推崇为“神”,在另一层表述里也肯定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效果,是对运动健身的积极宣传,既迎合了疫情当下推广全民健身的趋势,也展现了国家良好的防疫成果和国民健康的身体素质。
四、结论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各项国际性的运动赛事已成为国家形象的展演平台和国家力量的对抗赛场。作为运动赛事的主角,尤其是那些站在项目领域前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也获得了神圣性地位,逐渐成为神话般的英雄人物。
运动员成“神”历程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的出色体育竞技力,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成绩,体现了他们超常的个人素质,也成为了他们成“神”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大众对他们的身世进行了神圣化或优越化处理,关于谷爱凌父亲的身份猜测、苏炳添是否是苏轼后代的争论,都在有意将两人与普通人“相隔”开来,赋予及合理化他们的“神”之身份。同时,在消费型社会,运动明星具有无可替代的商业价值,广告商借用广告的叙述,反复呈现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超常表现,夸大他们的“神”之光环,再次为这些运动员构造神话。最后,来自官方的媒体报道和表彰仪式从最高层面对这一身份进行了肯定,巩固了运动员的神化。
运动员作为民族和国家的代表,在世界舞台上为国家赢得荣誉,赢得大众的尊敬与推崇,出于此种心态,大众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进行神化,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广告形塑运动员成“神”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希望凭借运动员的神化来推广品牌特质,获取可观的利益。从国家层面来看,运动员是国家身份的一种彰显形式,运动员的赛场表现可以抽象为国家形象的展演,满足书写国家崛起新神话的需求。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拥有健康体质的运动员更是极大地满足了官方推广全民运动健身的目标,因此官方也会对这一身份加以肯定。
神话般英雄之名的授予,既是对运动员卓越表现的肯定,也满足了多方不同的需求。神化运动员是当下社会神话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探寻运动员成“神”的历程和背后动因,或许能为我们理解神话意识的当代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苏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