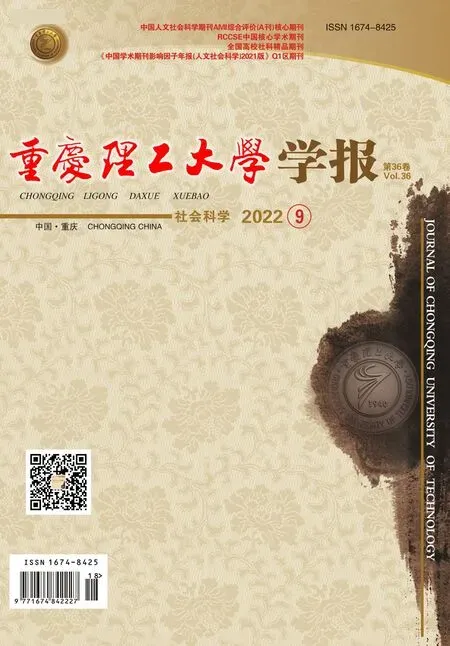消费强制逻辑及其生态后果
万冬冬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科社教研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生产强制逻辑运作的过程,也是消费强制逻辑展开的过程。相比生产强制逻辑而言,消费强制逻辑是一种更为隐性的逻辑。对于这种隐性的逻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1]33消费强制逻辑支配下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这种需要驱使人们大量消费,从而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虚假需要驱动的异化消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需要。正如当代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休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对‘真’‘假’需要即人们确实需要的事物与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所需要的事物进行了区分,并对导致虚假需要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2]169马克思用“臆想”“幻想”“奇想”“怪想”等词语来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虚假需要。
资本主义为实现资本的持续增殖而营造出人的虚假需要。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3]69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需要,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于人的“自然的需要”。这种“自然的需要”逐渐被“历史形成的需要”所代替。“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需要形式。“自然的需要”是维持人类本身再生产的需要。比如,人需要吃饭、穿衣、休息等。“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一种超出人的正常需要的欲望。
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消费是异化了的消费。“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4]445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虚假需要,这些虚假需要改变了同自然相联系的社会物质变换。
资本积累为人的虚假需要欲望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人的虚假需要欲望的增长满足了资本不断积累的需要。“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5]716-717,人的需要服从于资本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消费需要被异化、被当作资本家谋取私利的手段。虚假需要是人的不合理欲望的体现,是人们所追求的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因而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6]729这样,人就在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成为虚假需要的奴隶。
马尔库塞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指出:“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7]6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虚假需要并非是人的真实需要,而是由社会这一外界力量所控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说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它通过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驱使人们狂热地追逐虚假的物质需要,压制人们的真实需要。“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7]9资产阶级不断制造、强加给人们各种虚假的需要,进而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对人们进行控制。
弗洛姆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消费现象。弗洛姆认为,人有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消费社会的生存方式,因为它以对一切存在物的占有和消费为目的。这种生存方式下,“人退到了接受性的、交易性的方向上,不再具有建设性;人丧失了他的自我感,变得依赖他人的认可,因而倾向于求同一致,却又感到不安全;人感到不满足、厌倦、焦虑,并且用他的大部分精力尝试补偿或掩盖这种焦虑感”[8]229。
虚假需要的突出表现是对奢侈品的盲目追逐。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奢侈品,那么以工人阶级和劳动资料占有者对立为基础的任何生产方式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奢侈品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生产方式为非生产者生产财富,因而一定会使奢侈品具有必要的形式,以便使它只能为享受财富的人所占有。”[3]528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原来表现为奢侈品的商品现在变成了必需品。
桑巴特将奢侈定义为“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9]86。在他看来,对奢侈品的追求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奢侈型社会。新社会、城市和爱情的世俗化是推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力量。宫廷是一切社会活力的源泉。爱情的世俗化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妇女阶层,她们在宫廷中过着奢侈消费和高级享乐的生活。资产阶级模仿宫廷的生活方式,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追求奢侈的风气。正因如此,桑巴特说奢侈“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9]233。
资本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把过去是奢侈的东西变成必需品,“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1]525,资本家的消费和挥霍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加。“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5]685无止境的奢侈消费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生活意义匮乏的表征,也是对这种匮乏的安慰与补偿。但奢侈消费满足的不是人们正常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要欲望。
需要本来是体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但在资本的魔力下,它却成了追求物质财富和虚假的消费。“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6]225消费领域的虚无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并伴随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全球化。“在消费越来越被虚无所主宰的程度上,人们的生活也相应地被虚无商品所包围,而且向一个越来越高的程度发展。”[10]2信用卡、古奇皮包、超级市场、形形色色的连锁商店、购物中心以及飞机场就是消费虚无化的表现。不仅日常购物越来越多地为虚无商品所支配,而且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消费也为虚无的商品所支配。
虚假需要也表现在对金钱的贪欲上,马克思称之为“货币主义的幻觉”。在马克思看来,对金钱和财富的贪欲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唯一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亵渎了,货币成了人的最高追求,人沦落为一种没有归宿的工具性存在。“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6]5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以金钱为中介的交易关系,人们把愿望和价值的实现寄托于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的金钱之上。
马克思认为,金钱既剥夺了人的世界所固有的价值,也剥夺了自然界本身的内在价值。“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6]247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在成为商品的一般价值后使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买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失去了价值。
二、日常消费的过度化和奢侈化
马克思把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只有完成了这一“惊险跳跃”,商品才能销售出去并转换成货币,资本的自我增殖也才能实现。而要把生产出的商品销售出去,就必须扩大需求和刺激消费。
资本代表追求价值增殖的欲望,它驱使人们产生消费欲望和奢侈欲望。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是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要求消费的不断扩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主要通过3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89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对工人的统治不只是发生在生产领域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已经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所有的工人都禁锢在资本的需要范围之内,成为资本运转的润滑剂”[11]255。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是在劳动过程以内还是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的一个要素。而“随着资本疯狂地侵入日常生活世界,生活性消费逐渐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重心”[12]。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为实现这一目的,资本家通过一切办法强迫工人有新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需要和欲望不是人的真正需要。“欲求某物就是处在一种意向性的心理状态,它促使人们试图得到该物;而需要某物就是为了它处于这样的客观状态:为了获得某种目的或物品,该物是必需的。”[2]164欲望实质上是异化了的虚假需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209。异化了的虚假需要不过是一种幻觉,它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不仅有对财富的无限的欲望,他还有享受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5]685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把奢侈当作是致富的一种手段。“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5]685资本家在积累欲和享受欲的驱使下过度消费和挥霍。资本家对人的蔑视,不仅表现为对维持人生存的东西的糟蹋,而且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这种幻觉就是,“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6]233。于是,资本家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看作自己无度的要求和突发的奇想的实现。
资本家挥霍的背后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因为“奢侈不但是资本家满足享受欲的需要,而且是资本家取得信用、进行投机、以便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手段”[13]467。和货币贮藏者靠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来积累财富不同,资本家用于挥霍的财富的增长是通过榨取别人的剩余劳动来实现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通过购买和消费商品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新消费工具促推了人们的这种展示行为。在瑞泽尔看来,为了吸引消费者,消费圣殿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神奇的、梦幻的和迷人的东西供消费者消费。迪士尼世界代表了一种新消费工具,它是一种使得我们能够消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新形式。迪士尼世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通过一个被称为“迪士尼化”的进程,为其他的新消费工具提供了模板。
有些消费工具能够比其他消费工具显得更具有魅惑力。比如,迪士尼世界、拉斯维加斯赌场或者一艘巨型邮轮看起来要比当地的麦当劳、沃尔玛或者商业街更有魅惑力。“通过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规模的铺张华丽的表演和模拟(以及甚至模拟的模拟),新消费工具已经变得越来越引人入胜。这些奇观被用于为消费工具重新赋魅,这样它们将会持续吸引越来越疲倦不堪的消费者。这些铺张华丽的表演和模拟一般是由那些控制着消费工具并怀有使这些曾经具有魅惑力的场所重新赋魅的意图的人创造的。”[14]170消费工具的激增,既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又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信用卡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展示行为。通过延长支付期限等手段,信用卡怂恿人们不断地进行消费。“以前,人们必须存钱买东西,但有了信用卡以后,可以沉溺于满足的即时兑现。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新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新手段的诞生,改变了经济体系。”[15]21作为一种便利工具,信用卡使人们从消费圣殿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成为可能。无论新消费工具是如何的“引人入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人们不是为真实需要而消费,而是在消费中寻求慰藉和满足。
莱斯认为,被诱导的消费往往不是出自人们的意愿,而是被操纵的。为了达到控制人的目的,资本家不惜使人的一切方面都依附于官僚体系,让人通过消费来消除痛苦。但是,“高消费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心理危害不比生理危害小”[16]17。他以包办旅游和露营为例说明了这一点。本来是充满个性的旅游,现在却被人为地包装。被安排的露营也有类似的特点。“这种包办旅游和露营活动暴露出人们需要和目标的深层困惑。人们只能体验到那些经过多层商品组成的筛子过滤后的东西,这些商品包括旅行用的物质装备、大批量生产的纪念品、预先计划好的菜单、告诉人们应该看些什么东西的种种解释性说明。”[16]22在经过商品过滤之后,那些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被简化了。
凡勃伦把奢侈品消费称为“炫耀性消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为了消费者自身的享乐所做的消费。”[17]59它是有闲阶级博取声誉的手段和标榜身份的象征。“炫耀性消费”体现的是财力的攀比。在现代社会中,财产取代掠夺式功勋所得来的战利品,成为优越性和成功的约定俗成表征。若想跻身社会名流,拥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已成必要。若想维持好名声,获取财产已成必然。
在凡勃伦看来,服装是财力水平的一种展示,服装的展示格外能体现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和挥霍。“要展现出某人在财力上的排行,借用别的方法也能有效达到目的,而且这些别的方法也一直无时无地不在流行着,但花在服装上的支出却比大多数别的方法更具以下的优势:我们穿的服饰是随时让人观赏的,并且足以让所有旁观者在看了第一眼后就了解我们的财力排行。”[17]125炫耀性挥霍的法则导引着衣服的消费。像导引其他事物的消费一样,它主要是通过先形塑品味和礼仪的规范再产生作用。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异化视野出发,通过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已经蔓延至消费领域,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作为消费的运行平台受到官僚主义的控制。他将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这种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消费组织着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在国家官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侵蚀下被切割开来,各式各样的国家组织以及大量的、流行的、隐性的次体系无孔不入地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领域,使之成为组织化的对象和客体”[18]120。通过对人的欲望和需求的控制,“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将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被组织和盘算的对象。
三、消费强制逻辑的生态后果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19]12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占有;他生产的物品是他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的物化”[20]33。为了满足人们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资本主义通过大量地掠夺自然资源来进行大量的生产,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靠不断扩大生产和消费来维持的。这样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不仅导致人们从自然界掠夺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导致人们向自然界排放大量的废弃物。“‘消费异化’使人把消费当作目的本身,追求一种对自然的无度的索取和占有,自然资源大量地被浪费,污染物大量地被排放,最终超越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导致了环境危机。这样,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背离了,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正是异化的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21]54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使得自然资源迅速被耗竭,大量的废弃物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消费强制逻辑的驱使下,商品大量地被生产出来,人们大量地消费商品,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消耗,而产生的废料则被扔向大自然。然而,大自然的净化能力是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自然界就会出现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制造出大量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人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6]410。这不仅污染了土壤和水资源,而且也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不仅如此,它还导致鱼的存在本质的异化。“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6]550在这种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中,鱼的种类必然会不断地减少和灭绝。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废弃物对河流和空气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22]342艾尔克河成了一条废弃物和污染物堆积的小河。河里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
在莱斯看来,为了满足消费,就要生产更多的产品。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就要更多地占有物质资源。把人们的一切愿望和追求引向消费领域,使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既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也无法缓解由此带来的压力。“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主观需要的无限性,决定了 ‘缺乏’是当代西方社会无法解决的宿命。”[23]高兹认为,在劳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人们把消费同满足等同起来,无度地索取和占有物品。“生产将不再具有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现存需要的功能,相反,需要逐渐地具有了使生产不断增长的功能。”[24]114由异化劳动引起的异化消费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
四、结语
消费强制逻辑是资本的强制逻辑在消费领域的呈现,它造成人性的扭曲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引导大多数人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目的和价值,其结果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困境。”[25]我国要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必须破除消费强制逻辑,改变消费主义“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形成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