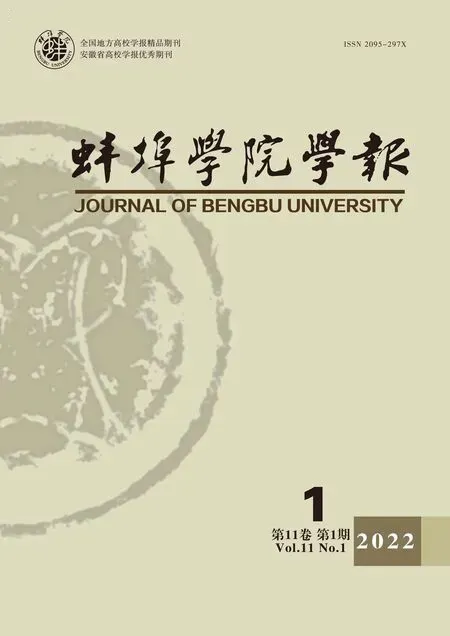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 以《小妖精集市》为例
董莉莉,李 海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1851年起,英国已有超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与乡村的疏远令人们的穿着、语言、习性越来越去自然化,以城市商业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基督教传统愈行愈远,原本连接信仰与生活的文学,也越发显得呆板造作。为抵制这种感受与现实的断裂,有革新精神的诗人们开始致力于在复古与现实的统一中寻求真实,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便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的魅力来自于其本身的矛盾性,她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其内心的不同声音的冲突。表面上看她的作品似乎非常传统,根植于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民间故事,长期被认为是一位善于抒情的宗教诗人。然而,她诗歌语言和题材表面的“追古”始终是为了“思今”,她的作品中处处透露出对她所生活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的记录、思考和回应。通过和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密切交往,她发现艺术传统、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都在无声地改变、崩塌。这种幻灭感成为其诗歌创作中的现代性元素。她试图在传统的断瓦残垣上搭建新的诗歌蜗居,于是在这种表面的简单和稳定之下,她重新发现了语言的多重魅力,发现了作为宗教诗人和抒情诗人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及转换,并以此为线索,揭露了文学场对女性诗人的压迫。
本文将以她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小妖精集市》为例,从以上三个角度讨论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复古与革新并存的现代性。
1 传统中的现实主义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出生于文学氛围浓厚的意大利移民家庭,作为女性,她从未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却从家庭教育中获益良多。诗歌创作于她而言是游戏;节奏、韵律、选词和意象,都是她信手拈来的玩具。这令她的诗歌创作更接近纯粹的美学表达。当时的诗坛矫饰成风,“人们开始追求技巧而不是思想,追求美丽而不是真实。”[1]当同时代的诗人还在“为赋新词强说愁”时,罗塞蒂选择了真实的诗歌。在她的笔下,日常家居、市井生活、闲言碎语、讨价还价等都能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传统诗歌体裁中,从一处处细节中反映当时社会的独特面貌。
1.1 生活化的语言
《小妖精集市》表面上采取了童谣形式,但克里斯蒂娜对诗歌的语言、节奏和韵脚都采取了精心的处理。长诗几乎一开篇便是小妖精们的叫卖声:“来买,来买”[2]2,带着亲切随意,仿佛平日里人们听惯的走街串巷的小贩的吆喝:“尝一尝,试一试。”[2]3这种纯粹的日常语言与当时诗坛惯用的文雅考究截然不同。当读者被吸引就读时,诗行突然转成扬抑格,一长串各色水果名字倾泻而出,恰似各种水果源源不断堆叠眼前,让人产生顾此失彼、目不暇接之感。
苹果、橘子,柠檬、橙子,圆润饱满的车厘子,甜瓜、覆盆子,红粉芬芳的桃子,结实黝黑的桑葚子,野生蔓越莓,红果露莓,菠萝、黑莓,杏子、草莓……
葡萄新鲜藤上摘,石榴饱满亮异彩,枣子和李子,上品的青梅、梨子,蜜李、山桑子。
尝一尝,试一试,鹅莓以及加仑子,明亮如火的伏牛花子,无花果嘴里塞,佛手柑南方来[2]2-3。
这种不厌其烦地列举与以往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点到为止大异其趣,这些水果不是比兴的载体,而成为诗歌本身。短诗行多以/ai/作为尾韵,仿佛林间小妖们在一口一口大快朵颐炫耀水果何等美味;长诗行都以/s/音结尾,闻者不免啧啧称奇,继而口唇生津,想要一尝琼汁玉液。正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言: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越吃越想吃,语言如何催生欲望被直白地描画出来,却完全没意识到这嘶嘶声正是恶魔的召唤,因为拉丁字母S本身便“采用了蛇的象形图案,读音用的是蛇发出的嘶嘶声”[3]。正因为有了这一铺垫,所以后文中和颜悦色貌似人畜无害的林妖们陡然露出残暴的真面目时,也就不觉得突兀了。
当诗节进行到最后五行,突然而来的头韵令已然眼花缭乱的读者在这极强的节奏感中心跳加速,只想频频点头,当林妖们再次高喊“来买,来买”时,想必只能乖乖就范。
罗塞蒂充分调动语言的潜能,诉诸听觉、视觉等各种感官,甚至产生了味觉效果,让魔果比看得见摸得着的水果更真实更有诱惑力,也更危险。诗歌就这样通过激发想象力超越了现实,建构出充满精致细节的真实。这种种细节并非对现实的呆板临摹,而是用沉浸式的审美体验唤醒了当时读者日趋麻木的感知。
1.2 语言中的生活
魔果真的美味吗?没有了叫卖声的渲染,不仅它的果汁又酸又涩,它的果核亦不能发芽,只是纯粹的死物。这正是诗人对于诗歌的思考:诗歌的吸引力来自语言的魔力。如果诗歌的语言无法传达崭新的生活经验,人们自然会去寻求新的表达。当时的矫饰主义令诗歌只会咏古怀旧。克里斯蒂娜对此并不赞同,她认同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观点:“如果每个诗人、每个画家、每个雕塑家都认可他最好最独创的思想源于他自己的时代……那为什么要把它们转移到遥远的时期去,使得它们今天一无是处呢?”[4]《小妖精集市》中这种令人眩晕的繁盛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农业的丰饶、贸易的发达和社会的繁荣。她精心记录其中的很多水果如甜橙、菠萝、石榴等并非英国所固有,而是来自海外:正是工业化的英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和掠夺,才让这些奇珍异果为英国的普通百姓耳闻,为上流社会所享用。围绕魔果的疯狂辞藻呼应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海外遍地黄金的传说,隐约勾勒出帝国的庞大身影。
拉斐尔前派的成员擅长在复古的艺术形式中精心挑选空隙填满逼真的细节,以反映社会现实,而这也是克里斯蒂娜的创作特点:以点带面,让读者得以窥见时代独特的风貌。
2 矛盾的象征意象
在克里斯蒂娜的诗歌中经常以姐妹关系为主题,她歌颂姐妹之间的相爱相持,但也展现她们之间的竞争和对峙。如《莫德姐妹》《三个女郎》《高贵姐妹》《少女之歌》《最矮的房间》等作品中,姐妹们彼此牵引,互相限制。这种复杂的羁绊表面上看是来自诗人对生活中人情世态的洞察,其实这种相斥相吸象征她诗歌创作时面临的两难:热情天性与克制信仰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
2.1 作为抒情诗人的萝拉
在《小妖精集市》中,克里斯蒂娜用“好奇”来定义萝拉。她对什么都想看想听,她代表自然的欲望。而莉兹是作为萝拉的对应面出现的,她谨慎虔诚,象征信仰的力量。这种双生子的设定很容易让人把萝拉和莉兹看做是两位一体的。两个人一个冲动,一个克制,“一个赞颂白天的锦绣,一个渴求那黑夜的降临。”[2]18她们都是罗塞蒂诗思活跃时的主体,又都会在另一方发声时沉默下来,象征罗塞蒂本人兼有两种性情:作为抒情诗人的热情敏感和作为宗教诗人的冷淡自制。
诗中萝拉貌似仅仅被欲望驱使行事,但她拒绝一成不变的日常,好奇现有秩序之外的未知,频频深入“荒野”久留等种种行为,带着拉斐尔前派一心复归自然的强烈印记。萝拉作为罗塞蒂抒情诗人的一面,她对声音敏感,与自然贴近。当莉兹以代表人类文明的屋舍为活动中心时,萝拉更愿意深入到自然的山谷丛林之中。她对自然界中的一切自然感应,自发回应,她会被从未得见的魔果俘获是一种必然。妖精们要求用作交换的一缕金发象征肉体,尽享魔果的饕餮盛宴无疑是场感官狂欢。对于诗人而言,敏锐的感官是不可或缺的,丧失了这种感受性,诗歌也就失去了其魅力。相对于莉兹,萝拉对于未知体验的渴求反而更令读者印象深刻:出让对感官的控制获得对经验的感受,比出让自我获得信仰似乎更有吸引力。吉尼亚·伍尔夫敏锐地发现了她诗歌中的这种冲突:“像一切天生有才能的人一样,你对于世界上的视觉之美具有一种敏感……说实在话,你那眼睛在观察一切的时候,带着拉斐尔前派才有的那种强烈的声色之感,恐怕一定会使得作为英国国教徒的你大吃一惊吧?”[5]这种感官上的声色审美,和神秘圣洁的宗教信仰令她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张力。
2.2 作为宗教诗人的莉兹
然而,当抒情诗人的自我过多地沉溺于感官刺激时,不但有可能失去敏锐的感受力,更有“堕落”的危险,这时宗教诗人压抑的自我便会显现出来。谨慎的莉兹形象,正是女诗人自己作为虔诚信徒的自我投射。莉兹从不行差踏错:有意识地避开一切诱惑;警告萝拉迟归的危险;时时把珍妮的悲剧记在心中;日常劳作一丝不苟。警惕未知,拒绝愉悦,犹如后期的克里斯蒂娜主动弃绝了世俗的欢娱,为一位冷峻的上帝奉献一生。
当克里斯蒂娜形容萝拉时,多用天鹅、白杨枝等自然意象,暗示萝拉和自然的本能冲动间的联系。而对莉兹的比喻则是礁岩、灯塔、无法攻克的城池等无机物。尽管让人肃然起敬,却比萝拉少了勃勃生机和温度。莉兹通过不听不看的方式来躲避林妖。若是一味逃之夭夭,终会被屏蔽在新一代的言语之外,无法超越日常语言枯燥的现实,更不可能接近诗歌语言揭示的真实。萝拉命悬一线之际,她终于勇敢地离开代表传统的生活区,进入了林妖们主宰的世界,“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去听去看。”[2]27这一过程象征着超越了现实的真实直抵想象的真实。最终莉兹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带回了魔果。“吃我,喝我,爱我;萝拉,尽情享用我!”[2]38这里关于圣餐的指涉不言而喻。如同领取圣餐养育灵性,以魔果为中介,莉兹和萝拉实现了血肉相连。被救赎的萝拉惊觉日思夜想的魔果居然又苦又涩,欲望的虚幻最终得以戳穿。
克里斯蒂娜通过诗歌创作努力来平衡自己浪漫情感和宗教戒律时,却无意间发现:真实意味着对现实幻象的揭露;而信仰和幻象往往也只有一步之遥。克里斯蒂娜后期很多悼亡诗表达出顿悟之后的放下,也许每首诗都是对一个已经破除的执念的纪念。
3 文学场中的女诗人
在罗塞蒂生活的时代,女诗人是一种点缀性的存在,虽然有勃朗宁夫人、L·E·L、赫曼斯等人活跃在诗坛,但人们普遍认为她们才气远不及男性诗人,她们的作品印刷册数也远不如男性诗人,更多的是作为礼物进行馈赠。女性作品始终是由男性“导师”来挑选修改。市场上对她们作品的评价也均来自男性。恰如《王子的历程》中,公主只能等待王子的到来,不管他几多蹉跎。“贯穿全诗的都是王子的声音,从未听到新娘的声音,她处于失语状态。”[6]女诗人也只能奢望男导师慧眼识珠,可惜她最有个人气质的诗篇居然生前全被退稿,让伍尔夫也惋惜不已。
3.1 女性、诗歌与刻板印象
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场里的强势文类是小说,诗歌已经沦落边缘,被类型化为带有多愁善感女性气质的阴柔文类,“女人就是诗歌。”[7]这种刻板印象无异于让女性诗人圈地自锢,令她们的处境十分为难:想要诗人的名声,就要符合男性读者对她们创作内容和风格的期待,但这种迎合又无异于让女性诗人沦为市场的工具,不利于她们在变革的时代发出个性化声音。
《小妖精集市》中爱冒险的萝拉闯入的禁地可以被视作男性垄断的文学场。围猎她的林妖们则等同拥有能指资源的场中权贵。群聚的林妖们把持着资源,在交换时非常强势,他们对萝拉评头论足,随意制定标准。一绺金发看似微不足道,却意味着放弃了对自己金子般贵重的原创性的坚持。所以萝拉在剪发时会落泪,但在诱惑之下,还是成交了。可惜诗人一旦失去了原创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会迅速地被市场抛弃,如同失去利用价值的萝拉。更有甚者,在尚且年富力强时因创作力枯竭而断送写作生涯,如同诗歌中那位不幸去世的新娘珍妮。现实中则有L·E·L企图突破传统,尝试“男性”主题,从而被围攻、排挤,最终死于贫病交加。
先觉者如勃朗宁夫人一直积极号召女性诗人不要为了男性写作,而要为自己和女性代言。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并未像勃朗宁夫人那样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女性在文学艺术圈中的物化现象毫无察觉,她已经感觉到活生生的女性艺术家在变得扁平,趋于符号化。《在艺术家画室》一诗中,她发现:女模特作为一张脸,一尊像,一个镜中影存在,为艺术家提供灵感的给养,闪现在他的梦中,但真正的模特本人,却不在诗中,不在此处[8]。她想到哥哥的模特、妻子——西德尔,尽管才貌双全,但只能作为激发但丁·罗塞蒂诗情的媒介存在,难有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
3.2 挑战文学场
作为当时少有的能靠写作获取独立收入的女性,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通过兄长与一众文人骚客,和编辑及出版商不断交流,甚至在文化消费这一领域接触的资讯还相当前卫:她的作品总会交由其兄但丁评鉴,且负责插画,在当时堪称时髦。她对同期女作家的稿酬也相当清楚。商业社会的发展令她这样天赋出众的女诗人也有了更多的读者,然而市场对于女诗人的聚焦往往不在作品本身而在别处。看到资质平庸的女诗人的诗作因为迎合市场偏好,居然能一年再版8次之多,罗塞蒂不满的同时,也意识到出版界就是一个市场;诗人们前赴后继,用自己的灵感交换每年十磅左右的收入,还要忍受编辑们对自己作品删改至面目全非,她不禁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小妖精集市和其他诗》于1862年4月初次出版便大获好评,出版商亚历山大·麦克米伦第二年便力劝克里斯蒂娜趁热打铁出版第二卷诗集,克里斯蒂娜婉拒道:“尽管没有什么比看到第二卷诗集出版更让我高兴的了。但我恐怕手头的素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已出版的诗集相比。”[9]出版商的催促日益频繁,克里斯蒂娜的抗拒也日渐加深,甚至会因插画与哥哥争执,只为坚持传达出自己诗作的原意。再去看诗中女孩们和林妖交易的情节,就会发现其中暗示了女诗人在创作时坚定的原则性。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莉兹去和林妖们交易时,带去了一枚银币,要求以此进行交换。当遭到林妖拒绝后,她坚持要回这枚银币,这体现了诗人坚持自己的体系,拒绝被市场方牵着鼻子走。即使遭到了林妖们的集体霸凌,她依然没有妥协,而是在维护自己主张的情况下,纠正了以往不平等交换对诗人感受力的伤害——萝拉不再被魔果所蒙蔽,迅速恢复了活力。
善于感受的诗意和坚持原则的信念合力之下,才会留下原创性的佳作。因此在诗歌结尾处,萝拉和莉兹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便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留给世界的纪念。经典的诗篇有生命,会生长,一代代之后仍然生生不息。
4 结论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声誉经历了起伏。二十世纪后半期读者和评论家们一度因为她不够先锋和新潮而冷落了她,认为她诗歌中传统的声音过强。但传统只是她的一面,在她的诗歌叙事中,既能看出宗教的保守影响,也有对现实的关注和时代的鲜明印记,更有向现有秩序挑战的勇气。传统和革新相伴相生,种种极大的反差和矛盾最终都于诗句中取得平衡,令她的诗歌具备了现代性的张力,具有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