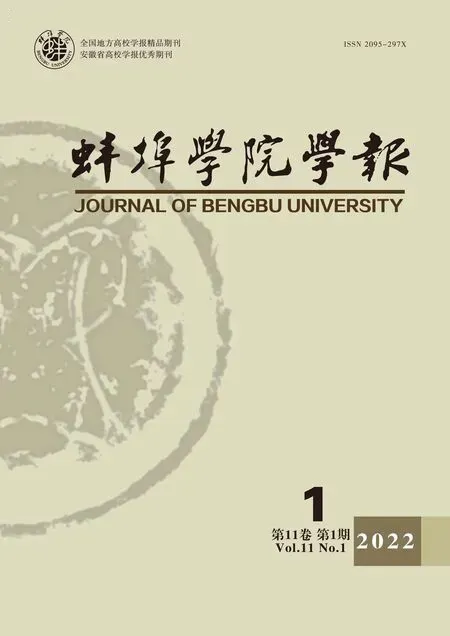原型批评视域下莫言小说中的女神崇拜研究
杨 阳
(1.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安徽 合肥 230011;2.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2011年,莫言凭借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他击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目前,莫言已经成为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的当代作家,其作品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在阅读莫言的作品时,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莫言小说中呈现出一种“阴盛阳衰”的现象。莫言曾坦言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他在小说里对一系列女性人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塑造了诸多性格鲜明、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无私奉献、宽容坚忍的“大地母亲”上官鲁氏,独立自强、敢爱敢恨的“我奶奶”戴凤莲,为爱痴狂、无怨无悔的美丽女子方碧玉,性感泼辣、美丽风流的“狗肉西施”孙眉娘等,她们一改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小鸟依人、弱柳扶风的柔弱形象,即使出生低微、命运坎坷,依然坚韧顽强,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散发着宽容博爱的人格光辉。
目前中外学界对于莫言的研究方兴未艾,如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魔幻现实主义研究、叙述视角研究、民间写作立场研究等,对于莫言小说中的女性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明晓琪《母性崇拜与生命信仰——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1];莫言与其他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如段鲜维《川端康成和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2];从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女性形象,如万惠玲《略论民间纸马中女性形象的母题与图式》[3]等。本文基于原型批评理论,结合文化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根据大母神的原型及其特征,阐述了莫言小说中女神崇拜的具体表现,探究了莫言小说中女神崇拜的成因,分析了莫言小说中女神崇拜写作所传达的现实意义。
1 原型批评与女神崇拜
原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影响较大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原型主要是指原始的、最初的模型,在文学批评领域主要指作品中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文学形象。原型批评理论由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著作《心理学与文学》中将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称之为个人无意识,认为这只是无意识的表层,而无意识的深层则为集体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有着明显的区别,“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4]可见,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不同,它不是源于个人经验,而是先天的。荣格指出,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情结,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不同,他将其称之为原型,这种原型是遗传的、先天的,是祖先们的生活经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下来的。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在荣格的原型理论基础上对原型的概念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系统建立了一种文学批评范式,其中心为“神话-原型”,这一批评理论主要侧重于文学类型的共性以及文学整体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原型批评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并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详细介绍了原型的内涵和外延。目前,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对莫言作品进行文学批评的作品包括《论莫言小说中的母神原型》以及《莫言民间叙事的原型与祭仪特征》等。
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认为大母神是一切母亲形象的来源,原始女神崇拜的原型便是大母神[5]。大母神是女性的原型,是母亲的象征,世界上多个民族都有关于大母神的传说,她不仅是传统部落的保护神,也是部落间互相识别的标记,在后期逐渐被泛化为不同的祭祀仪式、服饰和图形符号,在部落联盟出现后,上升为整个联盟的共神。大母神在神话和后神话体系中不断扩展其外延,演变出了五种相互交织的符号与母题,这些符号与大母神的特征有着诸多相似性,分别为:大容器(The Great Container)、大卵(The Great Eggs)、大圆(The Great Round)、大地(The Great Earth)、大树(The Great Tree)[6]。由于大母神具有包容、庇护、博爱等特征,人们常将大母神比作“大圆”“容器”等。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大母神孕育了生命,另一方面,她也能够吞噬一切。在许多国家的神话中都展现了大母神危险、恐怖、阴暗的一面,如印度神话中的迦梨女神,虽然平时她较为温和、广受欢迎,被人们称为雪山女神——帕尔瓦蒂,然而,当她发怒的时候,她就会失去理智,成为“吞噬一切时间,佩戴骨环的骷髅屋女主人”,变成了代表死亡的迦梨女神。
2 莫言小说中女神崇拜的书写
2.1 身体上的“丰乳”与“肥臀”
女神崇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诞生之时。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智力还未完全开化,生产力水平较低,对于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等现象充满未知的恐惧。土地能够滋养万物,为人们的衣食提供来源与保障,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面对土地能够孕育万物的现象,先民们感到十分好奇,对土地逐渐产生了敬仰与崇拜之情,人们现今谈论的地母原型便来源于此。在生产与生活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土地孕育万物和女性孕育孩子十分相似,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土地与女性、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加之女性在食物采集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优势,以及在种族延续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较高,由此产生了早期的女性崇拜。
莫言说:“只要大地不沉就能产生五谷,只要有女人就有丰乳就有肥臀就有生命,人类就能生生不息。”莫言毫不掩饰对女性的崇拜,甚至有些夸张地描写了她们的身体特征,他笔下的女性大多拥有壮硕的身体,强健的体格,丰满的乳房和臀部。《白棉花》中的方碧玉,不仅庄稼活干得好,还会拳脚功夫,尤其是她那对“趾高气扬的乳房,如同喜马拉雅山”。《爱情故事》中女知青何丽萍,“两只乳房把两个军便装的口袋高高挺起。”《丰乳肥臀》中描写母亲的乳房“像是两个丰满的宝葫芦”。这些身材丰满的女性用她们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子女,用生命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她们是生命最初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庇护者,她们以自己的血泪养育了子女,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是他们生命的守护神。莫言认为“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 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因此,他把那部讴歌伟大母性的小说命名为《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人类生命之源,对丰乳肥臀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生殖崇拜。在谈及《丰乳肥臀》的创作冲动时,莫言也说过是因为自己观看了一座女性的雕像而有所感悟,那座雕像对女性的乳房和臀部进行了夸张,它朴素的风格和大胆直露的表达使他瞬间领悟了母亲的伟大。对女性身体大胆而直白的描绘表现出莫言对母性的崇拜和对生殖的礼赞。
2.2 强烈的生殖欲望和旺盛的生殖能力
女性身体上的丰乳与肥臀是生殖力旺盛的标志,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具有强烈的生殖欲望和旺盛的生殖能力,《生死疲劳》中的二姨太,“通过她的丰乳和肥臀,就能看出定是一个很能生养的女人。”《爱情故事》中的何丽萍,身材丰满,一胎生育了两个孩子。还有《弃婴》中黑水口子的老婆,《白沟秋千架》中的暖,《秋水》中的“我奶奶”等人都有着旺盛的生育能力。最典型的要数《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她先后生育了八女一子,表现出了强大的生殖能力。在莫言笔下,生育似乎成为女性的一种本能,虽然每个女人都知道生育子女的艰难与危险,但仍然阻挡不了她们强烈的生殖欲望。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她们也要坚持生下孩子,这样的行为在小说《蛙》中有着淋漓尽致的描写。
莫言的代表作《蛙》既是对特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写照,也传达了他对于生殖和母性主题的深层次思考。作品直接以“蛙”作为题目,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叫蝌蚪,在文中,小狮子和蝌蚪的对话中曾说过“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蛙的繁殖能力非常强,蛙崇拜在人类文明早期较为普遍,在我国山西、河南等地出土的彩陶上人们均发现了青蛙纹,这与蛙所具有的旺盛的生殖力紧密相连,它们大多代表着相似的文化含义,寄托着人们追求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蛙崇拜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先民们的一种生殖崇拜,蛙成为他们祈求多子多福的图腾。赵国华先生认为:“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生殖女神。”[7]女娲因此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神”。据《说文解字》记载:“娲,古人神圣女,化万物者也。”[8]证实了女娲有创造万物的能力,表达了人们对女娲生殖的崇拜。有关女娲的神话传说,如《女娲造人》中就赞扬了女娲孕育万物、创造万物的精神。女娲原型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藏于人们意识深处,积聚了中华民族最古老、最基本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集体无意识被唤起之后,会带给人们久违的归属感,因此,很多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与文学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2.3 充满包容博爱、无私奉献的精神
大母神的基本特征是包容、博爱、庇护,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使之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常将其比作“大圆”“大地”“容器”。《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宽容隐忍、默默奉献,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完美诠释了大母神的包容与无私。上官鲁氏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她自幼父母早亡,从小寄居在姑姑家。出嫁后,由于生不出男孩,遭到婆家的重重压迫与虐待。在她即将临盆前,婆婆认为她已经轻车熟路了,只递给她一把剪刀就跑去照看家中将要生产的驴;丈夫在她生出女儿后气愤不已,对她拳脚相加。此外,她还经历着外界的战争、动乱、饥荒所带来的多重磨难。但即便如此,她始终顽强地支撑着,即使身边的亲人们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相继离她而去,她也没有被苦难打倒,她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活着?”就如同《活着》中的福贵一般,上官鲁氏的身上展现了中国底层人民最顽强的生命韧劲。此外,上官鲁氏充满了无私奉献与博爱的情怀。在她眼里,不论是自己的子女,还是女儿们送回来的孩子:沙枣花、司马粮、大哑、二哑、鲁胜利和韩鹦鹉,每一个人都是值得珍惜的生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她都会竭尽所能、用自己的全部来保护孩子们的周全,一个都不会放弃。莫言说“这部作品是写一个母亲并希望她能代表天下的母亲,是歌颂一个母亲并希望她能代表天下的母亲”。上官鲁氏艰辛的一生象征着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对种种苦难的承受中展示出惊人的生命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欢乐》中,母亲的脊背弯曲了,脖子细细的,外表丑陋、肮脏,但是为了让儿子考大学,她拖着佝偻的身躯到县城里挨家挨户地乞讨,最终讨来了一堆纸票和硬币。她身上那份母性的执着令人动容,强大的母性光辉使她显得如此美丽而伟大。《四十一炮》中,父亲与性感漂亮的野骡子私奔,要强的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辛苦劳作、勤俭节约,在捡破烂中学习本领,把家里经营得有模有样,还盖起了漂亮的院落,村里人都对她赞不绝口。多年后,当在外走投无路的父亲带着私生女回来时,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母亲接纳了这个曾经背叛她的男人。《儿子的敌人》中,母亲的小儿子在战争中不幸牺牲,负责抬尸体的民兵弄错了尸体,将一具可能是“儿子的敌人”的尸体给抬了回来。虽然痛失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出于母爱的本能,母亲仿佛听到了那句尸体对她的乞求,求她不要抛弃自己,母亲内心在想“这也是个苦孩子啊”,最后,她认下了这具可能是“儿子的敌人”的尸体。这种伟大的博爱精神催人泪下,令人震撼。母亲是生命的创造者,更是生命的守护着,这些母亲是历史与现实中无数历经沧桑的伟大母亲的缩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女神。莫言讴歌了母亲的伟大、包容与博爱,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母性的崇拜。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三个部分构成,即本我、自我与超我,它们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呈现出灵与肉的搏斗。正如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固化的、单一性格的人物一样,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往往也是复杂的圆形人物,其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是典型环境的产物。在莫言的小说中,这些女性既有伟大、无私、博爱的一面,也有在常人看来不够完美的一面。例如,上官鲁氏为了能够生出男孩,不断借种生子,她的九个孩子分别来自七个不同的男人,在生出上官金童以后,她表现出极端严重的重男轻女倾向。在《红高粱》中,余占鳌背叛爱情,和恋儿走到一起,九儿表现出了她的抗争与决绝。为了报复,她转而与余占鳌的死对头黑脸姘居。即使后来余占鳌回归家庭后,九儿依然十分强势,处处压制着二奶奶,直到二奶奶惨遭日本兵杀害。面对着在鬼子酷刑下一死一傻的母女俩,她们之间的恩怨才得到最终和解。《蛙》中的姑姑万心,作为妇产科医生,她尽职尽责,迎接了无数小生命的到来,被一些人亲切地称作“送子观音”。但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她毫不动摇,十分强悍,毫不留情地为他人做结扎、引产,使侄儿蝌蚪的妻子王仁美因流产而在手术台上丧生,导致村里的王胆在木筏上生下孩子后大出血而死亡。在她手上,2000多名胎儿先后夭折,她因此被人视为“杀人魔头”。晚年的她,内心十分悔恨、痛苦,嫁给了捏泥娃娃的师傅郝大手,希望通过这些泥娃娃来为自己赎罪。
3 莫言小说中女神崇拜的原因分析
3.1 个体潜意识中的女神崇拜
在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母亲曾给予我们食物、母爱与安全感,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一切。长大后,我们逐渐离开了母亲的庇护,但是在我们的无意识深处,对母亲的依恋与崇拜从未断绝。仪平策在《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中指出:“中国人在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时,总是把美好、神圣的事物比喻成母亲而不是父亲……比如,大地母亲、黄河母亲、祖国母亲等……母亲被置换为伟大、无私、奉献的概念符号。”[9]女神崇拜与母性崇拜根植于人类意识深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对女神的崇拜从未消失。即使是在男权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反映女神崇拜的作品。清代杰出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很多兼具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花妖狐媚形象,这些女子率真自然、重情重义,从不忸怩造作,她们常常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往往比男子还要果敢、深情。莫言曾说过:“让我难忘的女性形象,不是貂禅也不是西施,而是我们山东老乡蒲松龄先生笔下的那些狐狸精。她们有的爱笑,有的爱闹,个个个性鲜明,超凡脱俗……”[10]大作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初衷之一就是要“使闺阁昭传”,让世人都知道“闺阁中历历有人”。他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写道:“忽念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如彼裙钗。”在他笔下,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贾探春、香菱等女性不仅外表美丽,而且“行止见识”不凡,有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令男性都自愧不如,与之相比,感觉逊色很多。在现当代文坛中,路遥、张炜、张承志、韩少功、张贤亮、岳恒寿等男性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饱含着对女性的赞誉。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人生》中刻画的贺秀莲、田润叶、田晓霞等形象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宽厚博爱、无私奉献的美好品质;岳恒寿的《跪乳》更是他对母性文化的最高赞誉。王安忆、铁凝、张洁、苏童等女性作家在作品中也塑造了诸多形象丰满、充满光辉的女性人物。在莫言笔下,女性人物大多独立担当、爱憎分明,既有传统女性宽容、隐忍与博爱的精神,也具有现代女性独立与自强的意识,她们是生命的创造者、守护者,散发着包容博爱的人性光芒。
3.2 身边女性对莫言潜移默化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视角与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以及身边女性的影响密切相关。莫言的母亲对于他的性格形成以及后期的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他在小说《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表达了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与由衷的赞美。莫言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父亲不苟言笑,很少与人交流,家里的孩子们都很惧怕父亲。但是在母亲那里,莫言能够感受到温暖的、源源不断的母爱,这种爱犹如一道亮光,给莫言压抑的童年带来了巨大的慰藉。一次,莫言把家里唯一的一个热水壶打碎了,他战战兢兢,害怕极了,跑到外面躲藏了起来。母亲找到他之后,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并没有责骂他,她的举动给莫言带去了极大的安慰。母亲和蔼可亲、待人和善、为人正直、乐观坚强,这些优良的品质对莫言有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1]。通过母亲,莫言感受到了母性的温暖与力量。莫言的奶奶是一位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农村妇女,不论是外出下地干活,还是在家操持家务,她都能做得十分出色。奶奶还是一位颇具胆识的妇女,即使面对持刀端枪的日本鬼子,她也表现得镇定自若,反倒是爷爷被吓得瘫坐在地上。莫言从奶奶身上看到了几千年来沉淀在中国女性身上的美好品质,她们坚强能干、有胆有识、充满智慧,进一步深化了莫言内心深处的女性崇拜意识。莫言的姑姑是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医术高超的妇科医生,她一生中迎接了数万条生命,在高密深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姑姑的慈悲心肠和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令莫言十分敬佩,并且深受感染,小说《蛙》中的女主人公万心的身上就有姑姑的影子。莫言的妻子温柔贤惠,与他相知相守,在生活上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他的创作事业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可以说,身边的女性对莫言创作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莫言曾说过:“我的作品里经常是女性很伟大,男人反而有些窝窝囊囊的……关键时刻,女人比男人更坚强,更给力。家,国,是靠女人的缝缝补补而得到延续的。”[12]
4 莫言女神崇拜书写的现实意义
丰乳肥臀作为一个与原始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相关的象征符号,不仅被莫言用作小说的标题加以凸显,而且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在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体现了莫言文学创作中强烈的女神崇拜意识。女性身体上的丰乳象征着哺育的绵延不绝,肥臀意味着繁衍的生生不息,精神上的包容博爱与无私奉献体现了大母神包容一切的特征[13]。以莫言笔下的上官鲁氏为代表,她不关心政治、不懂战争,打心底排斥这些东西,她的心理状态代表了我们民族和历史中最本真的部分;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她只想着竭尽所能地哺育和庇护着自己的子女,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她是大母神与生殖女神的象征,是人伦、和平与正义的化身,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上官鲁氏身上不仅体现出强烈的母性情怀,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她个人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叛逆与挣扎的女性苦难史,象征着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苦难历史,是华夏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表。通过她与苦难抗争的经历进一步彰显出生命的坚韧与母性创造力的伟大。
女神崇拜与母性崇拜源远流长,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莫言以民间写作的立场,从老百姓的视角还原了为人类生生不息所默默奉献的伟大女性,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类生命的敬重与悲悯。小说中对女神的崇拜与追寻唤起了我们对母亲、对女性的敬畏与感恩,唤醒了人们心中最朴素、最原始的对爱和温暖的渴求,是现代社会人们所追寻和守护的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