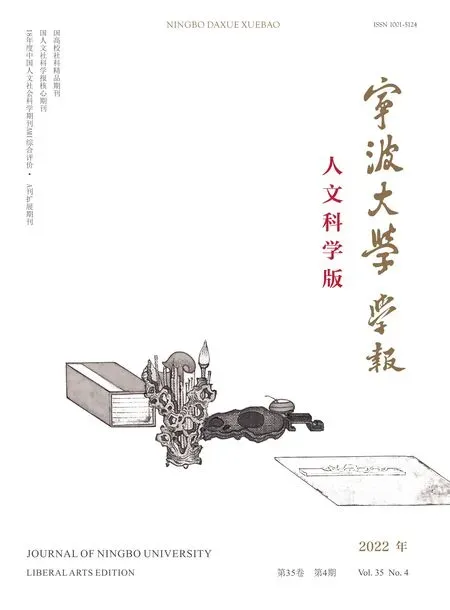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伊纪民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伊纪民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李秉衡;毓贤;大刀会;拳会;惩首解从;非正式合作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发展的研究,学界多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或从清廷统治集团对拳会认识的分歧①,或从西方列强、教会势力日益威逼的态势②等视角加以阐述。这些研究大多以“革命史”的视角下展开,过于粗疏。
促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只考虑清廷对教案、拳会态度及列强的威逼态势,随着革命史研究范式的逐渐弱化,路遥等学者从当时的民众的生存环境出发,考虑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与当时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恶劣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③。林华国等学者虽然仍以“革命史”视角立论,指出“义和团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主要在于前几十年民众反洋教斗争的历史积累和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激化”,但也认为“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组织的长期广泛存在也为义和团的迅速兴起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20-29。
义和团运动诚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义和团毕竟得到过清廷一定的、或明或暗的鼓动与支持,否则,它绝不会在短时间内席卷冀鲁地区,甚至在京畿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排外行动。
综上,清廷的鼓动与支持仍是义和团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清廷内部统治阶级的分歧,并认为这种分歧所显现的犹豫不决及之后的宣战上谕导致义和团力量的不断壮大[2]。此种研究结论虽有大量文献资料予以支撑,但难免过于宏观。事实上,1899年夏季的平原事件就已正式拉开义和团运动的帷幕,平原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义和团运动的最后成熟”[3]252,268。路遥指出,平原事件对早期义和拳(团)运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突破了反洋教斗争的局限而与官军相对仗”[4]270-271。1899年夏的义和团运动不仅反教会洋人,也与官府相抗衡,官府与义和拳的关系在之前或许不像此时这样剑拔弩张,这恰好印证了“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组织长期广泛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上,李秉衡抚鲁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因此,即便大刀会出现不法情事,只需惩办首要,加以遏制即可。之后,张汝梅、毓贤(更为明显)均对大刀会、拳会等组织持相对宽容的政策。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平原事件之前,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团体组织与官府间的关系就是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合作大于破裂、破裂大于合作但二者始终并存的不同模式。正是长久以来官方与大刀会、拳会复杂的缠绕关系,即便没有官方的明确鼓动与支持,只要不施加严厉、持续的、绝对的镇压,义和团在列强、教会势力的逼迫下便会运动起来。
总之,在官方迫于列强威逼,正式宣布绞杀义和团之前,官方与地方拳会、刀会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的,而是处在一种相互试探、非正式合作且非正式破裂的微妙状态。从此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另一种内在逻辑,进而对当前宏观研究作出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与补充。那就是:导致1899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诱因之一——官方对拳会、刀会的态度并不能简单以“纵容”“宽容”等词语笼统概括,探析大刀会、梅花拳等民间组织为何能够长期广泛存在,追溯、考察官方与刀会、拳会或对立或互动的多重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才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603
19世纪末,诸如大刀会、义和拳、红拳、梅花拳、神拳等民间组织,名目繁多,他们之间关系复杂,相互缠绕,尤其在官方看来,很难清楚地区别开来。“义和团、大刀会、金钟罩是一回事”[6]489,正如官方在处置教案中屡屡提出“只问其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7]56。义和团必然是多种民间力量的交融汇合形成的组织。再者,与1899年拳会极为相似的是1895年前后的大刀会。鉴于研究时限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至1899年夏平原事件这一时期,大刀会活动也贯穿于此时期,故本文以大刀会为例,探究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的关系,进一步厘清大刀会、义和拳长期广泛存在的多重原因。
一、非正式合作:大刀会助剿盗匪及壮大
1895年初,苏鲁边界“土匪勾结游勇蠢动”,时值中日交战期间,清廷担心“山东曹济土匪”的活动会使“运道有阻”,影响军火向山东沿海地区的转运,“若不及早扑灭,恐致酿成巨患”,故谕令山东巡抚李秉衡“拨营勇前往迅速剿灭”,而对于金钟罩(大刀会)“教徒设法解散以靖地方”[8]739-741。李秉衡随即饬令时任曹州知府的毓贤加紧剿匪,毓对剿匪谕令的反应极为积极,“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二千许人”[9]262,于是声名卓著,被时人称为“酷吏”。剿匪固然是官方行动,但是,剿匪之所以如此快捷,与大刀会有极为紧密的关联。
关于大刀会助剿盗匪的做法,徐州道台阮祖棠曾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报告,“其时曹方苦盗,官民交倚为重,一习其术则贼不敢侮。遇有抢案,则会中人聚抄贼巢,必获贼而后已”,“会中人均感之,乐于捐官捕盗”。况且“杀贼亦无冤抑”。该会除剿贼外“绝不掠财奸掳”,滋生事端,会众所需者仅“为之供饭而已”,实为“专心仗义”[10]151。大刀会还具有保乡护民的职能,以致“绅士亦与往来”[10]152,“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甚至营县局卡,亦有招募防卫”。该道台指出:“今年菏泽、成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直无一贼,皆赖大刀会之力。”[10]151徐州道台显然认为毓贤剿匪的胜利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大刀会的活动,山东地方官也颇为认同。李秉衡注意到:以刘士端为首的部分绅民入大刀会,并帮同民团“捕获巨盗多名送宪”,“屡试屡验”,乡民互相学习,“藉资保卫,珍为秘诀”。大刀会“除防身御贼之外,并无不法”。李赞誉其“习试不虚”[10]144。因剿匪等政绩升任按察使的毓贤也指出:“良善殷实之家,亦多学习,为保卫身家之计。”[10]240相关口述资料证明:“由于大刀会势力大,当时曹州府的毓贤爱它打土匪得力,很扶持大刀会。在有大刀会的地方,就绝除了土匪的足迹,哪庄有戏,有会,大刀会一去三四百人,镇压住,不让土匪作乱”,甚至有人声称毓贤是“大刀会的头”[6]735。
但是,无论大刀会还是所谓的金钟罩,清廷从来将其视为邪教,地方官不能不谨慎行事。李秉衡曾向清廷解释大刀会兴起以及该会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是大刀会“由来已久”“根株总未能绝”[7]4;二是受甲午中日之战的影响,毗邻前线的山东各处兵勇纷纷调离内地,开往东部沿海地区,山东的匪徒逐渐蠢动,以致“民心恐惧”,“防贼保护心切”,开始筹划防范之策。中日甲午战争中,官方军队接连败绩,给内地的人带来更大恐慌,民间遂主动寻求庇护之策,大刀会宣扬“此教可避枪炮”,“故习练异术”[10]144,随之,“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7]4。
即便如此,李秉衡于抚鲁之初就指明金钟罩乃邪教,饬下属“出示查禁金钟罩明目,如有递相传徒学习,从重惩办”[11]6。时任山东按察使毓贤也认为大刀会“迹近邪术”,应“严行查拿禁止”[7]38。毓贤抚鲁后屡发禁令,“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等名目”,并不准设厂习拳,以免聚众滋事,“先后出示有八次之多”[7]39。然而,山东当局虽出示禁绝大刀会文告,但在行动中采取了相当程度的容忍态度,“地方官以其亦不滋事,虽经出示禁止,而相沿已久,亦不敢操之过蹙。”[10]222-223徐州道台阮祖棠更是直接称,毓贤遇“刀会获匪送府”,“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10]150-151。
大刀会在官方容忍下迅速发展开来。一方面,他们人数众多,“一倡百和,党类日繁……蔓延传习,愈结愈盛。东省最多,豫省次之,皖省又次之,徐郡与东省壤地相接,近亦有人入其会者,共约有两三万之多”[10]151。另有游历内地的传教士说大刀会“大约有十余万不止”[12]183。另一方面,大刀会在一定时期聚集,公开举行有组织的活动。该会首领如刘士端、曹德礼、尤金生、彭桂林等均自立门户,“号召徒党”。1896年初,大刀会在单县举办祖师诞辰的庆典,方圆数百里的门徒“俱至演剧作会”[10]151,“唱戏四天以聚会友”[12]183。像刘士端、曹德礼这等有威信的会首,当地绅士常与之往来。“偶至邻境,迎送不少。且有旅帜马匹,民熟亦无惊怖”[10]152。当大刀会在鲁苏边界出现不法行为时,刘坤一奏陈总署,让后者电令毓贤出面,“招令会目东归,解散余党”[11]12,这或许只能从山东官宪与大刀会关系中加以理解。
二、有限的破裂:山东地方官的“惩首解从”政策
大刀会的活动除协助官方捕杀盗贼以及保护乡民生命财产外,其他活动并未得到官方许可,大刀会作为邪教仍在禁止之列。1895年初,官方就已敏感地嗅出其僭越官府职能的意味,并流露出相当程度的警惕与隐忧。
李秉衡抚鲁之初看到大刀会中既有狡黠之人,也充斥着游匪。“黠者遂借以逞其凶暴”,“外来游匪从而煽惑,渐至聚众滋事”[7]4。毓贤也指出大刀会“流传既广,盗贼亦渐习之”[10]240-242。惩治盗匪方面,大刀会“初尚送官惩治”,但“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10]151。江苏方面,徐州道台直接指出,“从前自称避火,专用刀矛,近则亦多火器。从前自称义侠,不取财物,近则专抢好马。行径日异,其心可知”[11]12。萧县知县刘本檍称该会“妄则冀煽诱愚民信其邪术”,“第愚民无知……受其所惑”,“可聚众谋逆”[13]159。
1896年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奏陈,大刀会不服从官方领导,“甚至与民团开仗,并抗拒官军”[11]9,“势极披昌,形同叛逆。若使得逞,则凶焰益张,本地伏莽与外来游勇从而附和,将有燎原之祸,大局不堪设想”[11]18。这不仅是地方官员的普遍认识,就连当时游历曹州的传教士也认为大刀会并非只捉拿盗匪,为扩大自身力量,该会公然强迫百姓加入其中,如有“有不随己者,群起而攻之。兵丁偶有触犯,鸠众而击之”[12]183。这是对官方权威与职能的一种僭越,深刻反映出清廷统治无力的状态。既然大刀会敢于与官方的民团发生公开冲突,那么,随着其势力的日益蔓延,大刀会与专横跋扈的教会势力发生冲撞也在所难免[6]674-680。
江苏砀山县加入大刀会的庞姓家族与入天主教刘姓家族争夺东湍土地所有权,冲突的缘由、过程及结果,相关学者有详细阐述[3]110-117,不再赘述。从官方视角看,无论冲突起因如何,大刀会袭扰范围涉及鲁苏二省,不仅抢劫教民,扬言“非毁尽教堂不散”[7]1,打毁“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一处”[7]6,且平民财产有不小损失,甚至官署“江南裁缺外委衙门”也遭到袭击。另外,抢劫教民财物引起教会及外国势力强势干预与恐吓,这是官方极不愿面对的。因此,必须严厉遏制大刀会的活动,即便是潜在的力量也必须加以剿除。清廷谕令江督刘坤一、鲁抚李秉衡速派队伍联合镇压,“如敢抗拒,即就地剿除,慎毋姑息养奸,致贻巨患”[7]1。刘坤一接令即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行动,饬令下属“实力防剿,俾免蔓延为患”[10]150,“匪首或斩或擒,无一漏网,匪徒死伤数百,余悉逃回山东”[11]19。表面看来,官方与大刀会有限的合作已走向破裂。
李秉衡采取的政策与刘坤一有所差异。李秉衡认为该会声势较大,如“一概剿捕,恐激则生变,转至结成死党,为患滋大”,故应先“出示晓谕解散胁从”,以安民心。对于“大股抗拒者,饬即严行剿办”,派按察使毓贤及兖沂曹济道锡良会同曹、单等县地方官先行周历劝导,“悔罪出会”者,“准其自新”[7]4-5,最终只将“匪首刘士端、曹得礼,并匪众三十余人拿获正法”[11]23,“余令归家,不准再习”[12]184。颇耐人寻味的是,大刀会首领刘、曹二人被逮捕过程极为简易,李秉衡称此举曹、单两县县令“均能不动声色……擒获正法,不令远飏为患,尚属宽猛合宜”[7]5。相关口述资料谓曹县令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刘士端赴会,刘士端跟他前往马上遭到逮捕,毓贤审问之后便交将其斩首。单县县令用同样的方式将曹得礼诱捕[6]578,582。之后,毓贤向李秉衡报告,余众“见首恶伏诛,皆悔过自新,闾阎一律安堵”[7]5。李秉衡向清廷陈奏镇压大刀会的情况提到,“是圣主如天之仁,原不欲概行诛殛”[7]5。显然,毓贤的报告和李秉衡的陈奏都表达出处置大刀会的基本政策,那就是徐州道台提出的“只论匪与不匪,不问会与不会”[11]12,如是匪,则以擒杀头目为要,其余可不问,即“惩首解从”政策。
1899年,大刀会、拳会的活动仍然较为频繁。7月29日,两江总督刘坤一鉴于鲁皖苏边界有“有刀匪纠众滋事”,“以致精健营营官剿贼阵亡”。因此电祈毓贤“祈饬属会同兜拿,以期早绝根株”[11]367。毓贤在回电中承认“济宁、嘉祥一带有外来拳会,为首者邵士宣等,来东聚众生事”[11]369-370,并陈言刘所指“刀匪”与山东当地的红拳会不同,不应按照处置盗匪方式处置拳会。
例如,“外匪朱红灯等乘机窃发,抢掠平原教民”。毓贤复派部下“于十月二十日将匪首朱红灯及僧人本明一并拿获……并出示解散胁从”[7]39。毓贤批示“朱红灯与丁家寺和尚心诚,因教民凌侮平民,藉端纠众滋事,抗官拒捕,放火杀人,殃及平民,实属愍不畏法。既经该府提审明确,自应照章惩办,以昭炯戒”[14]17-18。又如,就“拳首陈兆举率领率众持械拒伤庄民”一事,已属匪事,毓贤即令属员将其“就地正法”[11]394-395。从中也可以看出,毓贤严厉镇压匪患暴乱,针对的是“匪首”,实行的仍为以前的“惩首解从”政策。
山东官员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等看到,利用大刀会的力量缉剿盗匪已经显示效用。既然大刀会可以与乡绅、民团首领在缉拿盗匪时进行合作,以致“绅士亦与往来”,既然“良善殷实之家,亦多学习,为保卫身家之计”,那么大刀会自然就可以得到官方的默许。但是,大刀会势力的不断蔓延,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僭越官府职能,而且随着盗匪等不良分子的加入引发波及数省的骚乱,给西方各国及教会势力干预地方行政留有口实。这时,就不得不对此加以镇压。至于如何镇压,李秉衡、毓贤等地方官认为,作为协助民团剿杀盗匪的大刀会毕竟不能等同于完全的作乱分子,只要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遏制即可。如果说,刘坤一严厉镇压刀会、拳会的主张呈现的是一种与后者全面决裂态度的话,那么,李秉衡、毓贤的这种政策则是一种有限度的破裂,即山东地方官与刀会、拳会仍在一定程度保持了达成某种合作的契机。山东北境的天主教会编印的《拳祸记》有相关记载:毓贤令“义和拳教授兵勇拳艺,在按察司街设厂”,毓“赴兖州时,途次拳匪持刀出迓,中丞赏以银两,谕善习法术,以期大用,随即密奏朝廷,谓‘拳民具神力,能避枪炮,力胜洋兵’,并选拳民数人发往京师教徒授法。是时,省城内外多设拳厂……茌平县治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八百余处”[12]193。来自传教士的记载,从侧面说明以毓贤为首的山东地方官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的确促进刀会、拳会组织力量的发展壮大。
三、半合作与半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
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拳会半合作与半破裂的关系,上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下终1899年夏的平原事件。在这数年间,有时合作的成分多一些,有时破裂的成分多一些。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激烈的像“平原事件”般的对抗性事件。究其原因,除了考察官方与大刀会在剿灭盗匪方面有过合作经历之外,还需探析其他因素。
首先,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是官方与大刀会(包括平民)共同的仇恨点,是达成合作的基础。1898年底至1899年春,沂州府属兰山、郯城、费县、莒州、沂水、蒙阴、日照七县发生的十数起反洋教斗争,统称为“沂属教案”。这里以沂属教案中的日照事件为例展开叙述。
1898年11月,德使以驻日照县街头庄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被平民绑架殴打一案,照会总署将日照知县撤任[11]214,安治泰(山东南部教务的管理者)与德国驻胶澳总督叶世克达成一致,出兵沂州,强占日照县城,占据官署,并限制官员人身自由,“严查出入”[11]166-267。张汝梅随即致电叶世克,声言按照《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兵队只准在(租借地)边界内过调,并无擅入内地之文”[11]246-248。卸任之际,张汝梅“取古人临别赠言之义”,写信给德国亲王亨利和德国驻胶澳总督叶世克,表达了强烈谴责[11]251-257。张又上奏清廷:“东省民教不能相容莫甚于今日,其故皆由教民虐待平民,教士又袒护过甚,百姓衔恨日深,无论贤愚莫不痛心疾首,直有不可终日之势,地方官遇有教案极力弥缝,一不立结即受严遣。百姓亦知教民势大难犯,遇事含垢忍辱,敢怒而不敢言。教民因而气焰益张,任意陷害良懦……此民教结怨日甚之实在情形也。”[10]32日照县令杨耀林将情况上报给新晋山东巡抚毓贤,洋兵“终日托枪往来逡巡”,稍有违抗不从,必为德兵所拿。所需食物,亦系由县署“垫价代买”[11]263-264。更有甚者,德军“看守县令”,扬言将其“拘执带回青岛治罪”[11]250。此时毓贤刚刚肩膺鲁抚,清廷诏命其面对教案应“慎重办理,相机因应。……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不宜顾一时毁誉,率意径行,是为至要”[7]22的交涉谕电刚刚下发。尽管毓贤极为愤恨地向总署报告,称这是“有意要挟,藉端讹诈”[11]260-261,但他仍不希望履任之初就发生如此令人棘手的事件,为暂时稳定局势,遏制以安治泰为首的教会势力的攻势,毓贤决定由兖沂道彭虞孙与安治泰协商,向德方作出一定妥协。同时,为免民众“因畏成忿,酿生变端”,毓贤急调登州镇夏辛酉“督队来沂,弹压布置,以备不虞”[11]267,双管齐下,以求“赶紧设法了结”[11]261。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德军延长了占领日照,德兵每天进行勘验铁路、矿地等作业,意欲即行开工建造[11]284,这势必在当地惹下诸多事端。根据毓贤统计,德兵在兰山、日照、即墨三属,仅一月时间,就轰毙民人七名,另有伤重者两名,并焚毁房屋达几百间,损失粮物无数,共估值四万七千余两[14]304。毓贤“日夜焦思,苦无良策”,知会总署这不仅使山东当局难以容忍,地方民众的“忿怒情形”更是几难抑遏[11]350。此后,安治泰就沂属教案前往济南会见毓贤,毓贤采取明显的强硬态度,拒绝会见安治泰。于是,安治泰吁请德国公使海靖向清廷总署施压,“新任巡抚未怀善意,不肯相商,且不以礼相待……该巡抚必以为随意可发其仇恨之心,故将本教堂理应请办之事置之不议”,此举必“与中国大局见损”[10]347。恰在此时,德军强行带走日照五名绅士退回青岛,放言处罚匪首、赔款后才能放归[11]298。总署迫于压力,饬令毓贤即行会见安治泰,求得妥善解决。这一系列事件令毓贤颇为愤慨,不禁感叹:“德人要挟太甚,以理谕之不能,以力御之不可。”[11]262但为了“维大局而免开衅”,毓贤再饬彭虞孙等地方官就此事展开交涉,“据理力争,近乎决裂”[11]395-401,另一面强烈建议总署照会德方应议给中方衅款银四万九千九百二十余两,“以昭平允而顺舆情”[11]304。最终,山东当局以赔偿衅款七万余两了结沂属教案,五名绅士也被放回,但毓贤要求的德方赔款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回过头来看,毓贤抵任之初,清廷的谕电虽有不得“衅自我开”的指示,但同时明确强调中外交涉中的另一点:“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7]22一道谕电,两种态度,既有强硬的,也有妥协的,这不能不使毓贤和山东当局陷入极端的窘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毓贤拒绝面见安治泰这一问题。事实上,日照事件已然进一步激化了山东当局与民众仇外、拒外心理,这种心理必然也存在于与官方、普通民众关系比较密切的大刀会、拳会组织当中,以致有人“说声剿教堂,一号召几个村就联合起来……也不攻打官府,专门反对洋教,地方官也不过问”,大刀会“以为这样可以制住洋人及教徒的气焰”[6]730,1076。
其次,1895-1899年,李秉衡、张汝梅、毓贤担任山东巡抚,这三人均属颇具浓重保守主义思想的官僚,对刀会、拳会组织施以某种程度上的包容。处置教案时,李秉衡“持平办理”,继任者张汝梅主张“民教调和”,毓贤则是“偏袒私会”。时西人曾言:“李与毓贤交善,毓则以刚毅为护符,三人皆守旧,痛憾西人,峻拒变法。”[12]207
毓贤“以武健严酷著称”,擅长治理盗匪、水患[15]12757,一向提倡处置教案需“持平”。在1899年夏大刀会、拳会掀起频繁的反教斗争中,毓贤更是采取了“中立政策”,如出现暴乱,地方官要“分别查办”,如一概剿杀,“诚恐怕株累太多”[16]41。这样宽容的政策引起西方教会势力的普遍反对。英国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中表示:“山东近来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位官员(毓贤)对反对基督教的结社抱有同情。”[17]3耶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指斥毓贤之在东省“以官助盗”,弄倡言:“山东大吏办事荒谬致贻朝廷不测之忧……是则可羞,可恨,皆毓贤之罪也。”[18]374
1899年10月中旬,曾任高密知县的季桂芬赴鲁西东昌、曹州一带查勘淤塞河道及荒旱情形,路经茌平,看到“各庄习义和拳者则不下数百处”,对此,“上峰颇奖许”,故“练拳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季桂芬将此情形写给泰安知府姚松云指出:“此辈乡曲豪强,原非善类,今骤拥此声势,藐视官府法纪,日后隐患,正难预料。”[12]192季所言“上峰”虽不一定专指毓贤,但也多是与毓贤一样对刀会、拳会持相当宽容政策的州县官。
最后,刀会、拳会组织积极响应官方“化私会为公会”声明。“当时这一带大刀会很多,各村都有,因当时毓大人下告示,叫学大刀会,挡土匪学的人。”“毓贤因洋人横行霸道,故痛恨洋人,所以利用老百姓恨洋人的心理去拆毁教堂。”[6]681-684面对列强及教会势力的威逼,刀会、拳会开展的一系列反教活动当然需要寻求清廷官方的支持,即便这种支持是流于表面的,即便官方对刀会进行了一定程度镇压,刀会、拳会仍对官方的指示视作一种外力的凭恃。即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抗拒官军,大刀会、拳会仍不愿作为官方的对立的打击面。
1900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只问其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7]56官方与大刀会、拳会这种非正式合作关系得以强化,义和团随即席卷冀鲁地区,挺进京畿。在清廷正式颁布“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19]4677的谕旨之后,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绞杀下即告覆灭,足见官方态度、政策对刀会、拳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
四、余论
总之,1895-1899年间,官方与大刀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半合作与半破裂模式下。李秉衡抚鲁初期,官方就与大刀会形成一定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之后的张汝梅、毓贤均对大刀会、拳会等组织持相对宽容政策。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团体组织与官府间的关系就是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也正是此种样态与模式的存在,即便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反教运动施以镇压,也绝不会赶尽杀绝,这便是破裂大于合作的表现。官府处置教案时所持的“中立”态度则成为维系刀会、拳会存在并快速发展的契机,这时合作关系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是基于这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二者互相利用,引为奥援,拳会、刀会借用官方权势反洋教,官方利用拳会、刀会的力量剿灭盗匪及缓冲、抵御列强及教会的威逼。这种宽容政策的延续性是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既合作又对立模式形成以及义和团运动于1899年爆发的重要因素。
如果尝试打破1895-1899年山东与大刀会、拳会这一研究的视域,是否可以发现更多关于官方与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之间的多重关系?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与地方大刀会、兄弟会之间存在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拮抗的双重关系。中共党组织嵌入地方会社势力既是分化后者的一种手段,又是加以控制并为我所用的一种途径。地方大刀会等民间会社为求自保,有选择地与各种外来势力(其中就包括中共)进行合作。比如,相关学者指出中共利用大刀会根植于地方社会的特性及其与地方政府的矛盾,通过地方革命精英的社会关系成功联络大刀会,显示出双方合作的可能性[20]。从另一侧面显现出大刀会、拳会等民间会社存在的广泛性与长期性。然而,就义和团运动而言,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的催逼,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官方对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内外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①中国学者孙昉等指出这样的分歧“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外交政策的严重失序设下了伏笔”。参见:孙昉、孙向群《己亥建储与晚清政治危机》,《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第75-79页。美国学者柯文认为“朝廷的犹豫不决以及民众的普遍支持使义和团得以发展壮大起来”。参见: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7-39页。
②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1分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陆景琪《义和团在山东》,齐鲁书社,1980年;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89-106页。
③路遥、程啸指出:“清廷对山东拳会斗争所以不敢采取过分的‘一意剿办’政策,其更重要原因乃在于它对苏鲁豫皖麕集着数十万饥民深感隐忧。……给清廷和地方统治者以严重威胁”。参见:路遥、程啸《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第263-264页。又见:周锡瑞、叶文心《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第22-31页。
[1] 林华国. 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M].北京: 古籍出版社, 2002.
[2] 廖一中. 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J]. 天津社会科学, 1985(6): 79-84.
[3] 周锡瑞.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 张俊义, 王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4] 路遥, 程啸.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5]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 路遥. 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G].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0.
[7]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 中华书局编. 清实录: 第56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9]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 第1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教务教案档: 第6辑: 第1册[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0.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2]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 山东近代史资料: 第3分册[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1.
[13]佐藤公彦.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M]. 宋军, 彭曦, 何慈毅,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4]《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山东义和团案卷: 下册[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5]赵尔巽. 清史稿: 第4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6]《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筹笔偶存[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7]胡滨, 译.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M]. 丁名楠, 余绳武,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8]廉立之. 山东教案史料[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19]王彦威. 清季外交史料: 第9册[M]. 王亮, 辑编. 李育民, 等, 点校.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0]黄昊辰, 王才友. 浙西南大刀会对中共革命的对抗与合作(1935-1937)[J].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1(5): 1-10.
Cooperation and Rup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dong Local Officials and Big Sword Society
YI Ji-mi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The tolerant policy of Shandong local officials towards Big Sword Society and Boxer People has a long history. As early as in the Sino Japanese War, officials and sword formed a tacit understanding in busting bandits. However, when the boxer society was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joint fo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half cooperation and half rupture due to the continuity of the policy.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Big Sword Society only provide a possible source for Boxer movement. Though the possibility being high, but extremely unstable, they need to be dug, guided and tempered by the official and external forces. In other words, they need the official’s tolerant attitude and the bullying on the part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church with the former being more important.
Li Bingheng, Yuxian, Big Sword Society, the Boxers People, leader punishment and member disbandment, informal cooperation
2021-09-25
伊纪民(1995-),男,山东济南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E-mail: 1023153435@qq.com
K25
A
1001 - 5124(2022)04 - 0092 - 08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