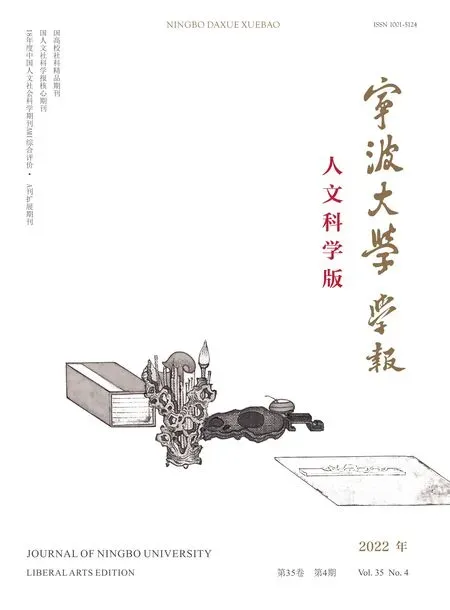论《山乡巨变》的范式意义
刘智跃
论《山乡巨变》的范式意义
刘智跃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在20世纪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山乡巨变》具有突出的范式意义。在小说叙述话语安排上,拥有权威力量的叙述者赋予小说叙事以明确现实意义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话语规范;在结构安排上,以运动发生的线性时间过程,讲述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经济个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主体的必然,剖析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大大小小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该类题材小说的基本结构模式;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矛盾冲突焦点,次要矛盾服从且围绕主要矛盾展开的冲突方式,已成为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典范。
《山乡巨变》;农村题材;范式意义
“范式”是20世纪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术语。该概念运用以来,一直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思维,以至于因广泛随意使用而酿成了滥用风险。本文使用“范式”概念,并不是刻意利用它的模糊性[1]来混乱视野,而是试图从“范式”概念内涵比较明确的方面,即事物内部的规范、引导作用的意义上来探讨一个文学问题,即作为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山乡巨变》建构的叙事形态及其审美内涵,在20世纪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具有的范式意义。
在20世纪50-70年代,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重头戏,产生了如《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名篇巨制。在要求文学题材的重大性、文学主题的政治性和人物形象的先进性的激进社会主义文学时代,那些富有时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试图以文学的方式“通过主体本质的建构来确立现实意义秩序”[2],不断探索农村题材小说的审美规范。在上述这个同样显示着创作时间序列的小说作品序列中,《三里湾》被认为囿于赵树理创作“问题小说”的局限性,仅仅将合作化看成是农村的一项具体工作,没有将它提升到建构现实意义秩序的高度。《创业史》则被誉为总体上堪称规范的“成功”之作。这样,创作时间处于《三里湾》与《创业史》之间的《山乡巨变》则沦为了一部有创作意图却未能实现的遗憾之作[2]。
如果从农村题材创作文本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角度,探寻20世纪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基本规范,《山乡巨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小说叙述话语安排上,设置了拥有权威力量的叙述者,予小说叙事以明确现实意义的方式,奠定了基本话语规范;在结构安排上,以运动发生的线性时间过程讲述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经济个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主体的必然,剖析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小小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该类题材小说的基本结构模式;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矛盾冲突焦点,次要矛盾围绕且服从主要矛盾展开的冲突方式,已成为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的铁律。
一
热拉尔·热奈特说,叙事话语既有描述外在事物的“显示”功能,又有表达说话者主观态度的“讲述”功能[3]。小说的叙事话语,既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又是作家明确的主观意图的表达。
小说《山乡巨变》开头: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涌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这里包含的事实信息如时间、地点、县委会、下乡等,和接下来小说交代主人公邓秀梅的工作任务等,表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运动,邓秀梅下乡正是为了指导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这项工作,是中央部署到省、到地区,地区安排到县,县委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反复学习,讨论“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之后,吃透了理论精神,摸透了政策路径,研讨了具体做法,才培训、派遣干部下基层乡村具体开展起来的。这样的叙事话语安排,叙述者因获得了政治权威力量的授权与支持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与优势地位,主人公自身也被赋予了权威与力量。
作为小说叙述者,邓秀梅的意义既在于她自身又超越了她自身。作为个体的邓秀梅,她虚心、热情、有干劲,但也年轻、稚嫩,有性格和能力上的不足,作为下乡指导工作的干部,她代表县里,贯彻并实现上级的政策,因此,她的意义是在整个叙事话语体系中建构起来的。从纵向秩序来说,有两个具体层级,上面层级是县委毛书记→区委朱明书记→邓秀梅,这是领导她的层级。下面层级由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这是她领导的层级。前者使叙事者获得了话语力量,后者是叙事者话语力量的具体实现。
其次,叙事话语在小说中具有贯穿性,成为持续的叙事动力。从整部小说来说,开头的叙事话语形成的叙事动力,持续贯穿整部小说,成为叙事红线。“区上”一节,区委书记朱明说:
搞社会主义,大家要辛苦一点。这次合作化运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哪一个敢不上紧?少奇同志说:不上紧的,就是存心想要调工作。
这段描写呼应了小说开头。会上朱明还强调了区委制订的具体工作指标:“根据各乡今天汇报的形势,大家再努一把力,我们全区的入社农户,跟总农户的比例,可达百分之七十。请大家注意,这个百分之七十,就是区里要求的指标。”指标分配,是将这次下乡工作任务定量化了,这充分显示了上级对合作化运动的重视和盯得紧、催得勤、抓得实的事实:“有电话的乡,每天跟我打一个电话。没安电话的乡,隔天写个汇报来。刚才跟地委、县委来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再过十天,我还要开一次这样的战地会议。”到小说正篇结束“成立”一节,清溪乡合作化任务基本完成,与小说开头形成了完整的叙事圆圈:“忙了一个月,邓秀梅和李月辉领导清溪乡支部在全乡建成了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个社大小不一,最小的三十五户,最大的是九十户。全乡四百零九户,已经有三百十二户提出了入社的申请。这数目,超过了上级规划的指标。”邓秀梅在农业社成立会上说:“全乡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六,超过了区委规定的指标。我们的清溪乡可以说是基本上合作化了。”这一节两次特意点出清溪乡的工作超过了上级“规划的指标”,再次回应小说开头的同时,又回应了前面领导部署安排工作的具体要求,叙事线索清晰,链条完整。
再次,赋予小说冲突以明确的力量对比,直接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和结局。《山乡巨变》以成功塑造人物而为人称道,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设置一系列的冲突来凸显人物的思想和个性。冲突双方分别是代表政策一方的工作组成员,以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等为代表,另一方则是他们的工作对象,代表小农经济个体的清溪乡贫雇农如陈先晋、王菊生、亭面糊等,工作组由于拥有政治权威话语背景因而具有绝对心理优势,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工作对象则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邓秀梅第一次到王菊生家摸情况,王菊生“吃了一惊”,邓秀梅第一次到陈先晋家做工作,陈先晋采取回避策略。不管是自私的王菊生还是顽固的陈先晋,虽然他们对合作化运动思想抵触,不肯入社,却无人敢与工作干部公开叫板,正面交锋,更不敢公开反对合作化运动,这使得干部可以用批评、教育、引导、示范的方式帮助他们认清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帮助他们摆脱传统个人发家致富的“落后”思想,共同走上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康庄大道。因此,才有了从亭面糊、陈先晋到盛佳秀、王菊生、张桂秋先后入社的胜利结局。每一次矛盾冲突,都以叙述者一方的胜利告终,标志着叙述者的价值得到实现。其中的过程尽管可以有反复,但故事走向和发展结局始终牢牢掌握在叙述者手里,具有非常明显的价值倾向。
这种叙事安排,当时受到过一些批评。小说发表后不久,评论家黄秋耘认为小说的“气”不够,即作品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小说“没有充分写出农村中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也没有充分写出基本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斗争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进一步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集体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4]。新世纪以来,文学史家则认为,恰恰相反,当作家把合作化写成一场并非农民群众“如饥似渴的要求”,而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被发动起来的运动的时候,这本身就已说明它是现实主义的一个胜利了[5]65。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实质上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小说叙事话语的艺术效果: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
因此,这种叙事话语安排以文学方式阐释了党的领导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山乡巨变》的话语方式,成为了小说《创业史》和《艳阳天》的基本规范。《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作为小说叙述者,其地位、作用跟《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类似。虽然邓秀梅是外来干部,而梁生宝和萧长春则是农民身份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似乎更能体现农民群众对集体主义合作化道路的“自觉追求”,但邓秀梅借助权威话语使自己成为权威话语叙述者的话语建构方式,梁生宝和萧长春同样需要。梁生宝的互助组是县里、区里和乡里树立的典型,一方面,他以自己的坚定决心、无私无畏、关心帮助和辛勤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阻碍,赢得大家的拥护,另一方面,来自乡政府卢支书、区委王书记和县委杨书记等为代表的党的领导的信任和支持,赋予他不竭的工作热情和话语力量,而且,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面临打击的时候,苦闷彷徨的时候,这种权威力量的支持就越发不可或缺。萧长春在东山坞的工作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乡党委书记王国忠的权威支持和思想启发,他不但无力击退阶级敌人的进攻,而且自身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和工作方法也无法提升到新的高度,更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
关于《山乡巨变》的叙事结构,作者遵循的是“现实事实的逻辑”,“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这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以合作化运动进程和线性时间来构建小说基本情节,采用“串珠”式结构表现运动进程中各种“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6]的基本模式。
邓秀梅到清溪乡指导开展合作化运动,前后一个多月时间,经历了下乡摸底、思想宣传、个别串连到合作社成立等几个阶段,这是“现实事实的逻辑”过程,在小说中是清晰而比较内在的。小说重点讲述与主要刻画的,是运动各阶段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以及一个个成功的转变故事。矛盾主要集中在个别串连阶段。农村合作化是在土改基础上的又一次革命,此时,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因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对象主要是贫雇农、中农和富农。从社会物质条件来说,贫农耕具少,畜力不足,生产困难大,一般情况下会比较积极拥护,富农和中农耕具多,畜力足,田地肥,对加入合作社并不积极,所以,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工作是争取富农和中农入社。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贫农也有好多的顾虑”,有的思想上有顾虑,有的顾惜面子暂时不愿意入社,也有土改后分得土地的贫农,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收入增加,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有的甚至已经上升到新中农甚至新富农的程度,也不愿意入社。
小说冲突的复杂性,决定了叙事过程的曲折性。小说选择以冲突来讲述故事,以矛盾来推动叙事发展,叙事发展和矛盾冲突紧密结合。如果说事实的逻辑发展过程是叙事“线”,那么个别串连动员一个又一个人入社取得工作的一次又一次胜利,成为线串上的“珠”。邓秀梅下到清溪乡,摸底发现全乡合作化基础差,只有一个完整的互助组。经过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到“区上”一节,清溪乡申请入社的农户达到全乡农户的45%。到“成立”一节,全乡入社的农户比例达到76%。这个成绩的取得,正是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等人通过宣传教育,深入家家户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冲突的结果。虽然工作过程只有一个月时间,但叙事过程跌宕多姿、生动有趣,矛盾冲突高潮迭起。在这个过程中,盛佑亭、陈先晋、张桂秋、盛佳秀等人的入社故事,是小说表现矛盾,讲述故事的中心。
小说讲述不同人物的入社故事时,紧密结合具体人物的思想、心理、性格特点和人生阅历,展示了不同的矛盾冲突。比如盛佑亭,他听了宣传队的号召,主动叫儿子写入社申请,看起来非常主动,好像思想进步,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好面子,喜吹牛,怕人低看自己,表面上积极,内心里有顾虑,真正行动起来又常常落后,非常矛盾,可爱又可笑。陈先晋是一个在旧社会经历了很多磨难,有着痛苦记忆的人,被社会和生活销蚀掉了反抗的棱角,他有着惊人的勤劳苦做的自律精神,只相信自己一双手,只相信土地不会亏待勤苦人。这样一个人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是极其艰难的。因此,在自己的亲人崽女都鼓动他入社的情况下,他仍然非常抗拒。同样是贫农,陈先晋入社和盛佑亭入社故事不一样,入社方式不同,而且冲突过程也完全迥异。盛佑亭入社带有喜剧色彩,而陈先晋入社更多悲壮风格;盛佑亭入社后还左顾右瞧,陈先晋入社后就一心一意。因此,两个人的入社故事富有不同的审美内涵。
再看两个中农,张桂秋和王菊生是两个最顽固的人,直到整部小说结尾他们才走上合作化道路。王菊生是个勤劳的“作家”,劳动力强,但他自私,狡猾,耍小聪明,顽固地坚持走个人发家之路。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等人做工作他始终不听,还装病、夫妻故意吵架,变相抵制合作化。闹得自己里外不是人,仍然不肯入社。合作社成立后,他又在挖塘泥、插秧和双抢等生产环节跟社里竞赛,似乎铁了心单干。王菊生入社,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教育下逐步觉醒的结果,尤其是在双抢环节,社里早早完成了生产任务,而王菊生家的谷子在田里生芽了,老婆和孩子都累病了,眼看到手的收成要泡汤。是刘雨生组织社员,帮他渡过了难关,使他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合作化的优越性。再加上大粪、石灰、农药、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买不到了,逼得他只好入社。
与王菊生相比,张桂秋更多负面的品性。解放前,家里穷,他当过兵痞。土改时,划作贫农,如今靠副业特长成了上中农。他鼓励妹妹跟刘雨生离婚,想把她嫁到城里去,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他的心思本来就不在农村。由于他品性有问题,自然跟坏分子龚子元走得近,他不但平时跟龚子元有瓜连,而且还听信他的话,差点杀掉了耕牛。明知龚子元有非法阴谋,他也不去告发。张桂秋入社,是迫于政治形势的严峻,是“形势所逼,他不得已”,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一个人扳不住了。
展示大大小小各种类型不同方式的冲突,在冲突中塑造性格迥异的人物,是《山乡巨变》最精彩的方面。这些生动的故事,充满个性的人物系列,精准的心理描写,成为这部小说大大小小不断闪光的珠玉,极大地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山乡巨变》采用的线性叙事与冲突叙事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在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小说中具有范式意义。
《创业史》虽然采用以“系列的冲突关系”作为小说的主要结构原则,但同时,“展示运动过程”的线性叙事结构也非常清晰。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买稻种—进山割扫帚—搞水稻密植等过程,它们既是时间的流程,同时也是互助组历经考验发展巩固的进程。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矛盾冲突,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买稻种体现了互助组的集体生产优势,进山割扫帚帮助贫农度过春荒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使互助组顺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克服了最严峻的考验。科学栽种水稻密植使得生产丰收,互助组得以巩固壮大,为办社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山乡巨变》由于注重于运动进程而使得结构有松散之嫌,那么《创业史》则通过集中笔墨于矛盾冲突而使得结构更紧凑,故事更集中,艺术性更高。事实上,两者区别仅在于运动进程的线性叙事结构和矛盾冲突的冲突叙事结构各有所侧重而已。《艳阳天》进一步凝练了冲突叙事结构,层层剥笋,最后揪出了潜藏的敌对分子。但它也是与线性叙事融合使用的,冲突展现过程同时伴随着麦收前—收麦—晒麦的时间序列。麦收前,中农们就酝酿搞土地分红,并唆使马连福在干部会上吵架、骂人,企图通过对干部施加压力来重定分配原则,遭到萧长春等的反对。随着收麦、晒麦的到来,阴谋未能得逞的坏分子更加疯狂报复萧长春,破坏合作社。两者紧密结合,使分配矛盾随着麦收进程而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紧张,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戏剧性效果。
三
《山乡巨变》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矛盾冲突焦点,其他次要矛盾冲突围绕且服从主要矛盾冲突的写法,成为20世纪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表现矛盾冲突的铁律。在主要矛盾的统率下,人物思想的新与旧、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先进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各种关系得以尽情展示。
是否选择加入农业合作化是检验人物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唯一标准,因此,围绕入社的矛盾是小说的中心矛盾。那些对入社持观望、犹疑和拒斥态度的,如中农王菊生、盛佳秀,新中农张桂秋,贫农陈先晋、符贱庚、盛佑亭等,遂成为小说矛盾冲突的焦点。小说抓住不同对象的特点,细致入微而又入情入理地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心理矛盾。
对于中农来说,他们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他们的家庭财产都是靠自己勤劳苦做,流血流汗换来的,他们“财心紧,对人尖”也就顺理成章。让他们加入合作社,跟贫农共享生产资料,肯定吃亏。盛佑亭说张桂秋和王菊生“心像钩子,叫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生怕吃亏”。他们只想维持生产现状,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这在当时就成了私心重,甚至思想落后分子,与党倡导的农村合作化道路形成尖锐对立。
以中农王菊生为例,他甘愿单干,不希望有人来做他的入社工作。因为他家住瓦屋,自己耕牛农具肃齐,生产可以独立,还有上好的肥田,加之仓里有谷,屋里有柴有肥料,猪栏里喂养着两只壮猪一只架子猪,是个比较富足的家庭。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他“一天到黑,手脚不停的勤快”地做出来的。王菊生的犹豫、观望和抗拒心理非常有代表性:
要是大家入了社,一个人不入,他怕人笑骂,怕将来买不到肥料,又怕水路被社里隔断;要是入呢,他深怕吃亏。耕牛农具,一套肃齐,万事不求人,为什么要跟人家搁伙呢?在他看来,贫农都是懒家伙,他们入社,一心只想沾人家的便宜。他自己的一条大黄牯要牵进社里,放足了肥料的上好的陈田也要跟人家的瘦田搞一起。“这明明是个吃亏的路径,我为什么要当黑猪子呢?”他这样想。
中农张桂秋也是这样,他有特长,会“整副业、喂鸡、喂鸭和养猪”,讨了一个勤俭发狠的老婆,劳动能力赛过一个男子汉,家里南奔女做,“两人一套手,早起晚睡,省吃省穿,喂了一大群鸡鸭,猪栏里经常关两只壮猪,还买了一条口嫩的黄牯”,可谓家成业就。搞合作化,牛要归公,吃眼前亏,他心里有抵触。因此,尽管邓秀梅跟他仔细算了账,认为他入社收入会增加,但他仍然犹疑不定,“只怕社一办起来,人多嘴杂,反倒搞不好”,艄公多了打烂船。中农盛佳秀,丈夫出走,只身带着孩子过日子,平时就靠着家里有几亩好田,因为觉得土地入社的报酬低不划算而不想入社,“万一社里烂场合,我一个女子,带个孩子去指靠哪个”,总之,中农们考虑的多是眼前物质利益方面的得失。
中农怕失去财产,贫农本来就穷,从理论上说,他们应该会积极入社,但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顾虑,因为他们完全缺乏试错的成本。社会主义是新事物,一旦办社失败,他们就生计无法保障,有生存之忧。盛佑亭表面上积极入社,其实他心里很纠结,一直都徘徊在单干和入社之间。虽然奈于面子,他写了入社申请,但他也怕社里烂场合,他自述的入社申请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就是蛮想有保留地入社,给自己留点退路。陈先晋顽固地不想入社,既有传统心理的遗留,“积古以来,作田的都是各干各”,“树大分杈,人大分家,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又有小农经济意识在作怪,“龙多旱,人多乱,几十户人家搞到一起,怕出碌戏”,还有因为家境穷,家底子薄,生活上毫无退路的生存之忧,“烂了场合,我一家身口,指靠哪个”。因此,他是战战兢兢的,患得患失的,入社过程最曲折,最易受各种因素影响。小说用了长达四节的篇幅写陈先晋入社,可谓详尽而细致。尽管邓秀梅做他的入社工作时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但过程并不顺利。陈先晋由不愿意入社,到有条件地入社。前一天答应了入社,第二天却又反悔。最后子女一个个要带自己的土地入社,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才不得已答应入社,已经决定了,临行前还去到自己的田地里痛哭一回。陈先晋的入社过程充分表现了贫农思想上的沉重负担和走出历史困境的莫大不易。
主要矛盾统率次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展开既有自己的特点,又不游离于主要矛盾,形成有主有次,多层次发展的多姿多彩的斑斓故事,成为小说展示矛盾冲突的独特艺术安排。小说中的次要矛盾,如刘雨生与张桂贞的家庭纠纷,陈大春与盛淑君的爱情故事,盛佳秀与刘雨生的爱情故事,陈先晋的家庭纷争,王菊生夫妻的吵架表演等都是这样。
刘雨生和张桂贞的夫妻矛盾,起因是刘雨生一心扑在社里的工作上,对家庭照顾少,激发了张桂贞的不满。与之相反,盛佳秀和刘雨生的爱情正是由于刘雨生主持社里的工作,盛佳秀觉得自己入社有了心理依靠。张桂贞懒惰爱享受,盛佳秀勤劳愿付出,这才有了对待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张桂贞离婚后,小说让她跟竹脑壳符贱庚结婚,因为两个人都对农业社不热心,也算是臭味相投。陈大春和盛淑君的爱情故事写得一波三折,盛淑君爱陈大春,是觉得大春进步,积极参加社里的工作。当盛淑君也积极参加社里的工作后,陈大春也纠偏了自己对她的看法,喜欢上了对方,以至于他打破了自己跟朋友们制定的年满28岁才恋爱的计划。这些分分合合的爱情,原本是人们对待意中人的非常隐秘的个人心理,在《山乡巨变》中加入了较多的社会内容,因而普遍明朗起来。
再说陈先晋的家庭矛盾,起因就是陈先晋不愿意入社,而儿女们希望入社引发的。陈先晋顽固地走单干路线,抵制合作化运动,家庭矛盾延伸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同时也为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条件。假如没有家庭矛盾,陈先晋还会继续顽固地坚持单干,正是因为有了老伴的转变,儿子孟春的转变,女婿的劝说,才促成了他思想的松动。家庭矛盾越尖锐,陈先晋的进步就越快,最后儿女们纷纷要求带自己的土地入社,陈先晋才不得已答应入社。王菊生夫妻为对抗入社,先是故意装病,想以此堵住干部们的嘴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夫妻“相里手骂”,向外人表演夫妻不和意见不一无法入社的家庭闹剧。在《山乡巨变》中,家庭矛盾、人际纠纷等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而是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因素,甚至是社会问题的延伸。
在小说《创业史》和《艳阳天》中,不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小说的主要冲突,而且它们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跟《山乡巨变》如出一辙。《创业史》的主要内容是梁生宝互助组的组建、发展和巩固过程,梁生宝一心扑在互助组的工作上,带领大家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最后取得办社的胜利,而以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为主的反对力量却千方百计要搞垮梁生宝互助组,破坏农村合作化,走私有化道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了生产互助的巨大成功,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民众,号召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艳阳天》的主要矛盾是围绕麦收分配展开的,土地分红还是劳动分红成为双方矛盾冲突的焦点。社章上明明白白写着按劳动分红,马之悦、弯弯绕、马大炮等人顽固坚持土地分红,是幻想开历史倒车,回到剥削制度的老路上去,因此,这场矛盾冲突的实质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次要矛盾的安排方面,《创业史》和《艳阳天》也符合《山乡巨变》的基本规范,比如粱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家庭矛盾,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姚士杰和素芳的奸情等。粱三老汉要走个人发家的老路,与梁生宝热心互助组的工作形成尖锐对立。梁生宝喜欢改霞,改霞喜欢梁生宝,本来是一对美好的鸳鸯,但梁生宝以为改霞对农业生产没兴趣,一心向往城市生活,于是坚决冷淡了这份感情。姚士杰抓住素芳的心理弱点,奸污了她,还把她家拉出梁生宝的互助组,起到了破坏互助生产的目的。在《艳阳天》中,次要矛盾如萧长春的爱情,焦淑红的爱情,马翠清的爱情,以及焦淑红的家庭矛盾,马老四的家庭矛盾,韩道满的家庭分歧等都不是单纯的生活矛盾,而是被统率进了主要矛盾中来。小说一开始就写萧老大急慌慌操心萧长春续弦的事情,萧长春回了家,却一直没有顾上半点个人的事情。马立本追求焦淑红,焦淑红却对他完全没有意思,她从心里爱的是萧长春。马翠清喜欢韩道满,却对他进步不够有意见,对他落后的父亲很不待见,甚至威胁要跟韩道满分手。马老四一心为社,儿子马连福却思想落后,听信中农的怂恿,跟萧长春争吵,甚至骂人,因此老人跟儿子才势不两立。韩道满要求进步,跟父亲韩百安发生了矛盾,他选择了离家另住,甚至不怕跟父亲闹崩。次要矛盾因主要矛盾而发,且内容上围绕着主要矛盾而展开,且仍然属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
以主要矛盾统率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围绕且服从主要矛盾的方式,使得小说的矛盾冲突非常集中,尤其适合于表现尖锐复杂的矛盾。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的风格,与小说采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思想内容高度集中的艺术表现方式不无关系。从《山乡巨变》到《创业史》,再到《艳阳天》,矛盾一个比一个激烈,矛盾的安排一个比一个集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也就一个比一个深入而尖锐。
《山乡巨变》创作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探索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配合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创造新中国的人民文艺,广大作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体验生活,熟悉人物,改造思想。1955年,作家周立波举家迁到益阳农村定居,深入体验家乡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挟“暴风骤雨”之势,于1956年开始创作《山乡巨变》,1957年底完成正篇,1959年底完成续篇。
在左倾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如何大写新中国农村的新人新貌和社会成就,发挥文学艺术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7],成为摆在艺术家面前的重大政治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全国性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当时中央政府力抓的“一件大事”[8]。开展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完成中国农村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周立波这样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位强调要“终生坚持”毛泽东“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方向[9]的作家,是抱着怎样的热情和觉悟投入到《山乡巨变》创作中。他以自身的文学努力和创作天赋,奠定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基本规范。
虽然时代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但60余年来,《山乡巨变》一直被誉为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10],当代具有鲜明风格特色和重要历史地位的优秀长篇[5]64。究其原因,与作家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努力挖掘真与美的创作努力分不开,至今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山乡巨变》发表后,评论界肯定小说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成就,盛赞小说题材的政治意义和人物塑造方面的巨大成功①。新世纪以来,人们又挖掘出小说蕴含的更多价值与意义,如小说在乡村叙事方面的艺术内涵[11]以及在话语建构和文化融合方面的价值[12]。总之,不管当时人们赞美小说在建构规范方面的成就,还是今天人们注意到小说超越规范的新价值,《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都不容置疑,具有永久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
注释:
① 如王西彦《读〈山乡巨变〉》、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江曾培《〈山乡巨变〉变得好》、朱寨《谈〈山乡巨变〉及其它》《读〈山乡巨变〉续编》等文章,都持这样的观点。
[1] 陈丽杰. 模糊的“范式”[J]. 理论界, 2017(7): 35-41.
[2] 萨支山. 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J]. 文学评论, 2001(3): 117-124.
[3] 南帆. 文学理论 [M]. 新读本.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4] 黄秋耘. 《山乡巨变》琐谈[N]. 文艺报, 1961-02-26.
[5] 张炯.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6] 周立波. 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M]//“人民文学”编辑部. 评《山乡巨变》.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9: 4.
[7] 郭沫若. 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M]//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史料选.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172-178.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27.
[9] 周立波. 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J]. 北京: 人民文学, 1977(12): 79-82.
[10]江曾培. 《山乡巨变》变得好: 谈《山乡巨变》及其续篇[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2.
[11]毕光明. 《山乡巨变》的乡村叙事及其文学价值[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0(5): 54-60.
[12]刘起林. 论《山乡巨变》的双重话语建构与文化融合底蕴[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5(1): 83-88.
On the Paradigm Significance of
LIU Zhi-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The novelhas formed a paradigm for the novels on the theme of rural co-operation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In terms of the discourse arrangement of the novel narrat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rrator with authoritative power and the way that gives the novel narrative a clear realistic meaning have become the basic discourse norm. In terms of structural arrangement, the linear time process of movement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inevitabl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from scattered small peasant economic individuals to the main bod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to analyse the large and smal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had become the protype of this kind of novels. To tak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roads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and the conflict mode of the secondary contradiction revolved around the main contradiction has become the norm of rural cooperative novels.
, rural theme, paradigm significance
2021-06-22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莫言文学的传承创新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关系研究”(XSP20YBC098)
刘智跃(1968-),男,湖南永州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 zhiyueliu@163.com
I207
A
1001 - 5124(2022)04 - 0043 - 09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