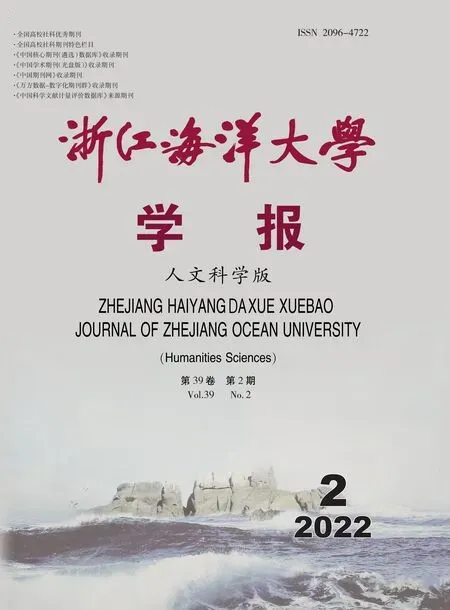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海员换班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陈 悦 张晏瑲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流行至今,各国防疫措施各显成效,但随着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变种病毒出现,防疫形势仍异常严峻。各国加强进出口岸的管理,控制人员流动本无可厚非,但“一刀切”式的防疫模式却让肩负全球80%[1]以上商品贸易货运量的海员因为换班、遣返、疫苗接种等问题承受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2]为切实解决海员现实困境,我国先后发布9 版《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成立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工作专班,开通船员疫苗接种“绿色通道”;国际海事组织在其第32 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采取综合行动应对海员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面临的挑战的决议。然而各国防疫政策侧重不一,部分国家拒绝承担国际义务,海员的处境仍如纳履踵决般艰难。笔者拟通过分析部分国家现行防疫政策中海员换班遣返的管控措施,剖析现行国际条约框架下国家对海员换班的当然责任,①探索后疫情时代保障海员顺利换班的国际合作渠道的建立以及国内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一、海员换班与疫苗接种的现实困境
海员换班涉及国内以及国际间人员流动,部分国家和地方防控措施弹性的缺乏以及换班遣返接续措施的冲突,导致海员原本换班计划被迫改变,临时更换停靠港口、改变遣返路线不仅直接导致海员回家“遥遥无期”,且在部分海员未接种疫苗而船上出现疑似病例时,海员的心理防线也极易崩溃。[3]
(一)海员换班的政策阻碍及执行障碍
1.国内换班政策阻碍
我国交通运输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严格落实港口的熔断措施。截至2021 年8 月25 日,已执行5 次熔断,累计暂停24 家航运公司、531 艘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境内港口换班。[4]熔断缘由为过错船舶或船舶所属航运公司未能有效履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防范措施不到位,防控效果不明显,但熔断之结果为一定时间内禁止过错航运公司所属全部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国港口换班,此种结果使港口熔断举措略微带有“连坐”意味。该处理措施虽对防疫不力的航运公司有一定惩戒作用,但此举影响更为直接的是过错航运公司所属的其他认真防疫的船舶原计划在我国港口换班的外籍船员,他们因其他船舶船员或管理公司的过错而导致自身合法的换班权利丧失。②
2022 年3 月3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九版)》,第2 部分总体要求中支持引航机构按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对出现疫情的船舶及其船公司的所有经营船舶采取调后引航次序的限制性措施,坚决防范水运口岸疫情输入风险。此要求自该工作指南第5 版始规定至今,其中对出现疫情的船舶调后引航次序尚可解释为染疫船舶需进行更为严格的检疫与消杀,港口单位尚需时间组织工作,但对染疫船舶归属船公司的所有经营船舶均调后引航次序实与上述熔断举措同犯打击范围过大的错误。且较之于时间相对明确的熔断而言,调后引航次序的规定则相对模糊。次序是根据受染情况按标准调后,还是所有牵连船舶无论轻重均直接调至最后一位,被调后的染疫船舶在等待引航时是否可以同时进行检疫及紧急的医疗救助等问题是船员所关心的。
江苏省《关于建立水路口岸涉外疫情防控熔断机制的通知》第15 条规定第一入境口岸应保障中国籍船员“应换尽换”,但并未保障外国籍船员“应换尽换”,证明我国在对船员换班问题上并未做到一视同仁,在便利外籍船员换班责任的承担上有所欠缺。且该通知对口岸未尽到中国籍船员“应换尽换”责任和码头单位防疫措施不规范的处罚均是7 天以上禁止该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停靠。对口岸单位的处罚,无辜殃及计划靠港的国际航行船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办法》第25 条可知,对违反本办法和有关卫生法令、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境口岸卫生检疫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处罚措施。因此,口岸单位的过错承担主体应是其本身,不可累及其他无过错方。江苏省该文件的确构建了防止病毒的“铜墙铁壁”,但口岸防疫不力的过错却由即将停靠该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买单”,且较长的整改时间也让江苏省在疫情防控下有避责之嫌。
2.国家间换班接续政策阻碍
新加坡最新的港口海事通告自2022 年4 月1 日起生效,规定完全接种疫苗的海员可作为短期游客进入新加坡,但未接种疫苗的上、下船海员最多在新加坡指定临时处所停留24 小时。[5]加拿大规定海员无论是否完全接种疫苗,只要提供出发前72 小时内核酸检测与血清抗体检测(以下简称“双检双测”)均为阴性的报告,且无感染症状,则可进出加拿大境内,无隔离要求。[6]两国防疫政策迥然不同,也代表了国家防疫的两个方向。
据我国对海员在他国登陆后需遣返赴华的一般规定,海员应在赴华航班始发国进行14 天的隔离闭环管理且登机前双检双测皆为阴性。如此,国家间对换班下船接续措施规定的时间冲突使得我国未完全接种疫苗的海员在新加坡无法正常换班下船。而于入境换班上船的海员而言,只要未被推定为携带新型冠状病毒,加拿大不仅不要求其必须接种疫苗,且对其入境前后均未做任何隔离规定。众所周知,仅是检疫并无法保证海员处于绝对未受染状态。故,检疫后径直离开或入境登船前仅做检疫都将极大地增加受染病毒但处于病毒潜伏期的海员在遣返或船上作业过程中传染病毒之可能。若将可能感染的海员遣返回不同的国家,则病毒将会呈放射性扩散,感染地区将大幅度增加;而若让可能感染的海员登船远航,则整艘船将会成为“病毒的天堂”。同时,因各国间防疫形势与政策的变化,国家间的航班熔断也时有发生。航班稀少,要想回国常常需等数月,使得每换一名海员就要花费数万美元,[7]航班遣返成本急速增加。
各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或“严防死守”,尽量规避海员可能携带病毒在本国传播的风险,减少本国防疫压力;或“放松大意”,为减轻本国检疫压力而无视海员间病毒传播风险。但在疫情容易反复,变种病毒不断出现,海运至关重要的情形下,衡量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海员群体切实的保护和关怀尤为必要。
3.实践中海员换班执行障碍
2021 年8 月9 日,一艘名为Formosabulk Clement 的大型船舶上的中国籍大副在澳大利亚开放海域换班下船时出现意外,落水而亡。该轮原本应在目的港——澳大利亚的Newcastle 港平稳靠泊码头后进行换班作业,但该港所在新南威尔士州疫情防控期间禁止国际海员在该港上岸。无奈之下,该轮只能铤而走险,在允许海员下船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开放海域进行海员换班工作,但因开放海域风浪太大,船舶碰撞,中国籍大副不幸落水而亡。[8]
见微知著,上述案例直接反映了当前国际海员换班受阻的现状。探究事件发生的根源,两个问题尤其突出:一是区别对待现象严重。部分国际港口仅保证本国籍海员应换尽换,对外籍海员则是能推则推。二是部分国际港口过度执行管控措施,“防毒”变“防人”,错误地将防止病毒境外输入风险的任务认为是防止一切染病或者可能染病之人进入的任务,“一刀切”式地直接拒绝染疫船舶停泊换班。“外防输入”作为当下国际疫情防控的重要着力点之一,防控对象应该是深层的病毒输入而不是浅层的人员进入。在对疫情的防控中,相关国家不应一味地注重封闭性的防止,还应当注重疏导性的控制。
(二)海员疫苗接种困境
截至2022 年3 月20 日,全球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比例不到57%,在低收入国家该比例甚至不到12%,[9]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持续流行的风险依然很大。海员作为各国之间货物运输的枢纽,是否接种疫苗对航运的安全至关重要,但实践中海员的疫苗接种却困难重重。
1.疫苗种类繁多造成接种周期长短不一
截至2022 年3 月22 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认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清单共有九种疫苗。其中只有Johnson 是单剂疫苗,阿斯利康、辉瑞、Moderna COVID-19、CovovaxTM、Sinovac、Nuvaxovid、中国国药COVID-19 疫苗和科兴均是两剂次的疫苗,同一种类两剂疫苗间隔时间最短为Sinovac,间隔时间为2-4 周,最长为阿斯利康,间隔时间为8-12 周。[10]对于计划上船的海员,须提前安排疫苗接种计划,尽早进行疫苗接种工作。但在全球疫苗接种比例不足60%且部分国家未将海员列为疫苗优先接种对象的情况下,要求即将上船海员均应尽数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多有困难。若接种第一剂疫苗后即换班上船,可能无法及时进行第二剂疫苗的接种,从而超过最长间隔期限,导致疫苗防护效力逐渐降低。对换班下船计划遣返的海员而言,即使能在遣返起始国接种疫苗,在考虑疫苗接种剂次全部完成所耗的时间成本后,归心似箭的海员对疫苗接种的意愿或有所降低。若只接种第一剂次的疫苗,回国后也存在无法保证能继续接种到第二剂次同一种类的疫苗的可能。基于多数疫苗接种剂次间隔周期较长,单剂次的疫苗难以大量供应,海员完成疫苗接种工作难度大。
2.多数国家将外籍海员排除于接种疫苗之外
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海员中只有25%接种了疫苗,[11]这与多数国家仅为本国海员接种疫苗,将外籍海员排除在疫苗接种的范畴外不无关系。海员作为全球货物运输者,连续在船时间较长,且部分海员并未常住国籍国,因此,在国籍国完成疫苗接种难度较大。但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暂时未开放对外籍海员的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尽管美国、新加坡、德国汉堡市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始不分国籍对海员进行疫苗接种,但面对庞大的海员群体,少数几国无差别的疫苗接种活动进程缓慢。③同时对部分低收入的港口国家而言,本国公民的疫苗接种尚需对外购买或者国际援助,更无力承担对外籍海员的疫苗接种任务。即使效仿新加坡对外籍海员使用由国际海事组织或者航海业者提供的疫苗,但由于本国医疗资源的紧缺,也无力承担大量海员的疫苗接种工作。因此,虽不分国籍接种疫苗对即将上船的海员而言,增强了其抵御病毒感染的能力,减少了海员交叉感染的风险,有利于海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但基于各国的不同情况,想要建立全球港口国家均不分国籍地对海员进行疫苗接种的防疫模式难度较大。
3.部分国家缺乏疫苗研制能力且无力承担大量的疫苗购买费用
根据国际航运公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简称ICS)统计,约有90 万海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占据全球海员的半数,而这些国家可能要等到2024 年才能实现大规模病毒免疫。[12]部分港口国家的科研能力不强且经济并不富裕,但新冠疫苗并未完全实现知识产权豁免,故其既无法自行研制可供国内紧急使用的疫苗,又无力购买国家间认可度较高的疫苗。[13]因此,在国内新冠疫苗供应紧缺的情况下,倡导海员优先接种疫苗无异于“天方夜谭”。
4.部分国家之间的疫苗不互认造成海员接种合适疫苗难度大
除世卫组织公布的九种可紧急使用的疫苗外,部分国家国内也研制了其他单剂次、两剂次或三剂次的疫苗,但尚未获得世卫组织认可。[14]然而,即使是世卫组织认可的疫苗也可能遭到部分国家的拒绝承认,造成不同疫苗存在国家间不互认的现象,海员接种之后仍可能在未互认国家面临被禁止进行装卸作业、换班等工作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对于外籍换班上下船的海员而言,若接种自己即将遣返或入境的国家并不认可的疫苗,回国或入境后仍需隔离,且有被要求再行接种目的国认可的其他疫苗之可能。因此如何保障海员接种到关联国家互认的疫苗,破除海员在疫苗接种后换班、遣返仍受限制的困境尚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二、海员换班的理论支持与困境
现行《国际卫生条例》《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以下简称《海事劳工公约》)等国际文件为港口国组织海员换班、遣返工作及提供适当医疗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持,但由于疫情下各国采取“自保措施”,且现在并无针对成员不适当履行义务的制约机制,因此理论难以指导实践。
(一)对未染疫船舶的靠港换班的理论支持
《国际卫生条例》第28 条第1 款规定除第43 条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之外,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同条第2 款规定除第43 条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之外,缔约国不应当出于公共卫生理由拒绝授予船舶 “无疫通行”,特别是不应当阻止上下乘员、装卸货物等必要工作。由此可知,在船舶防疫得当并无任何疫情情况下,港口国无其他正当理由不应拒绝未染疫船舶的靠港换班。其中的无其他正当理由可解释为无任何能证明船舶靠港工作将对港口造成疫情输入风险或船舶存在靠港手续不规范及口岸疫情不可控等确实不适宜船舶靠港情形的理由。虽“无疫通行”制度存在两项例外情形(第一,若入境口岸不具备执行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的能力,可命令船舶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驶往可到达的最近适宜入境口岸,除非该船舶存在会使更改航程不安全的操作问题;第二,根据该条例第43 条第1 款规定,当发生特定公共卫生危害或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缔约国可采取第28 条原本禁止的“额外的卫生措施”),但除疫情中的高风险地区可能无法执行标准的卫生措施外,其他港口的正常开放足以证明其具备实施相应卫生措施的能力。且该条例同时规定,“额外的卫生措施”对国际交通造成的限制以及对人员的创伤性或干扰性不应大于可合理采取并能实现适当程度保护健康的其他措施。在病毒肆虐的情况下,若染疫风险可控的港口拒绝未染疫船舶的靠港换班,将会极大增加该船舶在更改航程途中的染疫风险。故风险可控的正常开放港口无正当理由不应拒绝未染疫船舶的靠港换班工作。
(二)对于染疫海员进行救助的理论支持
根据《海事劳工公约》规则 4.1 船上和岸上医疗第1 条规定,各成员国应确保在悬挂其旗帜船舶上的所有海员均被保护其健康的充分措施所覆盖,并且他们在船上工作期间能够得到迅速和适当的医疗。由此明确了船旗国应当为海员医疗救助义务的第一承担者。但通常情况下,受感染海员在被感染或者感染症状显现时并不在其船旗国的管辖范围内甚至相距甚远,而新冠病毒潜伏周期长、传染性强、症状发作快,受感染海员在症状发作后或没有足够时间等待来自“大洋彼岸”的救援。同时,根据《海事劳工公约》规则 4.1 船上和岸上医疗第3 条规定,各成员国应确保在其领土内的船舶上需要紧急医疗的海员能够使用成员国的岸上医疗设施。此条文中的领土应理解为扩大含义,即包括领海在内的领域。且该条规定并未特别注明应分国籍对海员提供紧急医疗,因此,在《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缔约国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阻止船舶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的情况下,若港口国风险可控,则船舶在停靠该缔约国港口的同时,任何国籍的染疫海员均可使用成员国岸上的医疗设施。同时,《海事劳工公约》规则4.1 船上和岸上医疗第4 条规定需向海员提供尽可能相当于岸上工人能够得到的健康保护和医疗的措施标准。综上所述,船旗国对海员具有主要的救助义务,但在救助无法及时实施且由离船较近的成员国进行救助更为及时和有效的情况下,港口国应当为染疫海员不分国籍地提供与岸上工作人员相同标准的医疗救助。
(三)海员换班遣返的理论困境
由以上论证可知,海员无论是否受染,均有权在风险可控港口进行合规的靠港换班工作。船舶的换班可能会涉及后续的遣返问题,外籍海员换班后又常遇遣返困难。《海事劳工公约》 标准 A2.5.1 遣返第5 条(a)规定船舶有权悬挂其旗帜的成员国(以下简称“船旗国”)的主管当局应安排有关船员的遣返;如果它未能这样做,海员将被遣返起程的国家(以下简称“遣返起始国”)或海员为其国民的国家(以下简称“国籍国”)可安排该海员遣返,并向船舶所悬旗帜的成员国收回遣返费用。此条明晰了船旗国对海员遣返的主要责任,同时也规定了海员遣返起始国与国籍国对海员遣返工作承担的补充责任。但海员遣返起始国与国籍国替代船旗国承担海员遣返的效果仅是有权要求不履行义务的船旗国做出费用偿付,偿付金额与所支出的费用一致。然而,对船旗国不进行偿付时的救济措施仅为滞留或要求滞留有关船东的船舶,直至其按本守则标准进行偿付。显然,替代船旗国遣返海员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且若是船旗国、遣返起始国、国籍国等相关国家均不履行遣返海员之责,如果对谁负责有疑问,法律诉讼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解决问题。[15]现行国际法框架下并无对船旗国等相关责任主体不履行遣返义务时的强制约束性的罚则,也无相关对遣返起始国等积极帮助海员遣返的激励措施,海员遣返权利受侵害后救济困难的情况或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将更为严重。
三、海员换班困境的应对策略
疫情全球化背景下,从根源消灭病毒尚需国际国内双重努力,海员换班难题也应从国际国内两处着手。国际层面各国应相互配合,勠力同心,协力解决海员换班遣返、疫苗接种等责任的划分,推动构建全球海员换班信息系统公开平台;国内层面应加强各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切实提高港口城市疫情防控的专业能力,同时落实疫情下的执纪监督,推进尽职免责和避责惩罚并用体系。
(一)划分国家间对海员遣返及疫苗接种工作的责任
建议我国以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永久政府席位拥有者身份提议国际劳工组织进行《海事劳工公约》的讨论修订工作,细化公约规则2.5 遣返及规则4.1 船上和岸上医疗的内容,补充遣返、医疗方面海员权益在全球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的实现方式,划分国家间对海员遣返及疫苗接种工作的责任,即由海员遣返起始国承担海员换班下船后的闭环隔离及双检双测之任务,居住国承担海员疫苗接种之责任。具体而言,在海员换班下船后,由海员遣返起始国对海员在口岸隔离点进行14 天的闭环隔离,并在海员乘坐遣返航班之前进行双检双测,在确保海员未受感染的情况下,可要求海员径直乘坐航班离开。海员到达居住国后,居住国按照一般旅客回国的程序进行防控即可。如此,有利于确保海员在乘坐返回居住国的航班时不会携带病毒进行传播,也减少了海员归家之后的检疫程序。但此项建议需以其他类型旅客在乘坐航班前进行14 天闭环隔离与双检双测结果均为阴性为基础,以避免在航班上的交叉感染。同时,由此造成的部分遣返起始国隔离、检测等压力或可进行分散缓解,即受益国家对遣返起始国进行适当补偿或支援。
遣返起始国对本国的海员毫无疑问负有绝对的责任,但对外籍海员,该海员纳税国中的居住国或者国籍国可选择以下三种方式对遣返起始国进行支援:第一,给予遣返起始国相应的资金以帮助其对海员进行妥善的处置;第二,派遣直升机等飞行器将海员接回并自行进行隔离;第三,由国际海事组织统一成立海员检疫隔离基金,专门用于补贴港口国家的海员检疫隔离工作。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当务之急不应是思考如何避免海员入境以减少病毒传染风险,而应思考国家间积极合作,制定有效的抗疫合作机制,使海员能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健康安全地从事海上工作,各国间的货物贸易也能顺利进行。此外,海员纳税国中的居住国或者国籍国对遣返起始国进行资金支持也是对遣返起始国代替自己进行海员闭环隔离的对价补偿。对于海员存在较为分散、补偿主体较多的情况,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按照一个年度内工作海员的大致比例向该基金缴纳预存资金,以帮助在其他港口登陆的本国海员回国前顺利进行闭环隔离。对部分换班遣返人数较多的港口,为减少港口隔离压力,或可借鉴我国上海港将隔离三天的海员闭环转移至相邻省份进行继续隔离的做法,[16]以保障海员闭环隔离的有效推进。
(二)增强国内口岸单位组织接受海员换班的积极性
可对尽到应检尽检、应查尽查的口岸单位实行免责,对既做好防疫保护又有序进行船舶换班工作的单位进行激励,对无正当理由逃避责任的单位进行一定处罚。在国内严格的疫情防控框架下,口岸单位拒绝靠港海员进行换班工作的最大顾虑应是出现疫情输入后被问责。避责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官员面对当前或未来负面事件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17]出于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株防疫的担心,部分口岸单位为尽量避免自己在即使做到全流程防控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口岸疫情输入的可能性,避免可能会被处罚或问责的风险,对靠港船舶中可接受或可拒绝的船舶多会选择拒绝,对即使允许停港船舶上的海员换班批准也较为严格。但全球防疫想要取得切实的效果,重点应在疏而不在堵,即应注重检测、控制与治疗,而不是逃避与拒绝。例如在防疫前线的海关应充分发挥监督检查作用,立行立改,确保疫情防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强化口岸人力资源调配,多种方式开展培训和实操演练,切实提升疫情防控的专业能力。[18]防疫能力建设与执行监督并行,正面激励和负向惩处并用,可以打破问责力度越大、避责越多的怪圈,[17]构建所有港口正常有序地实现海员换班遣返的体系。
(三)构建全球海员换班信息系统公开平台
建议我国以国际海事组织A 类会员国身份在该组织中提议加强与世卫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快构建包括港口卫生信息在内的全球海员换班信息公开平台,为海员的顺利靠港换班增添助力。《国际卫生条例》第5条第4 款规定,“世卫组织应当通过监测活动收集有关事件的信息,并评估事件引起疾病国际传播的潜力和对国际交通的可能干扰。将根据第十一条并酌情根据第四十五条来处理世卫组织按本款收到的信息”。世卫组织所掌握的各国卫生安全数据较为全面、及时且权威,国际海事组织可加强与世卫组织的合作,通过世卫组织获取港口国家疫情传播情况和港口防疫情况,与世卫组织共同评估疫情对国际交通的可能干扰。同时授予成员国及时更新本国各港口防疫政策的最新规定的权限,且将最新讯息及时传送给在相关港口有停泊换员计划的船公司,以方便其在目的港防疫形势严重的情况下尽早更改船舶换员计划。同时,根据船公司提前上传的计划停靠港口与船舶大致停靠时间,由国际海事组织与世卫组织合作向港口国家进行资金补贴和物资援助,以帮助港口国顺利完成换班海员的闭环隔离任务。不分国籍对海员进行疫苗接种的国家应在系统内注明向外籍海员提供的疫苗种类,由外籍海员自行选择接种或者不接种。
加强与各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及时获取各成员国的港口防疫力量数据,并向即将停靠该港或者计划停靠该港的船舶建议在有受染海员的情况下,尽快驶往就近港口中医疗力量相对较强的国家寻求医疗援助。对即将有大量海员登陆但是该国医疗资源紧张的国家,国际海事组织应及时寻求世卫组织或者其他相关资金组织的资助。
建立疫情下的国家同等对抗机制,对于不积极履行甚至逃避履行海员换班责任的港口国家,或可在该信息平台上进行及时披露,各国可对不履行责任的国家进行同等对抗——拒绝该国海员在任何国家换班遣返,通过民众倒逼政府履行责任的途径实现海员全球换班机制的建立。
病毒“越治越少,越推越多”。目前疫情防控在形式上是隔离,本质上却是关联。[19]新冠病毒变种毒株不断出现,全球防疫网却迟迟未成功建立,这对全球疫情防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航运运输包括了重要的医疗用品、食品和其他对COVID-19 应对和恢复至关重要的基本物资。[20]海员作为全球贸易的媒介,对他们在疫情下的有效保护也是对全球贸易的有效保护。促进海员在疫情下换班遣返、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进行将有利于海员继续为全球运输防疫物资、推动国际防疫网的尽早建立。风险总是和机遇并存,对于病毒境外输入的重大风险,应着力防范化解,做到未雨绸缪,做好预防和处置“两手”准备,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1]我国或可通过国际组织积极促进全球海员换班信息交流系统的构建,给出划分国家间对海员遣返及疫苗接种工作之责任的方案,积极搭建国际防疫合作平台,同时完善国内相关政策制度,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积极承担组织力量进行海员换班遣返的国际义务,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
注释:
①此处的当然责任可解释为对某事物起着关键作用且应承担法律、条约或职务等规定义务的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疫情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出台了不同的防疫政策,而海员在疫情下仍需承担全球货物运输工作,国际间的流动性较大,也是各国在防疫政策制定时应当考虑的重要群体。各个国家对海员换班的顺利进行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且负有根据《海事劳工公约》等国际条约促进海员顺利换班的义务。故国家对海员换班负有当然责任。见陈良安:《肺癌早诊早治是呼吸学科之当然责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8 年第10 期。
②四次熔断原因均为“AKIJ MOON”轮(IMO 编号:9300506)等24 艘轮船上多名海员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呈阳性,暴露出船舶及其航运公司未能有效履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责任,核酸检测呈阳性的在船船员数量达到有关暂停船员换班的规定要求。熔断结果均为自通知发布之日起15 或30 天内禁止包括“AKIJ MOON”轮管理公司Akij Shipping Line Ltd 在内的24 家过错船舶管理公司所属531艘船舶在我国境内港口开展外籍船员换班。见交海明电第8号,交明海电[2021]76号、交海明电[2021]111号、交海明电[2021]147 号、交海明电[2021]204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官网。
③以新加坡为参考,4 月—11 月,为8 000 多名外籍海员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计算可知新加坡为外籍海员接种疫苗速度为每天约34 人。但在任何一天,全球约有100 万海员在大约60 000 艘大型货船上工作,而船上的平均国籍至少为三个国籍,有时甚至多达三十个,外籍海员群体庞大。见《新加坡将为外籍海员提供额外12 000 剂疫苗》, 载海事服务网,2021 年11 月17 日。见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how COVID-19 is impacting seafarers,载国际海事组织官网,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ages/FAQ-on-crew-changes-and-repatriation-of-seafarers.aspx。见Shipping industry demands vaccine priority for seafarers amid renewed crew change struggles,载国际航运工会官网,2021 年1 月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