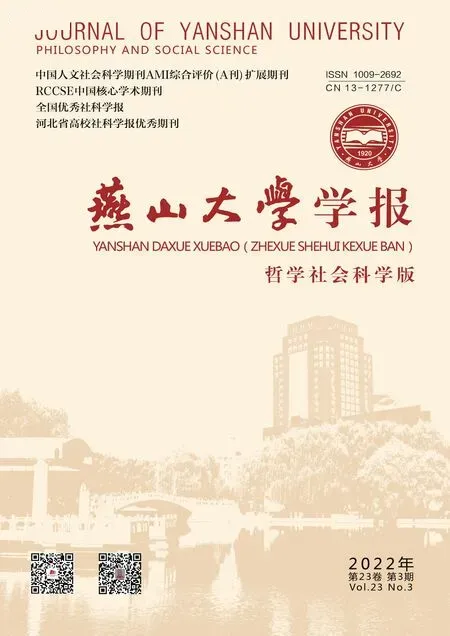典籍典译:《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张秀仿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民族典籍英译是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部分。民族典籍,尤其是民族文学,通过翻译途径借助“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的资助,能够实现对外文化交流的愿景。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力支持民族典籍译介与研究,尤其是在民族史诗的英译与研究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成为中华学术著作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中国典籍译介事业孜孜不倦,挚爱一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2020年李正栓教授的新著《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出版,对藏族典籍英译与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首先,《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是一部民族典籍译介与传播的经典之作,对深入理解藏族格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认识藏族格言诗在文学史、哲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这部著作收录的《国王修身论》汉英双语对照文本以汉英藏三语形式在尼泊尔天利出版公司出版,对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藏族格言诗、近代藏族社会文化以及藏族人民的智慧有很大的帮助。最后,这部著作的体例结构、研究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产生的影响,为通过典籍翻译实现文化交流目的提供了范本,尤其是在民族典籍英译领域,译者身份、英译原本的传播与翻译史、翻译策略和原则等具有普遍性特征和研究价值。
因此,本文将以李正栓教授的新著《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为例,从译者、译本和译论三个方面,探究民族典籍英译的典型性对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民族典籍英译者的典型性
民族典籍译者的典型性是指从事民族典籍翻译译者的典型特征,主要包括译者的能动性、研究意识和文学素养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一)能动性
虽然典籍翻译非民间自发行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政府机构牵头和组织的中外译者是其发展的主要力量”,但译者的能动性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本文所说的能动性,借鉴了查明建教授对译者主体性的阐释与定义:“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2]
具体而言,译者的能动性,是指心怀促进文化交流的愿景,数年如一日地执着于典籍英译,特别是民族典译翻译与传播事业。《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成书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萌生的想法。根据有关《格丹格言》翻译与传播情况的论文记载,译者“从1979年开始更加集中地注意到西藏,但对西藏产生浓厚兴趣却是从阅读西藏格言诗开始的”,并且发现藏族格言诗在英译领域还存在着诸多空白,“想把中国宝贵的藏族格言诗文化介绍给全世界,让更多人感受藏文化所特有的魅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3]自此之后,李正栓教授致力于典籍英译与研究,与汪榕培教授一起组织典籍英译研究学术活动,促进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并在汉乐府和毛主席诗词英译方面出版相关著作。
从确立促进藏族文化的传播到2013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萨迦格言》译本,译者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执着付出与十年磨一剑的坚持。在不断坚持与努力中,译者除了翻译能力得到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典籍的研究与理解中培养了研究意识。
(二)研究意识
研究意识是典籍英译者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在翻译过程中总结翻译策略,将翻译实践升华为翻译理论与原则,以促进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翻译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发展,都伴随着译者对于翻译实践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提升。如道安翻译佛经提出 “五失本三不易”原则,严复翻译《天演论》提出“信达雅”标准,钱钟书先生翻译文学作品提出 “化境” 理论等。因此,面对浩瀚的民族典籍,不仅需要学贯中西的开拓者,也需要更多后来者借鉴前人的经验和理论,积跬步以至千里。
换言之,研究意识是译者对中国悠久译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的体例结构涵盖了中华民族典籍传播的翻译学研究的两个部分,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前者为历史研究、译学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及跨学科理论研究,后者为传播学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批评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等。”[4]通过研究,译者结合文本分析,对翻译策略或者风格展开探讨,使翻译过程可视化,使译著成为翻译学的经典。
(三)文学素养
文学素养是民族典籍英译译者的重要特征。民族典籍主要是通过译介民族史诗或者是格言诗实现中外文化交流的目标。这些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哲理性,对译者的文学素养和表达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在民族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成果中,藏族典籍以《格萨尔》史诗、藏族格言诗和仓央嘉措的诗歌等民族文学作品为核心。同样,北方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和西南少数民族英译也是以民族史诗英译为核心。[5]
从民族典籍翻译史的角度来看,民族典籍英译事业的中坚力量大多是英美文学的研究者。他们不仅具有坚实的双语功底,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在汉语文学典籍英译方面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李正栓教授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诗歌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之后,在乐府诗歌英译和毛主席诗词英译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成为21世纪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二、民族典籍英译原本的典型性
(一)传播力
民族典籍,尤其是民族史诗,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载体,深受本民族的喜爱和欢迎。但是,民族典籍是否能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通过翻译途径进行传播,不仅要取决于译者的素养,更取决于民族典籍的生命力,即取决于在国内与国际的传播力。民族典籍的国内传播力是指民族典籍被译介为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被读者阅读和接受,成为促进文化沟通交流桥梁的能力。
通常来说,民族典籍的国内传播主要是依靠精通民族语言、文化和哲学的学者,在多年对民族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民族文学作品翻译为汉语。例如,在藏族文学汉译领域,王尧、于道泉、耿予方和次旦多吉等民族文化的研究者,翻译了大量的藏族文化典籍。王尧先生翻译的《萨迦格言》,是20世纪50年代跟随贡噶仁波切学习时的心血译作。
正是这些倾其一生研究民族文学的学者,使更多的读者通过汉语阅读民族典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为民族典籍走向世界构建了一座座桥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李正栓教授翻译仓央嘉措诗集为英文时,才能以于道泉先生(1901—1992)的汉译本为底本,将优美的藏族诗歌翻译为英文。同样,在译介藏族格言诗时,才能依据耿予方和次旦多吉的汉译本为底本(包括1986年出版的《水树格言·格丹格言》和1987年《国王修身论》)将更多的藏族格言诗译介为英文。早在1856年,外国译者从藏语直接将《萨迦格言》翻译为英文,但是直到国内汉译本出版之后,英译本的数量才急剧增加。如第一部是从藏语直接译成英语的乔玛选译本,ABriefNoticeoftheSubháshitaRatnaNidhiofSaskyaPandita(1855;1856);第二部是簿森基于《萨迦格言》的藏语版和蒙语版,即从藏语和蒙语译成英语的博士论文,把格言诗翻译成散文;第三部是1977年由塔尔库(Tarthang Tulku)依据乔玛译本进行诗体翻译、校对和整理的译本;第四部是达文波特直接从藏语到英语的译本。[6]5
从汉语转译民族典籍,一方面说明英译者没有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民族典籍在汉语语境中也能得到读者的认同,其传播力和接受度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这有利于拓宽民族典籍英译的范畴,促进民族典籍在世界的传播。
因为经由汉译本将藏族格言诗翻译为英文的翻译过程具有两个特征:“优势在于经过深思熟虑或集体研究汉译的藏族格言诗已经具备了较规范的现代文本和整饬的艺术体现形式,但藏语原文的个人风格往往难以确认,英译者只好信赖汉译者”。[6]232从翻译实践来看,译者不仅需要从风格来鉴别汉译者的译文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对汉译本中伦理价值的认同。
(二)伦理价值
伦理思想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的进程中,藏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积淀,日趋完善,底蕴深厚,别具一格。这些思想观念既反映了当地的社会习俗风貌,又体现了汉藏两个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
《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诗的伦理思想和文化内涵。比如,《国王修身论》第14首和15首,探讨了学问对国王的重要性。
国王只在境内称雄,
学者到处都受尊重。
学问比起地位有益,
每人都可学到手中。
A king rules only within his borders,
A scholar is respected everywhere.
Learning is more useful than position;
Everyone can acquire it as his own.
学问可下功夫学好,
但是不会自然来到。
那些憎恨学者的人,
呜呼总被业力所拋。
Through hard work learning is gained;
It can never be gained without pain.
Those people who hate scholars
Are always abandoned by Karma.[6]24
(三)文化价值
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实行了微格管理,大到翻译原则,小到翻译“佛”字眼儿的翻译,都是有据可循,有章可依,但是又不照本宣科,而是顺势而为。以《国王修身论》中第456诗节中“佛法”的翻译为例。李译本借鉴了达文波特的翻译方法,使用了(Dharma)。如第44 首借鉴(梵文的)箴言,使其表达自然流畅,从而使“Dharma”与“sutra”押韵,实现音韵对等。
佛法解脱从何而来?
要靠智慧攻读经典。
有了经典若不运用,
那同牲畜完全一样。
How can people be freed by Dharma?
Wisdom is required to read sutra.
If a manlearns the sutra without assiduity,
He is like a farm animal rather than a man.[6]245
在《萨迦格言》中,李译本将佛法翻译为“Holy Buddha”:
只有通晓世间的一切,
才能实施神圣的教法;
因此实施教法,
是菩萨的天职。
Only when one knows the world well,
He can implementthe power of Holy Buddha.
And thereforeBodhisattva is the soul,
Who has put it into effect indeed.[6]67
由此可见,民族典籍能否走向世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取决于译者的能力和素养,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传播力、伦理价值和文化价值,能够通过译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民族典籍英译策略的典型性
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民族典籍英译应该尊重“忠实对等”原则[7]。为了实现文化融通和交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尊重动态平等的文化价值观,构建通顺易读的译文文本。民族典籍英译策略的典型性,体现在对等原则的四个层次:在文化交流层次,坚持忠实对等原则和文化专有项补偿策略;在文体类型层次,坚持以诗译诗;在语言层次,追求自然流畅。
(一)坚持忠实对等原则
从国内外翻译史发展来看,忠实对等地传递文化是指译者解决文化杂糅与交融引发的翻译问题采用归化的策略和异化的策略。
同时,忠实对等包括两个方面:直接忠实对等,即译文与原文的对等;间接忠实对等,即英译文与汉译文之间的对等。用文学翻译家北塔先生的话来说,“间接忠实对等是指在第二语言(此处指汉语)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对等,即将藏语文本先译成汉语,然后再将汉语本翻译成英语。这种间接忠实对等保证了译文风格的统一,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8]因此,藏族格言诗英译应忠实对等地理解原文,包括结构特点解读、思想内涵解读、艺术魅力赏析和社会历史文化解读。
(二)对文化专有项采用补偿策略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民族典籍翻译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因此,为了实现文化平等沟通交流的目标,民族典籍译者在涉及原文民族文化形象时,应“努力保留这种形象,再三权衡,力戒随意性,避免过度归化”,对文化专有项采用补偿策略[9]。具体而言,文化补偿策略包括三个层次,语言补偿、文化补偿和交际补偿三个方面。这种补偿策略,接近于胡庚申教授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三维转换法”,即“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10]。
一般来讲,语言补偿比较容易操作且广泛使用。在“语言层面,译者可以通过词汇、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体等多种形式进行选择转换,并采用加注释、增译、略译、泛化、明晰化等语言手段”[11]。
在李译本中,为了实现以诗译诗的目标,通常采用意译、直译或音译等策略填补文化空缺。如在翻译《水树格言》第135首时,译者对其中涉及四的词汇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分别译为“Four Joys”,“Four Emptinesses”和“Four Rivers”。中文原文和英译文如下所示:
四喜的先天之福上升;
四空的聪明才智横生;
四河的清水川流不息;
南海的马口烈火熊熊。
The predestined fortunes of Four Joys rise;
The wisdom of the Four Emptinesses flourish;
The water of Four Rivers flow constantly;
The blazes of South Sea burn fiercely.[3]193
(三)坚持以诗译诗
以诗译诗,是于道泉先生在翻译藏族格言诗采取的策略,以诗歌的形式,将文学形式传承下去,是藏族格言诗能够吸引更多读者的重要因素,这也是藏族格言诗英译的重要缘由。
以诗译诗,可以保持音韵美。在英译过程中,“用韵对等往往取决于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才学水平,还有灵光一现的发挥状态”,“在翻译中能押韵时要押韵,不能押韵时不强求”。[6]209如在翻译《国王修身论》时,李译本尽量保持原诗歌的音韵模式,传递原诗意义。如第六章《真言授记》的第43首的翻译:
那些妖魔精灵鬼怪,
散布瘟疫危害四方。
生命财产变得渺小,
只有制止方有安康。
Those demons, spirits and ghosts
Spread pestilence to do harm with disease.
The lives and property are decreased;
Only stopping it can bring health and peace.[6]301
该诗的汉语译文的押韵是,第2行和第4行押韵,译文没有做到用韵的格式完全对等,但是还是做了补偿,在第2行和第3行押韵,即“disease”和“decreased”。即使押不上韵,还是尽量地贴近。
同样的翻译策略在第44首也得到了体现:
倘若国王变成暴君,
人民痛苦火热水深。
虽然谁也不能治罪,
但是必然自毁其身。
If the king becomes a tyrant,
People are plunged into dire suffering.
Though none can punish a tyrant,
He willfall inevitably into self-destructing.[6]301
在汉语译文中,这首诗是1211的押韵模式,因而译文也竭力遵循押韵的格式,但用韵的模式截然不同。英文译文采用了第1行和第3行完全对等尾韵(exact ryhme)的“a tyrant”,而第1行和第4行则以suffering和self-destructing,为近似韵脚(slant rhyme)的押韵模式。
(四)追求语言自然流畅
从文学形式来讲,格言诗是一种民歌体,通俗易懂,但是藏族格言诗又有其独特的佛教文化特征,如何实现文学性、哲理性和佛教思想的结合,需要译者深思熟虑的选择,能够沟通陌生的世界,然后实现互通互融,使这种具有哲理表达的诗歌方式能够成为世界文学中重要的部分。
从《萨迦格言》到《国王修身论》,藏族格言诗的生成年代从12世纪到19世纪跨越了六个世纪,其语言风格和词汇等方面都有了很多变化。对此,译者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标准的阐释,“我们认为,只要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并对原文的形式有所兼顾,译文读起来流畅自然,朗朗上口,便称得上是成功的译作”[6]235。
李译本的语言标准是具有可读性和音韵美,而这种音韵美不仅仅体现在韵文,而是能体现自然语言的美。求用韵对等,不是强求绝对的用韵对等,乃至因韵害义,而是竭尽可能利用音韵和格律之美为译文增添韵味。
四、结语
历史证实,翻译浩瀚的民族典籍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够使“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中国故事丰富多彩历久绵长。《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民族文学的重视,更体现了译者对典籍英译事业精益求精的追求,对典籍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模式。
李正栓教授翻译历程和成就进一步说明汉族译者可以在民族文学典籍翻译方面大有可为,能够加快促进典籍翻译学发展的步伐。翻译尤其是典籍翻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浸润式成长。一个合格的译者是没有国界的,同时也是没有学术界限的。无论是注重学术注释,还是重视格言诗的文学性,都是通向藏族格言诗的研究路径。因此,民族典籍的译者除了语言的融会贯通,还要能够实现文学和文化的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