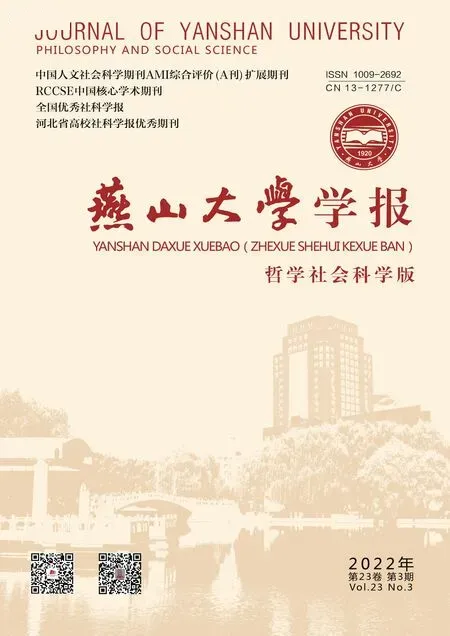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学实作与帝国主义
——以罗伯特·福琼游记为例
周建琼
(1.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一、引言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和分类等。[1]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博物学不仅被视为“大科学”(bigscience)[2]4,而且与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紧密联系,一起绘制出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版图。[3]博物学为学界考察近现代西方海外科学活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典型有效的路径。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对拉美、非洲等地的西方博物科考活动进行研究,①而对早期在华西方博物学研究,除了学者范发迪的《清代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著述外,鲜有深入细致的相关个案研究。西人在华博物科考活动晚于拉美、非洲等地,19世纪才渐成规模,加之19世纪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于作为西方殖民地的拉美、非洲等国家,西人在华的博物科考活动具有特殊性。本文旨在以罗伯特·福琼的游记为文本,展现西人在华博物科考活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张力。
19世纪西方列强对华发起侵略扩张,西人来华科学考察活动随之不断发展并进入高潮。众多西方科考人员在中国的领土上留下足迹,也用笔墨记录下了科学考察的过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著有《鞑靼西藏旅行记》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著有《中国——亲身游历和据此形成的研究成果》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著有《在中国北方各省三年游记》的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等。其中,博物学是当时西人致力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科考活动,吸引了从科学界、政府机构、海贸公司到殖民地官员的广大兴趣与支持。[2]4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是19世纪西方来华博物学家的代表人物,在来华之前,曾任爱丁堡花园的植物管理员,格外关注有关中国园艺和园艺方法的信息。1842年进入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eity)设立在奇斯维克(Chiswick)的植物园工作,任职暖室部主任。[4]257-270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先后受雇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东印度公司等,五次来华开展博物科学考察活动,采集移植了大量茶叶等具有经济价值的中国活株植物,其个人的博物活动与当时大英帝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并被称为植物猎人。[5]13
福琼除了在华博物考察外,笔耕不辍,将每次博物科考活动详细记录,撰写成数本游记,其游记兼顾文学性与科学性,被视为19世纪西人来华游记中科考类的典范。[6]2451847年出版第一部中国游记《在中国北方各省三年游记》(ThreeYears’WanderingsintheNorthernProvincesofChina);1852年出版第二部游记《中国茶乡之行》(AJourneytotheTeaCountryofChina:IncludingSung-loandtheBoheaHills)。为了迎合阅读市场需要,福琼将上述两次游记合为一部,于1853年出版《两访中国茶乡和喜马拉雅山的英国茶园》(TwoVisitstotheTeaCountriesofChinaandtheBritishTeaPlantationsintheHimalaya)。②1857年游记著作《和华人同居——内地,沿岸和海上》(AresidenceamongtheChinese:Inland,ontheCoast,andatSea)问世。1860至1861年间他游历了中国首都北京,同时还去了日本的横滨和东京,1863年出版游记《江户和北京:日本和中国首都纪事》(YedoandPeking:ANarrativeofaJourneytotheCapitalsofJapanandChina)。福琼的游记有着众多欧洲读者,兼具文学性与科普性。其中《在中国北方各省三年游记》在英国刊行时,赢得了专业人士和大众的一致好评,《泰晤士报》的书评如是写道:“若读者曾醉心于《汤姆叔叔的小屋》这被刺激的酒,那么我们推荐读者酒醒之后,……轻啜福琼温润的武夷茶。”[5]24与此同时,他对在华博物科考活动的科学客观详实记录,真实再现了植物考察采集工作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情感思想,并为他的科学观与中国观提供了隐晦的表达途径。
二、“沃顿盒子”里的活株植物采集
活株植物采集移植是19世纪博物学田野考察的重要内容。面对海外具有科学研究用途,特别是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博物学家们除了制作成标本外,还想方设法采集植物活株运回本国移植栽培。19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保存植物活株的工具和方法局限,采集到的植物活株很少能够被成功移植。为了提高活株植物采集移植的存活率,著名的用以远距离运输活株植物或者种子的沃顿盒子(Wardian Case)被发明。作为海外帝国植物学蓬勃发展的技术产物,沃顿盒子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异国植物抵达英国后的存活率。正是由于沃顿盒子的使用,福琼成功地把大量采集自中国的珍贵植物移植到了英国,出色完成了他的植物采集移植工作,成为有名的“植物猎人”。在这种密封玻璃容器出现之前,采集自中国的活株植物和种子往往很难生根发芽,以至于不少植物学家都怀疑是狡诈的中国人煮过种子或者给种子浸泡了药水。
在福琼的游记中,沃顿盒子常常被称为“玻璃柜子”反复出现,构成了福琼植物采集移植活动描写的重要意象。“我北上广州,从那里搭乘前往伦敦的约翰库珀号轮船,18个装满中国北方珍贵植物的玻璃柜子就放在这艘船的船尾”,“植物状况都很好,他们马上就被移植到皇家园艺协会位于奇西克的花园中去了”。[7]208这是福琼在游记中关于一次运输中国活株植物的描写。放在玻璃柜子里这些植物或者种子,绝大多数都能成功被移植到遥远的英国。利用这种玻璃柜子,福琼还发明了能提高存活率的远距离运输茶树种子的方法。“我准备了两个玻璃柜子……我把茶树种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掺杂在种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铺上这样一层泥土、种子的混合物……”[7]401福琼小心谨慎地打包好运往英国或是印度的数量众多的沃顿盒子,成为福琼采集转移中国植物的帝国博物实践工作的象征。
从福琼装入沃顿盒子里的植物品种和数量来看,福琼在中国的植物采集及其移植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博物知识的渴望以及科学研究的需要。具有商业经济价值是福琼采集植物的重要标准。如果说经济是殖民扩张驱动力,那么博物学无疑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投资。[8]62福琼采集的植物中,包括茶树、桑树以及果树等有较高商业价值的植物。福琼在上海附近发现了一种又大又好吃的桃子,他称之为“重要的植物资源”。[8]208福琼还将外皮可食用的小型柑橘类水果——金桔引入英国。金桔的英文名称以福琼的姓名命名为Fortunella,足以让他声名远扬。茶叶是福琼重点采集且贡献最大的植物。19世纪英国的中国茶进口量急剧增加,从1830年的3000万磅增长到1879年的1.36亿磅。[9]82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生产的商品用于茶叶贸易交换,从而导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了扭转英中茶叶贸易逆差,英国一方面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向中国输入鸦片,另一方面试图盗取中国茶叶树种及其制茶技术,将中国茶叶市场转移至英国殖民地印度。1834年英国成立了茶叶委员会,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树种子的可能性,在印度选择适合种植中国茶树的地区,并开展试验性种植。[9]89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丧失了对华茶叶贸易垄断特权,也开始积极参与到在印度种植茶叶的计划当中。福琼先后数次来华,为园艺协会、东印度公司甚至是美国农业协会等寻找茶树树种和树苗。福琼在1848—1851年期间,寻访杭州、松萝山、福州、徽州、武夷山等地,通过沃顿盒子成功运输23 892珠幼小植株和大约17 000 个发芽的种子至印度阿萨姆和锡金,在一次向印度西北邦植物园和政府茶园移交茶树时,福琼这样写道:“打开柜子的时候,所有茶树都长得非常好,柜子中一共有12 838棵茶树,还有很多还处在萌芽阶段”[7]404,移植至印度的茶树数量多到惊人。同时,福琼将数位中国茶叶技师带到印度,为东印度公司试图将中国茶叶市场转移至殖民地印度立下了汗马功劳。[10]
其它罕见稀缺的植物也被福琼放进沃顿盒子里。福琼多次在舟山群岛进行博物田野调查,主要在于“很多山陵与川谷都还处在一种原生状态,这儿的植物资源很丰富,让我满意的是,我还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植物,这引起我的极大兴趣”[7]34。福琼在宁波时,听说有一种黄色山茶花之后四处打听,说道:“如果有人能给我弄一株来的话,哪怕付出10块钱的高价我也在所不惜。”[7]49他进入中国官员们的花园中,为了寻找稀有物种。一位官员将自己视作珍品的园艺植物送给福琼,福琼拒绝的理由是“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而且我的植物收藏已经够丰富了”,而另一位官员送给他的园艺植物,他却欣然接受,“我得到的这些植物或者切枝当中,有一份部分属于稀罕品种”[7]52。这些来自中国的稀罕植物被福琼运输到了英国,种植在各地的植物园中。英国植物园中异域植物的繁盛与品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帝国海外势力强盛的标志。英国民众观摩欣赏这些来自中国等东方异域国家的稀有罕见的植物,除了满足对异国情调的好奇心,同时也满足着帝国扩张的欲望,强化着对于海外帝国扩张的支持和肯定,激发了由帝国主义所唤起的狭隘的爱国情感。
福琼在他的沃顿盒子中,放入的不仅仅是作为植物学意义上的中国植物,更是作为大英帝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符码。福琼的中国活株植物采集与转移,尽管具有一定的科学田野考察色彩,但更多的是以大英帝国的政治及经济利益为考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福琼来华从事植物学工作背后的赞助者所决定。福琼效力于皇家园艺学会、东印度公司以及美国专利局等机构,[4]257-270在19世纪,这些机构都带有帝国海外扩张的性质,海外植物学与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所言:“博物学探索及知识成为帝国扩展利益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吸引着政府越来越多的投入与资助,享受着政府和君主的庇护。”[3]然而,福琼在华活株植物的采集活动并非畅通无阻,由于中国具有独特的博物生态环境,加之西方人在华语言不通,行动范围受到局限等,想要获得植物活株,离不开中国助手的帮助。如若没有松萝乡的乡民们帮助——“那天他打来三株完好的植物,把她们都卖给了我,后来我把他们带回上海,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带到了英国”[7]262,福琼又怎能获得只见过一次的让他难忘的美丽小檗新品种?
三、西方博物学知识系统下的中国知识生产
福琼的游记中描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博物知识,包括动植物属性特征、地质风貌、水陆交通、土壤气候、农业生产加工技术等。福琼每到一个地方开展田野调查,都会细致记录上述内容。舟山群岛是福琼在中国开展博物田野实作的重要地区,福琼记录了舟山岛丰富的博物知识。舟山岛“有20英里长,10或12英里宽……”;“山上的土地属于肥沃的砾质土壤,山谷中的土地则显得更硬一些……”;“岛上出产苎麻,高约三四英尺,表皮含有强度很高的纤维,本地人生产并出售这种麻制品,制作绳索或船缆”;“油菜(一种油料作物)在5月初结籽……它是白菜的一种,花茎有三四英尺高,开黄花,接出来的长荚菜籽与其他白菜属植物相似”;“山野中常见的还有几种桃金娘属、杜鹃属植物,但石南属植物却一种也没有见到”[7]30-34等等。同时,福琼还记录了舟山人的晒盐方法、提取乌桕脂的方法(“采摘乌桕籽一般在11月或12月……蒸10-15分钟,蒸好以后倒入石臼里……”[7]38)和人工控温孵鸭法等。在福琼的游记中,中国博物知识除了被贯穿在旅程中,还会以专章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在第一部分的第六章记录了宁波附近的冰库、鱼鹰的捕鱼方法、鱼鹰的生活习性;第十二章记录了中国棉花的种植、分布地区、施肥方式、播种时间方法、采摘加工等;第十四章记录了山区土地、茶田、平原土地、夏季作物、冬季作物、庄稼的连续生产和轮作等;第二部分的第十四和十五章记录了武夷山土壤、茶树的种植管理、茶树地理分布、茶树树种、加工方式、气候、繁衍对茶树的影响等。
福琼对中国博物知识的记录过程也是对知识重新再生产的过程。福琼在记录中国博物知识时,总体上能够“把说话者和体验者的主观评价与形象要素的客观描述区分开来”[11],采取客观准确严谨的科学写作方式,呈现出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然而,他的记录是以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作为标准。福琼以西方博物学为原则,将中国的自然生态指标化,分析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按照林奈植物分类法(Linnaeus)中的属、类等描述动植物,林奈分类法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掀起了自然科学热潮,被视为西方博物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在知识描述时常常以英国的博物知识作为参照系,通过中英对比,描述中国的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在描述记录著名茶叶产区休宁县松萝山的地质特征时,他写道:“这一带的岩石主要由留纪石板构成,与英国发现的此类石板差不多……”[7]254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导致科学知识体系迥异。福琼始终以其已经具备的西方博物学知识体系,而不是中国自身的科学知识体系,对中国博物知识进行记录、描述。这一方面是由福琼的西方博物学知识教育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种西方科技优越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这是当时西方来华科考人员普遍具有的。在福琼的中国博物知识生产中,西方的博物学知识体系以一种强势的姿态,作为认知论上的权威,将中国博物知识纳入到他们的书写叙事规范当中,操纵宰制中国的博物知识,呈现出科学帝国主义的色彩。
科学帝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并生产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这种知识号称是真实、客观、科学及无可置疑的。[2]114在19世纪英帝国对华侵略扩张的背景下,西方来华科考人员一方面用西方科学体系对中国知识进行所谓的“真实”“科学”再生产,一方面对中国本土科学技术知识进行否定性评价,认为中国人没有科学或者科学落后,对“事实”态度草率,不可避免地将幻想、神话以及各种错误信息和事实混合在一起。福琼在其游记中,同样以西方博物科学作为权威对中国本土的博物学知识进行判断、选择。福琼认为中国人是没有科学的,全凭经验的,比如在记录中国人控温孵鸭法时,在福琼看来,温度的掌握是孵鸭成功的关键,尽管孵鸭场成功孵化鸭子的数量惊人,但是中国人在关键流程上竟然依靠个人经验,“中国人则依靠自己的感觉来调节温度”,而他则使用科学精确的方法,“通过温度计,我观察到这一温度大约维持在华氏95°-102°之间”[7]40。面对中国人的不讲科学、不注重“事实”,福琼将其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相联系。在福琼看来,“这就是中国人的品格。他们不会跟你讲真话,除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我常常认为,如果对他们利益无损的话,他们更愿意说假话”[7]263。中国人不诚信,欺诈成性的主题在福琼的游记中反复出现,这无疑为福琼利用西方博物学知识判断生产中国本土博物学知识提供了合法性。福琼以西方科学为标准,将中国本土博物知识从其原有的博物知识体系中剥离,编织进大英帝国的博物知识秩序与模式当中,可以说,是当时来华西方科考者在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的缩影。
事实上,用西方科学体系去否定中国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西方科考人员时常需要利用中国本土科学知识,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肯定与赞赏。福琼在中国采集植物时,必须雇佣中国采集工,或依靠当地农民的帮助,这实际上间接承认和利用了中国本土的博物知识。当地居民对本地动植物的习性和栖息地的了解,往往来自于世代相传的中国博物知识传统。在科学技术上,福琼对外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保证存活率的种子运输方法,其实他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本土树种保存方式的启发,福琼曾在徽州见过茶树树种的保存方式,“茶树种子采集下来,人们通常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沙子和湿土混杂在一起,这样一直保存到春天”[7]257。再如,福琼在宁波附近看到中国保存冰的冰库,面对中国的存储冰块的技术不由感慨“即使是我们英国最好的冰库,处在这样阳光下其效率如何也是有待检验”[7]55。可见,中国本土博物知识并非总是宰制与服从的关系,并非总是冲突与对抗,中国本土博物知识对福琼的帝国博物知识生产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南京条约》强权外交下的博物实作空间扩张
田野实作是博物学的伟大传统,19世纪博物学海外田野实作的地理空间,正是依傍帝国海外殖民势力的蔓延而不断延展扩张。就英国而言,博物学者总是举着英国旗帜,然后又跟随着英国旗帜踏上新土地。[8]英人在华博物学田野实作的地理空间范围以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来华英人只能在广州,并且是在有严格规定的一小片区域内活动。这极大限制了来华英国博物学家们的博物田野考察活动,能采集获得的动植物在数量和种类上都非常有限。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通过武力强迫中国于1842年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并且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来华英国博物学家在中国的活动范围。福琼于1843年后来华,作为大英帝国对华殖民扩张表征的《南京条约》多次出现在他的游记中。福琼一方面要求中国人遵守《南京条约》的条款,寻找大英帝国的利益保护,另一方面自己却违反《南京条约》,以最大限度拓展在华植物学活动的地理范围。
在《南京条约》的保护下,福琼被容许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舟山等地活动。福琼在香港登陆后一路向北而行,不错过任何一个条约中开放的通商口岸,对所到之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植物学考察,获得大量罕见珍贵植物活株及其丰富的中国博物知识。福琼正是由于亲自到达浙江的绿茶产地与福建的红茶产地,通过实地观察对比才解决了长期困扰英国人的难题。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普遍认为红茶与绿茶的区别来自于树种的差异,福琼指出红茶与绿茶的差异是由茶叶加工工艺导致的。[7]365
当身处条约保护的通商口岸地区时,福琼往往对《南京条约》持有肯定态度,强调《南京条约》的规约性,从而保障他在各通商口岸的活动范围和权利。舟山群岛植被丰富多样、地理位置优越,福琼多次在此田野调查,并且将其当作北方之行的总部。舟山群岛在《南京条约》中并未割让给英国,也没有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但是《南京条约》中规定了“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7]32。舟山只是作为英国临时的驻军地。但是为了享有对舟山群岛植物采集的合法性,福琼在文中强调“我在舟山的时候,舟山还在英军手中,按照《南京条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6年才结束”[7]31。福琼在上海进行植物采集时,想到上海西边内陆的几个山丘看看,但是清朝官员发布禁令不容许船夫们带着洋人沿河上溯超过宝塔的位置,福琼很快以《南京条约》的条约为依据,获得了进入上海内陆山村的机会。福琼写道:“这直接侵犯了我们在《南京条约》中的取得的权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对此很快就做出必要而有审慎的反应。之后不久,在所谓的划界确定以后,中国政府容许外国居住者可以到内陆做一天的短途旅行。”[7]127
对于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博物学而言,田野实作对异域地理空间需求很大,以期获得尽可能丰富的种类。福琼并不满足于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通商口岸及活动范围。除了五口通商口岸,福琼试图将其活动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中国内陆,而这是违反《南京条约》的规定的。关于这一点福琼很清楚,“按照《南京条约》,在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中,如果有英国人越过了指定的边界线,他被逮捕送交最近的英国领事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将对越界的英国人施以重罚”[7]179。当《南京条约》成为福琼向内陆行进的障碍时,福琼开始解构《南京条约》的权威性,不止一次抱怨并违反《南京条约》。这种抱怨不是对大英帝国对华侵略行为的谴责,不是对中国主权丧失的人道主义同情,而是对英国政府所获得利益不足的声讨。在他看来,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个港口太少了,而且没有放开内陆是最大的失误。他认为“像英国这样一个又伟大又崇高的国家,在与中国这样软弱无力的国家达成严肃条约时,完全就不需要和中国进行什么谈判,也无需做出什么承诺……”[7]163如果可能的话,他建议中英条约做一些改动:“容许英国商人到全中国各个港口进行贸易”,“取消那些荒唐的居住限制条件”等。[7]164对于禁止英国人进入中国内陆这一规定,福琼认为“多么愚蠢,这个条约,中国人不遵守它,我们英国人也不遵守”,“我们可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打破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成很多事情”。[7]273为了扩展植物采集的地理空间,福琼数次违反条约进入内陆,包括苏州、乍浦、徽州、武夷山等。福琼在内陆博物活动时,会记录下详细的水道信息,这为之后大英帝国进一步的殖民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资料。帝国殖民扩张与博物实作地理空间扩展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正如有学者说,博物学活动是政治扩张的前奏,政治扩张又为博物学发展扫除障碍,两者合力形成“博物学帝国主义”。[12]
尽管福琼博物田野实作的空间范围拓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英国在华的殖民扩张,但是他的博物活动范围并非毫无限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受尽屈辱,签署了各种有利于西方列强在华享有特权的条约,但是并没有彻底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具有独立的主权,加之中国民众的团结与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都使得福琼等西方科考人员在华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他们不得不采取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欺瞒手段拓展空间范围。当福琼想去徽州时,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我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换上中国人的服饰)是不可避免的。……我的仆人给我找来一套中式服装,还有一根发辫,这个发辫我前几年戴过。”[7]214福琼对于装扮成中国人不情愿但却又不得不为之,揭露了强权外交下西人在华科考活动的虚伪本质,也反映出中国在19世纪在华帝国主义科考活动并非是一个彻底的被宰制者。
五、结语
19世纪是西方(特别是英国)海外帝国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在19世纪和 20世纪初期,英法文化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可以见到帝国事实的种种暗示。”[13]帝国主义构成了这一时期中西政治、乃至文化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底色。博物学作为一门科学,源自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在19世纪成为欧洲重要的科学门类。然而,西方科学所标榜的普世主义价值和客观性在19世纪中西文化关系背景之下难免捉襟见肘,当博物学跟随着欧洲海外殖民扩张旅行至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帝国主义文化底色的印染,参与了近代西方帝国体系的构筑,同时海外帝国殖民扩张也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正如前文论述所示,福琼游记中的博物实作生动再现了博物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打破了19世纪来华西人科考类游记中建构的西方科学神话,为19世纪西方科考类游记的研究提供了帝国主义这一更为慎重的态度和视角。与此同时,当笔者在福琼的博物实作书写中挖掘科学帝国主义的证据时,发现中国本土博物学知识并未离场,它作为一种反向力消解了帝国博物学体系的生成与建构。这也启发着后来研究者,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科学帝国主义研究存在局限,凸显中国本土科学作用的科学帝国主义研究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注释:
①参见闫建华:《试论马弗尔的“植物之恋”与植物“缔国”》,《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第143-153页;李猛:《私人科学与帝国野心:1834—1838年赫歇尔在好望角的博物学实作》,《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41卷第11期,第9-16页;姜虹:《性别之眼:帝国博物学家玛丽安·诺思的思想及其冲突》,《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41卷第11期,第17-24页。
②福琼游记未全部译入中国,只有这本游记的中国部分在2015年由敖雪岗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