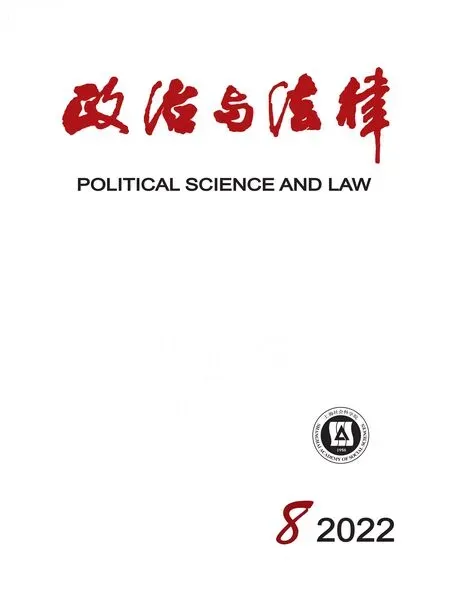去组织体化用工及其当事人确定与责任承担*
沈建峰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1)
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维护问题为各方所关注。对此,人们聚焦的问题是劳动者和平台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他们之间是否可以建立劳动关系。〔1〕参见沈建峰:《数字时代劳动法的危机与用工关系调整的方法革新》,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2 期;常凯:《平台企业用工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法律规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4 期;阎天:《平台用工规制的历史逻辑——以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理论为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4 期;汤闳淼:《平台劳动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规范建构》,载《法学》2021 年第9 期。但实际上作为该问题的“前问题”是劳动者和谁之间存在法律关系?在相关实证调查中,人们一再发现的问题是:“平台企业正在将外卖员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一步步打碎。”〔2〕《劳动关系认定越来越难外卖员的雇主去哪儿了?》,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1/09-25/9573319.shtml,2022 年1 月15 日访问。因此,确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谁存在法律关系是一个比认定其法律关系的性质更基础性的问题。其他国家学者在研究众包这种典型的新就业形态用工时也提出:“只是将众包工人宣布为劳动者,而不能确定谁真正是雇主一方的义务承担者,则调试劳动者的概念是没什么意义的。”〔3〕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 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23,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实际上,我国相关部门在制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时,对该问题已经有所关注。《指导意见》规定:“对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但此处平台企业之外的主体是谁、平台企业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什么、相应责任按什么标准确定等问题均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予以明确。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原因而进行的用工过程和用工主体拆分以及由此引发的用工主体及其法律责任认定困难,并非数字化用工特有的问题。建筑工地上的层层转包、普通用工过程中的外包等都是将一个完整生产过程或者生产组织体肢解、拆分后进行用工的现象,也都引发了劳动者权益维护的困境。实际上,用工过程和用工主体的拆分还是合并是所有时代用工关系选择时都会面临的问题,也有一套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但在劳动法学研究中,以劳动关系为基点的理论却忽视了该“前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劳动者受雇佣于一个用人单位”的思维模型还影响了该“前问题”的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于本文中将回归用工过程和主体拆分引发的用工主体和责任确定困境这一原问题,发现该问题形成的根源以及解决该问题的一般原理,希望对解决数字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问题有所助力,也对劳动法的一般理论完善有所裨益。由于如下文所述,用工过程和用工主体拆分导致的结果是用工组织的解体,为了术语规范,本文将其统称为“去组织体化用工”。
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机制及其法律治理逻辑
解决新就业形态用工中主体和责任确定的难题,包括理解其他去组织体用工的现象,不应以劳动法为原点,管窥劳动力市场,而应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角度来反思用工关系的法律协调制度。当我们承认人力资本也是一种市场要素时,〔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2022 年1 月15 日访问。就已经为从市场经济、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认识用工关系问题提供了前提。
(一)交易与组织体作为人力资源配置的两种机制
理解去组织体化用工的密码在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市场和组织体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只是市场交易,而是交易和组织体两种形态,具体而言,“在企业之外价格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5〕[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 页。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遵循这一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关系用工和民事关系用工分别代表了通过组织体和市场交易配置人力资源的两种不同方式。〔6〕Vgl.Eva Kocher,Crowdworking: Ein neuer Typus vo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n? Eine Rekonstruktion der Grenzen des Arbeitsrechts zwischen Markt und Organisation,in: Hensel/Schönefeld/Kocher/Schwarz/Koch,Selbstständige Unselbstständigkeit,Nomos,2019,S.173-213.
劳动关系用工是一种组织体用工。尽管劳动合同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方式,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7〕参见沈建峰:《论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地位》,载《法学》2016 年第9 期。但通常情况下劳动合同对工作时间、地点以及内容等并不能做完全确定的约定,而需要用人单位行使指示权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定。〔8〕参见沈建峰:《论用人单位指示权及其私法构造》,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 年第2 期。正是指示权成为用人单位组织单个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形成用工组织体的法律工具,通过该权利实现了从市场配置资源到组织体生产的一跃:指挥是雇主与雇员这种法律关系的本质,〔9〕参见[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年版,第30 页。通过指挥,组织体得以建立。具体而言,通过用人单位指示权的行使,劳动者加入用人单位组织(组织从属性)、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并听从用人单位指挥(人格从属性),成为了用人单位生产组织体的构成部分。交易止于企业之外,企业之内是用人单位的指挥、组织,劳动者的服从、隶属,这就是劳动关系组织性的一面。劳动关系组织性的一面实际上也成为解释集体劳动法等劳动法核心制度的重要依据。“因为进入他人决定的劳动组织中,所以不承担孤立的劳动给付,而是在与其他劳动者的联系中劳动,这一点构成了个人自治完全不充分而要通过集体性的群体自治进行补充的实质性理由。”〔10〕Münchener Handbuch zum Arbeitsrecht,Band 1: Individualarbeitsrecht I4.Auflage 2018,§3 Gegenstand und Leitprinzipien des Arbeitsrechts,Fischinger,Rn.28.和劳动关系用工相比,非劳动关系的用工不存在组织从属、人格从属这些特征,劳动者不加入用人单位组织、不服从用人单位的指示。用工的过程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完全通过协商一致等合意机制来确定,价格变动决定资源流向。〔11〕参见[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年版,第31 页。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合意或者合同只是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因此,非劳动关系形态的用工是交易性用工机制。
总而言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关系(组织)和非劳动关系(交易)这两种相区分的用工方式,代表了组织体和交易两种协调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对二者的调整与治理也遵循完全不同的法律逻辑。
(二)治理交易与组织体的法律逻辑
交易性用工和组织体用工奠定了理解劳动力资源法律协调制度差异及其内部逻辑的市场经济基础。“组织协调机制的传统特点是层级和合作;市场的协调机制是平等和竞争。”〔12〕Eva Kocher,Crowdworking: Ein neuer Typus vo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n? Eine Rekonstruktion der Grenzen des Arbeitsrechts zwischen Markt und Organisation,in: Hensel/Schönefeld/Kocher/Schwarz/Koch,Selbstständige Unselbstständigkeit,Nomos,2019,S.173-213.对调整交易的法律机制而言,其经济目标在于保障市场依托个体的经济理性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实现该经济目标,其制度设计的要点是保障市场公开透明、契约自由以及平等竞争,强调主体独立、意思自治及责任自负,这一目标通过传统民事法律和竞争法来实现;对规范组织协调机制的法律而言,其一方面要保证组织体中层级结构的存续和运转,另一方面要保证组织体中服从和隶属者的权益,是服从和保护的法律,团体主义的思想渗透其中。在传统中,上述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整个法律制度内部结构上的楚河汉界,人们也因此将私的法律区分为了组织法和行为法,两类法律在不同理念指引下运行:行为法是平等与竞争的法律;组织法是服从和保护的法律。
上述两种法律机制具体落实到劳动力资源配置上,则“经济上自主工作的托付给了经济法上的调整机制,也就是一方面合同自由,另一方面保护市场透明和平等竞争”。〔13〕Eva Kocher,Crowdworking: Ein neuer Typus vo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n? Eine Rekonstruktion der Grenzen des Arbeitsrechts zwischen Markt und Organisation,in: Hensel/Schönefeld/Kocher/Schwarz/Koch,Selbstständige Unselbstständigkeit,Nomos,2019,S.173-213.与这种主体平等、合同自由相匹配,不具有从属性的民事用工强调当事人的主体独立和责任自负。与此不同,涉及劳动关系的法律,其一方面要规定用人单位享有指示权限,劳动者承担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义务,以保证生产组织的存续和运转,另一方面要通过保护性的法律(劳动基准法)〔14〕参见沈建峰:《劳动基准法的范畴、规范结构与私法效力》,载《法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以及参与管理、集体合同等机制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用人单位享有指示和组织生产权限的前提下,其也承担用工过程中的风险,对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遭受的不利益承担责任。据此,作为传统劳动法研究起点的劳动关系用工和非劳动关系用工的区分,也是在区分人们是用交易法的理念还是用组织法的理念完成对相关用工关系的法律协调;在传统劳动法清晰切割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的理论和制度现实基础上,也可以认为交易法和组织法的理念也是清晰贯彻于不同用工关系协调的制度之中的。
二、去组织体用工的趋势及其问题
上述两种人力资源配置的机制在所有时代都并存着。英国学者梅茵所描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5〕[英] 梅茵:《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97 页。以及现代学者所提出的重回身份的趋势,〔16〕[日]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第74 页。也同样适用于用工市场的法律调整,劳动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重建用工组织法的历史。〔17〕Vgl.Hermann Reichold,Betriebsverfassung als Sozialprivatrecht,C.H.Beck,1995,S.327ff.当下用工关系协调中,人们所谈的去劳动关系化趋势,却是一种去组织化趋势。
(一)去组织体用工的动力与趋势
如上所述,去组织体用工不只是数字时代用工特有的现象,而是由来已久;在根本上属于组织体用工还是交易用工首先是个市场判断问题。“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18〕[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年版,第33 页。这是企业或者生产组织体存在的经济根源。反过来,当市场运行的成本低于组织体运行成本时,经营者则会选择市场交易而非通过组织体生产。将这一原理用于人力资源的配置,则其可以解释两种不同用工方式的可能及二者的功能替代关系:建立劳动关系,让劳动者加入用工单位组织的优势是获得了稳定的劳动力以及根据经营需要对劳动者管理、指示和组织的权利,与此相应,用工单位也应承担劳动者的保护义务,如受到解雇保护规则的限制、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等;非劳动关系的交易方式用工充分灵活并承担较少社会保护义务,但无法稳定地对劳动力提供者进行组织和管理。上述有利和不利的比较权衡会直接影响经营者的用工方式选择。当以组织体方式进行经营的成本和收益优于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劳动的成本和收益时,生产者就会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反过来则会将相关的经营通过外包、加盟等方式交由他人完成,或者不要求劳动者加入自己的组织而是以一对一的交易来获取每一个劳动或者劳动结果。
从受经济规律约束角度看,经营者对用工方式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生产条件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限制。故此,“任何重大技术/管理转型均会带来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19〕[法]伊莎贝尔·道格林、[比]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比]菲利普·波谢编:《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5 页。工业化时代,“随着科学管理系统的引进,泰勒想要控制工人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能够制定一项招聘政策,用非技术工人取代熟练工甚至工会会员”。〔20〕[法]伊莎贝尔·道格林、[比]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比]菲利普·波谢编:《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年版,第14 页。这种生产技术就需要严格的生产组织,而满足这种生产组织需要的只能是劳动关系用工。所以,工业时代是以劳动关系用工为中心的时代,也是以组织体用工为中心的时代。
然而,在组织体用工发展的同时,一种去组织体用工的动向已经出现。在通过组织体对生产过程和劳动者的控制同时匹配保护义务,进而导致成本增加的前提下,当生产技术能够达到不通过过程控制而实现结果控制时,就没有必要一定形成巨型企业并将所有劳动者放在流水线上实现有组织生产;或者当人力资源管理手段能够实现不通过流水线也能控制劳动过程时,去组织体用工也会发展。现代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满足了上述要求。“到20 世纪末,由市场而非管理层级协调的网络企业理论不断出现,打造了全球价值链,并且普及了外部服务供应这一做法。合同外包、价值链、子公司协调等,这些都属于管理策略,而且都带来同一个社会后果,即工作地点的原子化。他们正在重新设计分工制度,这次划分的是哪些工作需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哪些可以托付给市场解决。除了作为公司盈利核心的经营活动外,其他一切运营活动都可以外包出去。”〔21〕[法]伊莎贝尔·道格林、[比]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比]菲利普·波谢编:《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 页。以德国为例,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受德国劳动和社会部委托2017 年完成的调查,“通过运用承揽合同而使用外部劳动力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大概90%的德国企业都是承揽合同的委托人”。〔22〕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forschung GmbH(ZEW),Verbreitung,Nutzung und mögliche Probleme von Werkverträgen,https://www.bmas.de/DE/Service/Publikationen/Forschungsberichte/fb495-verbreitung-nutzung-moegliche-probleme-von-werkvertraegen.html,S.276.2022 年1 月15 日访问。
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助力了这种趋势。“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使用,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角度看,企业有组织的模块化会越来越导致其精细区分的结构。在该发展过程中,生产链条越来越少地受到工厂限制,散见各地的组织单位通过时间上限定的、信息技术媒介的合作构成生产链条。法律上独立的企业或者作为营利中心偶尔独立的企业部分或者单个劳动者通常都可以作为受托人以及承揽或者雇佣合同的当事人。”〔23〕Drucksache 13/1 1004,S.55.总体上来看,信息技术一方面更加有利于不将劳动者组织进入企业而实现对其劳动行为的控制,另一方面有利于未处于同一时空的生产单位之间的协调和配合,这些均会导致生产组织的解体。通过平台以众包形式最终实现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劳动力的组合以及对企业这种生产组织体的替代,只是上述信息时代去组织体化趋势发展的“高级”形态。
(二)去组织体化用工的形态
去组织体化用工笼统的说是生产组织用工向市场交易用工的转化,“企业这一雇员加入其中并在其中持续性完成其活动的稳定空间和组织上的统一体被侵蚀了。”〔24〕Ruediger Krause,Digitalisierung der Arbeitswelt-Herausforderungen und Regelngsbedarf,Verlag C.H.Beck,Muenchen,2017,B19.尽管当下讨论该问题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去劳动关系化的平台用工等问题,但实际上去组织体化用工却首先开始于组织体自身的解构,“创设片段化(模块企业)及网状的结构”。〔25〕Ruediger Krause,Digitalisierung der Arbeitswelt-Herausforderungen und Regelngsbedarf,Verlag C.H.Beck,Muenchen,2017,B19.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安排是:业务的解构,将能够模块化或者进行结果控制的生产环节外包给第三方企业;或者自体的解构,直接在模块化生产单位基础上成立独立企业。解构之后,通过市场交易即合同形式获得该第三方企业或者独立企业的劳动成果。我国《劳动合同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劳务外包或者项目公司、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现象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平台用工过程中,平台企业解构为信息商、支付商、物流商、人力资源商等也是这种组织体自身解构的表现形态。在企业组织体解构的同时,也是上述解构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组织体也在解构,“固定的、层级建构的劳动结构解体为大量领域,并为不断变动的团队中目标导向的合作劳动形式所代替”。〔26〕Ruediger Krause,Digitalisierung der Arbeitswelt-Herausforderungen und Regelngsbedarf,Verlag C.H.Beck,Muenchen,2017,B19.劳动者不再加入本已经解构的用人单位的组织体中,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方式劳动,而成为劳动组织之外的劳动力提供者,出现通常所称去劳动关系化的现象。企业组织体的解构与劳动组织体的解构两方面因素结合的经典形态就是众包用工:平台以中介者的身份出现,需求者将本应在企业内部完成的任务肢解成标准化的单元并通过平台外包给大量自由的单个劳动力提供者。在此过程中,平台出于管理的需要,也为了规避法律上可能的责任,将自身又进一步肢解为信息发布平台、支付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平台等等。整个用工的组织过程都分子化了,最终的结果是劳动者不仅不知道他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而且不知道他的交易相对人是谁。
(三)去组织体化用工的后果与治理难题
去组织体化用工的后果如下。其一,用人单位的碎片化。“普遍来看,目前存在一个雇主责任碎片化的趋势,雇主的责任由多名个人或企业共担。与责任碎片化同时出现的,还有合同义务的逐渐稀释与消失,乃至于当前意义下的雇主一词已经不再适用。劳动者们发现,自己面前是一个无雇主的黑洞。”〔27〕[法]伊莎贝尔·道格林、[比]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比]菲利普·波谢编:《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年版,第49 页。用人单位碎片化导致合同当事人不清晰,也导致经营者和劳动力提供者身份混同:从用人单位中解构或者拆分出来的劳动者可以成为独立的劳动力提供者,也可能成为经营者(劳动者经营者化)。目前我国平台用工领域出现的个体工商户是要鼓励注册还是防止滥用两种矛盾的政策反映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势引发的问题。其二,用工关系的交易化。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表现为通过合同获取所需要的劳动力或者成果,而无需建立组织体。“如今的公司已经成为协调控制中心,非常灵活地运用各种资源,通过劳务合同控制着遍布全世界的分包商链条、加盟店、自由职业者、众包工人和子公司生产商品和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工人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企业自己的技师、司机或者操作员,而是来自外部的服务提供者。”〔28〕[法]伊莎贝尔·道格林、[比]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比]菲利普·波谢编:《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 页。其三,技术控制的强化。上述两种后果结合,从形式上呈现出一个无数碎片化的小组织或者个体劳动力提供者通过自由竞争而实现劳动力供给的格局。但实际上,去组织体化的用工绝非一种无组织的用工;现代生产一定是一种合作生产,组织体可以解构,但是生产的有组织性却不会变化。当下的趋势是去组织体化的同时,组织性却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加强。这种组织性主要通过合同或者技术手段(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
去组织体化的上述后果使无论是治理交易用工还是治理组织体用工的法律逻辑在此均存在不合适之处。首先,以组织体化用工为基本制度前提的劳动法律无法应对去组织体用工引发的问题。在此,经常出现的是无法找到承担责任的组织体的情形;并且,即使找到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配置模式也不符合组织体用工的特点。以限制用人单位组织生产权力为后果的工资、工时等劳动基准制度会因为多雇主、不考勤、计件制等陷入适用困境;以企业为单位的民主管理也无法按照既有模式开展,“企业作为劳动者一方对雇主一方的决策进行制度性影响的社会基础的中心地位被削弱了”〔29〕Ruediger Krause,Digitalisierung der Arbeitswelt-Herausforderungen und Regelngsbedarf,Verlag C.H.Beck,Muenchen,2017,B19.;当劳动者已经通过组织体解构转化为独立的经营者时,在其之中推行集体协商,让经营者形成统一的价格标准,可能将出现一种价格联盟。总体来看,在数字时代“如果企业合作和沟通过程越来越多地转向数据网络、由技术推介和部分地不同期发生,那么这种‘解散企业’的倾向也将威胁到工作领域里传统的劳动法规制平台、社会经验、冲突解决和调解”。〔30〕[德]米夏埃尔·施韦姆勒、彼得·韦德:《一切皆在掌控之中?——数字时代的劳动政策和劳动法》,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2019年版,第26 页。
其次,完全的协调交易用工的制度也存在适用困境。从形式上看,去组织体化就是走向交易式用工,但为了实现生产的有序,这种用工中又有着极强的组织性控制,而非完全靠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如果遵循交易和竞争的理念,就应当通过法律制度消除所有合同性选择控制,保证主体的自由和平等;肢解平台企业,防止形成垄断,妨碍竞争。但一旦这样进行制度安排,数字时代的生产将无法存续,平台通过大数据整合资源的能力将会削弱。我国在治理新就业形态的过程中,从市场竞争角度做的制度安排,也更多是为了实现透明和公开,〔31〕《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发改高技〔2021〕1872 号),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1/t20220119_1312326.html?state=123&code=&state=123,2022 年2 月1 日访问。而不是消除合同性控制或者肢解平台。所以去组织体化用工的治理既不是原来充分市场竞争时的法律体系能完成的,也不是充分组织化的劳动用工制度能完成的。我们需要一种协调无组织体的有组织用工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上述组织体用工和交易用工之思路和制度的融合;这种制度的要点,除了纠结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性,更重要的是针对组织体解构的现实,明确当事人之间用工关系的主体,并根据通过合同或者技术控制的实际状况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形式上无组织体(交易的一面)但实质上存在组织性控制(不完全自主和独立的一面)的用工关系特征为我们指明了解题方向和依据。
三、用工关系当事人的确定
用工关系当事人的确定解决以劳动力使用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发生在哪个或哪些当事人之间的问题,但不考虑这种使用劳动力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还是其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交易的面向出发,按照意思自治、责任自负的法则,每个人都只能给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因自己的行为而承担责任,私人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32〕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0 页。因此,除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当事人的行为而建立,探究法律关系当事人,原则上就是探究行为人。如果法律关系通过合同等法律行为建立,则就是探究意思表示人。对用工关系来说也是如此,但运用该理论之前却需要首先澄清一个劳动法学理论中广为流传的误解。
(一)意思还是事实:一个误解
按照意思表示的内容及其当事人判断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观点在劳动用工领域首先面临所谓“事实优先理论”的挑战。“事实优先原则是各国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时普遍适用的原则。……。事实优先原则要求在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应优先以执行劳动和支付报酬的事实为指导,而不考虑当事人达成明示合意的合同名称与合同条款,……。”〔33〕陈靖远:《事实优先原则的理论展开与司法适用——劳动法理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载《法学家》2021 年第2 期。这是否意味着上述按照意思表示内容及其当事人判断用工关系当事人标准的失灵?笔者认为,事实优先和按照意思表示判断法律关系当事人及其内容并不存在实质性冲突,认为二者间存在冲突,更多是一种误解。其原因如下。首先,事实优先并不是认为对用工关系性质以及当事人的判断不用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为需要亲自履行的法律关系,如果其建立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就可能成为一种强迫劳动的制度。事实优先所强调的是实际履行行为和明示的意思表示冲突时,以实际履行行为为准判断法律关系性质。但实际上,实际履行行为从来不是简单的事实,而是本身承载着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事实。与其说事实优先不如说是真实意思优先。这恰好是法律行为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其次,法律行为属性的判断从来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法律判断问题。当事人只可以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但不能决定因该意思表示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私法自治性法律行为建构的形式和可能内容都是通过法律秩序确定的。……。当事人只可以建构得到法律秩序承认的法律关系,对于私法自治性建构而言,法律秩序包含着行为类型和由其建构的法律关系类型限制。”〔34〕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Zweiter Band,Das Rechtsgeschäft,4.Auflage,Springer-Verlag,1992,S.2.在其他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如此,在用工关系的认定上也是如此。所以事实优先并非劳动法领域的所谓特殊规则,而是传统法律行为理论在用工关系领域的具体运用。但事实优先原则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用工关系具有继续性合同的特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当事人通过行为变更原合同约定内容的现象,在法律关系的性质、内容和当事人确定上更应当关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真实的通过履行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思,而不能囿于法律关系建立时当事人的静态约定。
综上所述,用工关系的性质及其当事人的认定依然仍应着眼于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这种意思表示可能通过明示的表示行为表达,也可能通过具体的履行行为体现,在明示的意思和实际履行所表现的意思发生冲突时,应按照实际履行体现出来的真实意思依法判断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及其性质。以意思标准判断用工关系当事人及其内容,除了可以与传统法律行为理论实现衔接外,更重要的是为解决去组织体用工背景下用工行为拆分时的主体确定问题提供了准据。
(二)决定用工关系当事人的考量因素
在组织体将劳务外包的情况下,外包合同及劳动者与承包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劳动者为承包单位工作的意思表示将确定法律关系存在于承包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平台用工情况下,如果平台注册的条款明确平台就是用工关系当事人,则原则上可以将平台确定为当事人。但正如事实优先原则所说明的那样,实践中的问题是,在平台用工或外包用工情况下,一方面,合同条款都是格式条款,另一方面,当事人言行不一致普遍发生。如仅依靠合同条款,则平台或外(发)包公司只要一个条款就可以将自己排除于当事人之外而成为局外的第三方。这既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也可能侵害当事人权益。因此,对当事人身份的探究不能停留于表面的表示行为而应探究个案中当事人通过行为等表达出的真实意愿。以平台这种最经典的去组织体化用工形式为例,“是否所缔结的合同是平台本身承担义务,首先要根据规范的、客观的对其表示行为的解释而决定”。〔35〕Andreas Engert,Digitale Plattformen,in:AcP,2018(218),S.313.平台与劳动力提供者建立法律关系的基本标准是:“一个正直的意思表示的接受者根据客观的标准能够形成如下印象:平台有意与其建立法律行为上的约束。”〔36〕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 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23,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对于如何判断规范的、客观的意思表示,德国学者弗兰克·拜罗伊特(Frank Bayreuther)教授在给德国劳动和社会部以及黑森州政府的两份报告中的梳理是值得借鉴的。〔37〕Vgl.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 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23,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Bayreuther,Sicherung einer fairen Vergütung und eines angemessenen sozialen Schutzes von(Solo-)Selbständigen,Crowdworkern und anderen Plattformbeschäftigten,ISSN 0174-499,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Publikationen/Forschungsberichte/fb508-sicherung-einer-fairen-verguetung-und-eines-angemessenen-sozialen-schutzes-von-solo-selbstaendigen.html,S.44.2022 年2 月1日访问。他认为,在明确的意思表示之外,如果出现如下情况,则可以认为劳动力提供者与平台之间存在用工关系:其一,平台没有明示自己代理人或中介的身份,或者不公开自己背后的实际用工主体;其二,平台运营者的经营模式、网站首页的公告、公开场合的展示以及平台的交易条件等表明平台和劳动力提供者之间存在用工关系;其三,平台实质性的获取以及行使了用工主体的权利,例如它对劳动力提供者进行预选、约定合同框架及合同格式条款、对用工价格进行确定、排他的或者主要承担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对劳动质量进行监督、对等级进行确定、对工作进行拆分、对当事人的交易进行结算;其四,在极端情况下,法律的规避和权利滥用也足以导致直接认定平台和劳动力提供者之间存在用工关系。
(三)复数用人单位的引入
除了上述运用传统真意探求的思路寻找法律关系当事人之外,在数字时代通过去组织体化实现用人单位碎片化,但碎片化的用人单位又被组织起来,存在各种内在意思和外在管理行为的关联和协作的背景下,引入复数用人单位的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此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我国劳动法的传统观念:一个劳动者只能与一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就此问题,近年来理论和实践界已经迈出了突破的步伐:双重劳动关系的理论开始被讨论和接受。〔38〕参见曹艳春:《劳动合同法确立双重劳动关系之肯定论》,载《政法论丛》2006 年第2 期。但当前讨论的只是一种一个劳动者与两个(及以上)用人单位存在时间上切割的两个(或多个)劳动关系。从时间作为劳动给付计量单位的角度看,这种双重劳动关系对既有制度并无实质性突破。“劳动者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用人单位”这一观念在劳动法学的理论中依然根深蒂固,并影响了对其他用工关系的理解。但从用工关系也是从一种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39〕参见沈建峰:《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6 期。并无理由禁止用工关系,包括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一方出现多个主体,形成单一用工关系但多个用工主体的格局。实际上,从其他国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来看,〔40〕法国的情况,参见田思路主编:《外国劳动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7 页;德国的情况,参见Preis,Arbeitsrecht,Individual arbeitsrecht,5.Auflage,Verlag Dr.Otto Schmidt KG,2017,S.26;ErfK/Preis,§611a,2018,Rn.191;HWK/Thüsing,§611,2014,Rn.125;Zöllner/Loritz/Hergenröder,Arbeitsrecht,5.Auflage,C.H.Beck.2015,S.54。多雇主的同一劳动关系早已是广为接受的制度。
按照多雇主劳动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如同在劳动者一方一样(群组劳动),在雇主一方也可以是多个自然人、法人以及法律上独立的合伙参加到一个劳动关系中”。〔41〕BAG 27.März 1981-7 AZR 523-78;持同样观点的判决,参见BAG 15.Dezember 2011-8 AZR 692-10;BAG 19.4.2012-2AZR186-11。在认定存在同一劳动关系(eineinheitliches Arbeitsverhältnis)的前提下,多个雇主就用工义务及报酬支付义务构成了连带债务人。〔42〕ErfK/Preis,§611a,2018,Rn.191;Vgl.auch HWK/Thüsing,§611,2014,Rn.125.对于同一劳动关系认定的前提,理论界一般只是抽象地提出,“如果劳动者与两个雇主之间法律上的关联禁止对该关系分别处理,则出现了同一劳动关系。特别是当基于两个合意内容上的建构或者事实上的实施,可以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和共存亡的,则可以认为存在同一劳动关系”;〔43〕Zöllner/Loritz/Hergenröder,Arbeitsrecht,5.Auflage,C.H.Beck.2015,S.54.或者提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根据合同缔结者的观念,劳动者和雇主们的合意只应共同发生效力并共同履行,也就是说其构成了总体法律行为的一部分”。〔44〕Preis,Arbeitsrecht,Individualarbeitsrecht Lehrbuch für Studium und Praxis,5.Auflage,Otto Schmidt,2017,S.26.从德国联邦劳动法院的判决来看,“承认同一劳动关系的前提不是雇主之间存在特定的——尤其是合伙——法律关系,经营共同工厂,或者共同缔结了劳动合同。必要的更应该是劳动者与这些单个雇主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在法律上的关联,该关联禁止将这种关系在法律上分开处理。这一法律上的关联可以通过解释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但也可以通过强制法律上的评价而得出”。〔45〕Vgl.BAG 27.März 1981-7 AZR 523-78.从裁判的具体实践来看,多个雇主相互处于特定法律关系中,处于一个目标共同体中或者处于统一领导下,追求共同利益或相互依赖以及雇主对缔结或者履行劳动者与其他雇主缔结的合同事实上的影响都是认定上述“法律上的关联”的因素。
复数用人单位理论为去组织体化用工过程中当事人的确定提供了新的选择可能,也可以解决用工关系非此即彼带来的困境。根据去组织体化用工的特点,在用人单位将自己进行拆分(自体解构)或者将业务进行拆分(业务解构),同时又对拆分后的业务或者单位通过合同或者技术等方式进行实际控制,共同完成对劳动者的用工管理时,即各用工过程参与者在平台等的协调下,形式上独立,实际上相互依赖,为了完成生产组织和经营协同行为时,可以考虑认定劳动者和不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共同用工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即上述同一劳动关系)。针对众包用工的情况,已有学者提出:“如果众包人和众包工受到合同约束,平台在该合同中仅仅作为其他合同当事人参与进来,则此时在需方则出现了多数债权人和债务人。”〔46〕Bayreuther,Sicherung einer fairen Vergütung und eines angemessenen sozialen Schutzes von(Solo-)Selbständigen,Crowdworkern und anderen Plattformbeschäftigten,ISSN 0174-499,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Publikationen/Forschungsberichte/fb508-sicherung-einer-fairen-verguetung-und-eines-angemessenen-sozialen-schutzes-von-solo-selbstaendigen.html,S.46.2022年2月1日访问。
四、非用工关系当事人的责任承担
在上述用工关系主体确定的基础上,为解决去组织体用工的劳动保护问题,还应引入非用工关系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制度。所谓非用工关系当事人的责任承担是指,根据以上规则不是用工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主体,对用工关系当事人遭受的不利益承担责任——从本文研究目的来看,主要是指向劳动力提供者承担责任。尽管从结果看,和上述确定用工关系当事人一样,其也是确定有人向劳动者承担责任,但其与上述作为用工主体的当事人承担责任有着本质的区别,制度设计也不相同,在一定情况下还存在责任承担人向用工主体的追偿问题。按照市场法则,原则上所有市场主体都意思自治、责任自负,通过自己的行为进入法律关系并承担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尽管让非用工主体承担责任的立法和学术观点并不罕见:在我国现行法中,个人承包经营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平台用工情况下,学者们主张“不论是哪种情况(作为中介还是用工关系当事人——作者注),都不能阻止立法者将全部或部分雇主义务施加给平台”。〔47〕[法]伊莎贝尔·道格林、[比]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比]菲利普·波谢编:《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年版,第48 页。但毫无疑问让未进入用工关系的当事人承担责任必须有特别的理由。从现有关于他人责任承担机制的讨论来看,〔48〕参见尹飞:《为他人行为侵权责任之归责基础》,载《法学研究》2009 年第5 期;汪华亮:《基于合同关系的替代责任:一个法律经济学视角》,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1 期。让不是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人承担责任无外乎三个因素,即行为、分散风险(利益)、便利。考虑到非用工关系当事人与用工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可能不同关系,其责任也可能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
(一)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
如前所述,去组织体化用工是一种无组织体但有组织的用工。为了实现生产的有组织性,典型的情况是用工关系之外的第三人通过合同、技术等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介入或者干预。因这种介入而产生的责任,是因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在本质上符合市场经济意思自治和责任自负的基本原则,因此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非用工关系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事由。例如,就平台用工这种最典型的去组织体化用工而言,有学者提出:“能够将责任和风险归入的特别责任关系之前提是中介不再限于介绍和中立地位,而是就被要求介绍的给付和/或合同而言,承担了积极的角色(aktive Rolle)或者从一个谨慎经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必然会积极行为。”〔49〕Eva Kocher,Crowdworking: Ein neuer Typus vo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n? Eine Rekonstruktion der Grenzen des Arbeitsrechts zwischen Markt und Organisation,in: Hensel/Schönefeld/Kocher/Schwarz/Koch,Selbstständige Unselbstständigkeit,Nomos,2019,S.173-213.学者们为欧盟起草的《网络平台中介指令讨论稿》(Discussion Draft of a Directive on Online Intermediary Platforms)第18 条规定平台运营商对供应商不履约的责任关键的标准是,客户是否能够合理地信赖对供应商具有优先支配影响力的平台运营商。〔50〕Christoph Busch,Research Group on the Law of Digital Services,Discussion Draft of a Directive on Online Intermediary Platforms,Journal of European Consumer and Market Law,Vol.4,p.165(2016).
对于非用工主体怎样的行为构成上述积极行为或者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行为,上述讨论稿的作者们提出的如下考量因素是值得借鉴的:(a)供应商—客户的合同完全通过该平台提供的设施缔结;(b)平台运营商可以扣留客户根据供应商—客户合同进行的付款;(c)供应商—客户合同的条款基本上由平台运营商确定;(d)客户支付的价格由平台运营商确定;(e)平台运营商提供统一的供货钳或商标图像;(f)营销的重点是平台运营商而不是供应商;(g)平台运营人承诺监测供应商的行为。〔51〕See Christoph Busch,Research Group on the Law of Digital Services,Discussion Draft of a Directive on Online Intermediary Platforms,Journal of European Consumer and Market Law,Vol.4,p.168(2016).类似的观点参见 Eva Kocher,Crowdworking: Ein neuer Typus vo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n? Eine Rekonstruktion der Grenzen des Arbeitsrechts zwischen Markt und Organisation,in:Hensel/Schönefeld/Kocher/Schwarz/Koch,Selbstständige Unselbstständigkeit,Nomos,2019,S.173-213。当存在如上指标时,用工关系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已经受到平台控制,平台自应承担该法律关系中的相应责任。与上述讨论稿认为此时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不同,笔者认为此时应根据该非用工关系当事人产生支配性影响力的方式和程度,由其承担按份责任;同时这种按份责任是其自身行为的责任,不存在追偿问题。
需要关注的是,在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对用工关系双方法律关系的内容有上述实质性影响时,一种类似于劳务派遣的法律关系结构开始形成。欧盟的理论和实践中因此出现一种参照适用劳务派遣法的规则要求第三方承担责任的思路。针对平台用工,“欧盟委员会要求去审查,派遣工指令(2018/104/EC)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特定的在线平台;并认为许多不只是中介的在线平台在结构上与劳务派遣结构雷同(三方合同关系:派遣工/平台劳动者、派遣机构/平台、用工单位/顾客)”。〔52〕Europäisches Parlament,Europäische Agenda für die kollaborative Wirtschaft,(2017/2003(INI)),Rn.46.德国也有学者提出,在平台是合同当事人时,可将一些(跨境)劳务派遣的规则,例如委托人承担最低工资等运用于该用工主体之间,〔53〕Vgl.Bayreuther,Sicherung einer fairen Vergütung und eines angemessenen sozialen Schutzes von(Solo-)Selbständigen,Crowdworkern und anderen Plattformbeschäftigten,ISSN 0174-499,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Publikationen/Forschungsberichte/fb508-sicherung-einer-fairen-verguetung-und-eines-angemessenen-sozialen-schutzes-von-solo-selbstaendigen.html,S.46.2022 年2 月1日访问。Vgl.auch 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S.22,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产生非用工主体的连带责任。从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非用工主体介入到用工主体之间与劳务派遣有类似之处,但在制度前提上依然有很大差异。因此,与其类推适用,不如直接按照前述规则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
需要与上述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因自己介入用工关系的行为而承担责任区分的,是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基于自己与用工关系当事人的合同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如果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对用工关系当事人的筛选等享有权利,而在筛选时没有尽到必要义务或者未能提供真实情况,其也应对用工关系当事人承担责任。例如在平台用工的情况下,在德国,“如果众包人是合同当事人,可以基于《民法典》第311 条第2 款、第241 条第2 款、第249 条(所谓的物的管理人责任)以及第651b 条第1 款第2 句的类推等建立平台的共同(部分)责任,因为平台经常要求完全特别程度的信赖并对委托双方合同的订立享有特别的自身利益”。〔54〕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 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23,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在我国,根据我国《民法典》第3 编第23 章“委托合同”或第26 章“中介合同”的规定,平台也可能对劳动者承担未尽到委托合同或中介合同中义务的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不妥当行为基于其与用工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中介合同或委托合同而承担的违约责任或者缔约过失责任,并非上述基于正常的管理行为而承担的责任。
(二)基于非用工关系当事人的分散风险功能而由其承担责任
民事法上的责任是一种利益和风险转移机制。在特定情况下,让特定人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他存在过错,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将该风险通过保险机制或者价格机制转嫁出去。这是无过错责任存在的非常重要原因。〔5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544 页。在去组织体化用工的情况下,如果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基于自身的优势能够将不利益带来的风险转嫁出去,避免其他没有风险转嫁能力的主体遭受灭顶之灾,则出于社会政策考虑,可以由具有转嫁能力的主体承担责任,这就是大企业、平台等非用工关系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原因。
作为一种分散风险机制下的责任承担,该制度设计应遵循如下要点。其一,其以非用工关系当事人具有分散风险能力为前提,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通过微小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将不利益分散于大量客户群体间。所以,该当事人必须要进行大量交易,存在大量合同相对人。众包用工的情况尤其符合这一条件。其二,其分散的必须是必要风险,而不是用工关系当事人遭受的所有不利益。从分散风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生存受到影响的角度来看,可以分散的风险只能是保障用工关系当事人最低生存利益的风险,所以,非用工关系当事人以承担最低工资水平的保障为限度。基于同样的思路,有德国学者认为,通过中介平台用工的情况下,平台不是用工关系当事人时,平台责任限于最低工资保障。〔56〕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 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23,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其三,其分散风险机制带来的负担必须和同一行业其他用工方式的主体承担的不利益相均衡。因为要通过价格机制来分散风险,非用工关系当事人提供的产品价格自然会提高,在决定分散风险的额度时,必须保障此后的价格与同一行业其他方式经营的主体提供产品的价格相当,否则将会给该经营模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或者将导致规避法律。
(三)基于法律上的便利而由非用工关系当事人承担责任
效率本身也是法律的价值。在极端情况下,出于效率考虑,法律也会让不是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主体承担责任。在我国现行法中,针对转包、分包这种去组织体化用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30 条、第31 条设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总包代发工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这种思路。〔57〕参见赵大全、张义全主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1-106 页。回到去组织体化用工的平台用工,“众包工人并不总能清楚的识别平台背后的企业;也因此不能总是确切地说,需方的两个参与者中哪一个才是主要行使指示权的人”。〔58〕Frank Bayreuther,Arbeitswelt 4.0-Muss der Arbeitnemherbegriff angepasst werden? 1.Auflage,Redaktionsschluss: 2.Mai 2019,S.23,Sächs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Arbeit und Verkehr,https://publikationen.sachsen.de/bdb/artikel/33300,2022 年2 月1 日访问。在此背景下,尽管从规则角度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清晰的,但对劳动力提供者来说却存在识别和主张上的困境。为了便于劳动力提供者主张权利,也是考虑劳动力提供者的弱势地位,学者们的如下建议是可取的:“针对这些远程的当事人实现权利存在系统性的困难,平台的共同责任可以对此予以补救,因为平台对双方来说都是更近的、更了解的、无论如何也容易抓到的。”〔59〕Andreas Engert,Digitale Plattformen,in:AcP,2018(218),S.316.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由于这种责任是一种出于效率和便利考虑而由用工关系当事人之外的主体承担的责任,从责任目的出发,它应当是一种连带责任,这样才真正能够便利权利人主张权利;但同时它在根本上并非责任承担人自己的责任,因此在其承担完责任后,可以继续向用工关系中的义务人进行追偿,所以它是一种不真正的连带责任。考虑到追偿本身容易导致重复诉讼,这种基于效率和便利而设计的非用工关系当事人责任,仅限于实际用工主体不明确等特别的情况。只要平台等非用工主体能够明确实际用工主体的身份,则原则上可以免于承担这种责任。
五、结 论
去组织体用工带来了用工主体的碎片化和用工过程形式上的交易化,但实际上有组织用工的一面并未丧失。这一格局对用工主体和责任主体的认定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从市场交易一般法则出发,依然应按照当事人的意思来确定用工关系的当事人,此处的意思是真实的意思,尤其是通过履行行为表达出来的意思。同时,考虑到去组织体化用工带来的组织拆分现象,应引入共同用工主体的规则。用工关系的主体原则上也是用工过程中权利和义务的承受主体,但考虑到去组织体化用工本身的特殊性,用工关系主体之外的人基于自己的行为,基于分散风险的可能以及基于效率的考虑,也可能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不同原因的责任承担,其基础、范围、是否可追偿等并不相同。根据上述理论,《指导意见》中的相应责任应当是包含了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责任,而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