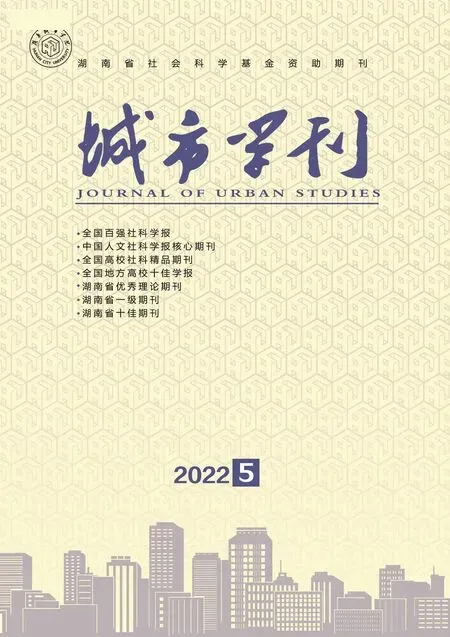早期闻一多的传统文化观念及其实践
史习斌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在新月同人群体中,闻一多可谓是对传统文化感情最深的一位,也是情况最为复杂的一位。在短短47年人生的不同分期中,闻一多之于传统文化的“恒”与“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实现学术“向内转”之前的早期闻一多,经历了清华求学、去国留学和新月前期三个重要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他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和实践都体现出了内在的一贯性。
一、清华求学时期: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本位主义
从1912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到1922年赴美留学,闻一多在清华园度过了10年的求学生涯。这10年是闻一多传统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段。闻一多是《清华学报》和《清华周刊》的编辑,在上面发表过大量文言文章和一些旧体诗。1917年在自传《闻多》中自言“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1]字里行间带有几丝沾沾自喜的陶醉;1921年7月在老家书斋“二月庐”亲手汇编并手抄旧体诗文集《古瓦集》,从文化心态来说,多少带有孤芳自赏的意味,并夹杂着一丝告别的不舍。在清华求学时期,闻一多不仅以对“古文辞”和“旧体诗文”的偏爱表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更是在对清华学风的批评以及由此发出的振兴国学的呼吁中确立了其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观。
1916年,《清华周刊》第77期发表了闻一多的《论振兴国学》,开篇便论述文字之于文明、国学之于国家的重大意义,“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葆吾国粹,扬吾菁华,则斯文不终丧,而五帝不足六矣。”[1]25针对当时的清华校方重西学而轻国学,清华学生因此普遍不重视国学的状况,表达了自己的痛惜之情,最后力倡国学:“惟吾清华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乃能不忘其旧,刻自濯磨。故晨鸡始唱,踞阜高吟,其惟吾辈之责乎!”[1]261917年作为《辛酉镜》总编辑的闻一多为刊物所写的《课艺·序》和《艺林·序》,都强调了作为清华学子对于国学应有的态度。《课艺·序》在思想甚至文字上与《论振兴国学》一脉相承,可以看作它的缩减版,表达了希望清华学子“刻自濯厉,以崇国学”的愿望;《艺林·序》则表达了他对清华学子“未能专攻国学”的遗憾和试图通过创办艺林倡艺崇文、提倡国学的主张。[2]
1921年4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描述了“比戏院,茶馆,赌博场还不如”的清华中文课堂,不仅课堂秩序混乱,“有的骂,有的笑,强狠的开门要走”,而且精神涣散,“在英文课堂讲诚实,讲人格,到中文课堂便谲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3]之所以如此,是清华自创办以来一直形成的重英文、轻国文的“传统”所致,而这种“传统”是被闻一多所诟病的。《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是继1916年闻一多发表《论振兴国学》之后,再次对清华学校的国文教育提出批评,只是在描绘课堂丑态和表达批评意见时,这篇用白话文写成的文章远比文言文写成的《论振兴国学》要酣畅淋漓。
或许正是长期的认知积攒起来的情绪在起作用,闻一多1922年5月在《清华周刊》发表了《美国化的清华》一文。作为闻一多清华十年的“总结”和“告别”之作,他给清华的“赠言”却是:“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4]他认为,物质主义以及由物质主义细分而成的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都是美国文化的精髓,美国人的特色,也正是美国化了的清华学生的现状。最后不禁怀着怨愤疾呼:“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东方文明啊!支那底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罢!”[4]5《美国化的清华》可以说是崇尚中文和国学的闻一多对10年清华受到的文化压抑的情绪总爆发,也是由此而形成的关于传统文化观点的总表达。
稍加分析可以发现,此时的闻一多并没有亲见美国,他对美国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当时清华重英文轻中文的学习氛围和学生的“做派”而得出的,是一种“间接经验”。联系此前闻一多在文学革命中的犹疑和被动综合分析,清华求学时期的闻一多对传统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言与白话的语言问题,而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且通过对新诗的毫无保留的提倡和对传统国学作为一种文化支撑的肯定,把语言与文化统一起来。之所以如此,除了性格的潜在影响和校园环境的现实刺激之外,更重要的是早期教育所奠定的传统文化根基在起作用。
闻一多6岁读私塾,“读的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和《四书》之类。”[5]7岁读改良家塾,“既读诗云子曰,也教博物、算学、美术。”[2]14“塾师是一位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旧学’的根底不错,又多少学过一些‘新学’,……要学生们除了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等,还要读洋学堂新编的修身课本;除了背诵《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还学新的国文、历史、博物等等。”[6]据闻家驷回忆,闻一多家“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7]“他常把新的思想和书刊带回家,对我们兄弟几人影响很大。”[2]1912岁时,也就是1910年,闻一多到武昌入读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采用的是新式教材与方法”,[2]20同时,“在叔父丹臣先生主持的改良私塾里补习,中文之外,并有英文、算学”。[5]3从闻一多所受的早期教育和日后的观念与实践可看出,在进入清华之前,闻一多通过对“新学”的学习开阔了眼界,避免他以后成为极端守旧分子,奠定了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基础,但真正为其打下思维和价值观底色的还是“旧学”。这一底色对身处开放包容的清华园的闻一多产生了显见的影响。闻一多在1918年5月12日致弟弟闻家驷信中,回复了父亲关于《汉书》阅读进度的询问,并报告了自己“改阅《史记》”“温阅《左传》”“阅毕黎(莼斋)选《续古文辞类纂》”等阅读成果,最后,得出了“兄现为文,气息尚不能醇厚,总由读周秦文字太少”的结论。[8]同年11月25日致闻家驷信,告诫弟弟“经、史务必多读,且正湛思冥鞫,以通其义”,[8]9并说自己写文章慢、枯涩,都是根底太薄,让弟弟不要重蹈自己覆辙。对于闻一多而言,这种观念可说十分稳固。1923年远在美国的闻一多致信闻家驷:“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先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亦当负同等责任,使此风永继不灭焉。”[8]67以至于在1938年5月写自云南的家信中,仍多次强调要重视孩子的中文教育之根,“在这未上学校的期间,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8]135“惟欲求中文打下切实根底,则非读旧书不可”,并托弟弟闻家驷“对两儿随时加以指示”,以期相互进步,“对驷弟或亦可增加读经之兴趣也”。[8]132由此可见,以重视中文为基础,闻一多已经将传统文化和国学融入家庭教育、家风传承和职业发展之中。
由于早期教育所奠定的传统文化根基以及在清华园目睹中文传统遭受到的挤压和由此产生的强力反弹,这一时期,在闻一多心中形成了较为坚实的传统文化中心观念,并以国学振兴和家庭教育为实践和发展途径,在与美国文化的比较中,确立了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本位主义。
二、去国时期:发掘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之维
1922年7月,留级一年的闻一多告别了求学10年的清华园去美国留学。梁实秋的《闻一多在珂泉》中说:“对于到外国去,闻一多并不怎么热心。……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过,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9]闻一多在去美国之前,通过清华和清华学生的状况想象美国,或者说间接地认识美国,形成了对于美国的刻板印象,从很大程度上,这种刻板印象成为支撑他在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也影响着他的留学生涯。初到美国的闻一多想做“东方的人”而不愿做“美国机器”,这种观念得到了一些留学生的响应,“与我同居的钱罗二君不知怎地受了我的影响,也镇日痛诋西方文明(我看稍有思想的人一到此地没有不骂的)。”[8]184-185半年后在致父母的信中仍在大吐苦水:“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8]47综合来看,闻一多对美国产生怨愤或者说没有亲和力的原因,一是出于弱者的自尊和自我防卫,二是种族歧视问题。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物质或技术弱者地位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闻一多这样的文化至上主义者,可以用自我认同的文化优势(至少是心理上的优势)进行对抗。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华人地位低下和生活的困难成为华人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写照,这才促使闻一多写出了《洗衣歌》这样的泣血之作。而种族歧视更是现实的难以排遣的问题,对闻一多产生刺激的事件有很多,比如科罗拉多大学行毕业礼时美国女生不愿与中国男生并排上台,校方安排六个中国人排成三队;比如同为清华毕业的同学陈长桐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匠因为他是黄种人而拒绝为他理发等等。
事实上,正是因为感受和自身遭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激起了闻一多对美国的心理对抗,这种对抗更加强化了他对美国的刻板印象,也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文化守持的信念。“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8]47闻一多留美近 3年,并没有被美国的生活文化同化,“他虽住在外国,但仍不能忘怀中国生活的情趣,在宿舍里用火酒炉煮水沏茶是常事”。[10]闻一多于1925年5月中旬启程提前回国,“当轮船刚驶进吴淞口,他立即把三年来束缚着他的洋装扔到海里,……自是以后,就一直穿着长袍布履”。[6]90在美国而煮水沏茶,回归后常穿长衫等,都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妙符号。在芝加哥美术学院,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古典文学和文化经典,成了原本研习美术的闻一多的“主课”:“我们有时竟拿起韩愈底《原道》来哼开了。今天晚饭后我们一人带了一本《十八家诗抄》,到Washington Park里的草地上睡起来看了一点钟底光景。”[6]185每天生活的规划,早上八时去美术学院,下午四时回来,“饭后我们还是要上华盛顿公园去读杜甫、李白、苏轼、陆游去。”[8]185闻一多在真正的主业美术上也有较强的厚中去洋的意味。他带一群中国朋友参观博物馆时,“不引他们久看西洋画,而到了有中国底美术品之处,我总对他们讲解赞叹”,在为自己的《红烛》设计封面的时候,反复修改,“不愿我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8]229在这些具体的行为背后,不仅体现出闻一多的文化好恶,还包含着闻一多关于文化影响的整体战略思考。闻一多在1925年为中华戏剧改进社预刊行的出版物取名时,欲取“河图”,认为其“代表中华文化之所由始也”。[8]262他认为中国有政治、经济、文化被人征服的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在谈到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时,他表示“我决意归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崇我国文化”。[8]265
正是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信念,闻一多对留学生的欧化风气进行了批评:“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8]67在文学领域,早在 1922年闻一多就开始反思当时的白话诗过于空洞、轻薄、贫瘠的现状,而原因之一就是“文章中外语的术语、外语的表现、外语的主题、外国的思想引进的混乱”,这其中他尤其提到了郭沫若,说:“他不过是巧妙的用中文表达了西方的思想而已”。[11]1922年末写成(发表于 1923年)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对当时的新诗及郭沫若的《女神》表现出来的“欧化的狂癖”进行批评: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12]
不仅如此,闻一多还将诗歌创作与爱国主题直接联系起来,认为那些过于欧化的诗人也并不是在情感上不爱祖国,但却在理智上缺少了一些对祖国文化的敬爱,并拿自己现身说法:“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12]121反观闻一多自己这一时期的新诗创作,则很多都是爱国热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1922年9月19日在致梁实秋的信后附有新创诗作《寄怀实秋》,在诗中,“红烛”被海风吹熄后的轻烟“不知往那里去才好”,“诗人”的尸肉仓皇着,“仿佛一只丧家之犬呢”,要借恋人的纱灯点燃“残烛”,“为我照出一条道路”。[8]187诗人写出了身在异国的迷茫以及重建信心的企图。1922年9月24日在致吴景超的信前抄的两首诗《晴朝》和《太阳吟》,无一例外把自己唤作“游子”,闻一多在信中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这个家不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8]1941922年10月27日在致梁实秋的信开篇抄录的一首无题诗中,直言自己在深秋“想着祖国,/想着家庭,/想着母校,/想着故人”,[8]214在随即抄录的诗作《忆菊》中,喊出了一个游子对祖国由衷的礼赞:“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8]2181925年7月15日《大江季刊》创刊号上,集中发表了一批闻一多去国时期创作的爱国主义诗歌。《长城下之哀歌》将长城看作“旧中华底墓碑”,相信长城“守得住你的文化”,但同时又隐含着对这一文化符号的深刻反思,如作者所说,“是我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8]243《爱国的心》以心脏之形状喻中华之版图,坚信没有谁能偷去“伊的版图”,更没有谁能偷得去“我的心”,在细微之处蕴含着救亡图存的爱国大志;《我是中国人》聚焦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五千年的历史”与“东方文化的鼻祖”,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热爱与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洗衣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华侨”的苦难和美国社会对“支那人”的侮辱与损害。同样写于去国时期,发表在《大江季刊》第2期的《七子之歌》更是写出了弱者的任人宰割和侵略者的虎狼之心,呈现出被割让的土地与祖国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迫切心情。
这一时期,闻一多受到了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北美的排华、文学的爱国都有具体的论述。闻一多求学清华时便意识到:“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8]14去国留美期间,闻一多通过现实行为、文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做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体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并将其和传统文化的热爱结合起来,发掘出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之维。
三、新月时期:新格律诗作为传统文化的形式载体
闻一多虽然留学的专业是美术,但他回国决意从事的却是文学;他急着在回国之前自费出版诗集《红烛》,一个功利的考虑就是想回国之前先在国内诗坛打响名号。回国后的闻一多很快在1925年8月参加了新月社茶话会等活动,8月11日便致信闻家驷“我等已正式加入新月社”。[8]88在靠近古典与传统这一方面,诗人闻一多的新月时期是他去国时期的延续。在美国留学时他曾说,“现在我极喜用韵。本来中国韵极宽;……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8]195他致信友人坦承《红荷之魂》是其“近主张新诗中用旧典”的试验品,[8]166又说从《园内》“可看出我的复古底倾向日甚一日了”,[8]247-248还自指《红烛》中《忆菊》《秋色》《剑匣》等“具有最浓缛的作风”的诗作受到了“义山、济慈的影响”。[8]228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用韵、用典无疑是受到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他在早期求学和留学美国时期对古典诗人的持续阅读,对其古典诗风和“复古”倾向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1926年初开始,闻一多家里就聚集了一群诗人,读诗、评诗,成为“一群新诗人的乐窝”,到了4月1日《晨报·诗镌》创刊,开始进行诗歌的改良实验,闻一多在上面发表《诗的格律》等重要论文和《死水》等诗歌创作,之后更是提出了“三美原则”,对新诗创作的过度自由化进行反省和修正,形成与自由诗派和象征诗派并驾齐驱的格律诗派。对此,虽然有的人认为“对文学革命言,似显得稍稍有点走回头路”,[13]甚至“有些悲观的人或者将以为这是新诗的回光返照,新诗的末日大概不久就会到临了。”[14]但是从走出了草创期的新诗的自我反省来看,他们并不理解闻一多的良苦用心,也没有达到他的高度和远见。实际上,闻一多的“三美原则”意在创建一种新的诗体,这种新诗体试图在形式感的获得和音乐性的传承上与诗歌传统产生尽可能多的关联,背后也隐藏着吸取传统文化精华为新诗服务的时代意味。
与此同时,对十四行诗的创作和译介成为闻一多新格律诗的又一实践途径。1927年10月译诗《樱花》发表,采用的是格律形式;12月,《“你指着太阳起誓”》发表,为十四行诗。1928年5月,诗《回来》发表,为商籁体。在此期间,闻一多翻译了二三十首白朗宁夫人的商籁体诗,而且尽量保存原诗的格律,在诗坛上形成了不小影响,以至于朱自清说,“现在商籁体(即十四行)可算是成立了,闻先生是有他的贡献的。”[15]闻一多虽然创作尤其翻译了不少十四行诗,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西方诗体的移植,而更多的是寻找十四行诗与中国诗歌在格律上的关联,以利于新格律诗的创制和推广。
闻一多的新月时期与他进入大学任教的时期有所重叠,且他并没有参与新月派的整个过程。在闻一多与新月派的交叉时期即新月前期,他在文学上的主要关注点和贡献是提倡和实践新格律诗。新月诗派提倡新格律诗的初衷是对新诗过度自由化的纠偏,在闻一多那里所能寻找和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便是诗歌和文化上的传统资源。这一资源的核心,正如闻一多在《一个观念》中的“五千多年的记忆”所指,实际上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因而,在诗歌背后的文化根源上也可以说,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其根本指向还是与他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他所追求的新格律诗的诗体,则是在为传统文化寻找一种合适的形式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