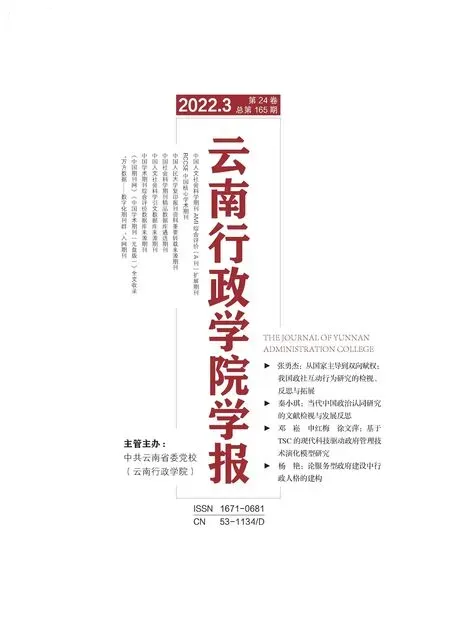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张勇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一、引言
在当代中国政社关系的研究中,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主线的讨论一直提供了有力的洞察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与争辩。①Perry,Elizabeth J.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9):704-713.但是我们却总能在复杂的现实情形中看到这样一种颇具张力的场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逐渐松动,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增长,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自主行动空间正在生成,并逐渐在社会治理、政策倡导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社会的发育、成长却又无时无刻不处于国家的建构与控制之中,在宏微观机制上受到诸多约束和束缚,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夹缝求生”的特征。①Ma,Qiusha.Defin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J].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02,Vol.13,No.2,pp.113-130;王信贤,王占玺.夹缝求生.中国大陆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困境[J].中国大陆研究,2006(01):27-51.而现实中,正是国家与社会这两种力量的事实相遇,使得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更为复杂与生动的情景,既存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争论,又存在社会对于国家依附和双向互动的现象。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总体生存模式逐渐式微,在社会领域内涌现了大量具有公共性、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并在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海内外的中国研究学者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将社会组织作为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并探讨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形成了早期中国政社关系研究中两个并行的视角,即公民社会视角与法团主义视角。其中,公民社会视角竭力说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界分,关注于“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②CharlesTaylor.Models of Civil Society [J].Public Culture,1991,Vol.3,No.1,pp.95-118.,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③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171.。法团主义视角则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截然分开和相互对立,而是强调国家在社会利益达成和团体作用中的决定性力量,主张发挥利益团体在国家和社会利益传递之间的协调性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化合作结构。④Pi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P.C.Schimitter and G.Lehmbruch(eds.),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Beverly Hills:Sage,1979,pp.9.
然而,不论是公民社会视角,抑或是法团主义视角,双方争论的关键点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各自权力的强度与边界问题,它们分别选择以社会组织作为经验研究的窗口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征,即“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权力究竟谁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一结构性视角在后来以及新近的研究中备受争议:一方面,在中国的事实经验中发现,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在国家使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发展进行控制的关系之外,同样存在对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建设性的支持关系,并且独立于控制而单独发挥作用⑤陶传进.控制与支持:国家与社会间的两种独立关系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里的情形[J].管理世界,2008(02):57-65;Jing,Yijia.Between Control and Empowerment:Governmental Strategie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China[J].Asian Studies Review,2015,39(4):589-608.;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主义学派和社会系统论的观点而言,“国家”与“社会”在实际中是碎片化的、分散的、多元的,诸如“碎片化威权主义”⑥Kenneth Lieberthal,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Jean C.Q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4):1132-1149.、“蜂巢式社会”⑦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M].Stanford:Standfor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4-135.等概念都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特征的再反思。如果只是将其作为边界明确且高度统一的静态性实体结构,是很难洞察实践中的复杂机制的。
因此,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分析,开始从“结构论争”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①张紧跟.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 研究述评[J].社会,2012(03):198-223;陈为雷.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3(01):228-240.诚如米格代尔所言:“国家和社会都不是固定的实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社会控制都会发生变化,它们在不断地适应当中。”②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7.鉴于此,他提出“国家处在社会中”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宏观转向中微观层次来分析现实情景中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复杂互动和动态过程。那么,从结构关系转向行动分析的过程中,当前学术界对于政社互动研究形成了哪些学术取向和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视角有何不同?我们又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政社互动的研究?下面笔者将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视角为依据,将社会组织作为切入口,分别从国家主导和双向赋权两个方面梳理已有中国政社互动的研究路径与学术观点,以期进一步提出一些拓展政社互动研究的方向。
二、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力量互动
从国家主导的视角来理解政社力量互动,本质上是从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康晓光认为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的发展远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相应的自主性,政府依旧处于支配地位,要理解中国大陆社会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把握“行政主导”这一大前提。③康晓光,蒋金富.政府-社会组织博弈研究[M].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13:9.那么,围绕这一中国情景,此研究路径以“国家主导”的特征为前提,据此分析国家是如何与社会组织进行互动以及社会组织在此约束性情境下究竟如何与国家建立关联。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以《找回国家》为标志的国家主义学派逐渐兴起,他们试图重新将“国家”找回来,来更好地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与变化。在国家主义学派看来,“国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行为者对社会以及其他国家的有意识的影响上,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的结构、功能与行动可以无意识地影响社会”④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8.。那么依循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种思路来进行阐述:一是分析作为能动性的国家是如何有意识地通过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来实现自己的意愿;二是分析现有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如何回应和采取行动。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路是在互动视角下来阐述国家与社会组织如何行动,这是区别于法团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组织研究,法团主义是试图将公民社会中的利益组织整合进国家的结构体系中,从而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合作结构,但是它对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关注不足,并且其将国家假设为静态的统一整体,那么此处更着重分析国家治理结构或者某一部分和社会某一部分互动关系的变化。
(一)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
从国家能动性的取向而言,国家作为独立行为体是具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利益诉求”,其可以根据自身的行为逻辑来工具性地处理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在国家主义学派中,其实早期已经有一批代表性学者分析了国家在基层社会秩序中的权力运作方式和目标。如蒂利(Tilly)认为国家政权建设是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是国家在基层秩序中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渗透和公共秩序建构。①Charles 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609.迈克·曼(Micheal Mann)提出了“专断性国家权力”和“建设性国家权力”的划分,其中“建设性国家权力”是指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空间中来调整社会活动以及增强其执行政策的能力。②Michael Mann.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Vol.Ⅱ: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59-61.在这一大的研究脉络之下,国内许多学者在中微观层面做了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如康晓光和韩恒认为国家处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一方面会采取“控制机制”来避免民间组织发起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以“功能替代”的方式来发展那些政府信任并具有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他们将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策略称之为“分类控制”。③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06):73-89.之后,他们又在专著中系统论述了政府可选择的策略类型,并将这种国家主导下的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概括为“行政吸纳社会”。④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M].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就改革实践而言,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态度和管理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刘鹏认为当代中国政府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方面正逐步从分类控制转向嵌入型监管,国家可以依据监管意愿与监管能力来灵活地采取对社会组织干预和管理的手段。⑤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5):91-99.郁建兴等通过对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的考察,发现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逐渐从双重管理走向合规性监管,监管的重心也由事前监管向事中和事后监管转移。⑥郁建兴,沈永东,周俊.从双重管理到合规性监管——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监管体制的重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4):107-116.江华等则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利益契合”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认为转型期国家在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二者的利益契合程度决定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支持或限制,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的策略性选择成为可能。⑦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J].社会学研究,2011(03):136-152.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文献将国家视为一个具有意识的整体理性人。
此外,近些年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也更加地多元化,在治理工具上也更加丰富化。例如,盛智明以A 市业主自治实践中的“体制化”现象为例,深度分析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再生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政策执行和人员选择等行政吸纳方式,有效地实现对业主自治组织的整合。⑧盛智明.制度如何传递?——以A 市业主自治的“体制化”现象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9(06):139-163.唐文玉基于一个乡镇基层文联的个案研究,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新的解释模式,认为在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的价值目标导向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出现了融合趋势,并予以更多的支持与配合。⑨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J].公共管理学报,2010,7(01):13-19.唐兴军通过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的行业协会管理方式,国家通过制度嵌入、组织嵌入与利益嵌入的方式与行业协会建立内在关系,这种“嵌入式治理”的思路既促进了行业协会发展的规制与自律,又提升了党和政府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①唐兴军.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8(02):187-188.还有一些学者创新性地运用政府治理中“项目制”“行政发包制”等概念来分析国家如何主导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②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04):126-148;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05):113-130;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15(02):82-102.王向明以近些年兴起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切入口,提出了社会组织管理领域项目制的发包体制与嵌入性过程监控的特点,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无论是社会组织的“内部化”,还是社会组织的体制内吸,反映的都是政府主导的管家模式而不是基于公平竞争的委托-代理关系。③王向民.中国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5):130-140.黄晓春指出在执行社会组织领域的政策时,地方政府往往承担较高制度生产风险,缺乏强激励且面对低强度的自上而下检查验收。在此情形下,作者提出“模糊发包”的分析工具在中观层面来理解渐进式改革中各级政府的行为及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④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5(09):146-164.
(二)作为治理结构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行动
从国家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行动的取向而言,是要打破“国家”被视为一体化的整体性思路,深入分析在制度复杂性下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与行动策略。李侃如曾指出:“中国的国家结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而是由许多拥有不同程度自主权的机构所组成,不同科层机构在功能上相互分割,条块之间经常存在张力。”因此,尽管中国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威权性,国家处于主导型地位,但是条块所构成的组织结构是分立的,使得真正的权威支离破碎。也正因为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中国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更加复杂多变。黄晓春、嵇欣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政策领域存在多种政策信号,从而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现象,这诱发了社会组织采取各种灵活的组织策略来发展自主性。特别是与不同“条”“块”部门之间的密切程度塑造了社会组织嵌入地方行政网络不同的组织特征和自主性效果。⑤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4(06):98-123.王信贤则借鉴公共选择学派“理性人”的假设,在碎片化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自利官僚竞争”的观点,指出正是各条块部门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特点,使得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更加复杂,并拉大了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⑥王信贤.争辩中的中国社会组织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M].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46-51.管兵基于三个大城市业主自治组织的考察,分析了不同城市政府结构下社会组织发育的差异效果,发现如果当地具有更高行政级别的政府时,那么多级政府结构有利于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⑦管兵.城市政府结构与社会组织发育[J].社会学研究,2013(04):129-153.正是基于国家治理结构的复杂性,一些学者站在社会组织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组织的行动特征和策略,如“依附式自主”⑧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3(05):50-66;康晓光.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组织外形化”⑨田凯.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04):64-75.“去政治的自主性”①唐文玉,马西恒.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1(10):58-65.“非正式政治”②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 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8(02):133-150、245.“以理抗争”③朱健刚.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J].社会,2011(03):24-41.,等等。
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些代表性的文献。鲁依依通过大量的经验案例研究挑战了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两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组织通常缺乏自主权;与官方社会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则相对更具有自主性。而事实上,她认为无论是在维持自主、动员公众支持,还是在实现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影响力方面,一些官办社会组织(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表现出比民间组织更强的自主性,并且在政策与执行的落差之间千方百计地寻求更大的自治权。因此,在她看来,在描述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大流行的概念都显示出严重的局限性,它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复杂性,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源于“体制、经济和个人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特别是各个社会组织在“与国家进行谈判”(negotiating the state)方面的技能通常会对其享有的自治程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④Lu,Yiyi.The Autonomy of Chinese NGOs:A New Perspective[J].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7,5(2):173-203;Lu,Yiy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The Rise of Depedent Autonomy?[M].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2009.Hsu 等认为由于中国不同城市社会组织所拥有的资源环境和制度条件差异显著,这使得社会组织需要构建适当的资源策略来匹配现实资源环境的条件。作者通过对北京、上海、昆明和南京四个城市的调研,提出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三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模式:即依赖捐赠者的模式、依赖政府合作的模式和依赖志愿者的模式,并且认为依赖志愿者的模式相较于其他两种模式而言,对于塑造具有参与性的积极公民身份具有重要意义。⑤Jennifer Y.J.,Carolyn L.Hsu & Reza Hasmath.NGO Strategies in an Authoritarian Context,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itizenship:The Ca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Voluntas,2017(28):1157–1179.安子杰(Spires)基于中国的草根NGO 的田野调查发现,国家碎片化的治理结构为草根NGO 的发展实际上提供了生存机会。它们一种关键的生存策略就是识别和利用不同政府级别之间以及任何既定政府内部的观点差异,来寻求资源支持和达成联盟的可能性。虽然在中央层面对于草根NGO 的发展态度是相对比较严格的,但是草根NGO 只要不进行权威挑战并能减轻政府对于公共需求的治理负担,那么双方之间能够相对默契地达成“权宜共生”(contingent symbiosis)的关系。⑥Anthony 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1,(117)1:1-45.朱光喜从我国复杂的政府组织体系和府际关系出发,认为不同政府组织对社会组织的立场和态度呈现出“分化型政社关系”的特点。这种政社关系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社会组织可以针对政府体系内部关系结构、外部关系结构中的分化型特点,采用借力打力、先礼后兵、上浮下沉、左转右移的行动策略,最大程度地谋求组织的发展。⑦朱光喜.分化型政社关系、社会企业家行动策略与社会组织发展——以广西P 市Y 协会及其孵化机构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9(02):67-78.
三、双向赋权下的政社力量互动
从双向赋权的视角来理解政社力量互动,本质上是从平衡的角度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此路径旨在关注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倡导将二者之间的友好合作来达成彼此良性互动和相互赋权的目标。这一理念来自修正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主义者认识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立与脱节抑或国家对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忽略和强制力支配都是错误的,国家权力建设本身就需要通过社会来实现其目标。那么这种修正主义的理念在米格代尔(Migdal)、科利(Kohil)和许慧文(Shue)主编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在第三世界中的支配和转型》中得到充分地论述。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他们提出要以更加平衡的视角来取代传统国家与社会二元独立的框架,认为国家根据其与社会的联系程度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力,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力量可能互为依据,能够为双方创造更多的权力。①Joel S.Migdal,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树立长远的发展战略来跨过特殊利益集团的短见;另一方面,政治发展通常需要健全的公民社会和社会的权力巩固。但是如果依循以往“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实际上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会深深陷入冲突之中,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通常会削弱现存的国家权力,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却离不开国家的有效治理,这种内在张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双重转型的困境”(dilemma of dual transitions)当中。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相互赋权理论的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绕过现有困境的新方法,并可以在经济发展与民主过渡之间建立积极关系。②Miguel Angel Centeno.Between Rocky Democracies and Hard Markets:Dilemmas of the Double Transi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4(20):125-147.
(一)规范论证和互动优势
双向赋权的观点在中国社会组织以及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快速发展。首先是在一些规范性研究的文献中,学者论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张康之认为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人类已经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需要构建适应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型社会体制来应对后工业化的压力。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打破政府本位主义,根除行政傲慢,在实现中心-边缘结构消解以及平等关系确立的基础之上,政府与社会力量才能生成共同行动的凝聚力。而这个过程不仅政府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创新,而且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促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③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02):2-13;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J].社会科学研究,2012(03):35-42.汪锦军指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然而,政府与社会合作更多是一种建构的过程,而非一种自发秩序。这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还依赖于政府与社会的自主性、双方互动的初始状态、互动过程的资源依赖情况以及微观的机制设计。④汪锦军.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J].政治学研究,2015(04):98-105.之后,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三种合作模式的分类框架,包括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阙,并探讨了各种合作模式在功能、制度化程度、资源依赖、非营利组织的地位差异。①汪锦军.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三种模式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9(10):77-80.
此外,其他一些理论视角也对双向赋权提供了新的拓展性思路。如在跨部门合作视角中,不仅仅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而是期待在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两个或多个组织间达成一种合作安排。由于这些组织部门的属性各有不同,使得不同的参与方能够超越各自的视野局限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问题,从而形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②Barbara Gray.Collaborating:Finding Common Ground for Multiparty Problems[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9; Barbara Gray,Jill Purdy.Collaborating for Our Future: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for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可能是必要的且合乎需要的,由于跨部门合作更有可能在动荡的环境中形成,且持续性地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这需要多个部门通过组织链接、共享信息和资源来减少复杂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以共同实现单一部门无法单独实现的结果。③John M.Bryson,Barbara C.Crosby and Melissa Middleton Stone.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44-55.社会资本理论则为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双向互动提供了更为重要的实现机制,特别是帕特南所提出的信任、网络和规范等社会资本的要素,对于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互动、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升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绩效具有重要作用。④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此外,帕特南还区分了横向社会网络和纵向社会网络的不同作用,认为横向社会网络有助于增进公民的信任与合作,纵向社会网络则呈现等级和依附性。⑤罗伯特·D·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那么,从社会资本而言,国家与社会组织要达至双向赋权的目标。国家需要通过横向社会网络来获取社会合法性,改进公共治理的方式;社会组织也需要嵌入于纵向社会网络来获得行政合法性和资源支持,从而实现双方协作共治的局面。⑥汪锦军,张长东.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4(05):88-108.
(二)经验实践与协同发展
另外,在经验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关注社会组织在一些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和递送中的作用,学者们用“合作治理”(cooperative governance)、“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等词来描述社会组织是如何增强了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又是如何提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⑦敬乂嘉.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71;Kirk Emerson,Tina Nabatchi,Stephen Balogh.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2,22(1):1–29; Taco Brandsen & Victor Pestoff.Co-production,the Third Sector and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06,8(4):493-501.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公共服务供给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且有效地应对了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推动了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⑧Stephen P Osborne,Zoe Radnor & Kirsty Strokosch.Co-Production and the Co-Creation of Value in Public Services: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6,18(5):639-653.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递送中,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了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越来越有组织地参与到地方福利服务生产的网络当中形成制度化的供给体系,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资源、合法性、制度支持方面嵌入于国家,而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嵌入与社会组织的运作中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双方实现了共生式发展。①Stephen P.Osborne & Kate McLaughlin.The Cross-Cutting Review of the Voluntary Sector:Where Next for Local Government– Voluntary Sector Relationships?[J].Regional Studies,2004,38(5):571-580;杨宝.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14(02):51-59;王清.共生式发展:一种新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以N 区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为例[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05):16-23; 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 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J].浙江学刊,2017(01):49-56.围绕这一脉络,相当一部分学者专门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会组织参与为例,分析了国家与社会互依联盟的重要性。②Shen Yongdong,and Yu Jianxing.Local Government and NGOs in China:Performance-Based Collaboration[J].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7,15(2):177-191; Lin Peng,Wu Fengshi.Building Up Alliances and Breaking Down the State Monopoly:The Rise of Non-Governmental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18(234):463-485; 张荆红,丁宇.互依联盟何以可能?——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改革走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131-140.而在过去几十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合作也已发展也成为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的新的治理模式,它能够将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与政府机构一起召集在集体论坛中,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达成共识性的决策。当然成功的协作会受制于多种条件的制约,如双方冲突或合作的历史记录、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动机、权力和资源的失衡、领导能力和组织设计以及合作过程中双方面对面的对话和信任建立的情况。研究发现,如果当合作论坛能够专注于那些加深信任、承诺和共识的“小胜利”(small wins)时,合作会趋于良性的循环发展。③Chris Ansell,Alison Gash.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18(4):543–571.埃文斯(Evans)则进一步发展了双向赋权的理论,其代表作《嵌入式自主性:国家与产业转型》是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协同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他认为“嵌入性”和“自主性”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国家不能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操纵和俘获;另一方面,国家制度精英需要嵌入于公民社会中的私人部门的网络之中保持紧密联系。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使国家能够确定和寻求长期的发展目标,并从社会中获得信息和合作,从而使政策得以实施。④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他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信息产业发展中,比如韩国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中建立其比较优势的原因在于国家“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强大的官僚体系以及与私人工业资本的紧密联系使韩国政府能够扮演“助产士”的角色,从而促进了韩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成熟。在埃文斯看来,国家和社会力量的这种深度互动已远远超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补性观点,并且在更为复杂和动态的嵌入式自主中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⑤Peter Evans.“Government Action,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in Peter Evans,State- Society Syner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Berkeley:International and Area Sr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7,pp.187.换言之,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并不会削弱国家的建设性权力,相反,可能为公共治理方式的变革提供有效的途径。因此,强大而稳健的社会组织可以与强大而有弹性的国家并驾齐驱。
四、中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反思与拓展
回顾中国政社关系的研究,既有文献总体上围绕结构与行动视角展开,而当前主流的“行动分析”则呈现出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趋势。早期的“结构视角”以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两大流派的争辩为起点,深入探讨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双方支配性权力的结构边界以及规范性预设的政治社会意义。然而,此视角实际上预设中国的发展应当依循西方社会的发展路径,将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基础性要素和国家结构性的制衡力量,而忽略了中国的现实国情。结构视角无疑戴着西方社会理论的“有色眼镜”看待事实的结果,他们只看到了甚至只愿意看到事实的一面,而有意或者无意掩盖了事实的另一面。这使得关于中国政社互动的行动分析成为打开政社关系黑箱和内在机理的关键路径。归结起来,“行动视角”以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融合、边界模糊为前提,深入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如何进行互动的问题,以此形成了两种分析趋向,即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力量互动和双向赋权视角下的政社力量互动。这种基于政社双方力量平衡与否的前提性依据,创设了中国特色情境下有关政社力量互动行为研究的一些修正性阐释和本土化概念。然而,在本着“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①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01):83-93.的理念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党、政府的制度改革、运行机制以及技术治理嵌入等实践的不断深化,政社力量互动的时空环境及其阐释框架也相应不断调试。因此,无论是从理论拓展还是深度的经验研究,当前中国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具体而言:
一是既有中国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却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政党角色在中国基本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体制构成了我国行政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在功能和运行方式上,党和行政体系存在深度的重合和嵌入关系,甚至决定重大治理政策选择和排序。②孙柏瑛.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逻辑[J].行政论坛,2021(04):50-57.而这种“以政党为中心”的制度构造,无疑拓宽了政社力量互动的主体对象和行动边界。以往“两新”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往往成为管党治党的边缘地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加强对于“两新”组织的扩覆盖工作,并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积极融入到社会组织的战略规划决策之中。党从幕后走向前台的过程,实际上使得社会组织与国家互动关联的纽带转向了与党的新制度关联,而社会组织作为能动者权宜性地生产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将会具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因此,党和国家在与社会互动中有何种行为差异,两者的行动逻辑有何不同,其交互性制度特征又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复合效应,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是既有研究通常将市场力量包含于社会分析的范畴之内,但是对于“社会-市场”甚至三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分析关注不足。虽然从广义的“国家-社会”框架而言,市场力量通常被包含在了社会的概念之内,例如,在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中,有一些观点试图把市场因素融入其中。甚至于在一些经济学观点之中,已经反复强调了市场对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特征。但是,在“国家—社会”具体的文献中,却将社会组织和市场融入在“大社会”的范畴中统一而论,而这无疑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市场”“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和区别。尤其是,市场作为一个愈发独立和自成体系的组织,它已经与社会组织的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这使得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形成“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来推进研究。值得欣慰的是,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有一大批文献聚焦于“国家-市场”的分析,但是当前的文献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市场”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当市场力量也逐渐融入国家—社会的复杂互动之中时,社会又如何同时在两种力量下游刃有余地发挥自身功能性作用并实现组织的持续发展,这也是社会自主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三是既有研究更侧重于互动方式、互动策略来解释政社之间的复杂逻辑,但是对于技术治理变革所带给政社互动行为的影响力缺少反思。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变革与发展,数字化技术给人类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不仅改变了社会的互动交往模式,而且推动着整个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方面,信息技术在政社互动行为的中应用和扩散,除了在不断颠覆科层组织结构的运作逻辑和支配机制,而且也为社会力量赋予新的权能和动能,降低了社会力量集体行动的成本,极大地拓宽了社会汲取资源和捕获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作为新的治理载体,使得政社互动的时空逻辑发生了多维转变,甚至型构了政社力量的边界。如今,在数字化时代,以技术为支撑的平台载体正在高速改变着政社互动的运作模式,成功地将政府与社会连接到具有共同体属性的价值互动结构之中,从原有的主体双向赋权开始借助于技术赋权,通过依托技术赋权转向被平台赋能,从而参与到更多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中来。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嵌入和平台载体在迅猛崛起重构着政社互动行为的新秩序,而我们正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最佳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