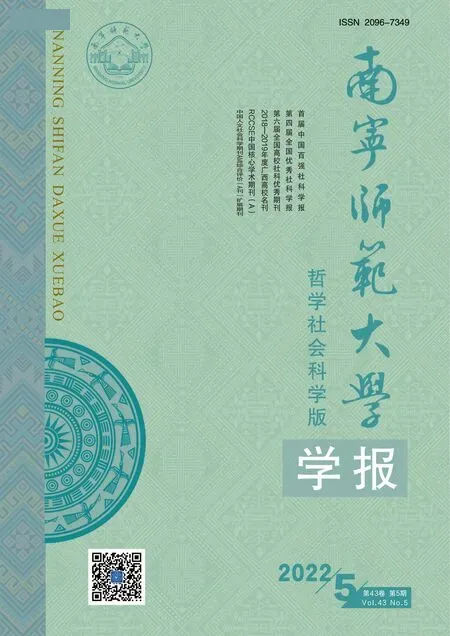季节性集市的空间建构与地方感形成
——以云贵川鸡枞集市为中心的考察
杨 丹
1.贵州师范大学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发展研究基地,贵州 贵阳 550001;2.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集市(Marketplace)是乡村或城镇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空间场所,也是满足农民社会交往、宗教信仰、休闲娱乐、社区认同等公共生活的社会空间[1]。集市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作为人类学的经典议题,有关集市研究的文献和学术积累蔚为大观。西方人类学对集市的研究始于对初民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流动和交换现象等经济行为的探索。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结合早年对“库拉贸易”中的仪式性交换的关注,以及晚年对“墨西哥瓦哈卡乡村集市”的研究,认为交换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经济行为的呈现,“集市在当地人的概念和观点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一种经济机制(Economic mechanism)”[2]。集市的运作给生计方式、劳动分工和物质福利带来极大影响的同时,将分散的聚落和族群整合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
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类学界对集市的研究面向发生了转变,西敏司(Sidney Mintz)、杜威(Alice Dewey)、沃尔夫(Eric Wolf)、库克(Scott Cook)等学者(1)这一时期,关于集市研究的成果有西敏司关于中美洲的集市研究论文《作为联结机制的内部集市体系》,该文将集市交换区分为垂直交换(Vertical exchange)和水平交换(Horizontal exchange)两种,认为买卖双方拥有固定的交易场地、交易时间以及交换规则,便也拥有了一套内部集市体系。杜威通过对位于爪哇岛中东部的莫佐克托(Modjokuto)的个案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爪哇的农民集市》一书,目的在于强调集市与社会环境、贸易模式与农业社会的经济之间的功能关系。继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库克和迪斯金主编了关于瓦哈卡的第三部集市研究著作《瓦哈卡的集市》,该著作分析了集市如何将分散的区域社会联结到一定的区域经济之内。开始关注乡村集市的社会功能和区域时空,认为乡村集市是民众互动交往的重要场所和社会联结纽带。史密斯(Smith)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研究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认为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同时也是行政管理中心[3]。将中心地理论引入中国集市研究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威廉·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通过对中国成都平原传统农村墟市的静态分析来揭示农村市场的形式及规则[4]。有学者认为施坚雅以市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空间结构,从而建构起一套有效的时空协同框架(Spatial-cum-temporal framework)[5]。尽管后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基尔(Alfred)等人类学者分别从符号学、阐释学等视角对印尼的莫佐克托、印度的杜莱等集市展开了“深描”,但施坚雅借助“地理学的区位论、中心地理论作为工具”[6]来研究成都平原集镇墟市的方法,为人类学乡村集市空间体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对中西方集市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在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版图中,集市研究大都立足于杨庆堃、费孝通、施坚雅的集市研究理论,从结构性分析方面分析集市外显的经济功能,从而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问题。当然,基于施坚雅提出的理论框架建立中国的市场体系只是集市研究的一个方面,有学者对施坚雅的集市研究理论提出质疑,如邵俊敏在《近代直隶地区集市的空间体系研究——兼论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一文中提出有别于施坚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三级市场体系的“基层市场-中心市场”的两级市场体系,认为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需要修正[7]。史建云指出,在现实中难以找到施坚雅提出的六边形市场区域[8]。中国云贵川地区一度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集市贸易研究的焦点。如吴晓燕通过对川东圆通场的研究,把乡村集市的发展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相结合,探讨“国家在场”背景下乡村社会经济的自我整合与秩序建构[9];张跃、王晓艳通过对云南昙华彝族“赶街”习俗的调查,透视民族地区集市的文化内涵以及其社区网络功能[10]。贵州农村的定期集市普遍形成于明初,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之后,随着卫所屯田、鼓励垦荒等政策的推行,人口增加和商贸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商业活动的发展及农村集市的兴起,但这一时期的集市主要分布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屯军地或坝子里。清代是贵州集市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贵州边远山区的集市数量迅速增长,集市贸易十分活跃[11]。总的来说,明清时期贵州集市的称谓(2)在贵州,民众称集市为“场”,称“赶集”为“赶场”,一般以地支和与之相应的十二生肖命名。场名多数按十二生肖分别命名鼠场、牛场、虎场、兔场、龙场、蛇场、马场、羊场、猴场、鸡场、狗场、猪场。如某地每逢子午赶场,是因为子属鼠,故每逢子日赶场,称为“赶鼠场”;午属马,故称为“赶马场”。参见肖良武:《20世纪30年代贵州集市研究——以贵定为例》,《贵阳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类型(3)李良品根据农村集市的功能以及地理空间,将贵州农村集市的形成类型分为行政中心型集市、卫所屯堡型集市、土司署城型集市、驿道驿站型集市、水运码头型集市、物资集散地型集市、节日集会型集市和庙会活动型集市八种类型,认为贵州集市的形成与贵州特殊的地位区域位置、丰富的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参见李良品:《历史时期贵州集市形成路径的类型学分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场期制度以及社会功能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回顾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有关集市的研究主要偏重对集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的揭示与探讨,而对集市的交互空间和集市参与者的实践逻辑着墨不深。近年来,受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集市研究开始关注公共空间、消费空间的建构方面。在全球化进程和流动性背景之下,人地关系、“恋地情结”等开始引起人文学科的高度关注,在施坚雅的时空协同框架基础上,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 Y F)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观点——“地方空间理论”也被引入传统定期集市研究之中。而在乡土大量存在的,与自然环境、气候密切相关的季节性集市如何构建其地理和社会空间,以及流动性背景下季节性集市中的食物如何将人地、人人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构建富有价值情感的“地方感”,都是以往集市研究所忽略的。基于此,为丰富集市研究类型,本研究力图提供一种特殊的集市案例——中国云贵川的鸡枞集市。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与传统定期集市不同,每年的四月至八月,中国云贵川三省的城乡之间,会悄然衍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临时集市,专卖鸡枞。这些集市开市时长约4个月,每日的交易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作为野生菌中的珍品,昂贵的野生鸡枞以每千克250~1 000元的价格在这里被交易。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笔者曾多次跟随从事鸡枞贩卖生意的叔叔来往于云贵川三省的野生菌市场。本研究将“鸡枞集市”视为一个日常交互的空间和富有多重意义的地方,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试图剖析集市实践主体如何通过食物的流动建构临时性集市空间。田野调查中,笔者全程参与体验了鸡枞商贩、拾菌人以及食客的日常生活,对集市实践主体进行深度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一般为1~2小时,对部分访谈对象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跟踪调查,搜集到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从而奠定了本研究的实证基础。本研究的田野点主要涉及贵州省水城县、盘州市、花溪区,云南省南华县、易门县,四川省资阳市、泸州市等地,所选取的深度访谈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访谈对象及相关信息见表1。

表1 部分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续表
三、云贵川鸡枞集市的空间建构
传统乡村集市多是依赖血缘、地缘等乡村社会关系来组织、协调和建构的,它建立在约定俗成规则之上,是一种乡土场域中人们相互熟知的交互模式,是人们在特定关系及社会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空间实践[17]。然而,随着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闲暇时间被压缩且呈现碎片化的特点,乡村集市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云贵川鸡枞集市的衍生一方面受当地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近10年来,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已不仅局限于吃饱,地方食物被赋予“有机”“原汁原味”“原生态”“绿色”“富硒”等标签。与白蚁共生的鸡枞对其生长环境的温度、湿度以及土壤的酸碱度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因此,与传统的乡村集市不同,云贵川鸡枞集市的时间与空间是由鸡枞商贩、职业拾菌人、村民以及食客凭借自身对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的感觉经验来参与建构的,其空间分布和时间制度呈现典型的区域性和自发性特征。
(一)云贵川鸡枞集市的时间制度与空间分布
云贵川三省民众喜欢用“五月五,鸡枞拱土,七月半,鸡枞烂”这样的谚语来判断鸡枞上市和退市的时间。事实上,云贵川鸡枞集市的开市时长远远超过了五月、六月、七月这3个月时间。自春耕开始,起早摸黑的村民在农事活动中时常会与刚冒土的鸡枞不期而遇。随着雨季的到来,职业拾菌人也开始在山间忙碌起来。当鸡枞的“头种”出现在市场上之后,“消失”了大半年的鸡枞商贩不约而同地开始争抢“头水鸡枞”(5)“头水鸡枞”:又称“栽秧鸡枞”,指每年插秧时节首度出现在市场上的鸡枞,也是大自然每年第一波生长出来的鸡枞,“头水鸡枞”一般出现在春季,呈骨朵状,数量稀少,因此,其价格高达1 000元每0.5千克,是普通鸡枞的数倍。,鸡枞集市因此而形成。云贵川鸡枞集市在时间制度上与传统集市的计时和场期制度有所不同,为保证鸡枞的“鲜”,村民、职业拾菌人、鸡枞商贩以及食客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日日集”的时间节奏。对于忙于农事活动的村民来说,鸡枞是昂贵的,卖0.5千克鸡枞能换来几千克肉,因此,每日捡到鸡枞的村民一般会将鸡枞送至乡镇的临时集市,以合理的价格卖给熟悉的鸡枞商贩之后重返土地继续从事一天的农事活动。“鸡枞再贵也比不过自己地里的庄稼,捡鸡枞靠运气,不一定天天都能捡到,但种了庄稼就一定能有粮食瓜豆吃(V-01)”(6)此文中的访谈对象用编号指称,文中所引用访谈话语的出处均以编号形式列出访谈对象,置于该引用话语之后,表明该引用话语出自该访谈对象之口,采访者均为笔者本人,特此说明。。可见,“一块不流动的土地便是农民能够生活下去的根本,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以土地占有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的封闭的闭合性”[18]。对于村民来说,农事活动是首要之事,因此,村民的拾菌范围多局限于一定限度的土地范围内,一般不会越出土地的范围去谋求一种超越土地之上的生活,拾得鸡枞被归结于“运气好”。
与“好运”的村民相反,从传统农业生产者中逐步分离出来的职业拾菌人,随着拾菌收入的增加,他们逐渐以此为职业,主动放弃农业生产,发展成以拾菌为职业的稳定群体。每年的三月至九月,职业拾菌人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鸡枞展开,他们于凌晨出发寻找鸡枞,清晨交易完成之后再返回拾菌地,查看老的“鸡枞窝”,寻找新的“鸡枞窝”,其拾菌范围具有不固定性。职业拾菌人对鸡枞的生长环境、市场规律有专业的判断。“下雨天鸡枞冒土快,鸡枞是和白蚁一起成长的,土质疏松的地方,就可能会有鸡枞。鸡枞放不久,吃鸡枞讲究‘新鲜’,职业拾菌人都是凌晨4点多出发,到了7点左右不管找到多少,都要赶到乡场去,鸡枞老板还要运到城里,晚了不好卖(F-01)”。“鸡枞是一波一波地成长,每个捡鸡枞的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鸡枞窝’。捡鸡枞不能用铁器去挖,鸡枞‘聪明’,它们会挪窝,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打着手电筒,悄悄出发找鸡枞(F-02)”。由此可见,职业拾菌人对鸡枞的成长环境以及临时形成的鸡枞集市的交易时间有着十分详细地了解。
作为集市的关键性人物——“鸡枞商贩”的身份角色是双重的,他们有自己的时间节律。每日上午6点至9点,鸡枞商贩在乡土社会扮演着“买家”的角色,他们的手机通讯录或微信里储存着一大批村民和职业拾菌人的信息,对每一位拾菌人的“收获”了解得一清二楚。每日清晨,鸡枞商贩驾驶着简易的摩托车或面包车进行收购,几个来回下来,方圆十几公里地的鸡枞便被他们“收入囊中”。每日上午9点之后,鸡枞商贩的活动空间从乡土转移到城市社区,其角色也从“买家”转换成“卖家”。在乡土社会,“买卖”双方有固定的交易场所,有“熟悉”的交易对象,清晨的交易简单快捷。到了城市社区,由于鸡枞商贩没有固定市场摊位,在集市管理制度的约束之下,野生鸡枞很少进入社区菜场,其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作为城市社区的“卖家”,每一位鸡枞商贩都有自己熟悉的集市空间。“在城里,我们一般是在人流量大的小区菜场旁卖鸡枞。哪些地方有鸡枞卖,市民是知道的,有时候他们比我们来得早,我们这边的人很会吃,不管多贵,鸡枞上市之后总是要吃上几次的。新鲜的鸡枞不愁卖,货源不足时,我们会在云贵川三省之间来回跑,大家相互供货(S-04)”。贵州鸡枞的主要产地是六盘水发耳镇。发耳镇位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年平均气温24℃,年降雨量1 150毫米,温热的地理环境和降水量为鸡枞的生长营造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鸡枞大量上市的时节,贵州发耳镇、盘州市的鸡枞被鸡枞商贩流通至六盘水市中心黄土坡与钟山两个小区附近。四川安岳县的鸡枞大部分流通至春天半岛、刘家湾、狮子山、三贤祠等地。素有“菌香之城”之称的云南易门县,除大部分鸡枞被批发商流通至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销往全国各地以外,玉溪市的菜园、葫芦等农贸市场是新鲜鸡枞交易的主要聚集地。
(二)参与者的实践逻辑
“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讲,乡村集镇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地理空间系统,在这个空间系统内和城市相比,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现象,即‘熟人社会和裙带社会’。”[19]在乡土社会,作为“买家”的鸡枞商贩会根据鸡枞的品相给出合理的交易价格,大家都是“熟人”,讨价还价的现象极少,整个交易过程十分简单干脆。在鸡枞商贩看来,“大家都是知道行情的,一般情况下,抛开耗损,0.5公斤鸡枞平均能赚20元,我们也不会昧着良心乱砍价,捡鸡枞也不容易,凌晨三四点就要出门,还要看运气(S-01)”。作为“买家”,鸡枞商贩对拾菌人的理解换来了彼此的信任,“我跟王老板打交道很多年了,除非他有事不来场上,不然我每天捡到的鸡枞,都卖给王老板,都是熟人,他出价合理,称头也足(F-02)”。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的鸡枞集市与传统乡村集市的交易规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熟人活动的公共空间,乡土场域中的“熟人”关系是“买卖”双方进行合理交易的基础,人们在这种特定关系及社会文化环境中建构集市空间。事实上,不管是乡土还是城区,集市上的买卖都是讲究“人情”关系的,每一个鸡枞商贩都有一群“熟客”,“熟客”通过“人情”关系在交易中得到的实惠最常见的便是价格上的优惠。商贩与“熟客”之间讨价还价的方式千篇一律,如:“我卖给人家都是120元0.5公斤的,你是老顾客了,0.5公斤便宜10元钱卖给你,多少要让我赚点。”“熟客”之间类似这样的讨价还价一般不会持续太久,且成功交易的概率较高。当然,“熟人”的“人情”效用远不止体现在价格方面,鸡枞的“质”和“量”一定是有保证的,慷慨一些的商贩,在称重结束之后,会送出一两朵不完整的“边角货”给他的“熟客”,彼此愉快而顺利地完成交易。
格尔兹对塞夫鲁集市研究时用老主顾关系(Clientelization)来形容“熟客”关系,“老主顾关系是一种趋向,这在塞夫鲁是很明显的,对特殊商品和服务的重复购买者与它们的特殊供应商建立持久不断的联系,而不是在需要的那一时刻搜遍整个市场”[20]。在云贵川鸡枞集市中,食客与鸡枞商贩之间这种老主顾关系并非一对一,同一个食客可能会是两三个商贩的“熟客”,食客会对几个商贩的鸡枞进行比较和选择,这种老主顾关系有效限制了鸡枞集市的规模,新的鸡枞商贩很难融入市场。“尽管中国农村集市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是一个讲人情的‘熟人社会’,但不信任和欺诈交易同样十分常见”[21]。对于食客来说,贸然前往陌生的集市或陌生的商贩那里可能会遭遇“缺斤短两”。昂贵的鸡枞,“在不熟悉的人那里买不放心,万一称头不足,不划算,熟人一般不存在质量问题(C-01)”。因此,彼此之间通过微信或电话了解“供需”,买卖双方形成的老主顾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鸡枞集市的“经济”风险。商贩对自身商品的销售去向心里有底,食客对鸡枞的质量和数量也足够放心,买卖双方基于彼此的信任,通过持续的空间活动实践,共同建构和维系着鸡枞市场的空间秩序。
四、鸡枞的流动与地方感的形成
文化、身份和群体依恋常常通过食物来维持和呈现,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22]。流动性背景下,远离家乡的群体在陌生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陷入维系家乡饮食习惯与融入所在地饮食文化的两难境地,从而引发饮食调适与身份焦虑等问题[23]。在人们看来,来自家乡的食物是在一定的水土特征和自然环境下生产的,这些食物往往比城市工业化生产的食物更具地方风味。人们通过品尝家乡食物来增进与地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在云贵川鸡枞集市中,鸡枞商贩每日的鸡枞销售渠道除本地食客与菌类餐饮商之外,其余三分之一的鸡枞一般会被邮寄给外地食客或销售给鸡枞代购商(7)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云贵川鸡枞市场衍生出了“鸡枞代购”这一职业,外省食客一般通过微信、快手、抖音等平台寻找鸡枞代购商,在代购过程,一般通过视频让食客了解鸡枞质量及来源,在此基础上每0.5千克加收20元代购费。,这两个渠道的鸡枞均流动至浙江、上海、广东等地食客手中。而这些外地的鸡枞食客基本为云贵川三省籍贯,即使他们因地缘阻隔而在集市空间中“缺席”,但基于他们与鸡枞商贩或鸡枞代购商建立的“熟客”信任关系,他们仍然能在短时间内品尝到新鲜的家乡美食。
远离家乡的食客对鸡枞的依恋首先表现在具身的味觉记忆方面,“老派云南人有句谚语,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春天的蕨菜、夏天的莲子和雨季的鸡枞。鸡枞是山珍,自带鸡汤味,又鲜,又香,又甜,小时候寨子里哪家煮鸡枞汤或炸鸡枞油,整个寨子都能闻到香味(C-04)”。“在上海工作快10年了,每年只要端午节一到,我们就会请鸡枞商贩邮寄鸡枞,200多元0.5公斤也不会觉得贵,新鲜的鸡枞,加几根青辣椒,不用其他调料,味道又鲜又香,这种味道只有我们老家有(C-03)”。在对云贵川三省不同籍贯的食客进行访谈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吃出自己家乡的鸡枞味,“有了油鸡枞,可以食无肉,我们小时候吃开水泡饭,但只要在饭里加几滴鸡枞油,开水泡饭便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云南的鸡枞没有我们贵州发耳镇的味道鲜,不是不好吃,就是味道不一样,我们只吃本地鸡枞(C-01)”。 食客的味觉判断与鸡枞商贩的市场规则是吻合的,当市场供不应求时,云贵川三省的鸡枞商贩会进行联动,相互提供货源,外省流通过来的鸡枞在进入市场销售时,一般只卖给生客,熟客熟知本地鸡枞的品相和味道。从食客对故乡鸡枞的味觉偏好可以看出,食物已成为一个地方的象征,反映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故乡食物的特质以肉体记忆的方式烙印在个体之上,成为最深刻的文化基因与最持久的文化行李”[24]。味蕾是有记忆的,鸡枞以其独特的“地方味道”承载着人们对故乡的集体记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鸡枞跟随人的流动而流动。
由于鸡枞本身的“地方味道”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流动在外的食客常常通过品尝地方食物来感知家乡。受访的食客谈论起鸡枞时,很少有人主动提及鸡枞有限的产量和昂贵的价格,但他们一定会饶有兴致地谈论自己、家人、祖先与鸡枞的故事。L先生已经在宁波生活了十几年,每年鸡枞成熟的季节,L先生都会请家乡的鸡枞商贩帮其邮寄鸡枞。在L先生看来,每次吃家乡的鸡枞,都能让他想起小时候满山遍野找鸡枞的情景:“每年这个季节,吃到家乡的鸡枞,都会把小时候的事儿通通回忆一遍,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老家玉米地、小树林里的‘鸡枞窝’。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们捡到的鸡枞,都会拿到乡场卖给鸡枞商贩,我母亲有时候会留下几朵,用牙刷仔细地将鸡枞上的泥巴洗掉,几节青辣椒,加入满满一锅水,煮出来的鸡枞汤比杀年猪的‘刨汤’还好吃,太鲜了(C-05)。”来自家乡的鸡枞不仅是食客忆苦思甜的媒介,还一度成为农村孩子学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我的家乡不产脆李、不产甜桃、不产鸡枞,我估计好多孩子都上不起学,走不出大山,因为那个年代没地方打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几个同乡不管哪家买到鸡枞、蚂蚱、香椿、蕨菜、腊肉一类的家乡食物,都会聚在一起,哪怕只是喝上一碗汤,都稀罕得不行(C-02)”。从食客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食物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事件或场景的丰富情感与生动记忆,尽管身处异地,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品尝家乡食物的味道来保持与家乡的联系,慰藉乡愁。食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被吃、被消化和被消费的对象,它成了唤醒人们记忆、塑造边界、加强团结的特殊物。流动在外的食客邀请同乡品尝来自家乡的鸡枞,这是一种通过享用地方食物完成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在异地他乡,鸡枞在同乡看来是难得的美食,获得鸡枞的主人与大家分享这道菜,这个社交行为背后表征着对同乡的认同和对家乡的想象,“通过品尝的方式与‘地方感’达成最直接的现象学契合”[25],从而唤醒他们对家乡的依恋与认同。
结 语
通过考察云贵川三省的鸡枞集市发现,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乡村定期集市的临时集市。这种集市在中国各省(区、市)的城乡之间大量存在,其主要职能是完成季节性地方食物的交易与流通,笔者将此类集市定义为季节性集市。随时令成熟的各类地方食物,附着当地人的集体记忆与地方情感通过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流向全国各地,围绕着食物的流动,食物生产者、食客、商贩通过持续的空间活动实践,有效地将人地、人人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共同建构了季节性集市的空间秩序,形成了富有情感价值的地方感。从时间和空间定位上来看,季节性集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施坚雅“基层市场共同体”所界定的活动范围。在传统乡村集市社会空间开始萎缩、经济功能和交往功能开始弱化的背景之下,季节性集市与传统定期集市的流通、社会交往等功能实现了互补,在维持乡土社会秩序、促进乡土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