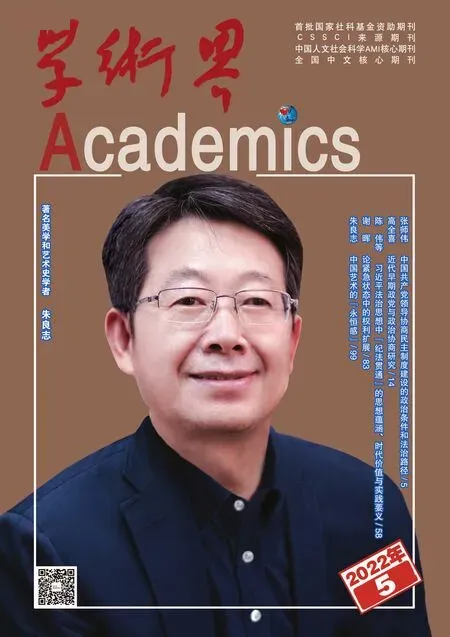近代早期政党与政治协商研究〔*〕
——以梁启超与进步党为中心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30)
政治协商是一个既新且旧的话题,它在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越来越重要,同时,它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事物。如学者埃尔斯特指出的那样,“协商民主的观念与实践,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它们两者皆源自于公元前15世纪的雅典”。〔1〕在近现代法政思想史上,代议制民主的一些不足,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深刻反思,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背景下,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开始兴起,它强调平等协商、积极参与、理性对话等精神,从而弥补与克服了传统民主制度的某些不足。而且,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恰恰是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一些国家在特定时期近现代转型的失败。
亨廷顿曾经描绘了民主化浪潮的三波潮起潮落,近代中国也曾被卷入此历史洪流,且是其第一波浪潮,如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建立等历史事件,皆为明证。尔后,正是因为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民国陷入了所谓的“民主崩溃”。如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所言,“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由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各路军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溃”。〔2〕此论自为学界共识。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国民党和袁世凯”两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独立且重要的历史视角,即梁启超与进步党。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中,不是只有国民党一个政党,而是存在两种对立、制衡的政党力量,它们分别是保守主义政党与激进主义政党。在民初,保守主义政党与激进主义政党渐渐地整合为两个大党:进步党与国民党。〔3〕其中,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进步党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它与国民党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发出着不同的声音,并与其在国会的场内、场外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为近代早期政党与政治协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素材。
一、梁启超的政党理念
虽然在宣统三年《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颁布前,党禁森严,但在事实上,民间早已兴起了各种政治团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改良运动团体与孙中山、黄兴主导的革命运动团体,两派团体的名称虽时有变更,但它们的领袖人物及其抱持的基本政治宗旨则始终未有大的更改。故民国初年的政党,其能在政治上形成各自的团体,并不是在民国初年才组织起来的,它们早在清末就已然成形,所以在党禁解除的民国初年,政党才能以雨后春笋般的形势不断涌现,并隐隐地分为激进与保守两派,在其后的政党持续分合中,最终形成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两强对立。
如前所述,进步党属于保守主义的政党,它是民初各股保守主义力量集结的产物。不过,保守主义只是一种态度或者说价值倾向而已,它并非一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相应政党的特征,当然也决定了作为此类政党代表的进步党的历史命运。因为保守主义势力并非铁板一块的共同体,所以它的整合是非常艰难的,整合的程度也极为有限。在清末,保守主义势力就存在各种区别,当时政治纲领最为明确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当然在清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下,政党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康、梁的结社,主要是以文人间的学会为组织基础,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4〕
然而,梁启超等人并没有放弃组党的愿望,而且正是因为梁启超对政党事业的不断追求,他最终成为了聚合保守主义力量的中心人物。在民国初年成立的进步党是保守主义力量的大集合,而梁启超正是推动它成立的核心成员。如李秀清教授所言,“梁启超虽然只是担任进步党的理事,但实际上是该党的灵魂人物”。〔5〕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对组党又开始抱有非常高的热情,而且此时的任公已经有着非常明确的政党意识。梁启超在此年10月28日给蒋观云的书信中指出:
此度改革,不饜吾侪之望,固无待言……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窃以为此能力之练成,必赖有一机关,若今者能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以组织一机关乎!虽少数,而有机关的发达,可计日而待矣。〔6〕
梁启超此年11月,又写信给其老师康有为:
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7〕
梁启超在此封信中,将组织政党的事宜筹划得非常细致。他认为,首先必须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吸纳、培养党员,以作为将来在国内形成势力的基础。然后,任公认为应该将旧有的“保皇会”改组为“宪政会”。其主要的纲领为:尊崇皇室、张民权、要求良善之宪法等等。〔8〕在梁启超的精心筹备下,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在1907年又成立了政闻社,政闻社是一个以“开国会”为中心目标的政党组织。〔9〕但梁启超毕竟是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钦犯”,在海内通缉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归国公开地活动,所以他只能以幕后指导者的身份来指挥政闻社的相关活动。虽然政闻社罗列了4条宗旨,〔10〕但它主要的任务,其实是促成国会的召开。它一方面公开倡导速开国会,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动员朝廷、地方的大臣,请他们向清政府施压。
在政闻社等多方力量的鼓荡下,清政府在召开国会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政闻社作为一个政团的存在,却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1908年,清政府处分了作为政闻社成员的法部主事陈景仁,并直接指出:“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11〕然后,清政府又直接下达谕旨,宣布查禁政闻社。〔12〕
在清政府的严行查禁下,政闻社被迫停止运作,梁启超主持的此种政团活动乃陷于停顿,他不得不寻求与国内其他立宪派的合作,在其他的结社名目下,继续他的政治活动。然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长期流亡海外,其立足的根基也在海外,国内的立宪派势力非常复杂,其实并非可以藉梁启超一人之力而完成整合。更何况,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前,国内倾向于改革的保守主义力量,就多有不支持康、梁者。陈寅恪先生曾在回忆戊戌变法的派别源流时,指出“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13〕在陈先生的忆述中,乃祖陈宝箴并不认同康、梁的“公羊春秋之学”,虽然他们都主张温和、渐进式的改革,但他们的思想源流迥然有别。茅海建教授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是一部极为杰出的史学著作,该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为陈寅恪先生的“孤论”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论证,或者不妨说,该书其实正是陈先生论断的一则“附注”。茅海建教授在该书中,揭示了张之洞、陈宝箴等改革派对康、梁的激烈反对,例如其指出张之洞写作《劝学篇》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14〕可见,在张之洞、陈宝箴等改革派的眼中,康、梁维新派与支持义和团运动的顽固守旧势力,怕也只在伯仲之间,不过是“邪说”“迂说”的差异罢了。而从字义上看,“邪说”毫无疑问比“迂说”危害更甚。
二、进步党的组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抵可以得出结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力量其实已经被排斥在国内立宪派主流之外,以任公为中心,来整合国内的保守主义力量,注定是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任公在推动保守主义力量结合的过程中,也常常不能不感到意懒心灰。但国内立宪派中,却也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取代任公的位置来牵头组党,因为任公虽然在人事关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尴尬地位,但在流亡海外期间,他运用手中那支具有无限魔力的笔,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政论文章,已然获得了温和派领袖的绝对地位。不过,由于保守主义力量内部复杂的人脉关系,以及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保守主义并非一种真正的“主义”,它赖以团结大家的,不是意识形态式的信仰,而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在政治上的温和、稳健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保守主义的涣散性,以及将其整合的艰难性。
如前文所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维新派,其实与国内的立宪派势力在理念上颇有差异。但在政闻社被严禁后,如果梁启超不想放弃在国内的活动,就必须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合作,毕竟他们在政治上有某种契合性。作为团结国内立宪派的组织,在政闻社被查禁后,“宪友会”承担了这项任务。在清末,可以公开活动的政党组织也只有“宪友会”,它是由“国会请愿同志会”演化而成,国内立宪派势力,以及同情梁启超维新派的势力,皆在其中。“宪友会”的成立,是由于1910年资政院设立后的政治形势使然。资政院的成员有两种,一种是由各省谘议局选举,另一种则是由皇室钦定。其中,前者经由地方民意机关选举而出,可以称之为“民选议员”,后者则可以称之为“钦定议员”,两者在资政院中,各据一半。〔15〕“民选议员”与“钦定议员”在理念上颇相对抗,隐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团体,因此“民选议员”乃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宪友会”,它是立宪派势力在国内的公开聚合,因此在清室退位、民国初建的时期,它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保守主义势力的主要党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李剑农先生甚至称:“宪友会可算是后来进步党的老祖宗”。〔16〕
在梁启超个人的不懈推动中,以及在宪友会的既有组织基础上,民初的保守主义力量在不断地聚合。1913年5月3日,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名通电,宣布合并,成立进步党。其后,在5月11日、13日,又先后公布了《进步党宣言书》《进步党党章》,并在29日正式召开进步党成立大会。至此,梁启超可以说最终实现了他的组党理想,建立了一个统一、温和、稳健的中国式“保守党”。
如前所述,进步党乃由三个政党合并而成,它们分别是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其中,统一党起源于1911年章太炎等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它是江浙地区立宪派势力的结合,在清朝覆灭后,该“联合会”与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合并,在1912年3月宣布改组为统一党,它是一个反同盟会的组织性结合,以保守主义为核心,但也掺杂了各种力量,如其宣言书所言“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17〕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同盟会独大,为了对付如日中天的同盟会,统一党、民社、国民党(此国民党并非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合并,组织共和党,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值得一提的是“民社”,〔18〕该党是由武汉方面的势力组成的政党,它本来属于革命主义的阵营,但由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除了黎元洪获得了一个“副总统”的虚衔外,武汉方面的势力几乎没有分享到任何权位,这引起了“首义”省份势力的不满,他们团聚在黎元洪周围,组织了“民社”,并积极地转而与立宪派势力谋求合作,以制约同盟会。在共和党的建立中,黎元洪的“首义功臣”形象,再次成为了他的政治资本,也成为了共和党用以对抗以革命党自居的同盟会的重要招牌。这也反映出民初政党并非纯粹的以“理念”“国家政策”为导向,相反,在其中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因素。这种以“利”而合的政党组合模式,将在后来的北京政府时期继续上演。
在统一党被合并到共和党以后,由于在合并过程中,多项事情引起章太炎不满,〔19〕他宣布统一党重新独立出来,但只有小部分党员追随之,章反过来对共和党以恶语相骂,认为他们的“腐败”比同盟会的“暴乱”更成问题。由于章太炎的独断专行,随着他重新独立出来的这部分党员对章也越来越不满,章在重新独立的统一党中也日益孤立,不得不宣布脱党,还宣称“亡中国者必政党”。章太炎的这种激愤言行,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同为统一党要员的唐文治即曾致信章氏:
吾辈联合政党,确定纲领,原以改良政治为目的,非以抵制他党为宗旨,若抵制不已,日后不至两党流血不止。……大抵待人不留余地,即系待己不留余地,惟望先生此后以和平广大为心,勿谩骂以为名高,勿偏激以致奇祸,至于办事更不宜鲁莽专制,以集众怨。〔20〕
唐文治的此封信件可以说确实抓住了章太炎个性中的问题,例如“待人不留余地”“谩骂”“偏激”,同时也抓住了民初政党政治的问题,即其不以“改良政治”为目的,而专以“抵制他党”为宗旨。可以说,在政党的分分合合中,“利”占据了主导,而“义”却退而居于其次,像章太炎先生这种性格有些“偏激”者,尚且只是真性情的流露,尚有其可敬、可爱之处,但其他专以“利”为导向者,则成为了民初政党政治腐败、堕落的根源,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印证了章氏对政党“腐败”的指控,以及他对“亡中国者必政党”的预言。
在共和党的纲领中,〔21〕我们可以隐约地把握到进步党的政策导向,因为共和党实际上是进步党的核心,在纲领中,“统一”“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等字样最可表明它的立场。保守的共和党是想以“国家主义”对抗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以“统一”来对抗同盟会主张的“地方自治”。
就在共和党成立的同年(1912年),10月27日由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发起的民主党也正式成立,汤化龙当选为干事长,这也是一个保守主义政党。《申报》1912年8月25日早就刊发了关于民主党拟组的消息,其中指出民主党的组织是出于“……以中国政党萌芽伊始,国民政治观念尚形薄弱,如仅有二党,恐党争日烈,国家异常危险。故决计发生第三党,……定名为民主党”。在是年10月,梁启超归国后,加入民主党的任公曾试图促成共和、民主二党的合并,以完成保守主义势力的大结合,但未获成功,梁个人乃于次年2月宣布跨党加入共和党,同时兼为两党成员。
三、进步党和近代政治协商
在1913年的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取得明显的优势,这让共和党、民主党以及重新独立的统一党都感到巨大的压力。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原先对政党并未过分置意,他想的是在各个政党之间保持相对的均衡,都不过分地亲近,以超然其上。袁世凯显然是立足于传统君主的基本态度来看待党争的,在各股力量的争执中,不左不右,保持作为最后仲裁者的超然地位。可是,1913年的国会选举结果打破了袁世凯的规划,取得国会选举胜利的国民党,在宋教仁的主导下,不断地鼓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等等,这已然威胁到了他的地位。〔22〕袁世凯既然已经注定做不了超然总统,他就不得不开始扶持亲近自己的党派,他甚至决定加入共和党,希望以自己的威望来给共和党壮大声势,但后来因为宋教仁被刺案,袁的“入党”计划被搁浅。〔23〕但袁世凯对于促进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统一党的大合并则给予了很大的助力。这与梁启超的打算不谋而合,梁启超在归国后,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乃与曾经的政敌袁世凯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但袁世凯对保守党派的支持,对于保守党派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短期内支持了保守党派的合并,但袁氏毕竟不是真心帮助保守党派,只是在利用它完成打击政敌的任务。〔24〕对此,进步党人也未必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曾指出:
进步党袒袁总统,袁总统助进步党,事实上不可掩。但袁世凯何爱于进步党而助之,不过欲借以抵抗国民党耳。一旦有数省地盘之国民党消灭,进步党又宁幸免?故两党实有利害共同之点,特愚者不察,专认国民党为敌。〔25〕
当然,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并不属于其中的“特愚者”,他其实并非真的是简简单单地依附政府,梁启超早已宣称国民党是“乱暴派”,袁世凯北洋集团是“腐败派”,保守党势孤力弱,难以同时向它们开战,所以只能先联合危害较轻的一方来压制危害较大的一方,而梁启超认为在“乱暴派”国民党与“腐败派”袁世凯中间,国民党为“祸国最烈之派”,对于袁世凯则“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26〕
在进步党的合并成立过程中,保守主义势力的涣散性,以及政党政治的趋“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袁世凯、梁启超的推动下,三党均有合并以对抗国民党的意向。但民主党作为一个“小党”,却将自己在国会中的十余个议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共和党虽然有两百左右的议席,可缺少了民主党、统一党的支持,它难以与国民党的两百七十个议席对抗。如果加上民主党、统一党的议席,则三党合计也恰恰可以达到两百七十席左右,可以与国民党对抗。故民主党虽然仅仅握有十余席国会议员,但却挟此自重,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要求,逼迫共和党、统一党向它妥协。最终,通过艰难的谈判,在共和党、统一党的不断退让下,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由民主党人汤化龙取得,一个仅仅有着十余席位的国会少数党,竟然取得了众议院议长的位置,这自然是共和党、统一党妥协、支持的结果。但民主党还不满足,最终共和党、统一党不得不又将组建新党后的财政权交给民主党,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拨付的数十万元的政党合并资金,全部由民主党的刘崇佑等人控制。因此,在三党的合并中,原本最小的政党民主党,却反复利用手中的议席,攫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27〕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统一党不可能不心怀怨恨,即使两党的上层能够容忍,广大的党员也很难接受这种权力分配,因此三党的合并其实是极为脆弱的。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部分极感愤懑的共和党成员宣布脱离进步党,重建共和党,就是其例证,这是6月29日的事情,离5月29日进步党召开成立大会,才过去一个月而已。而且,在宪法起草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候,由于政局的变化,进步党最终彻底崩溃,四分五裂,则更是显证。
进步党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讨论,在1913年5月三党联合发出合并通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党的基本理念,该电指出:
(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决议合并,定名进步党,推黎副总统为理事长。党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28〕
将此条电文揭示的进步党“党义”与前面提到的共和党的“纲领”稍稍对比,即可看出它们的相似性,特别是其中的“国家主义”字样。可以说,“国家主义”是保守主义者们在民初共同的理念,具体的体现则是进步党“党义”中提及的“建设强善政府”,“强”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表述,意味着进步党希望建设的是一种以行政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善”则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表述,它意味着它对政府价值取向上的基本诉求。关于“强”与“善”的解读,我们可以从进步党精神领袖梁启超的一篇宏文中得到启发,该文即为任公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明专制论》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宪法学的政论文章,其中“专制”大概可以解读什么是“强”,“开明”则大抵可以对应于“善”。因此,我们可以从该文所昭示的政治、法律理念,来理解梁启超及进步党的核心主张。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进步党的理念虽然相对稳健、温和,但它缺乏一个坚定的核心领导集团,它的整合也非常艰难,往往在吸纳新的成分入党的同时,就会有部分党内势力因为不同意见而脱党,在后期甚至出现了内阁高层党员与国会普通党员的决裂。而且在后期的上下隔阂形成后,高层竟然也决定抛弃普通党员,副署袁世凯的解散国会命令,让国会的进步党成员集体“失业”,这不啻为政党的自我解散。梁启超曾撰文表达他对本党国会议员的强烈不满,该文名为《国会之自杀》,意在表明不是进步党高层附和袁世凯政府来断绝国会生路,而是国会自绝生路,而趋于“自杀”。进步党可以说完全没有政治整合的能力,虽然它是由一群具有相近理念、态度、价值的成员组成,但它在运作上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失败者,这样的一个“保守党”,其实并没有保守的能力。虽然进步党持稳健的政治态度,但它却缺乏力量可言,它的稳健最终并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政治秩序与法秩序。所以,我们不难看到,作为近代早期政党的进步党,它不仅在对外政治协商方面存在形形色色的问题,其内部的政治协商也有极大的问题,而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则是其中的根源。也正是这种缺失,让民国初年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最终失败。
注释:
〔1〕Jon Elster,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Introduction”,p.1.
〔2〕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0页。
〔3〕在民初国会中,进步党与国民党是其中的两大党派,参议院议长、副议长皆为国民党人,众议院议长、副议长则皆为进步党人。
〔4〕与强学会同时期,康、梁党人还曾经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并创办了《湘报》。
〔5〕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6〕〔7〕〔2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8-369、369、667页。
〔8〕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24页。
〔9〕根据史学家张朋园的考证,梁启超组织政党的决定,乃受黄遵宪的影响而成。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23页。
〔10〕《政闻社宣言书》揭示了该社的宗旨: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改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11〕《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12〕上谕曰:“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
〔13〕陈先生谓:“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149页。另,亦可参阅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寒柳堂集》,第170-172页),以为辅证。
〔14〕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15〕北京大学李启成教授点校、出版了《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辩论实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一书,该书详细地收录了作为“预备国会”的资政院的议事记录,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1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3页。
〔17〕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88页。
〔18〕有学者指出,“民社”取意于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其“以卢梭的《民约论》为根本主义”。参考刘劲松:《民初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19〕根据学者张永的分析,引起章太炎不满的合并事宜主要是:1.章太炎理想中的合并,其实与其说是合并,还不如说是吞并(由统一党吞并其他政党),他要求统一后的政党仍然命名为“统一党”;2.合并大会未由章太炎来主持,这是引起他彻底发怒的直接诱因。参见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0〕《读唐蔚芝致章太炎书系言》,《大公报》1912年5月11日。
〔21〕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为:“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和平实利立国”。《共和党成立大会》,《申报》1912年4月28日。
〔22〕在此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均超过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席的总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谷丽娟、袁香甫:《中华民国国会史》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26页。
〔23〕此事见载于梁启超的《致梁思顺书》(1913年3月15日)。
〔24〕张玉法先生指出:“当保守派势力较小时,他(按:指袁世凯)分别扶持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并联合三党而成进步党。当进步党仍不足以与激进派对抗时,他另用分化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击激进派,并不完全仰仗保守派。二次革命后,激进派势力转弱,他就不再器重保守派。时保守派以拥袁有功,欲推展宪政理想,袁就另外扶植没有政治理想的新保守派,冷落或打击具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44-445页。
〔25〕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运动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38页。
〔27〕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9-221页。
〔28〕《三党合并之通电》,《时报》1913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