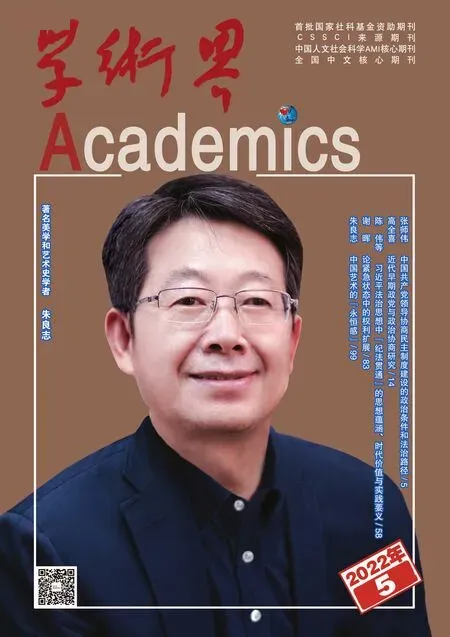20世纪中国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方法反思
——海外中国研究的视角
章立明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概念在研究者身份上虽有部分重合,但两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却大相径庭,如前者主要利用文献资料法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后者则运用田野调查法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民族等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由于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条件,再加上特定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情感体验等,造就人类学村庄民族志虽成为20世纪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在近现代中国史书目中则挂一漏万。〔1〕现在适时对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百年发展史进行梳理,在反思其经验研究与中国研究范式〔2〕之间的关系时,也探讨纾解其方法困境的思路。
一、海外人类学中国研究〔3〕的百年发展史(1877—2019)〔4〕
以1949年和1978年这一近现代中国史的两个关键年份作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人类学中国研究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与成熟期,在全面梳理人类学中国研究百年发展脉络时,厘清其代表人物与成果,为反思其民族志作必要铺垫。
(一)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萌芽期(1877—1949)
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萌芽期始于传教士对山东村庄的调查,而止于新中国成立后对海外研究者关闭在华调查大门。其中以1930年代现代人类学方法成型为界,之前是根据游览经历或者实地收集资料为主的中国游记(调查报告),之后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村庄民族志,成功串连起1978年以后海外学者在中国大陆的再研究(Restudy)。
1.以游览经历或者实地收集资料为主的中国游记(调查报告)
在1860年以后,欧美传教士、外交官、记者和探险家等根据在华经历撰写游记的做法十分流行,〔5〕而本文所说的中国游记除了具备一般旅途见闻的异国情调外,还因为撰写者熟悉相关语言,并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各类典籍和文物,而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参考。
19世纪末期,高延(J.J.M.de Groot)的《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1877)和《中国宗教系统》(1892)就是根据在厦门南普寺一带的调查,特别是收集当地秘密教派活动情况以及官府法令而写成的,现在仍是海外从事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参考书。而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1919)、《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1925)和《中国文明》(1926)等,则是其利用了在华期间收集的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完成的。
国际学术界把蒙学、藏学、苗学和汉学等都视为东方学的分支,而本文则把19世纪末以少数民族地区游览(调查)经历撰写的成果都归并在中国研究当中。主要包括以下成果: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的《喇嘛之国》(1891)、《1891—1892:蒙藏旅行日记》(1894)、《西藏民族学札记》(1895);鸟居龙藏的《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1902)、《苗族调查报告》(1905);葛维汉(David C.Graham)的《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4)、《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58)、《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1961)等;史禄国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1924)、《通古斯人的心理特质综合体》(1935)等;成为纳西学研究典范的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947);费子智(C.P.Fitzgerald)的《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1941)、《大理1936—1938》(2006);顾彼得(Peter Goullart)的《被遗忘的王国》(1955)、《彝人首领》(1959);石泰安(Rolf A.Stein)的博士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和1962年出版的《西藏的文明》。
2.立足中国乡村的村庄民族志
正如萨姆·柏格理(Samuel Pollard)的成名作《在未知的中国:一个传教先驱在中国西部野蛮而未知的诺索部落中的观察、体验与探险记录》(1921)书名所展示的,报告是在“观察、体验与探险”的基础上完成的。而马林诺夫斯基通过长期生活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来了解岛民的文化事实与活动细节的做法,“奠定了田野调查法在现代人类学中的权威地位”,〔6〕正因为如此,对于国外学者没法提供村庄生活细节的成果就不能算作是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当然,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村庄民族志之所以备受争议,其中除了研究者本人身为村庄中的一员(如费孝通之于开弦弓村、杨懋春之于台头村)外,就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并非是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等问题。
1872年,明恩溥(Arthur H.Smith)在山东恩县庞家庄(现属武城县郝王庄)建立美国公理会第一个农村基地,他认为“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7〕撰写了《中国人的气质》(1894)和《中国乡村生活》(1899)等;任教上海沪江大学的葛学溥(Daniel H.Kulp)也认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选择某些群体、村落和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中国社会的功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未来的趋势”,〔8〕他根据对广东凤凰村(广东归湖镇溪口村)的调查,写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1925);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身份来华的西德尼·甘博(Sidney D.Gamble)根据对华北农村的调查,撰写了《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会》(1954)、《1933年以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活动》(1963)、《定县秧歌选》(1970)等;莫顿·弗莱德(Morton H.Fried)的《中国社会的结构:一个中国县城的社会生活》(1953)主要考察了土地改革前安徽滁县地主与佃户的关系;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的《旧中国的乡村生活——云南高峣村研究》(1963)描写了其1938年在云南昆明高峣村的观感与体会。
除了以上这些冠之以村庄研究的成果外,这一阶段能被称为村庄民族志的作品主要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他们留学欧美受到专业训练,选择了具体村庄从事调查,而且全部外译的成果成为海外中国学者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具体包括如下成果: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4和1948);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云南乡村经济研究》(1945);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和《共产党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村庄》(1959);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以及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1947)等。
(二)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发展期(1949—1978)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成熟期,依托一个具体村庄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田野调查已成为写作人类学民族志的基本前提,1951年我国高校经过院系调整,人类学系停办后人类学民族志也就名实俱亡。在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包括少数留在大陆的外籍人士亲历中国革命与政治运动的文字记载,以及那些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学者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作为替代田野点,书写的包括家庭婚姻、经济交换、民间信仰与社会交往等内容的村庄民族志。
1.大陆农村政治运动亲历者的红色中国报告
除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1928)和《中国人征服了中国》(1949)、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的《中国的惊雷》(1946)和白德恩(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1949)等少数有关红色中国的报告外,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访问中国农村的外籍人士所留下的文字记载,它们都成为海外中国研究了解红色中国的重要资料,从而“通过小村庄里村民的生活,让美国人第一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CIA报告中的中国”。〔9〕
当然,这些基于中国村庄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研究的成果其实屈指可数,有代表性的如加拿大国际观察员伊莎贝尔·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Isabel Crook & David Crook)夫妇基于对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的调查而撰写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1959)、《阳邑公社的头几年》(1966)、《十里店(二):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1979);美国记者韩丁(William Hinton)根据山西省张庄土地改革而撰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1966);悉尼大学人类学系葛迪斯(William R.Geddes)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1963);以及瑞典作家兼记者简·米尔达尔(Jan Myrdal)的《来自一个中国农村的报告》(1965)等。
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敏感期,因此这批成果的调查时间普遍不足,如最长的十里店调查为6个月,最短的开弦弓村调查只有4天,但是这些描写中国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作品在人类学中国研究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如韩丁在整理张庄土地改革运动1000多页调查笔记基础上写成的《翻身》,先后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和孟加拉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
2.作为剩余中国(Residual China)象征的港台村庄民族志
1950年代,施坚雅(George W.Skinner)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组织实施的伦敦-康奈尔项目(London-Cornell Project)把港台视为“非华人学者唯一能够进入的华人社会”,〔10〕也就是说,即使大陆对海外研究者关闭了调查大门,然而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把港台视为剩余中国的象征以此走上学术之路的大有人在,如(前往)“台湾从事汉人社会研究的至今不下四五十位”。〔11〕除了葡萄牙、英国和日本等国在上述地区留下的官方资料外,日据时代的冈田谦和富田芳郎等人关于台湾宗教信仰、方言族群和婚姻家庭等内容的研究也不断激发后续研究者的延伸与对话。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港台村庄民族志主要有如下成果:增田福太郎的《未开化社会中习惯法的建立》(1957);弗里德曼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1957)、《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中国宗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1966);葛伯纳(Bernard Gallin)的《台湾新兴村:一个变迁当中的中国村庄》(1966);波特(Jack M.Potter)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1968);裴达礼(Hugh D.R.Baker)的《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水》(1968);芦蕙馨(Margery Wolf)的《林家:中国农民家庭研究》(1968)、《台湾农村中的妇女与家庭》(1972);戴瑙玛(Norma Diamond)的《昆生:一个台湾渔村》(1969);焦大卫(David K.Jordan)的《神·鬼·祖先: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仰》(1972);帕伯特(Burton Pastermak)的《两个中国村庄中的亲属与社区》(1972);劳伦斯·克瑞斯曼(Laurence W.Crissman)的《台湾西南彰化平原的乡镇:中心市场理论和中国人的市场体系》(1973);芮马丁(Emily M.Ahern)的《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丧葬礼仪》(1973)、《人类学中的台湾社会》(1981);华琛(James L.Watson)的《移民与中国宗族:香港与伦敦的男性》(1975);孔迈隆(Myron L.Cohen)的《合家与分家:台湾美农镇的中国家庭》(1976);武雅士(Arthur P.Wolf)与人合著的《中国的婚姻与收养制度1845—1945》(1980);柏桦(C.Fred Blake)的《一个中国集镇的族群与社会变迁》(1981);郝瑞(Steven Harrell)的《犁头村:台湾的文化环境》(1982);末成道男的《台湾阿美族的社会组织与变化:从上门女婿到娶媳妇》(1983);科大卫(David W.Faure)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香港东部新界的宗族与村落》(1986);以及桑高仁(Paul S.Sangren)的《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与魔力》(1987)等。
在1960年代,立足香港作中国大陆研究的也不乏其人,这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1963年香港成立大学服务中心,即1988年落户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能提供涉及大陆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等内容的报刊查询服务;二是能在香港找到大陆农村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并且愿意提供自身的经历和想法,如陈村研究的基础就是“通过26人223次访谈收集到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材料”。〔12〕依据文献与访谈资料撰写的成果主要包括:帕里什(William L.Parish)和怀特(Martin K.Whyte)的《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1978);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乔纳森·安戈(Jonathan Unger)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1984);以及赵文词的《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和权力》(1984)。
(三)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成熟期(1978—2019)
随着视中国为头号敌国的冷战思维开始消弥,再加上1978年中国大陆逐渐对海外学者开放田野调查,回归学术的人类学中国研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成熟期,一方面表现在海外学者对中国大陆经典田野点的再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国研究者基于性别和族群敏感性,撰写出内容丰富与视角多样的人类学民族志。
1.对中国大陆著名田野点的再研究
1981年,费孝通因《江村经济》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他在颁奖大会上发表“三访江村”演讲,既是感谢国际人类学会对中国人类学成果的认可,也是中国将对海外研究者重新开放田野点的重要信号。
作为人类学重要方法之一的再研究既可以是研究者对自己田野点的研究,如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en Lynd)之于中镇(Middletown)(1890—1925);也可以是对前人田野点的研究,如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对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萨摩亚岛(Samoa)的批判性研究。费孝通、林耀华和杨懋春等人也曾多次访问过自己的田野点,如费孝通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曾经27次到访江村;而“截至2014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朝鲜、新西兰、冰岛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访问江村超过100批次”,〔13〕调查内容涉及家庭生活、人口结构、民间信仰、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等。此外,宝森(Laurel Bossen)对禄村、戴瑙玛对台头村也进行过再研究,以此来把握我国乡村发展的整体轮廓,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规律。
1989年,陈佩华等人第一次踏上陈村的土地了解改革开放以后陈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写作了《陈村》的姊妹篇《陈村:全球化中的变革》(1992)一书,现在“陈村”系列已成为海外研究1949年以后我国华南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成果。此外,1940年,伊莎贝尔·克鲁克曾经在重庆璧山大兴镇对1500余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态进行过调查,从1981年起,她又5次重访大兴镇,直到2013年出版《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
2.拓展中国研究的相关内容与视角
自1980年代开始,海外学者在中国大陆从事田野调查的条件大为改善,从而不断拓展中国研究的研究内容与视角。首先,年轻学者在高校做访问学者,如石汉(Hans Steinmüller)之于清华大学、朱爱岚(Ellen R.Judd)之于中山大学;或者以特聘方式任教于国内高校,如柏桦之于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林(Colin Mackerras)之于中国人民大学、王富文(Nicholas Tapp)之于华东师范大学和魏乐博(Robert P.Weller)之于中山大学等;其次,调查时间相对充裕,如《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在历经9年18次的时长数千小时的访谈基础上完成,葛希芝(Hill Gates)等人所作的缠足研究访谈了陕西农村1800多名缠足妇女;最后,研究水准提升且上乘之作不断涌现,如《文化、权力与国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和《私人生活的变革》就先后斩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在1979年以后,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孔飞力和科大卫,社会学家戴慧思(Deborah Davis)和经济学家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等人进入中国大陆,通过具体村庄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已成为中国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一阶段的成果有萧凤霞(Helen F.Siu)研究广东新会环城公社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1989);黄树民聚焦福建厦门林村的《盘旋之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眼中的中国农村变迁》(1989);波特夫妇关于广东东莞茶山镇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1990);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Pickowicz)和赛尔登选点河北饶阳五公村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991);阎云祥研究黑龙江双城下岬村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199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2003);任珂安(Andrew B.Kipnis)以山东邹平陈家村为调查点的《制造关系:中国北方农村中的情感、自我与亚文化》(1997);安东尼·赛奇等人选择以广东东莞一个村庄的变迁来研究中国全球化的《中国村庄,全球市场:新集体与农村发展》(2012)等,内容涉及大陆基层社会的运转机制、婚姻家庭与计划生育、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招商引资等。此外,海外中国学者对于原有宗教主题不断拓展出对墓碑、烧钱和慈善等新内容的研究,如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2001);柏桦的《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2011)以及魏乐博的《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2015)、《宗教与慈善:中国社会生活中善良品格》(2017)等。
除了拓展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常规内容外,海外中国研究者还从性别和族群视角来聚焦全新的主题。如从性别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梳女、缠足和性别制度等方面,其中,对自梳女的研究主要包括马乔里·托普利(Marjorie Topley)的《广东农村的婚姻排斥:中国社会中的妇女》(1975)、詹尼斯·斯托卡德(Janice E.Stockard)的《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中国南方的婚姻模式与经济策略1860—1930》(1989)和萧凤霞的《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1996)等;对缠足的研究包括桑德拉·亚当斯(Sandra M.Adams)的《19世纪英语世界解读的缠足现象》(1993)、柏桦的《中国理学下的缠足与对女性劳动的占用和剥削》(1994)以及宝森与葛希芝合著的《缠足的双脚,年轻的双手:中国乡村缠足的消亡》(2017);而宝森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2002)和朱爱岚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2008)则关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别制度变迁过程。
从族群视角关注的内容多集中在身份认同、民族识别以及主体性等方面。1980年代,郝瑞和王富文等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地区,从而带动海外中国研究从汉民族转向非汉民族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戴瑙玛的《给苗蒙下定义:明、清和当代视角》(1997)、杜磊(Dru C.Gladney)的《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1998)、郝瑞的《西南中国的族群性》(2000)、埃里克·缪格勒(Erik Mueggler)的《野鬼的年代:中国西南的记忆、暴力和空间》(2001)、路易莎·沙因(Louisa Schein)的《少数民族法则:苗族与中国文化政策的女性主义》(2000)、李瑞福(Ralph A.Litzinger)的《另类中国:瑶族及其民族归属政治》(2000)、海伦·瑞丝(Helen Rees)的《历史的回音:现代中国的纳西音乐》(2000)、王富文的《中国的“蒙”:情境、能动性与想像性》(2001)、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2010)以及石汉的《共谋共同体:中国农村的日常伦理》(2013)等。
二、人类学中国研究与中国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厘清
自1955年以来,哈佛学派在“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观”和“后现代无中心”等基础上形成了“西方中心”“中国中心”和“全球化无中心”等中国研究范式。作为中国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学村庄民族志描述的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抽象理论,而我们确有必要厘清这种经验研究与中国研究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14〕除了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外,人类学中国研究也为中国研究范式提供了民族志材料;而强调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内部差异,多民族国家内部非汉民族存在等中国研究范式也形塑着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村庄民族志。
(一)“西方中心”范式及为其提供佐证材料的村庄民族志
“西方中心”研究范式至少包括“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其共同点都是把西方的入侵作为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唯一因素,而“这三种模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和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15〕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1948年初版,此后数度再版)、《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1954)、《中国:传统与变革》(1978)等书中,根据1840年以后中国遭遇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即从《南京条约》到巴黎和会,“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16〕在费正清看来,近代中国社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困境,必须要由强大的西方来推动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新兴力量不少又源自西方”。〔17〕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传统-现代”模式。他说:“尽管中国曾有过重要的科学成就,但儒家文人整体上对科学缺乏热情,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传统中至多只有科学的火花,缺乏那种汇入世界潮流的,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18〕于是儒教从普世性价值变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乃至博物馆的陈列物,导致了反映中国思想变革结果的共产主义变体的产生,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已经产生。〔19〕也就是说,在海外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已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变化,只有经历西方社会的猛然一击后,才能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走入近代社会。
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崩溃、民族灾难以及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harat Brown)在《帝国主义之后》(1970)一书中说:“帝国主义无疑仍然是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在这些关系中,经济不发达国家从属于经济发达的国家。”〔20〕这种认为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都是在西方刺激下所引起的观点,本身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因素,导致了不能从中国内部来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因与过程。
在“西方中心”范式中,影响最大的是成型于1940年代晚期并不断得到完善的“冲击-反应”模式,它虽然主要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献档案,但是也得到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民族志材料支持。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做得非常好,如果没有了他的书,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将大大贫乏”。〔21〕《江村经济》描述了开弦弓村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面临解体并被裹挟进入世界市场的现象。如1934年,日本向美国大量倾销蚕丝,同年中国蚕丝出口量与1930年相比下降了80%,“国内蚕丝市场随着(外部)市场的缩小,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22〕从而间接佐证了“冲击-反应”模式的合理性,因为“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了)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23〕
(二)“中国中心”范式难以在中国田野中得到有效检验
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24〕而孔飞力、魏斐德、裴宜理、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业已证明,“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25〕从而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研究范式提出强烈批评。
1984年,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他说:“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件。”〔26〕具体而言,就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27〕也就是说,柯文是在对西方中心论的严厉批判中建立起自己以中国为中心的全新研究范式的。
具体而言,人类学中国研究如何理解这种“中国中心”范式呢?它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主位研究”(Emic Research),他在评价《江村经济》时说:“作者(费孝通)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28〕或者如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是“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29〕我们知道海外中国研究者进入的无论是汉或者非汉民族的村庄,其实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参与观察,再加上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他者化的过程。
当然,在“关注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的想法”〔30〕的人类学中国研究成熟期要检验是否以中国为中心则相对容易,比如足够充分的调查时间以及得当的访谈法能够接近观察对象,了解他(她)们的想法并接纳其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以缠足为例,柏桦等人的研究将缠足原因从满足男子的官能感受和性兴趣转入到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占用和剥削方面;宝森说:“在我1996年访问过的一个村庄里,我发现该村仅存的手织品,竟是老年妇女们用来绑小脚的薄长裹脚棉布”;〔31〕在她与葛希芝对陕西1800多位缠足女性进行访谈后也确定经济目的才是缠足产生的主要原因。阎云翔基于自己在下岬村7年的务农经历和8年当中多次访问该村的调查经历,才能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揭示不同年代男女情感表达方式和因老人赡养起纷争的家庭纠纷过程,最终展示了中国村庄当中村民私人生活出现的巨大变迁。
(三)“后现代无中心”范式引导人类学中国研究走向新变革
随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一书的出版,后现代多元无中心模式已初露端倪,即否定西方史学的宏大叙事、关注生活在村庄的人群和非汉民族的存在、拓宽非官方史料文献的资料来源、注重对文本意义的阐释等,从而引发人类学中国研究有关对象与方法的重大变革。柯文、杜赞奇和史景迁等人均有相关著述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1996),即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重新审视与最新档案材料的完美结合。
其实作为“冲击-反应”模式创始人的费正清自己后期的成果也已显示受到“后现代无中心”范式的影响。1991年,费正清在其引用627位学者930部作品完成的《中国新史》一书中,明确提出“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32〕当然,所谓《中国新史》的“新”既没有表现为以西方为中心,也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费正清最终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后现代无中心”范式。虽然从逻辑上看,西方中心模式和后现代无中心模式是不相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有悖后现代理论中的增生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liferation)。正如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所说的,“发明和阐发出一些同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不相一致的理论,即使前者碰巧是得到高度确认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法论都是多元主义的方法论。”〔33〕从这个意义上说,费正清的《中国新史》本身就契合这种多元解释特质,从这一层面上说,费正清既是“西方中心”范式的始作俑者,也是其终结者。就如同列文森在其早期著作中也说:“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其异国情调,或者对西方战略的重要性。研究它是因为我们试图用来理解西方的那个话语世界,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而不必强求二者有相同的模式。如果我们能这样去理解中国和西方,也许我们就能有助于造就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34〕
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2008)本身也超越了“西方中心”和“中国中心”范式,将中国国内移民和跨国跨境移民作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进行剖析,充分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其实人类学中国研究者也很快意识到即使是普通村民也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当中,而是与外界保持诸多交流,特别是对于跨国(境)居住族群更是如此,现已有多人运用多点民族志法(Multi-sited Ethnographic Research)撰写了经典民族志作品,如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1987)、《中国:一个宗教国家》(2010);王富文的《主权与叛乱:泰国北部的白苗》(1989)、《西南中国的部落民》(2000)、《中国的“蒙”:情境、能动性与想像性》(2001);路易莎·沙因的《少数民族准则》(2000);欧爱玲(Ellen Oxfeld)的《血汗与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1993)和《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2010)等。
三、人类学村庄民族志的现实意义及其解困之路
自1939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问世以来,在饱受赞誉的同时,也夹杂着批评之声,其实这是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人类学村庄民族志方法的现实意义与存在不足的讨论。我们知道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的可观察单位,也是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单元,但是无数村庄的叠加并不能堆积出一个完整的中国,而注重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对于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大型文明社会来说是不充分的,需要考虑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从而拓宽中国研究的视野。当然,人类学中国研究运用史料分析与区位地理相结合等方法已经作出回应,以此来纾解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
(一)人类学村庄民族志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野蛮社会或者简单社会中成熟起来的现代人类学方法,在1930年代被中国人类学家用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居住在村庄,于是村庄就成为其基本研究单位,那么通过研究村庄就能认识中国社会吗?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中的村庄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他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和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整个中国的缩影。”〔35〕当然,埃德蒙德·利奇(Edmund Leach)对此并不认可,他说:“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36〕弗里德曼和施坚雅也曾发表过类似看法。如果村庄民族志不能起到反映中国社会的缩影作用,那么,作为经验研究的人类学民族志有何现实意义呢?
1.人类学民族志聚焦小范围的人类活动
与其他社会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民族志本身是一种聚焦小范围人类活动的研究,如果村庄研究能够提供符合田野工作规范与描述方法达标成果的话就算是成功的研究,其核心是基于一个单一的小范围内人类活动的观察、记录与分析。既然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居高不下,那些细致入微且内容翔实的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就十分受欢迎。如1945年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初版出版,截至1966年已再版到了第7版,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劳作周期、季节性农作物以及农户的食物结构等内容。
1958—1960年,武雅士夫妇造访台湾的下溪洲,通过系统观察和访谈3~11岁在村头、河边和树下玩耍的儿童,再加上观察母亲的育儿方式并与之进行交谈,形成了一份长达2000多页的有关儿童日常生活与互动关系的精细记录,2015年因武雅士的离世书稿“中国儿童和他们的妈妈”就此搁下尚未最后整理。而在1990年代,海外中国研究者想对下溪洲儿童进行再研究时,发现当地儿童已全部住进了公寓,在城市化进程中研究对象已然消失殆尽了。其实民族志对下溪洲儿童研究的意义就在于“60年前,一个台湾汉人村庄中,小孩子的成长世界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对儿童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儿童发展,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人类共性和文化特性,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37〕
2.村庄民族志有助于完善中国研究的理论范式
“中国研究范式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其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研究,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中国田野经验击破它们,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中国的情况才有助于完善中国研究范式。”〔38〕
英国人类学家根据非洲田野经验提出无政府(无国家)社会中的裂变宗族概念,而弗里德曼则发现在中国东南地区存在着宗族和村落明显重叠的现象,即同一个姓氏的村民聚集在一个村落,他们声称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通过宗族祭祀和宗族谱系来确定不同宗族间的边界等。弗里德曼根据广东和福建在中国的位置来寻找当地宗族组织发达的原因,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随后,裴达礼、王斯福、芮马丁、帕伯特和庄英章等人在台湾的田野调查则发现台湾村庄以杂姓村居多,宗族组织并不发达,与中国东南地区的边陲性也没有关系;当地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并没有促进宗族发展,反而形成了非宗族组织;在台湾开发初期出现的“唐山祖”是一种基于地缘而非血缘的超宗族组织,这些经验研究是对中国宗族组织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思考,进一步完善了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或者说有利于完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纾解人类学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
弗里德曼认为从“无文字社会”或简单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民族志并不适用于研究一个像中国这样有着丰富历史文献,深具影响力的国家体制,以及区域内互动频繁的宗教、经济与族群的文明社会,也就是说通过村庄研究难以理解整个中国。当然,如果以村庄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联结点,强调人类学与历史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结合,也可以在强调村庄研究的微观洞察时增强历史纵深与整体性把握,从而纾解单纯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
1.把史料分析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的村庄研究
弗里德曼认为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高度分化的文明社会,“借鉴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和成果,在较广阔的空间跨度和深远的时间深度探讨社会运作机制,才能真正理解中国”,〔39〕从而为解决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提供思路。
1950年末,弗里德曼在香港新界待了十多天,认为“对于研究过去的汉人社会还有文献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地利用”,〔40〕于是他就在当地收集族谱、契约账簿等民间文献和港英当局的户籍等官方资料,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基于明清以后至民国期间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结构,宗族之间的祭祀与族谱,包括绅士、税收和秘密会社在内的宗族与国家关系,构建起一个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统一框架,即村庄不仅体现了国家力量的渗透,而且村庄内部宗教与宗族关系也象征着地方的分立过程。
从1980年代起,人类学村庄民族志已经不再将村庄当作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探讨两者的关系上,日本和美国研究者以满铁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基础,再通过田野调查获取访谈材料并收集族谱与契约等民间资料进行研究,以历史分析结合田野调查丰富了村庄研究成色。随着中日恢复正常邦交关系,日本学者对华北村庄进行了再研究,如三谷孝的《中国农村变革与家庭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1999);内山雅生的《从村庄解读中国——华北农村五十年史》(2000)、《现代中国农村和“共同体”》(2003)、《日本的中国调查和传统社会》(2009);而滨岛敦俊的《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2001)〔41〕则是在对长江三角洲的32个市、县、镇和村的多次访谈基础上,加上对明清和民国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组织架构与活动领域。美国学者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马若孟(Ramon H.Myers)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1969),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0),其中就有多部荣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2.基于史料文献与区域地理的立足村庄并超越村庄的研究
1949—1950年,施坚雅在四川华阳和金堂两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大型村庄很少,大都是由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各类小村庄,于是他放弃了最初设想的调查一个100来户村庄的计划,转而重点考察一个包括2500多农户在内的既分散又联系的经济区域,其中包括访谈若干村民,并且重点参考了当地的方志、报纸和相关的外国人游记等文献资料,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允许很多地区的市场体系在现代化开始之前达到充分成熟,还由于可供利用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市场的文献为研究传统社会内部全面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中国的情况对于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民交易活动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2〕1964—1965年,施坚雅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把农村市场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三种类型,并把低于基层市场水平的村庄分为聚居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考察了与之相对应的“小市”和“幺店”(杂货店),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市场的“正六边形”模型,即“假设在同一纬度的平原上,资源均匀分布,那么每个市场的分布应当符合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因此,每个市场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一个正六边形”。〔43〕施坚雅模型揭示了研究中国这样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和中央政权统治的文明社会,需要结合文献资料与区域地理才能作出既立足村庄又超越村庄的研究。其实杨懋春的“台头村”研究业已揭示山东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村庄—市场三级关系,即一个小村庄群由一个宗族的几个家庭组成,它们往往分散在邻近的两三个村庄当中,它们之间维持着内部紧密的初级群体(家庭)关系和次级群体(邻里、亲属以及学缘等)关系,并与外部市场保持着不计距离的松散关系。
当然,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正六边形模型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如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就采纳了施坚雅关于中国市场体系和基层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概念表述为市场社会,认为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市场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44〕即市场社会已经超越了村庄成为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台湾村庄民族志在立足村庄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村庄的“市场圈”“祭祀圈”“信仰圈”和“方言群”概念,涉及市场体系、宗教祭祀、宗族组织、通婚半径以及区域文化变迁等内容。虽然施坚雅模型不断受到人类学中国研究经验材料的挑战,但其将中国划分为县、镇、乡、村的基层社会思路已成为中国研究的共识,包括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和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内的作品也都从这一基本结构开始进行叙述与分析。
注释:
〔1〕1992年10月,美国加州大学圣迪戈分校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群收录257种文献目录,其中就包括杨庆堃、杜赞奇和陈佩华等人的作品;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十至十五卷中,涉及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其中也收录了多部村庄民族志;豆瓣读书列出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共258册,其中也有多部村庄民族志。国内学者对此已作过一些整理和研究,如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张海洋:《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上中下),《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4期;覃德清:《海外汉学人类学:方法抉择与价值取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孙庆忠:《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韩鑫:《读近年海外汉学家史学著作》,《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郑海花等:《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陈刚:《西方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等。考虑从学科分类(历史学与人类学)、遴选标准(汉学与中国研究)和时间分期(剑桥中国史截至1982年,国内研究截至2010年)等原因,本文认为需要对中国研究中的村庄民族志进行重新归纳并增补近10年的研究成果。
〔2〕1955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成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形成美国中国研究的哈佛学派。作为汉学向中国研究过渡的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哈佛学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指导的百余名博士后来任教于美国各高校(不限于哈佛大学)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著名的有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柯文(Paul A.Cohen)、孔飞力(Philip A.Kuhn)、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大卫·阿古什(R.David Arkush)、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毕克伟(Paul G.Pickowica)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人。中国研究范式是哈佛学派的主要成就之一,具体内容将在下文中涉及。
〔3〕汉学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在国内的译名往往与汉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社会人类学等的概念交织在一起。本文统称其为人类学中国研究或者中国研究的村庄民族志,特指在具体的村庄中进行田野调查,并以民族志形式来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成果。
〔4〕本文涉及中国研究著作的出版时间均为其外文版的初版时间,而2019年是柏桦《烧钱》中译本的出版时间。〔美〕柏桦:《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袁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5〕1998—1999年,时事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两辑图书,主要涉及西方人对于清政府和民国时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见闻。如第一辑包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和《中国乡村生活》;第二辑包括《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国变色龙》《美国的中国形象》和《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6〕Bronislaw Malinowski,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p.24-27.
〔7〕〔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页。
〔8〕〔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页。
〔9〕甘琦:《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记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读书》2011年第6期。
〔10〕〔澳〕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赵红英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1〕庄英章:《谈人类学家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张炎宪主编:《历史文化与台湾》,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1988年,第417页。
〔12〕Antia Chan,Richard Madsen,and 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2-6.
〔13〕《江村“朝圣”:喧嚣与困顿》,澎湃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775650424514429&wfr=spider&for=p。
〔14〕任放:《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15〕〔25〕〔26〕〔2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5、88、210-211、201页。
〔16〕Ssu-yu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
〔17〕〔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页。
〔18〕〔19〕〔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2、144页。
〔20〕转引自〔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04页。
〔21〕〔39〕Maurice Freedman,“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I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4,No.1,Mar,1963,pp.9-10,1-19.
〔2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23〕〔28〕〔3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序1”。
〔24〕James Peck,“The Roots of Rhetoric: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October,1969,pp.59-69.
〔29〕〔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30〕张小军:《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
〔31〕Laurel Bossen,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Yunnan.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Inc.,2002.p.71.
〔32〕John King 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78-179.
〔33〕Paul K.Feyerabend,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4th ed,London:Verso,2010,pp.223-224.
〔34〕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22064。
〔36〕Edmund Leach,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and New York:Fontana,1982,p.127.
〔37〕《下溪洲的孩子们:儿童人类学的历史足迹》,澎湃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996763988024921
&wfr=spider&for=pc。
〔38〕Kevin J.O’Brien,“Discovery,Research(Re)Design,and Theory Building”,in Maria Heimer and Stig Thgersen(eds.),Doing Fieldwork i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p.27-41.
〔40〕〔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41〕〔日〕佐藤仁史:《日本学者的中国农村调查》,https://kfda.qfnu.edu.cn/info/1160/1817.htm。
〔42〕〔43〕〔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44〕〔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