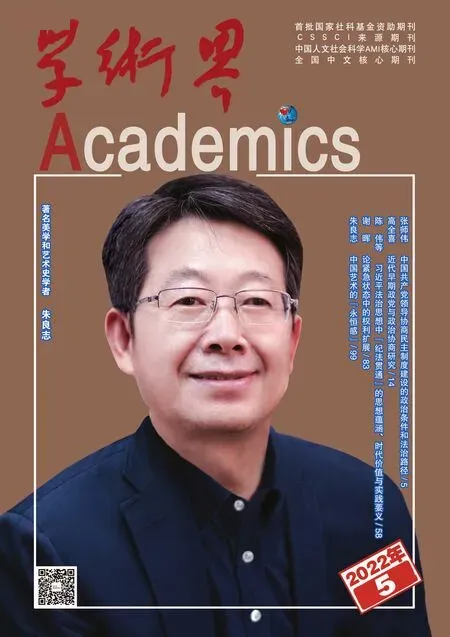审美显道与事理明道的统一〔*〕
——《淮南子》文道关系论
方国武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严格地来说,《淮南子》并没有提供纯粹文学意义上的文道观,但《淮南子》的文化思想延伸开来从而与文论相关,也是不争的事实。《淮南子》中的《原道》篇,是诱发刘勰的《原道》与韩愈的《原道》创作的重要源泉,后两者均是讨论文道关系的经典之作。且《淮南子》文本本身的文学特征已为众多学者所明确,〔1〕当其讨论道的问题时,却意味着也是在讨论文的问题并加以创作实践。《淮南子》中的文道关系论融合了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在道为文之本源的立论基础上,以审美之文形显大道、事理之文践行大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深刻影响文论史上的文道论述。
一、道为文之本源
《淮南子》论述了“道为文之本源”的观点。高诱题解《淮南子》第三篇“天文训”时指出:“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谓以谴告一人,故曰‘天文’”。〔2〕此处的天文是指日月五星等自然文象,即天道所垂之文象。这个文象承载着天道。在《淮南子》看来,天道以自然文象为表征,通过自然文象的变化征兆,警示君王(一人)之政。因此,《淮南子》论“道”,并非以现代自然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理性分析,而是将道的“天”性与现实人世始终关联。天道通过文象与人相通,人借助自然文象了解天道之意。文是道与人世关联的重要中介,是天人感应的发生通道。天文之义虽不是文学意义上的,甚至也并非指向文化作品,但仍可以看出文道一体的传统关联和道为意、文为形的基本格局,这也形成了《淮南子》关于文道关系的基本表达。
《淮南子》认为,一切自然之文的本源都是道。自然万物中一切美的形态都是道的产物,都自然带有道的精神光辉。《淮南子》承继道家的道本原理念,从哲学层面预设了道的先验性,并将其作为宇宙世界的本源。在《天文训》中,《淮南子》从宇宙发生论上将道设为天地万物的本源:
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3〕
这个道生万物可以明确为:道→虚廓→宇宙→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焉”,〔4〕道是万物的终极本源;天地万物都是大道的外在呈现,是道的物质存在和外观形态。大自然因“道”成“文”,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美的形态,《原道训》曰:
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5〕
自然界一切客观物象存在,大到日月星辰,小到鸟兽虫鱼,都因缘于道才能如此丰富多彩、生机勃勃。道不仅决定了万物之美的生发,还规定了万物的秩序,形成秩序之美:
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6〕
大道虽虚无,但无中生有,“至无而供其求”。〔7〕一切感性世界的外在形式、美妙音律、体验味感、色彩形象都由道生发。在道的审美规定下,一切感性世界都形成自己的生命特征和节奏之美,“不失其数”。〔8〕同时,《淮南子》借助于文,将道与自然、人世连接起来,使得道从自然秩序衍化成社会秩序,天文与人文相贯通,从而规范着人文的发展。因此,当文从自然文象延伸到人的文化创造,同样也都彰显出“道”的光辉。而此时之道,也从天性之道落实到现实人世,具体表现为社会中的人文之道。《淮南子》既将道作为先于一切文化作品的绝对存在物,又时时以道为文化作品最高的价值标准。《淮南子》在《要略训》开篇提到为文之目的,第一点就是强调“纪纲道德”。这个“纪纲道德”就是从天性之道中引申出来的人文之道,而其表现在社会治理上就是王道,且与文学创作相关联。《汜论训》指出: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9〕
《淮南子》认为,因为道在历史进程中的逐步缺失,《诗》《春秋》等文化作品得以出现,用来补救道的缺失。因此,《诗》《春秋》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明道扬道。对于文化作品的后世接受者来说,诵读《诗》《书》之文,其目的也在于透过“言者”领悟背后的“所以言者”即“弗能言”之道。至于文本表面的文辞,只要无益于道的领悟,都不必在意,“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10〕《泰族训》在对《诗》《书》等“六艺”文本功能界定的基础上,主张“六艺异科而皆同道”,〔11〕表明古代不同类型文化作品皆本—道。这一命题成为古代文道关系的直接表达,明确了道为文之本源的根本文学观念。进而,《淮南子》以道为文的最高价值标准,批判了各类文本出现的偏误,并指出其问题根源。《泰族训》中指出,在文本语言叙事等表达上,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影响道的精神体现,容易产生诸如鬼、淫、愚、拘、忮、訾、僻等偏误。《诠言训》又云:“《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12〕这些表达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说的理论滥觞,影响着后人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深度与广度。
二、道以审美之文而显
以《原道训》为代表,《淮南子》中大多所言之“道”是如老子那样的“太上之道”,是宇宙世界最高境界的本然状态。“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13〕道充盈在整个世界之中,包裹宇宙,超越天地,为无形状态。但《淮南子》对道的文本呈现带有明显的审美意想色彩。以丰富的想象性,依托审美形象方式,配以瑰丽精致的辞赋语言,神游于广袤无限的自由空间,这是《淮南子》以文显道的文本特性。陈静指出:“以想象的丰富性,取代老庄玄思的深刻性,这是《淮南子》道论的特点。”〔14〕这种特点开启了从哲学文本的“论道”向审美文本的“喻道”的转变。
在论道上,《淮南子》呈现出与老庄不同的特色。老子论道,强调思维的纵深度,将道引向人的深邃思考中,摆脱了外在感性世界对道的纠缠。老子之道是无法承载的,不可名,不可言,不可感觉把握。道只是思的对象,只能在玄思中澄明。因此,在老子这里,玄思冥想是体道最好的方式。庄子虽对道有更为形而下的叙述,但依然强调道的不可感知。在《知北游》那段著名的与东郭子的对话中,庄子虽描述道在“蝼蚁”,在“稊稗”,甚至在“屎溺”,但其实恰恰是在批评东郭子把道看成可以直接把握的物,希望人们摆脱这些具体的物象,去领悟物象背后的真正的道。老庄之道都强调道的不可承载性,道与外在世界相分割。这样,道就变成了孤悬在思维空间之上的精神本源。与老庄体道摒弃感性形式不同,《淮南子》将道放置在一个五彩缤纷、无限广阔的自然世界中,去呈现多样丰富的美的具体形态。《淮南子》有意识地以想象性思维去喻道,以自身审美性的文本表达呈现出道的精义,代抽象玄思为文辞想象。
首先,《淮南子》脱离了老子言道的纯粹抽象,以丰富多彩的自然形象展示道。在《淮南子》中,道更加形象,更加生动鲜活,《俶真训》曰:
至道无为,一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内守其性;耳目不耀,思虑不营;其所居神者,台简以游太清,引楯万物,群美萌生。〔15〕
道化生天地自然之美,“引楯万物,群美萌生”。道从一味的抽象哲理转化为鲜活生动的美感形象,“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16〕道能春风化雨,包含着丰富的感性形象;道蕴蓄生命之美,包含广阔宇宙事象,是一种具有浓厚审美意味的“大宇宙之总”。〔17〕这里的道不仅仅是一个玄虚世界中形而上的抽象实体,它与天地物象、四时图景浑然不分,是气象万千、生趣盎然的感性世界的依托,是真正可以感觉、可以触动、可以观照的形象之道。
《淮南子·要略训》在评述各篇写作方式时,就道如何表达,直接提出了“象”的概念:“《原道》者,卢牟(明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18〕用“象”来呈现道(“太一”)的真正面容,用来感悟大道至深、至虚的精神内涵,这是《淮南子》言道的特色。《老子》中也有“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说法,但其意旨并不在于这种现实物象,更未引向审美描述,而在于那个不可名不可形的本源之“道”。《易传》中也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的象更具有抽象性和虚幻性,是天道的精神呈现。到了《淮南子》这里,“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近者,往而复反。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物穆无穷,变无形像。优游委纵,如响之与景”。〔19〕象(像)与形组合成一个概念。形像相合,象不但保留了道的自由性等基本品格,而且与人的感觉发生关系;同时,形作为可以为人所感觉的经验具象,冲淡了抽象之象的玄思性。这样,形象从作为道的言说方式,到成为艺术创造的核心命题,《淮南子》以文—象—道的言说实践走出了第一步。
其次,为了强调道的宏大,《淮南子》在无限空间中铺陈道之形象。《原道训》:“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20〕这里呈现出道具有空间的延展性和时间的无限性。通过无穷想像,文为道创造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道的广大超越了天地四海、六合四维。可以发现,《淮南子》以文言道,不对道作深层次的追问,而是极力展现其广度的无限性;描述道时,不一味走向理性玄思,而尽显感性夸饰。借助于文本的审美言说,《淮南子》充分调动人的想象性意识去感觉、体验道。在这里,道是可以把握、可以表达、可以感觉、可以体验的。于是,《淮南子》将道化为自然界美的形态加以呈现,美无比丰富,无处不在,无奇不有。道化生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天地之文、大美之图景:
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萑扈炫煌,蠉飞蠕动。……浩浩瀚瀚。〔21〕
道在这里是一个个美丽和谐的生命,自由生长而又自然纯粹。为展现道之美在无限空间中的存在,《地形训》中历数五方,铺陈其间自然产物之美:
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闾之珣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王谷桑麻,鱼盐出焉。〔22〕
这既有自然物产之美,也有人的本质力量呈现之美。自然之美与人的创造之美无限丰富而不可穷尽。《淮南子》将道从老庄一味玄思之中释放出来,使其映照于整个中华大地,美不胜收。
在《淮南子》看来,人们对道的体认需要来自于对自然之文的审美观照。天地自然、宇宙万物纷繁复杂、形态多样,既承载道之天性,也成为人的审美观照对象。人们以审美主体的姿态来观照万物自然之美,并依据自然之美的丰富形态,以文来显现大美之道,从而走向艺术化的审美创造。这样,文以显道就成为一种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化创造。在《要略训》“书论”中,《淮南子》以文本创作为分析对象,表现出明确的审美自觉意识:
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捲握而不散也。〔23〕
这里包含了两个命题:一是文为何审美言道。《淮南子》认为,道虽为文之本源,即如音之根本为宫、商、角、徵、羽,但只有多根琴弦才能发出美妙的乐声;只有“龙首”不够,必须“具其形”,才能得见真容。文传达大道也是如此,必须从抽象、根本之物推演到具体形象之物,才能不会产生表达上的各种弊病。道是精深的,其意义在于感性世界的背后,一般人是无法深刻领悟的。如仅仅抽象玄思,不注重语言表达的鲜明和丰富,就会让人索然无味,无法感受大道之精华。《淮南子》从文本语言形式的层面触及到了为文传道的审美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文何以审美言道。道若想为人所感悟和体验,必须要用丰富话语和情感想象去表达。那就是“多为之辞以抒其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充满想象力的描述,铺陈夸诞的辞赋语言也就必不可少了。同时,看似繁缛曲折的语言,其目的仍然在于澄明道的意蕴,使其便于传达。
《淮南子》审美化的言道方式表现为语言的对偶化、文本的辞赋形式特征。将文赋的华丽辞风运用到道的言说上,形成了《淮南子》审美言道的特色。徐复观在评述《淮南子》的文字形式时,认为是受了当时辞赋盛行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把辞赋的手法运用到文章创作上,“在《淮南子》中,也有许多圆浑深厚的散文”。〔24〕屈赋传统为淮南王刘安注入了先天的文化基因;刘安对于屈原在心灵深处有着伤时感事的情感共鸣。因此,运用辞赋文体去表达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的本质思考,是《淮南子》最为自然的美学表达。夸诞华丽的文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文传道的思想深刻性,但却带来了思想表达的可接受性。对文本语言形式的突出和作者情感的抒发更为后世的文道关系开启了哲理与审美相统一的可能路径。《淮南子》将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从一味的内在思辨或社会应用,拓展到一种形式承载,实现了思想的形式化。
从一味地抽象的玄思走向想象,使得道的言说从纯粹的哲学走向审美与文学。想象力的渗入,是思想表达从历史文本、哲学文本、道德文本走向文学艺术最重要的审美因素。从中国文学史来看,先秦《庄子》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和汪洋恣肆的审美情感使其道的阐发极富有文学意义。但庄子并非是有意识地突出文本形式之美,而是更突出对外在形式的摆脱,如“解衣磅礴”般的效果;一切文本形式只是伟大思想表达的客观效果。《淮南子》虽也明确道以无为本,但却有意识地将道展示在一种形象化的想象世界中,并以一种审美化的文本形式加以呈现。这对于后世的审美文学从文史哲的混同局面中逐渐独立,具有标识性的意义。在对道的文本言说上,《淮南子》有意识地从哲学文本逐渐向文学文本过渡。正如学者指出,“文字写作的对偶化与思想的对称结构,很可能借助于书写与思考的共同材料即语言文字而产生交集。……哲学文本引导我们关注文字的思想内涵,……文学文本则强调文字本身的独立意义与视觉特征,从而将其从日常语言的链条中解脱出来,凭借自身而获得某种圆满性,这也正是审美化的语言”。〔25〕至少可以说明,在《淮南子》看来,大道本源是可以用想象的、美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三、道以事理之文而明
《淮南子》言道有两个层面,一如老子那样的“太上之道”,是哲学意义上的宇宙世界本然状态;一为落实到社会人世的“事”,是世俗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在“太上之道”层面,《淮南子》主张以文言道,即以充满想象力的文辞和审美形象呈现大道的无限之美,实现人的“与化游息”的审美自由追求。在社会文化规制之道层面,《淮南子》主张文以事明道,即以人文规制的事理表达道的世俗化价值,实现人在现实社会秩序中“与世浮沉”的价值。
首先,《淮南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视域出发,论证了道以事理之文而明的必然性。《淮南子》认为,道从本然性来说,是绝对性存在和意义根本。但事实上,道随着社会进程的演化在不断地衰减、分散。从道充盈其间的远古时代,到“事”全面呈现的今世,是社会历史必然的发展。《俶真训》曰:
至德之世,……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26〕
《淮南子》将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对应于人类社会的进程。道从原初的和谐统一已经散为万物。道由单纯转为复杂,由整一化为分散,由宁静变为躁动。同样,人类社会进程也从最远的“至德之世”逐渐下滑为衰世。道在现实社会中就无法保全其原初的精神存在,只能以个别的、具象的、差异性的、有局限性的世俗化“事”理形态出现。儒家的仁义礼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27〕
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28〕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29〕
一方面,《淮南子》承认仁义礼乐等人文规制是大道衰散的产物,但同时,在对待它们的态度上,还是依据因时所需的原则给予客观评价。特别在后半部分的篇目中更是如此,如《主术训》认为:“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30〕《说山训》更是将仁义放置在道德范围内加以肯定,“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31〕仁义与“道”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即“一体”的关系了。
与之相对应,作为各类人文规制的文本载体,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书籍,也在大道衰减的社会进程中随之产生。《氾论训》中说:“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32〕这些文化作品虽然是大道不行后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他们虽无法比类大道,但其中人文规制、社会事理的表达也是通向践行大道的现实路径。
正因为现实社会中,道的分散,社会衰落,人们“反(返)性于初”的难度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接近道的最高境界。原初之道不复存在,这就导致人们寻求生活意义的根据发生变化,于是,帮助人们协调、规范现实生活中具体问题的恰恰是事理规制。因此《淮南子》意识到,如果在大道不行的时代,还只是一味沉浸在对道的玄思幻想中,文化作品不仅不能为人接受,而且也失去了它践行社会之道的机会。《要略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未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宿乎昭明之术矣。”〔33〕《淮南子》认为,大道之精深哲理人难体悟,可能只有圣人才能明晓大道之意。但现实社会中,普通人没有圣人的智慧,就意味着无法获取体道的现实路径。因此对于文化作品而言,必须详细阐发,将道落实到具体的世间万象万事中呈现,才能为世人解惑明理。文可以通过对具体、现实的社会人伦事理的描述,传达社会性的价值规则,来承载道的精神。概括《淮南子》所言之“事”,有远古传说之事,有古代贤君圣人之事,有近世社会之事,都表现为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事功及其创造的社会文明。从《淮南子》勾勒出来的社会进程历时衰减模式来看,虽然这些“事”理与最初的那个纯粹整一的道越来越远,但也都是特定社会阶段的必然。每一种“事”理呈现,代表的都是符合所处时代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因此,文化作品中表达的事理,也能够让人们获得社会人生的行为智慧和价值规范,使人们能够在现实社会中顺利地生存发展,实现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价值。文以事明道,意味着人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按照既有的价值规范追求一种现实的生活理想。于是,从宇宙生成论的逻辑层面和人类社会进程的客观现实出发,《淮南子》肯定了文以事明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其次,《淮南子》认为,以事明道才能彰显文的价值。在《淮南子》看来,一定程度上文能对道之不行的时代起到补救作用。《泰族训》曰: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寻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34〕
《诗》《书》《礼》《易》《乐》《春秋》虽形态各异,风格不同,但都从各自的事理维度指向社会之“道”。它们各有所用,其共同目的都是建构一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很显然,《淮南子》虽然对大道沦散后的社会表达了失望,对以六艺为代表的言事之文有所批判,但也看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文以事明道的必然性及合理性,甚至在特定语境下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人间训》中描述孔子读《易》的损卦和益卦,能够觉察其中之理,并用来解读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就表明文能传达事物发展的规律特征。
而且,文能以事明道,因此文就往往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状态的表达。《本经训》曰:
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35〕
与“盛德之世”相比,“末世之政”的音乐因为承载了末世无道之政,就丧失了根本的精神价值。这里虽是论乐与社会政治事理的关系,但因乐与文具有文化表达的相通性,仍可以借用来说明文以事明道的命题。很明显,《淮南子》从文与现实社会关系出发,强调文以事明道的价值功能,正是继承了儒家实用主义理论,但其观点又比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儒家过于强调各类文化的伦理功能,甚至将文化置于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从属地位;《淮南子》则进一步发挥了文对于宇宙人生、社会自然的认识作用,它要求文“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36〕实现通晓天、地、人属性规律的目的,如《修务训》所说:“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37〕因此,在《淮南子》看来,只有凭借事的呈现和表达,才能实现文的社会性价值。
再次,文以事明道,才能实现“与世浮沉”与“与化游息”的人生价值统一。
文化作品中的事理之道,已经不再是本然存在的“太上之道”,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如胡适所说“虚位”的意义,具有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皈依的色彩。〔38〕借助于事,文具体展开了历史文化的叙事图景,去落实人文理想。但同时,文以事明道,并不表明文就一直陷于社会事理而沉沦于俗世;其所强调的是以事明道、道事并举这一价值目标。《要略训》:“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39〕这里说,如果只是言道,文就不能应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变化,无法通晓人文规制和时代观念,无法“与世浮沉”;反之,只是言事,文就始终居于俗世,无法实现人生的超越,去获取生命的自由境界,最终无法“与化游息”。“与世浮沉”表明了文关乎人的社会需求,体现社会性价值,是道对现实人生的落实和关怀。“与化游息”描述了文关乎人的自由状态,指向本真性追求,是道对事的超越和除蔽。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文以事明道,如能实现言道和言事的统一,那就像《淮南子》在《要略训》中所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40〕可以通晓天下之道,万事之理,无所不能了。文做到道事并举,就能体现出面向天地之象的视野,通晓古今之理的智慧,辨清万物规律的思维,以及因时而为的变通。在此基础上,《淮南子》规定了文化创造的最高境界,《要略》云: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41〕
这段话完整地论述了以“属书”为代表的一切文化活动的价值规律。首先,文化创造的目的是探究大道,开拓新的生命境界。其次,文化创造是认识价值、社会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统一。“知举错取舍之宜适”是塑造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举止适度得当;“外与物接而不眩”突出提升人在世界对象面前的认知水平;“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则感受天地之道的精华,而将自身本真之天性呈现出来,与道合一。这就是最高境界,实现个体的自由追求和精神超越性。“自乐”可以看作人生命存在的审美境界,意味着获得一种超越性、自由性、诗意化的审美体验。
《淮南子》道事并举,也是刘安生活的汉初时代精神体现。《淮南子》成书当在景帝后期。武帝即位,“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42〕此时段的汉代,历文、景至武帝,其国力达到鼎盛,呈现出恢宏庄重的盛大气派。人们也着力追求事功,但又并未受制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审视自己面对的世界、面对的生活时,才有了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有了一种囊括天下的激情,从极度满足之中产生出一种昂扬奋飞的心态。在日益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武帝时代,这种心态也最终造就了刘安的人生悲剧。汉初时代的道事并举最终在董仲舒的宇宙结构图式中,演变、固化为无所不在的天理秩序。
与先秦道家相比,《淮南子》的道更具有现实性和灵活性,因时而变,因事而为。“道”的层次性内涵也形成了《淮南子》更为丰富的文道关系。不同层面的道在《淮南子》中有不同的文道关系表达,且通向各自的文化发展路向。这充分显示出《淮南子》融汇儒道、追求圆融一致的文化理想追求。《淮南子》以事明道,道事并举的文道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文学中关注现实人生与追求精神超越始终是统一的价值追求。文以事明道,才能走进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展示鲜活的人生画卷,呈现现实图景中的人生万象,表达人在世俗社会中的思想情感,而不至于走向纯粹的虚无之境。更为重要的是,《淮南子》以事明道的观念,暗含一种宏大的文化架构。《淮南子》中“道”,从道家的“自然之道”延伸,以“事”具体形态展开,最终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文规制相融通。经《淮南子》至刘勰,都是以“道”为本体,指向文化创造及至文学本源的理论建构。“道”,不仅作为先验性价值目标具有超越性,而且在文化历史的过程中,早已落实为一种历史现实的存在。与《淮南子》以“事”明道一样,刘勰在《原道》中探究文学的根源,并非一味将其归之于纯粹玄思哲理之“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仰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43〕也是从儒家圣人文化出发,“敷赞圣旨”,在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的融合中去寻找文学的历史本源。
注释:
〔1〕从文学史来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谭巫模的《中国文学史纲》等著作都提到《淮南子》,只是过于简略。相比而言,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使用七百多字、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使用了八百多字来介绍《淮南子》,《先秦两汉散文专题》(韩兆琦主编)使用了2600多字评介《淮南子》,给予其文学史上较高的地位。
〔2〕〔3〕〔4〕〔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1〕〔22〕〔23〕〔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9〕〔40〕〔4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9、79-80、30、2、29、11、11、427、625、674、485、1、54、17、3、700、32、1、44、139、707、64、59、319、343、316、533、427、707、674、266、700、657、700、711、706页。
〔14〕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24〕徐复观:《徐复观全集·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72页。
〔25〕任鹏:《中国美学通史·汉代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8页。
〔38〕胡适:《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第21页。
〔42〕〔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28页。
〔43〕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