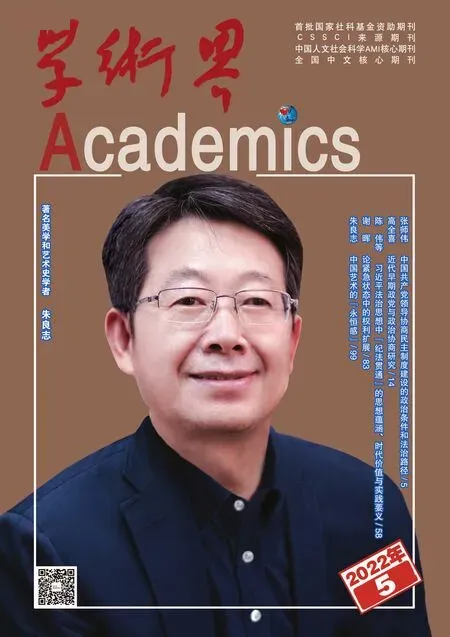从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共识稀缺困境及其出路〔*〕
李晓燕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多边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间交往的历史产物,是主权平等原则充分实现的需要。自19世纪初萌芽以来,多边主义的生成都是在国际关系局部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凝聚共识,然后又将这些共识转化成具体的规范和可执行的规则而渐次推进的。与此同时,多边主义产生作用的方式在其三个主要阶段:凝聚共识、形成规范、执行规则方面的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多边主义合作的常见方式是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定或条约、创建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但是并不能说有这些方式的国际互动都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扩散性互惠——才是辨识纷繁复杂的国际合作是否是多边主义的根本依据。
一、界定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即多数国家参与的国际治理,旨在定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特别是反对歧视性的国际安排。〔1〕针对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大国政治中的歧视性国际安排往往被认为是加剧国际冲突的根源。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被赋予了这样的预期,关于多边主义的具体定义也逐渐表现出分歧,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一种要求很高的制度形式,有学者则认可其为一种生成性原则框架。然而,无论倾向于具体的制度还是抽象的原则,分歧都是发生在概念的外延层面,关于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扩散性互惠——并不存在矛盾。主权平等是形成多边主义合作的前提,多边主义源于对歧视性国际安排的纠正,特别是二战后出现的多边主义国际安排大多数都强调主权平等,在公开的章程中有效规避了参与合作的障碍。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是确保多边主义合作生效的关键,也是将参与者的合作意愿转化成现实的过程。不可分割即指任何一方成员或者少数力量不能改变多边主义中经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换言之,决策会影响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扩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即指一旦达成一致,多边主义框架下没有任何角色可以预期使合作中的特定利益惠及特定成员,更不能对收益过程予以实际控制,只要合作按规则运行,产生的收益就是可持续的,这也是多边主义合作被追求的根本原因。
多边主义既不是一劳永逸的国际制度安排,也不是能够自我约束的机制化系统,它需要有关各方的积极维护,合作可能有先来后到之分,但是不应内外有别。为了实现上述内涵,多边主义合作从形成共识到生成合作的过程离不开成员方、合作目标、持续的行为及恰当的形式设计四方面外延。将外延等同于多边主义本身也是妨碍理解多边主义的常见偏差,是需要作出的概念辨析,比如多边主义不等于多边外交,多边主义也不等于任何具体的多边制度。
(一)多边主义、多边制度、多边外交
多边主义不等于多边制度/机制,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全部形式,二者存在的一个根本差别是多边制度可能具有排他性,而多边主义的首要内涵就是主权平等与开放性。比如,欧洲一体化合作进程从起步到统一大市场形成阶段都体现了明确的多边主义开放性,但是宣布成立欧盟和建立欧元区后则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多边制度。因此对欧盟的研究应该适用于多重多元的理论工具,有学者就将欧盟视为双边主义、多边主义、复合主义(polylateralism)的系统化运行产物。〔2〕
多边主义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政治过程,〔3〕将多边主义等同于多边制度事实上就把多边主义视为了一劳永逸的结果,特别是认为有了多边制度的多边主义合作就能彻底解决成本—收益的核算,加入和遵守多边制度是唯一选择。事实上,多边主义在凝聚共识、形成规范、执行规则三个不同阶段能够产生作用的方式并不相同,维护多边主义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而非最终结果。〔4〕并非所有的多边主义合作都可能经历完整的三个发展阶段,有些问题领域不可能也不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多边制度的出现是第三阶段“执行规则”的产物,而且制度的有效性离不开资金和资源的供应,一旦供应机制失灵就会引发制度失灵,进而损害甚至中止多边主义合作。再比如,即使有了多边制度,制度能否实现参与方的诉求?关于制度中的遵约行为产生的意义也有很多争议,并非一味遵约就能使制度奏效,遵约也不等同于维护多边主义。〔5〕更何况新千年以后的国际制度体系明显已经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需要,由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组合而成的新型全球治理复合行为体也在重新定义着多边主义,有学者将其称为“复杂多边主义”(complex multilateralism)。〔6〕
多边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多边外交,前者是抽象的外交形式,后者是具体的外交行为。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二者的不同。比如,1945年旧金山会议引入“工作语言”和“官方语言”的建设性概念,赋予了英语、俄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官方语言”的地位,被认为是秉持“多边主义”精神结束18世纪以来现代外交史上的语言之争的重要创新实践,与此同时,旧金山会议对英语和法语是“工作语言”的规定又是确保外交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平衡,是一种能够实现妥协和尽快达成一致的“多边外交”行为。〔7〕简言之,多边主义需要兼顾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扩散性互惠三原则,而多边外交不必兼顾,多边外交更多要以持续性推动交往和产生结果为目标,往往是在三原则之间权衡和妥协后偏向某些方面的优先性而取得成果。
将多边主义等同于多边外交是常见的误区之一,比如,19世纪初多边主义萌芽时期,频次很低的大国会议是很受欢迎和重视的多边外交形式,往往能凝聚共识、形成规范,甚至制定出具体规则,有效推动多边主义的进展。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国会议频繁且备受指责,矛盾重重也很难通过任何一次峰会得到解决,于是会议外交的挫折和低效往往被舆论过度解读为多边主义的前景渺茫和不容乐观。可以说,新千年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挫折一直也没有让多边主义摆脱这种责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被不恰当地划上了等号。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世界政治经济分裂危机大大降低了首脑峰会的频次,在转为线上的视频峰会中,国家元首们的发言和表态以更加清晰、直观、即时的方式呈现给舆论界,从中更容易分辨各方的立场分歧与可能形成的共识,对重启多边主义合作进程是有一定积极价值的。与此同时,来自社交媒体的独立声音也受到更多关注,关于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各国举措是否积极有效更容易形成真实的评判,因此重启多边主义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更多体现出来自民众的意愿和共识,这也是对传统多边外交方式的挑战与稀释,需要以创新的理念和实践方式来凝聚有效共识和形成相应的规范、规则。换言之,多边主义的本质是不变的,多边外交的形式却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时空与议题。
(二)多边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效用评估
多边主义生成有效的国际合作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凝聚共识、形成规范、执行规则。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多边主义合作都要经历完整的三个阶段,具体在哪个阶段产生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合作领域的信息透明度,二是该领域是否存在主导国。因此,并不能依据其发展阶段评判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和国际关系意义。特别是就问题领域的限制条件而言,在事关人类发展进步的问题领域,比如消除贫困、基本人权问题上,多边主义无论在哪个阶段生成有效的合作,都是有历史价值的。这就是多边主义符合国际关系的原生本质的根本体现,因为多边主义是纠正歧视性国际安排的基本形式。
第一,凝聚共识是多边主义的起步阶段,通过广泛接触与对话寻找到各方关心和关注的议题点,并将拟实现的目标阐明,这就是多边主义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共识(consensus),也是最困难和可贵的阶段。一旦找到共识,其他观望的和疑虑的潜在参与方就可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入共识,即使分歧和矛盾仍然无法克服,但是有了共识,多边主义才有生效的前提。凝聚共识阶段大体由四个步骤组成:(1)来自倡议方经验的细致论证;(2)提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立场主张;(3)阐明该主张的广泛适用性;(4)其他方同意该主张,使其成为共识。不难看出,在凝聚共识阶段,多边主义非常依赖于倡议方的知识供应,这种知识和经验的供应很可能还与其资源和力量密不可分,但是没有一般性和适用性主张是无法形成共识的,因此,主权平等原则在凝聚共识阶段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如果说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具有一定的重合度,多边外交容易被误解为多边主义本身,那也主要是发生在凝聚共识阶段,倡议方需要通过充分的细致沟通与相关方取得共识,多边外交官和多边外交平台是这个阶段不可或缺的活跃行为体。
第二,形成规范是指将参与方达成的共识转化成可行路线图的过程,旨在明确多边主义合作中主权平等和政治权责不可分割原则的具体实现方式,规定可实现的范围和轻重缓急之处。不同的问题领域和不同的参与方对同一多边主义共识给出的再定义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形成适合本国和本地区经验和条件的具体规范是多边主义合作生效的关键阶段。比如,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共识,1981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形成的规范就将“民族平等是人的平等”的前提这项属于非洲发展特有的地区经验纳入进来,是多边主义合作生效的必要保障。
第三,执行规则是通过系统性规定指导和约束参与方行为的过程,需要在已有规范的基础上形成落实规范的细则,并对其有阶段性补充和修订,还可能为指导和监督规范的落实而成立相应的职能部门。比如,旨在制止破坏臭氧层的气体排放行为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诸多议题中成效最为突出的,与其得以明确奖惩措施的细则规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再比如,《欧洲人权公约》是《世界人权宣言》之后第一个达成的区域性人权条约,而且自1950年签署以来就设立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并陆续补充了十余项议定书。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多边主义合作都要完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更不是一定要演进到执行规则阶段。事实上真正能将共识转化成规范和规则的多边主义合作毕竟是少数,但是,多边主义仍是符合国际关系本质的基本国际交往形式,即努力从差异和矛盾中寻求协商一致与合作的可能,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和分歧。就已经生效的多边主义而言,成效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扩散性互惠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使多边主义成为某些参与方实现诉求的工具和手段;二是不同参与方可以通过多边主义平台表达意愿、诉求和不满;三是多边主义在具体规范和规则的运行中事实上不断追求着自主性,由此可能衍生出对基础性共识的发展、突破甚至背离。
一方面,多边主义生效后实际是扮演工具、论坛,抑或是自主行为体的角色,其实是参与方和设计者不能预先设定的,多边主义具体发挥的作用和表现出的形式取决于议题领域和参与方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参与者的确是通过设计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式来实现共同目标和诉求的,这种设计要围绕参与各方的意愿凝聚共识和制定恰当的规范与规则并确保其顺利实施两个层面展开。换言之,多边主义在输入和输出功能两个方面都产生作用,但是输入功能是将参与各方的差异性汇聚起来,输出功能是将协商一致后达成的共识转化成能够影响参与方实际行为的结果。前者是从差异性中寻找一致性,主要遵循的是主权平等原则,因此容易得到参与方的支持。后者是用一致性去干预差异性,主要遵循的是政治权责不可分割与扩散性互惠原则,各参与方的矛盾就会突出表现出来。不同功能产生于多边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并非任何多边主义合作都需要完整实现全部功能,通过汇聚各方的差异性输入多边主义框架,与由多边主义框架输出具体规范和可执行的规则这两大类功能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明确这一差别对于我们理解和评判多边主义的实际效用,认识多边主义与参与各方的国际关系行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现实是有帮助的。
二、旧多边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局限性
多边主义自生成以来就是以局部地区的国际经验追求全球性国际体系目标的产物,无论19世纪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欧洲大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实践,还是二战结束后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多边主义理论研究和制度成果都概莫能外。多边主义在其产生的时代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业已得到肯定的价值确保其延续至今,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多边主义是一种不断演进的政治过程,并非一劳永逸的结果或者某种固定不变的互动模式。所以,每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多边主义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有在恰当的修正和更新后才能适应新的时代主题与国际环境。
欧洲主导和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经验对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贡献都在于它们探索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共识奠定了使世界市场连为一体的坚实基础,肯定了主权平等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都不能将联合国框架下的和平与发展宗旨有效转化成多边主义共识,仍在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和南北分裂说明了旧有的多边主义经验要作出恰当的修正,任何排斥特定参与方的倡议都是违背多边主义本质内涵的“伪多边主义”。坚持主权平等和开放性原则的真正多边主义才能带来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和突破。
(一)欧洲多边主义经验的身份同质性
所谓身份同质性是指参与多边主义的各方对“自我—他者”的认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欧洲国家在宗教信仰、历史互动的经验积累、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政党政治等方面的地区内趋同性是当今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效仿的,因此欧洲发展的历史上也形成了长期的欧洲与欧洲以外的“自我—他者”边界观念。这种观念早在重商主义驱动欧洲大陆发现新大陆的对外行为时期就有明确的体现,此后虽然经历世界政治经济的变迁,但是欧洲以外世界的变化要远远超过欧洲内部的变化,而且欧洲以外的世界变化日益强化了欧洲身份的自我认知,进一步塑造了欧洲地区特殊的身份同质性。
多边主义实践最早在欧洲萌芽与欧洲地区由来已久的“国家间联合”思想有关,18世纪早期圣-皮埃尔(Abbe de Saint-Pierre)在《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和《在基督教国家君主间建立永恒和平的方案》中完整表达了欧洲国家实现永久和平的可行路径,即“建立一个由欧洲各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拥有由各国全权代表组成的常设组织机构,各国保持其主权相对完整,但又必须部分地让渡主权的超国家联盟”,〔8〕并且认为国家间联合的可能性是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产生的,因此明确强调了主权平等与国家间交往的内在联系,说明欧洲国际关系中孕育出多边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多边主义经验往往产生于地区的积极价值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二战即将结束时,欧洲一体化的共识开始从倡议转为具体的合作规范,因为合作的前提是修补自凡尔赛体系以来造成的欧洲分裂,身份同质性的基础共识也成为欧洲重启多边主义合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德合作并共同发挥带头作用则是将欧洲共识转化成可操作规范的固有内容。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选择多边主义路径是内外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主要是受美国提供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影响,美国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增强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从而有效遏制苏联。欧洲内部为了消除两次大战造成的分裂,就必须确保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同时有效让渡主权和开展对话,多边主义显然是比大国均势或者其他路径都恰当的选择。
自从1952年正式开启一体化进程以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经历了70年的变迁,一体化进程无论取得进展还是遭遇挫折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焦点问题与典型案例,尽管(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理论也不断演绎出各种逻辑对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予以解释,但是这些理论还是以认可欧洲经验的针对性和局限性为前提的,并没有像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那样一直试图解释普遍性和全球性规律。欧洲之所以能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空前分裂的国家间关系中建立起超国家的治理模式,身份同质性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也是研究欧洲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始终无法解释欧洲以外的一体化尝试与探索的原因。仅就这一点而言,阿米塔·阿查亚将东盟地区经验定义为规范习得结果的“安全共同体”,〔9〕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对参与多边主义合作各方的身份同质性的准确把握,都符合多边主义的解释框架。
当然,一体化进程的成果并不能掩饰始终伴随的差异化和分歧,从1950年代新功能主义对一体化自我持续性的合作“外溢”(spillover)解释,〔10〕到1960年代开始政府间主义强调成员国的自主性起决定性作用,〔11〕再到1990年代经过重构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明确将多边方式视为欧洲的必然出路,〔12〕应该说欧洲一体化始终是在“克服危机—重建共识”的反复中前行的,这恰恰说明多边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演进的政治过程。特别是2008年以来接连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实际反映出的也是:一体化经验虽然给欧洲多边主义在战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提供了有效方案,但是不能调和的区域内发展差距(比如西欧与东欧)和价值观裂痕(比如南欧与北欧)反复挑战维护一体化必不可少的身份同质性,一旦失去这一共识基础,欧洲的多边主义经验也会陷入失灵的境地。身份同质性是欧洲多边主义的催化剂,同时也是助燃剂,脱离身份同质性的欧洲不仅在一体化合作方面要停滞和倒退,甚至可能出现极右倾向的政治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遇到的问题与欧洲国家遇到的问题不能简单划等号,〔13〕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展就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演进变得密不可分,制度主义理论对欧洲一体化和多边主义进程的解释与影响成为无法回避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就是集中体现为高度制度化的,甚至在新千年后表现为欧盟制度的社会化过程,制度主义的繁荣无可厚非,但是由此取代和稀释了多边主义的消极结果也清晰可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参与方与欧盟制度之间的所有互动解释为降低成本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抛弃了多边主义的任何进展都离不开协商一致的本质,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也就变成了静态的决策博弈。历史制度主义看重欧洲一体化的历时性政治过程,准确解释了不同的欧盟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与造成的路径依赖和政策锁定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如果制度的惯性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发生合作的断裂,哪些路径和选择能重建共识和重启多边主义并不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重点。社会制度主义将欧盟制度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解释为制度对成员身份和行为的塑造与重构,与欧洲一体化的身份同质性基础有高度的契合,却由于漠视从未消失的差异性而始终备受批评,特别是在多边主义处于凝聚共识发展阶段的情况下,社会制度主义反而可能刺激政治极化的声音。
无论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还是各种制度主义,他们都试图解释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也就是一体化的最根本动力。他们并不把欧洲一体化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也不认为研究欧洲一体化需要专属的方法。〔14〕欧洲一体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持续热度事实上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多边主义作为基本国际交往形式的重要价值,欧洲多边主义的经验具有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从这些理论解释力的变化中也得到了证明。
(二)美国多边主义经验的排他性
如果说欧洲多边主义的经验还在坚持将实现欧洲成员间的平等作为共识与目标的话,美国的多边主义经验则是通过创造象征性平等的国际制度,以代表权的象征性关系模糊了实际运行中的等级制。换句话说,欧洲多边主义因为始终发生在欧洲地区内,所以在多边主义的三个阶段都遵循主权平等原则。而美国推行的多边主义是发生在地区差异极大的全球体系,因此通过具体的国际制度取代全面的多边主义过程是美国经验的关键成分,由此产生了多边主义框架下的等级制。〔15〕
美国多边主义为实现其单向最大化利益的流入而处处根据排他性原则转化基础性共识,实则是公开或者隐蔽地破坏主权平等原则,要么会被其他参与方抵制和反对,要么就是用局部方案加以替代,这也是美国主导多边主义合作中长期存在“搭便车”(free ride)现象的根本原因。2014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蒙古国时发表演讲,明确表示了“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16〕既明确了中国多边主义主张的开放性,强调其与美国旧多边主义的根本差别,也切中要害地指出了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才是多边主义成为国际交往基本形式的源动力,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寻找基于主权平等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发展方式是任何阶段能够生成有效多边主义的共识基础,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更谈不上繁荣,旧多边主义不能消除的地区差距和南北分裂已经成为不得不克服的弊病。
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和美国利益优先原则决定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其认为涉及美国根本利益时,联合国框架下的协商一致就变成了毫无用处的无休止争论,绕开联合国甚至公然违背联合国决议而悍然行动才是美国的行为规律。比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导致美国操控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国内反对承担25%的联合国会费的人士就持续抛出所谓改革方案。1975年11月美国国会众议员马休·里兰多提出议案,建议美国对联合国的预算只负担5.6%,依据是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率。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凯撒巴姆修正案》规定美国支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会费不得超过其总额的20%,同时又要求在讨论重要问题时拥有25%的投票权,公然否定联合国大会的一国一票原则。以财政施压来达到操控联合国的目的反映了美国多边主义主张的排他性,主权平等和政治权责不可分割原则在美国的利益优先性目标面前都变得可有可无。
再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借用联合国“预防外交”的理念提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的口号,主张凡是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都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要彻底实现这些国家的无侵略性就必须对其进行民主改造。“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认定“失败国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可以对其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甚至在2003年绕过联合国授权通过战争方式摧毁和重建伊拉克国家。这也是冷战结束后依仗权力结构失衡的特殊国际环境,美国假借联合国多边主义框架实现单极霸权目标的最极端表现。美国把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事业中形成的基础性共识转化成仅仅符合美国意愿的排他性规范,以美国的民主标准制定规则,企图肆意侵犯别国主权。然而,这种排他性“伪多边主义”终究还是被联合国框架识破和否决了。同样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对外战争,同样是借联合国的多边主义框架提出规范和规则,老布什政府的海湾战争与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在争取联合国授权面前得到的不同结果,事实上也说明了排他性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美国可以借助霸权实施侵犯他国主权的行动,但是不能用排他性绑架多边主义。
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希望消除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国际威望的损害,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经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强调美国必须摒弃将联合国视为“过时的工具”的观念,建立新多边主义,与联合国合作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人道主义危机等在内的全球性问题。〔17〕与联合国合作就需要与多极力量的大国协商一致,这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方案中突出的排他性原则却是难以相容的,因此也始终无法成为美国政府的现实选择。仅以美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互动为例,自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美国经历了三年抵制(2006—2009年)、一次退出(2018年)、两次重返(2009、2022年)的反复无常外交,足以说明“与联合国合作的新多边主义”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霸权国推卸责任”实则是导致多边主义制度失灵的关键原因。
美国多边主义主张的排他性具有明确的议题指向和参与方指向。议题方面,以美国自1970年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以来的50年(1970—2020年)行使否决权记录来看,〔18〕美国全部81次否决权行使要么是美国单独进行(57次),要么就是与英国、法国两国共同行使(24次)。美国单独行使否决权的议题中有41次是关于中东局势或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问题的,充分说明了美国在这两个议题上始终明确的立场是为实现本国诉求,不惜排斥任何不同参与方的主张而破坏联合国框架下的协商一致。然而在多边贸易安排议题上,无论是关贸总协定的时代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时期,美国不仅遇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声音,而且与同为工业化国家的西方经济伙伴也有诸多摩擦,但美国却从二战后至今都没有放弃对相关谈判进程的主导权,并且不断设计排他性规则,旨在维护利益单向最大化流动的多边制度。
参与方层面,美国也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之内或者之外都坚持排斥不同意见的其他方,比如联合国早期运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只能以频繁动用否决权抵制美国,1973年以前在联合国的128次否决权投票中,美国与苏联的投票比例是4∶109。但是此后,美国为应对多极化格局的新形势,反而成了联合国安理会里否决权使用最多的大国,1973—1986年间美国与苏联的动用否决权比例变为54∶8,〔19〕意识形态左右美国投票行为的意图清楚可见。再比如,1983年以后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向国会呈交年度联合国投票行为报告,联合国内美国获得的投票一致率成为影响美国与相关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其2020年报告中统计的2019年联合国大会31项“重要议题”(important final plenary votes)全年投票行为中,与美国保持60%以上高一致率的国家有50个,与美国投票一致率低于30%的国家有15个,其余国家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都在30%~60%之间。〔20〕美国对投票一致率的分析与其外交行为有明确的联系,也是美国在联合国系统中动辄以排他性取代开放性原则的重要原因。2017年1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就公开表示,“我们在联合国的目标是展示美国的价值观,展示美国价值观的方式是展示我们的力量”,“对于那些不支持我们的人,我们将记下他的名字,并作出相应的反应”。〔21〕
通过排他性规则实现美国收益的最大化是美国多边主义的不变规律,因此美国并不排斥多边主义本身,无论是二战后塑造自由国际秩序,还是冷战后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在每个阶段都借助了多边主义安排,从成立联合国到亚太经合组织,再到成立二十国集团,包括拜登政府试图组建的扩展版民主俱乐部。这些多边主义安排的参与方不同、议题领域不同,具体规范和规则也不同,但是能够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是相同的,即美国要有绝对的主导权,不利于美国保持优势的议题和参与方则会成为美国排他性规范和规则针对的目标。以多边之名搞小集团政治则是美国多边主义经验自二战以来就无法摆脱的排他性本质,排他性多边主义(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终究会加剧世界的分裂与对抗,〔22〕即使在冷战时期也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更不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重启多边主义合作和支撑美国复兴霸权目标的有效途径。
与欧洲多边主义的身份同质性局限和美国多边主义动辄诉诸的排他性规则不同,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了适应自身发展条件与现实发展需求的多边主义共识与有效的合作生成方式。这些多边主义共识与合作始终强调参与方的主权平等地位,包容不同参与方的差异性与多元诉求,坚持协商一致的基本途径,是符合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和扩散性互惠原则的新多边主义,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
三、坚持主权平等与充分发展的新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的出现是民族国家互动交往中确保主权平等原则实现的自然产物,新多边主义则是适应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为有效多边主义合作的生成注入新内涵的结果。为确保主权平等的真正实现,新多边主义旨在兼顾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条件与诉求,而不是片面输出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新多边主义正视世界的差异性,强调参与各方的多元共生,而不是压制和模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个性与差距。新多边主义强调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合作共识,能够有效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活力。
(一)主权平等的充分实现需要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发展条件
发展是主权平等的固有内涵,也是民族国家捍卫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式。17世纪中期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标志就是以英法为先导的欧洲各国开启寻找适合各自条件的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道路,摆脱土地生产方式和王权利益至上原则束缚的国家内外变革的过程。作为岛国的英格兰与位于欧洲大陆边缘的法兰西,选择了海外扩张和连通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同时借鉴了重商主义时代欧洲的扩张方式,完全漠视了亚非拉民族国家应有的主权权利。19世纪世界市场雏形初现的时候,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禁止黑人奴隶贸易”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大国开始在铁板一块的国际体系中,预留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主权权利实现的合法性空间,以适应欧洲大国继续主导工业化加速发展的世界市场的需要。20世纪初为扭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集团的劣势,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才从少数欧洲大国掌握的权力资源慢慢转化成为全球性国际体系规范,广大亚非拉国家也是从这个历史起点上开始争取民族国家主权权利实现和独立发展机会的道路的。然而,探索的道路相较17世纪的欧洲要曲折和艰难得多,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工业化发展已经将世界市场分裂为“中心—边缘”的对立面,因此二战结束后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才会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同等重要和彼此关联的多边主义共识和目标。
联合国也是迄今最为有效的实现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地位的多边主义框架,回顾联合国的成就可知,之所以能维持人类历史上最长时段的体系和平,也是因为联合国在不断探索有助于成员国实现充分发展的有效方式。从1960年以来联合国先后提出的“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难看出,只有切实有效解决发展难题的共识才能成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共识,发展的模式也不是任何国家和国际制度可以单向供应的,无视他国发展诉求的模式和经验必然被拒绝和抛弃,充分尊重主权平等原则和经过协商一致产生的合作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符合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
发展是确保民族国家充分实现主权平等的根本保障,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不是既定不变的,要在尝试、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和确定合适的发展模式。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表明,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于国家层面的“增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都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清楚暴露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弊端。另一方面,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更侧重个体层面的减贫,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等议程,也不能从根本上给有关国家和地区带来持续的发展和根本的改变。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由此总结经验凝练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由最初被西方强国诋毁到联合国2016年11月将其写入大会决议,充分说明了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是新多边主义的重要标志。
(二)矛盾与冲突的各方可以是多元共生的行为体
新多边主义源于不同于西方工业化世界的认识论基础,并不回避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矛盾对立方的存在,但是能从矛盾中更多看到合作的可能性而不是认为差异和矛盾必然导致冲突。这也是后发现代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好适应17世纪中期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是局限于发展鸿沟带来的矛盾,反而能从对立面中寻找机遇,通过学习和融入旧国际体系,进而改革和完善旧制度与旧规则,最终实现真正的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的中庸辩证法就是一种将矛盾辩证看待的认知论,虽然中庸辩证法也认为事物皆有两极,两极各有差异,但中庸思想中的两极不是对立对抗,而是互存互容,互为生命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据此而言,全球化发展形成的“地球村”就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共同体,尽管多种成员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而是可以构成和而不同、互鉴互补的关系。中庸辩证法既界定了事物共同生存的依据和共同进化的条件,也解释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适切关系。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冲突、相向而行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依据。〔23〕
西方学界持文化多元主义观点的研究者也认为未来将出现一个明显深刻的、嵌入式的、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建立在共同首要制度的强大基础之上,并受到一系列共同命运问题的威胁。于是,如何平衡新兴的深度多元主义国际社会的发展,使其既能在全球层面应对共同命运问题,又能满足国际社会对文化多元化的需求,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关键问题。任何大国,无论新旧,都需要在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方面追求容忍和共存,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应对共同命运问题所必需的全球层面的具体功能领域的合作上来。〔24〕这也就揭示了新多边主义及其生成的有效合作是矛盾对立、但又需要多元共生的各种国际行为体应对共同命运问题的正确选择。
四、共识稀缺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
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联系,与任何形式的霸权结构秩序则是背道而驰的。一旦多边主义成为普遍有效的国家间交往形式,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作为管控国家间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形式也就大大削弱,转而成为了一种全球治理的工具。〔25〕然而,21世纪前二十年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清楚表明全球化的进路充满坎坷,全球治理时代的国家间互动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少矛盾和更易合作。相反,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世界更深入地交织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都比以往更复杂,民族国家的内外决策能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同时进入了需要更新观念和方式的历史阶段,多边主义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是空前复杂的。
(一)主观意愿与客观成效双低导致的共识稀缺
多边主义作为二战后国际交往的基本形式始终是与双边主义并行发展的,是在民族国家为实现主权利益而权衡多元路径选择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哪种共同利益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哪种价值目标与本国的价值观体系能够契合,都是在反复的交流沟通和充分的协商一致基础上才能成为多边主义共识,进而生成多边主义合作的。因此,多边主义的实现过程从来都比其他国际交往方式面临更多的挑战。当前阶段的最突出障碍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共识稀缺困境:一方面是出现民族国家多边主义合作意愿的最低点,凝聚共识成为最大难题,难度超过了此前长期存在的转化规范和执行规则分歧。另一方面是现有多边主义合作的成效产出进入周期性发展最低点,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合作方式革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族国家的主观意愿低,多边主义的客观成效差,进退两难的多边主义陷入了发展历史上罕见的谷底期。
当前多边主义合作面临的共识稀缺困境源于二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的“霸权国推卸责任”安全阀被执政四年的特朗普政府触动,此后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合作的悲观判断情绪持续蔓延,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扩散进一步使得民族国家行为体对利益目标和价值目标的估算呈现出加剧的高度内聚状态,多边合作的外溢性则呈现最低点,多边主义合作的意愿池几近枯竭,出现了“大河无水小河干”的窘境。尤其是2016年以来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回归欧美政治,西方工业世界的高失业率、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三重挫折统统被归咎于多边主义。〔26〕多边主义为维护劳动者权利和基本人权而生成的绝大多数国际规范和规则都被质疑和否定,“我们—他者”的边界被前所未有地划分为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的鸿沟,二战结束以来最活跃的多边主义推助力量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几乎彻底隐匿甚至成为最激烈的反对声音。G7集团代表的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冷战后一度被认为是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最佳模式,却在遭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急转直下地迅速失去吸引力,原本被认为理应最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精英阶层在反全球化的政治决策中竟然毫无违和感,舆论的转向造成的观念困惑和主张分裂成为多边主义发展史上最糟糕的环境条件。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史无前例地激发了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人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事务的多元感知和观点表达,以至于任何一国政府在内外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都相对减弱了权限,都需要争取更多的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和认可才能制定和执行决策,这也是当前多边主义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以美国为例,2021年10月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服务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的讲话中作了所谓“美国外交政策现代化”的发言。〔27〕明确阐释了“美国外交政策现代化”的五大支柱分别是:第一,在对未来几年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重塑实力和优势,特别是气候、全球卫生、网络安全、新兴技术、经济、多边外交。第二,宣扬新声音,鼓励更多创新和创造,设立新的政策思想渠道,让世界各地的职员能够与政府部门领导人直接沟通他们的政策观点。第三,建设和培养一支多元化、有活力、富有创业精神的工作队伍,充分发挥美国在种族、宗教、民族和国家来源方面的多元化优势。第四,实现技术、通讯、分析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最强国优势。第五,重振对提升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现场外交(in-person diplomacy)和公众参与(public engagement)。可以说,目前拜登政府对美国外交的改革创新几乎全都建立在适应多边主义发展的新方向之上,是适应新变化而试图重塑其多边主义领导力的应时之举。
当前多边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的另一方面原因是20世纪以来与多边主义进展相伴相生的工业化繁荣周期进入边际收益最低点,迫切需要根本性变革和转型。西方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繁荣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周期后,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生产增长和经济繁荣的边际收益显著低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南北差距等负面效应的谷底期。西方工业强国供应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不仅不能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而且恰恰相反会加剧相关问题造成的困境和恶劣影响。各国对自身安全与发展道路的探索都需要找到更适配自身地理、历史、文化条件的途径,〔28〕因此多边主义也进入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艰难时期,业已走过了仅靠少数西方强国供应的模式就能奏效的发展阶段。二战结束以来逐步建立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相继暴露出无法调和的矛盾,西方工业强国的经验从经济贸易领域的布雷顿森林制度设计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联合国体系,从气候变化领域的减排方案到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响应机制,在倍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几乎全面失灵的僵局。
此次工业化繁荣的周期持续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接近70年的超长时段,基本涵盖了当今国际社会的认知形成过程,出现了现有的国际关系知识精英和相关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的现象。然而,再长的周期也只能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2020年美国大选暴露的两党政治“古稀两难”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全面唱衰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终结。美国的经验仅仅是多边主义发展史中一个时期的经验,既不具有普世性也不是永恒真理。多边主义本身才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产物,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方式,旨在实现充分的主权平等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真正可持续发展。多边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中需要不同的实现方式,也是国际社会克服危机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必由之路。
(二)克服共识稀缺困境的可能出路
针对上述两方面困境,生成新共识就成为当前推进多边主义合作的首要难题,结合历史经验和发展现状可以预期几个可行的突破方向:一是另辟蹊径,积极开发民族国家以外的多边主义共识供应者。长期以来,多边主义共识的来源主要是民族国家,经民族国家充分协商后达成一致,凝聚共识,转化成规范和规则。如果该议题领域的多边主义合作长期化和常设化,则会建立相应的多边制度或国际组织,但常设化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和向好的,二战后大量多边制度和国际组织虽然提高了多边主义合作的效率,但其深受少数西方大国影响的弊端也饱受批评。有学者就提出,反全球化其实是反美主义的一种表达。〔29〕1999年西雅图抗议者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激烈批判就是针对其偏狭地将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的共识替代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共识,严重地损害了劳动者的权利,以贸易自由之名塑造的世界经济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破坏了人类共有的环境。2018年特朗普政府大搞贸易战和公然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更是用霸权国的意志直接扼杀了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共识。在经历了漫长的世界政治经济分裂危机后,国际社会的合作诉求逐渐回温,与全球治理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已经表现出从多边主义共识的需求方向供给方转化的明确动向。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在组织目标的实现方式中持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30〕有望规避大国战略竞争对多边主义合作的阻滞作用,尽快生成有效的新多边主义共识,将现有的资金资源投入到实际的国际合作中去。这种新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在民族主义高筑围墙之外积极生长的新多边主义共识也是多边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和新方向。
二是求同存异,重申民族国家的旧共识,避免共识稀缺的议题领域出现失控的风险。比如在2022年初大国战略竞争形势明显超过合作诉求的情况下,五个核大国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认为,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坚定表达了避免大国战争,维护战后世界和平是当前国际关系的共识基础,无论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多么不同的变化,决不能让历史倒退的基本共识不会变。同时,和平的保障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努力,深化合作仍然是坚定的方向和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任何合作都应建立在此共识基础上,因此《联合声明》指出五大国“强调愿与各国一道努力,创造更有利于促进裁军的安全环境,最终目标是以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我们将继续寻找双、多边外交方式,避免军事对抗,增强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并防止一场毫无裨益且危及各方的军备竞赛。我们决心在相互尊重和承认彼此安全利益与关切的基础上开展建设性对话”。〔31〕
三是多重叠加,在不同的多边制度之间互相激发可能的共识,寻找与国际合作的历时性外溢并行不悖的共时性黏连。针对当前多边主义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有学者提出了通过多边制度间合作的方式重启新多边主义的方案,认为合作不仅是为了战胜疫情,也是确保世界和平稳定、国际社会有序进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重启多边主义合作离不开对多边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国际条件看,“G20+1”的模式就是可行路径之一,亦即G20承担政治领导责任,联合国专门机构发挥咨询实施作用。比如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G20的政治领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咨询实施就可能形成一种比较有效的全球行动模式。G20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和欧盟等重要国际行为体,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比较充分的代表性,并且因为成员较少,更容易达成危机决策。一旦出现全球性公共安全威胁,G20可以宣示合作意愿,提出指导原则,协调各国政策,承担全面推进国际合作的领导责任,是霸权合作的时代终结后最为有效的多边集体领导的国际制度框架。联合国专门机构可以在全球合作框架中发挥政策咨询和任务实施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权威和权力资源,要求联合国专门机构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是不现实的。〔32〕但是,作为某一专门领域凝聚共识后形成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知识和技术权威性不容颠覆,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最合理途径,多边合作是应对全球性威胁的最有效方式。
四是包容创新,鼓励源自发展中国家的新多边主义合作方式。比如,在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金砖国家是一支建设性力量。金砖成员国都是地区或全球性大国,虽然各国实力和发展水平有所不同,但是在多边制度和全球治理中,金砖国家基于主权平等和协商一致原则加强协调和沟通,摒弃实力原则,也没有采取多数决策原则,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有效创新实践。〔33〕不同于传统南南合作主要集中于经贸领域,金砖合作致力于发展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新兴的数字经济发展,等等。传统南南合作主要“以说为主”,强调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金砖合作增加了“以做为主”的务实合作新内涵,创建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开发银行,在平权治理结构、与借款国关系、本币投融资与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等方面实现了制度创新,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理念和实践,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全球发展融资体系的制度变革。〔34〕2022年适逢中国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也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重要历史时刻,可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有效的新多边主义合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了新共识和新规范,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经验和创新观念。
五、结 论
作为国际交往基本形式的多边主义与国际社会寻求工业化发展和世界市场连为一体的进程是相伴相生的,是确保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充分落实的重要保障。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是在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扩散性互惠三原则的基础上经过参与各方的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共识,进而将共识转化成具体规范和可执行的规则。因此,多边主义不同的议题领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实现方式,在凝聚共识、形成规范和执行规则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多边主义的实践经验虽然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但是多边主义的实现方式并不局限于某些经验和模式。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共识基础上,欧洲和美国的多边主义实践经验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表现出的局限性又越来越无法适应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深化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特别是21世纪前两个十年里接连出现的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国竞争等世纪难题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旧有的多边主义经验的信心。多边主义的发展进入两次大战结束以来罕见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成效双低叠加的谷底期。
针对前所未有的共识稀缺困境,2021年国际社会在对抗新冠疫情的艰难磨合中渡过了多边主义的新元年,重启多边主义合作的努力已经在关键国际组织之间有效推进,核心大国也在尽其所能地“共同发声”强调国际交往的原则和边界。在经历了民粹现实主义的破坏和疫情全球传播的灾难性挫折后,国际社会逐渐认可了多边主义仍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的基本途径,但是新形势和新挑战又清楚地表明重走老路的选择是行不通的,旨在以充分协商一致为基础,确保实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与充分主权平等的新多边主义才符合时代之需。
注释:
〔1〕李晓燕:《多边主义再思考与世界秩序重构》,《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
〔2〕G.Wiseman,“‘Polylateralism’and New Models of Global Dialogue”,Discussion Paper,Leicester 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me,1999:59,pp.10-11.
〔3〕Vincent Pouliot,“The Practic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 Ole Jacob Sending, Vincent Pouliot, Iver B.Neumann,Diplomac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81.
〔4〕Robert Kissack,Pursuing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Decision Making,Palgrave Macmillan,2010.
〔5〕〔美〕乔治·W.唐斯、戴维·M.罗克、彼得·N.巴苏姆:《遵约的福音是合作的福音吗?》,〔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国际组织指南》,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0-352页。
〔6〕Robert O’Brien et al.,eds.,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7〕A.Ostrower,Language,Law,and Diplomacy,2 volumes,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5,p.408.
〔8〕宋新宁:《探寻和平之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渊源》,《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
〔9〕〔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Ernst B.Has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1950-1957,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11〕Stanley Hoffmann,“Obstinate or Obsolete?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Daedalus,1966,95(3),pp.862-915.
〔12〕Andrew 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sstrich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13〕宋新宁:《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
〔14〕〔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主编:《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译者前言”,第11页。
〔15〕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ecking Orders: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Multilateral Diplom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47.
〔16〕《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重要演讲 强调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共促亚洲稳定和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xjpzxdmgg_675167/zxxx_675169/201408/t20140822_7954338.shtml.
〔17〕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Investing in a New Multilateralism:A Smart Power Approach to the United Nations,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90128_mendelson-forman_un_smartpower_web.pdf.
〔18〕笔者根据联合国官网统计数据作出的分析,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veto-usa。
〔19〕刘金质:《美国与联合国》,《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3期。
〔20〕Report to Congress on 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for 2020,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1/Report-Voting-Practices-in-the-United-Nations-2020.pdf.
〔21〕Somini Sengupta,“Nikki Haley Puts U.N.on Notice:U.S.Is ‘Taking Names’”,The New York Times,Jan.27,2017.
〔22〕Yan XueTong, “Becoming Strong: The New Chinese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2021,100(4), pp.40-47.
〔23〕秦亚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价值与实践意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9期。
〔24〕〔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88页。
〔25〕Ole Jacob Sending,Vincent Pouliot, Iver B.Neumann,Diplomac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300-301.
〔26〕Kathryn C.Lavelle,The Challenge of Multilater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p.234.
〔27〕Secretary Antony J.Blinken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merican Diplomacy,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on-the-modernization-of-american-diplomacy/.
〔28〕Ian Bremmer, Nouriel Roubini, “A G-Zero World:The New Economic Club Will Produce Conflict, Not Cooperation”,Foreign Affairs 90, 2011.
〔29〕Jagdish Bhagwati,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7.
〔30〕周逸江:《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卫生与气候治理协同中的角色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国际观察》2022年第1期。
〔31〕《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01/t20220103_10478507.shtml。
〔32〕秦亚青:《合作: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铁律》,《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33〕王磊:《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路径及其实践》,《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34〕朱杰进:《金砖合作引领国际发展治理体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