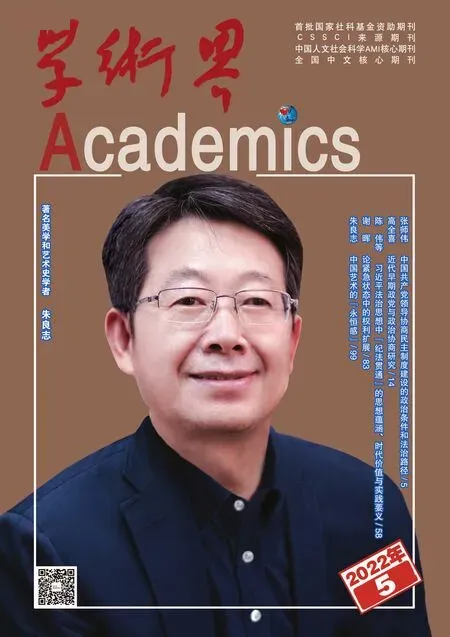转型与重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逻辑悖论及超越〔*〕
赵银亮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价值
世纪之交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随着大国权力的深度调整和全球局势的剧烈演进,关于大国关系的研究,作为对不同文明世界发展的总体研究,以及对文明与地缘、权力与话语叙事相关关系领域的探讨,指出文明与帝国现象交织、大国权力与世界格局重塑等内在关联,是全球话语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以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圭臬,忽视乃至抵制非西方世界发展模式及道路创新的动力,是催生传统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体系重塑的经典式要素。〔1〕至于把随着新兴国家崛起而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的变革作为又一新的切入点,观察国家权力、文明样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及讨论如何处理外部关系,成为国际关系叙事学研究的关键问题。〔2〕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围绕中东变局、金融危机和俄乌战争所带来的欧亚大陆格局的剧烈波动,全球性权力的演进过程始终难以离开各大力量、各大文明间的相互审视和相互激荡。如果说,金融危机、伊核危机和俄乌战争等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反映着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单位以及大国权力的此消彼长、内在冲突,那么中美之间围绕意识形态、贸易和安全等方面的摩擦与冲突,围绕全球秩序和地区安排所呈现的大国深度博弈,则表明长期以来维系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内在逻辑正在经历演变。
文明与权力演进中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变化,不同文明间尤其是东西方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思想史的传递、演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围绕某些重要的关键事件、议题和理念所呈现的分歧与斗争,对于当前国际关系话语叙事走向有何意义?在西方国家围绕大国的“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等宏大命题存在认知分歧的情况下,关于“崛起大国”的学术争论,以及对国际体系可能带来的深度调整等议题的讨论不断聚焦和深入,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国际关系话语叙事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思考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全球权力变革与国际关系新秩序重构十分重要,尤其是对“话语叙事”中相关理念范畴的研讨,有利于我们把握全球国际关系变动的深层原因。
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崛起”必将深度调整国际关系格局,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霸权国的话语叙事。当前,围绕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学术讨论甚嚣尘上,从西方学者近年的研究成果看,类似的学术争论通常赋予国际行为体“修正主义(revisionism)”或“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标签,针对“崛起(rising)”国家的对外实践和外交理念,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习惯于进行简单的二分法归类。依据他们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思路,不同历史阶段“崛起”的新兴行为体大致可分为不同类型的“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和“维持现状者(status quo actor)”;而对于不同类型的“修正主义行为体”,他们又依据不同的标准规范,将其分为“积极”或“消极”的修正主义者。〔3〕在他们看来,修正主义者试图寻求“改变全球商品分配”,这些国家拥有“领土、地位、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对国际制度进行改革”的野心和抱负,而“维持现状者”则不寻求分配结构的改变。〔4〕
令观察者们感到困惑的是,通过对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全球力量进行实证比较研究,无论从本体论还是方法论角度,关涉“修正主义者”和“维持现状者”的争论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晚近四十余年,中国“崛起”为国际关系格局调整注入了新的元素,关于中国崛起的学术讨论和政策实践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西方主流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是国际关系格局调整中的“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世纪之交国际体系变革的“建设性”力量,〔5〕而不是一个“对现有秩序不满足并准备取代这一秩序的革命性力量”。部分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僵化思想和认知,他们客观看待新兴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和影响,强调国家间力量的变动是自然的、无法改变的时代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不同的国家行为体必将在国际社会中经历“社会化”过程,其国家地位和行为体认知也将随之变化。〔6〕
对于欧盟这样一个超大体量与内涵极其丰富的超国家行为体而言,其兴衰起落的过程极为复杂,学界主要关注欧盟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全球体系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对欧共体(欧盟)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该联盟通过不断扩展进而“努力重塑和设计国际体系的轮廓”。〔7〕在政策实施层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欧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承诺。〔8〕如果按照西方对于“修正主义者”的假设来判断,显然,欧盟正在从“地区性力量”逐渐转向“全球的市场力量”,〔9〕并通过“对民主、人权和发展”等相关议题的话语叙事和意识形态革新,“积极地影响并推动了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10〕另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欧盟是国际体系变革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和“规则的维护者(norm entrepreneur)”。〔11〕随着欧盟力量的不断增强,其在全球权力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新兴的全球行为体”演变为“超级集团”,但依照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欧盟并未被贴上“修正主义者”的标签。〔12〕
在传统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体系中,对于美国力量成长的认知同样是复杂而微妙的。从21世纪初的小布什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一系列外交政策实践,暴露出其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侵犯,体现出其对于传统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体系的破坏,显然带有强烈的修正主义色彩。〔13〕
需要追问的是,通过对上述包括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在内的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比较研究,学界是否就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修正主义者”和“维持现状者”有了清晰完善的理论界定,是否意识到其中关于话语叙事逻辑的内在悖论;对于国际权力的兴衰起落这一复杂过程的研究,是否可以有更多超越西方单一的线性思维、超越单一维度和学科的知识性解释;是否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单一的话语叙事逻辑,而是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地缘等各领域之间的复杂互动来进行系统考察,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于国际权力格局和话语叙事演进这一宏大过程的深层结构,对尚有争议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内涵作出更富开拓性、也更加符合国际力量发展趋势的深层次探究。在这样的拷问之下,我们需要不断超越传统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窠臼与陷阱,重新厘定国际权力轮替所需要的观念,并对思想层面的话语叙事逻辑进行更新及构建。
对于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研究,尚需从迄今为止未被重视的长时段视角入手进行思考,需要与时俱进地探寻对于这一事关当下国际权力变化的认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认为,从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相互结合的视角展开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十分必要。就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和国际权力轮替这一议题而言,对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体系的演进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于分析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等表现,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当然囿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样的探索性研究也必将充满挑战。
如果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推向大航海时代和西欧工业革命时期,就会发现当前围绕国际关系行为体“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学术争论,主要聚焦于西方设定的所谓“道德与进步”的“指令性叙事(ordering narrative)”逻辑。这一话语叙事逻辑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于世界事务和国际秩序的选择性叙事话语演进,通过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和对外扩张,渐趋形成了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国际秩序和体系规范,其中最为关键的即是作为西方制度基础的“道德与进步”叙事,任何对于西方所主导的制度和规则的破坏或颠覆都被视为对“道德与进步”的抵制。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帝国主义侵略史作长时段的考察,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话语叙事逻辑背后道德规范的制约。〔14〕数百年来,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强化对这一国际体系和话语叙事逻辑的承诺与捍卫,对于任何挑战这一国际体系和话语叙事逻辑的新兴力量始终抱有仇视甚至对抗的态度。与其说,西方国家对于当前国际关系行为体中“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话语叙事表现出浓厚的自我叙事的色彩,倒不如说这一话语叙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兴行为体挑战时无奈和保守的一面。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抽取西方国家对于“道德与进步”的顽固守护,并从更广泛的维度揭示国际体系变化和国际关系行为体演进是一个自然的、绝非按照西方意志设计的过程,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西方对于国际关系行为体中“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单方面定义,才能够推动当代国际关系朝着平等、民主的方向迈进。〔15〕
从国际力量比较的角度看,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快速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一系列地区乃至全球公共产品,按照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发展对于全球和地区秩序而言属于需要加以防范的“修正主义”;欧美等西方世界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是否可以不断调整对修正主义内涵和外延的定义,进而肆无忌惮地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行抑制和打击。显然,很大程度上,关于“修正主义”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国家对于新兴力量发展的双重标准和刻意仇视的矛盾心态。〔16〕
二、国际关系中的西方话语叙事及逻辑冲突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话语叙事的研究有着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和丰富的学术成果。虽然对于“叙事”这一概念本身的定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见解,但从目前研究来看,各学科依然有着类似的界定。从文学、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作为话语工具的“叙事”,成为一段时期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通过强调或忽略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不同行为体以不同的角色和身份选择性地进行“叙事”呈现。〔17〕话语叙事需要一定的场景和行为体,不同行为体呈现不同的角色特征,借助不同的场景和目标,行为体可以进行自传式(autobiographical)叙事,通过对行为体身份、目标和场景的重构,“叙事”主体能够描绘基于不同目标的叙事框架,突出主体间的合作与共赢,进而推进共同认知和共有知识的生成。〔18〕
由此可见,叙事本身包含着主体的自我认知,叙事主体对于国际“规范”或“制度”的理解通过一系列事件得以体现,这些事件要么是现实的真实呈现,要么是虚构的“现实”。通过赋予“现实”以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叙事主体便能够以“过去的自我认知”来“解释和指向当下与未来”。〔19〕国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体有着不同的话语叙事逻辑,因此,只要能建构起符合自身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叙事框架,便能够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系网络”中获取有利地位和话语优势。
(一)话语叙事的维度及内在逻辑
美国学者玛格丽特·萨摩斯(Margaret Somers)和格罗利亚·吉布森(Gloria Gibson)描述了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叙事维度:〔20〕
一是概念性叙事(conceptual narratives)或学术性叙事,这一叙事方式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借助“社会”“行为体”“文化”等概念性术语,从其历史性和关联性中凝练话语意涵。萨摩斯和吉布森认为概念性叙事包含以下要素:剧本(drama)、情节(plot)、解释和选择性适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等。
二是本体论叙事(ontological narratives),这一叙事方式突出个体行为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通过话语叙事来表明他们的存在,体现其身份特征及行动模式。按照萨摩斯和吉布森的解释,国家行为体或代理人(agents)通过对叙事环节和内容的设定,使其适应自己的身份特征。当然,国家或个体行为体也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灵活性叙事,实现国家目标或个体性目标。根据这一话语叙事逻辑,不同的国家或个体行为体出于某种共同的目标或利益,通过对文明因素——包含以宗教和哲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心理与行为习俗及其表征体系等——的共有知识认同形成更为广泛的集体规范网络(webs of normativity)。从而,本体论叙事进一步演化为与共有文明因素、文化和制度结构相关的公共叙事,叙事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和政府,也包括家庭和教会等行为体。由此,由本体论叙事演进而来的公共叙事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形成集体共识和公共政策。〔21〕
三是元叙事(metanarratives),这是一种相对宏大或普遍的叙事方式,尤其包含颇具时代意义的宏大历史叙事。无论是对落后野蛮的中世纪的描述,还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文明与发展的伸张,抑或是对自由进步的国际道义的支持,都能够通过元叙事的形式得以呈现。从历史上看,包括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在数千年来前赴后继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随的是它们之间不断的交往和抗争。但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勃兴,西方文明通过元叙事将其内在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深深植根于时代的时空之中,自近代以来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中不同行为体的思想建构和制度设计。〔22〕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谈到的文明单位间的“挑战—应战”模式那样,人类不同文明创造的成果可以通过元叙事得以巩固或轮替,这种“挑战—应战”在共鸣和博弈中兴衰起落,某一历史时期的主流元叙事也在这样的兴衰起落中缓慢演进,并被新兴行为体的选择性叙事(alternative stories)所取代。〔23〕在此轮替过程中,主流叙事和反主流叙事(counter-narrative)交相辉映,在新老国际主体间纵横博弈,作为国际体系或秩序的潜在修正主义者(potentially revisionist),新兴国家不断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及其话语叙事的规范和钳制。
从文明史演进和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角度切入,观察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演变及权力结构的更新,不能只关注国家间权力的较量和博弈,还需要从各种文明、不同国家话语叙事的互动、合作中揭示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当然,围绕着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主体和逻辑,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争议,这些争议不仅伴随着几十年来整个世界的转型进程,而且,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以来有着鲜明文明兴衰背景的国际主体间的博弈,甚至关系到国际秩序的重塑与建构。尽管,亨廷顿和福山关于文明冲突的论调并非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本质,但显然围绕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讨论,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场域中已经无处不在。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已深深地嵌入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西方所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理念正在形塑着绵延几十年乃至更久的世界秩序,而这一制度和理念的核心就是标榜西方所谓的“道德与进步”。在西方看来,二战以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无疑加速了其所建构的国际秩序和话语叙事逻辑的崩解。西方秩序赖以维持的“道德与进步”的思想制高点,构成了西方话语体系元叙事的核心,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合力巩固这一思想制高点,并将其奉为“整体社会治理的理论核心”。〔24〕通过这一元叙事的形式和理论核心,西方国家以双重逻辑来谱写对于自身及“他者”的元叙事,进而以西方制度和规范为载体维系既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引领一轮又一轮的关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宏大叙事。在这样的宏大元叙事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确立了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基本规则、制度规范和演进逻辑,并对有可能挑战这一秩序和话语叙事逻辑的行为主体实施遏制与制裁。〔25〕
回到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分析视角。西方国家通过既有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将新兴的、潜在的国际社会中的“修正主义者”描述为国际体系和秩序的“破坏性或革命性力量”,继而通过强大的叙事能力建构,迫使这些新兴行为体经由体系改造、自主学习和社会化等一系列主动或被动的进程,“建设性地”参与或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之中。总之,西方国家通过强大的概念性叙事、本体论叙事和元叙事等多种方式,不断塑造新兴行为体自觉学习和社会化的动机和能力,进而不断培育其关于国际体系的共有知识和身份认同,并将这种知识和认同深刻融入新兴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决策和政治实践之中。〔26〕
东西方文明所处地域空间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缓慢而又深刻地演进,伴随着的是西方文明在晚近五个世纪通过概念性叙事,对于西方秩序和体系中“道德与进步”等话语叙事的凝练与弘扬,刻意营造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对于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西方秩序的修正和抗争,刻意忽略不同文明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发展的贡献。
(二)西方关于“道德与进步”话语叙事的逻辑悖论
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和话语叙事,二战后至今的学术发展有着一条清晰的逻辑理路并渐次展开,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沿循着相近的话语叙事逻辑和重要命题,呈现出基于西方“道德与进步”理念核心的话语叙事脉络和知识谱系。总体来看,随着这些相互独立但又彼此关联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演变,以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演进,不同理论范式在交往中逐渐凝练出西方话语叙事框架的关键特征。
二战后的70多年间,从学术史角度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问题的探讨,有若干方面的进展值得关注。尤其是按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进行谱系阐发,能够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西方世界的话语构成及运行逻辑,虽然当前研究还只是初成格局,很多问题尚有争议,但相关命题、视角和方法值得参考。
首先是传统现实主义者的知识谱系。20世纪中期,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世界即将面临的巨大变化,也在不断思考帝国主义列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情势下将会有着怎样的命运,且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现状又将带来怎样的深刻影响。〔27〕在他看来,二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推动西方国家对战后形势进行谋划和重构,部分国家将倾向于加强自身权力,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另有部分国家也将为获得更多的权力,寻求有利于自身地位的变化,进而奉行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帝国主义政策。虽然,当时的学界从摩根索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研究中难以判断,其论断是否隐含着世界局势包括权力格局行将大变,或者依旧仅仅是书生之见,于是将“修正主义国家”或“维持现状国家”的论断推到西方学术界知识生产的前台,但是,同时期其他学者也在追寻摩根索研究的视角,关注战后国际权力的分配问题,无论是地区大国围绕“满足现状”“革命的修正主义”等展开的热议,〔28〕还是新兴国家聚焦世界秩序重构和针对威尔逊主义展开的学术及政策争论,都推动着学界和政治精英围绕西方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话语叙事进行前沿性探索。从传统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谱系来看,尽管是通过多重道德棱镜观察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观察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发展和民主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但从中不难看出传统现实主义者对于当时大国力量变动和国际体系变革有着深深的忧虑,他们清晰地感知世界将面临“对国际秩序满意的大国与新兴的崛起国之间围绕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在其话语谱系中充斥着“强权政治下的权力和利益的纷争”。〔29〕传统现实主义者对于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诠释,未能超脱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僵化思维,隐隐体现出约翰·霍布森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制度主义”思想,以及其背后基于西方所谓“道德与进步”的理论假设。〔30〕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的视域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源自奉行“扩张主义”、对国际关系“现状”不满的德国与西欧大国之间的冲突,“修正主义”的德国对于西欧大国及当时的国际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在摩根索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缔结同盟条约旨在维持国际关系和地区格局的现状,而德国等“修正主义”国家试图破坏这一现状及现状背后的秩序体系。〔31〕
把国际关系话语叙事演进的逻辑置于19世纪中期的历史时空中观察,就能发现重大历史事件中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涉及“道德与进步”等理念时,西方学者和政治精英对于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有着复杂矛盾的心态。比如,有学者认为英国是一个“和平的、满足现状”的大国,通过维持国际关系现状和保护殖民地权益免受某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侵犯和扩张,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32〕而在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看来,共有身份的建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如何处理世界事务,以及与外部行为体的关系,是关涉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问题,而运用国际道义的力量对“修正主义力量”进行围剿和打击,是西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所需要的。〔33〕
其次是结构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谱系。随着1970年代全球局势的转变,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蓬勃发展,世界权力格局被重塑,围绕“修正主义者”的学术辩论进入新的论战场域。尽管与20世纪中期相比,国际环境和总体形势有了深远变化,围绕帝国纷争、国际力量重组等方面的议题存在不同的学术面向和政策走向,但总体来看,霍布森所提及的“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叙事逻辑依然得以延续和传承。这一时期,随着新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权力的调整,尤其是伴随着西欧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东亚、拉美等地的现代化发展,新兴的国际力量在欧亚美等地崛起,既有的国际秩序和话语叙事亟待重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看来,日益“开放和自由”的经济秩序容易催生新的权力,进而造成“既有权力秩序”的崩解,因此,只有维持既有霸权才能推动新形势下全球秩序的稳定发展。〔34〕吉尔平及其他新现实主义学者以历史的眼光比较了18—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时期、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的国际秩序,进而提出权力转移理论(PTT)。无论是霸权稳定论还是权力转移论,其核心思想都认为“崛起的新兴力量”有足够的实力接近甚至超越昔日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大国,并进一步“修正”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从而引发国家间的冲突。〔35〕在他们看来,战争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中成员国权力的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主导国所维系的国际秩序、规则和规范”的不满或挑战。“新兴国家不满于当前的国际现状,需要通过修正主义方式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这将引发主导国家的抵制和对抗,由此,国家间脆弱的权力均势和新兴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不满”相结合,为战争提供了必要条件。〔36〕
尽管,在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论者看来,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变动源自国家间力量的失衡,他们也尝试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但显然,这两种思维范式和学术路径依然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理论,难以超脱传统现实主义者所勾勒的知识谱系。正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强调的,当前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能够从西方文明发展中找到渊源,都是围绕西方话语叙事逻辑而打造,其理论假设和政策实践也是建立在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错误认知基础之上。〔37〕某种程度上,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均是为了“维持既有大国的现状”,巩固西方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而演变和深化。正如阿查亚所指出的,尽管西方世界的话语叙事从理论谱系到政策实践,正在被西方国家打造成普适性的理论,但依然难掩其内在的为西方国家权力体系伸张的本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新兴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等方面的诠释,本质上体现的是西方国家选择性地开展“指令性叙事”的事实——欧美等国故意掩盖其在亚非拉等地进行殖民扩张的恶劣行径,而这恰恰是西方所谓“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在西方国家选择性地进行本体论叙事和元叙事的过程中,刻意忽略了欧美等国对地区秩序破坏性治理中的“修正主义”元素。西方学者和政治精英坚持认为,欧美等国在亚非拉殖民地的扩张行为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重组和完善,是对“道德与进步”之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坚守与弘扬,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修正主义”。
三、西方“修正主义”的概念性叙事及时代局限
对于国际关系“现状”概念的描述,涉及一个较为具体,但却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两次历史浪潮中去揭示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演变。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后期国际关系所经历的两次重大调整来看,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视野中的“现状”并非一直处于静止或相对静止的状态,相反,在西方的国际关系或政治发展的话语叙事中,对于“现状”的概念性或学术性叙事通常围绕“以西方为中心”的逻辑展开,且以西方所谓的“进步性”作为衡量标准。
(一)西方主流思想中“进步与文明”的内在悖论
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论著中所指出的,如果全球没有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霸权国家存在,“国际经济秩序就无法实现蓬勃发展”,在他看来,类似于苏联这样的“潜在霸权国”或“修正主义国家”会破坏这一带有明显“进步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而通过对世界施加政治和经济限制以实现其“修正主义企图”。〔38〕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也认为,英美等“维持现状”国家通过对全球货币体系、自由贸易体系和决策共识的制度性构建,加强对“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培育,推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进步”,但这些努力却不断遭受来自于新兴崛起国的挑战和威胁。〔39〕
在西方主流思想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认知视域中,“进步”被看作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这一“进步”理念和范畴的价值,充分体现在西方科技和物质文明的提升与改进上,“进步”主要体现的是西方意义上的“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沿循此逻辑,世界日益凸显“进步与文明”的西方与“落后与野蛮”的非西方的分野。〔40〕再加上西方历史学家从长时段和中时段的视角对所谓的“进步与文明”进行演绎和诠释,在国际学界和政治精英的认识过程中,渐趋形成了西方进步与文明的线性发展轨迹(linear trajectory),这一轨迹沿循从古希腊到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逻辑展开,由此,“进步”逐渐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内在产生的概念性叙事范畴,并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得以强化和巩固,而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则是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41〕
通过对“进步”与“文明”进行概念性叙事,这两个丰富且多元的概念范畴就进一步被简化为西方“独特的政治秩序和哲学概念”,从而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逻辑”。〔42〕在许多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著中,美英等西方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自然就是这一“独特的政治逻辑”作用下“进步与文明”的最好的实践和体现。虽然对于西方世界的发展和所谓“独特的政治逻辑”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尚未有足够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检验,但西方通过“进步与文明”的概念性叙事和“独特的政治逻辑”,进一步将“现代化”和“发展”等范畴纳入西方话语叙事体系。〔43〕经由西方学界大肆渲染和选择性叙事,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进步”思想和全球实践,被认为是帮助诸多发展中国家迈入“现代化和进步的新时期”的必然选择。〔44〕
通过对相关范畴的概念性叙事和选择性叙事,西方将国际关系中对“现状”的定义和描述纳入了西方中心主义设定的“进步与文明”话语叙事体系中。按照这一话语叙事逻辑,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围绕民主建设、人权发展和制度改革等开展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活动,都是旨在推进国际关系“现状”的改善和提升,而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也被赋予了推进全球“文明”进程的宏大历史意义,这些改革与发展不仅重塑了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在不断推动着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化”进程和文明发展进程,同时还在不断加强着世界体系内部的关系发展。正是借助从自由秩序到“社会化”的概念性叙事,西方经济体系对于新兴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由此,新兴经济体通过政策和理念的“趋同效应”,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二)西方“修正主义”概念性叙事的二元论思维
在欧美学界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对于后冷战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实践和全球愿景的表述充斥着西方中心论视域下的西方霸权论调,〔45〕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历史观、全球政治发展的现代性和政治趋同等角度进行剖析,〔46〕经由西方媒体大肆渲染,西方世界的精英和大众普遍认为新兴行为体应“追寻西方崛起的脚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所谓的“进步与文明”,否则将会被描述成秉持“修正主义”道路的“他者”而受到西方的抵制或制裁。〔47〕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故意扭曲“修正主义”的内涵及评判标准,他们通过否认对“修正主义”概念性叙事中任何规范性内涵(normative connotation)的限定,通过美化西方国家对于既有旧秩序的捍卫,宣扬现时代的国际秩序对于新兴国家的形塑功能,从而在学术性叙事中提升现有秩序的引导力和影响力。〔48〕
以历史观照现实,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关于修正主义者和维持现状者等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争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学术谱系,但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对于数百年来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中的核心概念和命题的解释依然局限在传统的学术理解之中。在他们看来,涉及“进步与文明”“现状与修正主义”等看似中性的核心命题之实质,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依托、以“道德与进步”为指向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圭臬。渐渐地,这些原本属于中性的概念和命题,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中,不断被强化为西方自我与非西方“他者”的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这一话语叙事逻辑颇具误导性和倾向性。在各大文明和发展模式交流激荡的绵延历史发展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总体判断和实践,被强行纳入西方话语叙事主导的全球发展逻辑中,非西方国家任何背离西方话语叙事逻辑的道路选择,都被看作是消极的“修正主义”,饱受争议。这种二元论的叙事逻辑切割,使西方国家进一步主导着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路径。
西方国家借助“道德与进步”“文明与发展”等单一线性标准,将多样态发展的世界抽象成“进步与文明的西方”与“落后与野蛮的非西方”两种图景,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间的隔阂与对立。正如霸权稳定论者所坚持认为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对世界的改造和征服,事实上体现了“倡导新型文明的宏伟使命”。〔49〕以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依照大不列颠和美国治下的和平霸权叙事,将英美描述成为世界历史秩序的建筑师,而故意忽略长期以来东西方其他文明对于“秩序”和“文明交流”的共同期待和重视。〔50〕迄今为止,全球文明史的发展也验证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于世界秩序和全球发展的贡献,很多学术研究也在不断质疑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和框架,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世界秩序中的西方话语叙事,推动着学界和政治精英对相关问题的深度思考。〔51〕可以看出,霸权稳定论者倾向于将西方中心主义自传式话语叙事逻辑定义为世界秩序话语叙事的本真面目,进而将数世纪以来不同文明间的传承和交流割裂开来,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叙事,从而为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叙事逻辑提供学理基础。显然,这一阶段的话语叙事是对19世纪中期摩根索等传统现实主义者的话语叙事的又一次提升和弘扬,使其能够绵延几十年,在经历漫长的历史演进后,依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体系的核心意涵。而随着完全不同于传统权力的逻辑演进,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崛起,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必将面临深层次的挑战和重构。
四、国际关系中的“当代中国崛起”叙事及超越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渐趋遭遇新兴国家崛起的挑战,学界围绕全球权力和秩序的重构纷纷著书立说,纵论应对之策。关于国际关系行为体中“修正主义力量”和“维持现状力量”内涵的学术争论亦随之而来。与此前两轮因大国力量对比而衍生的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相比,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已有了新的逻辑发展。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从另一个视角重新书写转型中的国际关系,重新考量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可能的国际秩序重塑。〔52〕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以微妙且复杂的心态审视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转型,〔53〕十余年来他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些关键问题是,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既有的西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否一如历史的过往,沿循霸权轮替的逻辑,是否能够通过制度和体系的规制性作用推动或引领新兴国家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并通过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推进新兴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自由化发展。〔54〕中国在南海呈现的“改变地区现状”的战略意图,以及通过创建亚投行体现的地区战略部署,是否能够通过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体系和秩序加以规制和约束。〔55〕
在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学者看来,中国在亚太所推进的地区发展战略,对于“地区秩序的维护者”美国来说隐含着极大的挑战。〔56〕艾利森的观点在美国精英阶层中极具代表性,他们对于中国这一有着悠久历史传承和独特政治文明、发展视野的国家抱有深深的忧虑,这些精英讨论的核心在于一个“崛起”的新兴国家究竟是代表着一种现有秩序的“稳定性力量”,还是代表着可能冲破西方中心主义制度藩篱的“修正主义力量”,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能力的重塑将是潜在的巨大挑战。〔57〕
显然,由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国际体系的调整和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重构,依然围绕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道德与进步”“文明与发展”等核心理念展开,其中呈现的依然是西方国家的“指令性叙事”逻辑。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新的国际形势,西方国家依然固守传统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的核心和基本路径,尝试将“崛起的新兴力量”与“发展和现代化”等一系列西方内在核心思想勾连在一起,希冀通过制度和体系的力量维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话语叙事。〔58〕
耐人寻味的是,与上述对中国的认知和期待相比,西方国家对于同样是“新兴国家”的印度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话语叙事逻辑,印度在西方国家的话语叙事逻辑中没有“西方”与“非西方”的显著分野。在近年来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及印太战略实践中,对于印度的崛起所带来的地区安全影响,并未在美国决策精英层引起广泛争议。正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对于近代“新兴国家”德国的认知一样,如今的印度犹如昔日的德国,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中呈现出相似的一面,这也揭示了所谓“西方”与“非西方”的身份识别和时代分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国家对于既有国际秩序核心理念的固守抑或摒弃,取决于新兴国家是否对于重塑新的秩序抱有热切的期待或努力。〔59〕凡此种种,通过对德国、印度和中国晚近百年的实践例证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正在不同的场景和时空中缓慢演进和调整。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乃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文明、地缘等长时段因素,有力而鲜明地重返国际关系话语叙事进程,与这一进程相伴而生的,是非西方文明群体兴起的总体发展趋势。西方世界对这一重大历史转型时刻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数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其思维也难以跳脱汤因比所说的各大文明单位间的“挑战—应战”模式。〔60〕由此,作为新兴“挑战者”的中国,自然被西方当成国际社会的“他者”,需要以制度学习和规范引领的模式加以诱导和制约。
总体来看,围绕中国“崛起”而引起广泛热议的西方学术性或概念性叙事话语,正在经历漫长的调试和审视过程,而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所固守的自传式叙事模式却未有根本改变,其主要根源在于依托西方自由主义理念而长期衍生发展出来的固有世界观。在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看来,当今西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遭遇的困境和挑战,并不主要来自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叙事逻辑的墨守成规和落后停滞,而主要在于受到了外部世界“新兴力量”的修正主义实践的冲击。而社会历史、战略文化、文明传承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这一“修正主义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拷问,从而,中国正在经历的任何方面的政治发展和经济进步,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中,呈现的总是区别于西方的“非西方力量”,总被看作是影响乃至危害西方自由、民主、进步和发展的威胁或挑战。〔61〕
这一思维定式其实涉及的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上的分歧。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中,所推崇或沿用的基于非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刻意抽取不同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主体性特征,强调西方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塑造和整合作用。以此方法来观察中国所带来的国际体系变革性的影响,就不难理解美国国内精英和大众普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忧虑,也不难理解其背后深刻的学术性叙事话语的力量,这一思维也是美国对华政策遵循的逻辑主线。〔62〕
从文化史或文明史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文明”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新支柱,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与复兴,所有这些现象,已经把对文化和文明的认同置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核心。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赖以维系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体系正在加速重构,显然,中国和俄罗斯、印度等国已被渐次纳入这一体系重构的时空之中,被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不断审视和观察。西方国家希冀在不撼动传统话语叙事逻辑根基的基础上,以改良的方式引导中国等新兴国家沿着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实现转型。
五、国际关系话语中“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
随着国际权力加速重组尤其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衰落,从学理和政策实践层面重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不仅反映出西方国家精英对于当前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等核心命题的困惑与忧虑,也从学理层面动摇着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逻辑根基。
“反西方话语叙事”的变革首先从学术研究领域展开。自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国际学界对于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关系话语叙事逻辑已开始进行反思和审视,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正是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对于国际规范的“修正主义倾向”,〔63〕美国一直“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对外征战还是榜样主义立场上(in crusading or in examplarism)都是如此”。〔64〕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教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霸权国最有可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虽然很多情况下美国被描述成维持现状的国家,但其外交实践表明“美国在特定情势下会毫不犹豫地沿袭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65〕从本质上看,国际学界通过对过往20多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实践进行观察,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在特定事件中所表现的集体性的霸权行为逻辑”,颠覆了西方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原则,呈现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所坚守的基本原则的背离。
西方国家本身的外交实践和学术困惑挑战着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性叙事。无论是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实践,还是从近年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全球外交实践,都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叙事内在的悖论和对立性,〔66〕更体现出西方国家对于概念性叙事的双重标准和选择性运用,表现出西方国家对于“新兴崛起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功能的深深忧虑。换言之,面对新的全球治理形式和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国家单纯以“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帝国秩序观”为判断标准和原则,对任何非西方世界主导世界事务的理念和实践冠之以“修正主义”并大加挞伐,其实质是继续维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叙事逻辑和全球霸权。〔67〕
最终,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日益走向“双标化”和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新兴国家和行为体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良善性改革正在不断动摇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叙事根基,使其日益陷入“标签化”的境地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也推动着西方进一步思考何为“积极的修正主义”和“消极的修正主义”,推动着西方进一步以理性的方式看待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带给世界的进步。〔68〕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和美国国防部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NDS)中都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修正主义大国”,其背后的逻辑是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悖的世界”,希望能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重塑印太地区秩序”。在美国部分政治精英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及其外交实践,正在“削弱二战后所确立的国际秩序”,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正在夺取西方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对西方有利的全球秩序”。〔69〕
西方精英认为,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需要将中国“塑造成邪恶的修正主义者”,更要强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输出国家中心主义的经济模式,不断提升军事能力”的盲目认知,将中国“全面勾勒成对国际秩序造成消极影响的修正主义国家”。2017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进一步指出,类似中国这样的“修正主义大国”正在“寻求颠覆支持西方经济繁荣的全球秩序”,因此需要全方位加以警惕并采取一系列遏制策略,美国从2018年7月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广泛征收关税,即为例证。〔70〕此外,美国政治精英认为,美国在许多领域必须拥有关键能力以应对挑战。2018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特朗普的军费开支法案,该法案提议将国防预算增加610亿美元;〔71〕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也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崛起”。由此,中国等新兴行为体在西方传统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中被描述为“消极的修正主义力量”,因为“这一力量”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概念性叙事相矛盾,中国并没有像欧美等西方国家预期的那样,通过对西方秩序的学习和模仿逐渐趋同并“合流(converging)”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信念背道而驰,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理念上并未被看作是“道德与进步”,对此西方国家需要谨慎应对,甚至采取遏制战略。
六、结 语
西方国家围绕新形势下新兴国家发展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所形成的叙事模式,正在不可避免地经历重构和颠覆。数百年来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思维所形成的话语叙事逻辑正在遭遇困境和挑战,以“指令性叙事”为范式、以“道德与进步”为核心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体系,在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已遭致全球社会的全面审视、反思和抵制,其“自传式叙事”“概念性叙事”的理论根基正在坍塌和崩解。尽管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殚精竭虑,推动着一波又一波的理论更新和重塑,但依然难掩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在新时代的迟滞与孱弱,摩根索、吉尔平、温特们苦苦的理论探寻和政策设计,终将不能再为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叙事提供进一步的、顺应时代进步的知识生产,其研究也终将日益陷入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无法自拔。
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目前需要反思的,是如何以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以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眼光、行动看待和理解世界新兴力量对于国际秩序的改革和推动。国际学界需要围绕“道德与进步”“发展与文明”等西方传统概念性叙事进行反思与重构,需要从学理上深刻阐释新时代的全球秩序对于既有陈旧理念和思想的颠覆性影响,需要更广泛地吸纳新兴国家建设性的理念和思想,丰富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框架和逻辑。对于全球治理行为主体尤其是西方国家而言,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陈旧思维,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着眼全球政治发展和民生福祉,推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密切交流与相互学习,打造基于现时代语境、符合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现代性话语叙事。〔72〕更重要的是,学界应加强概念性叙事的创新性“知识生产”,并以极大的耐心和热忱审视中国等新兴行为体的积极作用,而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进一步通过话语创新,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世界勾勒出丰富、具体而又符合时代发展的书写模式。
注释:
〔1〕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2〕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3〕Behravesh,Maysam(2018),“State revisionism and ontological(in)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complicated case of Iran and its nuclear behavio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21:4,pp.836-857.
〔4〕Davidson,Jason(2006),The origins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 quo states,London:Palgrave,p.14.
〔5〕Johnston,Alistair Iain(2003),“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27:4,pp.5-56;Davidson,Jason(2006),The origins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 quo states,London:Palgrave;Ikenberry,G John(2011),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chweller,Randall(2015),“Rising powers and revisionism in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s”,Valdai Papers # 16,May;Wilson,Jeffrey(2017),“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from a revisionist to status-seeking agend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19:1,pp.147-176.
〔6〕Ward,Steven(2017),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81;Gries,Peter and Yiming Jing(2019),“Are the US and China fated to fight?How narratives of‘power transition’may shape great power war or peace”,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32:4,pp.456-482;Thies,Cameron G and Mark D Nieman(2017),Rising powers and foreign policy revisionism:understanding BRICS identity and behavior through tim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pp.3,15;Ward,Steven(2017),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Rousseau,David(2006),Identifying threats and threatening identitie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15.
〔8〕Manners,Ian(2002),“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40:2,p.239.
〔9〕Davidson,Jason(2006),The origins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 quo states,London:Palgrave.
〔10〕Damro,Chad(2012),“Market power Europ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19:5,p.697.
〔11〕Merlingen,Michael(2007),“Everything is dangerous:a critique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Security Dialogue,38:4,pp.435-453;Vadura,Katharine(2015),“The EU as ‘norm entrepreneur’ in the Asian region:exploring the digital diplomacy aspect of the human rights toolbox”,Asia Europe Journal,13:3,pp.349-360.
〔12〕Piening,Christopher(1997),Global Europe:the European Union in world affairs,London:Lynne Rienner.
〔13〕Hurd,Ian(2007),“Breaking and making norms:American revisionism and crises of legitimacy”,International Politics,44:2-3,pp.194-213;Bukovansky,Mlada(2016),“The responsibility to accomodate.Ideas and change”,in TV Paul(ed.),Accommodating rising powers:past,present,and fu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87-107;Schweller,Randall(1999),“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pp.1-3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256页。
〔15〕〔16〕〔20〕〔22〕〔24〕Somers,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1994),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in Craig J.Calhoun(ed),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Cambridge,United Kingdom:Blackwell,pp.44,62,62,63,63.
〔17〕Suboti,Jelena(2016),“Narrative,ontological security,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Foreign Policy Analysis,12,pp.610-627;Hagström,Linus and Karl Gustafsson(2019),“Narrative power:how storytelling shape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32:4,pp.387-406;Patterson,Molly and Kristen Monroe(1998),“Narrative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p.316.
〔18〕〔21〕Suboti,Jelena(2016),“Narrative,ontological security,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Foreign Policy Analysis,12,pp.612,610-627.
〔19〕Patterson,Molly and Kristen Monroe(1998),“Narrative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pp.315-331.
〔23〕Autesserre,Séverine(2012),“Dangerous Tales:dominant narratives on the Congo and thei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African Affairs,111:443,pp.207-208.
〔25〕欧阳向英、〔加拿大〕阿列克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26〕Winkler,Stephanie C.(2019),“Soft power is such a benign animal:narrative power and the reification of concepts in Japan”,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32:4,pp.483-501.
〔27〕〔31〕Morgenthau,Hans,1962(1948),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pp.39,41.
〔28〕Schuman,Frederick L.(1948),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destiny of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New York:MacGraw-Hill;Kissinger,Henry(1957),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Wolfers,Arnold(1962),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 Hopkins Press,p.18.
〔29〕Schweller,Randall(1999),“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p.18.
〔30〕〔49〕Hobson,John(2012),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85-187.
〔32〕Carr,EH(1939),Britain: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versailles treaty to the outbreak of war,London:Longman Green,pp.26-27.
〔33〕Cox,Michael(ed.)(2000),E.H.Carr:a critical appraisal,London:Palgrave Macmilan,p.213.
〔34〕〔38〕Gilpin,Robert(1987),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72.
〔35〕Organski,AFK and Jacek Kugler(1980),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4.
〔36〕〔53〕Lemke,Douglas(1997),“The continuation of history: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34:1,pp.24,32.
〔37〕Acharya,Amitav and Barry Buzan(2007),“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7:3,p.288.
〔39〕〔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13-229页。
〔40〕〔41〕〔43〕Buzan,Barry and George Lawson(2015),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2-98,36-98,123.
〔42〕〔44〕Deudney,Daniel,and G.John Ikenberry(2012),“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or a post-exceptionalist era”,Working Paper 11,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pp.18,4.
〔45〕Mandelbaum,Michael(1997),“Westernizing Russia and China”,Foreign Affairs,76:3,pp.93-97.
〔46〕〔62〕Nymalm,Nicola(2013),“The end of the ‘liberal theory of history’? dissecting the US congress’ discourse on China’s currency poli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7:4,pp.388-405.
〔47〕Nymalm,Nicola(2017),“The economics of identity:is China the new‘Japan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48〕Jaschob,Lena,et al.(2017),“Was frustriert die Gewinner? revisionismus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und das Rätsel revisionistischer Aufsteiger”,Zeitschrift für Auβen-und Sicherheitspolitik,10:1,p.10.
〔50〕Stuenkel,Oliver(2016),Post-western world: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Cambridge,United Kingdom:Polity,pp.34-47;Hobson,John(2004),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1〕Suzuki,Shogo,et al.(2013),International order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fore the rise of the west,London:Routledge.
〔52〕Lim,Yves-Heng(2015),“How(dis)satisfied is China? A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4:92,pp.280-297;Goldstein,Avery(2007),“Power 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30:4/5,pp.639-682.
〔54〕Segal,Gerald(1996),“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International Security,20:4,p.108.
〔55〕Wilson,Jeffrey(2017),“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from a revisionist to status-seeking agend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19:1,p.150.
〔56〕〔美〕格雷厄姆·艾林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0页。
〔57〕Kastner,Scott L and Philip C Saunders(2012),“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56:1,pp.163-177.
〔58〕Turner,Oliver(2014),American images of China:identity,power,policy,London:Routledge,pp.152-154.
〔59〕Turner,Oliver(2016),“China,India and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 Pacific:the geopolitics of rising identities”,Geopolitics,21:4,pp.922-944.
〔60〕〔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67页。
〔61〕Turner,Oliver(2013),“Threatening’ China and US security: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ident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9:4,pp.903-924.
〔63〕Hurd,Ian(2007),“Breaking and making norms:American revisionism and crises of legitimacy”,International Politics,44:2-3,pp.194-213.
〔64〕Hurrell,Andrew(2005),“Pax Americana or the empire of insecur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5:2,p.164.
〔65〕Schweller,Randall(2018),“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1:1,pp.23-48.
〔66〕Shambaugh,David(2001),“China or America: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Survival,43:3,pp.25-30;Ikenberry G John(2017),“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17 April.
〔67〕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
〔68〕Buzan,Barry(2010),“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3:1,pp.5-36;Ikenberry,G John(2008),“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87:1,pp.23-37.
〔69〕Breuer,Adam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2019),“Memes,narratives,and the emergent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32:4,pp.429-455.
〔70〕Economist(2018),“A full blown trade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looks likely”,21 July.
〔71〕Myre,Greg(2018),“How the Pentagon plans to spend that extra $61 billion”,NPR,March 26.
〔72〕Acharya,Amitav(2014),“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and regional worlds: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58:4,pp.647-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