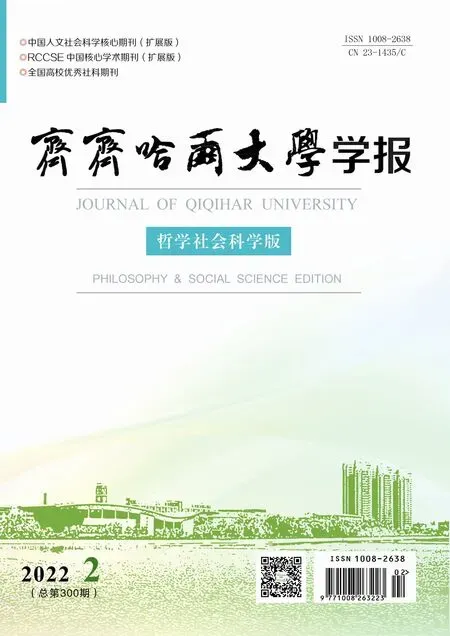《还乡》中的空间共同体想象
王华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托马斯·哈代是跨越两个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大文豪,卡尔·韦伯称其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哈代通过诗意的语言在英国19世纪传统文学与20世纪现代文学之间建构起一座桥梁,成为转型期英国文学中书写现代性焦虑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哈代不仅继承和传承了传统英国文化,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现代意识,其笔下既有古朴恬静的牧歌与田园,又有躁动繁华的商业与城市。哈代基于故乡多塞特郡想象的威塞克斯王国,在赋予其作品真实感的同时涂抹上一层亦真亦幻的神秘感。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横轴上重要的时间概念,在承载历史承前启后与风云巨变的同时,展现出一幅包罗万象的宽屏幕与沧海变桑田的时代画面。维多利亚时代不仅代表历史横轴上的推进,而且象征空间纵轴上的延展,它像似一种空间意义上的三维图景,而纵向切面比横向平面更具审美想象力与空间诗意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着转型与变革,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英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国向新型工业国转变的历史变革。工业革命在带给城市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其触须逐渐向偏远落后的农村延伸。借工业化的东风,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另谋出路,或胸怀梦想,或背井离乡。伟大的时代不只是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黄金年代,维多利亚时代象征着英国文学另一个鼎盛期。许多伟大的作家在这一时期走向英国甚至世界文坛的高峰,托马斯·哈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哈代一生一共创作15部长篇小说,出版14部,几乎部部经典,是维多利亚小说的高产与领衔作家。
《还乡》的问世,预示着哈代的小说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也让其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获得关注。雷蒙德·威廉斯在《英国小说》中曾经指出,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百年英国小说,一直致力于对共同体的探索与想象。于哈代而言,其作品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共同体意识与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1]它在作家所生活的社会烙下了一道深深的传统记忆痕迹,一种糅合了焦虑、理想和超越的冲动。《还乡》虽现实情怀浓重,悲剧色彩明显,但其中蕴含的共同体精神以及作家对威塞克斯乡土空间的诗意想象同样溢于言表。
一、威塞克斯之梦:诗意的家园
哈代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多塞特远郊乡村度过的,其生活体验和创作源泉无不是围绕着真实的故乡而展开和想象。哈代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空间为创作的原型或背景,建构起一个承载着梦想与记忆的美好家园,并赋予其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威塞克斯(Wessex)。威塞克斯显然是一个半真实半想象的空间存在域,它是集古朴、宁静、亲切、贫穷、偏僻等传统特质于一身的共同体画面,却又在现代工业与商业文明的影响与冲击下蠢蠢欲动。记忆中的美丽和现实中的悲凉正在经历着看似有形更似无形的变化,乡村空间在一点点缩减,城市空间在一步步延展,城乡之间的地理和心理距离都在悄无声息中拉近,原本近乎平行的两个世界即将迎来彼此之间空间格局的大变革与大融合。
面对乡村的衰落沉闷和城市的繁荣喧嚣,哈代并没有顽固地坚守着日渐被解构的传统共同体不放,更没有一味地为城市化商业化唱赞歌,但作家依然在创作过程中为怀旧情怀和诗意乡愁留足想象的空间,哈代的内心深处总是希冀有朝一日可以为生活在埃顿荒原的人们重建美好如初的栖居之地与田园之家,这梦想不仅童真更有诗意。“只要人们意愿相同并能达成共识,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就会形成这种或那种共同体”。[2]这种建立在荒原村落基础之上的共同体,长期以来维系着人们的地缘情感与集聚风俗,并在人们内心形成诗意化的印记。一旦共同体的诗意遭遇危机和解构,荒原就会失去原本的宁静与舒适,也必然意味着威塞克斯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萎缩与坍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昔日笼罩着乡土世界的田园风光被不断扩张的城市空间挤压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现实中的威塞克斯从有序一步步滑向无序。祖祖辈辈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因传统共同体动摇带来的危机与焦虑,男主人公克莱姆由城及乡的还乡之路表明,哈代试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以此为基点为乡土世界找到重构过去、复兴传统的诗意路径。
工业革命以降,英国乡村世界曾经的“绿水青山”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金钱地位”的无尽迷恋与疯狂追求,结果造成“外来工业主义同乡村人性的对立”。[3]传统乡村共同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暴风骤雨的冲击下,难以继续维持乡土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长久以来约定成俗的共同体架构不断被解构和瓦解,哈代儿时记忆中的威塞克斯美好家园与其它乡村一道成为“天涯沦落人”。自然环境的退化、生态空间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异化和经济结构的重组,使得曾经幽静闭塞的荒原面临巨大危机,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家园、失去土地,广大农村地区走向贫困和萧条。主动放弃巴黎体面工作与地位尊严的克莱姆,其返乡之旅凸显出哈代对回归自然、生命与自我的诗意探索。
自然与生命是乡土世界得以维系的命脉,它们与乡村一道建构起一个“三位一体”的空间形态,并彼此成就形成相对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还乡》中处处可见传统乡村共同体留下的蛛丝马迹,但曾经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淳朴的乡风民俗伴随着乡土世界的巨变走向衰落甚至不见踪影。现实与儿时记忆之间的落差,让威塞克斯成为哈代及其读者内心一种神秘、古朴而诗意的存在,故乡虽已不再是曾经的世外桃源,乡愁依然是主人公克莱姆返乡的动力所在与情感所系。返乡后的克莱姆,不论其理想与抱负遭遇何等阻力与不幸,他继续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想走的路,并对爱情充满期待,这其中无不包含着哈代对乡村行将逝去美好生活的流连与眷恋。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还乡》在内的哈代小说尽管充满悲剧色彩,但哈代本人并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甚至可以断定他对英国乡土现实依旧抱有一种诗意的浪漫主义态度。哈代清醒地看到处于衰落与解构困境中的威塞克斯所面临的病痛与苦难,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为“生病”的王国寻找重构乡村共同体的良药,在《还乡》中哈代的这种情怀表现得尤为明显。
克莱姆的返乡将哈代对威塞克斯乡土世界的不舍从精神层面推至现实空间,从荒原到巴黎再从巴黎到荒原的双向空间位移,暗含着作家对童年故土的美好记忆和对乡村未来的诗意理想。“当我们在孤独中沉入悠久的梦想,远离现在重新生活在生命的最初年代,几个孩子的面孔迎着我们而来”,[4]所有童年记忆在克莱姆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基于此,内心孤独的克莱姆从未真正离开过荒原故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始终无法适应和接纳巴黎的花花世界和珠宝店无聊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浑身上下都是荒原挥之不去的印迹、画面和气味,他既是荒原儿子也是荒原的象征。这种与荒原剪不断的关系,使得远在巴黎的克莱姆觉得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荒原的喜欢超越任何大都市。对童年的梦想使得克莱姆再次看到故乡最初的美好,他怀揣绅士梦想,毅然决然放弃巴黎的体面工作与美好前程,返乡“创业”,开办教育。作为哈代代言人的克莱姆被赋予神圣的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帮助那些穷人和愚昧之人获取知识、远离沉沦。只可惜,曾经再美好的乡村共同体也抵不过现实英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变,克莱姆对传统荒原共同体的流连和对重构乡村共同体的期许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
二、荒原之痛:逝去的田园
威塞克斯与巴黎等大都市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空间位移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多元化的复杂关系,看似矛盾体的背后却是另一种统一体。梭罗曾经在《散步》一文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人们只有在荒野中方可守住世界的整全,这一点在克莱姆身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论巴黎的都市生活多么繁华、富足和体面,依然无法和克莱姆心中的故乡埃顿荒原相提并论,在经历了巴黎的身心俱惫之后,克莱姆在荒原迎来生命的“第二春”,尽管返乡后的经历充满坎坎坷坷,但至少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要的生活与理想。但是,自从和荒原上到处游荡的精灵尤斯塔西亚相遇相恋相离,克莱姆便与自己梦想拯救的田园世界渐行渐远。
与克莱姆形成鲜明对比的尤斯塔西亚,有着和克莱姆完全不一样的对荒原的空间化情感体验与需求,她是出生在荒原以外的荒原之子。尤斯塔西亚出生在美丽富足的海滨城市,她对童年的记忆充满许多荒原孩子无法感知的幸福与自豪,她不仅有出众的颜值做担当而且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做后盾,尤斯塔西亚所有诗意而美好的记忆都停留在了让她魂牵梦绕的城市。这一切使得从小在荒原上游荡的尤斯塔西亚显得“与众不同”,与祖祖辈辈坚守贫穷落后闭塞埃顿荒原人形成鲜明对比,也使得她与整个荒原空间格格不入,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办法逃离的荒原建立亲密关系。自幼失去父爱母爱的尤斯塔西亚,迫于生存压力随外祖父费伊迁居埃顿荒原生活,并逐步养成荒原般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坏女孩”性格,她对荒原的感情显露出非常明显的“非亲生”趋向,她始终认为,荒原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园,而自己也不该属于沉闷阴郁的村庄。对于克莱姆如同田园般美丽的埃顿荒原,在尤斯塔西亚眼里却变成身体的牢笼和精神的地狱,她百般挣扎与反抗,却命中注定般难逃荒原的束缚。
自幼缺失父母之爱的尤斯塔西亚,养成了与荒原上其它女孩子迥异的性格,她不仅热情高傲而且敢爱敢恨,成为荒原上绝对的另类存在。虽然看起来整日在荒原上到处游荡,尤斯塔西亚内心深处的家园依然停留在无法回去的记忆中的海滨城市,也存在于她朝思暮想的大都市巴黎。和荒原一样,大都市同样成为尤斯塔西亚遭遇现实创伤的根源,她始终无法摆脱套牢自己的“怪圈”,她既是都市的弃儿也是荒原上的游魂,实际上都市才是造成她痛苦的真正深渊与主要根源。尤斯塔西亚厌弃荒原上的一切,期待从荒原逃至大都市,过上城市人灯红酒绿的生活,只可惜她执迷不悟地两次选择以爱情和婚姻为逃离荒原的跳板,这就注定了她悲剧化的命运。原本想要彻底逃离荒原的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完成自己在荒原最后一次露面,以自我的香消玉损将自己永远淹没于荒原的洪水之中。尤斯塔西亚的意外死亡预示着威塞克斯田园世界无法挽回的解构与消解,某种程度上讲尤斯塔西亚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还乡。
于尤斯塔西亚而言,埃顿荒原如同边沁和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一样,时刻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让她感到窒息、痛苦和害怕。在受到荒原规训与惩罚的同时,她的悲剧与其不合时宜的天性和命运不无关系,她像一个不该存在却又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游荡于黑夜下的荒原,她或被称作黑夜女王、高贵女神,或被视作女巫、异教徒,甚或被约布莱特太太视为不正经的女孩。正如处在变革与转型期的荒原一样,尤斯塔西亚的内心同样充满躁动、焦虑与叛逆,她成为荒原的对立体,也变成自我的矛盾体。尤斯塔西亚天生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愿意为别人所左右,也不愿意寄人篱下,她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打破传统伦理道德与约定成俗的社会秩序带给自己的束缚与捆绑,这就使得她和整个荒原关系紧张,甚至走向敌对状态。如天堂般存在的埃顿荒原,在尤斯塔西亚心中却成为地狱般的空间事实。
与之不同,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托马沁则在荒原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身心归属,因为她能够将自己完全融合于荒原之中。托马沁淳朴善良、真诚坦率,简单的如同一种透明般的存在,她已经化身为传统荒原共同体的缩影,与荒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生共存关系。在尤斯塔西亚眼中无聊乏味的荒原生活,却被托马沁过得诗情画意,并撑起埃顿荒原所剩无几的田园诗意。从巴黎返乡的克拉姆希望自己貌美如花的堂妹托马沁能够找到一个有着稳定工作的如意郎君,并随丈夫搬到城里生活,但却遭到托马沁的拒绝。在天真诚实的托马沁看来,尽管埃顿荒原非常闭塞落后,但是她早已习惯这里的一切,住哪都不会比住在荒原让她更加快乐幸福。生活在同一片荒原中的尤斯塔西亚和托马沁,却与现实社会建构了不一样的空间关系,他们在身体上看似存在于同一个空间共同体,却归属于不同的精神空间共同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形成一张一弛的双重空间格局。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家,哈代善于将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情结推动置放于特定的空间中,空间成为哈代小说不可或缺的主体要素。作为土生土长的乡村人并对乡村抱有深厚感情的地域作家,哈代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19世纪英国乡土世界可谓了如指掌,他对那片土地有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体验与审美期待,他以空间为载体将个体、自然、社会和情感纳入整个荒原共同体之中。“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这样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地域的层面上,也体现在家庭内外之间,禁止的和容许的行为之间,以及合法的与违法的行为之间。在文学作品中,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5]通过与空间频繁互动,使得克莱姆和尤斯塔西亚超越自身存在而建构起与荒原无法割裂开的共在关系,哈代就是这样实现了情感、道德和价值的空间化。
《还乡》通常被归入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作品不仅以语象的方式透视着埃顿荒原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象的全景图,而且以广角镜头的方式呈现出人物与环境、性格与冲突之间多元复杂的悲剧关系网。全景图和关系网既是作家对埃顿荒原上不同场景进行的并置化处理,也是作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同生共存关系进行的同一化建构。具体表现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和处于不同视域的人相互凝视,并以彼此为中心或焦点形成极具画面感的场域,从而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构建起一种相互依赖、彼此融合的统一体,虽有矛盾、冲突甚至毁灭,但谁都无法真正离开这个有机整体而独立存在。无法摆脱荒原共同体而“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们就无法阻止童年记忆中曾经美好的田园世界走向衰落与支离破碎,所以他们的痛不只源自荒原,也和他们在荒原上编织起的肉体、精神、道德与情感空间关系密不可分,这其中爱情空间的复杂多变让荒原之痛雪上加霜,更让田园诗意化为灰烬。《还乡》聚焦克莱姆、尤斯塔西亚、托马沁、维恩和韦狄之间的爱恨情仇,但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埃顿荒原撒下痛苦的种子。自从海滨圣地布达茅斯搬到穷乡僻壤的迷雾岗起,尤斯塔西亚的悲剧命运与爱情纠缠便与这片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荒原连在一起,但爱情只是遮蔽真像的幌子而已,她痛苦的真正根源是布达茅斯和巴黎等大都市在其内心深处种下的诱惑与祸根,没有活在大城市的命却日日夜夜做着逃离荒原的梦。其实从一个空间逃至另一个空间,并不代表一个人可以摆脱共同体的限制与约束,相反可能是从天堂坠入地狱。尤斯塔西亚的意外溺亡,恰好表明即便是情愿搭上后半生的生命,也无力改变注定的痛苦。当然,这种宿命般的艺术想象,并不能证明哈代是一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相反作家想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悲观与悲剧为威塞克斯找到更好的出路。或许单从克莱姆梦想改造荒原计划的流产,足以说明日渐消失的乡土在哈代的内心依然是挥之不去的痛,更或许和谐共生的田园世界才是作家心中最理想的空间共同体。
三、“他者”空间:想象的共同体
当地理学与文学联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文学地理学,空间取代时间成为全新的叙事路径,空间叙事也因之获得更大范围的关注。空间属于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概念,与地理学、物理学、艺术学、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文学等众多学科存在关联,早在古希腊已经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谈论过空间,到了近现代尤其是空间转向的发生,不断涌现出莱布尼茨、休谟、尼采、马克思、列斐伏尔、福柯、巴仕拉、哈维和苏贾等一大批空间理论家,经由他们,空间较之时间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作为人类存在的两个主要维度,时间和空间影响到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过去由时间承载的东西在现代尤其是后现代背景下逐渐被空间所替代。“空间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现实,它还意味着文化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方位参照,还是一种价值反映;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还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并生产着叙事本身。”[6]空间一改过去被遮掩被忽视被遗弃的命运,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力与认知度。尤其是20世纪下半页以降,空间理论快速向文化、艺术和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空间转向的发生标志着人类透视世界的视角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克朗、福柯和列斐伏尔等对文化地理学的阐释进一步深化空间理论的实践面向。
就文学与空间的关系而言,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指出,空间理论改变了小说中地理自然景观的阐释路径,并赋予彼空间全新意义,空间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背景、容器与某个地方,其背后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社会、哲学与审美含义,也承载着权力、意志、情感与伦理道德等意象。埃顿荒原所承载的空间是在建立传统基础上的共同体,曾经的酒馆、篝火和教堂等意象代表着荒原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荒原共同体的习以为常。但在所有的个体当中,尤斯塔西亚是个绝对的例外。尽管每天游荡于荒原之中,但是她却始终徘徊于荒原共同体的边缘,同时也无法走近都市共同体,完全沦为他者化的存在。与其它作品一样,《还乡》担负着哈代批判19世纪英国社会至暗现实的使命,工业革命的触角已经蔓延到曾经静谧、美好而和谐的荒原空间,生活在荒原的人过去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不仅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也主宰着荒原的今日与明天,并一起坚守着面临被解构命运的荒原共同体。这一曾经不可动摇的传统共同体却因工业革命而摇摇欲坠,曾经的主人沦落为他者,个体命运与荒原命运一道淹没于轰轰烈烈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浪潮,曾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在遭遇新的历史考验。
空间相较于时间的边缘地位与存在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对地理的审美想象力,空间转向的发生不断提升空间理论的广度与深度,伴随这一过程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三类,即可感知的第一空间、可想象的第二空间和不断解构与再构的开放型第三空间,列斐伏尔对空间的认知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批判视角。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著名空间理论家和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明确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索亚赋予空间碎片化、拼接化、多元化、并置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等后现代特征,使得空间在理论层面上更加接近共同体。尽管哈代小说创作的时间背景属于19世纪下半页,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较早地将维多利亚时代空间化,埃顿荒原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空间表征,并与共同体联姻形成空间共同体。这其中,小说人物的他者化与边缘化存在事实便是最好的例证。
对生命和未来抱有热情和满怀期待的尤斯塔西亚,尽管事实上生活在荒原,但她却将自己置于大都市与荒原之间的纠缠中,在试图逃离荒原空间的种种努力中,一次次把自己的身心困在荒原的最深处而无法真正逃脱。尤斯塔西亚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7]失去可以居住的空间,尤斯塔西亚随之失去所有的庇护。这样看来,尤斯塔西亚的悲剧并非命运使然,而是由深处转型期的维多利亚社会所造成,她既是城市的弃儿也是乡村的他者,这种看似悖论性的存在背后恰好表明作家通过空间隐喻的方式凸显了维多利亚时代乡村世界的他者化与边缘化命运,尽管城市和工厂离荒原越来越近,但是荒原却被城市和工业推土机般的发展速度推向更远更孤独的空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迅速扩张的后方,威塞克斯依旧“远离尘嚣”,传统宗法制与父权制在荒原上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女性的他者化生存空间与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一直以来,尤斯塔西亚都在试图冲破、逃离荒原对自我身心的禁锢与压制,渴望自由的恋爱和高雅的生活,却在追求理想与实现梦想的路上屡屡碰壁、遭人白眼,甚至以生命的代价实现自己对荒原束缚最后的抗争,同时完成自我作为荒原空间共同体中独特个体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对于尤斯塔西亚而言,近在咫尺的传统共同体难以容纳自我的存在,心中理想的城市共同体却因过于遥远而无法企及,她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却又无法脱离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独立存在,工业革命将她带入一个如此熟知却又非常陌生化的世界。“传统价值分崩离析,人际关系不再稳定,社会向心力逐渐消失,贫富差距日益扩大。”[1]71村庄、农舍、教堂等传统空间符码正在经历着消解甚至消亡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工厂区以及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已经表达了对故土传统衰落的担忧与沮丧。农舍、乡野小路、教堂等传统意象正在一个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市场和公司等现代资本庞然大物。哈代对城市空间共同体的想象,恰好为自己塑造的新女性提供冲破旧传统、追求新希望的机会。尤斯塔西亚从未真正喜欢过荒原上存在过的、依然存在的一切,使得她对不同于荒原共同体的城市共同体充满期待也就不再难以理解。
总之,共同体书写是英国文学的古老传统,也是历代英国小说家的必然选择与审美取向,并与各个时期的英国社会变迁相契合。由哈代想象并建构的威塞克斯王国,既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在早期英国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地理空间,这个亦真亦幻的空间代表了作家对处于急剧转型期维多利亚社会的摇摆态度,他在期待资本主义这一新鲜事物到来的同时,更加表现出对曾经宁静、和谐与朴实乡村田园世界的诗意怀念,这种带有明显复魅色彩的精神返乡凸显了哈代对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深情回望与无限留恋。荒原、海滨城市、大海以及大都市巴黎都不再是简单地理意义上的地域空间,它们超越自身而存在,更多地象征哈代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更好生存方式的审美化努力。不论是克莱姆回乡创业失败还是尤斯塔西亚命丧湖底,都无法完全代表作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学期待,反倒是朴实而又安于现状的托马沁与维恩终获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并给予哈代和读者莫大的鼓舞和启迪。所有这些共同指向一点,那就是哈代怀有抹之不去的荒原情结和怀旧之情,乡村田园空间才是其心中理想的共同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