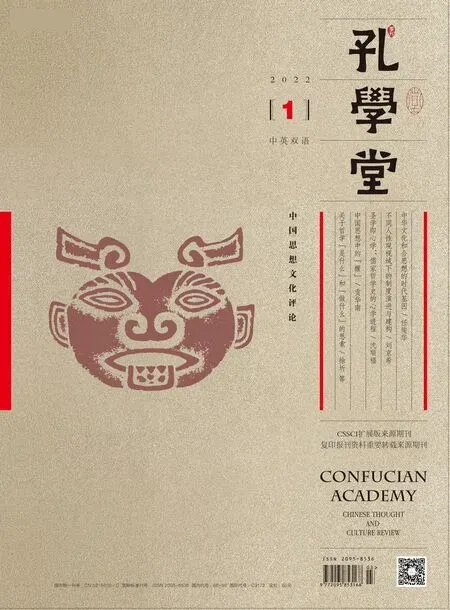圣学即心学:儒家哲学史的心学进程✴
□ 沈顺福
哲学追问本源。本源分为两类,生存本源和存在本原。所谓生存本源,它指事物生存的源头,如同火之苗、水之源。所谓存在本源或本原,指思辨性本原或终极性本原。在一般人眼中,本源便是本原。但是在哲学家看来,本源之中,还有一个终极性本原。它是本源成为本源的最终根据,具有超越性。因此,本源分为两类,即经验性生存本源和终极性存在本原。其中,经验性本源是可知的,而终极性本原则是超越的,只能够通过思辨的方式而明白。对这种终极性存在的思考与求索便是哲学的真正使命。
本源即源头。对于人类生存而言,人的生存本源便是心。心的本义是心脏(heart)。《说文解字》曰:“心,人心也。土藏。在身之中,象形。”①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第217页。心指心脏,简称心。它是人体的一种器官,和“肝、脾、肺、肾”等合为“五藏”②参见王冰注:《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79页。。人的心脏,在中国传统生存论看来,是人类生存之本。首先,心脏为生命体的延续提供动力,故心是生存之本。其次,人的生存不仅仅是生命体的延续,同时还是行为或活动。此时的生存表现为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也以心为本。故《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成人的关键在于修身,即修身是本。修身的中心在于“正心”。因此,心是人类行为的源头,也是行为的主宰者。合而言之,心是人的生存之本源。作为本源的心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考的中心主题。儒家哲学史可以说是一部追问本源之心的历史,儒家哲学史便是一部心学史。古人云:“圣人之学,心学也。”①王守仁:《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集》卷七,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此言不虚。在追问本源之心的内涵进程中,传统儒家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从经验性本源向超越性本原的演变过程。也正是这种转折,标志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从经验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向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转变。两者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传统儒家心学史。
一、以性释心:先秦儒家心学及其初次转向 [见英文版第50页,下同]
儒学始于孔子。从孔子起,儒家便已经开始关注心灵问题。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一方面,孔子希望能够顺心而纵欲、尊重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他又时时不忘规矩与社会秩序。事实上,在动乱的时代,孔子更强调了规矩与原则对人心的约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心要时时以仁、义、礼为标准,遵从仁义之道,以礼持心。虽然孔子已经开始思考心灵问题,但是,此时的认识相对简单。朱熹评论曰:“凡此等皆心所为,但不必更着‘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说在里,教人做。如吃饭须是口,写字须是手,更不用说口吃手写。”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38页。虽然孔子已经有了心的观念,但是并没有直接讲心(“不言心”)。《大学》已经意识到了心灵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和基础性地位,并说出了“一个当然”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页。。《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做事都有一个先后与本末。对于儒者来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身修才能成就天下大事。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修身最重要,而修身的主要内容便是诚意和正心。心正才能身修:“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修身便是正心,心思合理,行为才能合法而可行。正确的心灵是合理与合法行为的基础,心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性要素,是本源。
这种本源之心,在孟子那里叫做性。孟子认为人天生有气质之心,他从道德的角度对天生的气质人心进行了定性——分为善恶两类:一类是善良的本心,另一类是不好的利欲之心。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天生具有仁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这种仁心,又叫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种四端之心,孟子将其视为合理行为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四端之心是人类生存的根据或起点,更是人们合理或正确行为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本。孟子又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作为本源或基础的恻隐之心等是人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别物的根据。这种天生固有的、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本源性存在,便是孟子所说的性。生存,在孟子看来,无非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尽心即尽性,成人便是成性。成性,不仅能够成圣贤,而且足够明智。性不仅是生存的基础,而且也是智慧的根基。孟子的人性论说到底也是一种人心论。心本论转变为性本论。或者说,性本论是心本论的一种演变形态。唐君毅称孟子“即心言性”①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毋宁说是孟子以性释心。心本论向性本论的转向标志着心学向性学的转向。心学向性学的转向,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此,儒家开始借用人性概念来思考人的本质等问题,这便是孟子的人禽之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由此提上议事日程。
荀子也以性释心。荀子也将气质人心分为两类,一类是善心,另一类是利心。荀子并不否定人生来有善心,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它的作用。但是,荀子很少主动讨论它。荀子更关注利欲之心。荀子曰:“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荀子·王霸》)人人都有好利之心。这种利欲之心,“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荀子·修身》)。利心甚至可以发展为虎狼之心,从而祸害人类。这种能够为害的心,因其是天然的禀赋,故而荀子将其定义为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性即天性,它的活动形态便是情和欲等。荀子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好利之心常常带来灾难,因此是坏的,这便是性恶论。性恶论其实也是心恶论。荀子认为,性恶或心恶是人类不良行为的本源,这依然是一种心本论。目前的学术界常常将心和性分开,提出所谓的心善性恶论等,这些观点并不准确。在荀子这里,心和性具有部分一致性,天生的坏心便是人性,性也是心的一部分。
和孟子不同的是,荀子更倡导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观的核心是有为心,有为心的主要表现便是思维。荀子将心比作天君,用以主导人类的心灵活动或思维活动。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能够思考的心灵,如果没有约束,常常自行其是,以至于带来危险和风险,因此,心并不好,或曰心是坏的。对自由思考的心灵的定位,其实属于性恶论的一部分:情欲与心等都是不可靠的人性。因此,尽管荀子重视认识、重视心灵的思维作用,但是,事实上,荀子并不相信心的思维功能的合法性或合道德性。或者说,对于天然的心的活动,荀子并不放心。因此,荀子提出一种心灵之术,即以道来规范人心。教化因此成为必然和必须。
从上述分析来看,《大学》、孟子、荀子等先秦时期的文献或哲学家逐渐开始关注心的活动,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揭示心的性质、作用等。心被理解为人类生存的起点或本源,它具有两个向度,即正确行为的本源以及错误活动的本源,前者为善心,后者为恶心。善心或恶心,孟、荀分别称之为性。孟子以善心、善性为正确生存的根基,而荀子以恶性、恶心为错误活动的本源,这便是以性释心。其中,心与性不是分别之物,而是部分重叠。在孟子那里,成人便是成德性,成性便是尽善心;在荀子那里,修身便是化恶性,化恶性便是改造坏心。与此同时,人心的思维功能也开始显露。在这个时期,人心在人类生存与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得到揭示,心学逐渐转向性学或人性论。人性论或与之相关的讨论直接引导出人的本质观念。
二、偏重有为心与汉代儒家心学 [52]
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字的基础内涵是作为一种动物的生物体。由人的行为而产生“人”字的第二个内涵:人为或人文。人的活动是人类的有意行为。这种有意行为的基础便是有为心。有为心首先还是气质人心。这种气质人心,对于人类而言,其首要功能便是生存之本。董仲舒曰:“故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六,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48—449页。心是生存之本,这便是心的生存功能。它的主要职能便是延续生命,养心便是养身与长寿的主要手段。从传统儒家的生存哲学来看,生命在于气。“故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②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六,钟哲点校,第452页。养生便是养心、养气、养精神。精神或人心是生命的核心,养心便能够长生。
人的生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而且表现为各种社会性行为。这些行为尤其是正确行为的基础便是有为心。董仲舒将这种作为本源的有为心叫做性。董仲舒曰:“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③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钟哲点校,第303—304页。董仲舒提出人性有善端。这其中至少包含两层内涵。其一,善良行为的基础出自人性。这便是性有善端。其二,人性不仅有善端,而且还有恶端。人性是善恶混杂之物,其中的善端便是仁心。董仲舒曰:“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④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钟哲点校,第293—296页。心如栣,能够让人们扬善气而抑制恶气。据此,董仲舒高度肯定了心在生存中的积极作用,心因此获得了肯定。董仲舒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⑤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九,钟哲点校,第263页。只有义才能够和心相匹配,心的活动能够带来仁义,仁义的本源便是仁心。“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八,钟哲点校,第258页。仁便是善心或仁心的扩充与完善。董仲舒曰:“仁,天心。”②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六,钟哲点校,第161页。这并非说仁即天心,而是说仁产生于天心,天心的活动结果便是仁,心是仁的本源。这种仁心说可以说是孟子人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人心不仅是道德仁义之本,而且是认知思维之本。这便是人心的另一个功能即认知或思维。董仲舒曰:“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着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③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三,钟哲点校,第357页。董仲舒意识到心具有思维功能。和以往儒家相比,董仲舒更重视智的作用:“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④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八,钟哲点校,第258—259页。这里的智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理智与智慧。重视理性必然重视心灵的理性作用。对理智心的重视,反映了董仲舒积极有为的人生观或人生态度。以理智为形态的有为心追求智慧,这种生存与智慧的结合,便是神、圣。扬雄曰:“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敢问潜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⑤汪荣宝:《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7—141页。圣人存神,存神即是尽心。尽心者不仅能够长寿而神,而且能够无所不能而神。心是因,圣是果。操心而成圣,舍之而无成。这里的心类似于孟子的性,它不仅是生存的基础,而且是智慧的源头。汉儒更重视理智心或有为心。
三、无心之心与魏晋玄学心学 [54]
人类有为心的最突出表现便是理智活动。理智活动体现于人的日常生活与实践中,如国家治理等。王弼曰:“智,犹治也,以智而治国,所以谓之贼者,故谓之智也。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也,当务塞兑闭门,令无知无欲,而以智术动民。邪心既动,复以巧术防民之伪,民知其术,防随而避之,思惟密巧,奸伪益滋,故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⑥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智即治,有意的行为,它以心思缜密的方式、借助于制度而治国,属于典型的理性活动。王弼曰:“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⑦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8页。“心怀智”即心灵刻意思考。人类的思考活动常常体现了人的个性化的想法与欲求。郭象曰:“彼我之心,竞为先识,无复任性也。”⑧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9页。彼我之心即认知心。郭象将这种认知心叫做“心术”:“耳目,外也;心术,内也。”⑨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4页。内在之心指导人的感觉与活动。郭象进一步指出:“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谓之成心。……人自师其成心,则人各自有师矣。人各自有师,故付之而自当。”①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16页。人人都有“成心”。所谓“成心”即已有之心,它主要指那种自己认可的、成为行为的指南的是非之心,它又叫“师心”。按照现代人类学的观点,理性的人类总是在理性指导下生存。这种生存便是“师其成心”。郭象曰:“任其自然,天也;有心为之,人也。”②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6页。有心之举便是故意地、人为活动,简称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定义揭示了人类的某些基本性质——人类的生存并非自然的生生不息,而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存。不过,郭象却曰:“有为而致恶者乃是人。”③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5页。故意而有为的行为未必是好事。
这种积极有为之心或思虑之心,在玄学家那里,并没有获得认可或肯定。王弼曰:“夫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④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30页。智力常常带来纷争、带来危险。“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薉,虽竭圣智而民愈害。”⑤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94—95页。各种主观的理性活动,哪怕是圣人之智,都有害。因此,王弼主张放弃主观理性的活动,这便是无心。嵇康以养生为标准,认为人为的、理性的活动有害于养生。嵇康曰:“所以贵智而尚动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动则悔吝生,智行则前识立;前识立则志开而物遂,悔吝生则患积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内而接于外,秪足以灾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德〕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⑥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页。崇尚理智、过分追求并不是厚生之道,而是灾身之源。阮籍曰:“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贞。”⑦阮籍:《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1页。刻意的人为之道和自然之理常常是相悖的。最好的方式是无善无恶,放弃理智与是非判断。郭象曰:“夫心以用伤,则养心者,其唯不用心乎!”⑧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39页。用心而伤心,最好的养生方法是不用心。这便是无心、去心:“有心则累其自然,故当刳而去之。”⑨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40页。有意做某事不仅是用心,更是累心、伤心。在郭象看来,这些活动或心术,“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术,遗其耳目。”⑩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4页。故郭象主张无心:“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穷万物之妙数。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旁礴万物,无物不然。世以乱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为不应世哉!”⑪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14页。无心便可以无拘泥。“无心故至顺,至顺故能无所将迎而义冠于将迎也。”⑫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3页。无心即无主观刻意,顺其自然。无心即游心:“然遗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虽宗尧,而尧未尝有天下也,故窅然丧之,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⑬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14—15页。所谓“游心”中的“心”,与其说是思维之心,毋宁说是生存之心或性。游心即随心或顺性。郭象曰:“直无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将迎而靡顺之。”⑭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3页。无心即任由自然,而非刻意去做。刻意便是“迎”:“不将不迎,则足而止。”①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3页。放弃刻意便是无心。无心即任性:“言夫无心而任化,乃群圣之所游处。”②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63页。无心而任自然便可以成圣。
玄学家们倡导无心,并非说不要心,而是主张一种无心之心,即没有思虑的自然心。这种自然心或生存心便是人性。王弼曰:“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能使之热者何气也?热也。能使之正者何仪也?静也。”③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631—632页。不失真的活动发自于性,这种人性的活动,体现了人类行为的自然性或必然性。这便是“性其情”,即一切行为与活动皆顺从自然之性。在嵇康看来,人性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嵇康曰:“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④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第275页。知性便可以知人。对于生存而言,性是基础。嵇康曰:“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⑤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第271页。循性而动,便能够安心或安身。郭象曰:“初,谓性命之本。”⑥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49页。初即性,为生存之本源。既然性本身便是本源,任性便是一种必然,任自然即顺天性。郭象曰:“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⑦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22页。“自然得”即获得固有之性,又叫“真德”:“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得〕也。”⑧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83页。顺性自然而获得之德才是“真德”。“真德”即全性。所谓全性即是率性:“率性而动,动不过分,天下之至易者也;举其自举,载其自载,天下之至轻者也。”⑨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24页。率性而为便能全性、成性。全性、成性又叫率性。郭象将这种全性真德又叫做“率心”:“率心为德,犹之可耳;役心于眉睫之间,则伪已甚矣。”⑩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83—84页。率心其实就是率性:任由自然之心或自然本性。自然人心即自然本性,心即性。
性是气质之物,顺性便是尽性命。这种尽性命,不仅有道德内涵,更有自然内涵,其自然价值便体现于长生中。长生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在王弼这里,重生存心而轻有为心的真正原因在于养神。王弼曰:“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⑪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81页。以无心为心,便能够不害其神。所谓不害其神,其目的便是养神而长生。生存是第一位的。嵇康曰:“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⑫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第45页。尽性命可以长寿。嵇康曰:“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⑬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第45页。长生便是保神,保神便是修性,尽性命而长生。郭象主张通过无心而全神。郭象曰:“夫神全心具,则体与物冥。”⑭郭象注:《庄子注》,《二十二子》,第25页。神全心具,与万物相冥合。圣人之心与万物合为一体,这便是郭象所追求的生存状态。这种融合,从天人观的角度来说,便是万物一体。万物一体也是一种尽性命:享尽自然之禀赋。这便是寿命或受命。享尽寿命者便是长生之人。
四、天地之心:早期理学家的心灵哲学 [55]
魏晋万物一体观的产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场革命。人类和天地之间,由早期的天主人从的关系转变为手足同胞关系,人类取得了与天地相平等的地位。那么,究竟谁来主导或主宰这个一体之物的生存呢?这便是摆在宋明理学家面前的时代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早期理学家们找到了一个传统术语——“天地之心”①关于“天地之心”的起源及其内涵,参见沈顺福:《“天地之心”释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天地之心”,字面意思指天地宇宙的心脏。这个心脏不仅是宇宙生存的源头,同时也是它的主宰者。探讨“天地之心”逐渐成为理学家们最重要的任务。
最初,人们依然按照传统思路来追问宇宙本源或“天地之心”。邵雍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②邵雍:《邵雍集》,郭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3页。天地之心即宇宙万物生存之本。作为本源的天地之心便可以理解为宇宙万物的决定者。张载指出:“心,内也,其原在内时,则有形见,情则见于事也,故可得而名状。……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3页。天地之心即万物生存之本。它不仅是宇宙生成的本源,也是宇宙生存的决定者。既然宇宙有一个决定之心,那么把握了它似乎就可以主宰世界了。于是,张载豪迈地提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320页。传统学术界常常从现代意识出发,以为“为天地立心”的意思是为宇宙提供一个大脑或心脏,这种违背科学常识的观念无法得到现代人的接受与认可。事实上,张载的此番誓言仅仅表示:我们人类不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期待着成为宇宙世界的主宰者。这不仅是古代人的梦想,同时也是现代人的理想。这便是“为天地立心”的雄心所在。所立之心便是“天地之心”,作为本源的“天地之心”,又叫天地之性。张载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页。天地之心必定内含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不仅天生如此、天然地成为生成的基础,而且因为它与天的天然联系,也是天然的合法存在体。因此,由太虚与气所结合而成的性或天地之性便成为生存之本。生存无非是尽性:“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⑥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4页。扩充天地之性便是生存。这个过程便是仁。张载曰:“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立本以此心,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从此而辨,非亦从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则无有不善。”⑦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66页。存心或成性而为仁。张载试图为天地立心、从而建构一个仁义的宇宙世界。仁成为宇宙的生存方式。
作为生存方式的仁,在二程看来,便是宇宙之公道。二程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①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3页。仁本来是儒家的人道。现在,人道不仅于人类有效,而且遍行于宇宙,成为宇宙的生存方式,成为天地之公道。二程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尽?不能有诸己,则其与天地万物岂特相去千万而已哉?”②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79页。我与万物贯通一体,万物与我便不再相去千万里了,而是贯通一体。贯通一体便是仁。于是,二程曰:“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故敬为学之大要。”③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84页。我与万物自然一体。这便是万物在我,即,万物便与我不离。仁即气化流行而贯通一体。
贯通之仁的开始处便是天地之心。二程曰:“于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④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74页。心为仁的开端,仁则是心的活动。二程曰:“阳气所发,犹之情也。心犹种焉,其生之德是为仁也。”⑤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74页。心是种子,仁便是其潜能或存在状态。仁由心而生成。二程曰:“心是所主处,仁是就事言。……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谓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谓之心之用。……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⑥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83—184页。仁生于心。心中有性,而性才是仁的真正的终极性本原。二程曰:“爱出于情,仁则性也。仁者无偏照,是必爱之。”⑦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80页。仁不仅是情、是爱,更是性。性是仁爱的根据。二程曰:“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谓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⑧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01页。天地之心,动而呈现。在生生不息的活动背后隐含着天理。天地之心内含天理。由此,二程找到了仁的形而上的根据。二程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⑨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73页。仁道之中有形而上之理。二程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⑩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90页。天道以天理为根据。二程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⑪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92页。性即理。既然性理一致,那么绝对的终极性的理便也是人类生而固有的东西了,或者说,终极性的理或性内在于人心。这便是朱熹以及后来的心学家的立场:人类天生之心固有天理。
尽管二程将天理视为宇宙的终极性根据,且理在心中,但是,他们并未赋予心以终极性的性质与地位。在小程子看来,“释氏本心”⑫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74页。:佛教以心为终极性本源。儒家则与之不同:“圣人本天”⑬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74页。。儒家以天以及天所具备的天理为终极性依据。“理必有对,生生之本也。”⑭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71页。只有天理才是生生的本原。在二程那里,心虽然也是本源,但是还不是终极性本原,因此并没有得到重视:它仅仅被视为佛学的核心概念。尽管二程也常常提及心,如二程曰:“夫事外无心,心外无事。”⑮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63—264页。事(物)外无心、心外无事(物)。在这里,心仅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是一种形而下的气质之物,也是万物生存的基础或本源。但它仅仅是生存本源,而不是终极性的存在本原。在二程那里,终极性本原是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二程的理学有别于宋明时期陆王之心学。
五、“理之在吾心”:南宋理学家的心灵哲学 [57]
按照传统生存论,生存乃是气的活动。人的生存乃是气的生生不息。其活动主体便是气质。故朱熹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页。人天生有性有气。天生的气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这便是气质。朱熹道:“天命之性,本未尝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王星贤点校,第64—65页。人因为禀赋的缘故,才有了圣愚之分。对于普通人来说,天生气质并不可靠。气也可能是恶的。
如何确保气质活动的可靠性与合法性呢?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想到了天理。朱熹曰:“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③朱熹:《论语集注》卷九,《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8页。万物生存,莫不有理。比如笔有笔之理。朱熹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王星贤点校,第61页。任何活动或存在离不开一个理。朱熹曰:“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3556页。理是人类生而即有的实体。这个实体之理,在人便为性。朱熹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⑥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人物之生,自然禀得天赋之理。这种自然之理便是性,理在人便转为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王星贤点校,第83页。人天生不仅有气质之躯,而且有合法之理。这个理,便是人类天然固有的本性。正是这种终极性的天理,最终决定了人类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只有符合天理的气质活动,才是合理的活动。理成为正确行为的终极性根据与决定者。
虽然朱熹强调格物穷理、追寻天理,事实上,朱熹并不否认天理内在于心中。朱熹曰:“盖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具于人心者,其体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圣愚而有加损也。然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则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动而不知所以节之,则人欲肆而达道有所不行矣。”⑧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58—559页。人天生心,不仅有情,而且有理。这个理,在人的身上便是性。这便是“心统性情”:“盖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说一个心,便教人识得个情性底总脑,教人知得个道理存着处。若先说性,却似性中别有一个心。横渠‘心统性情’语极好。”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王星贤点校,第91—92页。性是心之理。心则由两个部分构成,形而上的性和形而下的气。后者表现为情。其中,形而上之性便是理。朱熹曰:“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⑩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王星贤点校,第88页。性是心的根据,心是性的存在场所。心中有理,或者说,理在心中。因此,天理在我。朱熹曰:“天道无外,此心之理亦无外,天道无限量,此心之理亦无限量。天道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吾心。(那个不是心做?那个道理不具于心?)天下岂有性外之物而不统于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则为天地公共,不见其切于己。谓之吾心之体,则即理之在我。”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40页。此理虽然流行于天地万物之间,却同时以性的形式而内在于我心中。人天生之心固有天理,这便是“理之在吾心”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41页。。这个心中之理,在儒家看来,便是仁义之性。朱熹曰:“所以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为一身之主,浑然在中,虚灵知觉,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谓人之心。”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38—2739页。天生我心,我心不仅有气质之情,而且有形而上之性。其中的形而上之性是超越之理。心中有理,心即是理。这便是陆王心学的核心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④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9页。朱子学其实也是一种心学,和陆王之心学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或者说,以存在论的观念来看,朱子学也是一种心学:内在之理或性是宇宙生存之本。
六、理即心:陆王之心灵哲学 [58]
“理在心中”的观点,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说,意味着内含天理的人心乃是宇宙生存的终极性本原或主宰。这便是陆王心学的主张。陆王心学赞同传统理学家的观点,认为理是宇宙事物生存的决定者。陆九渊曰:“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⑤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第10页。宇宙间的理便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或主宰。这个主宰不仅是经验性主宰,更是终极性主宰。这便是“极”:“极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畴之中而曰皇极,非以其中而命之乎?……同指此理,则曰极、曰中、曰至,其实一也。”⑥陆九渊:《陆象山全集》,第19页。理是极,终极性的存在。理是天地事物生存的最终极的本原、根据或主宰。王阳明曰:“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⑦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58页。天理是万物合为一体后的生存之道,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王阳明曰:“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⑧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吴光等编校,第123页。万物生存无非天理之流行。
这个终极性、主宰性的天理,陆王心学家们果断地将其收归心中。陆九渊曰:“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⑨陆九渊:《陆象山全集》,第3页。爱之情、敬之礼、恶之事、义之宜,都源于本心或理。事物、事情之本的理存在于心中,心即理。王阳明直接将天理叫做良知:“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⑩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5页。天理即是良知。由此,事物之理便转变为心中之理。王阳明曰:“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①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吴光等编校,第2页。天理便是无私之心、公心或良知。天理在心中。天理是心。心具有两层内涵,超越之心与气质之心。其中超越之心与理同一,而气质之心内含天理。这便是陆王心学的基本观点。气质之心,在王阳明看来,由于天生禀赋的气质有清浊之异。其中,浑浊的气质妨碍了天理的澄明。在现代中,气质浑浊的普通人,其良知便被遮蔽。因此,对于这些钝根的俗人来说,纯洁气质而“致良知”便成为必需的工作。“致良知”便是变化气质的工夫。这和朱熹的“天理之昧”说与工夫论等几乎完全一致。
由此看来,狭义的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在宇宙观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在朱熹看来,天理是宇宙生存的终极性根据。这个天理不仅存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心中。我们心中也有天理,那便是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心即理。只不过朱熹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而陆王心学明确说出了这句话。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说与没说。或者说,在观念上,朱子学和阳明学并无二致。不同的仅仅是在概念使用上,朱熹并没有提出心即理的概念或说辞。王阳明曰:“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②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5页。尽管所谓的“晚年定论”不太精确,但是,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朱子理学是心学的早期形态,阳明心学则是理学的成熟形态。在心学发展进程中,朱子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阶段,他们共同将主宰宇宙的力量,由外在的天理转向内在的人心。人、人心最终成为宇宙的真正主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宋明理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天人之辨中,人类最终成为宇宙的主宰者。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理学家们也从思辨哲学的角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宇宙生存找到了终极性根据。既然心成了宇宙的主宰,那么,心自然成了这个时期理学家们最关注的概念。心学的内涵便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佛学的概念,而且也是儒学最重要的概念。由此,明代很多学者纷纷提出圣学与心学的一致性。传统儒家哲学,在心学时期达到了顶峰。
七、结语:心学史的逻辑 [59]
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过上美好而正当的生活。过上美好而正当生活的方式便是道,因此,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或哲学家都最关注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荀子提出君子“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闻道、从道是儒家的最终追求,道是正确的方法。如何践道、从道呢?朱熹曰:“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〇八,王星贤点校,第2686页。治道在于正心,心端才能够行正,心是人类正确行为的根本。
对源头的关注一直都是哲学的任务。从现有的《论语》资料来看,孔子论述心的地方并不多,但是已经有所意识。他一方面希望美好的生活能够从心所欲;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心之所想、身之所为不违背仁义。孔子希望以仁义规范心灵、以心灵主导生存。大约是从《大学》开始,心的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大学》明确提出了正心是修身、为仁的根本。心是本源。从孟子开始,儒家哲学家们开始对本源之心进行了性质分类,即,将其中的好的部分挑出来,将其命名为性。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等四心统称为性。心是性。准确地说,作为本源的心中的善良部分便是性,这便是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的产生标志着心学的转向,即,从心学转向性学。其后的荀子也以性释心。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将人天生的心中不好的部分即坏心叫做性,如好利之心便是性。这便是性恶论。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它们都是以性释心,即,用人性来解读作为生存本源的心。这种本源的追问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开始。
对心的本源性地位的确立与性质的界定,为人们理解人类生存的性质与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心的问题也因此而成为汉儒学问探究的中心之一。董仲舒吸收了先秦儒家的性善论与性恶论,相信人心不仅有善气,而且有恶质。人心是善恶混杂的气质之体。和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侧重于心的认知功能及其积极作用,并大力倡导。对有为心的过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威胁了人的自然生命体的延续与存在。魏晋玄学家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作为生命本源的自然心与作为人文活动本源的有为心之间的张力或冲突,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重自然的生物心,而轻有为心,从而将生命体的生存与思维之间的张力发展到了极致。在这种张力下,玄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型宇宙观,即天人一体观。自然人心和有为行为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本末结构,这便是玄学家的本末论。
本末论的世界观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命体。那么,谁才是这个生命体的主宰呢?这便成为宋明理学关心的问题。早期的理学家们如张载、二程延续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以为天地之心是宇宙的主宰。故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心即宇宙之心,为天地立心即主导宇宙的生存。二程虽然没有这般豪言壮语,但是,他们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二程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统一于仁。仁才是宇宙万物的基础,或者说,仁贯通万物。这种流行之仁自然有一个起点,那便是天地之心。和早期儒家不同的是,二程对天地之心进行了深化,提炼出一个新概念即天理。天地之心之中内含天理。或者说,超越的天理才是宇宙存在的终极性本原。至此,本源之心由早期的经验性本源升华为超越性本原。本源因此而分化为两类,即经验性的生存本源和思辨性的存在本原。对天理的思考即理学,其实是一种思辨的本原学或“心”学。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以为天理才是宇宙存在的终极性本原。在朱熹看来,人天生不仅禀赋气质,而且固有天理。这种天生之理,在人为性。人身中的性其实就是天理。也就是说,人生来不仅有气质,而且有性或理。由于天生禀赋气质的差异,普通人的浊气将这个天理遮蔽了。这种被遮蔽的心便是人心。人心因此不可靠。只有通过格物致知而穷物理的方式,人们才能够涤荡心中的杂质、使天理澄明、人心变为道心。这便是理学家的工夫论。理学家的工夫最终还是落实在心上,即“心中有理”。“心中有理”的实质是以超越的天理作为生存的终极性本原。尽管朱熹强调穷物理,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人心固有天理的主张。朱熹的这个思想被王阳明完全继承和发扬。王阳明将心中的天理叫做良知。良知才是宇宙生存的终极性根据。由于人的私欲遮蔽了良知,而使人气质不纯、良知不明。因此,和朱熹等人一样,王阳明也强调做工夫,主张通过工夫来变化气质,使自己气质纯净而良知澄明。良知之澄明成为做人的标准。良知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最终根据,而且是宇宙生存的终极性本原。王阳明最终将主宰宇宙生存的终极性力量交付人类自身,并从思辨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类主体性地位。从孔夫子到王阳明,从心灵哲学的角度来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发展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哲学史其实也是心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