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着慑人光芒的文学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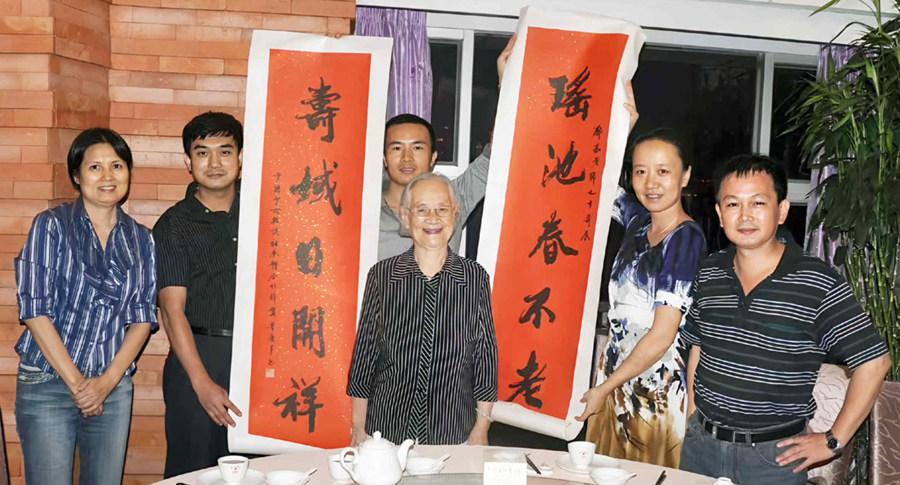
百岁女作家郁茹,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以一部《遥远的爱》惊艳中国文坛。新中国成立后,郁茹曾担任广东《南方日报》记者、编辑、文艺部副主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少男少女》杂志社总编辑等职务。数十年来,郁茹著作颇丰,其儿童文学作品《一只眼睛的风波》和《西湖,你可曾记得我》曾先后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
郁茹的创作经历,可分为三个创作丰收期。
第一个创作丰收期:
《遥远的爱》《龙头山下》
1944年出版的小说《遥远的爱》是郁茹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之作。《遥远的爱》出版,开启了郁茹第一个创作丰收期。
在写《遥远的爱》时,郁茹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春少女。她在重庆曾沐茅盾、叶以群恩泽,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协助茅盾编《文艺阵地》,并在叶以群的鼓励下写了这部小说。而书名《遥远的爱》和笔名“郁茹”,则是茅盾为她起的。
郁茹在《遥远的爱》中,以温婉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受过现代民主与革命洗礼的女性知识分子罗维娜,从追求女性解放和自由,到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爱情与民族解放大业之间艰难地抉择,最终成长为革命新女性的过程。
“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新型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从而表现出小说在思想认识方面的慑人的光芒。”【1】这是茅盾先生对郁茹《遥远的爱》的一段评价。
新中国成立前,郁茹还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龙头山下》。
第二个创作丰收期:
《一只眼睛的风波》《曾大惠和周小荔》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关部门多次听取了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并要求各部门尽快做好这项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制定了抓好儿童文学创作的具体规划,敦促各地作协分会切实执行。党和国家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视,激发了各地作家的创作热情。作协广东分会也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力量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去。不但有儿童文学作家努力创作,而且不少成人文学作家,如欧阳山、秦牧等,也纷纷“跨界”参与儿童文学创作。
一直童心未泯,深爱孩子的郁茹,也积极为孩子写作。这其间,她创作了儿童小说《一只眼睛的风波》《曾大惠和周小荔》等作品,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其中,《一只眼睛的风波》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三等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儿童的苦难生活和少年儿童参与革命斗争的题材;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反映孩子们在校园内外的生活题材。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儿童小说,主要是反映孩子们在党和国家的关爱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美好生活。特别是在同期的不少作品中,都凸显了爱党、爱国的主题,并大力宣扬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歌颂校园内外的好人好事。
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这时期一些儿童小说的矛盾冲突构建,以及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往往都是围绕着两种形成强烈反差的类型形象——“先进”与“落后”,或“有缺点”与“没缺点”来设计。在这些小说中,那些先进的好孩子、好学生,失去了本来应该具备的朝气蓬勃、调皮可爱的个性,变成了一个个循规蹈矩、暮气沉沉,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小大人”。
郁茹在这时期的创作却似乎有点另类,甚至与“小大人”的套路反其道而行之。她笔下的儿童形象,个个天真可爱、生动活泼、灵动跳脱。无论是“先进”孩子,还是所谓的“落后”孩子,儿童的天性在他们身上,都得以充分地释放。可以说,与许多同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相比,郁茹的创作更为细腻,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生动。
在《一只眼睛的风波》中,因为乙班的纪律和成绩跟不上,学校要求从甲班调4位先进同学去乙班,成为乙班同学的好榜样和老师的好助手,帮助老师建立良好的课堂秩序。于是,甲班的郑老师挑选了陈国荣等4位同学去乙班。而能被选中的,无疑是老师和同学都公认的先进同学。
作为先进同学的陈国荣,第一天在乙班上课时,就挨了“后进同学”金朝光三次拳头戳。陈国荣向老师打小报告,还想到了报复。但是,当课堂上金朝光背不出课文向他求助时,陈国荣仍忍不住偷偷给了金朝光提示。课后,陈国荣成了金朝光的玩伴,一起踢足球,偷看杂技团排练,还一起用弹弓打鸟。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先进学生陈国荣,忘记了自己来乙班的任务,不知不觉脱离了四人“帮扶”小组。“他(金朝光)总能想出许多玩的花样来,每一次都使陈国荣大开眼界,所以,陈国荣就死心塌地的和他交上朋友,宁愿听他的指挥。”【2】
结果,陈国荣玩弹弓失手,射伤了女同学的眼睛。他追悔莫及,主动承认自己是肇事者。最后,还是金朝光出的主意,两人在课后努力去捡废铁卖钱,给沈凤娟交住院费……
在小说中,“先进”同学身上有不少缺点,甚至还闯了大祸。而所谓的“落后”同学,顽劣中却充满善良和智慧。无论是“先进”同学,还是“落后”同学,他们身上都会存在淘气、贪玩、好奇心极重等“毛病”。其实,这些“毛病”都只是儿童天性的真实表现,无关“先进”与“落后”。
《一只眼睛的风波》正是通过对儿童天性的自然表达,让小说变得真实、自然、灵动,相信不少孩子读后都会感同身受,产生共鸣。
最好的教育是人的自我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是为了引导孩子进行自我教育。让孩子从认识自我开始,到打通与他人、以及打通与社会的联系路径,让成長成为一段激发好奇心,完善人格,养成自主能力的内心旅程。所以,保护孩子的天性非常重要。
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郑老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教师,面对犯下大错的陈国荣和“落后学生”金朝光,她表面上是严厉的,却没有喋喋不休的说教批评,也没有简单粗暴的责罚,而是始终尽自己的绵力保护着孩子的天性,理解、尊重并信赖他们。
而这也是作家郁茹的苦心,她冀图通过文学的力量,让孩子的天性得以继续向善、向上发展。这是《一只眼睛的风波》区别于那个时代的“小大人”文学的成功之处,也是作家郁茹的成功之处。
年龄越小的儿童,心理和生理特点也越明显,他们观察事情的角度和考虑问题的方式也越特殊。所以,刻画他们的形象也越困难。熟谙儿童心理的郁茹,善于用情节和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把他们的内心活动也剖析得很到位,使儿童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小读者面前。
在中篇小说《曾大惠和周小荔》中,同学们要和海军叔叔联欢,大家都交出了准备送给海军叔叔的礼物。当梁老师问到“熊孩子”曾大惠准备送什么礼物时,曾大惠说:“老师,来,你爬上树,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梁老师果真千难万险地“和曾大惠一起爬到了大榕树最高的一个丫叉上了,曾大惠亮闪闪的眼睛望着自己的级任老师,他觉得老师很勇敢,居然肯和自己一起爬树,简直像好朋友一样”。【3】于是,曾大惠终于向赢得了自己尊重和信任的好朋友梁老师敞开心扉,拿出了藏在一个高高的树洞里的秘密:一份“争取下学期每周有四个一百分”的决心书。
作家的笔触下,充溢着浓厚的儿童生活情趣,把一个憨厚可爱的小顽童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语言质朴、清新、自然,极少藻饰,也是这时期郁茹儿童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
为救人受了伤而住在医院里的曾大惠,吃着同学周小荔妈妈给的梨子时,想起了自己去世多年的妈妈,不知不觉在病床上抽噎起来,眼泪都掉在枕头上了……周小荔知道曾大惠一直想当解放军,就大声地说:
“‘解放军叔叔从来就不哭!
曾大惠羞得不得了,他急忙扯起白被单,把脸蒙上,就在被单下面大声嚷了起來:
‘我才不哭,我当然没有哭!”【4】
只是寥寥几笔,一个纯真烂漫的孩子形象,便跃然纸上,让人久久回味。
第三个创作丰收期:
《西湖,你可曾记得我》《小猴王大摆泥巴阵》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作家思想解放,创作欲望井喷式爆发。年近六十岁的郁茹重新焕发青春,活跃于儿童文苑,创作再获丰收。在1979—1984年间,郁茹创作了自传体儿童小说《西湖,你可曾记得我》、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小猴王大摆泥巴阵》等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西湖,你可曾记得我》曾获全国儿童文学奖。
《西湖,你可曾记得我》是作家的童年记忆,郁茹以孩子的触角探视人生的悲欢离合、人间百态。她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悲惨的童年:在除夕的爆竹声中,父亲突发疾病,来不及请医生,便匆匆离开了人世,“我”—一个从小对知识有兴趣的小女孩,过早地被打入生活的漩涡,辍学去当了学徒。在西湖边上的照相馆,小女孩饱受生活的摧残,处处遭打压,一个老妈子该干的活小女孩都要干……
或者可以说,苦难是一笔财富,但童年生活给作家带来的并不只是苦难的回忆,更是应对艰难苦困的精神守望,也自然彰显了作家的生命意识和童年情愫。
面对苦难,主人公没有沉沦,她不断地抗争,虽然历经种种坎坷,却从未缺少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温暖的赞美。
在杭州西湖边上有名的扇子庄当画师,并教会小女孩画画的大伯;思想进步,不断为小妹拨开人生迷雾的大哥;破格把连小学也没念过的小女孩录入艺校的慈爱善良的老校长,他们让主人公在艰难困苦中,在求生的挣扎中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和前路的光明,让她得以畅快地读书、写作、玩耍,生命得到滋养而舒展。
郁茹在《西湖,你可曾记得我》中始终保持着对西湖文化血脉的承袭和尊重,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执着。作家将这种记忆与回望放置在故事中,营造了一个蕴含着西湖文化气息的成长故事。在她对现实鞭辟入里的童年记忆描写中,时常会有大自然的种种物象以及乡间民风民情穿梭其中——故乡山上的野菊花,过年时的红春联和红灯笼,胡同转角处的路灯……以及乡人为求大伯一幅荷花画作,偷了小女孩最爱的那棵“玉圭金钩”,最后乡人被大伯勒令必须用大红花轿将“玉圭金钩”抬着送回小女孩手里……这些自然景致、乡间轶事,为原来苦涩、灰暗的童年回忆,增添了明亮的色彩和成长的喜感。
童年记忆不仅仅只是童真童趣,《西湖,你可曾记得我》还承载着作家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郁茹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抒写青春,描绘成长,展现了少年人在成长中遭遇挫折和困惑,在不屈的抗争中从青葱走向成熟的生命历程。
小女孩虽然历经坎坷,却在语文老师、大表姐的家教及大哥等人的指引下,不懈探索追求。她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甚至成功驱赶了骚扰女同学的国民党教官。最后,老校长在被国民党特务带走前,把船票、路费、行李都交给她,让小女孩找到共产党的联络点,在茫茫大海中漂流的小舟终于汇入了革命的洪流。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小猴王大摆泥巴阵》,则是郁茹在这时期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出现了转变、进步。更加明确树立了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主体”的创作理念,作品更加贴近儿童,走向儿童,注重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和人文担当。
《小猴王大摆泥巴阵》仍延续了郁茹原有的创作特色,作者从学校和家庭平凡生活中取材,以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突破中国儿童文学的种种禁区,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如人意,甚至丑恶的现象进行披露和鞭挞的同时,也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小猴王”周绰等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及其充满乐趣的童真世界。
小说的背景是“十年动乱”期间,小猴王是个淘气却又极聪明的孩子,在“四人帮”宣扬的“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思想毒害下,他无心向学,经常用泥巴袭击同学,扰乱课堂秩序。
郁茹通过木偶剧《我要读书》的三次演出来架构情节:
第一次演出,班主任谢老师顶住重重压力,启发同学们组成兴趣小组,学习用泥巴制作小木偶,演出木偶剧《我要读书》。班里的同学为了让小猴王好好念书,把《我要读书》中的高玉宝形象塑成小猴王的模样。小猴王因此产生误会而怨怒,在演出时,将大把大把的泥巴扔上舞台……
谢老师说服同学们,平息了同学间的矛盾,并想办法吸引小猴王等调皮同学参加到木偶剧的演出活动中,让小猴王得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可被老师有意安排饰演高玉宝的小猴王竟擅自改动剧本,认为读书不如拳头有用,在舞台上演群殴地主周扒皮……第二次演出也失败了。
在同学们纷纷批评小猴王时,小猴王遇上因父母被“造反派”抓走,有家不能回,有书不能读,在社会流浪,甚至被威胁当小偷的同学罗岗。面对这个现实中的“高玉宝”,小猴王明白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靠拳头是不行的,”“还是叫他回到学校,我……不,我们一起帮助他!我保证他,不,我保证自己和他,都、都会学好的!”【5】
第三次木偶剧《我要读书》演出大获成功,“于是小猴王就和高玉宝一起,单独给观众又谢了一次幕。观众这才发现,这个木偶和周绰长得一模一样,就像一对小哥儿俩……”【6】
这个细节让人忍俊不禁,也隐喻着小猴王未来的成长路径:热爱学习的孩子,无论他以后的际遇如何,也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是一个有出色、有作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可是,就在小猴王爱上学习,走上正途时,热爱孩子、热心教育事业的谢老师,却被扣上毒害孩子的罪名。这天晚上,谢老师被软禁在办公室里——
“忽然,她听见有连续敲玻璃窗的声音,就好像有个苍蝇或什么虫子撞在玻璃上一样。她抬头一看,只见在桌前那盏灯的映照下,玻璃窗外出现了小木偶高玉宝,是它在用小手敲玻璃,并且向谢老师举手行了个礼。
‘这是在做梦?谢老师揉揉眼睛再看窗子,玻璃外边当真有一个小木偶,它在向她点头、招手……它的手里捧着那本小书,向她扬了扬,随即就做了个认真读书的动作……
谢老师明白了。这是小猴王利用小木偶在向她表示要好好学习的决心。”【7】
《小猴王大摆泥巴阵》虽然时时不忘将社会和时代的影子投射到童真世界,但是真正唤起小读者审美感应的,仍然是那一尘不染的童稚的纯真。无论是小猴王扔泥巴上舞台,还是冒着危险用泥偶偷偷向自己敬爱的老师表达情怀,表现的都是儿童的真实生活、真实情感和想法,完完全全反映了儿童的世界,极富童趣。
郁茹应该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有明确“为儿童创作”动机的作家。但从写出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她便将全副身心投入到为孩子写作上。在这里,郁茹有一种自发的,甚至是本能的主动倾向——并不是儿童题材不期而然地撞到她的笔底来,而是她的灵魂与儿童,与儿童文学之间那种神奇的吸引力,使她必然投身到这个美妙的文学领域。
郁茹曾经说过:“我之所以要给孩子写东西,是因为我爱孩子。我的童年、少年是非常不幸的,完全没有孩童生活的乐趣。解放后,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先烈已经为孩子敞开了进入幸福生活的大门,那么,我们应该为孩子们认真描绘一下他们光辉、灿烂的未来,让他们成为有理想的人。”于是,“我开始为孩子写起东西来。在写作中,我自己感到无比幸福、无比满足。我笔下是一个明朗、美好的世界,我们新的一代在这里成长。”【8】
郁茹充溢着童心童趣的儿童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主体”的创作理念。热爱孩子,是郁茹文学之旅中最重要的特征。她对孩子的爱,甚至超出了母爱,她似乎与儿童有一种天然的投缘。而正是这种儿童般的天性,让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种强大的亲和力,并成为一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经典。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闲话·闲画》《少男少女》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广东省作家协会开会传达有关指示,对主持人长篇大论的报告,谁也没有真正感兴趣。会场上的郁茹觉得无聊,随便扯过一份报纸来,漫不经心地在那些空白处乱画,“画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折枝梅花。我旁边坐的是秦牧,他也没有认真听讲话,倒是对我画的东西看得津津有味。将要散会时,他拿过我的钢笔,在那张报纸上写了一首诗,好像也是歌颂梅花的,最后两句是:‘相识郁茹数十载,不知作家是画家!我们两人相视而笑……”【9】
郁茹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但她最早接触的艺术其实是国画。郁茹的大伯是个画师,有自己的画室。早在年纪很小的时候,郁茹就跟着大伯学画。少女年代,还在艺校就读过一段时间。后来当了作家,郁茹仍是一手鋼笔,一手画笔。
从小到老,梅花和荷花是郁茹画笔下的至爱。特别是以荷花为主体,表达自己心境的画作较多。她说:“故乡的荷塘,是我童年时代的栖息点,那片无穷无尽的浓绿和清香,在我童年时悄悄地用只有我才能听懂的语言,造成我与它们相通的个性,一种自强不息,努力创造条件改造自己命运、前途的能量就会油然而生……”【10】
郁茹的梅花和荷花画作经常出现在各种画展上,在87岁时,她还出版了一本画册《闲话·闲画》。
创作高产的郁茹一直热心扶掖后辈。20世纪70年代,郁茹亲自发掘并组织了一批工人文学爱好者,成立了广州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小组,并给予这些来自工厂、车间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文学爱好者热情细致的指导和扶持。后来,从这批作者中,走出了李科烈、谢继贤、戴胜德、黄令华、廖致楷、李彦雄、肖敏刚、李国伟等一批作家。
不得不提的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精神粮食,1983年,已经年过六十岁的郁茹和黄庆云一道,创办了《少年文艺报》;数年后,又创办了《少男少女》杂志。《少男少女》杂志后来不但连续三年获国家期刊奖,成为全国名刊,还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特别是1985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关夕芝,还有刚刚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胡永红,都曾在《少男少女》杂志担任过编辑。
郁茹的《遥远的爱》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杨沬的《青春之歌》至今仍并列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经典佳作。而先后获全国儿童文学奖的《一只眼睛的风波》《西湖,你可记得我》等也成为新中国儿童文学标志性的优秀作品。郁茹的作品,无论是女性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闪烁着慑人的光芒。
百岁作家郁茹不但赢得了文学艺术界同仁的拥戴和敬重,而且也是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快乐之源,更是整个文学艺术界的宝贵财富。其文品与人品,堪称文学界楷模!
注释:
[1]《茅盾文集》第10卷《关于遥远的爱》;[2]郁茹:《一只眼睛的风波》,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郁茹:《曾大惠和周小荔》,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郁茹:《曾大惠和周小荔》,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5]郁茹:《小猴王大摆泥巴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6]郁茹:《小猴王大摆泥巴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7]郁茹:《小猴王大摆泥巴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郁茹作品选》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10]郁茹:《闲话·闲画》,2008年;《少男少女》杂志社。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