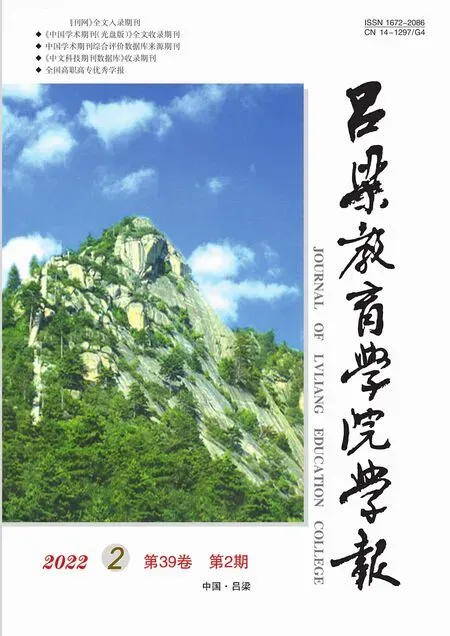《呼啸山庄》的悲剧性分析
薛文梅
(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3000)
作为英国文坛传奇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自小就有着异于常人的性格和思维模式,这种异于常人在夏洛蒂口中体现为,她们在小时候躲在家里玩耍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诗就有着特殊的风格,她总能把纯净美好的东西笼罩一层恶的纱幔。她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是潜藏着一种自我对于善恶的困惑与不安。在现实当中,女子受到社会现实的束缚,不能酣畅淋漓的表达自我,因此艾米丽用《呼啸山庄》这样一部作品,虚幻的构建了自己内心当中的善恶世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的实质是伦理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从这一理论来看,《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正是解构了作者艾米莉·勃朗特的自我伦理观念的分裂与冲突,最终通过作品的虚幻和解,实现了作者自我的情感释然。
一、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一)希斯克利夫
在《呼啸山庄》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初读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他不仅残忍无情,破坏他人的人生,摧毁美好的情感,更连社会的法治也不放在眼里[1]。然而不同于一些小说中对恶人的刻画那样彻头彻尾,正当读者将要把所有怒火和愤懑都发泄在这个反派人物身上,给他冠以“冷血无情”的标志时,作者却通过全书中最温暖的场景描写了希斯克利夫内心的柔软。“希斯克利夫朝窗外探出身去,哀求卡瑟琳的鬼魂进来。”这让读者迸发了一丝探究的欲望,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希斯克利夫的冷血无情,又是什么让他在冷血无情的躯壳下还能潜藏着一颗至死不渝的逐爱之心。作者在希斯克利夫身上所体现的悲剧性是从出身便给予了卑微的社会地位,幼年时作为孤儿流落在利物浦的街头,看尽了人情冷暖,饱受风餐露宿之苦。有幸能够被老欧肖先生带回呼啸山庄,却仍然体会不到除了老欧肖先生和卡瑟琳之外其他人的公平对待。老欧肖先生去世之后,唯一寄托真情的卡瑟琳也选择了背弃他的情感,与他人成婚。他被迫离开了山庄。然而,这样的他,穿着光鲜,成为了体面的绅士再次回到呼啸山庄,展开报复的直接目的却不是为了得到幸福的人生,扭转可悲的境遇,而是以牺牲自我、迫害他人、践踏婚姻、无视法律来实现了自己对于不可能得到的爱情的执拗。穷尽所有,蓄谋已久的报复和执拗着的爱情,他最终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正如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所谈到的,家庭环境对于人幼年的影响极为巨大,而希斯克利夫在幼年时期经历的悲惨生活本就给他留下了社会冷酷无情的印象,到了呼啸山庄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现实不断让他巩固了这种冰冷的认知。这造就了他用更加冷酷无情的方式回报曾经令他不堪的过往。而作为黑格尔所分析的悲剧的对立面关系,希斯克利夫这种种的做法似乎又是能够被理解的,他的确有报复和痛恨的理由。他唯有坚持自己这种错误的认知,一直用近乎残忍的方式来报复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这就成为了他悲剧人生顺势发展的路径。归根结底,希斯克利夫的悲剧性人生源自于社会对弱势儿童的残害,让他们丧失了感知、判断、理解和接受的能力,而唯一让他寄以希望的情感一旦被打破,这种无度的报复就体现为人性的扭曲[2]。
(二) 卡瑟琳·欧肖
卡瑟琳·欧肖在《呼啸山庄》这部作品中只存活了一半,后半段她早已不在人世。但不得不说,她是这部小说不折不扣的女主人公,她的存在既有着自己的悲剧性,同时也成为了促成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悲剧人生的主要诱因。作者在塑造卡瑟琳·欧肖这个人物时,把她定位为一个思想激烈交锋的复杂型人格。在她人面前,她不仅是温柔可人的,有时也透露着一股暴戾和狂躁。她有时温文尔雅,气质不凡,有时却不拘小节,洒脱率真。从社会现实来说,她作为呼啸山庄的小姐,应该与同社会阶级的人一样颐指气使的冷眼对待希斯克利夫,甚至是瞧不起这个黑小子。但是她并没有,反而与希斯克利夫萌生了情感,产生了爱意。从情感角度来讲,她既然与希斯克利夫产生了情愫,也深知自己不爱林顿,却因为内心资产阶级对金钱的渴望,惦记着林顿家族的画眉庄园。最终卡瑟琳·欧肖选择了嫁给林顿。但是当多年以后,她与希斯克利夫再次在荒原上碰面的时候,她真正认识到她的灵魂和爱永远是与希斯克利夫合二为一的,也在内心当中承认了自己是为了得到画眉庄园的上流生活而背弃了希斯克利夫。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看,在卡瑟琳·欧肖的内心当中,始终有着对立面之间的博弈,她深知自己对画眉庄园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也承认自己不爱林顿。但她在生活与爱情之间,选择了生活。这就注定了她在情感上是悲剧性的,她以牺牲情感作为了换取生活品质的筹码。当多年以后,她与旧爱重逢,才发现原来爱情远远比生活的品质要可贵。卡瑟琳·欧肖的悲剧性源自于出身于即将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但自带有资产阶级的优越感,深知自己的情感归属,却又无法在情感与生活品质之间做出真正听从内心的取舍。
二、作者本身的个人悲剧性
艾米莉·勃朗特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悲剧性人生的作家,她自小生长在英国的一个荒原之上,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并且是激进的保守党人,受到父亲的影响,艾米莉·勃朗特对书籍有着高度的热爱,这为她后来创作《呼啸山庄》奠定了文学基础。然而,她的童年处在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生产力的急剧变化时期,社会生活对于金钱的需要越来越大,而她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后,家中的收入一度非常紧张。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学创作只有大姐的《简·爱》取得了比较大的轰动,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呼啸山庄》却甚少有人关注,甚至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令人感受到恐怖和毛骨悚然的。在作品不被理解,唯一的兄弟也因为酗酒、吸毒得病致死的双重打击下,艾米莉·勃朗特身体越来越差,在年仅三十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直到她离世之后,这部《呼啸山庄》才引起了文坛的巨大关注和追捧,甚至评价这本书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小说”。虽然在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恋爱的经历几乎是空白的,但她却能够写下《呼啸山庄》这样充满情感纠葛的作品,可见艾米莉·勃朗特虽然不善言语,但她的内心其实是充满勇气并渴望探索世界的。她的作品当中浓缩了当时社会的人性缩影,从近乎极端的反面形象塑造和凌厉、独特的描写手法,能够看到她对人类善与恶、好与坏、对与错之间的思想探索,她也穷尽心力去探索如何让人类的恶获得救赎,如何正面面对内心当中的丑陋面与对立面。她塑造人物的方法,是通过自我剥离、自我分裂、自我对立来实现的,最终达到对人性完整自我的探索和重塑。回看这位天才作家的一生,短促而平淡,既没有在生前享受盛赞,更没有在身后被发掘出更多的作品,这部《呼啸山庄》成为她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作品。而她在写下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究竟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情感挣扎也无人知晓。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认为在自然的冲突、人与外界的冲突、心灵的自我冲突这三种冲突中,心灵的自我冲突是最高冲突。而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是在这强大的心灵的自我冲突中渡过的,正是这样才能在没有任何外界经历的情况下,用如此独特的笔触撰写出这样一部奇书。
三、社会现实的悲剧性
《呼啸山庄》以文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呼啸山庄”为题,本身就具有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隐喻。“呼啸”表面上看是指山庄在经历风雨的洗礼和侵袭,实际上暗指了社会在工业革命前期发生的观念动荡。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英国社会开始崇尚金钱至上的理念,在金钱面前,人情变得凉薄和寡淡。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也简单粗暴的以阶级、种族和身份地位、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正如作者在小说中的塑造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他的出身就注定了在社会最底层,从小还缺乏家庭的关爱,幼年就因此饱受了社会的欺凌和冷酷。在畸形的社会观念下,没有人会同情这样社会底层的孩子,更不会有人给予他爱护。即便到了呼啸山庄之后,周遭人的白眼和冷漠、欺侮,都让希斯克利夫的内心不断扭曲。当唯一寄托情感的卡瑟琳·欧肖也选择背弃他之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怪人。小说中能体现悲剧社会根源的另一个点在于,本来饱受资产阶级欺凌压榨的底层人民,妄图通过赚取大量的财富来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并变成资产阶级的身份来报复曾经给予他伤害的人,用娶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来报复自己爱的人。这种病态的报复,在希斯克利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提出:“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而在希斯克利夫身上发生的一连串的暴力、冷漠、残忍的报复行为,都是这部《呼啸山庄》悲剧冲突的一部分,而推动这个悲剧冲突出现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残忍的社会、冷漠的人情对希斯克利夫造成的连续性打击和伤害,这些打击和伤害促成了希斯克利夫人格的扭曲变态,他的本体已经无法判断对错,内心也早已无力感知情感,只是一味的想要变成伤害自己的人的模样,用同样的方式实现对对方的报复,从而达到黑格尔所强调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片面的伦理实体的交锋。”[3]《呼啸山庄》的结局让女主人公在死后灵魂回归荒原,最终结成伴侣,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行为意识群体之间无法真正在社会实体环境中无矛盾的相处,只能寄希望于一种虚无的幻境,通过灵魂的交融来实现对无法突破的矛盾进行化解。最终达到了黑格尔悲剧理论对于悲剧结局的描述——“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同时让“心灵的自我冲突”归于宁静。
四、“爱”与“恨”的悲剧性
艾米莉·勃朗特著作的这部《呼啸山庄》问世之后,并没有马上获得热烈、正面的社会反响,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讨论和激烈的思想碰撞之后,才有了后来的文学地位。许多人认为,艾米莉·勃朗特对于爱情的描写有悖于以往人们对于爱情的认知,这里的爱情似乎与美好的憧憬与和谐的画面都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用近乎暴力和凶残的方式,给报复找了一个借口。而实际上,这正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她用极致的“恨”来表达极端的“爱”,也许这种“爱”并不是为世人所容纳和称颂的,但却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纯粹。小说中,希斯克利夫虽然从小就经历着社会冷酷的洗礼,甚至连老欧肖先生对他的收养也是出于对上一任佣人的替换目的,他在山庄受尽了周遭的冷言冷语、歧视侮辱。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隐忍、退让,并感恩于老欧肖,钟情于卡瑟琳·欧肖。致使他完全扭曲了内心的导火索还是卡瑟琳·欧肖的背叛。这里强调了“爱”带给他最深的伤害,也突出了这部作品的一大悲剧性,就是“因爱生恨”。结合小说的后续剧情能够看到,无论如何“恨”,希斯克利夫都从未对卡瑟琳·欧肖本人造成过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尽管在他的报复之下,卡瑟琳·欧肖的生活处境也不断的遭到破坏。这里体现出的还是他对本心当中“爱”的坚守与执着。希斯克利夫在返回呼啸山庄展开报复的过程中,有一句常说的话:“我,没有怜悯。”这是他对自己报复形象的树立,更是对自己时时刻刻的提醒,作者透过这句话希望读者感受到的,除了对希斯克利夫的冷酷形象加深印象之外,更饱含着对这个分裂了自我以追求爱的极致之人的怜悯。对于在书的前半部分就已然离世的女主人公卡瑟琳·欧肖,作者用一个她离世前留下的孩子作为替代她出场的影子,这个影子在今后的数年里一直陪伴并温暖着希斯克利夫。在希斯克利夫将“恨”转嫁到大仇人亨德雷的下一代身上时,他认为哈里顿就是亨德雷的替身。可悲的是,这两个替身相爱了。此时的希斯克利夫为了成全小卡瑟琳,放弃了复仇,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实际上对这两个替身相爱的成全,既是对卡瑟琳·欧肖爱的延续,更是“爱”与“恨”之间的和解。如果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解释这部小说中“爱”与“恨”的对立与和解,能够看到,矛盾的不断触发源自于“爱”与“恨”的不断交锋,这不仅体现在主人公的外在行动上,更体现在他的内心与思维上,通过不断暴力的报复和冷血无情的言语,“恨”得到了交锋中的暂时性胜利,但最终却因为“爱”,放弃了自己的“恨”[4]。这恰恰突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对于“爱恨”的认知,她让人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解构自我,摧毁对立面,重构自我。最终,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也推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恨,读者也领略到了一次内心的起伏跌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