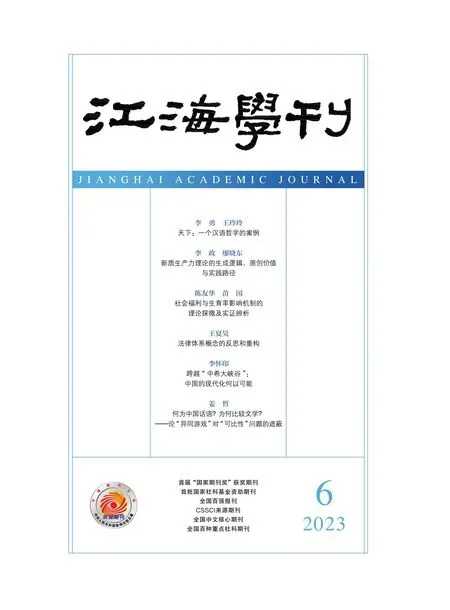学习:先秦儒家的核心属性
曲柄睿
考察先秦历史,可以发现儒家主要的代表人物都特别重视学习的意义。无论是《论语》中孔子反复提及的“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卷二《为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35、5348页。还是《荀子》中君子所倡导的“学不可以已”,(2)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一《劝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都指向了学习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的重要意义。倘若排除古今共通的对学习行为的常识性理解,而从上古中国政治理论的角度探讨其内涵,又能够发见学习的另一种面向。
《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3)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8页。阎步克据此指出,儒家传承礼乐诗书,教育学子的职业特征,有别于诸子。(4)阎步克:《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孔子序《书传》、言《礼记》、删定《诗经》、习乐与《易》,显示出儒家在整理文献并以之作为教材广泛传播方面有相当的专长。(5)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5—1937页。侧重知识传承,因而提倡学习,自然是儒家学术传统中的天然需要。
先秦儒家更提倡通过学习而达到“圣”的境界。王博在研究《荀子·劝学篇》后提出,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的荀子学说,倡导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掌握“化性而起伪的能力”。与认同人性本善故而提倡“思以致圣”的孟子不同,荀子提倡“学以致圣”。王博所说的“致圣”,指的是“通过学,通过虚一而静的心来了解作为生命之衡的道,进而由此道来规范自己的自然生命”。(6)王博:《论〈劝学篇〉在〈荀子〉及儒家中的意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由此能看出,儒家倡导之“学”,绝非停留在知识获取层面。同样可以讨论的是,葛兆光从玄学兴起的角度判断,儒学缺乏对生命本体的追问。(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倘若将“学”的意涵重新发掘,则这种论断似乎也并非完全可靠;进而可以指出的是,当下对于早期儒学的某些理解尚有深入研讨的空间。
好学之风:先秦儒家的重学主张
先秦儒家有门派之别,诸子之间互相辩难的情形很常见。然而现存儒家各分支经典中存在大量提倡学习的文字,表明他们即便在参与政治的手段上或许有所区别,但是对知识的尊重则是共识。翻阅儒家各种典籍,“劝学”“博学”字样屡屡出现。提倡博学,追求实现知识上的渊博,是先秦儒家思考宇宙论和人性论的基点。不满足这个前提,则儒家的种种政治主张都无法展开。如此重视学习,在其他诸子那里很难找到近似的情况。因此,思考学习在儒家学说中的意义和地位,是考察先秦政治理论诸多面向的一个有益切入。
观察文献内部篇目结构,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先秦两汉儒家典籍中,“劝学”之类篇目往往摆在首篇或靠前的位置。《论语》开篇《学而》;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以《学行》为首篇;《荀子》将《劝学》置于第一篇的位置,这种情况与其他诸子学说不同。余嘉锡揭橥古书形成与结集情形,提示:“诸子之文,成于手著者,往往一意相成,自具首尾,文成之后,或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至于门弟子纂辑问答之书,则其纪载,虽或以类相从,而先后初无次第。”(8)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1—212页。按此说,扬雄将《学行》设定为首篇,是有意识的撰述工作;《论语》和《荀子》都经历了后人整理,属于纂辑之书,(9)邢昺疏称:“当弟子论撰之时,以‘论语’为此书之大名,‘学而’以下为当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或亦以类相从。”(《论语注疏》卷一《学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35页)刘向称:“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7页)两书以劝学开篇,并非率尔之作。
先来看整理《荀子》的刘向所处的社会环境。汉武帝以后经学大盛,汉代史料中所谓的“好学”,往往和儒生、经学相联系。《史记·贾谊传》称谊孙贾嘉,(10)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503页。《儒林列传》称魏文侯、申公弟子皆好学,(11)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6、3122页。说的是他们爱好经典。《汉书》中的“好学”字样明显多于《史记》,书中所载好学人物,更直接与儒生相联系,如郑弘、郑昌兄弟,龚胜、龚舍两友好学明经,更有疏广、王吉、鲍宣、韦玄成、夏侯胜、萧望之等辈,皆为当世名儒。(12)具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诸人本传,第2902、3080、3039、3058、3086、3108、3155、3271页。《史记》《汉书》所载“好学”之人多寡不同,与两书成书时代社会风气差异有关。《史记》作于黄老大兴之时,《汉书》则作于儒学兴旺之际。黄老并不以好学作为成就的法门,而儒家将学问看作立身的根本。一方面是在汉初黄老风气流行之际,儒生在政治上没有特别的地位,故而能为司马迁所记载者少;另一方面是在汉武帝以后,不明经则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以班固所记儒生尤多。(13)胡宝国揭示《史记》《汉书》成书环境与文化上战国时代的结束有关,参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再看刘向本人的学术经历。刘向少好文辞,后转习《穀梁春秋》,完成了从文学家向经学家的身份转换;其三子皆好学,已经是纯粹的儒家弟子了。(14)班固:《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28—1929、1966页。士人由好文辞转向好经典,由文学家转向经学家,是汉代中后期常见的现象。否则,在政治上无法取得发言权。刘向身处经学大兴的时代,加之经历了学术上的转换,推崇“好学”“劝学”,是可以理解的。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刘向本人的身份转化经历,才使得他对“好学”有着独到深刻的体会。
刘向的学术编纂工作更具有参考价值。他“采传记行事”编订的《说苑》明确反映出刘向的价值判断。(15)刘向编订《说苑》事,见班固:《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57—1958页。此书以类相从,有强烈的儒家色彩。(16)参见曲柄睿:《刘向、扬雄对〈汉书〉合传的影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刊。书中涉及的儒家基本美德都无法形成具体的讨论,只能以各种例证敷衍而成,但是论说学习的例证却非常集中,主题极其明确。从内容上看,学习与仁孝并列,构成儒家基本价值观念。据此,刘向重视学习的倾向明确,也可以推知刘向以前的早期儒家把学习视为基本的美德。
进而看《论语》的篇次排列。诚如前贤所论,篇章内部以类相从,而篇第之间的关联似乎不太紧密。不过,现在的《论语》篇第次序的确定与西汉张禹关系密切。《隋书·经籍志》记载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17)魏徵:《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9页。当然也不能排除《学而》作为《论语》第一篇,是更早期汉人主张的影响。即便不考虑今传鲁《论语》定本受到汉代学术环境的影响,只从《论语》内部的记载考虑,“好学”也适宜被置于首要位置。
《论语·雍也》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18)《论语注疏》卷六《雍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81页。此论让人深感费解。孔门弟子中对后代学问传承贡献最大者是子夏,诸经皆由子夏所传,此事已经多位学者申明,无需多言。(19)皮锡瑞:《经学历史》二《经学流传时代》,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页。按:颜回生于前521年,卒于前481年;鲁哀公卒于前468年。哀公发问时可能距颜回身故不远,孔子作此悲鸣。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生于前507年,卒于前420年,乃孔门后起之秀。或许哀公问孔子时,子夏尚未脱颖而出。不过,即便是与颜回同时代的子贡(前520—前456),长期陪伴孔子左右切磋琢磨,至有人以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尚未被孔子判定为“好学”,可见“好学”在孔子那里并非取决于学习的内容,而是在于学习的效果。颜回凭借“不迁怒,不贰过”获得肯定,证明孔门弟子孜孜以求的乃是通过学获得高层次思考方式提升人生境界。皇侃说:“好学庶几旷世唯一,此士难重得”,(20)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卷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6页。应该不是一句空话。
此外可作旁证的是,学者整理先秦“书”类文献得到经验:类似文本经过了人为的编次,可以提炼出的原则是以人物为中心或以类相从,等等。(21)程浩:《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82—284页。言语类的“书”与《论语》可以看作是同类的文献,前者的编次既然能明显看出某种归纳和排序的倾向,后者的编次不可能完全如余嘉锡所说“先后初无次第”。皇侃说《论语》以《学而》最先的缘由,是“降圣以下皆须学成”,于是“此书既编该众典,以教一切,故以《学而》为先”。(22)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卷一,第1页。这个意见虽然是后见之明,但未必没有触及早期历史和文献编纂的某些真实。
基于以上各种考虑,《论语》以《学而》开篇,应是先秦至汉代经传整理者的共识;《荀子》以《劝学》开篇,反映了学者重视学习的理念性认识。(23)《大戴礼记》亦有《劝学》篇目,排序并不在首篇,这是不同整理者的倾向不同所致。然《大戴礼记·劝学》中最后一段子贡问“君子见大川必观”事,与学习关系不大,说明整理此篇时学者见识的混乱。参见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七《劝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136页。学习在早期儒家论述中的意义可以与仁孝之类的品德相等同,这是今天需要重新重视的情形。
学必有方:学习的内容、方式和目的
可以指出两点现象并展开讨论:第一,早期儒家提倡的学习,始于知识层面,强调人需要广泛了解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其后上升到理念层面,最为重要的知识是与“先王”有关的道理。第二,儒生所学的知识有明确的致用倾向。学习的首要目的是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学习的效果是让儒生能够深度参与政治生活,并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判断。所谓的“不迁怒,不贰过”的人生境界,仍然需要回归到政治实践中。
首先看知识层面上的学习。《论语·阳货》中孔子提到,学《诗》的好处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4)《论语注疏》卷一七《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86页。这是对追求自然知识的表态。自然知识之外,社会知识同样为儒家所重视。《礼记·内则》提出,男子自幼及长,先后学习一般的礼仪和数字、方向、朔望六甲、乐、诗、舞、射、御等技术知识,等到“三十有室”以后,更要“博学无方,孙友视志”,意味“学无常,在志所好也”“顺于友,视其所志也”。(25)《礼记正义》卷二八《内则》,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186页。此说又可以和同书《孔子闲居》君子“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联系起来。(26)《礼记正义》卷五一《孔子闲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508页。上博简《民之父母》有同样表述,注释者认为此句与《中庸》之“至诚之道”有关,(2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因其文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28)《礼记正义》卷五三《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543页。按:此说略显迂曲。因君子“博学无方”,故而无所不知,由现实的征兆即可洞察变化的萌发,不必等待蓍龟之灵。由此,学习以达到知识上丰富的境界,可以收获难得的效用。
前引孔子言学《诗》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功能后,他又说“人而不为《周南》《邵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29)《论语注疏》卷一七《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86页。将二《南》特意从《诗》中提取出来,说明其意义深远。马融注称两篇是“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也”。(30)《论语注疏》卷一七《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86页。汉儒之意,孔子对二《南》的态度不局限在“鸟兽草木之名”的获取,而是引申到了“先王之治”上。自然和社会知识只是儒家之学的基础,“先王之道”才是儒家之学的目的。有人曾向子贡发问“仲尼焉学”,从子贡的回答看,此人所问乃是孔子的老师是谁。然子贡之言很值得玩味,所谓“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31)《论语注疏》卷一九《子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503页。孔子所学乃是“文武之道”,无论大贤小贤,能传“文武之道”者便是孔子师。“文武之道”很明显是“先王之道”,亦即孔子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接着看学习与判断力的形成。《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子路讲授“六蔽”,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32)《论语注疏》卷一七《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85页。仁、智、信、直、勇、刚都是儒家称道的德性,但是如果没有学习的支撑与限制,这些美德将走向负面。《荀子·解蔽》载:“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注称:“乱,杂也。言其多才艺,足以及先王也。”郝懿行曰:“乱者,治也。学治天下之术。‘乱’之一字,包治、乱二义。注非。”(33)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一五《解蔽》,第393页。从文字学的角度看,郝懿行所说成立。孔子学治天下之术,而若从所学多元的角度理解,以孔子所学驳杂,亦通。而无论学治天下术也好,所学驳杂也罢,孔子所学,效用亦在“不蔽”。此论和《阳货》中之好学可解“六蔽”相通,应该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学以解蔽,即获得明辨是非的判断力。
还有将《论语》中的德性更明确为功能的提法,比如《吕氏春秋·孟夏季·尊师》将学习与判断力的关联具体化,称:“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34)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季·尊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页。这样看来,学习是人发现自己天生器官功能的基础。人倘若不学习,连天赋的本能都无法实现。这便是“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35)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季·尊师》,第93页。
上博简《性情论》有“用心各异,教使然也”之句,其中“教”字作“”,整理者指出此字读为“教”“学”均可,兼及两义。(36)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此说与《尊师》所论可并读。所学不同,用心自异。学是形成判断力、制约性情的前提。前文所谓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便是判断力的表现。
先秦之学又与行事相连,讲究学以致用。章太炎说:“周之故言,仕、学为一训。《说文》:‘仕,学也。’”(37)章太炎:《检论》卷四《正颜》,《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9页。阎步克据此称:“学士既受教育,又有职役,非宦于大夫,无所师。”(38)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儒家所谓学,是现实政治磨炼的结果。学于师,任于事,两者不可偏废。诸如性情的克制与调和,其目的是参与政治生活,其归结都在于行事。《礼记·杂记》说:“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39)《礼记正义》卷四三《杂记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398页。讲的就是学行合一、知行合一的道理。(40)章太炎称“古之能官人者,不由令名,问其师学,试之以其事,事就则有劳,不就则无劳”表达了同样的见解。章太炎:《国故论衡校定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页。
上述情形可以表明学习的效果可以检验。倘若只将学视作知识上的追求,似乎又将儒家所论理解得简单了。胡宝国曾指出,南朝有重视知识的风气,其表现则是经史、文学及玄学领域中的“知识的炫耀”。(41)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84页。现在看来,先秦时,儒家已经有了重视知识的风气。与南朝不同者,先秦儒家的知识重在致用,而非仅仅掌握知识而已。
上博简《容成氏》记有:“于是乎始语尧天地人民之道。与之言政,悦简以行。与之言乐,悦和以长。与之言礼,悦敀以不逆。尧乃悦。”(4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56页。尧所学乃政、乐、礼,统称为“天地人民之道”。知识虽然有分类,其边界却很模糊。今人看来,礼乐当然可以被统一在政教之内,时人却能区分其中的差异。与其说儒家重视在学习中形成知识分类,不如说他们更重视对知识的整体体会和把握。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是儒家知识体系最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后代认为儒家并无专长和显著特征的原因。
综合上述情况可作总结:早期儒家提倡“好学”,目的在于建立包含自然和社会知识的知识体系,进而养成制约性情的判断力,由此建构协调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
提及儒家的核心观念,人们都会理解为是“仁”。但是“仁”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表现呢?孔子又没有特别明确的指示。与此相反的是,学习在儒家的经典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孔子自己评价自己,也是从学出发的。史载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43)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季·尊师》,第96页。由此可以明确,“仁”的境界很难把握,而“学”则是通往仁的唯一途径。上博简《从政》甲篇曰:“言见善行,内其仁焉,可谓学矣。”(4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24页。此意即通过“学”来体会“仁”,实现“仁”。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通过人人都能够参与的“学”而向着无法直观感受的“仁”无限靠近,这是早期儒家在人性论层面的努力。
圣心备焉:学习所致的不朽
人们对儒家形成了刻板的印象,认为儒家并不关注生命,只关心现实的社会,于是形成了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等结论。现在看来,不惟道家出世不够准确,儒家入世也并不肯定。在先秦流行的各种思想观念中,老子、庄子以及黄老说都提倡某种形式的隐遁,以此塑造了出世的形象;儒家别具一格地提倡学习,让今人误以为儒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上面。隐居者未必不关心世务,入世者未必没有出世之心。事实上,儒家并非不关注个体生命,只是其表现方式颇为深邃。下文将论证,儒家通过学习希冀实现对性情的磨砺,进而达到不朽成圣的状态。
先秦学在王官,一般的贵族都会接受学习。学习只是一种自发的状态,习以为常。孔子有教无类,教与学成为改变身份、打破阶层的手段,学习也因之变成自觉的活动。由自发转化为自觉,一方面是改造自己,一方面是具备了教化民众的能力。学习改造人性、教化群氓的意义被孔子发掘出来。
孔子之后最看重学习的儒家学者是荀子。荀子对于学的论述,可以归纳出一套体系:首先,人性可以改变;其次,改变的方式是学习;第三,学习的效用在实践,学习的目的是成圣。这样一来就将儒家的学习观具体化了。
首先看学习改变人性的意义。《荀子·儒效》称:“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可以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45)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四《儒效》,第143—144页。性、情有待通过学习发现,是上文提到的内容。这里荀子表示,性、情天生,不但可以被发现,更可以被转化。移情化性是荀子赋予学习的新意义。
然后看由学习改变性情和命运。同样是《儒效》:“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4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四《儒效》,第125页。这里说的贵、智和富,指的是性情的变化,并非是事实的身份变化。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表现在并尧禹、分是非、成大器,(4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四《儒效》,第125—126页。其背后是学习带来一种向上向善向好的应然状态,却不是拥有财富和地位的实然状态。所以学的功用在于提供改变的机遇。当人开始向学之时,便拥有了成圣的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重于抵达终点,学习带给人审视世界方式的变化,升华了价值观念,其意义是人性论层面上的。
最后看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圣。《荀子·解蔽》称:“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注称:“言人所学当止于圣人之道及王道,不学异术也。圣王之道,是谓至足。”《荀子》所言以“圣”为止,注言似有所不及。因为《解蔽》此后作:“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48)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一五《解蔽》,第406—407页。在荀子那里,“圣”和“王”是相对存在的两种情况,前者是个体可以实现的境界,在于“尽伦”亦即实现天性;后者则是群体意图达到的境地,称作“尽制”亦即完备法度。两者称述的对象不同,希冀实现的状态也不同,所以注并未说清《解蔽》本意。即便如此,“至足”和“止于圣”的提出,表明了学习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掌握知识和形成判断力,亦不仅仅是参与政治生活与完成社会改造,其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完成个体生命的终极,实现和群体生命的共同和谐。
后来学者凝练荀子的表述,省去了学习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直接将学习与成圣相联系。《吕氏春秋·孟夏季·劝学》载:“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进而又说:“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49)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季·劝学》,第88页。这段话揭示了学习与成圣之间的关系。学习是成圣的途径,不学习不能成圣。圣人并非高不可攀,乃是人人只要力学便能实现的境界。成圣其实是启发天性、涵养潜能的过程。只要将人人体内孕育的本性找到,如同拂去其上蒙蔽的面纱,人就可以实现圣人的境地。具体的方法,就是学习。
还需要讨论的是“三不朽”观点的提出。春秋时,出现了“死且不朽”的观念。其说粗看有两层涵义,其一指的是宗庙祭祀不绝,其二则是追求个体生命获得精神层面的永生。鲁国的叔孙豹面对晋国范宣子关于“死而不朽”的提问,以臧文仲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回答,即“三不朽”。(50)《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五《襄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97页。类似的思想资源,构成了儒家政治理念与道德哲学的精神基础。
儒家追求成圣,成圣的目的是施化,圣人存在的落脚点应该还是治理国政与百姓。《论语·雍也》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对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同书《宪问》载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子路追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又回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继续追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回答说“修己以安百姓”。(51)《论语注疏》卷六《雍也》、卷一四《宪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85、5461页。圣人或者儒家君子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带动百姓、安集百姓。
孔子的成圣观念与“圣”字的本意不同,乃是春秋以后人们期待天降圣人,实现天下一统以救济民众的新发明。(52)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26—634页。回归到圣的本意,以《白虎通义》所说最清楚,其文曰:“圣者,通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53)班固撰集,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七《圣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4页。《风俗通义》转引其文为:“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故曰圣。”(54)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8页。这两条材料虽然出自汉代,却很能反映出“圣”的本来面目。“圣”字本作通达解,意指洞悉一切。获得这种能力的途径很明显是学习,上文讲到的儒家对于知识的种种尊重与渴求,都是“圣”本来意义的注脚,代表着一种有历史的儒家传统。拯民于水火的圣人,与通达的圣人相比,更重于德性和行动方面。放在政治哲学或者知识史的角度衡量,新变化实质上代表着社会环境的改变。
儒生们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和鸟兽草木之名,反映出王官之学的本来追求,属于贵族社会的当然需要;他们主张的先王遗言与文武之道,不仅被贵族所学习,更能成为春秋后期逐渐崛起的士人阶层申说论点的有力佐证。知识本没有高下之别,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学习的内容有了深浅的对立。以“治天下之大器举”为学习导向的儒生,自然逐渐冷落了技术流的知识。只有主动回避具体技艺,才能将自己与参与鄙事的庶人区隔开来,儒生也就逐渐结为边界清晰的群体,进而踏上身份提升的必由之路。此刻儒生所谓的不朽,也就是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赢得超越肉体的性情的巨大成功。
绝学无忧:反博学的意见
儒家提倡博学,战国以后社会上却存在一种反对博学的声音。
《老子》说:“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河上公注称:“绝学不真,不合道文。”(55)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二《异俗》,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9页。《河上公章句》将本篇名之为“异俗”,说明社会上有提倡学的风气。然而人倘若在错误的知识领域里掌握得越多,距离真正的“道”就越远。王弼注称:“下篇云,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然则学求益所能,而进其智者也。若将无欲而足,何求于益。”(56)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页。《帛书老子乙本》中王弼所引又作“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文句约略一致。(57)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3页。河上公注称:“‘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58)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三《忘知》,第186页。种种经文与注解都表明一个意思,人不应该太过执着于教化的目的去学习礼乐知识。老子、河上公与王弼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是否应该学习知识,特别是政教礼乐知识方面,他们的见解是一致的。
首先看道家中黄老的情况。《管子·法禁》:“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自注曰:“博学而不听令,奸人之雄也。”(59)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五《法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5页。同书《戒》篇也说“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注曰:“博学而不反修于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60)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〇《戒》,第510页。《管子》一书有很明显的黄老色彩,故而将“学”与“身”相对。博学发展了人的智识,儒家以此修齐治平;黄老提倡静身养生,上德下功,尊道贱物。只重视智识,忽略了内省工夫,结果只能是“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期身者也”。(6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〇《戒》,第510页。
“道家无为,又无不为”是黄老玄妙的理论,执行起来却很简单,只要能做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就可以了。(62)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2页。用浅近的话说,就是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黄老这里,身体的安逸既是目标,也是手段。说是目标,指的是圣君圣王天下大治的同时,获得身体安泰愉悦的状态。说是手段,指的是圣君圣王要镇静心神,将养性命展示给民众一种波澜不惊的宽舒姿态,由此获得他们的支持并效法。(63)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五《任法》,第900页。
人主养生的前提是放权,放权的核心在于任法。法度建立,照章办事,君臣上下贵贱各有依凭,是先圣一民之道。“间识博学辩说之士”为法所禁止,则儒生在法术面前早就与“请谒任举止人”等同。知识越多,越有可能破坏君臣上下贵贱的差等,越会妨碍人主的垂拱而治,越会“以其智乱法惑上”。(64)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五《任法》,第906页。儒家用以开耳目的智识,反而成为黄老禁绝的工具。智识本为人人所应有,人人所希求的本能,反而成为人主所不赞成,人臣所不能私的祸乱。
黄老学说的特点非常明确:时时处处从身体出发,又方方面面延伸到政治领域,点点滴滴关照到国计民生,里里外外不离家国同构。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宇宙论密不可分的先天连接,每想到人,便上升至国;凡思虑政,又反诸身。内外鼓荡,恣肆驳杂,无界限而有威势,牢笼天地,绳墨众生。
道家中庄子一派的观点相对黄老来说就简单多了。这一派的观点是破坏的而非建设的,只是否定博学无用,却不讨论如何治理天下。最直接的观点就见于《天地》中子贡与汉阴丈人的对话。汉阴丈人评价孔子和子贡说:“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65)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五上《天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35页。再看下面子贡对孔子说:“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今徒不然。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66)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五上《天地》,第436页。这段对话清楚地表示,庄子以为的圣人之道和孔子的圣人之道不一样。儒生们倡导的圣人之道是可事成功,力少功多。庄子一派的圣人之道是求执道神全,博学只可能“拟圣”,绝非真正的圣人。既然追求精神上的完备,何必在乎物质上的充盈。所以两边的区别是人生观的完全对立,那么政治行为在庄子一派也并无太多意义了。
《庄子·达生》假托颜回与孔子之口讨论学习划船,孔子说:“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67)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七上《达生》,第642页。“没人”一词,《庄子》郭象《注》以为:“谓能鹜没于水底。”成玄英《疏》:“鹜,鸭子也。谓津人便水,没入水中,犹如鸭鸟没水,因而捉舟。”(68)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七上《达生》,第642页。似乎是水性最好的人船也划得最好,因为他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忘却了生死,对于技术也完全做到无师自通了。
后世假托列子之名而作《列子》,其书虽晚出,却很能表现庄子一派的意见。书中把这段话略作修改,写成:“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数能。乃若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谡操之者也。”(69)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二《黄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60页。杨伯峻引曾广源说“谡即傻也”。(70)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二《黄帝》,第60页。这个描写就更形象了。按照津人的说法,擅长游泳的人能把船划好,但是那些从来没有见过船的人,莽撞地开始划船,往往能把船划得更好。这种现象在推崇依赖学习取得进步的儒生那里简直不可想象。孔子勉强解释为,没见过船的人无所畏惧于水,所以在波涛之上如履平地,进而他衍生出“凡重外者拙内”的结论,意味着人有所顾忌便失却天真之性,一事无成了。
假圣不是真圣,学而达道不如返诸己身。这种主张在战国以降很有影响,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某些现实。
就普通人而言,在乱世中自保尚且困难,谈何学习进而复兴礼乐呢?孔子学最高,德最盛,处春秋之世尚且郁郁寡欢,何况后人学行不及孔子,所处时代更劣于孔子呢?拿《孔丛子》中记载的孔子后人来说吧,子高以降,面目如同纵横辩士,依靠口辩安身立命,早就和孔子的形象相去甚远了。
就统治者而言,博学也并不值得推崇。因为博学使人不够专精。人主不专精,无法集中心智发动战争;臣民不专精,会因知识的驳杂而思想混乱。统一不只是军事上的征服,更仰仗于意志上的一致。这时候重提圣人,就不能是儒生们所说的礼乐雍容的先王,而是杀伐果敢的后王。自此“新圣”的意涵出现了。《商君书》多次提到“圣王”和“圣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明一法度,使民不乱。比如《壹言》说“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71)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页。睡虎地秦简《语书》中出现了“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恶俗”。(72)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到了始皇帝刻石中,反复出现了圣的字样,也是和法律相联系的,比如芝罘刻石中的“大圣作治”“圣法初兴”等。(7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9、250页。统一的法律是统一的治理的前提,统一的治理又是统一精神的表现。“新圣”因精神专一而获得统治的资格,臣民则必须遵循统一的法律而服从他。
一以贯之的“新圣”意涵,未必是秦人独创的政治理论改造,更有可能是知识界在统一前夜逐渐向权力集中和以法御下的精神理念靠拢。它从各种提倡道观念的主张中吸收了“专一精神”的概念,又将其进一步向前推动,将“无所不为”变成了实实在在通过法律执行的手段。正因为统一法令,黄老学说提倡的虚君政治才有了落地生根的基点;只能依靠新圣的学说,新建立的统一国家才有了配套的理论体系。
质言之,不通过学习,只需激发内在潜能便无所不能的圣人更适应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泰山刻石中提到了的“皇帝躬圣”,(7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3页。就是将始皇帝当作“新圣”来看待的。他的圣人地位也得到了儒生的认可。博士仆射周青臣上寿进颂,称赞始皇帝“神灵明圣”。(75)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页。此处的“圣”,儒生听来与皇帝听来可能各不相同,不过他们一定会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这个时代的“圣”只能是由始皇帝来担当了。(76)《列子》中记载了商太宰和孔子的对话。太宰问什么人是真圣人。孔子回答:“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杨伯峻:《列子集释》卷四《仲尼》,第120—121页)对话反映出秦统一带来的一种流行的历史认识,就是西方胜过东方。参考拙作《进山还是入海:战国秦汉海洋隐逸的历史记载》,《浙江学刊》2016年第5期。
结 论
汉代儒家曾试图弥合各种学说对学习的不同理解,语见《说苑·建本》。对不同历史时期圣人状态的理解不同,是造成人们选择不同的基本原因。在上古之世不是没有逍遥卓然的上圣,但是后人无法追踪其迹,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学习作为“崇名立身之本”。(77)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三《建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页。刘向加工的《说苑》,很明显是弥合黄老、道家与儒家对成圣的不同意见,达成一种对待学习的妥协共识。虽然这种观点尝试将对待学习的不同态度分散在历史演进的时间线上,却没有把握住历史运动的实质,因而并不能看作一种历时性的解释。
反之,章太炎总结先秦至汉代儒生所学内容变化,他认为,达儒知天、类儒知人、私儒知德、五经家专致的情形更给人启发。儒生的知识结构,从无所不知逐渐聚焦在经典之上,中间的私儒状态值得注意。《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无所不知到粗明德行,最后至专于今文经,儒生的学习行为在致用的路上越走越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儒生对学习的认识,与其说是越来越精专,不如说是越来越脱离对事物本质的发掘和探索了。
是否重视学习,表面上看是一种认识论的问题,深层次看是人性论的问题。不过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所有的哲学命题又都转化成了政治理论。人们在探讨政治的可能性时反思自身,也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旁及政治。所以中国的人性论又不能回避独特的政治性,一如中国的政治理论又多少带有生命色彩一样。上述命题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完善、成熟,并构成了后代类似讨论阐发的基础。必须要承认的是,正是先秦儒家积极地提倡学习,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绵延不绝的好学之风,这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