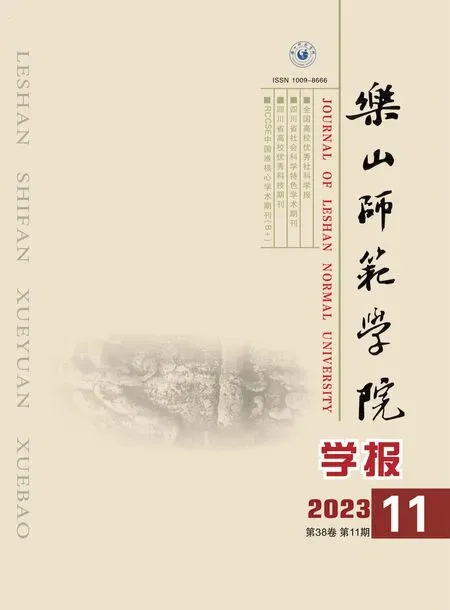《敦煌亡文辑校与研究》序
伏俊琏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悼念去世的同类,是诸多动物的本能。人对其亲朋好友的离世,总是充满悲悼之情。《诗经》中的《绿衣》,刘大白《白屋说诗》就认为是悼亡诗。“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中反复咏涵的是一件普通的“绿衣”,正是这件普通的衣服,勾起了他无限的伤感。因为这件绿衣,是他的爱妻曾经穿过的。现在物是人非,触目伤心,“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潘岳《悼亡》),“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元稹《遣悲怀》),只能一遍遍呼唤“曷维其已”?“曷维其亡”?还有《唐风》中的《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刘大白《白屋说诗》和闻一多《诗经通义》都认为这首诗是悼亡之作,先师郭晋稀先生《诗经蠡测》从之,并且补充了刘氏和闻氏的未密之处。这首诗真是哭着写出来的,诗人站在爱人的坟前,看着荒草丛生的坟茔,想着他(她)孤独地躺在地下,形单影只,五内崩裂,恍惚凝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无尽的思念,“惟将终夜长开眼,报达平生未展眉”(元稹《遣悲怀》)。清人陈澧《读诗日录》曰:“此诗甚悲,读之使人泪下。”
《列女传》记录的《柳下惠诔》是现存最早的诔辞:“柳下既死,门人将诔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邪?则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柳下惠是公元前七世纪中叶的人,这篇诔辞当产生在这个时代。诔辞先叙写功德,次哀悼去世,再评价并给予谥号。这一三段体式奠定了后世的这一类文体的基本格式。大约一个半世纪后,鲁哀公十六年(479)四月,孔子卒,哀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茕茕予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这篇诔辞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话语: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这样不仁,连一位老人也不放过,留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谁来保护我呀!伤心呀,仲尼!没有你,吾谁与归!
先师郭晋稀先生在《古代祭文精华序》中写道:“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离死别。或则夫妻同室,一死一生,生者既衿帱冷清,死者更冢穴荒凉。或者手足情深,一存一亡,存者既雁行折序,亡者更孤骨埋魂。或子女祭父母,生者既哭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死者不复顾复提携,浩然长逝。或父母吊夭殇,死者本幼未成德,生者则悲实依心,自然‘情往会悲,文来饮泣’。或以今人吊昔贤,如贾谊吊屈原,陆机吊魏武,死者既雄才抱恨,生者只好望古长嗟。更有为国从戎,枪林弹雨,舍命成仁;亦有救援不至,杀身取义。从古至今,死者既不可胜数,伤身之故又何可胜言。死者本情实可哀,生者遂悲从中来,作文吊唁。”所以,天下的文章,“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中,就有“诔”“哀”“吊”“祭”四类作品,宋人《文苑英华》中有“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类,明人《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列有“诔辞”“哀辞”“祭文”“吊文”四类,下及清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专列有“哀祭类”作品。“哀祭类”是中国文章中最富有真情的文类。
哀悼类作品的发达,与古代繁富的悼祭仪式关系密切。《仪礼》十七篇,而有关哀祭者即达七篇之多。《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礼”(吉、凶、军、宾、嘉)贯穿在丧葬、祭祀、加冠、结婚、朝会等各种活动中。古人认为天地、宗庙、神祇关系到国运之兴盛,宗族之延续,故祭祀之礼排列在五经之首,程序很多。如刚刚去世的士人,就有招魂、哭丧、告丧、洗尸、饭含、易服、送魂、停殡、修墓、入殓、吊唁、出殡、下葬、丧服、守孝、扫墓、祭祖等仪节,每一个仪节就有相关的致哀之辞。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祭悼仪式和祭悼文辞,几乎都是贵族文人层面的。而下层老百姓的祭祀形式、祭祀文辞,流传下来的很少。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宋初的写本,有数量不少的祭文、亡文,内容都是悼念死者的。过去这类文章的汇集校录比较零散,现在作者把它们全部汇集起来并加以校注和研究。关于祭文,作者在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结题成果《敦煌丧葬文书辑注》(巴蜀书社,2017 年)一书中已经加以辑录整理,共得包括书仪祭文和实用祭文文钞在内的150 余篇。亡文的数量更加可观,有170 多个写本,加之《为亡人舍施疏》等40 多个写本,数量在200 个以上,近700篇。根据这些写本,作者完成了60 余万字的书稿《敦煌亡文辑校》,并于2019 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2023 年撰成《敦煌亡文辑校与研究》(上下册),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上册为“辑校篇”,作者在充分吸收前辈学者校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新辑录亡文400余篇,并以写本为底本对这些亡文进行了详细校录。这些整理好的亡文为认识和研究中古时期我国民间的悼亡祭祀活动和相关应用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材料。与过去学术界对敦煌亡文的辑录和校勘相比,敦煌亡文辑校更关注写本的整体,在这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讨,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个写本,它上面可能抄写了体裁、内容不同的文本,这些文本之间是有关联的。通过认真阅读,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探讨写本制作者的用意,这是写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些写本的内容是分时段抄录的,抄写的人也不同,各自间的确很难说有联系。但有一些写本从字迹判断就是一个人抄写的,内容各式各样。那么,写本制作者为什么要把很多不同的内容抄录在一个写本上呢?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这个写本可能就是一个斋会的司仪平时准备的备忘录。还有一些写本,我们综合其上抄写的不同体裁的文本,可以恢复一个动态的立体的仪式过程。例如本书中《敦煌丧仪中的“劝孝”》一文就是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作者注意到敦煌写本中有祭文、亡文等复杂多样的应用文献夹杂佛教歌曲、俗讲、变文等讲唱文学作品的现象,而这类现象可能与敦煌寺院入破历中反复出现的一项“劝孝”活动收支记录密切相关。
1925 年,著名学者刘复先生整理出版了他在法国抄录的104 种各类文本,名曰《敦煌掇琐》,《前言》中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书名叫掇琐,因为书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这个小字,只是依着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并不是用了科学的方法估定的。譬如有两个写本,一本写的是《尚书》,一本写的是几首小唱,照着向来沿袭的说法,《尚书》当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书》当然是大的,小唱当然是小的。但切实一研究,一个古《尚书》,至多只能帮助我们在经解上得到一些小发明,几首小唱,却也许能使我们在一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文学上、语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见解。如此看所谓大小,岂不是适得其反。”根据散存的敦煌亡文写本,作者发现,始死、举发、临圹、七七、百日、一周(小祥)、二周(中祥)、三周(大祥)、忌日、迁葬、招魂等丧葬场合均有设斋延请僧道,以追悼亡者,并为生者祈福的仪式。而这些仪式上均有宣读亡文的环节。敦煌的亡文中,虽然没有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那样的大文章,但它们却是当时老百姓生活中运用的文辞,我们通过这些亡文,可以了解当时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普通人的生活、知识、信仰、语言。而这些亡文写本,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祭悼仪式的生动呈现。
除注重写本形态的描述,探讨写本各种文献之间的关系之外,“辑校篇”在字词考证方面亦颇见功夫。除综合运用音韵、文字及与传世文献互证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之外,本书还综合考虑抄手书法、书写习惯等,以便对写本中存在的疑难字词作出更加客观合理的推断。如《临圹文》中,“卜(或“择”)善(或“胜”)地以安坟,选××而置墓”是一惯用句式,共有13 件不同写本使用了这种句式,而其中“××”一词,出现了两种写法,一是“吉祥”,二是“吉晨”。写为“吉祥”者,如S.5573《临旷(圹)文》:“遂能卜善地以安坟,选吉祥而置墓”、S.6417《临旷(圹)文》:“于是择胜地以安坟,选吉祥而至(置)墓”,其他的如P.3765、Φ.263、P.2483、P.2991V、P.4694V、Φ.263+Φ.326V、北图“藏”字026V(7133)等写本中的《临圹文》亦写为“吉祥”。写为“吉晨”者,S.5957《临旷(圹)文》、S.6417《临旷(圹)文(二)》两件均写作:“遂以卜胜地以安坟,选吉晨而置墓。”“吉祥”“吉晨”两种写法都正确,还是其中一种写法是错误的,以往的一些校录研究未加区分,本书明确指出“吉祥”误,“吉晨”是。首先,作者从语法结构、词语搭配的角度论证了“选吉祥”之误,“选吉晨”之确;进而以《临圹文》近义语段“选此吉晨”“拣择良日”等印证了“选吉晨”之确;最后从抄手书写习惯和近音误读的角度讨论了写本误“晨”为“祥”的两种可能:
“祥”为“神”之笔误,而“神”乃“晨”之音误。敦煌愿文中“晨”或“辰”屡见写为“神”者,如P.2237《安散(伞)文》:“今烛(属)三春影月,四序初神(辰)”,同卷《燃灯文》:“乃于新年启正之日,初春上月诸神(辰)”。P.2237V《亡兄苐(弟)》“故于此晨”之“晨”原卷即先误写为“神”,后旁改为“晨”。盖抄手由“辰”而误为音近字“神”,进而承“吉”而笔误为“祥”而已。
“祥”为“长”之音误,而“长”为“辰”之形误,即抄手误以“辰”为“长”,进而受其前“吉”字之连累,写为音近误字“祥”。“祥”写为“长”者,如S.6417《燃灯文》(拟):“次为己躬宝寿延祥(长),合宅吉庆之福会也。”
以上推论是合理的。
《敦煌亡文辑校与研究》下册“研究篇”,作者对亡文做了诸多的理论方面的探讨:从写本出发,对亡文的定名和分类做了详细的梳理和阐发,进一步厘清了亡文和祭文的区别与联系,对亡文的结构和亡文结构与祭祀仪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从亡文文范制作和亡文文稿撰写的角度分析了敦煌亡文编选撰写的全面实用性和开放灵活性;从仪式推进、伦理教化、生命关怀、世俗祈愿等方面阐释了亡文的佛教实践功能;以讲唱文学和民间应用文的视角,从模式化创作与简便实用、骈俪文风与至情至性、结构严谨与艺术张力三个方面,概括了亡文的创作特色;结合敦煌地区亡文的应用情况,从口耳相传的仪式文学与民间抄写的角度,审视了写本中的借音字的类型、成因,以及对借音字的处理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启发性的。比如作者对敦煌亡文艺术性有深切的关注和独特的认识。敦煌亡文模式化创作的特征非常明显,这既是佛教文体仪式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佛教世俗化加剧的现实表现。但程式化、批量的生产和加工并不能完全掩盖敦煌亡文至情至性的一面。亡文中不仅具有传统祭文所特有的的“哀伤情重”的特点,还具有佛教应用文体所特有的“凄美华丽”的风格。有的直抒胸臆,呼天抢地。“所以母思玉质,断五内而哀悲;父忆花容,叫肝肠而寸绝”(S.343《亡女文》)写出了父母撕心裂肺的丧子之痛。“至孝等自云福(祸)愆灵祐,舋隔慈襟。俯寒泉以穷哀,践霜露而增感。色养之礼,攀拱木而无追;顾复之恩,仰慈尊而启福”(P.3562《亡考(一)》)道出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和悲痛。有的委婉曲折,寓情于景,更显悲戚色调。“陇树茫茫兮,白杨衰草;窗前寂寂兮,明月空堂。趍庭而魄散魂消,陟屺而槿枯兰谢。遂使哀孝等痛乖严训,恨隔母仪。醴泉涌而血泪难干,猿啼午夜;玄寝归而灵筵空在,雾淹九泉。”(P.3981《亡妣》)茫茫陇树、衰微白杨、稀疏草地、空堂明月,以形色营造悲凉;猿啼午夜、雾淹九泉,以声貌诉哀,与至孝的哀情交相呼应。“秋风而橘树含霜,鲤庭香坠;夜月而兰花泛露,岱岳魂飞。”(P.3981《亡考》、P.2820《亡考》)、“愁云幕幕(暮暮),悲风树之难期;若(苦)雾苍苍,恨啮指之何日。”(S.5639+S.5640,S.530V《亡妣文》)“橘树含霜”“兰花泛露”“岱岳魂飞”“愁云悲风树”“苦雾恨啮指”,都将景物拟人化,展现出恨之深、悲之切,这都是借以抒发追福之人的哀切情感。亡文还能和“唱导”融合在一起,于“号头”或“斋意”等结构段落处吟诵齐言韵诗。P.2044V《亡文》(拟)的“号头”“修矩(短)之分,鬼神无改易之期;否泰之时,真俗有叹伤之典。苗而不秀,宣交(父)之格言;林茂风摧,先儒之往教。历观前使(史),何代无斯者焉!”前插入了一首七言律诗:
稽首金容相好前,渌烟起处睹飞仙。
祥云了绕空中结,五天罗汉降清筵。
郑重玉毫生福惠,众人莫闹片时间。
跪悉(膝)捧炉生帝(谛)信,疏文具载说来看。
诗歌前两联描摹出斋会现场之热闹情形,后两联劝众人莫吵闹,静心倾听宣诵亡文。这可以算是亡文诵读开始前的一篇“押座诗”。再如P.3163V《阳都衙斋文》“斋意”部分这样写道:
比望长居人世,与彭祖齐年;何期命谢丹霄,魂魄归于逝水。谨课芭(芜)词,乃为诵曰:
雁行悲失序,□(鹤)林折一支(只)。
手足今朝断,贤兄何日期?
小弟肝肠烈(裂),儿女哭声齐。
傍人皆泣泪,□(邻)舍少衣恓(依栖)。
可见,亡文的制作除了引导亡斋仪式进行之外,用至美至情的言辞来表达活着的人对逝者的深深的悼念追福、对在世者的殷切祈愿,从而达到与神沟通且引导众生往生极乐的目的才是其核心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