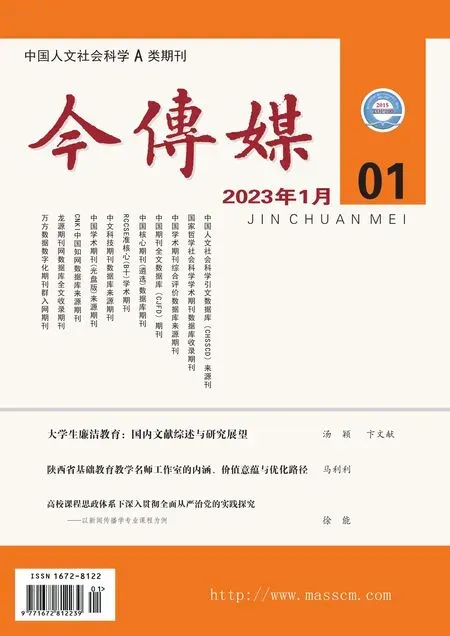警惕“舌尖”上的浪费
——基于“受众商品理论”浅析“吃播”浪潮下的激流暗礁
杨馨怡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一、初露锋芒:“吃播”行业蕴藏潜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智能设备的便携化、移动直播场景的生活化、移动直播内容的多元化等共享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搭上了快速发展的超车道,以吃饭为主要内容的“吃播”悄悄走入寻常百姓家,诞生了坐拥百万粉丝的“密子君”“小鱼”“浪味仙”等国内主播以及“SIO ASMR”“木下佑香”等海外知名主播,他们深受年轻人欢迎。“吃播”不仅影响了我们购物、生活的方式,也塑造了新的饮食观念,还催生了一种新的粉丝经济,即以“吃播”行业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一)重新审视“吃播”新内涵
顾名思义,“吃播”就是通过移动智能设备以直播或录播的形式将吃饭的视频分享在大众传播平台上,从而获得流量与打赏的行为。追本溯源,“吃播”属于舶来品。早在1989年,日本就推出过一档大胃王竞技综艺节目 《元祖!大食い王決定戦》;2014年,韩国也出现了直播吃饭的网络真人秀节目Mukbang,随后“吃播”慢慢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不少“草根”凭借“吃播”迅速坐拥百万粉丝,但是,“吃播”行业繁荣的背后存在着铺张浪费、欺骗消费等乱象。受众应该明白,“吃播”兴起的本意应该是享受美食、分享美食,绝不是单纯填塞浪费食物;主播也不应该用哗众取宠的方式来达到“流量变现”的目的。
(二)重新辨别“吃播”新类型
放眼当下的“吃播”行业,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种“吃播”类型:
1.“大胃王吃播”。这类主播通常会在短时间内吃下超乎常人食量数倍的食物,他们在镜头前大快朵颐,同时经过加速处理给人们营造出一口吃下海量食物的错觉,镜头中大部分女主播面容姣好、妆容精致,“颜值高+饭量大+吃相夸张”成为了他们的标签。比如,快手主播“@小鱼爱美食”的主页几乎被各类肥肉“刷屏”,猪捆肠、鱼肥油、辫子肠、大肘子等刺激性画面充斥其间,并且,视频均贴上了“一个就饱”“呲呲冒油”“一口一个”“满嘴油”“一个视频吃完”等刺激性标语。
2.“探店式吃播”。与“大胃王吃播”不同,“探店式吃播”主要是通过探索、“打卡”不同类型的美食店,并在现场录制“吃播”的类型。国内探店式“吃播”主播有“阿星探店”“大胃王密子君”“吃光吧金子”“p老板开饭了”“张喜喜”等,他们通过边吃边聊的方式营造出沉浸式的吃饭氛围,让“你看我吃”变成了“我们一起吃”,直播的“舞台”也由室内拓展到户外、家庭餐桌、街巷探店,甚至海外美食。“吃播”在全民互动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也乐于跟着探店主播一起参与到“打卡”的仪式中。
3.“养成式吃播”。之所以将他们定义为“养成式吃播”,是因为与现成的美食呈现方式不同,“养成式吃播”更偏向于沉浸式展示准备美食、制作美食、品尝美食、分享美食的全流程,注重在制作美食的过程中和观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与共情,勾起人们对美食的美好幻想。这类主播较为出名有“绵羊料理”“日食记”等,他们通过精心制作视频、输出高质量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广泛好评,并获得了大量粉丝关注。
二、警钟长鸣:“吃播”行业持续火热的原因
网络直播是资本和技术在消费社会之下融合的产物[2]。当“吃播”背后的灰色地带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就如同鲍德里亚的“媒介消费主义”所言,过度商业化易误导受众价值观,助长铺张浪费、奢靡的消费风气,带来不良社会影响。
(一)技术成本低裹挟着变现快的“糖衣炮弹”
在移动直播浪潮中,受众参与议程设置的能力和积极性不断提高,技术手段的迭代使得“技术简化”,参与技术的狂欢不再需要付出繁杂的脑力劳动,仅仅通过几个按键就能打通跨屏联系,使得“直播打破了围观与参与表达的界限,扩大了人的自主性”[3];同时,人们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依托于技术的巨大进步,媒介消费者成为了技术与人性复合了的“超级个体”[4],而被“空前赋权”的各类主播会更加频繁地进行生产和消费,吸纳粉丝,一旦凝聚了人气,便会将商品挂入商店平台,吸引潜在顾客。比如,“吃播小网红佩琪”就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例子,年仅3岁的女孩体重却达70斤,她的父母以“食量惊人”“几秒吃完”这种浮夸的词汇吸引流量,甚至不惜以摧毁佩琪健康为代价,让她吃下大量高热量食物,这是流量引发的悲剧。
(二)任由欲望在虚拟空间无限扩张
通过观看“吃播”而建立的强黏性源于受众心理的现实性写照。根据D.麦奎尔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正是基于对内容消费的满足心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代偿性心理,部分受众出于某些原因想吃却不能吃那些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观看“吃播”无疑成了一种“泄欲”途径,看着主播大口咀嚼食物,自身也体验到了类似“看过就是吃过”的快感;其次是窥私心理,窥私是一种人人皆有的心理,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获得安全感的需要,而“窥屏”给予了窥私者一个窗口,让人们在窥探的同时也构建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试图在未知领域里突破“自我设限”;最后是猎奇心理,很多喜欢看“大胃王吃播”的受众都会惊叹于这类主播惊人的食量、稀奇古怪的食物、浮夸的吃相,这种好奇促成了数以万计流量的围观,受众通过观看他们一口气吞下“10个汉堡”“五斤肥肉”而获得满足。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受众越兴奋,主播就变得越像一只“洪水猛兽”,进而用浮夸的演技来吸引受众的目光。
(三)现实土壤之上孕育出的“物化思想”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成就都令人瞩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物质生活逐渐富裕,因此,在部分主播的潜意识里就形成了“有的吃,吃不尽,随便吃”的刻板印象,他们通过摄入超于常人的食量、极端的表演形式、夸张的吃饭动作冲击和刺激着受众的感官,并为自己贴上“大胃王”“美食家”的标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品尝美食之心人皆有之,但食物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浪费的,虽然我们已经脱离了贫困饥饿的日子,但不能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物质生活享受中而忽视了精神生活的追求。
三、由表及里:基于“受众商品理论”浅析“吃播”行业
“受众商品理论”由传媒政治经济学家斯麦兹提出,他从广告资本、媒介、受众三者关系中揭示了资本逻辑下传播工业的运作机制[6]。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媒的功能更多集中于信息传播和服务,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受众市场的细分,传媒进入了“分众化”和“窄播”时代,视频内容不断细分、受众定位不断凸显,开拓短视频市场成为了实现主播经济效益的重要渠道。
(一)受众潜移默化成为了“商品”
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注意力来看,“吃播”行业盈利的模式并不复杂,一般是把直播或录播所获得的受众打赏、广告、平台店铺的产品以及入住签约的费用进行积累。在“吃播”行业中,广告是附加在主播和受众之间的一种变现形式,“观看”反而成了一份“免费的午餐”,用于为平台和主播吸引流量,最终转化为潜在的消费能力。因此,为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各大主播“争相斗艳”,然而作为“商品”的受众并不自知,反而觉得获得了满足感,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依偎关系进一步增强了用户黏性。主播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一个意见领袖,广告商所看重的并非大众,而是大众所产生的注意力经济,主播利用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向粉丝推介产品,发出强大的购买信号,同时由于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特殊性,流通性会比其他产品更大,因此,最终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而这正是广告主所希望的。
(二)“劳动”创造注意力经济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变成了众多社交媒体的“劳工”,虽然受众的主动性不断突破,从单纯的“消费者”变成了“产销合一者”,但是,随着人们对社交媒体依赖程度的加深,最终还是会被各类市场细分并销售给不同的广告商。受众在观看“吃播”时,就是在利用自己的注意力进行数字劳动,所增加的播放量、点赞量等数据都会被收集统计,最终被免费打包给高流量的主播。从资本的视角来看,受众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其媒介使用习惯成为了流量的免费劳动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受众滑动视频进行观看不仅仅是在享受闲暇时光,本质上依旧在创造价值,即一种潜在的注意力经济,围观增加了视频的曝光,曝光吸引了潜在的消费者群体,增加了接广告带来的经济潜力。因此,受众的视觉劳动不仅消费了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创造了商品的“象征价值”。
四、反听内视:“吃播”火爆场景下的反思
“大胃王吃播”造假、铺张浪费遭到了央视网的点名批评和公开整顿,这对“吃播”行业来说是暂时性的修整,但是对互联网的未来来说,的确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如果纵容这些低俗、虚假的内容蔓延,必将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换来的可能是一个贫瘠的信息化未来。
(一)驶离过度商业化的明滩暗礁离不开价值舵手
如今,网络盛行的“标题党”和包括“吃播”在内的各种夸张搞怪的直播,其商业模式本质上与19世纪70年代盛行的以发行量定胜负和以“广告优先”的“黄色新闻”是一样的[7]。可以说,我们对网络的探索和应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吃播”仅仅是行业逐利的一个缩影,它通过夸张的表象吸引受众注意力,最终实现变现。这几年,“吃播”行业从初露头角到因浪费、虚假被要求整改,再到有“春风吹又生”之势,甚至衍生出了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有流量的地方就有广告,为了分得这杯“羹”,部分主播绞尽脑汁,从“媒介时间”和“客观时间”的时间差里“下功夫”,数个小时的“吃播”可以通过快放、慢放等蒙太奇手法剪辑到5分钟内,更有部分主播边吃边吐。比如,快手播主“大牙晨晨”假吃30盘面食、“梨涡少女mini”假吃100根热狗,更有双胞胎饰演一人开展假吃直播……与此同时,主播主页购物车里的食品质量也难以保证,一旦出现问题追责维权较难,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且严重腐蚀了社会价值导向。因此,精准把握住流量的价值坐标是当下短视频行业最应该思考的现实问题,任何驶离社会效益而盲目追求流量的哗众取宠行为都应被限制,网络应发挥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二)审美异化和虚拟狂欢亟待自我拯救
被动的迁就于自媒体发布的内容,最终会丧失自我的主动性,正如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所概述的,狂欢的文化广场消除了等级、尊卑的对立,中心被边缘化[8]。“吃播”从一个“窗口”逐渐演化成为一个“狂欢的广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场虚拟的狂欢中。当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这是需要警惕的。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往往来源于我们自身的现实积累。饮食自古以来是中国人重要的文化载体,所以“吃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彰显和延续,并进行了新媒体式的转化。景观社会是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他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10]。主播们“各显神通”,“眼球效益”不断构建了饮食文化,并把它推向了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大胃王吃播”,这种形式将流量和浮夸程度相挂钩,哗众取宠式的标题、猎奇惊悚的内容不计其数,在审美异化环境中构建的“吃播”景观着实令人大跌眼镜。因此,在这场虚拟狂欢中,受众应该具有思辨意识、质疑意识,主动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正确看待饮食文化,助推吃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内容引导和创新。
(三)节粮减损以耕种“无形良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制止餐饮浪费。”哗众取宠式的“吃播”造成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粮食中有35%被浪费,其中餐桌外的浪费就高达700亿斤,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每年全球粮食从生产到零售全环节损失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4%,这个损失降低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2700多万吨粮食,够7000万人吃一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节粮减损相当于粮食增产,是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一块“无形良田”。粮食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我们不能因为物质生活富足而去浪费食物,相反更应该端好手中的这碗粮食,唯有藏粮于民,才能行稳致远,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五、结 语
身体不应该只是食物的容器,仅仅为了营造视觉冲击力,让“吃、吐、播”主宰流量,既是置身体健康于不顾,又背弃了社会诚信,这样的流量不过是过眼云烟。与其追求“吃多少”不如转换思维为“怎么吃”,将“浮夸”的吃相变为“优雅”的拍摄,将“浮躁”的功利心态变为“从容”的优质内容生产,从流量的“追捧者”变为质量的“把关人”。“俭,德之共者;侈,恶之大者。”善于发现“小米粒”中的“大民生”才是未来“吃播”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