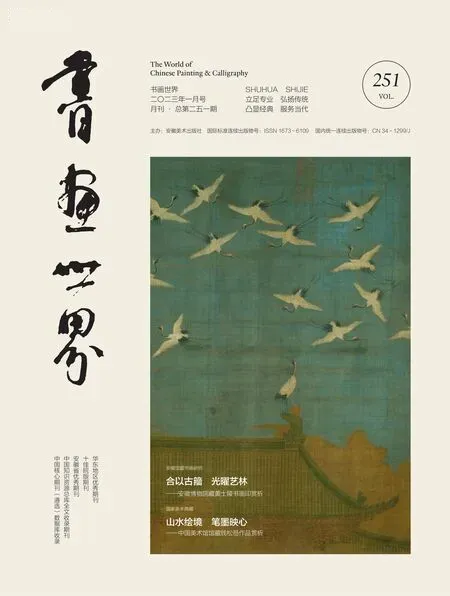论诗歌与绘画的关系—以苏轼诗画观为例
文_林锐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内容提要:对诗歌与绘画关系的探讨从古至今从未停止,中西方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以苏轼为代表,他深受禅宗通融无碍思想的影响,提出“书画一律”说;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以及莱辛为代表,莱辛在《拉奥孔》中详细地阐释了诗歌与绘画的关系。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经济、文化、政治,造就了不同的诗画观。在不同诗画观的指导下,诗歌与绘画呈现不同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但是事物因为内部因素的不同而又具有差异性。绘画与诗歌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作为艺术的一部分,诗歌与绘画必然有一定的通融性。但是诗歌与绘画毕竟不是同一事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苏轼是北宋著名诗人兼书画家,他与文人画家文同以及李公麟交往密切,在他们的往来书信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题画诗,以下通过苏轼的题画诗来论证诗歌与绘画的关系。
一、“诗画本一律”
绘画与诗歌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姊妹艺术一说。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首诗给出了诗与画相似的见解[1]33-44,即诗歌与绘画之间存在相通之处,诗可以描绘画境,画也可以描绘诗境。在唐代之前,绘画的地位是很低的,画画的人通常是民俗画师或皇宫画师,顶级文人和政界人士很少画画,而诗歌受到历代学者高度重视。古时候每一个文人都能说是诗人,尤其是到了唐朝,作诗变成很多文人表达志趣的艺术活动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层人士开始参与绘画创作,画论的逐渐丰富(如关于山水画创作过程的有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阐述人物画传神论的有谢赫的《古画品录》等),使绘画越来越受文人士大夫重视。再后来,张璪、王维等文人画家抬高了绘画的地位。在历史上,关于诗歌与绘画关系的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因观画而成诗”,如汉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就属于描写壁画的诗作;其二是“因诗而作画”,例如在宋代翰林图画院的考试过程中,考生按照诗歌的内容去作画。苏轼之所以说“诗画本一律”,是因为他认为诗歌与绘画在功能及对意境美追求上有相同之处。
(一)诗歌与绘画在功能上的相同之处
1.教化功能
在我国古代美学的构建中,先秦儒家美学占据着主导地位。孔子在《论语》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早期的诗歌与绘画经常与道德、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起到教化作用。首先,教化功能在诗歌中的表现——“诗言志”。“诗言志”最初在《尚书·尧典》中出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早期诗歌跟儒家的礼乐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教化功能在绘画中的表现——“成教化,助人伦”。西晋文学家陆机提出:“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陆机把绘画与“雅颂”进行类比,认为绘画具有与六经相等的地位[2]。我们可以通过古代名画去了解绘画所承载的教化功能。比如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图1),就起到了道德说教的作用;宋代李唐的《采薇图》(图2)表达了伯夷、叔齐的高洁品质,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效仿的对象。

图1 顾恺之 女史箴图(唐摹本,局部)25cm×349cm(全图)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图2 宋 李唐 采薇图27cm×90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怡情功能
魏晋时期,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玄学兴起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以及绘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这个时期,文人的性格和情感得到表现和释放,诗歌与绘画不再单一地为政治服务,而是转向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首先,怡情功能在诗歌中的表现——诗缘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认为诗歌是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的统一。诗歌表达志向,在表达过程中必然会渗透着强烈的情感。例如田园诗人陶渊明,通过描绘田园风光,表达自己平淡、恬静的心境。我们也可以在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诗歌中看到,他将国家和个人命运相结合,表达了浓烈的爱国情怀。其次,怡情功能在绘画中的表现——借物抒情。魏晋绘画评论家宗炳于《画山水序》中明确提出了“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神思”“畅神”等观点,通过山水去悟道,并抒发情感。画家通过绘画作品抒发情感,这在后世的画家中数不胜数。例如明代花鸟画家徐渭曾在其大写意作品《墨葡萄》中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抒发了画家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再如清代画家朱耷,他在《孔雀图》上题诗云“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表达了对清王朝的愤怒与蔑视。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情感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性。
(二)诗歌与绘画对意境美追求的相同之处
诗歌与绘画对意境美追求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诗、画在创作逻辑思维上是一致的。例如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诗人由春天的景物联想到目前是吃河豚的时节,表明了想象在诗、画创作中的重要性。顾恺之曾提出“迁想妙得”,“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也强调了想象在创作中的必要性。其次,诗、画在创作表达上都追求“以少胜多”。苏东坡曾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绘画还是诗歌,都不用刻意追求表面形似,而要强调神韵、意境,以及创作主体情感的抒发。这个观点类似接受主义美学家伊瑟尔所说的“召唤结构”,即画面具有大量的空白点和未定点,正是这种空白点与未定点促使欣赏者在欣赏作品时以无限的想象对作品进行审美再创作。诗歌亦是如此,诗歌常用比兴手法去表达作者意图,仅通过几个字就能抒发强烈情感,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最后,诗、画在赏析与评价上具有一致性。苏东坡云“诗画本一律”,即诗歌与绘画是“一律”的[1]19-32,我们在赏析诗、画时都可以用“天工”与“清新”作为它们的评价标准。“天工”所指的是天然,“清新”指的是清新、脱俗且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二、诗画非合辙—差异性
很多人认为苏轼的诗画观仅仅是“诗画一律”说,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苏轼的诗画观受到华严宗的影响,而华严宗的“事法界”就强调万物的差异性。诗歌与绘画是不同的艺术形式。诗与画的区别就是诗归于实践艺术和文学类的范畴,而绘画归于空间艺术范畴[3]。对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诗与以图像为表现形式的画之间关系的探索,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在《诗学》中认为诗和画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重现事物的形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创作主体要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绘画手段主要是运用点、线、面,诗歌的表达主要是以音乐的节奏和声调为主导。贺拉斯在《诗艺》中曾谈到故事的情节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以叙述出来。故事情节直接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直接看到,往往他们会感觉更加可靠。与听觉相比,通过视觉认知事物会获得更难忘的记忆。莱辛承继亚里士多德的代表性理论,觉得一切艺术都来源于模仿,诗和画全是模仿的艺术,但是它们的模仿对象和媒介完全不一样。它们的差别,导致了其特殊性。 莱辛在《拉奥孔》中说:古代画家并没有因诗而画(没有从荷马的诗歌作品中获取绘画素材),那么画家从诗人那里学到了什么呢? 画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诗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而是模仿诗中的高贵精神实质。诗歌可以为绘画提供创作思路或表现手段,而无法实现绘画所追求的高雅自然之美。绘画只能表现事物的瞬间状态,过去和未来需要画家进行想象才能完成,故莱辛说绘画要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时刻[4]。诗歌与绘画在叙事上所采用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诗歌所用符号是语言、文字,而绘画所用的符号是色彩与线条。苏轼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画家在取材方面,与诗人只是略同,诗歌运用语言文字描述,而绘画用色彩、线条描绘。另外,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形象上也有很大差别。苏东坡在点评王维的诗、画时表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诗而 “观”画,也说明诗歌与绘画具有某种差异性。苏轼也提出绘画具有诗歌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绘画也表现不了诗歌中的意境。例如苏轼《四时词》云“真态生香谁画得,玉如纤手嗅梅花”,明确表明没有哪一个画家能够画出美人的体香。
结语
综上所述,诗歌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认清诗歌与绘画的本质关系可以给予当下的艺术创作一定的启发。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虽然诗歌与绘画仍有界限,但早已相互融合。从唐代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宋代画院考试以诗为内容,再到元明清文人画成为主流,诗歌与绘画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