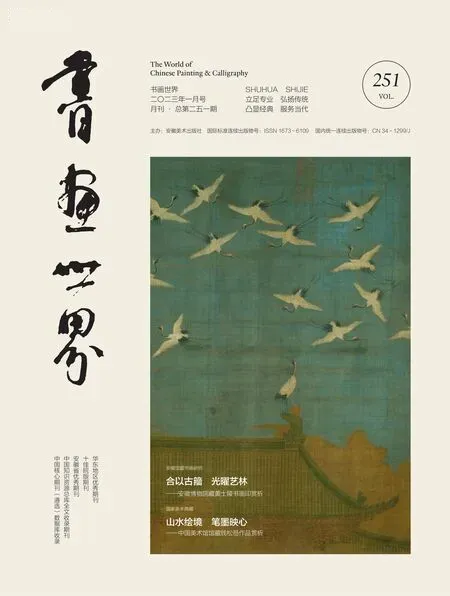从“幹惟画肉不画骨”争论探析唐代鞍马画“骨”“肉”品评
文_吕馨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内容提要:唐代马政强盛,鞍马画与之相应成为唐代绘画创作的热点题材,并在盛唐明皇时期达到了巅峰。韩幹为唐明皇的御用画家,风格独到,不同于其师曹霸,在当时引发了“画肉”和“画骨”的争论,本文围绕韩幹“骨”“肉”之争展开对唐代鞍马画“画骨”“画肉”品评的探讨。
一、关于韩幹鞍马画“画肉”“画骨”的争论
唐代马政强盛,涌现了大批鞍马主题的创作。鞍马画的创作紧贴着唐代马政两次兴盛产生了两个高潮期的主题,即“初唐的英雄主义、盛唐的享乐主义”[1]47。当时的诗人对绘画非常关注,尤其是鞍马画这一反映时代强音的绘画门类,留下了许多关于鞍马画的诗词,推崇曹霸画风的杜甫就曾题诗评韩幹的鞍马画“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2],他认为韩幹所绘鞍马画有肉无骨,使得骏马失去了神采和气概,尽显臃肿疲态。
针对杜甫的观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彦远以杜甫岂知画者,徒以幹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3]188,认为杜甫仅是因为韩幹所绘鞍马造型肥大,就提出这种观点,失之偏颇,为此他梳理了鞍马画的发展,并指出了当时鞍马的特点,膘肥体壮不同于前,韩幹受皇命作画,所作均为皇家马厩之马。顾云于观画后在《苏君厅观韩幹马障歌》中对张彦远观点表示赞同,称:“杜甫歌诗吟不足,可怜曹霸丹青曲。直言弟子韩幹马,画马无骨但有肉。”[4]
北宋张耒《萧朝散惠石本韩幹马图马亡后足》诗曰:“世人怪韩生,画马身苦肥。幹宁忍不画骥骨,当时厩马君未知。”[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认为韩幹画马身肥之人并不在少数,应是当时艺坛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张耒的观点是当时的皇家马厩之马“脽圆腰稳目生光,细尾丰膺毛帖肉”[5],因此“韩生丹青写天厩,磊落万龙无一瘦”[5]。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到皇家马厩中所豢养马匹的状态,更进一步理解韩幹所绘鞍马画的时代背景。
后有《宣和画谱》中谈此观点,质疑杜子美从何知韩幹师曹霸,以对韩幹师从何人的问题开端,论述韩幹虽师法曹霸,但由于其个人发展和艺术观念产生自身画风的革新,脱于其师之外。从古至今画马之事不绝,累代发展,在开元后由于政治经济因素,异域外邦的马匹络绎而至,受到精心照料,更为膘肥体壮。《宣和画谱》中认为韩幹所师为古人、为物象,观造化而变新风,评“所谓‘幹惟画肉不画骨’者,正以脱落展、郑之外,自成一家之妙也”[6]。
综上述记载可见在杜甫作出“幹惟画肉不画骨”的评价之后,以张彦远为首有许多人对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另外就杜甫本人的观点而言,其实是有所反复的,他在《画马赞》中对韩幹称赞有加,但是在《丹青引》中又改变了口风,其中缘由何在,是诗歌技法上的运用,还是杜甫与其本人心境或哲学思想变化暗合的观画思想的推进,为反尚肥的审美所带来的奢靡之风从而在书法品评上提出尚“瘦硬”的观念,从而影响其绘画上的审美偏向,仍在多角度有许多探讨的空间。
二、从唐代鞍马题材作品的图像看“画骨”“画肉”
唐代鞍马题材的绘画作品中曹霸和陈闳的已无流传,仅可靠古代文献资料窥见其艺术特色,难以和韩幹鞍马画做直接的比较,回归韩幹的鞍马画,以可基本明确为韩幹真迹的《牧马图》(图1)和《照夜白图》(图2)为例。

图1 唐 韩幹 牧马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唐 韩幹 照夜白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牧马图》绘一人二马,二马虚实相生、头小体肥,黑马的造型特征尤为明显,饱满肥硕,脖颈也呈现向外鼓溢的三角形,腿部、足部则有着极大的视觉反差。关于《牧马图》苏轼有诗《书韩幹牧马图》:“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7]从这番言论结合韩幹不愿效仿陈闳而是坚持尊重客观物象,可见韩幹确实推崇写实画法。在禄山之乱后,韩幹的端居无事更可佐证他对还原物象本真的追求。但是“画肉”和“画骨”在此处似乎是被简单化了,“肉”和“骨”的内在精神属性是否在这个讨论中被遗失了呢?苏轼诗中所言较为直白,从张彦远的回应来看,是否张彦远也是将杜甫诗中的“画骨”“画肉”理解成了肥与瘦呢?是否是将杜甫所评看作了他不懂画仅以肥瘦相较?这个问题在后文“骨”“肉”的含义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照夜白图》为极其富有动态美感的作品,画中玄宗爱马照夜白被缚于马桩之上,欲挣脱束缚,四蹄翻腾,怒目圆睁,肌肉紧绷,鬃毛飘扬,此幅画面之中照夜白虽肥硕圆润但力量感喷薄涌出,似溢出画面,这一股冲劲充斥在画面每一个细节之中。
两幅画作一动一静,线条细且劲挺,饱含张力,刨除色彩与晕染的技法,仍是两幅精彩非常的白描作品。韩幹之线条足以支撑画面,尽显马匹精神。
另外关于唐代壁画和雕塑方面的鞍马题材作品,余辉在《唐马天下震 骅骝长安肥——唐代鞍马画述略》一文中提出乾陵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狩猎出行图》中“奔马的造型与唐代《昭陵六骏》浮雕相近,纯系官马之相,是韩幹画马的艺术前缘”[1]48。初唐时期的浮雕《昭陵六骏》(图3)所呈现的是李世民开国征战时的六匹战马,展现了刚强雄劲的精神风貌,整体体型偏浑圆,四腿健壮,韩幹所绘鞍马画可能是继承了其英雄主义的艺术倾向,但在腿、足部有明显的不同,进行了艺术性的夸张。李贤墓壁画《狩猎出行图》整体视觉感受和马匹结构则与韩幹鞍马画更为相近,以图4截取的三匹鞍马为例,马匹有部分夸张的形式感,线条简练单纯,颇具运动感,和韩幹鞍马画的结构造型、线条精练度已经有了极大的相似。以“画骨”“画肉”的视野分析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它们是“画骨”或是“画肉”?我们判定的标准又在何处?

图3 唐 浮雕《昭陵六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图4 唐 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狩猎出行图》(局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三、“画骨”“画肉”的内涵和品评标准
最早将“骨”的概念用于绘画品评的应是顾恺之。顾恺之常使用“骨法”“骨趣”等词,如《论画》中顾恺之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8],这里的“骨法”应是由起支撑作用的骨头所引申的画面的结构、骨架的意味。后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曰“骨法用笔”,认为“骨法”为用笔的核心要求,与线条本身不同,“骨法”撑起线条的骨架,是线条得以构成审美趣味的基本要素。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试论六法[3]13-14,延伸出“骨气”,实与“气韵”意义相同,将“骨气”“形似”“立意”“用笔”与谢赫六法相串联,构成绘画品评的基础框架。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9],此“骨”强调笔迹,强调用笔的运动、变化和自由感,并非“骨法”二字能够完全涵盖的,在荆浩的艺术审美体系中,“骨”为标准之一。
“肉”作为绘画品评的词,早有见于张怀瓘用以形容张、陆、顾三家之长:“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3]115后在《评书药石论》中论书法云:“夫马筋多肉少为上,肉多筋少为下,书亦如之……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马为驽骀,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10]张怀瓘认为书法同相马,筋骨如果无法驾驭、支撑脂肉,在相马上即为劣马,张所言意在骨肉在于度,在于骨与肉相制衡之占比,无论是书是画骨肉皆需,不可无骨或是无肉,但是显然张怀瓘更加支持以骨为主要。前文提及的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对笔迹所呈现的效果的要求,即四势:“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9]荆浩所说的“肉”,指笔迹的圆浑丰满,他认为筋、肉、骨、气为一整体,缺少其一就会影响全局。“肉”与“骨”关系紧密,如人体结构一样,无骨之人不可生存,无肉之人也无法存活,其“肉”与“骨”的比例,展现两者的度,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
回到“幹惟画肉不画骨”的探讨之中,韩幹画马形体偏向肥大,虽有部分的艺术夸张,但是总体上看是对当时马匹的直观记录,那么形体上的“肥大”是否就直接对应了“肉”的评价呢?张耒在《读苏子瞻韩幹马图》中写道“韩生画马常苦肥,肉中藏骨以为奇”,苏轼也在《书韩幹牧马图》中写道“肉中画骨夸尤难”[7],二者强调了韩幹是肉中藏骨、肉中画骨,骨肉相衬、互为表里。杜甫的“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2]应不能单独提出前半句来理解,容易误将“画肉”理解为单纯的外表肥大,将“画骨”理解为简单的骨骼构架,结合后半句可知杜甫真正想传达的应是他认为韩幹画马没有内在的精神上的力量以及马匹神骏的气概,显得颓唐丧气,这也是杜甫个人审美的追求。但是从当前可知的文献遗存和图像资料并不能观当时对于“骨”“肉”品评的全貌,仅从鞍马题材完全解读“骨”“肉”品评以及定性标准也易陷入偏颇境地,因此本文仅辅以图像分析做争论的梳理和探讨,“骨”“肉”贯穿中国绘画品评体系的始终,不仅是对绘画造型的审美要求,更是对绘画内在精神内涵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