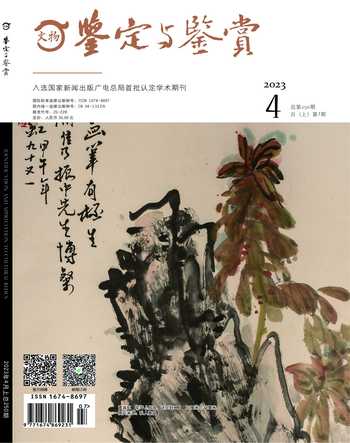《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元敬墓志铭并序》考释
靳花娜


摘 要:《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元敬墓志铭》是平顶山博物馆于2016年征集而来的。该墓志铭刻立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夏五月廿日,铭文由唐代光禄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昆撰书,记述了唐中期鸿胪寺卿元敬(776—840)的生平事迹、家族承袭及归葬地等内容。文章首次抄录墓志铭全文,并在志铭、文献记述的基础上考证相关历史事实。
关键词:元敬;墓志铭;考释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7.005
1 志铭
元敬墓志铭(图1),志为青石质,方形,带盖。盖长65厘米、宽64厘米、高13厘米,底长63厘米、宽63厘米、高17.5厘米。志文楷书24行,共548个字。盖铭文“大唐故元公之墓志铭”。
墓志首行题“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元府君墓志铭并序”,第二行题“光禄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昆撰”。志文如下:
君讳敬,字遵之,河南人也。后魏道武皇帝之苗裔,代为望族,名冠中外。曾祖成,大理丞。祖□眉州刺史。考原,左□(散)骑常侍。君则常侍府君之季子也。幼有□状,□□尚义,□从州县之职。因有徒劳之叹。是时,李公弘作镇睢阳,□□(求贤)若渴,召君□□,宛若□人。君遂感谢,即以许之,□途轻足□□□□三四岁余。遍历右职,及李为帅,讨叛淮夷,指麾群雄,歼殄□□,制置利益,皆出于君。时李帅入□觐及加慰,荐遂授□□□□□□□□。故太保裴公甚爱其才,累□奏陈□为定州刺史。宝历元年,转陇州兼中执宪充兵马留后,军声益振,边剿不开。居之五载,入选右神武将军,改授右金吾卫将军,复授鸿胪卿,统典□国,即叙者咸遵禀而悦服也。开成二年,爰有大德之命,莅职四岁,□□□然,军令□索,各得其要,向非上才全器,曷能如是者乎?天胡不惠?丧我英杰。开成五年夏五月廿日薨于河南河南县从政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四。天子震悼,辍朝三日。诏赠兵部尚书,追旧勋也。君夫人白水张氏。有女四人。子三人,长曰光绍,千牛卫□,次曰光远,亳州司□,幼曰光嗣,安州士曹参军。皆禀义训,思绍前□,哀毁来愬,托辞于予,且曰:日月有时,将及大窆,其年仲冬末旬有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阳县清风乡邙山之阳。龟筮叶从松槚巳□,虽有封树意,铭下泉□人先,君□馆自大梁启举而袱焉。□于君相过从也,谙君生平□历,故不让其辞。铭曰:山高千仞,象君之劳,河流无己,如君之义,北邙佳城,君之归宿,□□仕□,□北鄙虏,马远迹边,□不起所,所惜君者,半途而止,九原□□,播名沙漠,远比颇牧,未济卫霍,迫□遗烈,□古如何?(图2)
墓志铭记述了唐中期鸿胪寺卿元敬的一生。元敬,字遵之,河南人也,为后魏(即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的后裔,源自北方鲜卑族。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二十年(496)北魏孝文帝下诏改鲜卑族拓跋氏为汉族元姓,自此拓跋元氏与内地汉姓互通,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隋唐时期,由拓跋氏所改的汉姓元氏后裔大部分生活居住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一带,并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望族,河南即是唐代元氏郡望之一。据志文记载,元敬之曾祖元成曾官拜大理丞,唐代大理丞官秩从六品上,主掌刑判事宜。其祖父曾任眉州刺史。其父元原曾任左□(散)骑常侍。元敬为元原第四子,或为最小的儿子。
志文中“银青光禄大夫”为古代掌管皇帝顾问应对的官名。在汉武帝时已设置银青光禄大夫一职,即为掌管皇帝顾问应对的官员。魏晋南北朝以后,光禄大夫逐渐成为朝廷对有功勋的官员的加官,并无实际职权。到了隋唐时期,光禄大夫依然作为朝中有功之臣的加官和褒官。本篇志文中元敬被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官阶为从三品,但并无实际职权。志文中的“鸿胪卿”在唐代为鸿胪寺正卿,乃中央九寺之一的官阶,为从三品,主管外交接待事务和凶仪之事,即执掌朝廷四夷朝贡、宴享、慰劳、给赐和送迎之事以及有关国体的凶仪禁令等,可以说是当时唐朝的外交主政之官。从首行题文中可以得知,元敬生前最高职事为从三品鸿胪寺卿。其薨后,朝廷念其往日的功勋,追赠兵部尚书,享正三品殊荣。
2 元敬生平事迹
据志文记载,元敬应出生于公元766年,最初在州县任职,后投奔镇守睢阳的李(韩)弘,累积军功,经太子太保裴度保荐,任定州刺史。宝历元年(825),轉陇州兼中执宪,充兵马留后。太和四年(830),入选右神武将军,改授右金吾卫将军,复授鸿胪卿。开成五年(840)薨逝于河南县自家私宅内,享年七十四岁,朝廷感念其功勋追赠兵部尚书。
志文“李公弘作镇睢阳,□□(求贤)若渴,召君□□,宛若□人。……及李为帅,讨叛淮夷,指麾群雄”一节中的“李公弘”可能为许国公韩弘。根据志文中“李公弘作镇睢阳”和“及李为帅讨叛淮夷,指麾群雄”两句推断,李弘曾经镇守睢阳,后又统帅兵马讨伐淮夷,终获大胜。《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韩弘传》记载:“韩弘,为宋州南城将。宪宗方用兵淮西,乃拜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吴元济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许国公。”由此可知,韩弘初为宋州南城的守城将军,后升至宣武节度副大使,但实际上掌握有宣武节度使的军政大权。之后随着各地藩镇势力的日益壮大,在唐代中期宪宗时期,为讨伐淮西吴元济叛乱,遏制地方藩镇的发展,唐宪宗在元和年间先后多次组织兵力讨伐淮西,当时任命韩弘为诸军行营都统,统帅李光颜、乌重胤等出征淮西,后来淮西吴元济被俘,韩弘凭借平叛的功劳兼任侍中,被朝廷加封为许国公。志文中的“睢阳”,指的是唐代的睢阳郡。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元年(742)始置睢阳郡,下辖有十余县,为唐代“十大望州”之一。乾元元年(758)恢复旧制,再次改名为宋州,前后存续了十六年,直到大历九年(774)才再次改为睢阳。由此可知,睢阳在唐代又称为“宋州”,位于今河南商丘。故而志文中李弘曾镇守睢阳,与《韩弘传》中为宋州南城将记载相吻合,同时志文中李弘为帅讨伐淮夷叛乱,与《韩弘传》中乃拜淮西诸军行营都统的事迹也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志文中的李弘与唐史中关于韩弘的记载是吻合的,韩弘后封为许国公,可能赐姓李的缘故。其中“右职”在唐代指“武职”,唐代中期诗人羊士谔曾在《酬彭州萧使君秋中言怀》诗中提到“右职移青绶”,其中的右职佩戴青绶,即指武将的装束制式。
志文“故太保裴公甚爱其才,累奏陈□为定州刺史”一节中的“裴公”应为位列三公的裴度。据《旧唐书·裴度传》所载,元和年间,太子太保裴度在平淮之战时请求随军督战,得到唐宪宗的同意,随即朝廷任命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和时任征讨淮西诸军都统的韩弘共同征讨淮西。当时韩弘为都统奉诏领军,元敬作为韩弘的副手与裴度共同随军征讨淮、蔡,日渐与裴度交往过甚,之后经太子太保裴度在朝中引荐,元敬外放官拜定州刺史,后又经数度升迁,最终官至鸿胪寺卿。
据志文记载,元敬的夫人为白水张氏,即南阳张氏,在唐代为世家望族。元敬一生共有七个子女:长子为元光绍,供职千牛卫;次子元光远,在亳州任职;幼子元光嗣,为安州士曹参军;另有女儿四人,姓名不详。元敬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清风乡邙山之阳,即今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的邙山南侧。邙山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个理想的长眠之地,位于洛阳北边,山不高,也很平缓,土厚而密实,水不易渗透,是天然的墓葬佳地,也是道教典籍中的七十二福地之一,南边依傍洛河,符合世人对墓葬选址的山水要求。据考古统计,从两周时期到五代时期,就有二十四座皇帝陵墓修建在邙山,东汉即位的十一位皇帝就有十位葬在邙山。由此可见,邙山在古代为贵族阶层墓葬的首选之地。
据志文记载,此墓志铭为时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昆应元光绍之请托代为撰写,李昆与元敬生前乃是旧交,对其生平事迹甚是熟知,感佩元敬的为人,故而应其家人之请撰写志铭。其中“光禄大夫”和“上柱国”皆为恩赏之官阶,无实职。而“御史中丞”在唐代为二品实职,有监督弹劾百官之权。李昆应邀为元敬撰写志铭,一方面是因元敬生前与其关系甚好,另一方面是文人士大夫为逝者撰写志铭乃是当时流行的丧葬习俗。
3 志铭阐释延伸
依据志文所记元敬生平事迹和志铭撰写体例,以下对志铭中所涉及的元和年间平淮之战以及唐中期的古文运动作进一步探究。
3.1 该志铭所记与韩愈所撰《平淮西碑》的关系
本墓志中记载元敬追随韩弘讨伐淮夷的战争,与韩愈追随裴度参加的平淮之战,应该为同一场战争。关于平淮之战,唐史中也多有记载。《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元和十年,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帅师次蔡州界。……会朝廷征天下兵,环申、蔡而讨吴元济。”《旧唐书·李光颜传》记载:“元和九年,将讨淮、蔡。……元和十二年四月,(李)光颜败(吴)元济之众三万于郾城。”由此可知,元和九年(814),唐宪宗调集了十几个藩镇的兵力,准备讨伐淮蔡之地的吴元济叛乱,后诏命宣武节度使韩弘帅军抵达蔡州边界,节制诸藩镇将领。之后因数路讨伐吴元济的军队皆没有取胜,裴度亲赴蔡州了解军情。之后裴度回朝向宪宗复命,并向朝廷大力举荐李光颜。之后,李光颜违抗韩弘命令,擅自出兵,后因唐宪宗介入,为惩罚李光颜,遂与韩弘产生嫌隙。后来,李光颜率领大军攻克吴元济于郾城。《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元和十二年,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请愈为行军司马。淮、蔡平,诏愈撰《平淮西碑》。”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时任宰相的裴度自请赴淮西督战时,邀请韩愈随其左右,任淮西行军司马,共同赴淮、蔡之地参与征讨吴元济叛乱,待平定淮、蔡叛乱之后,韩愈跟随裴度返回长安,朝廷下诏命其就平淮之事撰写《平淮西碑》。后因碑文中对裴度的表述和赞赏之词过多,遭到李愬等人的反对,最终唐宪宗下令磨灭韩愈碑文,命人重新起草重刻,故而留存了两份不同的《平淮西碑》碑文。但韩愈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平淮事件的亲历者,其所撰的《平淮西碑》虽然被毁灭,但碑文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一直以来受到后人的认可与推崇。
此外,与平淮之战同一时期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曾在诗中有感而发。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春节,平淮战役进入关键期,朝廷下令停放炮仗的事宜,白居易此时身处都城长安,对于因平淮之战而停放炮仗事宜写下了“闻停岁仗轸皇情,应为淮西寇未平”的诗句。其诗文记载的与本文墓志铭中所载元敬跟随韩弘的平淮之役及韩愈《平淮西碑》中所记的平淮之战为同一事件,即元和十年到元和十二年的那场平定淮西吴元济之战,他二人皆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和实证人。关于唐中期元和年间的这场平淮之战,裴度、李愬的功劳孰大孰小尚无定论,但这次战争是唐中期的一次关键战役,有力地削弱了地方藩镇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出现了“元和中兴”的盛况。
3.2 该志铭文体与唐中期的古文运动的关系
唐中期之前,墓志文的创作体例以四言骈文为主,文章语句讲究工整对称,体例严格固定。到唐中期,特别是在韩愈、柳宗元的带领下古文运动走向高潮。古文运动对文风的倡导极大地影响了墓志文的创作,使墓志文在这个阶段经历了重大改革,在继承先代的文体规范、行文风格的基础上,经过创作者改革,最终在古文运动的带动下使墓志创作趋于成熟。这一时期的墓志文写作改革也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完成,由当时古文运动的推动者以及大批文学家进行,如韩愈、柳宗元等。他们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文学家,参与了大量墓志文的创作,使唐代的墓志文创作达到巅峰。唐代的墓志文在写作上更加侧重散文的运用,方便对墓主的生平事迹进行描述,使墓主的形象更加清晰。这一时期大量知名文人参与墓志文的写作,也为墓志文注入了更多的文学性。
唐中期的墓志文改革主要体现在由单一的线性结构文体走向多元化文体。线性结构也就是将墓志的基本要素按照固定的次序逐件描写,志文结构较单调,缺少变化。唐中期以后,墓志作者在基本要素的排列上不断打破常规体例,根据墓主的个人事迹进行自我发挥,使撰写者可以对墓主人生前进行更加灵活的叙述与刻画。这种转变不仅增加了墓志文的文学性,也使墓志文变得可读性更强。
此外,唐中后期的墓志文逐渐完成由骈文体向散文体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墓志的铭文部分。唐中期之前的墓志创作,铭文主要是用来褒赞墓主的韵文。唐中期以后,尤其是在韩愈墓志文的写作中,将铭文由骈变散,内容也不再仅仅以褒扬歌颂为主,也增加了许多警惕的内容,同时还增加了铭文中记叙内容的比重,将铭与志合为一个整体,铭文不再只是志文的补充。墓志由骈文转变为散文,增加记叙内容,使唐中期之后的墓志文更加利于对墓主事迹的描述,墓主的形象更加清晰。唐中后期,国力趋于衰退,国内陷入藩镇割据的混战中,这一时期的人们没有过多的精力投入丧葬制式之中,丧葬内容整体上变得日益简化,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墓志文的写作也跌下了高峰。
本文中元敬墓志铭在撰写体例上就体现了唐中期的这一文体变化,该志文部分打破了固定的四字骈文结构,其中穿插有字数不等的散文體,更加灵活地对元敬生前事迹作了刻画。由撰文者李昆所处的时代和身份背景可知,唐中期元和年间,在当时古文运动的推动下,统治阶级上层也对文体结构开始有所改变。
但李昆作为统治阶级贵族,自身接受的学识与惯例,使其撰写的志文中四字骈文运用仍占很大的篇幅,特别是后半部分铭文的撰写仍严格遵照骈文的体例,仅仅以褒扬歌颂墓主人为主,保留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体例。由此可见,该篇墓志铭撰写的体例结构处于唐中期的文体变革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学特征。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周玲.《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晚唐墓志整理与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5.
[4]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5]李奇斌.《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天宝至元和年间墓志整理与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