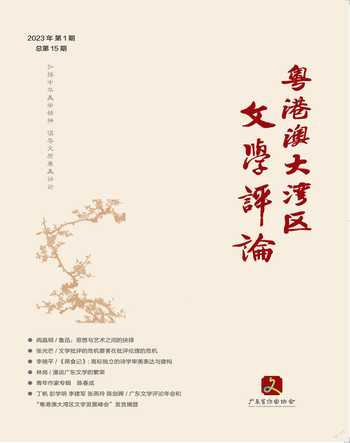冯乃超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与西田几多郎哲学
刘婉明
摘要:冯乃超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受到了西田几多郎哲学的重要影响,他通过在诗歌中以象征主义手法呈现“自觉的直观”来追求消弭主客、物我合一的“绝对的无”。“绝对的无”代表了西田哲学以“小我”融入“大我”的方式实现“内在超越”的追求,冯乃超最终以扬弃西田哲学的姿态投入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正是从象征主义时代的着重于“小我”走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大我”,标志着青年冯乃超向内探索的“小我”与向外探索的“大我”最终合二为一。
关键词:冯乃超;西田几多郎;象征主義
绪论
作为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冯乃超在高调提倡“革命文学”之前,曾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诗集《红纱灯》是中国19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重要成就。一直以来,对冯乃超早期诗歌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象征主义诗学层面的探讨。如朱自清认为其兼具“铿锵的音节”、丰富而浓郁的色彩和“催眠一般的力量”,所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1高利克(Marian Galik)从手法和主题上讨论了《红纱灯》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渊源关系,在他看来,冯乃超“是一个不真实的宇宙的创造者。(……)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中国现代诗人像冯乃超那样如此程度地把自己缩入‘象牙之塔”2。Л.Е.契尔卡斯基认为冯乃超是中国1920年代最颓废的象征主义诗人,在《红纱灯》中“可以看到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全部点缀,这些点缀用阴影和沙沙声织成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的神秘世界”3。孙玉石指出,留日期间对美术史的修习使冯乃超在接受法国象征派时尤其注重以具有强烈色彩感的语言来组织诗句。4程文超指出了冯乃超文学和思想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认为其前后诗风转变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民族情感的交互作用。1岩佐昌暲从分析《红纱灯》中的“苍白”一词入手,讨论了冯诗与当时日本象征诗人,特别是三木露风的关系,认为冯乃超通过将露风诗中的“蒼ざめる”“あおじるい”“青”等“被日本化了的”世纪末颓废词藻移入自己诗中,由此也就“将‘近代的感性、感觉移入了中国”。2刘静认为,日本文化中“物哀”情调的影响使冯乃超更易于与象征主义中的颓废感伤情绪产生共鸣。3
本文认为,除了象征主义外,日本现代哲学家、“京都学派”哲学的鼻祖——西田几多郎也对冯乃超产生了关键影响,冯乃超在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曾深深为西田哲学所倾倒。西田几多郎1911年出版处女作《善的研究》,标志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思想界开始摆脱对西方思想的单向移植,探索以东方思想为基础应对西方哲学挑战。该书出版后,在当时的日本青年中引起极大震动,一度被奉为思想圣经。冯乃超正是在上述时代思潮中接触到了西田哲学,他高中毕业后选择去京都帝大哲学系深造便是为了追随西田,而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和创作尝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4
就管见所言,目前学界对冯乃超早期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与西田哲学间的关系尚未有讨论,本文将从“自觉的直观”和“绝对的无”两个关键词入手,探讨西田哲学如何影响了冯乃超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
一、“自觉的直观”与
“内生命”的呈现
1923年以前,冯乃超是在横滨华侨富商家庭中过着优渥生活的贵公子,享受着从祖父辈积蓄起来的地位、财富和声望,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不仅导致了冯家的破产,也给冯乃超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按冯乃超自述,1924年至1927年间是其思想经历“剧烈的变化”的时期,他正是从此时开始接触西田几多郎的思想:
我目睹了地震后日本的在乡军人(退伍兵)残杀朝鲜人民的暴行,留下极深的印象;从横滨的一片瓦砾场的废墟回到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时,我对理科课程完全感不到兴趣了。我的交友范围本来很窄,生活比较孤独,这时心中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恼,便经常到图书馆去耽读些哲学和文学的书籍,以求得到一些慰安。我读了西田几多郎博士的著作《善的研究》,对这种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用自觉的直观去追求“绝对的无”的所谓“西田哲学”发生了兴趣。他是京都帝大的教授,为了听他的课,所以我在八高毕业后进了京都帝大的哲学系。5
震灾后的冯乃超站在废墟中,目睹了人类文明的脆弱和黑暗,从本来准备学习采矿、冶金的富国强兵志愿,转向了思考更深层次的自我与人类命运的哲学和文学。此时的他和大学毕业后困于人生出路的西田几多郎一样,亟须一种能够支撑“个人独立生存方式的自我内部依据”。6
自幼成长于日本的冯乃超是在日本旧制高等学校-帝国大学体系(明治维新后建立起的以培养顶级精英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体系,简称“帝高”系统)内完成青年时期教育的,他青年时代表现出的对哲学和文学的兴趣、以诗歌形式展开的对自我内部世界的探索,都是大正日本教养主义的典型表现,而西田几多郎正是教养主义的领袖人物。教养主义指通过广泛阅读,特别是人文经典的阅读而达到提升、完善自我人格的目的,进而成为更广大人类文化的承载者。教养主义萌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帝高”校园内,当时以高山樗牛、西田几多郎、夏目漱石等为代表的新式教师取代了旧武士风的教师。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记》、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仓田百三的《爱与认识的出发》等著作的刊行标志着大正教养主义的定形。井上克人指出,当时的日本青年受西方现代个人意识的影响,开始探索个体自我的内心世界,“人生问题”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阿部次郎、仓田百三等人的著作之所以被当时青年追捧为经典,正在于其对“自我内面的苦恼与探索”。1
包括冯乃超在内的创造社文人在这一时期留学日本,也受到了这种文化氛围的熏染。冯乃超在以自己“帝高”学生生活为题材写作的半自传小说《无彩的新月》里所写“以前我以为只有有教养的人才能够接近真理”,2指的就是教养主义的观念。郁达夫为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的汉译本做序时,就说其中反映出的“高等学校的学生的思想烦闷”“内心的苦闷”自己当年也颇有体会:
当时的日本,政治入于小康,思想纵横错乱之至。大家觉得旧的传统应该破坏,然而可以使人安心立命的新的东西,却还没有找着。所以一般神经过敏的有思想的青年,流入于虚无者,就跑上华严大瀑去投身自杀,志趋不坚的,就作了颓废派的恶徒,去贪他目前的官能的满足。3
明治以后的日本青年尽管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却无法真正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自我以面对急速展开的现代化进程和日趋强化的国家权力,因为找不到郁达夫所说的“安心立命的新的东西”而手足无措。冯乃超回忆中所谓“说不出来的苦恼”,除了大地震中经历的破灭体验外,还与这种因为找不到可以“安心立命的新的东西”而感到苦闷、虚无、颓废的时代氛围有关。1926年的冯乃超一面流连于剧院、美术馆、博物馆,在教养主义熏陶下进行着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一面加入学生中的左翼组织,阅读着马克思主义著作。4对西田哲学、象征主义诗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都是他为了在苦闷中寻求出路所做的探索。在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冯乃超实际上同时进行着两种探索:一是在教养主义文化氛围中,通过西田哲学与象征主义诗学,向内深探自我心灵世界及其与更广大人类命运相契合的可能;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向外寻找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这也就可以解释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为什么会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同步进行。
冯乃超在为自己的小说集《抚恤》所作自序中写道:
过去及现在的错综,梦幻和现实的交叉,这个特征必然地着色我的作品,一切是Double exposure的反复及连续。1
“过去与现在的错综”“梦幻与现实的交叉”所体现的正是彼时冯乃超心中向内与内外两种倾向的交互作用,《红纱灯》也是在上述思想语境中产生的。高穆评价《红纱灯》“极尽暗涩神秘的能事,几乎全以轻绡一般的梦幻为主题,他深溺于不可自拔的玄虚中,尽怀恋着过去,紧抱着往昔的尸骸。”2“过去”和“梦幻”作为冯乃超早期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其中不仅有历来研究者所讨论的象征主义影响,还包含着在西田哲学启发下“用自觉的直观去追求‘绝对的无”的尝试,它首先以诗人对自我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形式展开。
西田哲学和象征主义诗学都相信,在日常世界深处,存在着一个更为真实的、永恒的世界,它拒绝机械思维的介入,唯有通过人的直观感觉才能抵达,它是艺术家在灵感涌现的刹那中看见的永恒。冯乃超之所以重视“自觉的直观”,就是因为在西田哲学里唯有通过直觉才能深入自我心灵深处,回归主客未分前的永恒本源世界。这种状态下的体验被西田称为“纯粹经验”:“纯粹经验与直接经验是同一的。当人们直接地经验到自己的意识状态时,还没有主客之分,知识和它的对象是完全合一的。这是最纯的经验。”3《善的研究》序言中借用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体验来表达从直观感觉出发直达本源的观点:
费希纳自己说过:有一天早晨,他坐在莱比锡玫瑰谷的凳子上休息,在春天晴朗的阳光下眺望着鸟语花香、群蝶飞舞的牧场,心中一反过去那种无声无色的自然科学式的黑夜般的看法,而沉迷于当前现实的真实的白昼的思考。我不知受了什么影响,很早以前就抱有这样的想法,即认为实在必须就是现实原样,所谓物质世界也不过是从这种现实思考出来的。4
西田说费希特在眺望玫瑰谷的自然美景时发现了“实在”,也就是“纯粹经验”,它的获得不是通过主体观察客体的“无声无色的自然科学式”方法,而是诉诸于直觉体验。这一观念对当时冯乃超的“纯诗”实践有极大影响。
1925年,冯乃超从京都帝大转学至东京帝大,在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穆木天,对诗歌的共同喜爱使他们很快成为知交。5穆木天1926年写出的《谭诗》,正是二人交流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这篇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纯诗”宣言,大部分论者都是从穆木天所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方向对其进行分析,如金丝燕认为“纯诗”(poèsie pure)观念是受到了法国文学批评家伯雷蒙(Henri Brémond)的影响。6不过,这篇文章不能仅视为穆木天一人观念的反映,冯乃超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是冯乃超鼓励穆木天将二人讨论的意见写出,7这也是穆木天在文章中表述观点时多次使用“我们”的原因。冯乃超后来忆及此文,肯定其初衷是“对新诗歌很想闯出一条新路子”,是“一种创新与探索的行为”。1因此可以说,《谭诗》也是解析冯乃超早期诗歌观念的关键文献。
《谭詩》对诗之本质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内生命”,认为“纯诗”必须是诗人“内生命”反映:
要深汲到最纤纤的潜在意识,听最深邃的最远的不死的而永远死的音乐。诗是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
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是诗的本能。2
“纯诗”对诗人感官直觉的呈现将穿过日常生活的屏障抵达一般人难以触及的潜意识领域,开启“内生命”的神秘世界,而“内生命”世界又联接着无限世界里那个“深的大的最高生命”。这个深远广大的“最高生命”也就是西田哲学所描述的潜藏于自我意志深处的永恒本源世界:“我们的意志深处,是无法达到的无限深度,是一系列无限作用的极限点。”而要抵达这个极限点,不可依靠思维反省,而只能通过直觉,“真正的意志是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反省而限制的,能够限制的已经不是意志了。”3西田的“纯粹经验”是最本源的经验,是“唯一的实在”,它先于个人而存在,即所谓“不是有了个人才有经验,而是有了经验才有个人”。4但“纯粹经验”并非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外物,而是内在于个人心灵之中,个人的直觉经验都是“纯粹经验”的呈现:“我们的自我是绝对意志的临摹,是无限作用的结合,是作用之作用。(……)我们是神的肖像,是小宇宙。”5因此,唯有通过个体的直观体验对自我内心世界进行深度开掘才能通往永恒本源的“纯粹经验”。
《红纱灯》里的许多诗篇都热衷于营造李商隐式的缺月残花的幽凄情调或是李贺式的诡异意境,再用象征主义的通感笔法串起自我的各种感觉,反复哀咏无果的爱情、追怀已逝的往昔,感叹一切终将归于命定的死亡。这些都与诗人在上述“纯诗”理论指导下,以自我感官为媒介探索通往终极的“纯粹经验”世界之路的诗学实践有关。“纯粹经验”必须是在自我反省、在思虑加工之前“照事实原样而感知”的状态下才能获得,是“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瞬息之间,不仅还没有考虑这是外物的作用或是自己在感觉它,而且还没有判断这个颜色或声音是什么之前的那种状态”。6所以,冯乃超对于在诗中呈现“直观”尤为重视,他重视感官印象和内在幽微隐密情绪的精微描写,就是为了潜入自我的深层内心世界——“内生命”的深渊,回到意识和思维介入之前的“纯粹经验”,从而“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7
例如《生命的哀歌》开头由深夜的“雨声”“夜阴”引起对自我命运的哀叹,由此展开“生命的哀歌”,但诗人没有停留于表面的抒情,而是踏着这种由“雨声”“夜阴”唤起的“哀愁”“心瘁”,开启了一趟朝向超验世界的旅程:
我不愿再尝焚心的炽烈的酒精
我不愿多服迷神的剧性的镇剂
若得既涸的泪泉重新喷迸
我愿清醒一踏彼长夜漫漫的旅程1
在这趟心灵的超验之旅中,诗人先是游走于衰草丛中“零乱无名的荒塚”,发现“里面或眠着薄幸的古人/或朽着荣华一代的古梦”,2紧接着的第二章里,他又追随“凄怆的”跫声和“暗淡的灰色”的足迹,进入了另一个荒原世界:
我生的旅途阑入黑暗的夜深
运命的向导误入孤独的荒园
我听得可怕的静寂的声音
我亲着凝冻的化石的口吻3
在这里,他听到了命运的谶语:
一切都要毁灭
勿论新鲜与陈旧
一切都是哀愁
勿论命达与命瘦4
最后,诗人以“放逐的奴隶”之身来到“人迹不印的山隈/孤独地徘徊”,在这里凝视静寂的深渊,发现这深渊也正是自我心灵的深渊:
静寂的深渊
奥底潜着殘酷的蛟龙
无声的太息
里面蕴藏雄辩的苦痛
我底愤怒亲手交拜
我底哀愁谁人代转5
此诗收入《红纱灯》集中时改题为《哀唱》并做了较大改动,开头“我不愿再尝焚心的炽烈的酒精”至“我愿清醒一踏彼长夜漫漫的旅程”一段被全部删去,直接从“雨声”“夜阴”跳跃到超验世界的“荒塚”“荒原”展开巡游。删去这段承上启下的联接语句或许是为了增强诗的暗示性和神秘性,而从这番改动中正可看出,冯乃超是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呈现自我的直观体验,潜入自我心灵深处,召唤永恒世界的降临,如西田所言,“自然是从自我当中观察的”。6自我的情感既是引导诗人走向彼岸世界的桥梁,也是带领他回到此岸世界的径路,由此形成了自我“内生命”与永恒终极世界的循环呈现。
可以说,冯乃超是将象征主义经由自我感官直觉而追求超验世界的诗法当作接近西田哲学“纯粹经验”的路径,他以诗为媒介,呈现自我的“内生命”世界,由此再联接到那个更为深远广大的“深的大的最高生命”——“纯粹经验”的世界。
二、“绝对的无”与
“诗的统一性”
西田几多郎认为,要获得“纯粹经验”,不但需要深入自我内心深处,还要摆脱主—客二元的思维结构,进入“物我合一”的状态:“不可动摇的真理经常是由于消灭我们的主观的自我并成为客观而得到的”。7从西田对费希特的玫瑰谷体验的阐释中可见,“纯粹经验”里没有“知识”和“它的对象”之分,只有融为一体的“物”与“我”,无论“物”还是“我”,都是“纯粹经验”本身的呈现。西田经常举艺术家在灵感涌现时的创作状态,认为这体现了纯粹经验的“统一作用”,这种状态“是主客合一、知意融合的状态。这时物我相忘,既不是物推动我,也不是我推动物。只有一个世界、一个光景”。1
随着“纯粹经验”的获得,作为个人主体的自我将被消解,化为“无”,但不是消失,而是融入一个更大的自我——“绝对的无”中,“绝对的无”既包容万物,同时又呈现为万物。这就是冯乃超通过“自觉的直观”所欲追求的境界。井上克人指出,西田哲学中的“自觉”首先是对康德哲学中纯粹统觉(Ich denke)——即潜藏于人类意识根源的先验性形式——的发展,“试图在自觉的无限深渊中找到‘无的场所”,2而他对“绝对的无”的阐释则综合了宋学的“理一分殊”和佛教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种“绝对的无的场所”中,“个体的多样性无穷无尽地展现眼前,而场所本身也一直作为自我同一的事物带有回溯的秉性。”3也就是说,西田的“绝对的无”更接近于宋学的“理”和佛教的“空”,它并非凌驾于人间万物之外,而是内在于人间万物之中的“统一力”:“在宇宙万象的根基里有唯一的统一力,而万物是同一的实在所显现出来的东西。”4
相类似地,《谭诗》里也提出了“诗的统一性”。此处的“统一性”不单指诗的内容、结构、写法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所表现的对象、所使用的语言与所呈现的诗人“内生命”体验的统一:
他官能感觉的顺序,他的感情激荡的顺序,一切的音色律动都是成一种持续的曲线的。里头虽有说不尽的思想,但里头不知那里人感觉是有一个思想。我以为这是一个思想的深化,到其升华的状态,才能结晶出这个。(……)一个有统一性的诗,是一个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5
有明确的“我在思考”的意识就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西田哲学的“纯粹经验”是先于这种状态的,“思想”也不过是“纯粹经验”之统一作用的产物。所以,《谭诗》里说“纯诗”是思想的“深化”“升华”,“纯诗”应该“有说不尽的思想”而又不令人感觉“有一个思想”,就是说诗应该呈现思想,但不应有意识地表达思想,即“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6穆木天分别举出杜牧的《泊秦淮》和《赤壁》两首诗,认为前者正有“纯诗”风范,而后者则“如用胶水硬贴”般生硬。7《泊秦淮》从“烟笼寒水月笼纱”的感觉印象自然过渡到亡国之恨的感叹,由印象而至思想,又由思想回到“后庭花”的歌声印象,全诗浑然一体。而《赤壁》开篇便说理,自始至终都有一个怀古的主体在阐发议论,这种过度表现思想的诗显然不符合“纯诗”要求“统一性”的标准。
由此可见,穆木天和冯乃超此时所追求的能够体现“统一性”的“纯诗”必须打破思考、感觉的主体“我”与被思考、被感觉的客体“物”之间的界限,通过感官将“我”与“物”统一起来:“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1只有让自我的感觉融入自然的律动中,才能真正呈现出“内生命”的真实,它不可用理性思维语言“讲出”,只能通过直观感觉体悟。正如西田所言,真理只有在主客未分、自我反省意识作用——也就是思维作用——之前的状态下才会呈现:“真理的确信,就存在于主客相消失、天地间唯一的现实和将欲疑而不疑的地方。”2
冯乃超的《现在》就是上述“统一性”诗学理念的实践:
我看得 在幻影之中
苍白的微光颤动
一朵枯凋无力的蔷薇
深深吻着过去的残梦
我听得 在微风之中
破琴的古调——琮琮
一条干涸无水的河床
紧紧抱着沉默的虚空
我嗅得 在空谷之中
馥郁的兰香——沉重
一个晶莹玉琢的美人
无端地飘到我底心胸3
冯乃超和穆木天都主张取消诗的句读,认为这会破坏诗的旋律,因为诗是不可由人工限制的“流动的律的先验的东西”。4因此,冯诗除偶尔使用破折号表示情绪的绵延或声音的延长外,几乎不用任何标点,而完全以情绪的起伏顿挫、感觉的回旋律动来结构。《现在》中三段分别以“我看得”“我听得”“我嗅得”开头,三个词组后都不加标点,而是有意空出一格,标志着由此通过自我的视觉、听觉和嗅觉打开了“内生命”的世界。这里综合运用了象征主义诗歌手法中的“垂直感应”(correspondances verticales)和“水平感应”(correspondances horizontales),前者指从物体或感官联系到由其所激发的深层概念或情感,后者则表现为同一层次上不同感觉之间的相互呼应,如同用不同乐器演奏同一主旋律。5《现在》中,“我看得”引出的视觉体验唤起了苍白微光中的蔷薇残梦,“我听得”引出的听觉体验循着“破琴的古调”抵达了虚空的干涸河床,而“我嗅得”引出的嗅觉体验则在空谷兰香中发现了“晶莹玉琢的美人”。与此同时,三种感觉又是相互交错感应的:视觉场景中萦绕着蔷薇的暗香,听觉和嗅觉场景中同时呈现了“干涸无水的河床”和“晶莹玉琢的美人”的视觉意象,构成了一个重光叠影,声色交感的世界,現实世界中“我”的感官直觉与亦真亦幻的“物”的呈现在这种交感中融合在了一体,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另一首《冬》里更是越过了主语“我”的媒介,直接让感觉与“物”交响融汇:
徐步野外
山林穿上素色之衣
春花夏叶埋葬幽溪里
黯淡的丧钟荏苒——不尽地袅袅
草叶卷身睡眠
小鸟底翼搏凝冻
情思积着单调的白雪
无力地轻步在梦径之中
冬郊一面荒凉
树林空疏地哀伤
华丽的记忆有若退色的夕阳
浓冬底凄艳团成美人的死像
徐步野外
山林穿上素色之衣
春花夏叶埋葬幽溪里
黯淡的丧钟荏苒——不尽地袅袅 1
这首诗不是像浪漫主义抒情诗那样由作为主体的观察者“我”对作为客体的被观察者——冬景的描写而展开。诗中直接取消了代表主体的主语“我”,只留一缕“情思”游走于一片荒凉的素色冬景中,与不绝袅袅的“黯淡的丧钟”之声交相缠绕。随着积着“白雪”的“情思”一步步飘向通往彼岸的“梦径”,源于自我内部的“华丽记忆”和“美人的死像”也通过自然中的物象——“褪色的夕阳”“浓冬的凄艳”得到呈现。结尾处重复开头已经出现过的“徐步野外/……/黯淡的丧钟荏苒——不尽地袅袅”一段,不仅完成了整首诗的节奏循环,也完成了情绪的循环,“我”的情思与“物”的意象融合在最后袅袅不尽的丧钟声里,反复呈现又反复消融。“我”通过“情思”消融于“物”中,又通过“物”重新呈现出“我”,在“我”与“物”的不断融合与呈现中抵达由丧钟声所象征的终极的“无”。
西田几多郎相信,在“纯粹经验”的状态下,知、情、意是融为一体的,“物”与“我”是同一的,“正如我们的心灵被美妙的音乐所吸引,进入物我相忘的境地,觉得天地之间只有一片嘹亮的乐声那样,这一刹那便是所谓真正的实在出现了。”2他从东方传统“物我合一”的思想出发,对“纯粹经验”所体现出的这种“统一力”的描述与冯乃超对诗的“统一性”的追求正相契合,象征主义诗学中各种感觉交互契合的表现由此在冯乃超的诗中成为了消弭主客,融合知、情、意而走向“绝对的无”所代表的永恒终极世界的媒介。
查德威克(Charles Chadwick)说象征主义可以概括为“一种旨在穿透现实、进入观念世界的企图,这些观念要么是存在于诗人自身的(包括他的情感),要么是柏拉图式的,组成人类所向往的完美的超自然境界的理念”。3源于西方文化的象征主义的永恒世界更近于基督教的天堂,欧洲的象征主义诗人们通过诗歌走向超验世界——“一个并不存在的天堂”,4从此一去不归,他们只为超验之“美”而活,也因此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所言,“和现实严重脱节,承受绝不轻微的惩罚”。5就像维里耶(Villiers de lIsle-Adam)笔下的阿克瑟尔,在拥有了梦幻般的财富、爱情、荣誉后选择自我了断,因为已经“耗尽了未来”。6而在融汇了东方思想的西田哲学里,由“纯粹经验”开启的“绝对的无”的永恒世界却最终回归到了人间现世里。如冯乃超的《冬》所表现的,个体的小我在化为“无”之时,也就是以“绝对的无”重新呈现之日。西田哲学之所以被大正一代青年所追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越过西方式主—客二元的思维框架,提出了统一主客的更为本源性的“绝对的无”,由此克服了困扰当时青年的“唯我论”,提供给他们一个主客合一的、既超越自我又呈现自我的“绝对的无”,告诉他们“所谓认识真理,就是服从大的自我,也就是大的自我的实现”。1
冯乃超的半自传小说《无彩的新月》中曾写到主人公任夫在大学伦理学教授的影响下追求“大我和小我或宇宙的调和”,2说的正是西田哲学的上述观念。西田哲学对个体自我内部的无限深入最终是为了以个体小我化为“绝对的无”的形式实现对自我的“内在超越”,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冯乃超的诗歌并未终结于超验世界里的梦幻天堂,而是回到了现实,他回顾自己最终由象征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时,曾形容为“我还没有爬到冲入云霄的山巅,已经滚到大地上面来了”。3程文超认为冯乃超之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诗风发生了转变,与其心灵中不变的“民族情感”有关,这促使他从抒发个体的情感转向“抒发一种更趋向普遍性的情感”。4而冯乃超对“民族情感”这种更有“普遍性的情感”的追求,除了对故土的乡情外,还有西田哲学的上述启发,西田告诉他:“我们的意志越成为客观的,就越有力量。释迦牟尼和耶稣在千年之后还有感动万人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是很客观的。因此无我的人,即消灭自我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5这种对“客观”的大的自我的追求、对“无我”境界的向往,与冯乃超的故国情怀相结合,使他“用自觉的直观去追求‘绝对的无”的诗学实践最终落实到了“国民文学”上,故国成为了他的“大我”。
西田在阐说“大的自我”时,没有像欧洲象征主义诗人那样将之视为超越世间之外的彼岸世界,而是更加强调其“社会性”。他借助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论说个体的精神和肉体都与祖先、与其所生存其中的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个人的特性只是在这种社会意识的基础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变化而已”。6因此,追求内在自我的本源最终就是顺从这种内在于自我的“社会性”:“随着自我的人格越来越伟大,自我的要求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性的要求。”7视国家为拥有“統一的人格”的国家有机体观念也被西田拿来强调个人最终应该融入国家这个更大的人格中:“国家的本体乃是作为我们精神的根基的共同意识的表现。我们可以在国家里面获得人格的巨大发展。(……)我们所以为国家的效力就是为了争取伟大人格的发展与完成。”8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谭诗》对“纯诗”的阐释最后以“国民文学”做结,将体现国民生命与个人生命之交响的“国民文学的诗”视为“最诗的诗”。 冯乃超和穆木天沿着西田哲学的启示,在“内生命的最深的领域”所启示的无限世界里,发现了“故园的荒丘的振律”:
国民历史能为我们暗示最大的世界,先验的世界,引我们到Nostalgia的故乡里去。如此想,国民文学的诗,是最诗的诗也未可知。我要表现我们北国的雪的平原,乃超很憧憬他的南国的光的情调,因我们的灵魂的Correspondance不同罢?我们很想作表现败墟的诗歌——那是异国的薰香,同时又是自我的反映——要给中国人启示无限的世界。腐水,废船,我们爱他,看不见的死了的先年(Antau Mort)我们要化成了活的过去(Passé Vivant)。我要抹杀唐代以后的东西,乃超要进还要古的时代——先汉?先秦?听我们的心声,听我们故国的钟声,听先验的国里的音乐。关上园门,回到自己的故乡里。1
“故国的钟声”是自我“内生命”之“心声”通往“无限世界”的媒介,唯有通过“自我”的心声与“故国的钟声”的交响,才能获得无限世界的终极启悟。在《乡愁》一诗里,身在异乡的诗人在一个夜晚泛起“放浪异乡的哀愁”,冯乃超用他最善长的浓郁色彩勾勒出想象中的故国景色:
静悄地飞过了的哀愁
今宵荡回我空寂的心墟
我爱橙黄的月影
怀抱着故乡底淡青的情绪
我爱石砌的环拱的桥头
与桥底的缓慢的浊流
橙黄的月亮照着黄色的小舟
我念木版画里的苏州
异乡的欢乐若青焰
燃烧的欢乐带着雾霭的幽怨
听着浓情多恨的俚语民风
异乡的游女若神仙
我爱甜腻的胡琴的哀音
我爱空疏闲散的故园的夜深
任它飘荡我底灵魂
重翻琵琶行的古情恨2
这幅故国图画不是对中国任何一处地域的写实性描绘,但又的确来源于现实中的故国,它糅合了古今时间,跨越了地域,闪烁着冯乃超所追求的“南国的光的情调”:“橙黄的月影”与“淡青的情绪”相互映现,“木版画里的苏州”与“异乡的游女”交替登场,唐诗里“琵琶行的古情恨”与诗人“放浪异乡的哀愁”轮番呈现,由此也就模糊了“异乡”与“故乡”的界限,呈现出一个既充满“异国的薰香”,又回荡着“故国的钟声”的诗意世界。
冯乃超的故国不是欧洲象征主义诗人有去无回的彼岸天堂,他虽然在象征世界里关上了园门,但因为这是一扇通往“自己的故乡”的园门,所以也就留下了回到现实的窗口。他为送别归国的弟弟们所作畅想故乡南海的《南海去》是《红纱灯》集中少见的色彩明丽、情绪欢朗的诗篇,其中写到的“灰蓝的屋宇”“花岗岩的石柱”“龙眼的果树”“荔枝的老红”等意象就更多写实性色彩。它既是诗人自我心声的呈现,也是诗人自我的最终归宿。西田哲学对“绝对的无”统一物我的追求在冯乃超这里最终归结为让诗人的“小我”统一进故国这个“大我”。
结语
1927年,冯乃超在发表于《创造月刊》的《阑夜曲》附识中写道:“这是我过去的足迹,青春的古渡头;譬如我现在身在黑暗的荒海中,这是我偷闲的时刻望将天空去,那时的幽寂的远星。这是我旧稿的结束,也是一种可以微笑的墓碑。”1《红纱灯》的序言中也将这部诗集喻为过去的自己的“一片羽毛,一个蝉蜕”。2《红纱灯》所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时代是冯乃超走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前奏,诗集里虽然充满了对死亡、腐朽的持续凝视和书写,但其中仍然能够看到青年冯乃超对生命的执着。《生命的哀歌》中,诗人即便目睹了无名荒塚中的枯骨,也要想象自己死后能有一双“纤纤的玉手”将“鲜花插墓头”;即便“永眠在墓底”,也不愿忘记“红色的蔷薇花”,不忍抛弃“绿叶尽落的枯枝”,不忍毁坏“莺声死了的空笼”;即便在黑暗荒园里听过了“一切都要毁灭”的预言,仍然希望能用眼泪“淋浇开花来世的蓓蕾”。3正是这种对生命本身的执着,使冯乃超没有像欧洲象征主义诗人一样驻留于彼岸世界。《无彩的新月》里,主人公任夫在追求“大我和小我或宇宙的调和”时陷入虚无,觉得“只有否定自己的存在,只有消取自己的生存”,一度起了自杀之念,而当他终于战胜死亡的念头后,发现自己由此获得了新生:“当我九九还元到一无所有的洁白的身体来时,我已经是自由的我”。4这个新生后的自我在小说的结尾奔向了马克思主义和故国的广大民众,最终在“故国”这个“大我”里找到了“大的最高生命”。
诚然如工藤贵正所指出的,冯乃超是在感受到了西田哲学所代表的“大正生命主义”的破产之后投向了马克思主义,5但或许正是因为先经过了西田哲学的洗礼,冯乃超才能义无反顾地投向故国的无产大众。冯乃超从西田哲学中获得的“用自觉的直观去追求‘绝对的无”,就是通过感官直觉深入意识的深处,在主客合一、物我交融的状态下实现对个体小我的超越,作为主体的“小我”消弭之时,就是融入“绝对的无”这个“大我”中而重新显现之日。西田说个体正是因为知晓自我的有限性,所以希望“同绝对无限的力量结合”,以此“寻求自我的转变和生命的革新”。6人生的至善和最高幸福就是听从自我内部与广大人类理想相契合的庄严呼声,是“意志的发展完成”,是“严肃理想的实现”。7从这一意义上说,冯乃超最终以扬弃西田哲学的姿态投入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正是从象征主义时代的着重于“小我”走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大我”。1928年正式开启的“革命文学”运动标志着青年冯乃超向内探索的“小我”与向外探索的“大我”最终合二为一,在当年发表的小说《故乡》里,他通过一场想象中的还乡仪式,宣告自己从此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