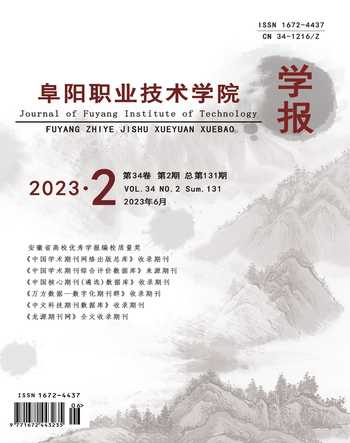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爱德华·福斯特小说研究
摘 要: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三个维度研究福斯特小说,论述作者构建的女性与自然和谐、女性与男性和谐,以及女性与自我和谐的生态命运共同体思想。
关键词: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福斯特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3)02-0066-05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英国20世纪闻名遐迩的现代作家和声名显赫的小说家。1905年,他创作出第一部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在随后的五年,他的小说创作迎来高峰期,先后创作出《最漫长的旅程》(1907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年)、《霍华德庄园》(1910年)。1914年,他完成《莫瑞斯》。此后十年,他未有小说产出,直到《印度之行》(1924年)问世。至此,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宣告结束。他一生创作的小说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却部部经典,使他声名鹊起,蜚声海外。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提出。如今,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外已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思想和批评方法,在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自然与女性的内在关联,试图找出二者之間的共同点,从而以女性的视角看待自然、关注自然和保护自然,进一步关注女性与男性的内在联系、女性与自我的内在联系。生态女性主义根据核心思想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可以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建构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这五种女性生态主义既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也各有偏颇各有不足,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即极力挖掘自然与女性之间千丝万缕的交织之处,崇尚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追求女性独立自主和自由平等。以下笔者拟立足小说文本的已有研究成果,破除单一研究,植根综合研究,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三个维度,点燃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星星之火,以期今后研究的燎原之势,这也恰恰是本研究的亮点和创新之所在。
一、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中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认为应该重点审视作为客体的自然与女性。自然养育万物,女性孕育生命哺育后代,这使得自然与女性在创造生命的本源上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妇女能够自然地认知自然、理解自然、与自然进行对话,并为自然代言。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极力主张女性价值与女神精神代表着一种生态价值与生态精神,指引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未来。”[1] 珍妮特·比尔(Janet Biehl)认为“肯定女性高于男性的自然本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似乎更倾向于妇女个体修为上的转变,而非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努力。”[2] 所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对父权制或男权制意识形态的反讽和批判,更是对自身价值形式的肯定,从而能够融汇于为大众共同接受的生态文化意识。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认为 “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 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3] 男性代表着人类,是文化强者的象征,而女性代表着自然,是文化弱者的象征。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毕比先生总是认为男女是不平等的,女人不可能像男人一样客套礼貌。教区长问:“难道我们要把女士们提高到我们的水平?”[4]80这些都充满了性别歧视的味道,他们都认为男人是走在女人前面的。塞西尔也是高高在上的男权主义者,他的本色就是不敢让女人来做任何决定,他把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用来塑造女人。“告诉你怎么样才算妩媚,怎么样才讨人喜欢,或者怎么样才算是大家闺秀,还告诉你男人认为女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风度。”[4]161福斯特把小说的第九章取名为“作为一件艺术品的露西”。这表明露西和塞西尔宣布订婚之后,露西依附于塞西尔,因为他的男子汉气概而钦佩他,成为他的的附属品。然而露西是个叛逆者,她希望与自己的爱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塞西尔一直认为男人是保护者,女人是被保护者。他洞察不出露西真正期盼的爱情是什么样的,而乔治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男女的地位,认为“男女将会是平等的。”“这种想统治女人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而男人和女人必须站在一起与之搏斗,才能进入伊甸园。”[4]214于是露西的障碍物去除了,她再也无法容忍塞西尔。为了获得完全的自由和真正的爱情,她与塞西尔解除了婚约,继而与乔治相爱。“青春笼罩着他们,……爱情也已得到。然而他们感受到一种比这个更为神秘的爱情。”[4]215 露西实现了从文化弱者身份向文化强者身份的根本性转变。《最漫长的旅程》中的安塞尔一直认为男人和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的要求不同,男人的要求是更多更高的,男人爱的是整个人类,男人接受的文明程度越高,就会关心更多的事情,“不仅仅要求得到妻子和孩子,而且要求得到朋友、工作,还有精神自由。”[5]安塞尔认为女人是造化的使者,只想着爱一个男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并嫁给他,她就完成了任务。女主人公阿格尼丝爱上里基,她支持里基关心一切事情,包括朋友、工作和精神自由,使里基陷入爱河,对女性有了不一样的认识。里基引用但丁《神曲》中引领仙子比阿特里丝,梅瑞迪斯笔下的女主角克拉拉·米德尔顿,以及《诸神的黄昏》中女武神布伦希尔德,盛赞不朽的女性将带领男性向前。然而,随着里基对阿格尼丝的深入了解和残疾孩子的出生,他意识到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为了对方而生,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走完最漫长的旅程,他们没有永恒的结合,没有永恒的拥有,但是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
“女性的价值和天赋,不管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文化建构的,在男性主宰的男权社会中,都被边缘化了。”[6] 福斯特小说一方面隐喻男性成为占有自然和支配自然的主体,另一方面隐喻男性成为占有女性和支配女性的主人,映射出自然和女性沦为无辜的受害者和被支配地位,从而降低身份堕为他者。
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中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的维度探讨女性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强调女性具有的母性有利于其与自然融洽相处,并有助于理解生命的诞生和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女性本身拥有的内在创造力量和女性精神生态的和谐,倡导建构女性关怀下的理想社会,促进女性与男性精神生态的和谐统一。诚如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所言:“性别的障碍,尽管在文明社会里逐渐削弱,仍是很高的,在女人那方面它就更高了。”[7]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受过良好的教育,精神世界丰富,思想独立,崇尚女权至上。她紧紧地把握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做着主人。如果男人是堡垒,女人就是山峰,她鄙视英雄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她保持着独立,这是多数女人都做不到的,爱情和婚姻改变不了她的性格。她爱着亨利,希望有一天把亨利改造成一个她心目中所期待的男人。“她知道了亨利不光彩的过去,但她选择原谅,依然接受了亨利的求婚。玛格丽特将联结的使命看做对亨利的救赎,希望通过婚姻来联结不同的民族性中的可贵品质。”[8]78庄园不仅仅是一处住所,也不仅仅是一处自然风景,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之所在。玛格丽特最终成为霍华德庄园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作为新女性,她需要把这种精神家园经营得更胜一筹。福斯特通过庄园这个象征符号,让玛格丽特担负起联结的使命,把社会的种种问题联结起来,展示给读者,这正是他的小说的高明之处。
《莫瑞斯》最为典型地表现了福斯特小说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莫瑞斯》是福斯特于1913—1914年创作的一部小說,是一部描写同性恋现象的爱情传记。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和他个人的顾虑,这本小说迟迟没有出版发行。福斯特自己生前对该作品的最后评论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所以,这部小说一直到福斯特去世的第二年(1971年)才得以出版。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一种另类,教义是明令禁止的。同性恋也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一种精神错乱,一种生态失衡。小说主人公作为性别男性的莫瑞斯实质上是一个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该小说主要描写莫瑞斯的两段与同性的恋情。一段是与剑桥大学同学克莱夫的恋情,另一段是与猎场看守者阿列克的恋情。背负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歧视,莫瑞斯与克莱夫相恋三年,然而这段恋情随着克莱夫与安妮的结合而宣告结束(莫瑞斯与克莱夫相恋,而克莱夫与女性结合,折射出莫瑞斯在内心深处的女性定位,暗合他作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客观存在,对男性的崇拜和爱慕)。这给了莫瑞斯沉重的打击,使他精神接近崩溃,产生精神生态的失衡和危机。“他考虑自杀的事情,……他对死亡本来就没有畏惧,……更不在乎使家族丢脸。……是否不如死了算了呢?……他会开枪自杀的……使他进入新的精神状态。”[9]然而,外祖父老有所成的典范给了莫瑞斯启迪。老人开导莫瑞斯要善良仁慈有勇气,用“内在的光”感染人。莫瑞斯随后确实变了,所起的变化说不上是皈依,但是他的确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决定找医生看一看。但是刚开始他内在的阴柔表现出他犹豫、矛盾、遮掩的一面,不愿意跟巴里医生说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崇尚阳刚之美。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向医生说出真相。巴里医生认为莫瑞斯是个正派人,不应该让自己的脑子里浮现这种邪恶的感觉,这是魔鬼的诱惑。巴里医生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充满权威的声音代表着传统观念对同性恋的申斥。遭到感情背叛的莫瑞斯来到彭杰庄园,认识了阿列克。阿列克来自中下阶层,阳刚淳朴,具有强烈的男性气质(再一次折射出莫瑞斯在精神层面的女性定位,又一次印证他作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自我认同,对男性阳刚之美的追求)。莫瑞斯狭隘的阶级意识使他觉得不能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所以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但是又无法忘却阿列克。肉体的欲望和精神的追求使他从懵懂的状态中解脱,产生顿悟,意识到阿列克才是他真正的爱人,随后二人开始恋情,产生精神上的欢愉,实现作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满足感。《莫瑞斯》“展现同性恋者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遭受的扭曲和孤绝,同时也把异性恋结构里关于欲望、性别与权力关系的问题以变形的方式复制出来。……福斯特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同性恋和异性恋和谐相处的社会。”[10]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莉莉娅在前夫查尔斯去世后,非常不受婆婆赫里顿太太的待见,于是随后的意大利之旅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让她感到轻松自如、独立自由。“但是在这里,在意大利,莉莉娅不管多么愚蠢任性,毕竟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11] 在意大利,她与作为意大利人的吉诺结为夫妻。她在骨子里十分崇尚英国式的家庭生活,两个人的家庭独立、和谐与秩序。然而她的丈夫,却经常不守家,彻夜不归,这让她失去生机与活力,郁郁寡欢。她也试图通过加入天主教堂来寻求精神寄托,但是看穿吉诺是因为金钱才与她结婚的真相,以及吉诺的不忠之后,她的精神家园慢慢失守,精神生态逐步失衡,渐渐走向悲剧的沙漠,直至精神之泉彻底干涸。这一点与《霍华德庄园》中的威尔科克斯太太的最后命运有异曲同工之妙。
福斯特的小说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方式向读者展示人类尤其是女性在精神生态层面出现的危机,“人性的极度扭曲导致精神的匮乏,信仰的不断缺失导致精神的困顿,爱与被爱能力的丧失导致精神的混乱。他认为人们只有重新认识自然,才能得返自然,回归初心本性,保持真我,实现身心和谐和精神生态和谐。”[12]
三、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中的哲学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凯伦·沃伦认为自然环境的恶化应该是女性关注的话题,人类与自然构成二元世界,人类是主体,是世界的中心,自然是客体,处于世界的边缘。男人与女人构成二元世界,男人是主宰,占绝对统治地位,女人是他者,处被支配状态。她进而深入探讨人类统治自然和男性统治女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薇拉·普卢姆德则认为人类与自然是统一的,男性与女性也是统一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失去一方另一方将毫无意义。人类理应扬弃世俗世界和传统观念中存在的一些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女性与男性、物质与精神、情感与理智等等,坚持把人类自身同外部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作为有机整体进行守正创新的研究,从而构成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实现三赢的效果。
《霍华德庄园》中的玛格丽特认为农村人和城市人作为自然人是和谐统一的,但是姐弟三人在会见巴斯特先生时,从他身上感受到农村人和城市人作为哲学人的二元对立,“文明把他们吸引到了城市,磨掉了他们肉体的活力,又没有让他们达到精神活力的境界。他身上还留有几分健壮的迹象,但是原生态的好样儿却是毫无踪影了。”[7]142玛格丽特认为文化是不可能让大多数人变得通情达理,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哲学的人之间永远都会横亘着一条宽阔深邃的鸿沟,多数竭尽全力跨越这条鸿沟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栽了进去。她知道这些人志向模糊、缺乏诚实、自满自大,因此,她力求站在男性与女性是统一体的立场,着力改造和拯救年轻人,随后对威尔科克斯先生的重塑亦是如此,从而实现男性与女性和谐辩证的统一,共同携手推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辩证统一,达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优化生存环境的目的。
《印度之行》中的阿黛拉与罗尼是一对恋人,作为自然人的他们在大英帝国的环境下接受传统正规的教育,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可以结合可以共存,所以两人相识相爱。但是作为哲学的人、独立的人,二者之间又是不同的,常有口角和争执,罗尼总是以男性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阿黛拉,而阿黛拉又鄙视大男子主义,不肯屈从于罗尼,致使二者之间已然存在的隔阂和鸿沟进一步加深加大。在一次出游过程中,由于汽车的颠簸,她的手触到他的手,然而,“两人都过于骄傲,都既没有将对方的手握紧,又没有抽回,一种虚假的浑融一体的感觉突然在两人心中产生,就像寄寓在萤火虫身上的亮光般微弱而又短暂。”[13]罗尼的傲慢自大、男性至上思想一步步将阿黛拉推向远方,二人都不需要爱情,直至二人最终分手,阿黛拉不愿臣服于罗尼,而选择呈现独立的自己。印度之行的种种经历尤其是马拉巴尔石窟之旅,让阿黛拉经历了满怀期待、精神震骇、自我重塑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实现从自然人到哲学人的转变。阿黛拉满怀期待地与莫尔太太来到印度,内心渴望看到并认识真正的印度及其文明。印度人热情好客地接待她们,安排举行桥会和马拉巴尔石窟之旅,然而,试图通过桥会联结彼此却没有成功,反而让她们对印度人留下不太美好的印象,尤其是马拉巴尔石窟之旅的结果出乎意料。莫尔太太感觉石窟简直令人恐怖,可怕的回声使她惊慌失措,几乎晕倒在里面,自此她心中憧憬的那个美妙的印度,那个她初次与阿齐兹相识的凉风习习的夜晚都荡然无存,也导致她未能实现自然人到哲学人的转变,最终在返回英国的途中死去。而阿黛拉则不同,虽然她在石窟里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可怕的回声使她惊慌失措,几乎晕倒在里面,自此她心中憧憬的那个美妙的印度,那个她初次与阿齐兹相识的凉风习习的夜晚都荡然无存,也导致她未能实现自然人到哲学人的转变,最终在返回英国的途中死去。而阿黛拉则不同,虽然她在石窟里也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可怕的回声刺激她的神经,使她惊骇莫名、心烦意乱,在幻觉中误认为阿齐兹试图侮辱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四处乱撞逃离石窟,并告发控诉阿齐兹,致使他被捕入狱。“印度文化促使阿黛拉的本能、热情和潜意识获得了不经意的释放,这种释放再加上她已有的情感困境,最终导致了她理智和秩序的休克。”[14] 但是所有人对阿黛拉的关心和体贴使她感觉到是她的罪过将一切事情变得更糟糕,可是理智再度苏醒,让她觉得又不是她的错,于是将她抛入又一轮毫无结果的思想斗争的轮回,幸运的是她最终撤回对阿齐兹的控诉,踏上归途,实现自我救赎,印度的一切在她眼前烟消云散,实现生命的一个转向和重返,在地中海的清澈澄明之中,她豁然开朗,看清看透一切,实现自我重塑!
福斯特的小说充满哲学的智慧和味道,他站在辩证的立场塑造其中的女性人物,一分为二地描写人物冲突,认为男性与女性既对立又统一,人类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因此,“人類只有容忍事物的多样性,承认女性和自然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地位,……男性和女性、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生。”[15]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女性问题,女性主义运动与生态主义运动完美结合是必然趋势,应该不断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女性的经济状况,充分发挥女性的能动作用,以保护女性合法权益、解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危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女性既是独立的存在,同时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常常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是和谐的结合体。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人类应该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关心自然呵护自然,自始至终关注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构建女性与自然和谐、女性与男性和谐,以及女性与自我和谐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福斯特小说表达了这一思想。
参考文献:
[1]陈英.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建构及其否定意义 [J].求索,2016(11):33.
[2]Janet Biehl.Rethinking Ecofeminist Politic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三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46.
[4]E·M·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M].巫漪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5]E·M·福斯特.最漫长的旅程[M].苏福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11.
[6]Sue Roe,Susan Seller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2001:212.
[7]E·M·福斯特.霍华德庄园[M].苏福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78.
[8]纳海.寻找英伦的神话:《霍华德庄园》中的“英国问题”和国民性[J].外国文学,2017(4):24.
[9]E·M·福斯特.莫瑞斯[M].文洁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46.
[10]朱姝.《莫瑞斯》中的同性戀话语权力分析[J].南方论刊,2014(1):62.
[11]E·M·福斯特.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M].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9.
[12]刘知国.论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中的生态思想[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56.
[13]E·M·福斯特.印度之行[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6.
[14]刘知国.印度之行,交往之旅[J].黄山学院学报2010(2):70.
[15]王敏,申富英.从“二元对立”到“和而不同”:对《幕间》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解读[J].外语教学,2019(4):108.
Exploration on E·M·Forsters Novels in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LIU Zhiguo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m Theory, the paper explores Forsters novels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ultural eco-feminism, spiritual eco-feminism and philosophical eco-feminism,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authors ecological thought which is to construct a shared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are in pursui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woman and nature, woman and man, woman and herself.
Key words:cultural ecofeminism; spiritual ecofeminism; philosophical ecofeminism; Forster's no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