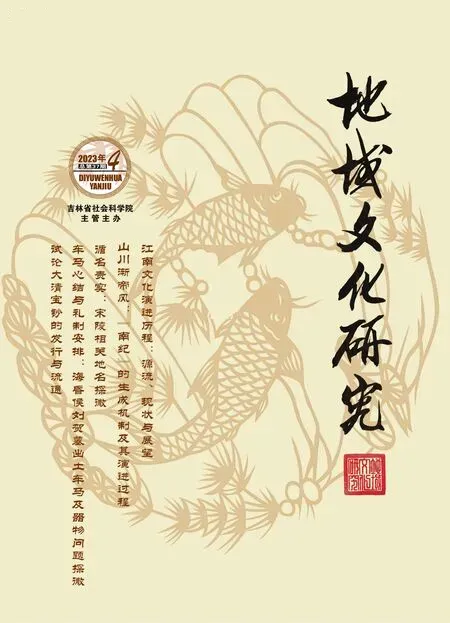鞌之战爆发原因与所涉地名考证
刘爱敏 徐 芳
鞌之战是鲁成公二年(前589)齐国与晋、鲁、卫、曹四国组成的联军在今山东济南一带展开的一次著名战役,这是齐国在霸业衰落之后的一次图谋复霸,结果大败,被迫向晋国献出宝器和土地,返还鲁、卫侵地,晋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加强。齐国并未服气,齐灵公时,齐晋又爆发了平阴大战,齐国同样大败。鞌之战,是齐国挑战晋国霸主地位的第一次试探,对齐国至关重要,传世文献《左传》《国语》《史记》《公羊传》《穀梁传》对此皆有记载,但彼此之间在时间、人物、地名上多有差异。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亦记有此事,学者对《系年》已有释读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67页。,对《系年》中的郤克聘齐和鞌之战问题亦进行过论述②如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代生:《从郤克使齐看史事的书写与传承——清华简〈系年〉与古书对比研究之二》,《海岱学刊》2016年第2辑;马建伟:《清华简〈系年〉所涉齐鲁地区古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申超:《清华简与先秦史事探研》,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等等。,本文则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着重对鞌之战爆发的原因和所涉地名进行考证。
一、鞌之战爆发原因
鞌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齐国在霸权衰落之后,不甘心服从于霸主晋国的统治,一直图谋恢复中原霸主地位。齐桓公死后,齐国经过了五子争位的乱局以及孝公、昭公、懿公、惠公陆续执政后,到了齐顷公时期,国力逐渐恢复,齐国便伺机挑起事端。战争的导火索,据《左传》所载,主要包括四件事:郤克聘齐受辱、晋执齐大夫、晋伐齐,以及齐与鲁、卫战,鲁、卫请师于晋。其中郤克聘齐受辱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开端,因为郤克在聘齐中受辱,才有断道会盟中晋执齐大夫,以及第二年的晋伐齐;因为晋伐齐,结果又招致了齐侵鲁,卫救鲁,最后鲁、卫、曹与晋联合伐齐,导致鞌之战爆发。
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对鞌之战前后事件的记载是:
晋景公立八年,随会率师会诸侯于断道。公命邭(驹)之克聘于齐,且召高之固曰:“今春其会诸侯,子其与临之。”齐顷公使其女子自房中观邭(驹)之克,(驹之克)将受齐侯币,女子笑于房中,邭(驹)之克降堂而誓曰:“所不复訽于齐,毋能涉白水!”乃先归,须诸侯于断道。高之固至莆池,乃逃归。齐三辟(嬖)夫南郭子、蔡子、晏子率师以会于断道。既会诸侯,邭(驹)之克乃执南郭子、蔡子、晏子以归。齐顷公围鲁,鲁臧孙许适晋求援。邭(驹)之克率师救鲁,败齐师于靡笄。齐人为成,以鶾骼、玉筲与淳于之田。①文本依据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67页。引用时采用了宽式文字,古字直接写成了释读后的今字。
邭(驹)之克,即郤克。本段引文主要内容包括约盟、郤克聘齐受辱、齐大夫盟会、靡笄之战及战后赔偿五部分。
记载鞌之战的传世文献有7 种:《春秋》三传、《国语》,以及《史记》之《齐太公世家》《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为便于论述,摘录各文献的记载如下:
《左传·宣公十七年》: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孟,高固逃归。夏,会于断道,讨贰也。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南郭偃于温。
《左传·宣公十八年》:十八年春,晋侯、卫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齐侯会晋侯盟于缯,以公子强为质于晋。晋师还。蔡朝、南郭偃逃归。
《左传·成公二年》: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②以上三段引文分别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71-773页、第777页、第786页。
《国语·晋语》:郤献子聘于齐,齐顷公使妇人观而笑之。郤献子怒,归,请伐齐。③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0页。
《史记·齐太公世家》:(齐顷公)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晋,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97页。
《史记·晋世家》:(晋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九年……晋伐齐,齐使太子强为质于晋,晋兵罢。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隆。鲁告急卫,卫与鲁皆因郤克告急于晋。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7-1678页。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使郤克来齐,夫人笑之,克怒,归去”一句,在鲁宣公十七年、齐顷公七年、晋景公八年;“(晋)伐齐,质子强,兵罢”一句,在鲁宣公十八年、齐顷公八年、晋景公九年;“齐取我隆”在鲁成公元年。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0-621页。
《公羊传·宣公十八年》: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
《公羊传·成公二年》: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④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288页、第2290页。
《穀梁传·成公元年》:冬,十月,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⑤《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417页。
把清华简与以上7种传世文献相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聘齐的时间、人数以及被讥笑的原因记载不一。对聘齐时间,《左传》《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所载都是鲁宣公十七年、齐顷公七年、晋景公八年,即公元前592 年;《穀梁传》为成公元年,即公元前590年;《齐世家》为齐顷公六年,即公元前593年。对聘齐人数,《左传》《齐世家》记载只有郤克1人;《公羊传》为晋使、鲁使2人;《晋世家》为晋使、鲁使、卫使3人;《穀梁传》为晋使、鲁使、卫使、曹使4 人。对使者被讥笑的原因,《系年》说“郤之克将受齐侯币,女子笑于房中”,《左传》说“郤克登,妇人笑于房”,《齐世家》说“郤克上,夫人笑之”,三者皆未说郤克有生理缺陷;《晋世家》则说“郤克偻”;《穀梁传》为“郤克眇”,《公羊传》则笼统地记述为“客或跛或眇”。
第二,讥笑使者的女子其身份、所处地点亦互有抵牾。
关于女子的身份,清华简《系年》记载为“女子”,《左传》《国语》为“妇人”,《齐世家》为“夫人”,《晋世家》为“齐顷公母”,《公羊传》《穀梁传》则皆为“萧同侄子”。“萧同侄子”之名,当源于《左传》所载郤克在鞌之战后点名要求萧同叔子作为人质。通过比较可见,较早的文献《左传》《国语》《系年》并没有直接说讥笑郤克者就是萧同叔子。因此有学者撰文说讥笑郤克者并不能断言就是萧同叔子,晋人之所以要求萧同叔子作为人质,也许郤克并不知道哪位女子讥笑了他,因为萧同叔子作为国母,其地位最高,所以以她做人质,才能发泄愤恨,以雪前耻⑥申超:《清华简与商周若干史事考释》,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8页。。当然,这种论断也只是一种推测。
女子所处的地点,《左传》《系年》皆为房中,《晋世家》为“楼上”,《齐太公世家》为“帏中”,《公羊传》为“踊于棓”,《穀梁传》为“处台上”。
第三,齐大夫被“执”还是被“杀”?《左传》的记载是高弱逃归,晏弱、蔡朝、南郭偃三人被执,后来三人皆逃回齐国。《齐太公世家》则是“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四人皆被杀,这与史实不符,因为《左传》襄公二年(前571)还载有晏弱灭莱之事。
第四,齐侵鲁时间,以及所围鲁邑之名是“龙”还是“隆”?《左传》记载为“(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皆作“隆”,且《十二诸侯年表》围隆时间为成公元年(前590),与《左传》所记成公二年(前589)不同。
上述各文献之间的差异,可参见表1如下:

表1 各传世文献记载差异统计表
总结以上论述,郤克聘齐的时间有齐顷公六年(前593)、鲁宣公十七年(前592)、鲁成公元年(前590)之别,出使齐国的人数有1、2、3、4人不同,使者被讥笑的原因不明,或跛或眇或根本没有点明有生理缺陷;讥笑者从女子、妇人到夫人、齐顷公母、萧同侄子,身份也逐渐变化;女子所处的地点由房中,到帷中,再到楼上、踊于棓、处台上,不断转移;齐大夫由被执到被杀;齐侵鲁的时间和所侵鲁邑地名亦皆有不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抵牾呢?首先,后出文献《史记》《公羊传》《穀梁传》在试图解释始出文献《春秋》和《左传》中,不断添枝加叶。因为《春秋·成公二年》载有“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5页。一事,所以《穀梁传》就出现了四国使者出使齐国共同受辱之事,解释了四国同打齐国的原因。《左传·宣公十七年》有“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的话,所以《史记》《公羊传》《穀梁传》就杜撰出郤克有生理缺陷。那么,郤克到底有没有生理缺陷呢?早出文献《左传》《系年》《国语》都没写。试想这些人都是朝中重臣,或出使别国,参与外交,或驰骋战场,奋勇杀敌,怎么可能或跛或眇呢?即使有,也应该不严重。因为《左传·成公二年》记有“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两句话,所以《晋世家》《公羊传》《穀梁传》就出现了齐顷公母萧同侄子讥笑郤克之事,为描述得更加具体,更杜撰出了“从楼上”“踊于棓”“处台上”等不同地点。
其次,史学家自身未细审史料而出现错误。出使齐国的时间、鲁邑地名“龙”与“隆”的不同、四使者被杀这些错误的出现,皆属此类。尽管中国古代史官一直自觉地秉持着“实录”精神,但在撰述史书中如何践行这种精神却是对史官能力的最大考验。始出文本往往过于简略,史家又不能一一调查核实,因此出现错误是难免的。
另外,史官个人风格对文本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司马迁对先秦材料作了通俗化、形象性的处理,他将《左传》艰深难解的语句转化成了通俗白话,增加了对话,使文章可读性增强,但也开始失真,时间、地点、人物皆有错误,但基本上并未有主观杜撰。而到了《公羊传》和《穀梁传》,作者便开始虚拟情节,不顾史实。《公羊传》作者就把逢丑父写死了,且还模拟出他临死前的一段对话:
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斩。”于是斩逢丑父。①《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290页。
这段对话解释了逢丑父与齐顷公交换位置后没被认出的可能,以及齐顷公能逃脱的原因,有点东野人之语的味道。如果晋国司马韩厥本就不认识逢丑父与齐顷公,还有必要交代两人面目与衣服相似吗?齐顷公被逢丑父第一次指使取水后,没有借机逃跑又返回来了,被再一次指使取水时才“佚而不反”,令人哭笑不得。《公羊传》和《穀梁传》还杜撰出了晋、鲁使者倚门交谈、移日乃去的情景,以及齐人对此事的议论:
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公羊传》)②《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290页。
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传》)③《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417页。
从《左传》《国语》《系年》,到《史记》,再到《公羊传》和《穀梁传》,我们发现史书的文本有一个“层累”生成的过程,就像滚雪球,越往后,细节越丰富,但离真相也越来越远,可信度也越来越低。所以最初的文本才是认识的基础,我们要了解事实真相,应从最早的文本入手。
二、鞌之战所涉地名
鞌之战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原文如下:
(晋)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师陈于鞌……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齐侯免……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0-800页。
上述一段文字提及的地名有11个:莘、靡笄、鞌、华不注、华泉、徐关、石窌、丘舆、马陉、爰楼、汶阳之田。其中“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一句中的“地”,未指出具体地名,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正好记载了此地名,曰:“齐人为成,以鶾骼、玉筲与淳于之田。”则此地为“淳于之田”,弥补了《左传》的不足。这样,加上“淳于之田”,鞌之战共涉及具体地名12个。下面我们对这12个地名逐一考证,落实其地理位置。
1.莘
莘有五地:(1)古莘国,又叫有莘、有莘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0页。;《墨子·尚贤中》篇“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③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8页。;《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作“有侁氏”④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0页。;《汉书》之《古今人表》和《外戚传上》作“有㜪氏”或“有㜪”⑤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84页、第3933页。,莘、侁、㜪字相通。夏、商、周皆有古莘国,如《大戴礼记·帝系》“鲧娶于有莘氏之子”⑥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页。;《左传·昭公元年》“商有姺、邳”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6-1207页。;《诗经·大雅·大明》“缵女维莘”⑧《毛诗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508页。。有莘之虚在今山东省曹县北18里莘冢集。
(2)蔡地。《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杜预注:“莘,蔡地。”⑨《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766页。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境。
(3)虢地。《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⑩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2页。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峡石镇西15里有莘原,即此莘地。
(4)卫地。《左传·桓公十六年》:“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杜预注:“莘,卫地,阳平县西北有莘亭。”[11]《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758页。《史记·卫康叔世家》:“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1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93页。则莘在齐、卫两国边界上,即今山东省莘县城北12里辛庄村。
(5)齐地。鞌之战爆发前夕,晋国出兵,在莘地追上了齐军。杜预注:“莘,齐地。”[1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894页。此莘当与卫国之莘为同一地,在齐、卫边境,盖此时被齐所占领。
2.靡笄
齐地山名,鞌之战开始前,晋师驻扎在此山之下,齐侯派使者到此向晋军请战。《左传·成公二年》载:“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杜预注:“靡笄,山名。”①《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894页。关于靡笄山的地理位置,有多种解释:
(1)历山,即今济南市南的千佛山,因《史记·晋世家》记载有“晋平公元年伐齐,战于靡下”,持此论者认为“靡下”即是“靡笄之下”,靡,当作“歴”(历),靡笄山就是古之历山、今之千佛山。
(2)今济南东北部的华不注山。元代于钦《齐乘》解释“华不注山”曰:“《左传·成公二年》鲁季孙行父帅师会晋郤克,及齐顷公战于鞌。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又云从齐师至于靡笄之下,逢丑父与公易位,使公下如华泉取饮。则此山亦名靡笄。”②(元)于钦撰,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齐乘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6页。
(3)今济南西部槐荫区的峨嵋山。《金史·地理志》载:“长清。有劘笄山、隔马山、黄河、清水。”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页。劘笄山,即峨嵋山,形似眉黛,状如曲笄。今山上犹存康熙二年(1663)石碑,上刻有《重修靡笄山碧霞宫碑》碑文。
(4)今济南西南长清区境内的开山。持此论者认为靡笄之“笄”应是“开”,形近而误,靡笄山,简称为开山④黄铭:《春秋列国地理图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63-64页。。
根据《左传》所记“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师陈于鞌”,则晋师从西来,壬申、癸酉一日之差,靡笄与鞌两地当相距一舍三十里左右的距离,而峨嵋山,正在鞌山(今千佛山西南3公里)西约三十里处。峨嵋山,原属长清,后归槐荫,西周时属祝国,距离西南方向的祝国古城(今尚存遗迹,即济南槐荫区之古城村)1公里左右,是齐国通向晋、卫、鲁等国的西南门户。而另外三种说法,千佛山、华不注山或在鞌之东,或在鞌之北,皆与晋军自西或南来的方向不合,而开山离鞌地有60多公里,与一天的行军距离相差较大。因此我们推定,靡笄山最有可能为今济南市槐荫区的峨嵋山。
3.鞌
鞌之战的主战场,齐军与晋、鲁、卫、曹四国联军在此展开大战,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马鞍山一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鞌,同鞍。鞌即历下,在今济南市西偏。”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1页。鞌,即济南马鞍山,古今学者对此多无疑义。济南千佛山西偏南约3公里有马鞍山,正是从西南方面进入济南的通道。
4.华不注
又名华山、金舆山,地处济南市东北角,位于黄河以南,小清河以北。在鞌之战中,晋国司马韩厥追逐齐顷公,三周华不注。《水经注·济水》曰:“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0页。因为此山“孤峰特拔”,故可绕行三圈。“华不注”之义,历代文人多认为“华”即“花”,“不”即“跗”,“华不”即花蒂,“华不注”意思是“花蒂注于水”,而当地老人却通常认为“华不注”是“花骨朵”的谐音。花蒂不是液体,何以要用“注”字?再说,山的得名,一般是因为山的形状像某种东西,如老虎山、峨嵋山、马鞍山等,简单直接,通俗易懂,“花蒂注于水”不符合这种命名方式。从音韵学的角度说,“华不注”是春秋时期的发音,上古声母有两个规律: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是说上古时期的唇音声母中,只有双唇音b、p、m,而没有唇齿音f;古无舌上音,就是说上古时期的舌音声母系统中,没有舌上音声母zh、ch、sh,而只有舌头音声母d、t、n。“华不注”三字,在上古时期应该读作“花不朵”或“花不嘟”,就是山东方言中的“花骨朵”。而华不注山的形状的确像花骨朵。所以老济南人的解释是合理的。
5.华泉
华不注山下的泉水,又名华水。齐顷公的车“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韩厥追上了齐顷公,车右逢丑父让齐顷公下车取水,才使得齐顷公趁机逃脱,危急关头,避免了国君被俘。《水经注·济水》曰:“山下有华泉。故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华泉,华不注山下泉水也……即华水也。北绝听渎二十里,注于济。”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0页。华泉北流注入济水,古济水河道即今黄河河道。
6.徐关
齐地关隘。鞌之战失败后,齐顷公自此关口逃回国都临淄,见保者,勉励其守住城门,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孝妇河西岸。此地东侧有孝妇河自西南流向东北,其东西两面分别为昆仑山与蒲笠顶山,地势扼要,齐国于此设关,为齐都的南面屏障。徐关应是齐长城最早建立的关隘之一。长城是在各关隘的基础上联结而成。
7.石窌
春秋时期齐顷公赏赐给锐司徒之妻的封地。齐顷公在鞌之战后逃回国都临淄,路上碰到锐司徒之女,此女子一问国君,二问其父,齐顷公以为有礼,遂把石窌赏赐给了她。杜预注:“石窌,邑名,济北卢县东有地名石窌。窌,力救反,一音力到反。”③《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895页。窌,音līu。济北卢县,在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二十五里归德镇卢城洼,靠近黄河东岸。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认为石窌在长清县,曰:“石窌,齐地,在今山东长清县(区)东南。”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6页。齐顷公遇到锐司徒之女,是在从徐关(今淄博市临淄区昆仑镇)到国都临淄的途中,那么此女子也应住在附近,为什么齐顷公赏赐给此女子的封地远在长清呢?因此,石窌不应在济北卢县(济南长清)。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西南多有以蹓命名的地方,而长清境内却无。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有白石磂村,在淄河流域太河水库西,在徐关(今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东南22公里,与徐关夹孝妇河东西对望,此地盖即石窌。
8.丘舆
其地有三:(1)郑邑。《左传·成公三年》载“三年春,诸侯伐郑……败诸丘舆”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2页。,在郑国东部。(2)鲁地。《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司马向牛“卒于鲁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舆”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88页。,在今山东费县西。(3)齐邑。此次战争“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即此。杜预和杨伯峻等历代注家皆指出丘舆为齐地,但其地不详。笔者把它定位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西南,具体位置当在博山区东、淄川区南、淄水西岸。之所以如此定位,基于两个坐标:首先,其与马陉同在淄河西岸的西南—东北一线上,晋师是沿淄河河谷的西侧进入临淄的;其次,丘舆与徐关都是自南部博山区进入临淄的出入口,在东西方向上,应与徐关大体一致。这样纵横两个坐标便大致确定了丘舆的位置。
9.马陉
春秋齐邑名,一名弇中谷,即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和镇马陵村,在太河水库东、徐关东南,距徐关(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30公里。《左传·成公二年》“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即此。《史记·齐太公世家》讹作“马陵”,作“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97页。。今尚有城址可证,其东村为东马陵,其西一村为西马陵,城址居其中。
10.淳于之田
最初是春秋姜姓小国州国的都城,春秋初年州国被杞国所灭,杞人迁都淳于,淳于又成为杞人之都,在今山东省安丘市东北三十里。《春秋·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句,杜预注:“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④《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724页。《左传·桓公五年》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杜预注:“淳于,州国所都,城阳淳于县也。”⑤《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749页。《括地志》认为:“淳于国城在密州安丘市东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国也。《春秋》‘州公如曹’,《传》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经》云:‘淳于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淳于国也。’”⑥(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8页。杨伯峻也认为淳于在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三十里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页。。鲁成公二年(前589),齐国在鞌之战中失败,把淳于之地送给了晋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又载晋人率领诸侯城杞之淳于,说明此时淳于又回归杞人。淳于城的归属变迁是:州国—杞人—齐人—晋国—杞人。淳于何时由杞人转移到齐人手中,史料阙如,暂且不论。
11.爰娄
《春秋》经作“袁娄”,《左传》与《穀梁传》并作“爰娄”。齐地,春秋鞌之战后,晋、齐在此盟会,商讨战后事宜。《穀梁传》曰:“爰娄去国五十里。”⑧《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418页。其地当在齐都之西,今临淄区齐都镇西。
12.汶阳之田
汶阳,因在泰山之南、汶水之北而得名。汶阳之田非专指一邑,是对郓、讙、棘、阐、龟阴等众多城邑的合称。郓有三地:一为西郓,今山东郓城县,《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人执季文子,成公待于郓,此为西郓;二为东郓,今山东沂水县。《春秋·文公十二年》载“城诸及郓”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86页。,此为东郓,是莒、鲁所争者,此时入于鲁;三为北郓,即汶阳之郓,在汶水北,今山东东平县。讙,在今山东泰安地区宁阳县北而稍西三十余里,《春秋·桓公三年》:“齐侯送姜氏于讙”,杜预注:“讙,鲁地,济北蛇丘西有下讙亭。”②《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746页。棘,在今山东肥城市东南约七十里。阐,在今宁阳县东北三十里。龟阴,因位于龟山北面,故称,在今山东新泰市西南。此众邑皆在今泰安、肥城、东平一带。
汶阳之田本是鲁地,鲁僖公把它赐给了季氏,《左传·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79页。后被齐侵占,鞌之战(前589)后,齐国把它归还给了鲁国。《左传·成公二年》载:“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9-800页。第二年(前588),棘地人反抗鲁人,《春秋·成公三年》:“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左传》解释曰:“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杜预注:“棘,汶阳之邑,在济北蛇丘县。”①《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1900页。到了成公八年(前583),汶阳之田重归于齐,《春秋·成公八年》载:“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7页。定公十年(前500),由于鲁国在夹谷之会上赢得了胜利,齐国又把汶阳之田中的郓、讙、龟阴三邑归还给了鲁国,《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杜注:“三邑皆汶阳田也。”③《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147页。纵观整个春秋时期,汶阳之田一直是齐鲁两国的争夺之地。
根据以上所考定地名的地理位置,可绘制出齐、晋双方的行军路线图(图一)。

图一 鞌之战行军路线图
从图一可看出,齐、晋双方尽管是一逃一追,但双方的行军路线,在“三周华不注”后并不一致,齐国军队是沿着孝妇河西岸逃跑,而晋国军队是沿着淄河西岸追赶。这里又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齐顷公为什么不走济南至临淄的平坦大道,而是绕到山峦间的徐关进入临淄?是齐顷公慌不择路,还是因为山区更利于摆脱掉追兵,以防止晋师长驱直入国都呢?齐国境内无险可守,一旦进入齐国境内,国都就面临着被屠城的危险,齐灵公时期的平阴战役、战国时期燕国率领五国进入齐都皆是证明,所以齐顷公绕道徐关,借山区之险阻挡晋师追赶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晋师追兵为什么从丘舆进入齐地,而没有跟着齐顷公从徐关进入?考虑到齐顷公对保者说:“勉之,齐师败矣。”晋师很可能在徐关遭到了守城人的阻挡,所以才在徐关东边的另一个山口“丘舆”进入了齐地。
第三,晋军进入齐国的都城了吗?《左传》《国语》《齐太公世家》《晋世家》和《公羊传》皆未载,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也未载,仅《穀梁传》曰:“一战绵地五百里,焚雍门之茨,侵车东至海。”④《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2418页。考虑《穀梁传》晚出及文本层累形成的情况,这种记载大概不可信,是后人增加的。
通过清华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我们发现《左传》和《系年》是两个不同来源的文本,二者记载各有详略,互相补充。在爆发原因上,《系年》与《左传》最为接近,而与《史记》《公羊传》《穀梁传》相差较远。在地名上,清华简《系年》记有“淳于”一名,为《左传》所未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