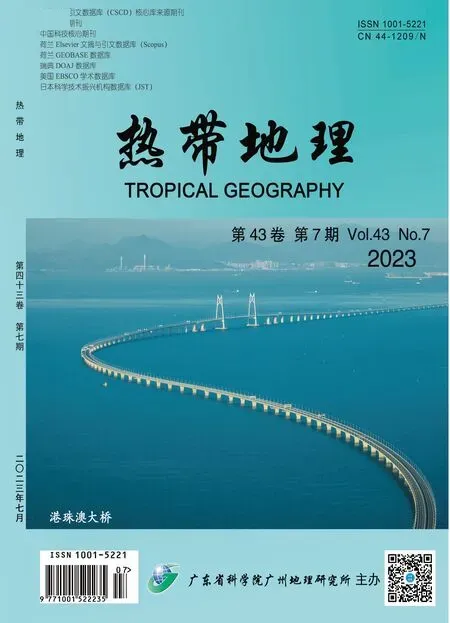地方餐厅的无地方性机理研究
——以广东河源客家菜餐厅为例
杨 亮,曾国军,张 杨
(1.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2.澳门科技大学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澳门 999078;3.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当今城市快速消费化转向,生产了批量的消费空间,加速了生活的同质化。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操控集中展现为消费空间对城市空间的操控,城市的商业化趋势加剧,标准化的消费空间形成(任政,2019)。同时,这也是一种去多样化和地方文化消弭的过程,无地方性景观在城市肆意扩张。城市正在沦为物质商品成批生产和大众消费理性化与自动化体系的牺牲品(戴维•哈维,2003)。地方和空间都具有尺度上的变化,地方餐厅是城市重要的消费空间,它以生产其所在地区的地域性食物为主,且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和历史延续性。作为地方菜烹制技艺与饮食文化生产和展演空间,地方餐厅承载了居民的地方记忆和情感。然而如同对城市其他地方的操控,商业化等力量也逐渐把餐厅变成了环境舒适但缺乏情感的消费空间。虽然产生了新的饮食文化,但是地方饮食被消抹了原初的痕迹,其生产过程及其包涵的种种社会关系,亦被逐渐解构,不见痕迹(陆扬,2009)。地方餐厅本应呈现的饮食文化趋于形式化。正如Kurtz 等(1973)所描述的无地方性餐厅:没有什么事物是能够焕发出自我魅力;这里简直就是平淡无奇……。你看见了这些东西,也听见和体验到了它们,但是你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和体验到……。在城市快速演变的宏观背景下,作为微观尺度的地方,地方餐厅为何在适应商业化、消费需求等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呈现无地方性,其与城市、社区、消费者的关系又发生怎样的变化,值得深思。
河源坐落于岭南山区,是客家人聚居地,被称为“客家古邑”。客家菜是河源的地方传统饮食,市内客家酒楼、餐厅众多。近年来,受城市化等因素影响,这个客家小城餐饮业悄然变化,客家饮食不断消逝、融合与创新,客家菜餐厅作为典型的地方餐厅在适应市场、平衡变与不变、地方性和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质。
地方餐厅是与居民日常消费、社会交往、情感体验等具身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场域,其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共生。既往研究对微观尺度场所的无地方性变化的过程性探索较少,多重视对物质环境和文化的无地方性表征分析,相对缺少对个体具身体验行为与无地方性关系的探讨。人对地方的体验是形成认同和意义的来源,而人对无地方性的具身体验也是其构建地方经验和认知的因素,对主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以河源市客家菜餐厅这一微观尺度的地方为案例,应用地方理论,反向分析其去地方化的过程:探索现代性力量如何推动该生活场所逐渐演变和呈现出无地方性,地方如何回应外界需求而衍生出新的发展路径。以期进一步拓展基于“人-物-地”关系的消费研究趋向,对无地方性理论提供有益补充。
1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后期,城市向郊区迅速蔓延,造成大量“媚俗”的标准化景观。由此,学界真正开始关注地方和无地方研究,并逐渐形成多个理论(爱德华• 雷尔夫,2021),一般认为主要分为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学派(周尚意 等,2011)。正统(科学)地理学属于结构主义学派,它把地方作为一个系统的、客观的、结构化的研究对象。而人本主义以现象学为基础,认为地方融合了人与自然的秩序,是人们直接体验世界的意义中心,充满了真实的对象和不止息的行动,它强调对于生存世界的直接经验与意识(爱德华•雷尔夫,2021)。段义孚(2018)认为地方是意义和价值感知的中心,人对地方有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依恋,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地方和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的载体和符号,即为恋地情结(topopphilia)。有学者认为地方的构成需更具包容性,应该包含客观和主观因素(Gieryn, 2000;孙九霞 等,2017)。Gieryn(2000)就认为地方应该包含地理位置、物质形式及其所含的意义和价值3 类要素。与之类似,Shelley 等(2003)提出地方三元结构理论,即地方包含区位(location)、场所(locale)、地方感(sense of place)相互关联的3个部分。区位指地方在系统中的位置、空间特征以及位置影响因素,反映了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区位对餐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餐厅的服务范围、对象以及关系,是经营者决策首要考虑因素。场所是社会关系建构所依赖的环境,是社会互动发生的物质性空间,它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工的。地方餐厅不仅具有物质环境特征,而且沉淀和容纳了丰富的社会关系,与场所的内涵高度契合。地方餐厅是物质消费空间也是情感体验场所,生产了地方感(杨蓉 等,2014)。地方感是人们对地方产生的排斥、喜好、亲切、依恋等主观倾向,聚焦于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连结(白凯等,2017)。地方感在时空维度上的差异体现为地方所承载的意义及其所具有的复杂性、深度和强弱变化。杨蓉等(2014)认为顾客在老字号餐厅消费体验中获得归属、认同等情感体验,并通过地方记忆和地方认同形塑怀旧的地方感。
地方若失去了意义,便不可避免地走向雷尔夫(2021)所谓的无地方性。Cullen(1971)认为无地方逐渐成为现实,多样化的景观和重要的地方正在消失,意味着我们自己也在遭受着无地方性的冲击,逐渐失去了原本具有的地方感。如果说地方蕴含着意义和情感,那么无地方性是以便捷和效率为目标,使地方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一化,意味着多样性和意义的消失。古典社会学家往往把现代性看作地方性的对立面,认为由现代性力量推动形成的均质化城市生活,导致了地方性的消逝(袁久红 等,2018)。快速城市化造成地方性消融正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造成了地方性社会面临地方意义的解体与认同危机,城市空间生产成为资本、权力和阶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Harvey, 1985)。袁久红等(2018)认为地方性正经历建设性破坏,这种破坏的力量来自新的生活方式、资本和外来文化,它们将“地方性”肢解为碎片化的记忆和乡愁。为了扩大市场,资本由权力协助在地方发展壮大,摧毁“一切地方限制”,不断创造均质化景观、标准化生产和无止尽的消费(孙邦金,2021;袁久红 等,2018)。流行的消费主义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异化,市场经济理论成为社会发展与组织景观的原则与方针。商业化、经营的同质化、连锁化对传统街区的地方主体形成挤出效应,加速了街区的无地方化(孙九霞 等,2017)。从本质上来看,地方感和地方依恋无法带来经济上的优势而被忽视,无地方性才是人们要去追求的对象,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空间效率(爱德华•雷尔夫,2021)。地方和社会屈从于技术、资本、经济与产业的体系,它们都是无地方的始作俑者(爱德华•雷尔夫,2021)。
相对于地方性研究,无地方性研究相对较少。Arefi(1999)重新回顾了地方相关概念,探讨了Agnew地方理论,即场所、区位和地方感的当代变化如何形成了无地方和非地方。总体上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地方性景观的去地方化,主要研究地方性景观的无地方性表征和原因,如孙九霞等(2012)分析了丽江古城族群文化的去地方化,燕海鸣等(2020)探索了哈尼梯田在国际话语体系下的去地方化,肖青(2017)和Sun(2018)等解读了少数民族文化“阿诗玛”的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现象,孙九霞等(2017)从制度脱嵌的视角解读了阳朔西街的非地方化;二是现代性景观的无地方性分析,如Penny 等(2009)分析了曼城足球场的流动性和无地方性,Birkeland(2008)研究了城镇的工业化和无地方性,蔡晓梅等(2016)探讨了高星级酒店的地方与无地方性构建,此外还有机场(Rowley et al., 1999)和 大 型 购 物 中 心(Shim,2014)等现代景观的无地方性研究。上述研究取得了诸多开创性成果,从不同维度丰富了无地方理论内涵。研究主要分析单个(如旅游)或多个(如制度、旅游、权力)因素对相对较大地理单元的无地方性呈现的影响。一方面相对缺少多维度与多因素相结合的无地方性分析;其次对微观尺度场所的无地方过程性探索不足;重视对物质环境和文化的无地方性表征,但缺乏对个体行为如情感、社交、消费等具身行为与无地方性关系的探讨。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看,地方具有个人主观性和情感性,在宏观区域演变背景下,对微观尺度场所的无地方性过程性探索可以清晰、直观地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机理。
无地方性的研究框架应以经典理论为基础,对微观尺度场所无地方性之形成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展开分析,同时研究框架应更具有包容性,既考虑物质性要素,也要纳入具身性要素。因此,本研究选择以Agnew 地方理论为基础,综合Mahyar 的无地方理论。Agnew地方理论被认为兼具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地方内涵,可以为现实场所的无地方性现象研究提供有效的解释,值得重新审视(爱德华•雷尔夫,2021)。国内学者已应用Agnew 的地方理论分析了怀旧餐厅、老字号餐厅、古城等不同地方的地方性构建,也有学者定量验证了该理论的部分内涵(杨蓉 等,2014;李凡 等,2015;白凯 等,2017;梁璐 等,2020),这些研究证实该理论适应于国内地方餐厅的地方性和无地方性研究。综上,本研究构建了地方与无地方研究框架,尝试分析城市空间和社会演变背景下,地方餐厅这一小尺度单元无地方性表征及其演变过程(图1)。

图1 地方与无地方分析框架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河源属于典型的客家饮食文化区。在客家人曲折的迁徙过程中,“吃”成为族群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饮食既吸收了南北方的饮食特色,又累积了各历史时期的饮食精髓,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东江客家饮食文化,成为粤菜的三大菜系之一。
1988 年,河源撤县设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几平方公里的古县城扩展成为建成区面积55.06 km2的现代城市。河源休闲旅游和餐饮业发达,地方餐厅具有鲜明的客家饮食文化特征,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和相对封闭性,使其适应外界变化而无地方性发展之过程尤为明显。研究者通过与资深餐饮从业者、美食达人和居民交流,以特色、知名度、代表性、影响力为标准,选取3家客家传统小吃餐厅(芳姨早餐、察记、然香)、4 家客家菜酒家(新升酒家、铭厨世家、幸福城食府、一方小院)和2家高档酒店的中餐厅(希尔顿酒店、翔丰国际酒店)作为调研案例地。其中7家地方餐厅主要包含了三种代表类型:从单体餐厅走向连锁化经营,代表了地方餐厅的标准化、连锁化发展;从古城街区搬迁到新城商业区,代表餐厅区位的变化;从传统饮食空间到现代性消费空间环境,代表场所的环境变化。即它们在区位、场所空间与环境、经营行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变化。其他2 家大型酒店的餐厅,主要作为本土餐厅的对比和参照系而纳入调研范围。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法。访谈对象包括3 类,第一类为餐饮从业者,包括老板、合伙人、管理人员、厨师;第二类为美食爱好者、旅游从业者、相关部门行政人员;第三类为本土客家人和外来常住居民。访谈和观察时间在2021年4—6 月,10 月补充调研2 人,共访谈24 人(表1),征求访谈对象同意之后对访谈过程录音,对从业者的平均访谈时间约57 min。实地观察了9 家地方餐厅,采用拍照和拍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其内外环境、菜单菜式、服务过程等信息,并在察记、然香、新升酒家、铭厨世家、一方小院、幸福城6家餐厅参与式观察餐厅的日常经营过程,并品尝了其特色菜式。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Table 1 Interviewees' basic information and interview situation
同时,从美团网、大众点评网、微博、携程收集上述研究对象的消费评价954条,剔除无关和重复评论后,得到评论317条,补充了访谈和观察资料。结合理论框架,对资料进行文本分析。
3 餐厅的无地方化展演与机理
3.1 区位的无地方性:从朴素区位到商业性区位的变迁
区位不仅具有地理、方位、经济的内涵,还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文化特征,能够彰显不同亚文化群体对环境和区间的区位价值响应(张中华,2012)。客家族群对区位环境有鲜明的认知观,并付诸实践。河源也称槎城,“槎”有木筏、树木的枝丫之意。因河源古县城被东江与新丰江环抱,三面环水,东西两侧为梧桐山和桂山,古城像漂浮的木筏,两条江犹如“丫”字,故称槎城,古城融自然风水于一体。另据《河源县志》记载:“河源本古越地,分野在牛女之间。”牛女属于古代天文分野中“十二分星”与“十二分野”组合之一(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可见河源古县城在规划选址和建造中体现了“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筑城理念。这种理念也表现在建筑的选址上,街巷的布局主要依从两江和两湖(鳄湖和西门湖)的走向,体现客家建筑背山近水的朴素理念。地方餐厅嵌入街巷之中,与居民楼、院落形成紧密、邻近性的区位关系。这种原发性的区位关系反映了客家族群的喜聚居、重血脉、围合向心的观念,其空间特性是地方性的表现形式。
这种状态在1988年发生巨变:国务院发布“关于广东省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函”,正式批准撤销河源县,设立河源市。新市区开工建设,进入建市发展阶段。随后几年,新丰江上架设了珠河桥、宝源桥、京九铁路,古县城与新丰江北岸半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彻底改变了老城历史上延续的区位。城市空间形态沿着小江桥—河源大道、珠河桥—中山大道、沿江路—大同路等快速拓展,餐厅逐渐沿着道路和居住区出现。珠三角的资本陆续进入河源,在景观突出的位置,出现了一些相对高端的酒店,如翔丰酒店、假日酒店、滨江金利酒店等,酒店的客家菜餐厅生意火爆。
“原来翔丰酒店周边还是荒地,农民就在那里放牛,桥修通后,位置很靓(好),有老板投资建了大酒店了。”——THF
“宝源桥没有修(之前),对岸一片都是山坡、水塘,后来桥通了,一下建了好几个酒店,假日酒店、滨江金利,我当时在那里做建筑工,旁边就变热闹了。”——HGQ
“我记得饭店都开得比老城的大,很气派,菜还是正宗客家菜,环境好,多了包房,大同路、河源大道那里比较多。”——ZHH
2000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与人口的增加,市政府编制总体规划(2001—2020),提出“强化中心城区建设,建设不同档次的居住小区,建立现代化交通系统”。河源进入新发展阶段,多条交通干线如越王大道、永康路的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空间。恒大、雅居乐、万达等外来资本与本土企业携政策红利建设了标准化居住区以及坚基、万隆、万达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共同推进城市生活和消费空间的快速演化(图2)。地点永远是一个相对于无限延伸的空间的“相对位置”(王天夫,2021)。在持续的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餐厅的区位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寻找优越区位,成为其提升竞争力及生存的砝码。

图2 河源城市发展阶段与部分饮食空间的区位Fig.2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location change of Heyuan City
“这两年周边(坚基—东江湾片区)新开了十几家酒楼,一个比一个装修的好,投资很大,人家肯定看好了这边的地段……,老城那边的有些早餐和宵夜还行,原来那些饭店搬走的搬走,关门的关门。”——LYP
“大同路原来的位置很好,靠近市政府,旁边是新丰江高喷(亚洲第一高喷泉),现在不行了,来的人少了,那里的饭店很难赚钱,找不到地方停车……”——CJC
“现在做酒楼与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好的(优越)地段要投很多钱,竞争大了,风险大。……大家(同行)平时没有什么好交流的,都是你不想(希望)我发财,我也不想你发财。”——LWQ
区位的物质空间特性与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不断地进行空间重组,构成了“区位价值”(张中华,2012)。行政力量和资本推动河源城市空间演变和区位价值重构,餐厅的区位价值要素中权力、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力增强,而人的情感、态度、地方知识的话语权弱化。餐厅与地方由自发、朴素、和谐的区位关系转向理性的商业性区位。餐厅基于资本和市场规则选取或竞争“合理”区位,其规模等级和空间布局均产生分化,区位原本附着的多元化价值和地方意义不断被消解和重构。
3.2 场所的去地方化:私密性与标准化空间的生产过程
3.2.1 从开放空间到私密空间的转换 场所的物质特征和其展演的社会关系是地方性的表现形式,去地方性不仅意味着场所物质特征的去地方化,更重要的是场所空间不能再生产稳定的社会关系。河源老城原地方餐厅作为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为居民面对面(face to face)交流提供了直接接触的机会。餐厅是居民生活空间的延伸,在这里他们吃饭、闲聊、打牌、交友。一个人可能与大部分前来吃饭的人相识、熟悉或有点头之交,餐厅充满市井气息。在频繁的社交中,餐厅成为具有情感认同和意义的地方。
“原来老城普通百姓吃饭的地方很多都是‘中伙’,地方不大,进门就是桌子,很少有包房,有些桌子支在外面,我记得那时候周边的农民都来赶圩(集),大家卖完土产(农产品)就会买一些猪肉啊、菜啊到中伙(中小型饭店)让老板加工,然后大家一起吃,很热闹。”——DYL
“周边的居民和餐馆的老板都认识,大家去吃饭,坐在堂里,很热闹,结账的时候,老板可以打折,有些人还会赊账,因为大家都比较熟,……,那时候的人也很朴实。”——YRX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隐私和个性化空间有越来越高的要求,经营者需在餐厅这个准公共空间中增设私密性空间才能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在开放空间内,物理屏障往往会形成一定的区隔,起着形塑空间形态的作用(朱伟珏 等,2019)。伴随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河源地方餐厅等级分化明显。从原来可以互相交流的准公共空间,通过隔断、屏风、包房、绿化、灯光等手段使之成为更加注重私密的半公共空间(half-public space),空间属性的变化体现了居民社交模式的演变。日常消费空间的物质环境,塑造了消费者的情绪(邓紫晗 等,2020)。现代消费者在安静、舒适的私密或半私密空间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环境比较舒服,灯光比较暗,氛围还是很舒服的。”——lovelyaiyou大众点评
“客人吃饭一般不希望被打扰,他们更喜欢包房,人少的话也会要求去包房,所以我们就布置了多个大小不同的包房,就算是大厅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让客人觉得有隐私。”——OWB
3.2.2 标准化的餐饮消费空间生产 标准化的全球力量对地方意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Arefi,1999)。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市场在城市中交叉整合,饮食消费更加务实(梁馨文 等,2021),促使商业化趋势加剧和标准化的消费空间形成(任政,2019)。
经历缓慢的发展期,在外地资本和管理进入河源之后,城市餐饮消费空间重构的尺度、速度显著变化,推动酒店餐饮业标准化、连锁化发展,制造了均质化饮食消费空间。2005年,外来企业投资建设翔丰国际酒店,成为河源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此后,假日酒店、滨江金利被评定为四星级酒店。外地资本投资的大型酒店还有汇景希尔顿、富朋喜来登、雅阁度假等,这些酒店都配备了中餐厅。调查发现汇景希尔顿酒店有全日制餐厅、轩悦中餐厅、逸·咖特色餐厅、溏吧,其中餐厅以客家菜、广府菜为主,设计和装饰豪华,酒店特意突出了餐厅的现代性和异域风格。
官网对轩悦中餐厅这样介绍:“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秉承健康、养生、创新的烹饪理念,为宾客提供传统的粤菜、客家菜及江鲜河鲜等特色美食。”
“逸·咖特色餐厅:“以乡村风格装饰为主,东南亚元素点缀,……,便捷时尚的五星级用餐体验。”
古典与现代风格和东南亚元素是酒店标榜的餐厅特色,网络评价的高频词是“豪华”“环境舒适”,但餐厅缺少河源地方文化元素,成为“其他城市”的餐厅和标准化的餐饮消费空间。城市高星级酒店从区位到设计、从产品到服务,重复着同样或标准化的布局和生产流程,进而塑造了一种不真实的地方,它与消费者非真实态度一起,完成了酒店空间的无地方建构(蔡晓梅 等,2016)。
这些大型酒店标准化、现代化的餐厅设计和服务对河源地方餐厅带来很强的示范效应。地方餐厅往往缺乏品牌意识,在空间营造方面,模仿进驻本地的大型酒店餐厅,且酒楼之间互相模仿,形成准标准化的布局方式:一楼为服务台、水产展示区、宴会厅和厨房,其余楼层为不同类型的包房,现代装饰风格,环境舒适、安全、私密。如新升酒家的宴会厅为河源流行的新中式风格,极为豪华,宴会厅有可移动的屏风,可以对空间进行区隔,这已经成为河源“标准”的酒楼样式。
“当时开业后,同行已经多次来暗访了,我自己都碰到几次,所以你看看现在新开的酒楼一个比一个有档次,很多都模仿我们,再晚几年我们也要升级才行。”——WAL
经营者用各种地方符号所拼凑的物质空间,已脱离了本土化本来的意义(梁璐 等,2020)。Kor‐telainen等(2021)也认为对原有地方文化符号及其蕴含的社会关系的剥离,将产生无地方性。一些地方小吃餐厅也通过循环投资,开始实施连锁化经营,如察记餐厅已经开了5家连锁店,并在环境设计和服务方面实现了标准化。
此外,传媒、流行时尚等因素引致消费行为呈现一致性。地方餐厅迎合了消费者的现代需求,但缺少对自身传统的深思和创新,无形中推动餐厅趋同化,形成“千楼一面”的景象,充满现代气质,但缺乏个性,生产了“无地方性的地方”。地域的本土和当地意义已经被渗透为一种标准化的产品”(任政,2019)。
“我们觉得没有太多必要去体现地方客家风格,我们的消费群体大部分是本地人,大家不太看重这些,另外去找人设计的话,成本很高,其实客家菜的净利润比较低,我们一般主推粤菜和海鲜,还是希望淡化客家风格。”—WAL
3.2.3 餐厅作为虚拟社交的资本:人地关系的虚无感趋向 现代人同时生活在实体和虚拟空间。网络社交中的饮食分享和互动,是对传统面对面共享美食进行情感交流方式的延伸(赵英楠 等,2014)。用手机拍餐厅环境、拍食物、修图、网络分享、社交互动成为“新式”餐前仪式。但网络社交挤占了面对面社交的时间和空间,对用餐环境、食物本身和网络中“他者”的关注替代了“面前的同伴”。通过对餐饮场所和美食的网络分享,完成虚拟社交和自我呈现。
调查发现,为了满足食客的“打卡”心理和虚拟社交需求,经营者在餐厅设计、环境氛围、菜品以及餐具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并根据不同的节日灵活调整,包括餐饮场所的不同空间,而不仅仅是菜品成为被包装和消费的对象。先进便捷的影像技术对食物画面细致、唯美的处理,通过微距细节拍摄、色彩和光线等要素的衬托,实现了“味道”的可视化(王斯,2018)。主题餐厅的饮食文化空间多是为迎合市场而进行的符号化生产,没有完成深层次的文化重构,致使主题文化的展演趋于商品化(曾国军 等,2015)。
“有些年轻人吃东西,不一定要求好吃,但一定要好看,环境要好,他们需要拍照发朋友圈或抖音。我们也希望客人这样做,帮我们宣传。现在我们这里有乐队表演,晚上的氛围很好,你看看周围这些盆栽、花卉都是我们专门到花木场挑选的,这个顶棚是可以移动的,晚上打开,就成了露天餐厅,很舒服,来晚了这里都没有坐位。”——GXB
“传统的客家菜就是家常菜,用大盘粗碗盛,不讲究装盘,现在借鉴粤菜的摆盘,漂亮多了,适合拍照。”——HZY
“听说日本有家主题餐厅布置了公仔,可以陪着客人吃饭,很有意思,我们也准备放一些,……,成为网红餐厅要有创意才行,那些老套的东西已经过时了。”——OWB
年轻食客们来餐厅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体验美食,更是为了把一个个餐厅和美食收集起来,成为网络社交和炫耀的资本。人们间接接触的普遍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曾经被视为地方性主要特征的社会联系和人-地纽带关系。这种转变对地方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Arefi, 1999),忽略了当下饮食社交中所要进行的情感交流(赵英楠 等,2014)。在某种意义上,餐厅成为取悦食客方便其开展虚拟社交的场所,一味对传统排斥,对流行事物追捧,在互联网加持下,生产了非真实的地方(inauthen‐tic places)(Arefi, 1999)。人对餐厅的认同是基于流行时尚,而非基于与餐厅的连续性关系和情感累积,人对餐厅的情感倾向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虚无感。
3.2.4 消费变迁逻辑下的餐厅食物去地方化 食物是地方餐厅的核心构成和地方性符号,对于旅游地来说,为满足游客对食物的地道性体验,地方餐厅会进行食物的原真性强化或再造。游客在原真性再造的循环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曾国军等,2020)。对于旅游城市来说普通居民和游客的饮食行为推动了食物的生产变化。
为了满足消费者饮食口味的多样化,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河源地方餐厅的客家菜逐渐淡化了其典型的“咸、香、肥”传统特色。笔者在幸福城食府等案例餐厅品尝部分客家菜整体感觉:盐焗鸡肉滑多汁、皮爽咸香;钵仔汤口感鲜嫩清甜;客家酿豆腐豆香浓郁,比较嫩滑;菜式的口感越来越接近广府菜的清、鲜、嫩、滑特质。可见,为了达到此类口感,客家菜融合了广府菜、潮汕菜等外来菜的烹饪技法。访谈内容和网络文本均显示居民越来越偏好“口味清淡”“健康”“多样化食物”,这使得餐厅菜式逐渐突破菜系和区域的边界。同时,餐厅也保留了客家菜“食材新鲜”“自然原味”的风格。为了满足新鲜、多样化食材的需求,餐厅扩大了食材的收集范围,跨区域、跨境食材采购已经常态化。此外,餐厅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口味需求,在客家菜的基础上,增加了广府菜、潮州菜、西北菜、川湘菜等外地菜(图3、4),并相应地在餐厅布局、装饰以及菜品装盘上减少了客家特征。地方餐厅在适应消费行为变化时,一方面保留了地方性基因的原真部分,并结合外来饮食文化,予以融合创新;另一方面,引入热门的外来菜,适当改良口味。所谓地道的客家菜在开放、流变的环境中不断演化,并引致了餐厅的地方特征、居民认同和地方感的变化。

图3 客家餐厅菜单(含客家、潮州、广府等菜式)Fig.3 The Hakka Restaurant Menu

图4 客家餐厅的外来菜——烤羊排Fig.4 Roast Lamb Chops in Hakka Restaurant
“市区的这些酒楼没有说全部是客家菜,基本上都融合了其他菜,正宗的客家菜只能去乡镇里找了,……,要赚钱的话,会搭配不同档次的菜,粤菜才能卖得出价……”——LH
3.3 地方感的变化:亲切经验弱化与情感非连续性
地方是具有意义的有序世界,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产生安全、熟悉、舒适、亲切、依恋的主观感受(段义孚,2017)。地方的价值是基于属于特定人际关系的亲切感,这种亲切经验是人们与地方建立安全感和依赖感的条件。地方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浪漫的、怀旧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方式,其形成需要时空的连续性(Arefi, 1999)。正如Till(2012)指出,城市作为生命体不仅是政治体或机能系统的隐喻,更是栖居者的持续场所营造。
亲切的地方经验往往无法用语言表达,但会铭刻在记忆深处,每当回想起它们的时候人们就会获得满足感。食物景观可以通过环境、功能和情感表征社会记忆(于雯静 等,2021)。河源老城的地方餐厅原本与街巷融为一体,居民和餐馆老板熟识,人们在这里不期而遇,轻松交流,在这里他们感到自然、舒服、亲切。餐厅虽然简陋,却承载了熟悉的味道,构成了居民街巷生活亲切经验,成为如段义孚(2018)所说的由人际关系所创造的亲切地方(created by human relationship)。
“这是一家邻家餐档,平凡普通却不失自己的特色。它没有很好的环境,人多时不免嘈杂,但却让平凡的一天充满活力。”
——拼命二千金-大众点评网
“做早餐说实话是做得开心,这个店87 年,我家公家婆(公婆)就开始做了,是传统(传承)下来的,我店里都是熟客了,他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来这里吃饭,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以前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的,现在他生了小孩,他也带小孩来了,爷爷带孙子来了,接着来吃这个味道。”
——YRX
一个人对餐馆的亲切经验意味着他对这里熟悉、信任、依赖,他在餐馆持续性地发展了人际关系,甚至可以把这里作为具有抚育意义的场所。在这里,居民把其生活历史中某些动人的过程、事件、情境捆绑起来,形成人地合一的整体意象,具有叠加在可见环境之上的过往记忆(王雪 等,2019)。
随着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围绕“物”产生的社交关系肤浅化,这种亲切感往往不断弱化或消逝。伴随原居民不断外迁,河源老城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客家人的生存场所转为低收入群体和打工者共同生活空间,餐饮场所也发生了转变。对于迁出的原住民来说,旧街巷成为一种怀旧场所。正如Marris(1986)所说,人们从习以为常的地方中被驱逐或迁出,对其生活意义是具有破坏力的,因为原有依恋关系难以在陌生环境中修复如初。对于大部分新生代客家人和定居河源的外来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不愿意和缺乏机会再与老街巷及餐饮空间建立联系。老城成为被忽略的、陌生的存在,他们的兴趣在现代化、时尚的餐饮商业空间。
“小时候经常走上城北直街的石板路、鹅卵石路,印象很深刻,现在变成了水泥路面,巷子里的客家传统小吃摊档和小餐馆都不见了。有钱人和年轻人都住到新城去了,现在很多打工的四川人住这里。”
——HYK
“去年,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整条街都刷白了(政府主导进行的旧城外立面改造),吃了多年的店换成了一家连锁麻辣烫,店老板一家也搬家了,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发展太快了,物是人非。”
——ZWF
“听说老板投了很多钱在新城开了几个分店,店装修得一样,服务员好多,原来店里的两个阿姨走了,现在这些人(员工)都不认识,好久没有见到老板和老板娘了,很多东西都变了,像一家新开的店一样,觉得有些陌生了。”
——XW
餐厅优质的服务并非产生亲切感的充分条件,亲切感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积累,重复性消费才能实现“简单暴露效应”(Mere-Exposure-Ef‐fect)。而地方餐厅不断更新或搬迁,加上流动的人口、餐厅服务人员的频繁更替、非忠诚的顾客、理性消费等使得主-客、人-地较难建立熟悉感和亲切感。
现代性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地方的情感依恋。城市更新、商业化、消费行为迭代、人口流动的速度远快于社会关系和地方感的重构速度。人们失去了去熟悉、去感觉一个地方所需的“慢”时间。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Agnew 地方理论为基础,综合Mahyar等无地方理论,以河源客家菜餐厅为例,完成了地方餐厅的无地方化机理构建(图5)。

图5 地方餐厅的无地方机理Fig.5 The Placelessnes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ocal Restaurants
1)政府通过区划调整、规划、制度变革等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启动了河源城市空间重构和商业化发展,是餐厅地方性演变的外在动力。区位是地方性的空间表征,河源传统餐厅的选址基于客家人空间环境认知,与居住空间形成了紧密、邻近的区位关系,隐含了主体的想象和情感,与社会、自然秩序耦合。政府和资本推动的城市空间易于流变,使得餐厅经营主体把区位作为竞争手段,区位的经济属性凸显,逐渐脱离于地方性的多元价值体系。
2)资本作为支配性力量,推进饮食消费空间生产和效率提升,决定了餐厅的价值。餐厅的区位竞争、环境营造、连锁扩张是资本的空间生产实践和创造需求的体现。
3)餐厅的空间性是饮食消费行为建构的产物,消费活动引导其空间的可视化表达和食物的生产,进而影响餐厅作为社交和情感体验场所的意义。随着消费行为变化,地方餐厅由日常性、亲切的场所成为舒适、私密、趋同的理性空间和虚拟社交的资本。居民对地方餐厅的情感变化,反映了人-物-地关系的调适过程。
4)市场规则与逻辑促使经营主体把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置于优先位置,盲目追求现代性,积极把地方餐厅整合进入现代餐饮系统之中,但缺乏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和挖掘。餐厅的商业性转向,使得消费关系表面化和不稳定,很难在餐厅生产连续性社会关系和情感,原有的人地情感趋于消逝,出现虚无感或无地方感。
地方呈现出多种尺度,尺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的意图、目的与关注点,建筑等微观尺度的感知单元,才能方便人们感知其独特性和真实性(爱德华•雷尔夫,2021)。本文主要贡献如下:1)在宏观区域发展背景下,从微观尺度的地方着手,探索现代性力量在区位、场所和地方感维度上推动形成的无地方性,拓展了基于“人-物-地”关系的消费研究。回应了新文化地理学对行为、场所、物质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消费研究动向(马凌 等,2019)。2)兼顾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分析架构下,完成了地方演化为无地方的过程性分析,即识别了无地方演化的过程,揭示了地方与社会经济文化相互构建的特质。研究有助于地方餐厅反思自身传统和发展路径,平衡餐厅的地方性和现代性关系;引导经营者重构与社区的联结,增加餐厅消费的社交价值,强化地方认同。地方餐厅作为消费和文化生产空间理应承担地方文化展演和教育责任,本研究对于城市地方性构建和文化消费空间塑造亦具有参考价值。
无地方之所以流行,自有其优势存在。而本研究并未对无地方性的优势进行分析,也未探究其他场域的无地方演变。其实地理单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地方只是相对的短暂停顿。地方性与无地方性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以难以数计的、矛盾性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张力,互相转化、共存融合(文彤 等,2020;爱德华•雷尔夫,2021)。有时候我们喜欢无地方性,有时候青睐地方性,如何把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服务于现代需求,还需立足实践深入思考。此外,日常生活场域与其他场域的无地方性演变规律差异也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