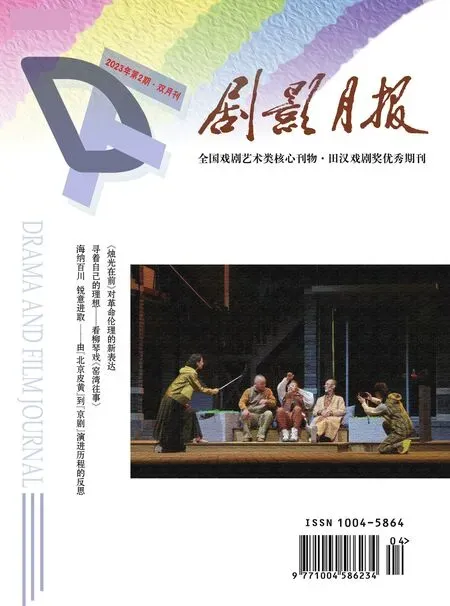从《网络迷踪》看桌面电影观影之变
■陈乐
电影是现实、幻想、梦境的三重奏:影像所呈现的现实、银幕所构筑的幻想、最终将观众带入想象的王国,为其打造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然而桌面电影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银幕电影所建构的想象王国,将观众再度拉回象征界,麦克卢汉曾做过一个比喻:媒介的内容好比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只留意到“肉”而放过了“窃贼”的人,是怀着“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在对待传统媒介时,我们常常将如何使用媒介以及媒介所呈现的内容视为至关重要的,却忽略了媒介本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仅仅留意到“肉”而放过了真正的“窃贼”是我们对待传统媒介时所采取的错误做法,这个生动的比喻警示我们应当将目光从单一的媒介内容转移到媒介本身。在桌面电影的研究当中,我们不容忽视的是“桌面”这种全新的形式所带给受众的全新体验感。
一、观影情境:从银幕到屏幕
吉尔·德勒兹在其著作《电影1:运动—影像》中提道:电影的力量在于电影过程与知觉思想之间的紧密结盟,电影不仅把运动置入影像之中,也把运动置入人脑之中。传统的银幕电影,将观众安置在电影院的座椅上,他们成为与婴儿无二的视觉能力早熟但行动能力并未完全获得的个体,被电影院的座椅所牢牢捆绑,影院之中仅有的亮光投射在银幕之上形成的图像便成为观众的感官汇聚之处,受众将自己代入其中,将银幕上完满的人物形象以及其所经历的奇特人生设想为自我,继发过程和现实原则在这里让位于初始过程和快乐原则。当影院之中灯光骤暗,影像投射于银幕之上时,这一场的“白日梦之旅”便开始了,所有的现实烦恼均被抛之脑后,影像此刻被深深地注入人脑之中,“想象的能指”所实现的观影者虚幻的完满感,主宰力和认同性,是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
屏幕的概念在当下主要指涉的是一些用于呈现彩色图像的电器,在手机、个人电脑等屏幕上观影,情境与银幕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不同于观众在影院时被座位所牢牢固定,在屏幕上观看影片时,没有固定的区域,区域是自由且随意的,观众可以随处选择自己的观影场景,且存在诸多的干扰因素无法使其如同“银幕前的婴儿”任其摆布。其次就时间来说,在电影院观众必须遵守约定的电影开场时间进场、退场,而在屏幕上,观众可以自如地掌控影片的播放时间,暂停或者切换。再次,影院在“钥匙孔的情境”之下,银幕成为唯一的光源所在地,观众的感官全部聚集于银幕,银幕界面的唯一和确定性与屏幕的多界面信息呈现形成了差异。从观众自身出发,时空的可选择、可切换,屏幕界面的不唯一性,观众成了屏幕的掌控者,其从银幕下被座椅捆绑的观众成了屏幕前主宰的智者,不再一味地沉浸于银幕世界所提供的幻想。他们已经从“具身化”感官化的被动观者变为“去身化”智性的主动观者。从银幕到屏幕的转变,使得受众的认知情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桌面电影以电脑屏幕作为镜头的拍摄对象,以桌面屏幕呈现的信息变化来完成叙事。在《网络迷踪》中,所有的故事都在桌面屏幕上展开,通过屏幕中诸多媒介呈现相关信息,帮助父亲找到了女儿并将事件的发展经过完整地呈现给观众。由于影片的叙事全部在电脑屏幕上展开,因此在电脑屏幕前观看成了最佳选择,影片在开始后的第一个镜头便是观众所熟悉的Windows系统的山水屏保,不少观众第一眼将其看成自己的电脑屏幕,而后出现的诸如待机画面暗示着危机的来临,无数跳出的弹窗,使得不少观众将其误认为自己的电脑屏幕,因此观众即便是在外部环境随意多变的情况之下,还得以轻松地进入“入片状态”。反观《网络迷踪》等桌面电影在院线上映时,不少观众第一感觉即是突兀,巨大的电脑屏幕投射在银幕之上,不同于以往熟知的视觉效果使得观众容易跳戏。桌面电影在屏幕前观看相较于传统的银幕下观看,受众的注意力被最大限度地吸引,同时其“视觉体验”也得到了满足。
二、感知方式:从白日梦的旅行者到文本的解码者
爱森斯坦在《蒙太奇论》中曾说道:在所有这些镜头之间相互作用、吸引、排斥中,为观众的眼睛寻找最佳路线,把这种大量的间隙精简为一种简单的视觉平衡,一种最完善的传递影片基本主题的方式。在爱森斯坦的理论之中,蒙太奇作为电影艺术的基础,被暴力地传递给了观众,当观众在影院坐下之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方式早已被设计,不论自愿与否,观众都将踏上这一趟“白日梦之旅”,成为想象王国的旅行者。传统银幕无论是观影情境抑或是影片文本本身都早已被设计好,观众在购买电影票的同时也获得“想象王国”的入场券。反观桌面电影,在观影情境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受众在感知方式上将会产生何种变化呢?
(一)心智游戏的参与感
影片《网络迷踪》的故事主轴简单且明确,即父亲寻找女儿的过程,然而通过多重悬念和反转的设置,这样一次极为寻常的女儿失踪的故事逐渐发展成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解除好友1》中故事开始于寻常的网络社交,即视频电话之中,然而由于神秘人“劳拉”的加入,事态逐渐地失去控制,参与者相继在“劳拉”的操控之下丢失性命。在影片之中,某些至关重要的信息被隐瞒或者模糊地呈现,观众成了游戏的参与者。不难发现,无论是在《解除好友》系列或是《网络迷踪》之中,桌面电影的建构均呈现出了某些“心智游戏电影”的特征。游戏化文本的建构,使得观众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获得类似于游戏的快感,这便是桌面电影在感知方式上给受众所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即心智游戏的参与感。分析《网络迷踪》的叙事结构,不难发现其与游戏时的闯关模式存在类似之处,即玩家获得信息开始行动、难度逐渐升级、玩家信息更新再行动的模式。托马斯·爱尔塞泽尔认为心智游戏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迷惑观众的乐趣,且总体上观众不介意被玩弄。相反,他们乐于接受挑战,解决难题。在游戏闯关式的叙事模式建构之下,观众不自知地便成为玩家,参与到影片设置的难题之中,寻找影片中被模糊化的关键信息。与传统银幕所建构的一系列心智游戏电影相比较,诸如《黑客帝国》《香草天空》等影片主要是让角色在多重空间之中来回穿梭,打破观众对于现实世界的固有认知,亦不同于《记忆碎片》《搏击俱乐部》中所建构的精神失常的人物形象使得银幕呈现其幻觉或是错觉。桌面电影立足于现实空间,建构精神正常的角色,“游戏”体验的获得以屏幕世界内多样化的信息媒介为渠道,辅之以多次反转的叙事,同时屏幕前观看的形式为受众提供了暂停、反复观看推敲的机会,受众在这种模式之中成了游戏的参与者。且由于“网生代”独特的桌面屏幕经历,他们得以飞快地适应这种“体系背后的迷宫通道和导航原则”,积极地参与到影片所设定的游戏之中,获得影片文本的信息,成为文本的解码者。
(二)一屏之隔的沉浸式体验
传统的银幕电影从生活之中提炼精彩片段,加之与现实本身无限的接近性使得观众沉浸于其中,因此再现现实成了影片拍摄时的首要目标,为此电影人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灯光、摄影、场景、剪辑、声音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缝合系统”,将观众缝合于其中。然而桌面电影在视听表现上与之大相径庭,其所营造的不再是一套又一套的“缝合系统”,观众的感知体验不再依赖于独特的光影以及缝合镜头所构建的真实可信的世界,不再通过架构还原时空的桥梁。通过屏幕,影片以一种镜面反射式的呈现方式以及主观视角直接让观众产生与角色仅一屏之隔相互对话交流的体验,观众形成了与角色宛如面对面的交流感。在这种镜像观看所形成的交流感以及屏幕所营造的一系列类似于“我看”“我想”的主观镜头,使观众获得了沉浸式的体验,这与传统的银幕电影所带给观众的体验形成了巨大差异。
1.镜像交流
镜面反射式表演是创作者在场,通过移动终端诸如手机、电脑等,进行自我拍摄的一种创作方法,观众在桌面电影中观看到的大部分的呈现方式都是镜面反射式的,主要有自拍和视频聊天两种方式。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媒介及屏幕充当了人的视知觉以及神经系统,将其延伸,视觉和神经系统启动了“接线程序”,看着屏幕之中的“他者”,观众与镜中的“他者”形成了一种镜像观看模式。当“他者”面对屏幕说话时,交流感也就此建立,这样,观众得以与“他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对“他者”所呈现的事物产生情绪。诸如在《网络迷踪》中通过Margot的社交平台所呈现的一系列其自拍视频,观众得以知道小女孩真实的心理感受和社交状态,同时也为观众参与到影片当中观察影片所透露的细节和疑点提供了情境。通过镜面反射式的表演,“缝合系统”已无处遁形,角色之间的对话、信息的传递不再通过正反打镜头进行表现,屏幕之上“缺席者”已然消失,这是桌面电影镜面反射式表演所带来的全新变革,正是在这种镜像观看当中,观众与角色之间得以建立强大的沟通桥梁,给观众营造了一种“交流”的假象。
2.情感传达
传统的银幕电影在其拍摄的进程之中,摄影、表演等多方面都必须以一个“缺席的在场”即将来观众的观看为前提,同时又务必充分地实践一个假定,并没有人在看,是故事在自行涌现,故事的自行涌现依赖于影片所构建的是时空、镜头之间的无缝组合,同时在人物视角上采用第三人称来讲述故事,或者虚拟一个人物讲述他的主观视角。这样的人物在影片之中是断然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的出现将会导致角色与观众的直接对视,观众将会瞬间从“想象王国”之中跌落。观众得以沉迷于影片之中,与影片建立情感沟通的桥梁均源于这些暗藏影片之中的“缝合系统”,然而桌面电影的情感传达完全有别于银幕电影,由于不在现实时空之中展开故事,因此它无须顾及时空的连贯性,角色开始直视摄像头,同时角色本身在影片之中又再度出现在屏幕上,在这一系列“破坏缝合系统”的操作之中,桌面电影的信息乃至人物的情感又是如何传达给观众的呢?这得益于桌面电影所提供的屏幕,以及屏幕之上呈现的诸如自拍、摄像头、视频等视角模拟人物的主观镜头,角色的内心状态、心理活动通过屏幕完美地呈现出来,完成了情感的传达。《网络迷踪》中,6分30秒处父女二人的聊天对话框呈现之初,伴随着大特写,Kim询问Margot是否忘记了什么,在6分40秒时转换成中景,屏幕的轻微抖动和起伏模拟角色的头部运动,在6分50秒之时,Kim等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删掉了对话框想给予Margot提示的想法,立刻发起了视频。在这短暂的20秒钟之内,观众不再需要通过演员的自白或者时不时插入的旁白来了解角色的内心状态,而是通过景别的变化,以及屏幕界面信息的呈现,角色的内心状态被完美地表现出来。影片的结尾段落与开头形成对称一般,父亲的主观视角再次呈现,94分钟30秒呈现大特写,而这次不再是怒气冲冲的父亲想找女儿算账,而是询问女儿的钢琴课是否有消息。94分45秒时转换成为中景,变成了女儿的主观镜头,通过景别的切换,桌面电影利用屏幕界面之间的相同性轻松地实现了主观视角的切换。钢琴课的重新申请,正视母亲的离世,父女二人的隔阂就此打破。通过开头结尾两次对称性的主观镜头的呈现,观众得以清晰地感知到父女二人之间的情感变化,以及角色们的心理状况,移情作用得以产生。
桌面电影通过构建一种游戏化的叙事,辅之以独特的影像,诸如镜面反射式表演和主观化的视角呈现,使得观众在远离电影院,摆脱一场白日梦之旅时,同样也产生移情作用的机制,从“旅行者”成为影片的“参与者”,参与到了这一场桌面游戏当中,成为文本的“解码者”。
三、信息传递:从现实世界到“赛博空间”
电影本身作为技术和工业资本现代化的一部分,在影像内容的建构上又无限趋近于现实——“电影媒体即是现实本身”,同时在影院内部真实的物理空间之中又创造了一个钥匙孔情境,传统银幕电影无论是从其产生条件、建构的机制还是影像本身都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众在现实生活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电影机构的影响,作为外部机器的电影工业,内部机器的观众心理学以及第三机器的电影批评、观念等,电影机构所创建的一种让观众自愿来影院的机制,均被部署在了真实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因此观众在传统影院之中银幕上呈现的内容来自现实时空,观众观影感的产生依赖于影院所提供的现实环境,影像呈现给观众的所有信息都依赖于现实的时空。然而桌面电影与银幕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让观众从现实世界来到了“赛博空间”,屏幕影像表现的是“赛博空间”,观众的信息接收途径是个人电脑屏幕,观众对于影像的认识不再基于现实世界和银幕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通过虚拟世界和屏幕二者之间的连接。
建构“赛博空间”这一概念最开始由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提出,其小说《神经浪游者》之中他提到一种存在高度交融性的信息媒介,这种媒介的产生来自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互联网的建立,他将通过这种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现实世界称为“赛博空间”。在“赛博空间”中呈现出许多完全不同于现实空间的特征,影像的建构不再依赖于光、影、声等现实因素,信息的传递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媒介。那么观众在“赛博空间”中又是如何获取信息的呢?当影像的呈现不再依靠于现实时空时,信息又是如何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之中传递的?
(一)“赛博空间”的畅游
在传统电影的创作之中,大多表现的是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之下涌现的故事,时空的同一性为叙事的真实可靠性以及观众与影片之间产生共鸣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然而在桌面电影之中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在二维显示屏之中通过多空间同一时间的组合弥补了二维平面所缺失的空间感。这种超时空的实现得益于“赛博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不同于其他的“自然媒介”,接收者必须使用视觉和听觉等感官系统来接收并且解码这些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何传统的银幕电影必须保证时空的同一性,只有在时空同一性的条件之下,接收者才可以通过视听等感官系统接收信息。其超越了“自然媒介”所带来的时空局限性,在“赛博空间”之中,声音、图像等信息可以被编码以及储存,不再需要通过“自然媒介”来进行传播,接收者可以随时徜徉在“赛博空间”中。“赛博空间”之中不排斥任何个体加入,为观众的畅游提供了条件,同时其裹挟着巨大的信息量将观众包裹,在《网络迷踪》中,通过被储存的声音、图像、视频等一系列包含巨大信息量的媒介,我们可以快速且清晰地了解到Margot一家曾经的情况,以及母亲去世后父女二人目前的生活状况。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跨越了10年之久的时间同时给观众呈现出了巨大的信息量,桌面电影在摆脱时空束缚的同时给予了观众直观可视的信息,使得故事的讲述更为可靠。而父亲也通过这个储存巨大信息量的“空间”,找到女儿Margot所储存的直播视频,带领着观众一步步破解谜团。受众被巨大的信息所包裹,同时在自身的意愿之下畅游于“赛博空间”之中。
(二)信息传递——虚拟主体
康德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黑格尔将主客体辩证统一起来,而在阿尔都塞的笔下,主体更是成为国家机器的驯服臣民。主体的概念历经了多年的演变到当下被认为“主体是社会存在和心理存在的统一体”。而虚拟主体的概念则可以理解为在由互联网所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之中进行“隐身交往”的主体。桌面电影之中角色身为“虚拟主体”,其实身体隐藏在文字、表情等符号之后,即便是在视频聊天之中,所呈现的身体,也不过是一种数字信息汇合。虚拟主体消解了恒定的主体,以符号来建构自身。譬如在《解除好友2:暗网》中,主角捡到了电脑,电脑的用户名是一个问号而密码也是,这一符号被主人公所破解,而真正的这台电脑的主人,一直戴着黑色的头罩在威胁伤害主角一伙人。被符号所代替的用户名,蒙面的威胁者,象征着在“赛博空间”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威胁,没有特定的指控对象,观众在观看此类影片时会不自觉地感受到来自这一虚拟空间的危害。与传统的银幕电影相比较,虽然观众在面对二者之时,都知道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在银幕之上所发生的离奇的、玄幻的故事,难以甚至无法找到在现实时空之中的对应体。反观桌面电影,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这些被演绎的故事在现实时空之中完全存在发生的可能性。《网络迷踪》中通过移动互联网寻找女儿的父亲,《解除好友1》中受到网络暴力的青少年们,《解除好友2:暗网》中不幸卷入暗网的人们以及维持并进行黑色交易的地下网络市场,这些都切实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存在着,即便故事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之中,接收这些信息的人不得不引起警觉。
通过对于桌面电影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桌面电影已经在审美机制、视听美学上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发展和有机联系的世界,而桌面电影所带来的变革使得我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再次发生了转向,桌面电影将触角延伸至无限宽广的“赛博空间”,为影像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美学形式,但是桌面电影的拍摄也表达了人类对于屏幕媒介的一种反思,当今绝大多数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可能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如果真如同布莱克所言,技术将人分割,成为人体器官的一种自我截除,人本身内在的东西得以外延、延伸,人终将会成为其外延物的傀儡。那么分析桌面电影之后,媒介本身作为一种信息,所反馈的社会现状和焦虑更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媒介本身对于人的催眠能够使人沦为傀儡,是桌面电影带给每个人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