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破晓
——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和早期研究
许渤松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一条起源于陕西西北白于山北麓、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这就是萨拉乌苏河,因河谷沿岸生长着红柳,又被称为红柳河。乌审旗境内的萨拉乌苏河由杨四沟湾、清水沟湾、滴哨沟湾、范家沟湾、邵家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杨树沟湾等8个沟湾组成,由于河流侵蚀下切作用强烈,河床深深嵌入高原之中,河流沿着狭长的深邃沟湾内曲折的河道蜿蜒流淌,形成了壮丽的沙漠峡谷景观。
一百年前,一名法国博物学家的到来使萨拉乌苏从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晚更新世动物群化石产地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蜚声海内外。他就是北疆博物院的创始人Emile Licent,中文名为桑志华。为了探索中国北方地区的地质和自然区系,寻找东亚远古人类可能存在的证据,桑志华于1914年3月来到中国。以天津为基地,在那个兵荒马乱、交通不便的时代,他经常只身一人在中国西北、华北及东北等地东征西考,白天探查采掘、摄影绘图,夜间则在微弱的灯光下奋笔疾书,记录所得。桑志华在25年间行程达5万公里,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

桑志华赴萨拉乌苏发掘执照

1918年的萨拉乌苏河(桑志华摄)
西部之旅,初探萨拉乌苏
1918年5月,在来华后的第五年,桑志华第一次踏上了萨拉乌苏这片土地。一开始,这只是他在1918年至1919年间持续达一年半之久的西部考察之旅中并不起眼的一段旅程。这次西行的主要目的是沿途采风、动植物采集和包括地貌、物候、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及与各地的天主教社团初步取得联系,为将来的科考工作打下基础。

旺楚克一家人合影(桑志华摄)
5月26日,桑志华第一次来到小桥畔天主教堂,并在附近一带的野外考察中发现“龙骨”,据其1924年出版的《黄河流域十年调查记》第686页记载:“……从地质学角度看,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带有许多化石。我在这里采集到了一些漂亮的标本,后来1922年我又在此工作,所采集的标本丰富了北疆博物院古生物部分的收藏。在南面的山里,化石也很多,但几乎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小型动物的骨架。……”
第二天,桑志华又在萨拉乌苏河下游再次发现含有化石的地层。此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该处地层的重要科学价值,不过由于当时没有做任何发掘准备,他只好暂时离开,留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回来发掘。此刻,萨拉乌苏已在桑志华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决定将这里作为今后发掘的重点地区之一。
收获满满,首次大规模发掘
桑志华再次踏上萨拉乌苏的土地已经是四年以后了。这期间,1920年夏季他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和黄土底砾层中发现了中国第一批有确切地层记录的旧石器,这个发现极大鼓舞了他,更加激起了他在中华腹地继续寻找远古人类遗迹的愿望;随后,桑志华在1921年3月发表了《召告传教士以及有关采集与寄送自然史物件之说明》,建立起以中国北方各地传教士为主要成员的高效标本搜集网络。
1922年5月末,桑志华开始着手进行赴萨拉乌苏发掘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重要的是解决了发掘的通行证和执照问题。6月19日,他从天津出发,穿越山西北部五台山、宁武森林一带,到达陕西榆林地区,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7月30日傍晚终于再次来到小桥畔。
8月初,桑志华来到城川。此时,他在萨拉乌苏发掘期间的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这就是内蒙古牧民旺楚克(Wansjok),后来萨拉乌苏的主要发掘点都集中在旺楚克家的领地内。据桑志华记载,旺楚克身体强壮、面容精干、不苟言笑,对化石十分着迷。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交谈的内容基本上都与化石有关。

上图:从上游拍摄的王氏水牛发现地(桑志华摄);

下图:从对岸拍摄的王氏水牛发现地(笔者摄于2021年10月19日)
1922年8月7日,桑志华来到旺楚克家所在地——邵家沟湾,并将营地安置在旺楚克家北侧的山坡下,正式开始发掘。当年的发掘涉及到具体的地点共有18处,桑志华在行程和发掘日记中分别用字母A至R来表示,字母顺序依据他在踏勘和考察过程中首次辨认出化石出露剖面的顺序,其中还有好几处都是旺楚克最先发现的。在萨拉乌苏河沿岸的科考和发掘工作中,旺楚克不仅作为向导,为桑志华指引化石出露的位置和地层,同时他本人和家人都积极加入到发掘队伍中,成为桑志华的坚定伙伴和得力助手。

上图:从桑志华宿营地位置拍摄的J点(笔者摄于2021年10月20日)
巧合的是,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桑志华便在邵家沟湾营地东北偏东方向的G点,在一大片崩塌的山体中,发现了“角的横截面为三角形的大型牛科的骨骼化石”,包含有头骨和大部分骨骼化石,“这里的地层以青色泥质砂岩为主,在贝壳状的裂口处有些质地很细的青色黏土层”。这套化石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同时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个体与其他牛科的不同之处。因为尚未确认其种属,因此在桑志华后来的发掘记录中,凡涉及到这一个体之处均不厌其烦的用“角的横截面为三角形的大型牛科的骨骼化石”来表述,以示其形态特征上的独特之处。随后他又分别于8月18日和次年8月4日,在G点及其附近发现了包括两根肋骨在内的其他一些骨骼化石。这便是后来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王氏水牛(Bubalus Wansjoki)化石的发现经过,而“王氏水牛”这一名称也正是为感谢旺楚克(Wansjok)一家在发掘工作中的贡献而特意命名的。

下图:J点地层照片(桑志华摄)
“牙”出惊天,人类化石出土
邵家沟湾的发掘多次受到洪水和混乱时局的干扰,桑志华一边抓紧发掘,一边随时准备撤离。在1922年8月的工作中,有一处地点的发现将会举世闻名,这就是位于桑志华宿营地北面大约100米处的J点。J点的发掘工作是从8月12日开始的,在8月17日的发掘日记中,桑志华清晰地记录了在当天J点的出土物中有一枚人牙:“我发现J点的地层看起来非常复杂。这里发现了许多象类、羚羊和啮齿动物的化石。另外还出土了绳纹陶器和上釉陶器、一颗人类的牙齿、马牙化石、珍珠、一件燧石石器以及一枚康熙时代的铜钱。这套含化石的地层是经过二次沉积的,含有不同年代的甚至是现代的材料。不过所有的象类骸骨仍保存在当时死亡时的位置上。我给这个地层拍了一张照片。”
桑志华认为J点的地层经历过二次沉积,其出土物的年代新老混杂、不太可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因此并未显露出多少发现人牙的惊喜。而且,此时他也已经与巴黎方面取得了联系,确信将来会有强大的外援来加盟他的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当时他并未对这枚人牙给予特别的关注,仅仅将它与一起发掘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混在一起,等待打包运回天津。
另一个重要的发掘点是位于营地东侧的A点,这也是8月7日最早启动发掘的地点。在连续多日的发掘工作中,陆续有动物化石出土。直到8月24日,桑志华在该地点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一件燧石钻具。根据对A点地层剖面的观察,他推测此处一定还会有更为重要的发现。不过,此时萨拉乌苏的发掘工作因时间和资金等问题已经整体进入尾声,桑志华不得不暂时停止A点的发掘,决定以后再来。

德日进(前排右二)和导师布勒(前排右一)
1922年桑志华在萨拉乌苏邵家沟湾的发掘从8月7日正式启动,至8月26日正式结束,共持续了20天。如果加上前期各项准备和后续整理、打包化石,以及在萨拉乌苏河上游一带的考察与采集等,按照桑志华行程日记中的时间线,本年度萨拉乌苏的工作是自7月31日开始,直到9月11日正式启程返津之前结束,共计42天。这一年的收获很大,化石、石器和动植物标本整整装了52箱。一是首次发现萨拉乌苏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发掘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包括举世闻名的王氏水牛化石、披毛犀和野驴骨架等;二是首次发现萨拉乌苏邵家沟湾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并开展了第一次发掘;三是人类牙齿化石的出土,不过其重要科学价值直到第二年才被认识到。
1922年的回程之路也颇为凶险。桑志华本想按原路返回,但当时东边军阀混战正值将平未平之际,散兵游勇和土匪强盗四处游弋,再加上萨拉乌苏河水上涨,无奈之下,桑志华只能先取道宁夏,绕路而行。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被迫绕路,桑志华才得以路过他心念已久的水洞沟一带,第一次确认了水洞沟第一地点的大概位置。这便开启了另一段故事,在此略过不提。

“河套人”牙齿化石模型(现藏天津自然博物馆)
“桑”“德”联手,开启崭新篇章
1922年8月在萨拉乌苏发掘期间,桑志华深深感觉到经费预算和研究力量等方面的不足,迫切地需要法国方面的协助。当月中旬他便迫不及待地写信联系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布勒的学生——当时已是著名古生物学家的德日进。在布勒的协调下,德日进决定次年到中国和桑志华共同开展工作。
1923年5月23日,德日进到达天津,与桑志华两人相见恨晚。他们组成“法国古生物考察团”,急切地盼望立即出发赶赴萨拉乌苏。不过,当时小桥畔一带的军阀混战还在持续,时局动荡不安,考察计划被迫一再拖延。德日进只好借此机会在北疆博物院整理和观察前一年萨拉乌苏出土的动物化石。意外之喜此时到来,在一堆鸵鸟蛋皮和羚羊牙齿之中,他竟然再次发现了那颗人牙。此时德日进的专业判断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牙齿的石化程度,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颗人牙不同寻常。他们翻阅桑志华当时的记录,确定了这颗人牙的出土位置和地层,并决定此次去萨拉乌苏一定要到这个地点再继续发掘。
关于这颗牙齿后面的故事人们便耳熟能详了。经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的研究鉴定,确认这是一颗8岁左右人类儿童的左上外侧门齿,德日进则根据其石化程度分析确信其年代属于更新世晚期。步达生将这颗牙齿命名为“The Ordos Tooth”,裴文中先生后来将其所代表的古人类称为“河套人”。“河套人”牙齿是中国境内出土的第一件有准确地点和层位记录的古人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其发现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开端。
1923年6月12日,考察团终于从天津启程。他们先乘火车经北京至张家口,因得知鄂尔多斯一带混乱战局仍在持续,出于安全考虑便决定沿黄河北上至包头,然后走黄河北岸的路线绕一个大圈。桑志华与德日进并不急于赶路,他们沿路考察,先是在三盛公一带发现化石,而后在前一年桑志华确认过的水洞沟地点发现了旧石器!桑志华和德日进激动万分。就在此时他们得到消息,鄂尔多斯一带的战事暂时平息了。经过讨论,他们立即决定先去萨拉乌苏,待萨拉乌苏的工作完成后再返回水洞沟进行系统发掘。7月30日下午考察团到达了城川,随即再次来到邵家沟湾,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系统发掘。
1923年的发掘自7月31日持续至8月25日,考察团内部实行了有效的分工协作,桑志华主要负责组织发掘和绘图照相,德日进则侧重于地层研究。A点是本次发掘的重要地点之一,8月13日起,考察团决定将A点称为“旺楚克剖面”(gisement Wansjok)。重要的发现于8月18日到来,在“旺楚克剖面”发掘出土了很多加工过的小型石英岩和燧石石器,以及破碎的动物骨骼,考察团分析认为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火塘”。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旺楚克剖面”的考古发掘工作面较1922年大为拓展,在原A点的基础上分别向北和向南延伸,长度达到200米。

旺楚克剖面(A点)全貌(桑志华摄)

旺楚克剖面(A点),旧石器时代地层发掘工作面(桑志华摄)
因萨拉乌苏河水上涨,考察团在8月25日结束了在邵家沟湾的发掘工作,全面打包。他们于8月26日离开小桥畔,到陕西榆林的油坊头一带考察。出发前,旺楚克向桑志华表达了希望能继续发掘A点工地北部的想法,桑志华建议他一定要谨慎,多日的发掘已使得工地越来越面临滑坡和塌方的危险。不幸还是发生了,在考察团9月9日返回小桥畔时听到了噩耗,旺楚克的女婿在几天前的发掘中遭遇塌方牺牲了。桑志华懊悔不已,在日记中痛心自责道:“我一直在后悔让他(旺楚克)在我不在的时候工作。我们本应该关闭工地。这样就能够避免这场灾难。……这个不幸的消息沉重打击了我,令我痛心不已。这一悲痛事件充斥在我整年的记忆中,刻骨铭心。”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科学家在冰冷理性之外所具有的温情与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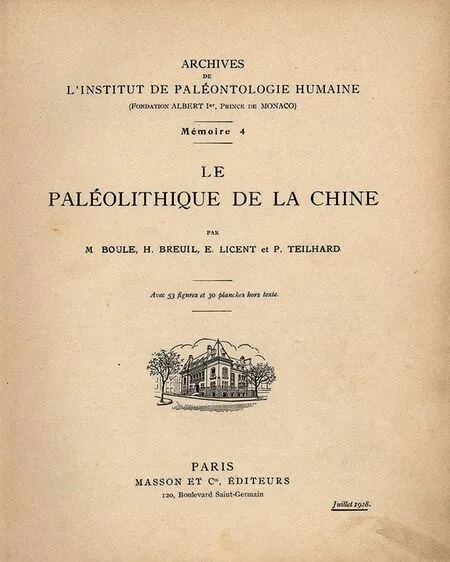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法文原版)》
硕果累累,构建学术根基
1923年“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在萨拉乌苏收获颇丰,共发掘出土动物化石和石器达26箱,尤为重要的是确定了A点(“旺楚克剖面”)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居址。随后,桑志华与德日进对包括萨拉乌苏在内的黄河流域一带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于1924年发表了三篇地质学方面的报告《鄂尔多斯南部和西部边缘的地质观察报告》、《鄂尔多斯地质补充观察》、《鄂尔多斯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缘的地质》及一篇考古学报告《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1925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法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文,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第一篇综合性的研究报告;1926年,桑志华、德日进和步达生合作撰写了关于“河套人”牙齿化石的专门研究论文《河套东南部洪积期人牙之发现》,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五卷中;1928年,桑志华和德日进与布勒(M. Boule)、步日耶(H. Breuil)合作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该书是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部综合性学术专著,成为日后中国古人类-旧石器研究领域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范式(该书中文版由李英华和邢路达翻译,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从理论、方法到实践等各个方面都兼具国际视野和世界水平,与当时在其他地域取得的科考和研究成果一同构建起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哺乳动物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石。其后一代代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砥砺奋进、上下求索,一次次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历史推向更为悠远的过去。
萨拉乌苏,一片沙漠之中的绿洲,一段悠远历史的见证,一部人类文明的史诗。它如同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反映我们的过去,也照亮我们的未来。百年前,当一名法国科学家不远万里来到此地,面对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而陷入沉思时,科学理性的光辉与浪漫的东方梦想不期而遇、交相辉映,编织出一首绵延百年的序曲;如今,百年未有之变局不期而至,人类再次面临抉择与挑战。先贤如能预见未来,当直面这轮红日,睿智的头脑中是否会迸发出惊叹:这究竟是人类的落日,还是新人类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