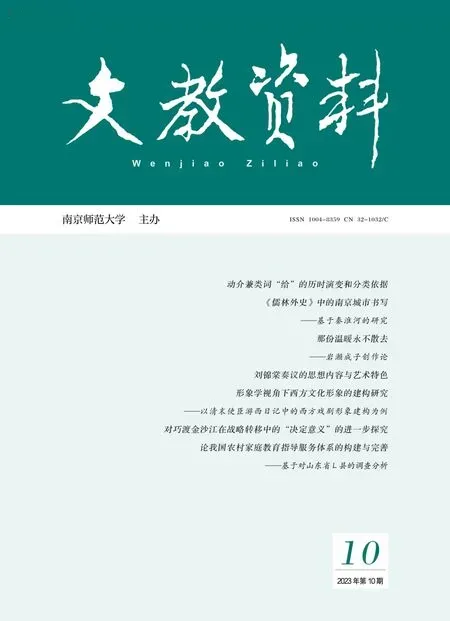《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城市书写
——基于秦淮河的研究
刘昱彤 秦 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儒林外史》中基于秦淮河的南京城市书写。“城市”和“文学”两个概念各自涵盖万千,但相互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所指出的:“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
纵观《儒林外史》全本五十六回,有二十一个章回故事都发生在南京或与南京相关,分量之重可见一斑。历经家道败落、亲人离丧的种种变故后,中年吴敬梓深感世事无常,于是携妻寓居南京秦淮水亭,以卖文为生,自号“秦淮寓客”。《儒林外史》以写实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立体、多方位”的南京,展开了一幅南京风物与人事的广阔生活画卷,而《儒林外史》中的南京故事大都围绕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这个文化地标展开。
吴敬梓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刻的批判力描摹世道人心,也以这种洞若观火的目光凝视着南京这座城市的风物、名胜、人事等等。学术界多关注《儒林外史》中宏大的南京叙事,而对小说中围绕秦淮河展开的“秦淮”空间关注较少,对于《儒林外史》中经常出现的“秦淮河”文化地标意象,目前的研究也远远不够。因此,本文以秦淮河为切入点,从城市空间、城市风物、文化风貌与城市气质三个角度探讨《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城市书写,试图从研究明清南京城市的全新视角,看到一个更生活化、更具情味与名士风度的南京城。
一、城市空间建构——秦淮河意象
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往往借由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来构建独特的城市空间,其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与地域文化,同时承载着作者独特复杂的情感空间与内蕴丰富的文化精神寄托。想要分析《儒林外史》中的城市空间,先来谈谈小说中以秦淮河为代表的地标意象。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文本中真实地理空间的呈现和搭建往往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特定地标建筑所承载的城市文化精神产生潜移默化的价值认同,这些地标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城市空间建构的支柱。因此,城市地标“常作为故事背景而出现并逐步演变沉淀为一种城市意象”[2]。《儒林外史》中对秦淮河的第一次直接描写是在第二十四回: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袨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3]
秦淮河是南京风物繁衍昌盛之处,又作为母亲河孕育着古金陵的城市文化,是南京城市名副其实的地标符号。因此,“秦淮”常常作为故事场景在文人作品中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可以代表南京的城市意象。
任何一种文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空间形态作为承载体的,而人作为文学叙事的主体,在不同空间中通过多样化的活动产生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在《儒林外史》中,人的衣食住行、心理、情感与城市形态紧密结合,而对于城市形态的描绘又与空间不可分割。空间的概念包含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物理空间又可分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这里的私人空间是指在物理范畴上具有封闭性和半封闭性的空间,与“开阔”相对,其中也包括人物隐私的情感空间;而公共空间则是指为大众所共有的城市外部空间。《儒林外史》中就依托秦淮河房建构了文人寓居的“家”空间与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空间概念之间是交叉关系,而不是可以彻底分割的全异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河房“家”空间半私密半公共的特殊性质。
(一)半封闭性的“家”空间
秦淮河上的私域空间,即“家”空间的建构主要是依托于一种明清南京特殊建筑类型——河房。河房又称河厅,是一种水阁式建筑。“夹秦淮河而居”,“水上两岸人家,悬椿拓架,为河房水阁,雕梁画槛,南北相望”。[4]也有个别的房前留出空地,杂植花卉苗木,以短垣围之,建成临水花圃。秦淮河房半私密半公共的特殊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首先是建筑结构。如小说第三十三回中对河房众人活动的叙写:“到上昼时分,客已到齐,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5]又如第四十二回中对钓鱼巷河房有这样场景描写:“两人坐定,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槅,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6]再结合明代吴应箕在《留都见闻录·河房序》中的记载:“南京河房,夹秦淮河而居。绿窗朱户,两岸交辉,而倚槛窥帘者,亦自相辉映。”[7]可见,河房这种建筑是一面临水的,两岸河厅之间存在着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有半封闭性与半公共性的空间特质,并不是以墙为界限的全封闭结构。
其次从功能来看,河房对于居住者来说是日常起居生活的场所,空间是相对私密的。但当它承担文人雅集、聚会宴饮的功能时,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对《儒林外史》中依托于秦淮河房的主要人物活动进行梳理后,得出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儒林外史》中与秦淮河房相关的人物活动
本文在这里主要讨论功能上的半公共性与半私密性。先说文人寓居的私密性。如小说第三十回写杜慎卿买定河房:“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择三日内过门,便忙着搬河房里娶妾去了”[8];第三十一回鲍廷玺与杜慎卿河房夜谈;第三十三回杜少卿与季韦萧言自己将要移居金陵,“杜少卿道:‘我如今来了。现看定了河房,到这里来居住。’季苇萧拍手道:‘妙!妙!我也寻两间河房同你做邻居,把贱内也接来同老嫂作伴。’这买河房的钱,就出在你!”[9]不管是买房娶妾还是买房居住,都显示了河房作为“家”的私密性与私人性。书中人物定居金陵也往往以“买河房”为标志,可以说河房是一种城市归属感与融入感的指称。河房的私密性还体现在私人情感空间的建构。汤克勤、丘森才在《秦淮河畔的“寓客”情怀——兼论〈儒林外史〉中南京名胜与士的关系》一文中就认为:“吴敬梓的‘寓客’情怀,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他寓居秦淮水亭,秦淮河是南京的灵魂,也是南京最具历史文化韵味的名胜,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给秦淮河注入了‘寓客’的漂泊情怀。”[10]基于此,吴敬梓借由秦淮河房开辟了一方包含隐逸山水、漂泊客居等复杂心绪的个人情感的私域空间。他在全书的第五十六回剖白心迹:“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11]秦淮作为治愈与疗伤之所,海纳百川般收容了他在故乡的全部苦闷与哀愁,以汩汩水流抚平他情感与生命里的崎岖沟壑。秦淮河及河房的地理景观,对于吴敬梓来说意味着一种家园感,这反而是他真正的“故乡”所不能给予和供他依恋的。
最后谈谈河房的公共性质。吴敬梓在小说中有意将南京的文人交际故事情节都安排在杜少卿的河房中进行,河房俨然成为南京文人的交际中心。如第三十三回写少卿新居落成宴请各名士,第三十四回写众名士商议泰伯祠祭祀,第三十六回写虞博士拜访杜少卿等,都是以杜少卿河房为位置背景开展的活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空间私密性的消解与解构,同时也是河房空间半公共性的表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河房的交际功能超过了居住功能,这意味着其公共性甚至超过了私密性。小说中对河房功能的描写也大多围绕文人雅集、宴饮聚会、交际往来等公共活动的主题,解构了原本的“家”空间应当具备的“宜居、便自洽、便独思”特征,“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才成为该建筑的主要功用。
(二)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公共领域开敞的为大众所共有的城市外部空间,它是以为满足一定城市功能而存在的连续性的空间体系,具有多功能性。”[12]公共空间承载着一个城市的主要功能,满足了生活在其间的每个个体的多样化、复杂化需求,是城市空间形态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儒林外史》中,城市公共空间以秦淮河两岸的各类商业、娱乐、民俗等活动为标识。城市中的不同群体被公共空间强大的交流与交换作用吸纳其中,其特有的全开放性使得空间内的人群阶层构成纷繁复杂,因而公共空间的功能也随之更加多样。
秦淮河流域南段自东水关入城,经古桃叶渡、贡院、夫子庙,至西水关出城,民间习惯把从东水关到西水关一段称为内秦淮。而内秦淮流经南京城南繁华鼎盛之处,故又称“十里秦淮”。秦淮河一带商贾云集,贡院也修建在秦淮河畔,每年数万考生赶赴南京,庞大的群体催生了贡院周边的一大批书肆、客栈、茶楼生意。《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写南京秦淮河沿岸是“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13]。书中则着重展现了秦淮两岸的饮食业,即酒楼、茶楼等的公共活动空间,如小说第二十五鲍文卿请修补乐器的倪老爹吃饭:当下两人走出来,到一个酒楼上,拣了一个僻净座头坐下。堂官过来问:“可还有客?”倪老爹道:“没有客了。你这里有些甚么菜?”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肘子、鸭子、黄闷鱼、醉白鱼、杂脍、单鸡、白切肚子、生烙肉、京烙肉、烙肉片、煎肉圆、闷青鱼、煮鲢头,还有便碟白切肉。”[14]
鲍文卿家住繁华的秦淮水西门附近,这座酒楼应该也在水西门大街上。秦淮河畔是当时南京核心的社交、娱乐活动场所,夹河流两岸而居的酒楼、茶馆、贡院等等也因此成为社会公众活动的舞台。两岸的各类商业、娱乐活动搭建了秦淮两岸独特的空间生活场景,也赋予了秦淮河包罗万象的公共空间性质。
二、城市风物与民俗书写:灯船与秦淮风月
《儒林外史》里写到了南京许多著名的城市风俗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秦淮河涉水民俗的刻画。秦淮河是南京城市地标与大众娱乐空间,寓居于此的作者因而对这些风貌非常熟悉与亲近。
(一)秦淮灯船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多次以鲜活动人的笔触描摹秦淮河灯火通明、火光耀天之景。在明清两代,秦淮灯船是南京市民最为熟悉的胜景,写特殊节日看灯船,亦以场面气氛胜。如小说第四十一回写秦淮四月半水上活动: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着河里,上下明亮。自文德桥至利涉桥、东水关,夜夜笙歌不绝。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在河内放。那水花直站在河里,放出来就和一树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15]
而到了农历七月,秦淮河上的游船又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16]
清代余怀的《板桥杂记》中写秦淮水上灯船是:“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17],与《儒林外史》中的描写两相印读,庶几可见秦淮灯船之胜。
(二)秦淮风月
秦淮风月是秦淮河的重要注脚,也是南京城市人文景观书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儒林外史》对这方面的描写比较笼统,仅在行文间穿插细节昭示秦淮两岸青楼业的发达。如小说第四十一回借李老四之口道明秦淮青楼业竞争之激烈:“近来被淮清桥那些开三嘴行的挤坏了,所以来投奔老爹。”[18]杜少卿和武书游河时,看到沈琼枝的卖诗招牌,对此武书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里偏有许多奇事。这些地方,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着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19]武书误会沈琼枝是“开私门”的一事从侧面传达了秦淮沿岸王府塘等地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的时事境况。
此外,贡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秦淮风月的勃兴。秦淮河两岸分别是青楼与贡院,才子佳人汇聚于此,这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租房一事中有所体现:“这年是乡试年,河房最贵,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20]而《板桥杂记》中也曾具体描述过秦淮名妓风流之地——旧院的位置:“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夜晚的秦淮河“灯船鼓掌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袨服,招接四方游客”[21]。十里秦淮是士子们寻求科举功名与诗酒风月的繁华锦乡,如小说第四十二回“公子妓院说科场”中汤由、汤实二公子来南京参加乡试,还未进考场便踏足风月之所饮酒作乐,大谈科场;出了考场更是听戏取乐,沉迷风月。
三、文化风貌与城市气质——以内秦淮河文人活动为线索
明清南京作为“东南重镇”的政治空间的同时,也是一座文化的空间,承载着文人雅集、节日庆典、梨园赏戏等等文化活动。秦淮河水长流,在小说中也如同一条细长而不断奔流的丝线,将文人活动串联起来,勾画出了南京城独特的文化风貌,塑造了城市气质、熔铸了城市品格。小说中描绘的南京城风貌区域主要是南京城南,即内秦淮河流域,而前文提到,内秦淮河特指秦淮河流域的南段,即俗称的“十里秦淮”。想要厘清小说中围绕秦淮河两岸设置了多少故事情节,就要先确立明清之际秦淮河的地理位置及两岸的津梁、第宅等等。据民国夏仁虎《秦淮志·流域志》[22]所载,可归纳出明清之际十里秦淮(内秦淮河)的流域大致是:通济门(东水关)—九龙桥—淮清桥—桃叶渡—利涉桥—文德桥—武定桥—镇淮桥—上浮桥—下浮桥—水西门码头。又据《秦淮志·宅第志》[23]可知,十里秦淮周围的著名宅第有古桃叶渡、钞库街、钓鱼巷、夫子庙、贡院、瞻园等等。基于此,笔者将《儒林外史》中围绕秦淮河两岸展开的部分文人活动进行整理,如表2 所示。

表2 《儒林外史》中围绕秦淮河的文人活动
小说第三十三回借杜少卿之口言:“这也极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24]第三十四回又言:“却喜卜居秦淮,为三山二水生色。”[25]“秦淮”意象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吴敬梓将对南京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更多寄托在文化景观的塑造与描摹上,而最能代表南京文化景观的便是“凝着六朝金粉”的“十里秦淮”。吴敬梓通过对秦淮河两岸文人活动的叙写与编排,呈现了南京独特的城市文化对文人群体的吸引力。此外,南京兴盛、宽容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又为文人的理想生活范式提供了可能性。吴敬梓借由寓居南京的外省文人,塑造了一种城市化的文人群体。书中以各种文人交往活动,如雅集、卖诗、选诗、避世等等,凸显了南京城作为“精神家园”在文人心中的地位。不管是莫愁湖高会的风雅之举,还是泰伯祠祭祀等等,其想法创意都是在秦淮河房中生根萌芽,然后借由文人活动在南京这座城市遍布生长。可以说,寓居南京的文人以自己的努力更新了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精神,创设了新的城市文化情境与风气。
综上,从吴敬梓对秦淮河文人活动的记叙,我们至少可感觉到三点:首先,吴敬梓对南京这座城市怀揣着深厚又独特的感情;其次,他记叙南京生活时采用的大多是写实笔法,其准确性与古代方志、写景记游类散文等相一致,这在白话小说中并不多见;最后,小说中对南京“名士”群体的塑造和对南京城“精神故园”的意义赋予,其实都展现了吴敬梓随性情云卷云舒的名士风度,同时寄寓了小说家崇尚隐逸的审美理想。
四、结语
正如孙逊、刘方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一文中提出的:“小说家很难完全凭空虚构和想象一个城市空间,他们往往凭借现实的城市进行书写和叙事。但由于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发生着的事以及传承着的历史。”[26]小说家笔下的城市是其审美理想及情趣的投射,因而作者常有选择地放大或缩小城市的某一部分以达到推动情节、深化主旨、塑造人物等等的创作目的。《儒林外史》中放大的即是内秦淮流域的城市生活空间,以此为基点还原了整座南京城的时代风貌。此外,城市书写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和外在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融合,因此,真正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带有作者主观色彩的城市部分面貌。吴敬梓笔下的南京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远比地理空间丰富复杂得多的文化表征和日常生活内涵,他以饱蘸的深情书写了他心中“六朝烟水气”与“三山二水生色”的城市文化气质,展现了真名士心中对南京城市印象的真实温情感知。
《儒林外史》中的秦淮河流域是南京城的缩影,作者以此河为基点展开了一幅充溢着“六朝烟水气”的金陵风俗画卷,叙事宏大而脉络分明、人物繁多而鲜明可感,称得上是明清南京城市书写的典范之作。《儒林外史》中写杜慎卿与友人徜徉雨花台岗上,黄昏日暮,只见两个挑粪桶的,一个拍另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27]历史赋予了南京城繁华风流又沧桑厚重的多样气质,坚实底色上又有十里秦淮贯穿岁月的温润风雅。南京是文学的城市,或许,正是因为有了人与情的浸润,才有了文学生发的无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