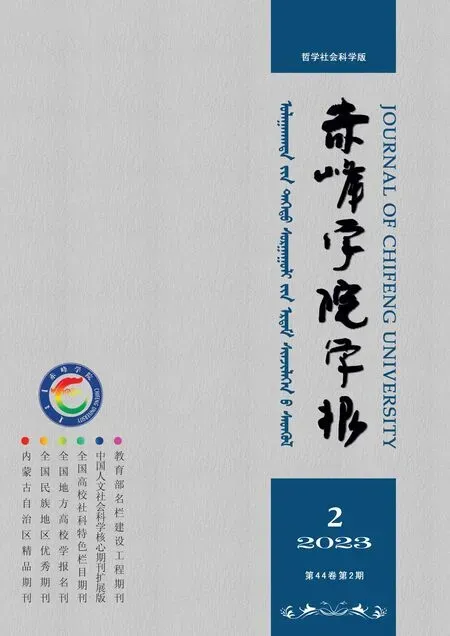隐喻认知理论视域下语言文字隐喻能力教学策略探究
丛日丽,佟桂芬,张静漪,薛春艳
(赤峰学院,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发现隐喻具备独特的修辞功能,因而隐喻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热议[1]。20 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专家纷纷意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它更是人类认知外界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人们从对隐喻的语言修辞的关注转向了对其认知的研究, 隐喻认知理论应运而生。1936年, 学者理查兹在其对隐喻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两个并置概念基于互动产生新的意义”的论断,随后,布莱克进一步肯定了“隐喻的互动性”。1980年,莱考夫与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著作中正式提出了“隐喻认知理论”,他们认为隐喻发生的前提是互动,两个认知域之间形成跨域投射,自此,隐喻的研究从语言学平面研究步入了认知研究的新阶段。近年来,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 人们也逐步引入了隐喻认知理论来指导实践,然而,由于对隐喻认知理论的理解深度不足,而导致教学实践难于深入。鉴于此,本研究从隐喻认知理论出发,剖析隐喻认知理论的主要特征与思维属性,进而,深入探究隐喻认知理论在语言文字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为语言文字推广的教学人员与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隐喻认知在语言学习上的功用
隐喻认知理论是在语言能力理论与人类认知理论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是认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交叉结合的一个新兴理论体系。相对于单一的语言学或认知学上的诸多理论,在方法上、功能性、创造性上有其诸多相对独特的一些功用。
(一)方法论的创新
隐喻认知理论是传统隐喻理论发展成为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从单一的阐述词语本体和语言运用转向对事物的认知方法论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呈现。隐喻认知理论的提出,是方法论上创新与变革。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方式,是人类在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2]。其内在原理是以类比、认知与推理的方式把一个具体事物投映到一个抽象的事物之上,把一个概念源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当中,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喻义。隐喻在日常生活、语言与思维中随处可见,其使用频率是较高的。语言学者理查德的一项研究显示,大量的隐喻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会话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表达含有或带有隐喻表述的意向。同时,这种表达行为普遍被看作是一种认识活动和表达行为。从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来看,隐喻认知理论关注的不仅是语言现象的阐释,同时,它更是对个体认知发展、思维的阐释,是认知理论上的一大突破[3]。
(二)扩展性功能
从语言学的最初对“隐喻”的认知来看,“隐喻”只是对语义的修辞表达,通过对语句的修饰、情感烘托,来提高语句的语言效用。随着人们对隐喻认知的不断加深,人们越发发现隐喻的存在不仅仅是两个事物之间,它所建构的更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即扩展性功能。具体而言,用简单、具体的概念来认知与理解复杂的概念,用一个具体事物或某一种概念来概括一系列事物或某一类概念,便是隐喻扩展性功能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当人们突破语言学来看待“隐喻”时,对隐喻有了更为深入的探究。人们发现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共性。这种共性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语境下,在人类社会,虽然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在使用隐喻的方式和载体上有所差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比如都以钢铁比喻坚强,用狐狸比喻狡诈。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讲,隐喻不仅仅是语义平面、语用平面、语法平面与语篇平面上的,它更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是语言学的重要现象,也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其具体的内容涉及概念的产生、理论的建构、知识的结构化、思维的拓展等等,可以说,“隐喻”本体贯穿于各类学科体系之中,助力各类学科发现问题、解释问题、拓展问题,也正是因为其“横跨”性的本体特征,而使得它具备了相对广博的拓展性功能。
(三)创造性功能
客观世界与人类的内心一样,都是复杂、丰富而细腻的,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难于概括所有的,但事物之间的表述又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在遇到新生事物或表达抽象事物时,自然或不自然地会借用其他方面的词汇,如此一来,隐喻认知也便开始发生了。从语义本身来看,隐喻作为语义理解与词义发展的重要方式,单一的词语往往均关联着一系列其他词语的解释义项,一般由最初的中心义,即原义,人们对事物的最初认识,而通过隐喻映射派生出诸多其他义项。这一过程中,信息源与目标域并置,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其中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4]。从信息源到目标域的生成,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与无尽的创造力给隐喻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支持下,也注定了隐喻生产的丰富与多样性,因此,也造就了隐喻的创造与开放力。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在意义上形成映射,发生关联,在一系列寻求相似性的认知加工中,人类的创造性意识介入,再结合当时的语境因素、背景知识便得出来不同的隐喻义。如唐代诗人李煜所写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所写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二首诗中同有“愁”字,意义却大有不同,正是隐喻的创造性与开放性功能,使得“愁”字有如此丰富的含义。
二、隐喻认知的思维属性与内在机制
就本质而言,语言的思维属性与内在机制往往是相互关联的, 思维属性决定着内在机制的向度。对于隐喻认知而言,类比性与差异性共存、发散性与完整性同在、激活性与独特性并置,鲜明地彰显了隐喻认知的思维属性特征,并体现出其相对独特的内在机制。
(一)类比性与差异性
在隐喻认知理论机制的剖析中,有一种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两个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是隐喻产生的基本前提,换言之,相似性是隐喻形成与理解的基础”。学者利森伯格指出,相似性在隐喻形成的结合点, 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泛泛而谈相似性是隐喻的特质,则未免过于宽泛与微弱。谓其过于宽泛是源于两个物体之间未免会有若干相似的属性,相似点也因界定不同有着诸多特点;谓其过于微弱是因为相似性不能解释两个物体为何能存在共性,从而由一个物体推展到另一个物体上[5]。利森伯格进一步指出,在隐喻认知的过程中,相似性只能说是隐喻产生的一个基本前置条件,而两个事物之间固有的相似性甚至都可以不被关注,而其隐喻产生的过程是在其相似的基础上的差异性的存在, 才能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隐喻认知的产生不但是要利用事物的相似性,同时,更加要注重相似基础上的差异性。
诸多研究也不断地证实,隐喻认知的一个重要思维导向,便是要在认知相似类的基础上对两个事物的差异性要不断给予关注,人们的隐喻能力形成的过程,也是激活原始信息与目标信息之间的相似基础上的差异性,关注两者的关联性。情境语义学则认为, 隐喻的存在就意味着相似与关联的存在,不过,从更深层次上来讲,隐喻的出现更加意味着要通过“关联”来表达“差异”,用差异与关联来促进解释。
(二)发散性与完整性
在隐喻生成的过程中,信息激活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而信息激活带有多元性而非唯一性又是隐喻生成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隐喻也因信息激活的发散性而生成。换而言之,根据已知的相关信息,若是从不同的角度、方向或范围进行思考的话,将会得到更多不同方面的新信息[6]。对于隐喻生成的本身而言,隐喻本身即发散而来,信息激活这一特性内含于其中,对一个事物的描述往往是涉及多方面的, 这些方面往往是不能用一个概念进行涵盖的,信息激活也便参与其中,成就了其隐喻概念的新创意义。当某一概念不强制性地对应另一概念时,则会产生多个不同的隐喻概念,且每个隐喻概念则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概念网络。
当然,隐喻除了具有发散性,它还具备整体性。从内在发生上来看,隐喻生成并非单一对应关系的产生,它可以是若干相互关联系统的发生,在个体的大脑中也并非一个单一的镜像,而是个体对自我与外界关系认知的反映,透过身体感官、神经思维获取具象事物,是通过类比等方式进行完成的。在人类的思维认知中, 诸多概念的建构是不断建构的, 在其基本系统上不断地进行新的意义的产生。一般情况下,目标源与信息源在单一的体系上相对固定的,在一个概念的建构中,话语的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会进行信息的流动,在此期间,某一概念节点会在原有的概念体系上不断地发生迁移,而形成一个新的相对完整的图式与意义建构。
(三)激活性与独特性
在隐喻产生的过程中,若是从目标域与源域上来看,二者之间是对应的关系,是从源域向目标域的迁移,是由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向潜在若干认知的另一个位置的迁移,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会经历一系列探索,形成一条相对独立而确定的路径,这一路径中有话语发出者的意象,也有话语接收者应该可以理解或接受的意象。由于外界环境信息的差异性,主体的认知不同,再加上个体加工外部信息的差异性, 自然也便产生了隐喻概念生成的种种意义,对信息传播产生的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7]。就语义现象本身而言,在目标域与信息源域并置的空间内,由信息源域到目标域的迁移中,则表现出选择分支概念上的差异,同时,还表现为在取舍焦点上的差异,这样一来,也便构成了隐喻生成的独特性。
具体而言,隐喻认知生成的独特性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关乎于不同的主体的认知与外界信息的取舍,其中,更为关键的是主体的取舍,通常情况下,认知主体往往会选择语义场边缘位置上的分支概念,构成新创意义[8]。另一方面,对于新奇的信息而言, 隐喻往往会以新的意象呈现,给主体信息带来新鲜感。通常情况下,主体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通常会采用“近距离”的方式进行语义的再创作。而信息域一般是相对固定的,而目标域则是相对开放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意象不断介入,随之产生的与目标域相关的信息与目标域之间的偏差也不断加剧,进而,呈现其独特性。
三、隐喻认知理论在语言文字隐喻能力培养中的运用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同时,它也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语言现象。注重隐喻能力的培养,在语言文字教学中是极为必要的。基于隐喻认知的特征、思维属性及内在机制,教学中培养学生们的隐喻意识, 帮助学生们发展对隐喻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原型意识,培养学生词汇扩展与类比能力
隐喻认知理论提醒我们,词汇是基本意义上的引申、转义或派生,其隐性寓意的存在更多是体现为一种类比性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同时,它又是一种发散性思维。个体的隐喻能力与隐喻思维培养的基础则是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认知, 当然,又需要对其施以创造性与发散性的引导。然而,正如大多数语言学者所讲,个体的词汇量大小往往指的是词汇的广度与深度,广度指的是个体词汇的关联能力,而词汇深度则指的是个体掌握的一个词语的全部意义与用法能力,其中,词汇的深度与广度往往又是个体词汇学习过程能够在词汇形态与词汇语义之间, 意义与意义之间所建立起关联的能力[9]。而个体对词语的关联能力的捕捉往往是通过隐喻或转喻而实现的,即以一个事物来喻说另一个事物,把具体的事物与抽象的概念关联起来,从而实现词义的扩展或概念的延伸。认知语言学认为,一词多义是语言上的一个基本的现象,几个词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其意义是基本意义上的引申、转义或派生。而引申、转义或派生往往又与隐性的寓意相关。而在一般情况下,引申、转义或派生通常是基本意义在发展的过程中,由隐性寓意的存在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意象。
人类在理解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往往可以通过类比获得对基本意义上的扩展信息的关联,促进信息在深层记忆中的保留及从记忆中对过去信息的提取,从而保证其对词汇的理解与学习[10]。因此,在语言文字推广的过程中,若要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隐喻能力,对类比思维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常教学中,要注重类比思维能力的培养,注重两类事物、概念之间的关联性的建构,锻炼学生通过已知事物属性推断另一个事物属性的能力,加强事物之间关联性探索能力训练,对学生的隐喻能力和隐喻创造能力的提升创造有针对性地培养。
(二)建构概念整合,培养学生隐喻的动态整合能力
随着隐喻认知理论的发展,学者马克特纳等人在对隐喻形成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许多语言现象均存在一种“概念整合”操作与认知方式。“概念整合”,顾名思义,对概念进行筛选、应答与再构。从心理学范畴上来看,“概念整合”是一种心理空间的建构,并且,这种心理空间建构又在不同的时段中呈现不同的状态。就一般意义而言,概念整合囊括四个心理空间建构过程,其中,有两个被称为输入空间,而在输入空间中将会产生一个跨空间,即类属空间,被称为第三空间。第四空间为整合空间,是输入空间中的信息在类属空间过渡后而形成的, 形成两个不同于输入空间的新创空间。语言学专家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认为,隐喻形成中的两个域,即始源域与目标域相当于心理空间的两个输入空间,而第四空间则是隐喻生成的喻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概念整合由两个输入空间产生一个第三空间,而在第三空间中生成新创空间,经过四个空间的概念整合,隐喻信息生成。换个角度来说,源域信息与目标域信息作为隐喻产生的起点与终点, 中间要经过一系列整合,而这个整合则便是隐喻产生的“概念整合”[11]。类似于一块木料打算打磨成一件工艺品,木料则是始源域,而工艺品则是目标域,而在这过程中则需要工匠的介入, 工匠的作用则是对木料进行整合与加工,即在整合空间产生新创意义。
就心理学而言,隐喻产生的内在机制即是概念整合,就隐喻认知理论而言,隐喻的产生即是语义的关联性、发散性与创造性的交叉而成,二者是异曲同工的。就隐喻认知产生的本源来看,它不仅仅是语言学的概念,它更是心理学在语言发展上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隐喻的能力的培养,其实质是就是培养个体的概念整合能力。显然,在推广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势必要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概念整合能力。虽然,人类在概念整合方面存在着个体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先天性,但面对信息差异悬殊、概念结构复杂的当下,对学生们进行概念整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三)运用意象图式,培养学生词汇的发散与结构化意识
意象图式是一种概念性的结构,是隐喻能力生成的关键因素,或者说是理解隐喻的关键。同时,它也是隐喻扩展性、创造性功能实现的基本路径。通常情况下,个体通过类比的形式难以完全获得对隐喻的理解,意象图式则会介入。从词汇生成的机制而言,意象图式可以帮助个体从理解一个领域过渡到理解另一个领域。一般而言,基本的意象图式根植于日常生活体验之中,与我们的身体姿势、构造,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对外界事物的操控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意象图式是个体在与世界万物的互动中,世界万物赋予并反映在我们大脑中的万物的秩序与模式。通俗地讲,意象图式是在我们大脑中各类相对有秩序的静态画面与动态画面的图景, 这些图景构成了人类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路径,为隐喻的产生奠定了一系列元素性与结构化的基础[12]。人类正是借助这种意象图式来实现对事物的理解与想象的,相对有序的意象图式作为媒介帮助个体建构了丰富的概念体系与思维结构,也便实现了个体对意义的理解与扩展。
既然意象图式是构成隐喻能力的关键,又是形成隐喻能力的核心所在。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中列举了27 个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图式, 概括了7 大类意象图式[13],包括部分、整体、前后、运动、平衡、对称、路径等。以路径图式为例,通常包括始源、路径与终点三个基本要素,路径作为路径意象图式的核心点,构成了始源与终点的连通, 即始源——路径——终点,在这里隐喻的类比思维发生在路径上,而以路径为核心的意象图式,完成了隐喻思维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善于进行意象图式思维就是具备了隐喻的能力[14],当然,莱考夫和约翰逊二位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隐喻意象建构的基本思维路径,在语言文字教学与学习中可以加以借鉴。因此,在语言文字推广的过程中,强化个体意象图式思维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路径。在语言文字的教学中,应加强学生们运用意象图式的训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意象图式的训练,训练学习者能够通过意象图式进行思维能力的提升,进而,使学生们从具体事物过渡到理解抽象、复杂的隐喻表达,以此来提高学生们对隐喻的理解。
作为语言学习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隐喻是个体掌握语言无法绕开的,无论是在语音、语义和语篇的学习,还是在语法的运用中,隐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主体对语言的认知。当然,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还在个体认知事物的过程中推动了个体对新知的理解与掌握,促进个体通过一种事物或某一概念来认识另一事物或概念,由旧的、过去已积累的知识来了解和掌握新的知识。因此,在语言文字教学过程中,充分把握隐喻认知与语言学习的关系, 充分理解隐喻认知的基本功能与思维属性,是极为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体在语言文字学习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