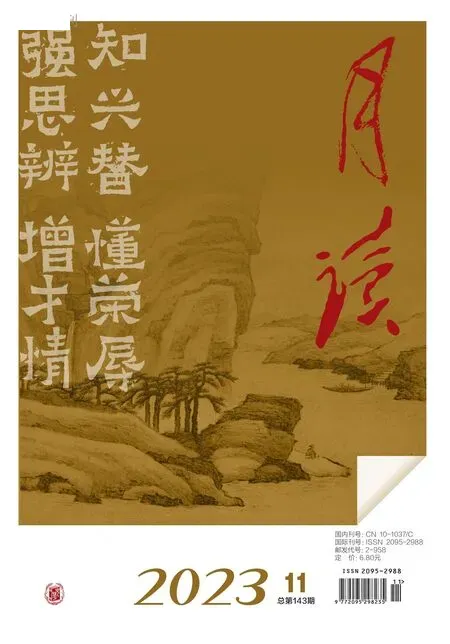紫禁城的苜蓿
◎ 张 程

庄严肃穆的紫禁城并非花草树木的乐园,三大殿、后三宫等主体区域都没有栽植草木花卉。可它毕竟是雨水滋润、四季交替的一方土地,终究难以抗拒自然法则。当春风再一次吹拂这片六百多岁的深宫禁苑,古柏紫藤、油松国槐、玉兰海棠在御花园、在宫院甬道、在内金水河畔扎根绽放。它们是宫苑常客,倒不稀奇。稀奇的是,在砖道缝隙、屋脊瓦楞和城墙根儿等处蓬开的二月兰、蒲公英、毛地黄、车前草、红苋荠菜苣荬菜等。这些常见于乡野田间的小花小草,散布在紫禁城的犄角旮旯之处,给春天的紫禁城涂抹上红黄粉紫的色彩,中和了皇家的华贵富丽气息。
要论紫禁城中最接地气的小花小草,还得是苜蓿。
草根出身的苜蓿,并非宫廷特意种植的对象,成为紫禁城的居民是它自力更生的结果。那么,它是如何在皇家宫苑生根发芽的呢?紫禁城里苜蓿最“合理”的生长地是现存箭亭东侧的那处开放式院落。清代,掌管宫中用马的上驷院衙署就在其中。清王朝将上驷院紧邻箭亭,彰显本朝骑射不分家。苜蓿是马匹的优良饲料,遗落种子再正常不过了。这些清朝的种子散落进入六角形的棱格状地砖中,扎下根去,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于来年从砖缝中伸出低矮的枝干,长出紫色、黄色的小花来。几百米外的城楼上,同源同种的苜蓿花在墙头俯瞰着这片世界现存最大宫殿群的沧桑巨变。遥想当年,城墙防御是紫禁城警卫系统的重要工作内容。四座城楼的城台内侧都有左右马道(蹬道)与地面相连,马道宽达数米。巡逻的骑士,跨马配枪由马道上下,在执行警卫和礼仪职能的同时,顺带着将苜蓿的种子带上了城墙。
如今,王朝已经灰飞烟灭,御马也已销声匿迹,而当年供给御马的苜蓿,却把种子撒在了这片土地上并繁衍至今。
苜蓿,本不是中国的物产。张骞通西域,除了乌孙宝马,还带回了苜蓿和葡萄。苜蓿可以喂马,葡萄适合酿酒。汉武帝刘彻对舶来品大为欣赏,《史记》记载当时“离宫别观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极望”是满目皆是的意思,表明当时苜蓿种植之广。汉武帝重视苜蓿,一则彼时中原与匈奴的战争需要大量战马,培育战马难免需要优良饲料。苜蓿西来,适得其所。中国的马政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也是西汉取得汉匈大战胜利的原因之一;二则苜蓿的象征意义,可以给西汉政治增光添彩。苜蓿、葡萄等,都是远人慑服、万邦来朝的象征,早在汉代就成为器物装饰纹样。苜蓿花叶美观、寓意美好,后世历代皆有沿用,成为常见的“苜蓿纹”。明清瓷器中常用苜蓿纹。现在查询故宫博物院官网的数字藏品,搜索“苜蓿”关键词,可以搜出145 件名字带有“苜蓿”二字的文物藏品。其中绝大多数是清嘉庆年间的青花苜蓿花纹盘。想必没有出现在名称中但刻画在的器物上的苜蓿纹藏品会更多。一实一虚,两大功用使得苜蓿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后来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小花草。
在我成长的浙东农村,早春时节,小麦水稻轮作间隙的农田通常是苜蓿的天下。那串串紫色的苜蓿花,和丘陵间星罗棋布的杜鹃花一道敲响了春天的钟声。浙东不养马,苜蓿就成为猪、水牛等家畜的饲料,尚未开花的嫩苗还是农家餐厅上的佳肴。苜蓿的嫩芽可以作为主菜清炒,也可以作为佐菜烘托肉食,或者制作面点,食之唇齿间能感受到一股悠长的青草香。相当部分农田中的苜蓿,肆意生长,最终碾作春泥增添肥力,也没有浪费,还充分利用了轮休期间的田力。
苜蓿逐渐融入日常生活,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印记:苜蓿“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长宜饲马,马尤嗜。”苜蓿得到大面积种植,为各种牲畜提供饲料。明朝皇家还专门在内城西郊开辟苜蓿种植区,供应御马饲料。《明世宗实录》载:“九门苜蓿地土计一百一十顷有余……给领御马监银一十七两,赁牛佣耕,按月采集苜蓿,以供刍牧。”这块皇家御用的苜蓿地,干脆得名“苜蓿地”。巧的是,明清两代客商驼队往来京城,也走西边。这块离北京城不远的苜蓿地渐渐成为客商们歇脚喂养牲口的地方。由于苜蓿二字对于贩夫走卒而言,显得生僻,地名逐渐被讹传为“木樨地”(关于这个地名来由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觉得苜蓿是牲口饲料,俗而不雅,便用代表桂花的“木樨”替代了)。不过,这并不妨碍苜蓿二字登堂入室进入紫禁城,不仅出现在明朝的青花瓷上,还成为御膳菜品。清代御膳就有面点“寿意苜蓿糕”,主料便是苜蓿。看来,苜蓿对味蕾的征服,是不分对象的高低贵贱的。
苜蓿凭借顽强的生命力,遍布田间地头、道渠野地、河岸沟壑,注定是一款低廉的食材。饥民寒士多选择苜蓿充饥,苜蓿便具有了清贫的文化内涵。《唐摭言·闽中进士》记载薛令之为太子侍从,待遇不佳,写了一首诗排遣烦闷:
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 苜蓿长阑干。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
只可谋朝夕,那能度岁寒!
薛令之面前的“苜蓿长阑干”,大致是焯水后横摆在盘中的苜蓿。虽然鲜嫩,常吃也不见得可口。无奈薛令之囊中羞涩,又不愿以权谋私,只能以苜蓿为常餐了。由此引出了典故“苜蓿盘”,形容官卑俸薄者的贫寒生活,多用在馆职、学官等清冷文职和私塾先生身上。古代诗歌多用此典,如苏轼“可怜先生盘,朝日照苜蓿”,苏辙“相从万里试南餐,对案长思苜蓿盘”,陈造“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苜蓿盘”,清朝黄景仁“醉时欲碎珊瑚树,醒来仍餐苜蓿盘”等等。这个典故继续延伸,包含有自甘清贫、清廉自守的意味。典型的如南宋陆游《书怀》:
苜蓿堆盘莫笑贫,
家园瓜瓠渐轮囷。
但令烂熟如蒸鸭,
不着盐醯也自珍。
明清的紫禁城内,想来也有不少人脑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浮现“苜蓿盘”的意象。奉调入武英殿编书的穷翰林,终日埋首于辞章句读和文牍书稿之中;夜晚值宿方略馆的军机章京,消磨难挨的夜晚的同时,常常纠结于前途;在御药房忙碌的御医们,工作繁忙且精神高度紧张,心中却还记挂着夫人的胭脂和儿子的束脩钱。他们偷得片刻闲暇后,不知道会不会沉思自己的命运,翻出“苜蓿堆盘”的旧意。更不用说那些顶着星光、从东华门摸黑鱼贯而入的小京官们,奔走在宫内朝房和本部衙门之间,重复着机械性政务,或许会在某段低头、垂手、肃立的漫长时间里脑子漫游向诗与远方,回过神后“对案长思苜蓿盘”。
正如紫禁城除了牡丹与海棠,还有众多不知名的花草,这座恢弘的宫殿除了帝王将相,更多的是如苜蓿般随起随灭的无名官吏。他们和宦官、宫女一道构成了紫禁城“居民”的大部,是他们在维系着紫禁城的正常运转,将这个王朝的心脏与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苜蓿融入了中国社会,他们也融化为了紫禁城生命的一部分。
苜蓿,还有众多不知名的小花小草,寂寞开无主,一岁一枯荣,在紫禁城中开放了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它们展现了生态系统的本真力量。自然界不是某种植被、某个群体、某类角色一支独大的,而是相互制衡、互惠互利的。苜蓿,唤来了紫禁城的春天,涂抹了紫禁城的色彩,还以自身的文化意味丰富了紫禁城的内涵。在紫禁城生态中,富丽堂皇与清雅素淡并存,荣华富贵与清廉自守共生,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株株苜蓿依然无声息地散布在紫禁城的墙角砖隙,不曾长草连天,没有花团锦簇,就这么过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