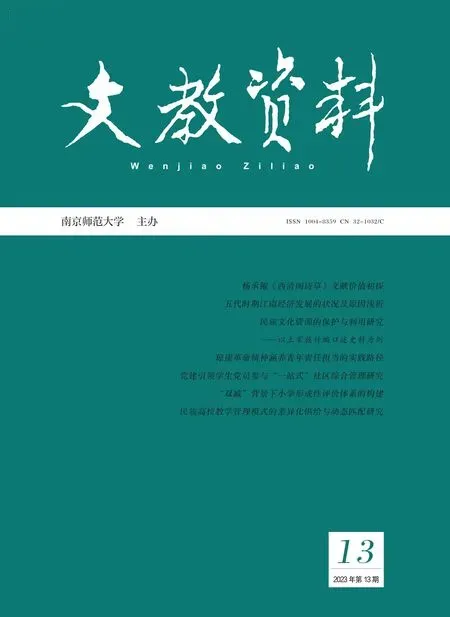身份之变,自我之立
——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视域下解读《新生活》
马 薇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新生活》是一篇现代诗歌,2016 年发表于第二届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是240 首终评作品的总冠军。作者炎拓通过描述一位妇女从喧闹的广场舞中回归家庭,准点为家人下厨,为家人无私奉献,午夜时分被月色惊醒,从试衣镜前忽而发现自我的场景,表现了中年女性平凡朴实的生活状况与两点一线的生命世界。炎拓的作品展现了普通家庭妇女的多重身份,从中可以窥见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这位女性的日常简单朴素,徘徊于“青菜”和“雪花膏”之间,在“广场”和“厨房”之间切换如常,丈夫与孩子充斥她的生活。或许她的物质世界能够获得丰盈,但她精神状态的世界略显空虚,为家庭所困,无法挣脱。诗中的“她”影射整个社会中年女性的现实状况——牺牲自我,维系家庭。自古以来,女性地位似乎始终处于下风,女人被默认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放弃事业照顾家庭的人通常多是妻子。但女性不仅是妻子、母亲的角色,其本质是人,是具有活的思想与灵魂的人。故本文将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视域着手,对《新生活》进行分析解读。
波普尔在《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中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世界分为物理世界、人类精神状态的世界、人类精神产物的客观世界[1],他的科学哲学被称为证伪主义哲学,核心就是试错、反驳、批判,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暂时的,一切理论都是可以被试错的。出于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理解,他提倡三种科学精神,分别是敢于犯错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他认为,否定旧理论是产生和发展新理论的前提,人们应具有敢于否定自己的精神。[2]否定自己,即否定之否定,人就会获得重生。只有否定过去的我,才能造就崭新的我。
一、身份转变,归时空场域之真
在本体论中,波普尔提出的“物理世界”包括三个层面,分别是无机界、生物界、人工物质世界。无机界指的是宇宙的物质与能量,生物界是指一切生物的结构与行为,也可以指代人体与人的大脑,人工物质世界主要包括工具的、机器的、书籍的、艺术作品的、音乐的物质基质。[1]
在《新生活》中,作者将空气、月色看作自然界,将下午五点、午夜时分等时间,广场、厨房、饭桌等地点视为无机界。在这些时间与场域中,共出现了三个人物,丈夫、孩子与“我”,组成了一个平常的三口之家,构成了生物界。在人工物质世界中,雪花膏、毛衣、商品、遥控器依次出现。以上共同构成了波普尔的第一个世界——物理世界。
在物理世界中,随着时空场域的变化,“我”的身份也在转变。从时间上来看,“我”从一出生便成为自己,在父母的精心养育下,逐渐长大成人,再与丈夫相遇,成为他人的妻子,随后孕育新的生命,成为一名母亲。因此,理想中的角色顺序应是自己—妻子—母亲。但是从《新生活》的原文中可知,“我”的自我角色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可以看到,“我”的日常生活路线是按照买菜—跳广场舞—洗衣做饭—做家务展开的,这俨然一位家庭主妇日复一日的生活,生活的重心是丈夫与孩子,完全失去了自我。一切以家人的需要为先,自己的需求被压制。在“我”的心里,家人平安幸福就是“我”快乐的源泉。这很现实,也很残酷。读者从中仿佛看到了一位中年女性被剥夺自我,负重前行的身影。
其实,人在同一时间段往往具有多重角色,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角色混乱与冲突。《新生活》中的“我”,在此时此刻也具有不同的身份。“我”是一位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中年主妇,“我”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我”是一名贤惠的妻子,“我”是广场舞的爱好者,“我”是购买雪花膏的消费者,“我”是患有腰间盘突出的病人……不论“我”是谁,“我”最先成为的应当是自己,只有成为自己,才有能力成为其他的角色。
从空间上来看,“我”的行动轨迹仅限于广场与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令人感到无趣。“青菜”代表的是“家庭的烟火气”,“雪花膏”象征着“精致的我”。去广场前, “我”坐在镜子前,对镜梳妆,涂抹散着阵阵幽香的雪花膏时,那一刻的“我”是喜悦的,“我”回归了本我的状态。当“我”从广场上回到家中,雪花膏的余味早已消散,随之而来的是黏腻的汗液、附着在毛衣上的痕渍,是腰间盘突出的刺痛感。在家里,“我”需要将一切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屋子整洁干净,以便孩子得到精心的照顾,丈夫回家就能吃到新鲜热乎的饭菜。不仅如此,“我”还要在饭桌前喋喋不休,缓和膨胀的、压抑的空气。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渐渐消失了,婚姻像牢笼,困住“我”不断向外延伸的四肢,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我”不仅仅是我,也是万千个家庭主妇的缩影,是中年妇女的世界和生命状态。
二、情感变换,求家庭与自我之善
波普尔在第一个世界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世界——人的精神意识世界。主观知识世界、意识与无意识状态、创造性与意向性经验共同构成了第二个世界。[3]
在人的主观知识世界中,“我”产生了“不要让面孔出现在新闻报道里”和“不要让青菜粘上雪花膏的味道”这两种认识。新闻报道里常出现的面孔是惊恐的、受伤的、哭诉的,主播清脆的声音时常传来“家暴”“离婚”的词眼,家庭妇女的婚姻显得岌岌可危。踏入婚姻的那一刻,新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岁月蹉跎,热烈的爱情总有一天会回归平淡,多年以前的期待与热爱如今已转变为麻木与恐惧。社会对女性的包容度不高,牺牲自我来成全家庭的戏码总是发生在女性身上。不知时间是否记得,“我”曾是青春靓丽的少女,“我”的心也曾为爱而悸动。因此,“我”才会喊出“不要让青菜粘上雪花膏的味道”。“青菜”是家庭生活的影像,是自我克制而不得不为的身份象征——家庭主妇。“雪花膏”是燃起“我”新生活的希望,轻柔滑嫩的肤感抚平“我”的疲倦与困顿,忽隐忽现的香气扑鼻而来,穿上华丽的衣裳,戴好璀璨闪烁的首饰,“我”终于成为我自己,不是谁的妻子。
意识与无意识状态的世界是主观的,比如爱与恨、痛苦与欢愉,它的存在依赖于心灵的存在。当“我”从广场上回到家中,为家人准备饭菜时,不会想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一种习惯,这样的妥协也被默许。毛衣上的痕渍是岁月施展的魔法印记,是忙碌操劳的见证,腰间盘突出是无声无息的病痛累积所致,这都是“我”无意识中的世界。当“我”打开衣柜,靓丽装扮,再在橱窗前敞开自己,被他人的目光遴选,这时的“我”充满自信、大气从容,任人打量也不慌不忙。同时,“我”也牢牢掌握选择的权利。作为顾客,“我”可以挑选好看精致的着装,让自己容光焕发,青春永驻。
在饭桌前,“我”依然可以主宰这一场域。“我”喋喋不休地摊开自己全部的皱纹,岁月催人老,但“我”勇于坦然面对,落落大方地摊开皱纹,使之暴露在空气中,而不是用多余的脂粉遮盖美丽的褶皱。于是,在午夜时分,顺着那散发诱惑的遥控器,“我”决意抛开所有的条条框框,奔向心之所向。在电视机屏幕的背后,有充满诱惑的极乐世界。一边放映着温馨甜美的婚姻生活,一边播放着黑暗世界的人情冷暖,“我”不禁要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这样的妥协与牺牲是“我”想要的吗?一旦出现怀疑,就代表“我”正向灵魂深处的自我迈进一步。
创造性与意向性经验可以解释为人的主观创造性。在《新生活》中,“我”在广场上跳动的时候感到自己“年轻了二十岁”,踏着节拍,随着喧闹的音乐,双手“向上,向上举,转个圈,一二,一二三”,摆姿势,定格。舞动的身姿曼妙,绽放的笑容迷人,这是属于自己的空间。跳舞的时候,每一个“我”都摘下生活的面具,重新做回自己。这是找寻自我的巨大转变。“我”在饭桌前想要缓释空气中肿胀的亲情,于是由“我”来打破沉默的僵局,此刻的“我”仍然拥有选择权。但从侧面也可看出,“我”的家庭关系并不和谐,理想的状态下,一家人应当是其乐融融、谈笑风生的。而“我”的家庭,需要靠“我”不停地讲话来维持气氛,空气中弥漫着冷漠、忽视、自私。
月色照映,“我”为每一个新身份战栗不已。未来有无限种可能,牢笼里的鸟儿突然被放飞,一定会感到不安与无措,“我”的未来又在何处?否定自己的开始,便是意识唤醒的基础。
三、意识流动,至自我觉醒之美
波普尔认为,精神产物的客观世界是第三个世界。包括客观知识世界,人类的智力成就以及理论体系。世界三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艺术作品的世界。世界三是从世界一和世界二派生出来的,构成了一个客观知识与精神的世界。[4]从客观知识的角度来看,人生来就拥有多重身份。作为女性,需要打破自我、追寻自我价值,获得世界重构。人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中,年轻姣好的面容总有一天会布满皱纹,人的意识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成家立业之时,“我”所向往的是神仙眷侣的婚姻生活,爱情与事业可以兼而有之。养育孩童之时,“我”的生活充斥着婴儿的啼哭声与丈夫的酣睡声,“我”所期待的是丈夫的呵护与家人的关爱。人到中年,看着镜子前的“我”,容貌不复,时光不返,婚姻生活也一地鸡毛。放弃职场,专注于家庭是“我”的决定;家人态度冷淡、家庭气氛压抑是对“我”的回应。终于,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开始觉醒。遥控器散发着诱惑,“我”轻轻按下按钮,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抛弃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过去的“我”。“我”就像试衣镜前的儿童,睁大了双眼,诧异地看着眼前人。原来,“我”的生活不止一种方式,“我”的身份是多元变化的,那么“我”也可以否定自己,重获新生。挥别过去,决定命运的权利始终紧握在自己手中。
青菜和雪花膏是人类智力活动的客观产品,一方面象征着家庭,一方面代表自我。“不要让青菜粘上雪花膏的味道”,说明女性在家庭和自我之间产生了冲突矛盾,如何构建平衡是女性需要解决的问题。牺牲小我,成全大家庭不是良策,女性应当注重发现自我价值,不破不立,重拾女性选择自由,不惧年龄,将身份选择的自主权交给自己。随着对自我认识的加深,女性身份选择的可能性会日渐增多。因为身份的构建不是一成不变或永恒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人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当下的“我”不是最好的“我”,未来的“我”值得期待。
第三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流动变化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回忆过去,“我”一定踩着青春的步伐,朝气蓬勃又打扮时髦。回顾当下,“我”的身份发生变化,成为一名母亲后,“我”的身材开始不受控地发福,污渍爬上衣服却不自知,“我”对这一切变化任劳任怨,甘之若素。然而,在这种稀松平常中,“我”压抑不住自己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对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期盼。趁着月光到访,“我”摇身一变成为试衣镜前的孩童,并为自己的新身份战栗。展望未来,“我”能够坦然接受眼前家庭成员间的貌合形离,能掌握命运的邮轮,超越自我,回归本我。镜像与孩童是自我意识启蒙的象征,由此“我”的自我意识得以重建。
在这三个世界中,还存在他人的意识。正因群体他人的聚集,才能够明确外部世界的构造。人与自然在世界中和谐相处,月色为“我”加持改变的力量。人与人密切交往,“我”与跳舞的姐妹相约一曲,互相惦念。
四、结语
三个世界中,世界一是外在的,能够被感知的,是世界的最基本层次。世界二指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和思维活动。世界三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凝聚。世界一产生世界二,世界二产生世界三。同时,世界二反作用于世界一,世界三也对世界二起反作用。因此,可以说科学的规律必须要经过人的主观意识与理解,才能作用于物质发展。一直以来,男权社会要求女性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女性曾久久无法摆脱这种意识。女性在重构自己“特殊”身份的过程中挣扎,为冲出重围、摆脱这种刻板印象而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女性应当明确探索身份构建的正确方式是勇于改变,摆脱内在性,唤醒超越性,做出自由选择。[5]女性应该认识自己,成为生活中的主体。女性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自我,才能实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