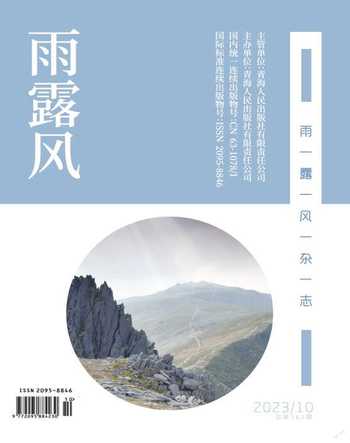探究《宦海升沉录》的主题内蕴
陈晓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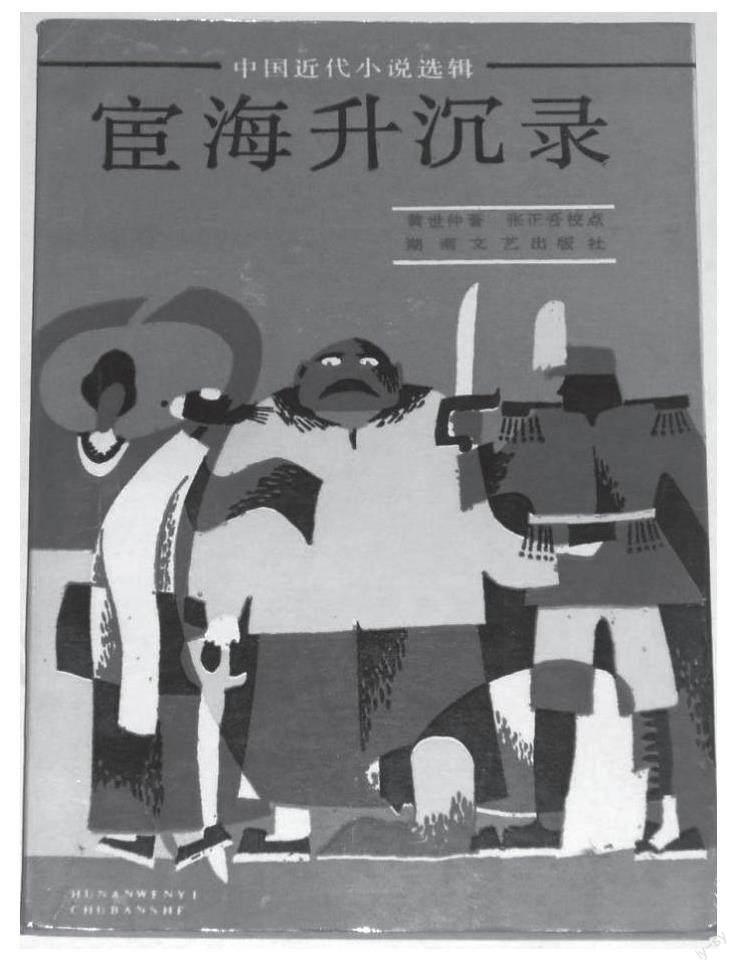
晚清革命派文学小说领域以黄世仲先生为代表。黄世仲先生是一位声震华南及南洋一带的小说家和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文学家,创作近事小说的初衷是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把小说当作政治的传声筒,其作品《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以袁世凯作为线索人物,通过对其发迹至被罢黜过程的详细描写,展现官场的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等弊端。但小说并不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轶事来补正史之不足,而是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对众多的历史事实进行取舍、抑扬乃至虚构,来达到“言志”的目的。
一、《宦海升沉錄》的创作背景
《宦海升沉录》贯穿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09年袁世凯被罢黜的晚清十余年间的军国大事。小说的两首篇首诗,不仅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意图,还说明当时中国的国土被外敌瓜分的国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当时各界人士纷纷寻求出路,而此篇小说正如黄世仲之兄黄世耀在该书序言中所称,是要“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1]1。
同时,黄世仲先生本人所经历的身世浮沉和世风变化对其作品有较大影响。黄世仲先生虽曾家世显赫,但其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他虽自幼聪明,却难谋出路,只得随兄长到南洋谋生,异国漂泊,倍尝艰辛。回国后,政局急剧动荡,清朝专制政府操持生杀升黜大权,官场变幻无常。他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且在此之前就参加过大量的革命实际工作。这种身份与经历,使得黄世仲先生的小说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表达其对现实人生的深切感受。
二、《宦海升沉录》的主题意蕴
《宦海升沉录》的直接创作动机是以袁世凯为鉴,警醒汉族官僚勿为王朝效力,“盖恍然于高官厚禄,名动中外,所为媚朝家而忘种族者,一旦冰山失势,其结局亦不过若斯也”[1]2。黄世仲先生想借这部小说唤醒像袁世凯这样效忠清廷,只为自身利益的汉族官僚倒戈反正,从而投身革命。出于这种创作目的,小说将描写的笔触投向政治活动方面,“一般的暴露官僚小说,只暴露他们的丑态,而《宦海升沉录》却把重心放在政治方面”[2]。在此基础上,我认为黄世仲先生在《宦海升沉录》中的主要思想意图,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批判社会之世态炎凉,揭露宦海浮沉之悲哀
黄世仲之兄黄伯耀为《宦海升沉录》作序时说,该小说“极世态之炎凉,尽人情之冷暖……胡功名富贵,风潮变幻,一至于此!此《宦海升沉录》之所由作也”[1]1,从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李鸿章得势之时,所有人都以被他责骂为荣,因为他责骂的都是他赏识之人,包括袁世凯。他一开始被无故责骂之后十分恼怒,誓不再与李鸿章来往,但知道该暗语之后,便又十分敬重他。而李鸿章因犯错误被降职后,在是否实行太后垂帘听政之事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却被一位亲王以“此乃我们家事,李中堂你不必说罢”[1]62噎住,不敢再说。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世情冷暖如此,正是由宦海浮沉而引发的。《宦海升沉录》以袁世凯作为统摄全篇的主脑,对影响其宦海升沉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按回分段,顺次铺叙。袁世凯出场时仅仅是一个道员,但他机警过人,“自念先人在清国做大官,有许多功劳,料然有许多同僚,都是自己世交,正要寻一条门径,拜谒一两个有位有势的大员,凭他扶助,才易出身”[1]11,善于察言观色,结交权贵,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又入军机,组内阁,最后因权势过大遭人嫉恨,在清朝权贵的排挤打压下,被迫称疾引退。这样的结局虽在作品开头便已埋下伏笔,“犹之国家有事,就要用能臣,及国家偶然没事,那些枭雄之主,就怀个妒忌之心,差不多要把那能臣,驱的驱,杀的杀”[1]10,但依旧令人唏嘘,官场没有定数,宦海升沉,顷刻变幻!
(二)反对专制独裁,提倡革命
黄世仲先生将清朝统治者及其政权放在暴露、抨击的位置上,揭露“清廷无道、官吏贪庸”、绞杀革命的种种罪行,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提倡革命救国。在经历宦海浮沉之后,作者深切地认识到清朝贵族的专制独裁乃是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最顽固的阻力。小说写袁世凯在政务会议上主张办理新政,受到清朝特权集团的强烈反对,至欲拔枪射击袁世凯。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清朝贵族的特权发生冲突,被扼杀在摇篮里。因此要革命,首先必须推翻清朝贵族统治。且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山东巡抚之位本欲推袁世凯,但满族官员认为直隶山东逼近京师,应用满族心腹。且满族官员的一番话语:“只说满汉平等的话。你道什么平等呢?难道要把我家皇帝的大位,还要给汉人轮流坐坐么!况我满洲人总不及汉族的人多。若是满汉真正平等,怕汉人强,就满人亡的”[3]69-70,
可以看出袁世凯再怎么得重用,但因其汉人身份终有诸多限制。再者小说的开篇以伍子胥为例,说明“异族专制朝家,杀汉人如同草芥”[3],从而警醒国人:只有推翻清朝贵族的统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立宪的梦想。
当然,作者主张推翻清朝贵族的统治,不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激愤,同时也是基于对清朝贵族统治下官场之腐败的深恶痛绝。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之下,“造反有理”,他说:“乱于文明之世者为反,乱于腐败之世者为义,使时当乱而不乱,是坐视斯民于水火之间,而不为之拯救,此逸民忘国者流,汤武等所不为也。”[4]此时的清朝就处于“腐败之世”,正因为黄世仲先生对当时官场的腐败有如此深切的认识,所以他才对官场腐败口诛笔伐。
(三)愤懑国势之衰败,唤醒国民以崛起
国势衰败的第一个表现是国家兵力薄弱,军官贪生怕死,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前因日本干涉朝鲜内政问题,交涉无果,暗中派兵万余人,而清国兵力不过数千,又不惯练,因此日人开战挑衅。一经交锋,清国就失牙山。后有叶志超贪功误事,眼见寡不敌众,枪械又不若他人之精,便乱报胜仗做逃兵,导致国土尽失。作者在这里概述中国国势衰败导致诸多战争及失利的情形,感愤国力衰微、国民麻木软弱。
国势衰败的第二个表现是外族频繁入侵,政府割地赔款,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小说第四回中写到日兵声势浩大,不断掠夺城池。而清朝已无兵力抵挡,投降求和,“整整赔二万两,割台湾一省,方才事”[1]40。此后不断地割地赔款,主权尽失,财政亏空,国民饱受战争的苦难。作者借袁世凯之口说出“己国自中东败后,焉能与各国相抗”[1]96这一事实,表达对国家无力、外族入侵的悲愤。
国势衰弱的第三个表现是外交上无法抬头。与英人争夺苏杭甬路事的主办权无果,汪大燮只能改议借款修路,但苏浙人士认为借款必受英人限制,与失权无异,也不同意。作者借汪大燮的辩驳和袁世凯之言说出国势衰弱、外交失利的无奈和悲哀:“自念国势力弱,一经决裂,必须言战,实无可以抵御之法”[1]185,
“国家里头,势力现在微弱,若外人不再来索取权利,已是万幸,还哪里好把已经让出的争回”[1]179。这些饱含民族屈辱的话语令人义愤填膺,作者望以此唤醒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奋发自强。
可就在这种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情势下,执掌朝政的京中官员们依旧没有革命救国之意,只想着借助外在力量以保全朝廷,保住他们的权力。当时,俄罗斯假意说欲助中国自强,要扶中国维新,清朝官员便以为俄国可靠,提出联俄之说。作者当即指出这只是哄骗清朝官员的说辞,且以当时许多转向外求实学的人组建拒俄义勇队的事实佐证,以告诫国民当自强。后因联俄事件的误会引起革命热血之士贾炳仁对袁世凯的刺杀,被擒住后,他视死如归,对袁世凯慷慨陈词,“炸药轰开新世界,狂澜倒尽逆潮流。此生羞读支那史,有几男儿识国忧”[1]115,抒发他的豪情壮志,使袁世凯为之动容,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和“士各有志,不能相强”的理由赠款刺客并使之南归。小说将袁世凯塑造成一个深明大义、同情革命的官员形象,鼓励国民从麻木中觉醒,奋起革命,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
(四)攻击政敌,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仅二十二回的章节中,黄世仲先生不惜以两回的篇幅,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采取讽刺、夸张的手法加以描写。首先是小说中称康有为为“康无谓”,“无谓”与“无为”同音,即含有康有为无所作为的意思,且在写到康有为宣扬自己主张的学说时,使用的是“鼓吹”“吹嘘”等贬义的词语。其次由于个人与党派的偏见,黄世仲先生对于康有为的变法持全盘否定乃至丑化的态度。在近代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戊戌维新,其诸多举措在黄世仲先生的笔下,都成了“统不过是说筑铁路、开矿产、设邮政、废科举、兴学堂、裁冗员这等话头,本是寻常之极”[1]50。甚至于不惜篡改广为人知的事实,将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改为康有为携密诏夜见袁世凯,袁世凯被康有为屡屡催促发兵,不得已向荣禄告密。这些混淆是非、违背史实的描写,曲意维护袁世凯,只为对康有为进行揶揄与攻击。作者在两回目的章节中极尽笔墨地描写了保皇派糟糕的一面。
當然,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世仲先生对保皇派的描写具有如此明显的片面性是有原因的。其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加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宣传,并谋求华侨的经济资助。而当时海外华侨的经济资助是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其二是他所代表的党派与康有为等人所持的政见不同,“以同盟会成立为嚆矢……由政见上的对立走向感情上的敌视”,[5]那么在自己的小说中丑化保皇派,也是在所难免的。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能看出,清政府是强大的反动力量,加上外国势力的支持,单靠软弱的光绪皇帝的开明政策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立的。中国要想有出路,只有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揭穿保皇派的反动面貌。因此,正是出于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海外华侨支持的目的,黄世仲先生才有意通过通俗小说这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揭穿康有为等人的庐山真面目。
三、黄世仲先生的革命书写
作者主张“取材从实”,认为小说应接近生活实际,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宦海升沉录》有大背景中的显著痕迹,也有自己主体性创造的内容,塑造了一个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精明强干、豁达大度的袁世凯形象,且十分传神地反映了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幻想——袁世凯手握偌大兵权,一呼百应,若能鼓动他开展革命便是极好的。尽管作者批评这种举动之无谓,指出“不知袁世凯固是无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1]136,
但在情感和艺术形象的内在魅力上,小说还是万分倾心于袁世凯,并为这“造世英雄”的最终被斥而深深惋惜。黄世仲先生所属的革命派以排满而否定立宪,倡导破坏而轻视建设,以狭隘的民族情绪,模糊革命党人的视线,使他们对于汉族军阀袁世凯抱有在如今看来极为幼稚的幻想。由此看来,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轻易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确实可以在其自身找到原因。小说所精确刻画出来的革命党人的微妙心态,已经预示了历史的某种必然性,这或许也是《宦海升沉录》的历史价值。
以文学样式鼓吹改良政治或宣传革命,为当时风气。黄世仲先生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他的小说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目的。《宦海升沉录》中的观点大都能渗透在生活画面的具体描绘之中,作者善于广泛地、多角度地反映生活本身,描摹世态情伪、暴露社会弊恶、反对清朝专制,表达对国势衰微的悲愤,力图唤醒国民以自强,其中也夹杂个人情感,褒贬过甚,因此其所叙历史,虚多实少,政论色彩浓厚。
注释:
〔1〕黄世仲.宦海升沉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2〕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梁冬丽,纪德君.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创作意图[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5):67-70.
〔4〕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方志强.黄世仲大传[M].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