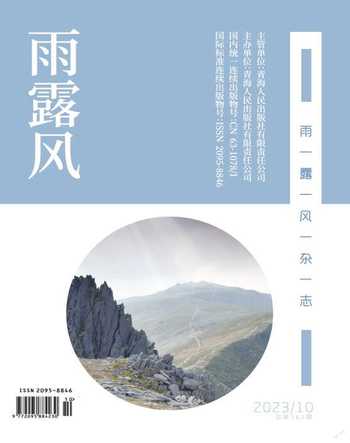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文学批评中的水域想象探析
在社會和经济急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生命健康遭受威胁等令人担忧的现实景象。劳伦斯·布伊尔作为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生态文学批评家,试图用自己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积极去寻求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方式。他在其第二本生态批评专著《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的第六章中,总结了全球生态文化应关注的重点,其中对海洋及其他河流流域退化的担忧最为突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中,海洋、河流一直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对海洋生态、河流生态的关注也就成为了布伊尔环境想象理论中的水域想象的主要内容。
一、海洋想象
布伊尔的海洋想象主要来源于他对海洋生态、海洋与人类关系以及对美国文学史上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的关注。他坚持认为从希腊神话伊始,文学创作就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盾上“海洋河流形成了‘最远的边缘的周长”[1]233。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一书中详细叙述了马洛在泰晤士河边的痛苦回忆,进行贸易的船员们举着“利剑”猎取黄金,追名逐利,肆意扩张,促使人们对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泰晤士河和刚果河在历史进程中的遭遇引发深思。
布伊尔认为卡逊虽然因为《寂静的春天》而出名,但在日常生活中,卡逊对海洋更感兴趣,其“海洋三部曲”使得卡逊成为一个关注自然生态进行自然写作的伟大女性作家。布伊尔认为,作为海洋想象写作的代表,卡逊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环境伦理与生态意识值得我们研究和考量。
布伊尔认为卡逊在“海洋三部曲”中通过对海洋的想象性描写体现了敬畏万物的伦理情怀。海洋其实就是一个庞杂的生态系统,食物链将各种形式的生命体联系起来,海洋生命周期就在食物链这样的循环中生生不息,循环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被保护,不能被人为过分地干预,就连海边的沙子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物质,沙子经过海水的冲刷腐蚀,太阳的暴晒,风雨的侵蚀,仍然美丽且神秘,对这些矿物质的了解,同时可以回顾到地球乃至生命的开端,这也表明了生命生生不息的现象。布伊尔认为,万物终将归于海洋,卡逊在《我们周围的海洋》一书中描绘了古往今来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流,以永恒回归的意象开始和结束,“把海洋作为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的、精神的和经济的资源”[1]233,以“最后一切都回归大海”作为结尾,象征着不论任何生物,最终以物质循环的方式回到大海之中,一切将回归于大海,海洋像母亲一样孕育着一切,也主宰一切。海洋也像时间,承载着永恒的生命,生生不息。
布伊尔认为鲸鱼作为海洋中的代表性生物,“分享了海洋神秘的、激进的、模糊不清的差异性:象征着神圣的力量,无论是良性的或威胁的。”[1]237因而,鲸鱼成为了文学创作中海洋想象的典型形象。布伊尔认为尽管关于鲸鱼的文学想象已经很丰富了,关于鲸鱼象征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但是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超过《白鲸》一书的文学高度。十九世纪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点在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上有所体现,鲸鱼作为大自然野性的象征,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了反抗人类的自然代表。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以美国十九世纪大量捕杀鲸鱼为背景创作了《白鲸》,书中主人公亚哈船长在一次与鲸鱼的抗争时失去了一条腿,之后变得越发疯狂,出于想复仇的目的继续大量捕杀鲸鱼,他不听船员的劝阻,最终落得船毁人亡的下场。亚哈船长的行为其实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违反,且试图改变这种规律。正是由于人类为了商业贸易对白鲸无休止的捕杀,使得白鲸为了生存一次又一次地与人类做抗争。因此,布伊尔认为,小说通过对海洋和鲸鱼的想象性描写提醒我们,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人或事都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二、河流想象
河流是古老文化的一种象征,没有水就没有人类的生存,没有水就无法产生文明。布伊尔说:“流域是一个审美的、伦理的、政治的、生态的明亮意象”[1]247。
他认为,流域想象的关键是要能创造一种流域意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部分美国文学家才注意到河流的生态问题与人类的生活生存有很大的关联,并创作出了具有一定生态意蕴的以河流为创作题材的文学文本。
布伊尔认为,河流文学文本在美国的文学史上有两个阶段的过渡,一是梭罗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个星期》(又名《河上一周》)一书,梭罗以独特的生态视角,揭示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两条河流的自然和文化生命,且提出了应该保持河流的自然和文化生命之间的联系来保持河流的生生不息;二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该书是一本自传式游记。马克·吐温回忆了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的经历,并认为那段经历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认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加深,因此应该回归人的自然天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真正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但是,布伊尔认为,第一个通向现代河流水域写作的作家是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其作品《福特》最具有代表性。布伊尔在对玛丽·奥斯汀的《福特》进行分析时指出,作家在对流域进行想象写作时应当具有开拓性的审美思考。“开拓之一在于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理想或者是一种生物区域经验的现实”,“为生物区的文化碰撞与文化多样的阐释奠定了基础”[1]256。布伊尔认为河流流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能够形成内部自给自足的“社区”区域,而是一个开放且能够一直与外部环境保持整体关联的地带,布伊尔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河流想象就是试图将“流域”建成一个自由开放、多样共存的“审美共同体”。
布伊尔认为,“小流域”不仅是一条小河,而且是一系列的社区,以及一大片与土地连接在一起的区域,所以,布伊尔不同意把城市、村庄以及河流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因为很多城市都是依靠港湾、河流而建的,因此,这些河流流域必然包括人类生存的陆地、城市以及其中的生物圈,流域意识也包含更显性的多元文化,人类建立、居住的场所也要与其依赖的河流流域保持整体关联。从生态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河流地质以及其他地理因素的影响,河流的走向、形成的冲积平原、林地、湿地等对于改善人们所处的环境,促进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促进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河湖泊是构成具有生态美感城市的重要因素。此外,布伊尔认为河流流域范围内同时积淀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因此布伊尔在批评、分析以河流为想象对象的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视“时间”问题,而这也延续了美国自然写作中对“季节元素”的重视。时间是文学作品进行叙述时的一个重要元素,除了年月、昼夜、时分外,季节成为了人们最为熟悉的时间概念,文学创作者尤其是生态文学作家一般会遵循季节变迁的时间顺序进行环境描写以及故事叙事。因此,布伊尔认为以季节顺序对水域内的人类和自然进行叙事是河流想象的文学创作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文学创作者感知自然、诗意地栖居于自然的重要方式。
布伊尔认为《瓦尔登湖》是美国文学史上河流想象的文学作品中采用季节变迁顺序进行创作的典型代表。《瓦尔登湖》开始的时间是第一年的春天,结束于第二年的春天,形成了一个以季节变迁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框架下,梭罗也并没有平均分配四个季节的占比,他对夏季的描写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为梭罗认为,夏季更能给人类以乐园似的生活,在夏季,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是最少的,需要去追求的物质也是最少的,不必为了取暖去伐木以及出现其他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破坏大自然的事情。这也传达出梭罗“物质多少并不影响诗意地生活”的观念,只有拥有富足的精神生活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
布伊尔不但关注河流想象中以季节为叙事时间的问题,同时他还认为可以用一个人的探险经历、游历、旅行的经历去展现河流想象中的文化记忆,这也是河流想象写作的一种基本叙述结构。布伊尔以艾伦·美洛伊的《乌鸦的放逐——绿河上的一季》一书为例分析了这种叙事结构,书中主人公在漂流旅行中展现了季节变化中河的水位的高低变化及其带来的其他植物的生长变化,以及主人公对绿河流域的记忆。布伊尔强调,我们在对某一河流的写作过程中,可以采用季节这一时间来进行描述,也可以用一个人的游历去展现,帮助读者看到主人公不同时期的变化,寻找到属于不同时期的特殊的文化记忆,同时可以传达出文学创作者以及流域内居民的生活理念和生态意识。
三、环境正义
以布伊尔为代表的第二波生态批评家在构建生态批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环境正义。布伊尔认为不管是在现实的层次上,还是在想象的层次上,都要注意到个人的价值和真正的目的,站在一个生态的总体角度上来看待环境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布伊尔主张,由于江河流域也包含了人居住的地区,因此,在对江河流域的写作中,也应注意到江河流域中的环境公正,即要反映江河流域环境所蕴含的深刻的伦理学美感。批判、谴责对穷人、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原住民聚集地造成的环境毒害与生态破坏,反对在这些弱势群体、受到歧视的人群的居住地区设立垃圾场和其他污染性的工厂。
布伊尔认为水域想象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更好地表现了这一点,要关注且承认整个流域中生物、文化存在的多样性,承认多样生物、多种文化之间的平等。例如蕾切尔·卡逊的处女作《海风之下》就是一部典型的自然写作风格的作品,但《寂静的春天》虽然立足于自然写作,风格有了更大的变化,卡逊初期的作品花大量的笔墨描绘自然景观,但是在《寂静的春天》的写作中,不仅关注自然景观,同时关注自然遭受破坏之后,人类尤其是弱势群体所经历的更多不公平的对待。布伊尔认为如果卡逊仅仅是关注自然景观,那《寂静的春天》也不会成为经典。再如,威廉姆斯在《心灵的慰藉》中,能够自觉将大盐湖的自然书写与家族女性患癌的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分析,能够在“关于环境性癌症患者群体的自传体叙事中,自觉地融入了大都市与城市远郊文学的体裁特点”[2]28。
布伊尔认为关于“环境正义”的思想在“流域文本”中也应有更多的体现,布伊尔通过美国小说家珀西瓦尔·埃弗雷特的小说《流域》阐明了这一观点。主人公罗伯特·霍克斯将个人所见与文化记忆联系起来,作品中暗含着生态种族主义的观念,实际上也是对环境正义的关注。
布伊尔通过提出“环境正义”,不仅将环境批评家们及文学创作者的视角从关注自然环境转向关注社会环境之中,而且希冀更多的人在思考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的同时,关注处在社会边缘以及社会底层民众们的生存困境以及命运发展状况。
四、结语
布伊尔的环境想象理论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乃至全球生态批评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即环境批评领域出现了更多的生态学者和生态文学作品,进而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持续关注,加强了公民对环境保护、人的生存境地、地球的命运等问题的关注。对于社会个体的生态责任,布伊尔如是说:“我们坚信世界正在忍受多重的生态危机……虽然文学艺术领域可能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法律或者应用科学那样,在处理生态问题上是一条实用的途径,然而它却是至关重要的。”[3]因此,笔者认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不应该只依赖应用科学领域,文学也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文学具有独特的优势,即运用艺术想象的方式,通过多种体裁、主题、叙事方式,以灵活的方式表现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借助文学艺术形式特有的感染力来影响读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唤起人类的生态意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交互的,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自然会以何种方式回报人类。人类与自然万物休戚与共、生生不息才是正確的生态文明态度。
基金项目: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1M2022004。
作者简介:陈怡(1998—),女,湖北宜昌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
注释:
〔1〕(美)劳伦斯·布伊尔著,岳友熙译.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美)劳伦斯·布伊尔著,刘蓓译.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岳友熙,劳伦斯·布伊尔.美国生态想像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访劳伦斯·布伊尔教授[J].甘肃社会科学,2012(5):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