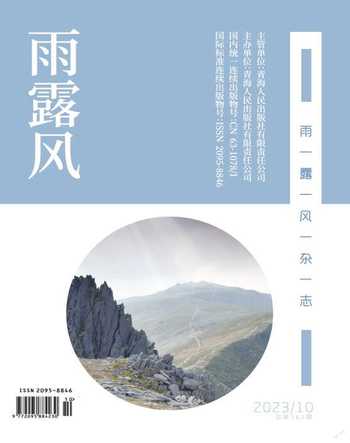从《美学散步》看中国艺术之“天人观”与辩证思想
李静怡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集中表达了对“美”的探讨与理解,从书法绘画等具体艺术形式到“充实与空灵”“中国意境之诞生”的空间意识等,中华文化蕴含的美学思想被他藏匿于字里行间,抒写着“美”的格局与风范。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艺术表现博大精深,但细究其根本,天人观念与辩证哲学思想是浮动在其中的主旋律。“天人关系”在中国艺术中对意境的创造发挥了极大作用,由艺术延伸到思维,其思想内涵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中国千百年的历史进程,至今仍可窥见其印迹。中国艺术表现手法体现出辩证法色彩,“辩证”并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对立,其中“虚”与“实”相生包含的哲学思维和宇宙观是整个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本文将在《美学散步》文本基础上,对其中蕴含的“天人关系”及辩证思想进行集中探讨。
一、天人观念
“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美学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便是“物我两忘”。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将中国大部分艺术表现形式的源头指向舞蹈艺术,认为舞蹈动作能够表现大自然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舞者在肢体舞动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同频共振。由此过渡到书法绘画和建筑艺术,人们习惯用“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矫若惊龙”等成语来形容书法作品的美,细观之这些成语无不在向人们表现着墨迹在宣纸上游曳舞动的风骨姿态。同时就其他艺术形式来看,书法讲究粗细长短的变化,如隶书讲求“蚕头凤尾”,古典建筑的屋顶多带有“飞檐”构造,如《阿房宫赋》中描写“各抱地势,勾心斗角”……这些表现形式不仅说明艺术在力图表现、再现自然,同时各种艺术形式在借鉴自然界万物的外形和功能的过程中,得到了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收益。
中国古代艺术家追求的自然与天人合一,上可追溯到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古人在思考人处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庄子曰“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可以说,这种以小观大、由近知远的空间意识,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特色,这一宇宙观更是进一步影响千百年来国人的思想观念。
晋代是中国诗人山水情绪开始与发达的时代,可为何是晋代呢?其实联系历史便可知,晋代世事复杂多变,文人求外物不得,只好将情感寄托于山水自然,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人与自然联系的重要原因。“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文人在自然中寻求生活的真意,“天狗吞月”百姓用天人观念解释超出认知范围的不可控事件,中国人的天人观念由此经历代延传而根深蒂固。
但就中国艺术来看,山水自然本无情,文人却将自我的深情或愁苦予以其中,花开花落等山水的自然动态变化,又无意间给了文人以回应。“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敏感的诗人捕捉到这回应,便完成了人与自然的沟通交流,由此诗人情感抒发也形成了有来有往的闭环模式。
这种人与自然的交流,对于排解抑郁、抒发情感是有利的,并且极大程度地主导了中国诗歌创作的走向。但是在人与自然的一次次沟通交流中,人们的思维也逐渐被固化。
这种固化一方面体现为国人似乎重新陷入了“看水便是水,看山便是山”的境地,即自然万物所负载的情感几乎固定。看到落叶忽感惆怅,看到嫩芽又似乎获得新生。为何“潇潇暮雨子规啼”配合“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便能一鸣惊人,为何“化作春泥更护花”“病树前头万木春”能够在一众诗词中脱颖而出?窃以为在这里文人们没有陷入思维固化的怪圈,但今之众人,却每每见落红、朝暮便无病呻吟,这不得不说是对古代山水天人观念的滥用。
另一方面,“看山还是山”体现在以小观大的观念上。古代由于交通闭塞,诗人每天望见自家门口的群山即发出感叹,进而展开想象,由近及远在天地漫游,这本也无可厚非。况且有说法指出,李白的《蜀道难》便是出于想象创作。“噫嘘嚱”,但世间再无李太白,中国古代宇宙观念的局限性并没有因为一代诗仙的想象而发生突破,“窗含西岭千秋雪”“两山排闼送青来”“朝挂扶桑枝,暮浴咸池水,灵光满大千,半在小楼里”的这些诗句将天地景物吸收于门户,表现出万物皆备于我气象。
“宇宙”二字中,“宇”是屋宇,“宙”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人在屋宇中得到时间观念,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习惯。“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一个“聚”字,在自然中聚集了千里之外之景,于诗词中凝聚成了整体意境与情感。这种现象或表现形式,用辩证关系解释,确实达到了以小觀大的艺术效果。同时他也确实从侧面反映出了古人对待自然与自我的态度,这一“聚”从艺术形式回到个人,便是回归到人的主体性上。万物皆备于“我”,“我”在一窗一户之间便能窥得整个宇宙,这无疑是变相地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人的主体性”这一意识和观念并不缺失,并且还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加深和阐释。
这种观念于今来看,是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古代中国的社会背景确定了这一进步有其局限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少数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极端。文化的解释权收归到上层阶级而不再具备普适性,这一现象也进一步巩固了政治上的权威性。“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诗句无不在表明,诗词歌赋等文学大多适用于上层社会,“天人观念”加之“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性,在政治上便反映为专权。再者从思想层面来看,当思维观念局限于“万物都可涵养于一屋”,试问我们有什么动力和欲望去向外探索呢?窃以为“独在小楼成一统”的困境由此初见雏形,以至于后来发展到思想固化、愚民政策、闭关锁国的历史结局便是后话。
于今我们在传承中国传统审美思维观念的同时,要警惕这种顾影独怜、“闭门观景”的深层思维局限,由此才能实现中国审美的思想的进步,实现中国天人观念在新时代的发展。
二、辩证思想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传达出的另一艺术表达技巧便是辩证思想,具体来说便是一种对比观照的形式。
中国艺术多传达意向、意境,而非看得见的美。一个年纪尚小的学龄前儿童,她看到花可能会发出赞叹,但见落叶却悟不出美,原因为何?因为花由于其色彩、花纹的协调性,它的美是出自审美本能可感知的美。这里需要着重强调,“协调性”同作者在前几章讲述“美”的定义是相契合的——“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两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现实人格的谐和的是‘美”。但落叶的美却似乎违背了“协调性”这一原则。若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文化积淀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乍然面对一片残损飘零的落叶似乎无法自然而然生发感慨。但这种基于文化涵养和人生境遇所感受到的“和谐”和“美”,才是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意境的内涵,这里的“美”是外物与个人情感产生的和谐。
艺术家与自然和内心的对话过程,可以理解为“写实—传神—妙悟”的进阶深入过程。写实在于单纯描摹自然万象,传神则是逐渐寻得了“物”与“我”的精神连接点,而最终达到“妙悟”则是于天地间生发体会,回馈到自身人格上便是实现了“物我相融”的境界。在这个过程里,艺术家完成了意境的创作,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内化。
宗白华先生说“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想要营造这种美和意境,艺术家可以将自身的情感注入到作品中,但艺术家却无法保证每一位观赏者都有与之相同的情感体验,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琵琶女可遇不可求。那么这便需要艺术家在技法上下功夫,辩证思想则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极具概括性的方法。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多次举例说明了这一技法的运用,如行书书法中各笔画能做到“形散神不散”、风骨气韵并生,依靠的便是“虚笔”的勾连;音乐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后须得有“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的配合;诗歌里有月照深林下,“僧敲月下门”的细腻推敲,以及董其昌的“摊烛下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这些艺术创作无不体现着虚实、动静、远近关系的相互观照。
“意象”中的“象”指真实存在的场景,而“意”则是给读者提供的臆想创作空间,两者结合为“虚实”创造了发挥空间。意境的创作,细思之便是从寻常物中获得“超脱物外”的情感。正是那一帘窗纱,隔开了虚实,创造了想象的空白,从而达到了诗人想要传达的意境。“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可无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是宗白华在作品中提到的中国艺术处理空间的表现方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虚实”这对关系在中国艺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这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强调这种“虚实”的宇宙观若表现在艺术上,则“要求艺术也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艺术的本质是真实,片面强调“美”,脱离现实,会使作品不接地气,如空中楼阁,陷入“唯美主义”的怪圈;而片面强调“真”,单纯写实创作,作品难免枯燥无味、缺乏灵气,随之局限于自然主义。艺术的装饰性是艺术中美的部分。但艺术不仅满足美的要求,而且满足思想的要求,要能从艺术中认识社会生活、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规律。传递“真、善、美”是对艺术品的统一要求,而“虚实结合”则是实现这一要求的要义。
宗白华先生提倡的是“艺术是一种创造,要化实为虚,把客观真实化主观的表现”。“虚实结合”,有“实”有“虚”是中国传统创作的美学思想,固定形象、景物为“实”,其表达的思想情感、 意境主题为“虚”;作者塑造的“物”为“实”,是现实的缩影与投射;其在“物”上赋予的精神、品质和情感为“虚”, 那是主观世界的表达,是灵魂的呈现与洗涤。宗白华在书中提到龚定庵在北京时曾对戴醇士说“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席前,不关风雨晴晦也”。“不关风雨晴晦”,那么关乎的便是看山的心境。山水的“实”与心境的“虚”构成了意境和情感的流动,虚实两维交替构成现实世界,以此引申出艺术“虚实”观的价值意义。
《美学散步》从各个艺术层面对“虚实”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书法绘画中,齐白石的“虾”是“虚实结合”的典型范例,他的艺术作品在画面中进行了留白,意在留给鉴赏者自由思考想象的“空白”。西方画作《蒙娜丽莎的微笑》中,人物的笑容包含多重意义。几百年来人们想要从这双眼中窥得秘密、分得幸福,但其实变换角度,“蒙娜丽莎”也在凝望着我们;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宗白华借用老子的话“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来表现其中的艺术塑造手法。宗白华先生指出中国园林艺术大多依靠亭台楼阁的配合,达到“一步一景”的效果。“隔床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帆影都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这些诗句所表现的“镜借”“对景”等取景方式,更是“景映镜中,化虚为实”,达到了丰富空间美感的效果。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以实际的作品形象传达思想情感和艺术品位,构成艺术美感中的“虚”与“实”。
综观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虛实相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艺术来源于现实,宗白华先生讲解“化景物为情思”时引用《小山画谱》 中“实则逼肖,则虚者自出”,点化出了现实之“景”与虚化之“情”的真意——“化景物为情思”并非对现实的过度解读,而是将“实”展现得通透淋漓,由此衍生“虚”的动人情致。艺术是创造,艺术家对现实观照的过程中,会掺杂进各种人生经历、情感体验,由此实现“化实为虚”,让现实成为意志的载体。作品形成后,欣赏者会再次对实物负载的“虚”进行解码,在相似的环境氛围、身世遭遇中发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从而解读出意境中的情感,这便实现了虚实的传达。
中国传统“天人观念”在《美学散步》中得到了艺术化的体现,从艺术表现形式到古人的宇宙观,中国艺术时刻与天地共振。在中国艺术中,自然是艺术描写的对象,是情感的载体。“宇宙大圆镜,沆瀣际空浮”自然很大,囊括万物;“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自然又很小,可涵养于一窗之间。这一大一小的辩证思想中,我们窥见了古人探索自然的故事流动,同时今天的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为“天人观”赋予时代新内涵,避免陷入自足自满、盲目自信的陷阱。
辩证思想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思想内涵及表现技巧。其中的虚实观念几乎作为艺术的脉搏与之相伴而行。宗白华先生谈道“一个艺术品,没有欣赏者的想象力的活跃,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一张画,可使你神游就是‘虚”。“虚实”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对于美的欣赏视角,创造了艺术家与观赏者对话的机会。“它将哲学和艺术巧妙地相结合,在深厚的古典底蕴和广阔的西方视野中更深、更好、更广地阐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从而实现了生命艺术化和艺术生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