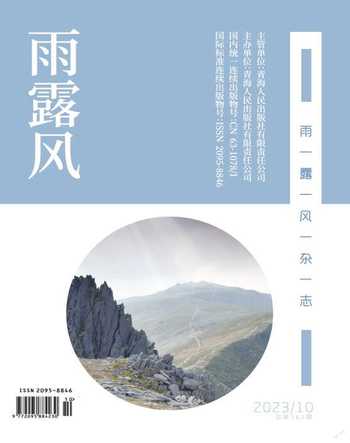人工智能诗创的语言学研究
赵碧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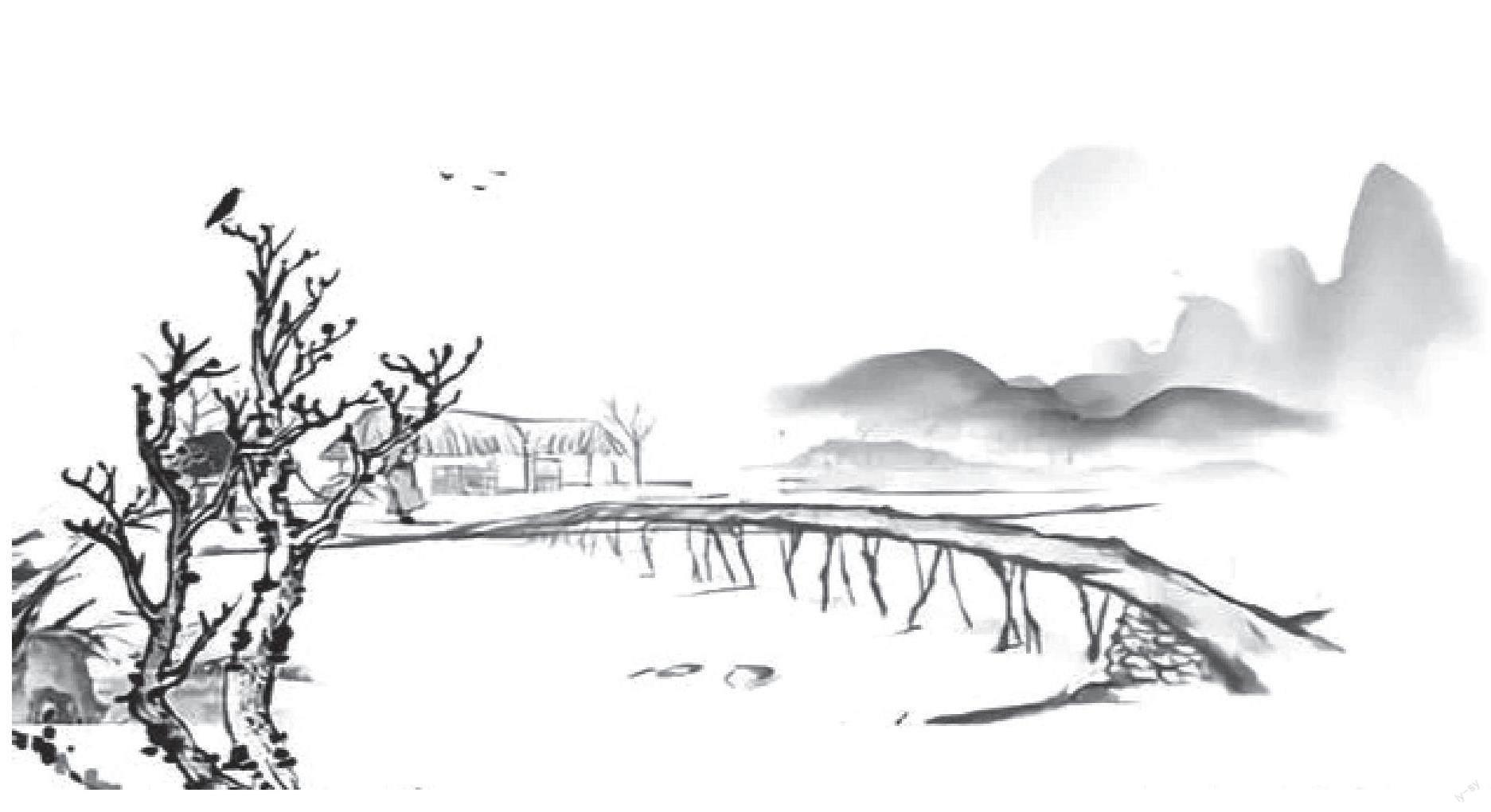
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作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一环,自然难以摆脱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曾引起国内学界广泛争议。米勒认为“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1]科技巨大变革所产生的新型产物给过去传统布景下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以强烈冲击。在新媒体发展带来的传统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导致“文学终结论”问题还无法解决时,人工智能便开始将其触角深入文学创作领域,引起学界对“人工智能创作是否可以取代文学创作”这又一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此亦使“文学四要素”说中的“作者”又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划分。就此问题,本文拟从语言学角度对微软小冰的《阳光失了玻璃窗》进行分析研究,尝试对此问题作出较为合理的解答。
一、诗歌创作的语言特征
从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诗歌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并且围绕诗歌本身产生了系统庞杂的诗学体系。关于诗歌的产生,多是“情感发生说”。中国最早在《毛诗序》论及“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言之为诗”。彼时的文人已意识到诗歌是诗人内心志向的抒发。无独有偶,西方的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也宣称“Poetry is a natural outpouring of strong emotions”。[2]诗歌的产生固然离不开诗人的强烈情感与具有个人风格的独特意象,但语言也是诗歌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是诗意表达的重要途径。其中诗歌语言的方式包括:语音(音、韵、节奏),词汇(生僻词、隐喻、转喻)、语法(倒装、排比),文字(排列),篇章(意境)。
情感是诗歌创作发生的原因,但情感并不能成为判定诗歌的依据。要真正判定所创作品是否为诗还需从语音、词汇与语法方面入手,这也是诗歌不同于日常语言的重要部分。
(一)语音与节奏
章太炎《答曹聚仁论白话诗》谓“以广义言,凡有韵者,皆诗之流”,[3]但丁在《论俗语》中也谈及“诗不是别的,而是写得合乎韵律、讲究修辞的虚构故事”。与此相同或相似的论断还有很多,都强调诗歌的韵律性,只有具备韵律与节奏才能称之为诗。
通过语音表达特殊的情感体验是很自然的。人处于精神亢奋状态时,会情不自禁地诉诸于声音,歌之、舞之。表达兴奋情绪往往通过不同于日常语言表达的语音组合或韵律。像唐代兴起的律诗押韵严格,被诗家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写道,“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中押“ai”韵,并且对仗极为工整,加上“四三式”的朗读节奏,进一步将杜甫晚年登台眺望时涌上心头的悲愁和凄苦展现得臻致巧妙。不单单是古诗,现代白话诗也需富有优美的韵律和朗朗上口的节奏。如食指的《相信未来》首两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尾字同押“ai”韵,节奏一致,富有韵律。可见,音韵和节奏是诗歌必不可少的元素,是诗歌区别于日常言语的要点之一,它使诗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增强了诗歌情感表达的能力。
(二)诗歌与词汇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毫无疑问,诗歌意义的表达依赖于词汇。一个词的选用与否,能够完全改变诗歌的意境。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推敲”便成了诗人创作中必经的过程,为此在唐代便产生了以贾岛为代表的“苦吟”一派,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歌创作经常选用的词汇手段包括词类活用、隐喻、转喻等。像贺知章《咏柳》中“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直称柳条,而以“碧玉”“绿丝绦”来隐喻,不仅将春天柳条喜人的碧绿之色点出,也将柳条婀娜、柔美的特点展现得恰到好处,并且触发读者对春天柳条形象的想象。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则可以解释这一“触发”现象,“每一个词都与相关的词构成一个网络。一个词的理解依赖该词在这一网络中与相关词的关系”。很多时候诗人为营造符合心境或所处环境的意象会对词汇进行推敲,以使之完美契合自己内心所想。
(三)诗歌与语法
句子是由词汇通过规范化的语法规则连接来传达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创作都较注重句子的语法规则,诗歌是诗人完全感情化的产物,诗人有时为了將积郁在心中的强烈感情以较为新颖的形式呈现,往往会突破常规的语法限制,另辟蹊径,去寻求一种最恰当的词语组织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有时破坏语法规则只是出于诗歌音律的考虑,这种情况在古典诗歌中俯拾皆是。
虽说在诗歌创作中并不需严格遵守语法规则,但单纯为跳出常规语言组织规则的桎梏,一味求新求异而无内在强烈情感的抒发,将诗歌创作当作语言的游戏,那这样的创作就不能称之为诗。
总的来说,从诗歌语言的各个层面来说,按照对表达诗意的重要性和创作过程需尤为注意的程度大小来排,大致情况为“句(篇)>词>音>书写>语法”[4],从这也可以看出诗歌创作并不恪守语法规则,有时甚至不惜“扭断语法的脖子”来达到表情达意的效果。
二、人工智能诗创的一般语言学分析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一大批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服务人类的产品,人工智能便是21世纪发展较快且争议较大的一项科技,并且在不断地走向成熟。2016年由谷歌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 Go 以 4∶ 1 的成绩打败韩国棋手李世石,着实令人唏嘘不已,但模式化的围棋游戏并不能引起人文学者太大的担忧,因为人工智能毕竟只是机器,不具备人的情感,所以也并不用担心人工智能涉足富有主观情感的文艺创作。但人工智能并未驻足自居,而是继续开疆扩土,在2017 年 5 月,“微软小冰”以少女般的柔情创作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并出版发行,再一次引起了文学圈和科学界的热议。并且罗先海在《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中提道:“这种人工智能系统能运用目前领先的中文情感解析引擎判断自然语言情感的正负极,并从语句中提炼出多维度的细腻情绪表现。”[5]可见人工智能开始逐步突破机械式的学习模式而开始学习人的情感,通过语句的情感来进行分析评断。下面对《阳光失了玻璃窗》进行具体语言层面的分析,来探究人工智能创作的特点。
(一)跳跃的意象组接
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组织形式,同样注意话语的衔接与连贯,且“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诗人在进行”。[6]诗人将映入眼帘的物体与记忆中的物体进行区别分类,以此在内心形成“聚合关系”,诗人可在日后情感觸发时开启自己内心隐藏的聚合系统,通过多个具有聚合关系的物象组接,读者可以由此联想理解诗意。若诗歌中的意象聚合性不强,各个句子的衔接性与连贯性不够,便很难使读者理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意思。如《阳光失了玻璃窗》中的《我拿了我的眼睛》:
“无灯火/这强烈的新鲜的/而他的眼睛/我是一个寂寞的梦/孤灯我的泥人/可要保存着那新鲜的酒/我命运的能赠给我的好人/我拿了我的眼睛。”
这首诗的意象“灯火”“眼睛”“寂寞的梦”到“泥人”“酒”“好人”的衔接性与连贯性不是很强,与此同时也很难形成一个聚合系统,读者难以通过这些意象间的关联来领会小冰的创作意图。
(二)扭曲的语法规则
上文中提到诗歌是最不拘于语法规则限制的体裁,现代诗人为抵制惯性,更是热衷于对语法的反叛。小冰学习了自1920年以来的519位现代诗人的诗,从根源来看也可理解《阳光失了玻璃窗》这首诗集存在语法扭曲的语言现象。但小冰诗歌中的语法扭曲与学界认可的可以让诗歌有更大的联想空间的语法扭曲似乎不大一样,它并没有产生让读者读后可以有更大、更奇妙的阐释空间的效果,有也是支离破碎地这一块,那一块,难以组接为一个完整的阐释内容。像余光中先生的《白玉苦瓜》一诗“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钟爱”,一般不能随意拆解,但在特殊情感体验下,把“钟爱”拆成两个语素,夹缠在大陆两旁,反而增加情愫的浓度,很不一般。这样的拆解不仅没有使整首诗晦涩难懂,还增强了诗歌的巧妙性和表情达意的作用。而小冰的诗虽然打破了语法规则却少有这般巧妙的效果,且令诗歌较为抽象难懂。小冰诗集中《到处都是天堂》一诗,“我将要象(像)古铜色光亮的个/用着悲剧的人生/好从一起到处都是天堂”。[7]这段将“量词”用作“名词”,充当句中的宾语,最后一句“好从”连用使句意一时难以揣摩。这样扭曲的语法规则没有使诗意得到更好的表达,反而成了阻塞。
(三)中心语的多重修饰
在《阳光失了玻璃窗》中,小冰偏向使用重复或者是两个定语来修饰中心词,如“美丽而且美丽的人”“幸福的人生的逼迫”“我命运的能赠送给我的好人”等等,定语之于中心语的作用便是修饰限定,对中心语的特征起了补充说明的作用,但在小冰的诗歌中,这些双重定语修饰并未给予中心语丰满的羽翼,有时甚至略显啰嗦、累赘或者怪异。这也或许是因为人工智能毕竟还不是人,不具备人主观选择的调节功能,在此也显示出了人工智能目前的局限性。
三、人工智能诗创的优劣
从语言层面对微软小冰创作的《阳光失了玻璃窗》进行评析可知人工智能向文艺领域的初步探索是较为成功的。人工智能诗创的可取之处便在其注重韵律、节奏。韵律、节奏都是格式化的、有一定规律的创作手法,而人工智能最擅长规律严整型的操作。现代诗歌创作并不像古诗要求严格押韵,更为注重的是诗歌朗读时的韵律及韵律与情感方向的一致性。《阳光失了玻璃窗》中的大多诗篇都韵律优美,富有节奏。如诗集中的《它常把我的海水洗甜》:我不起雪的时候/假如你冷冷的身/你像是梦中的一点平土/它常把我的海水洗甜。这首诗每行字数和句式结构都保持基本一致,将细腻的柔情借由富有韵律的诗行表达出来且具诗意。
人工智能诗创的不足便正是对“人工智能创作是否能取代文艺创作”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人工智能虽然比人脑运行更加快速且错误率也低得多,但是在主观倾向极为强烈的人文领域,人工智能还并不能完全适应甚至取代人类文艺创作。人工智能的不足首先便是不具备情感。如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8]计算机的程序可以完美精确地设定出各种优美而恰当的语言,但是这种精准的计算,却将语言的深度平面化,消解了语言所带的情感性。其次,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重意象、词汇的拼凑,不注重诗歌整体的诗意表达。语言作为人们沟通的工具,具备了社会属性,词汇的组接也需在社会公共认知领域的范围内进行,因作品创作的完成需要经历从作者创作到读者阅读的循环,而毫无聚合关系的词汇连接无法表达一个相对集中的情感主旨,因此读者无法从中获取有效信息,这便不能称为合格的作品。最后,人工智能诗歌突破常规的语法规则虽然使诗歌语言“陌生化”了,延长了读者的审美体验时间,但是却使读者一直处于思考感悟过程中而无法到达诗歌真正的审美境地。
四、结语
小冰的《阳光失了玻璃窗》一经出版发行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思考,也让文艺创作者产生了一定担忧。但通过对小冰创作的诗歌进行语言层面的品析便知,人工智能创作并不能取代文艺创作,且文艺创作会一直引领人工智能创作,人工智能只会随着文艺创作者创作手法的更新而更新。并且文学作为人学,一直以来都是以人为中心,只有人本身最关心也最了解人的所思所想,人工智能作为没有情感感知的机器无法或者难以生产出最切合人心境与体现人身际遇的作品。因此,对上述问题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文艺创作可在大踏步推进的同时引领人工智能向更成熟与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注释:
〔1〕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WilliamWordsworth,Lyrical Ballads, with Pastoral and Other Poems(1802),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M.H.Abrams,W.W.Norton&Company,Inc,1975.
〔3〕章炳麟.国学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0.
〔4〕束定芳.诗歌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角——以汶川地震诗歌现象为例[J].外国语文,2009(2).
〔5〕罗先海.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J].长江文艺评论,2017(5):14-19.
〔6〕李心释.索绪尔语言学视野中的诗歌语言分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62-66,92.
〔7〕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8〕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