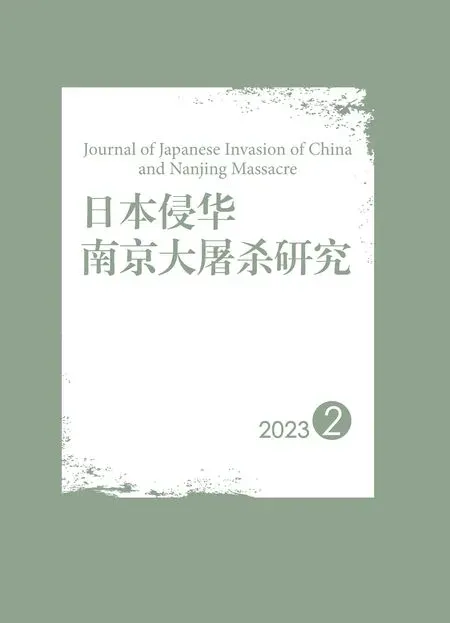华中日军宪兵与南京大屠杀
王 萌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在华中沦陷区犯下的重大战争罪行。正如人们所理解的,宪兵的职责主要在于监察和维持军纪,近代日本宪兵也不例外。南京大屠杀期间华中日军军风军纪的极度紊乱,导致南京城内外无数惨案的发生,反映出日军随军宪兵的严重失职。战后,由原日军宪兵组成的“宪友会”对此亦不得不承认,“南京事件对日军而言,是作为一大污点而留在历史上的,对于指挥官及宪兵而言,均为一大教训”。(1)全国憲友会連合会編纂委員会『日本憲兵正史』、全国憲友会連合会本部、1976年、510頁。学界既往关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宪兵的研究,主要在于揭露其对沦陷区民众犯下的罪行,然而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随军宪兵的动向及其失职问题却鲜有关注。(2)中国学界对于近代以来日本在华宪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伪满关东宪兵队的组织、职能和暴行问题上,代表性成果如傅大中《关东宪兵队》(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与霍燎原、潘启贵主编《日伪宪兵与警察》(黑龙江出版社1996年版)等。程兆奇注意到淞沪会战期间日军第十军配属宪兵的失效与士兵军纪紊乱之间的联系,参见程兆奇《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日本学界以大谷敬二郎、纐纈厚、荻野富士夫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系统梳理了日本宪兵势力在本国及台湾、朝鲜等殖民地不断扩展的历史脉络,具体参见大谷敬二郎『憲兵』(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纐纈厚『憲兵政治:監視と恫喝の時代』(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与荻野富士夫『日本憲兵史 思想憲兵と野戦憲兵』(小樽商科大学出版会、2018年)等。其中,荻野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宪兵在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组织网络,然而未涉及日军宪兵参与南京大屠杀等重大事件的情况。日军随军宪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面对日军官兵的暴行为何不能履行其职责?此后华中日军宪兵的“权威”又是如何树立的?本文希望结合如上问题,考察南京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的动向,以及大屠杀前后华中日军宪兵在组织与职能上的变化,揭示其与华中日军军风军纪之间的联系。
一、日军宪兵在淞沪及其周边战场上的失职
宪兵是近代日本政府模仿西方兵制的产物。1881年1月,日本政府在陆军部内设立宪兵,不久颁布《宪兵条例》,其第一条规定:“宪兵位于陆军兵科之一部,执掌巡按检察之事。视察军人之非行,兼有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之事。兼隶内务、海军、司法三省,负责国内安宁。”(3)田崎治久『日本之憲兵』、軍事警察雑誌社、1913年、517頁。由此可见,日军宪兵自设立之初即拥有对官兵的检察权,兼掌行政、司法警察的职权。此后,宪兵的权限不断扩大,从监察军风军纪,延伸至对民众运动的镇压、对社会思潮的监控等,其职能“不如说,比之普通警察,乃掌握更广泛警察业务的警察机关”。(4)憲兵司令部『日本憲兵昭和史』、巌南堂書店、1939年、6頁。
驻华宪兵伴随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与驻屯而出现。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成立关东宪兵队,是为日本对华派驻宪兵之始。日本学者将战前日本宪兵分为两类,即1920年代以来在日本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的“思想宪兵”,与1930—1940年代在傀儡国家、日军占领地实施殖民统治的“野战宪兵”。(5)荻野富士夫『日本憲兵史 思想憲兵と野戦憲兵』、緒言9頁。事实上,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宪兵队逐步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职能上兼具“思想宪兵”与“野战宪兵”双重角色。关东宪兵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镇压伪满境内抗日力量的“利器”,其所推行的“思想对策”工作,乃“对于妨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统治中国东北的一切思想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采取的行动予以镇压、逮捕、杀害或投入监狱”(6)《关于思想对策的罪行》,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伪满警察统治》,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7页。,可谓臭名昭著。
除东北沦陷区之外,日本还在沿海沿江口岸日租界或势力范围内派驻宪兵。全面抗战爆发后,驻华各地的日军宪兵分队迅速投入情报搜集等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侵华而服务。在淞沪会战前夜,日军驻上海宪兵分队即派出宪兵下士官大前旭及翻译,前往上海北站附近侦察国民党军的运输情况与保安队的备战状况。从日方档案可见,日军驻上海宪兵分队很早就在当地广罗间谍,建立情报网络。如大前旭于1936年秋抵达上海后,在南市中国人旅社中独居的数月间“完成密探网络之基础,屡屡提供有力之情报等,一贯至诚热心精励于勤务”。(7)「在上海憲兵下士官及通訳生死不明ニ関スル件報告」(1937年8月23日)、『支受大日記(普)其1 2/2 第1号の2 12冊の内 昭和13年自1月11日至2月4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3-2-144。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驻上海宪兵分队的情报搜集活动极为猖獗,源源不断为日本军部与在华中作战的日军提供情报,但另一方面,仅30人的日军驻上海宪兵分队,基本未被投入治安维持方面的工作。(8)长期以来,日军驻上海宪兵仅5人。1936年9月日本宪兵司令官中岛朝今吾向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建议,增派驻上海宪兵至30人。这些宪兵“在并无遗憾地完成本来任务的同时,要充分协助陆战队的警备工作,且要抓紧搜集情报及从事对领事馆警察、工部局公安局警察、在乡军人等的指导工作”,参见「上海憲兵増強に関する件」(1936年9月25日)、『昭和11年 「陸満密綴9.16—11.13」』、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11-10-42。据日军第十军军医早尾虎雄观察,11月下旬日军占领地区内完全不见宪兵的踪影,“每日每夜中国人的空屋处于被焚烧的状态,甚至连扑火者都没有。日人街区很多店铺都未开张,也没有所谓的慰安所,私设的卖淫屋不过在暗夜中私下交易”。(9)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不二出版、2009年、227頁。当时日军占领区内的治安,主要由日本海军陆战队维持。因日本军部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进攻南京的指令,故对士兵酗酒斗殴等违反军纪的行为,海军陆战队大多采取视而不见乃至纵容的态度。淞沪会战后华中日军官兵肆意违反军纪的心态,正如时为第三师团士兵曾根一夫所解读的:“上海激战结束后,大家本以为可以好好歇一下的,没想到又接着准备一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战役,这对士兵打击很大……大家想这次恐怕是活不了了。因此情绪变得自暴自弃。”在曾根看来,日军官兵的放纵心理导致军风军纪的紊乱,“我认为‘南京屠杀’就是这时才开始萌芽的”。(10)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68页。
另一方面,在淞沪周边战场,激烈战斗与强行军导致日军后勤补给迟滞。因给养困难,日军士兵四处抢掠,出现大量与之伴生的恶行。为了避免日后受到检举,日本士兵在作恶后往往杀人灭口,制造更大的惨案。第十军宪兵队长上砂胜七意识到随军宪兵人数过少的问题,“无奈相对于几个师团20万的大军,只配备不足百人的宪兵,这无论如何是管制不了的”。尽管一些军官呼吁增加宪兵或辅助宪兵以维持军风军纪,但在上砂看来,宪兵人数不足的问题在战事激烈的状态下难以解决,“在大敌当前的进攻推进中,各部队都希望使用尽可能多的兵力,根本不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只能制止实在看不下去的现行犯”。(11)上砂勝七『憲兵三十一年』、東京ライフ社、1955年、176頁。在急行军期间,随军宪兵在官兵眼中如同摆设。面对官兵的暴行,宪兵仅在被占领城市和村庄的主要场所张贴“预防火灾、杜绝盗窃、爱护居民”等告示,“委婉”地加以提醒。即便如此,宪兵的劝阻仍会受到一些部队军官的质疑与斥责,“这次随军的宪兵到底是日本军队的宪兵,还是中国军队的宪兵?管的实在太宽了!”(12)上砂勝七『憲兵三十一年』、177頁。
淞沪会战爆发以后,华中日军宪兵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十军随军宪兵,以及原驻上海宪兵组成,有130余人。宪兵作为主掌监察军风军纪的军事警察,其职责正如《宪兵服务规程》所规定的:“宪兵对于军人军属违反(军法军纪)的行为或认为有违反之虞时,对于同级以下者直接纠正之;对于上级者,要使其注意。”(13)憲兵司令部『日本憲兵昭和史』、1035頁。不难看出,华中日军宪兵在淞沪及周边战场未能履行这一职责,从开始便出现失职的问题。这一反常现象,固然与日军占领区宪兵数量较少且主要从事情报工作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为了达到尽快攻占南京、扩大战果的目的,唯我独尊,骄横无忌,对于下属官兵从事掠夺等违反军法军纪的行为采取漠视、袒护的态度,导致宪兵地位不彰、威信受损。
二、南京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的失职问题
当日军士兵在淞沪及周边地区肆意掠夺,最终上升至拒绝上级命令、无视日本国际形象的地步时,日本军部并不会袖手旁观。1937年11月,第十军随军宪兵向该军法务部报告了大量士兵从事掠夺暴行等军纪废弛的现象,法务部由此向该军司令官提出整肃军纪,避免引起国际问题的建议。(14)「第十軍(柳川兵団)法務部陣中日誌」、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みすず書房、2004年、29頁。不久,日本军部派出若干参谋,以指导作战的名义前往前线,参谋们开始指挥随军宪兵,追查所谓的“现行犯”。
在攻占南京前夕,日军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下达指令,“若是中国军队并不接受投降劝告,12月10日下午即开始进攻。进入城内部队的行动如上记同样处理,特别要严肃军风纪,尽快恢复城内治安”。参谋本部在传达的注意事项中强调,“对于掠夺行为或虽因不注意而失火的行为,要加以严厉处罚。使多数的宪兵及辅助宪兵与军队同时入城,防止不法行为”。(15)全国憲友会連合会編纂委員会『日本憲兵正史』、505頁。然而,日本军部的指令并未起到任何作用,华中日军上层没有派遣多数宪兵同时入城。沦陷后的南京,战争暴行无处不在,日军官兵视军风军纪为无物,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对此感叹,“今日我军价值竟如此低落”。(16)「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229頁。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日军宪兵的情报工作并未间断,如第十军随军宪兵始终密切关注底层官兵的思想动向,在给该军法务部的报告中记录了一些底层士兵对长官辱骂、掌掴等“下克上”的现象。(17)「第十軍(柳川兵団)法務部陣中日誌」、参见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60頁。正是通过随军宪兵的报告,华中日军上层确切了解到大屠杀期间底层官兵违反军纪的情况与严重程度,如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在日记中坦言:“根据宪兵报告,军纪上的违反者相当多。而召集少尉、准尉级寡廉鲜耻的行为,实在令人遗憾至极”。(18)「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75頁。但另一方面,面对日军官兵大肆违反军纪的行为,随军宪兵未能对之加以纠察与阻止,对于南京城内外无数惨案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后,“宪友会”以及不少原日军宪兵,均述及南京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的失职问题。他们大多强调宪兵人数过少之说,如“宪友会”表示,“沦陷当初南京并无一名宪兵,12月17日与松井司令官同行入城的宪兵,宪兵长以下仅17名……在南京发生不幸事件,遗憾的是,12月13日至17日期间宪兵并不在南京”。(19)全国憲友会連合会編纂委員会『日本憲兵正史』、510頁。原华中派遣宪兵队队员志村毅在谈及随军宪兵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问题时,认为“无论如何,若为事实,作为没能制止日军残暴行径的宪兵之一员,应该深刻反省……宪兵在日本军队里一方面有担负维持治安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有管制那些对中国平民施以非法残暴行为的义务。这一说法或有狡辩嫌疑,但是,当时在约两三万人的师团中仅有约50名宪兵,可以说,要防范过激军事行动以及暴力行为于未然,几乎是并不可能的”。(20)志村毅「戦争を知らない世代に語り継ぐ」、創価学会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会『揚子江が哭いている——熊本第六師団大陸出兵の記録』、第三文明社、1979年、187頁。作为这一说的延伸,也有将宪兵失职问题归因为战事紧张者,“在中国大陆,正规宪兵主要在占领后的地域内才能够实现任务……然而虐杀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占领前的进攻中。第六师团绝大多数前线士兵的从军记说明,他们大都置身于日夜行军战斗的‘进攻’阶段。故而宪兵之手几乎无法涉及,呈现出相当矛盾的状态”。(21)「座談会 熊本編を終えて」、創価学会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会『揚子江が哭いている——熊本第六師団大陸出兵の記録』、197頁。不难看出,这些说法基本处于为随军宪兵辩护的立场,强调其失职的客观原因,并未触及失职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无论是留守南京的外侨,还是当时日军其他官兵,对于随军宪兵的失职问题都有较为深刻的揭露。
在大屠杀初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即向日军提出,希望在安全区入口设置岗哨阻止士兵进入,同时建议日军立即派出宪兵维持治安。外侨拉贝等人期望日军宪兵能够切实履行其军事警察的职责,即“昼夜在安全区巡逻,对于偷窃、抢劫、强奸或抢夺妇女的士兵,宪兵有权逮捕”。(22)[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面对外侨的反复申诉,日本驻南京外交官员“仅限于作些有关宪兵的微不足道的许诺”。(23)《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通信副本及其按语》,陆束屏编译:《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英国外交文件与英美海军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12月19日,日军派出4名宪兵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24)[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这使外侨一度认为,“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25)[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第166页。
然而,外侨很快对日军宪兵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知道有宪兵在,但是他们人数太少,也太文雅,不能维持军纪”。(26)《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1938年2月28日),陆束屏编译:《忍辱负重的使命——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页。他们发现,尽管有若干宪兵在难民聚集的建筑门口站岗放哨,然而日本士兵到处爬墙越舍,毫无顾忌;尽管金陵大学图书馆等文教场所与难民营的门上贴有宪兵所书禁止入内的布告,然而日本士兵将之撕毁后,公然闯入掠夺财物或强奸妇女。当看到有士兵就在日本使馆大门附近实施强奸时,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贝德士讽刺道:“这难道就是贵国的几个宪兵重新恢复秩序的迹象吗?”(27)[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第199页。当传教士魏特琳看到上海路上小贩兜售赃物时,她在日记中写道:“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28)[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78页。因与日军宪兵经常打交道,拉贝在写给日本使馆的信中较为委婉地提到其失职问题,“如果执行上街巡逻命令的宪兵能增加双岗,以便在个别的房子中搜寻并且逮捕士兵,那么总的局势就会迅速改观”。(29)[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第208页。魏特琳对于涉及日军宪兵的申诉亦持谨慎态度,认为“要讲策略,否则,可能引起这些士兵的仇恨。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比我们目前遇到的麻烦更糟”。(30)[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54页。
日军官兵的记述则较外侨更为直接。步兵少尉前田吉彦目睹士兵在南京城内肆意掠夺,他在日记中批评道:“宪兵正在干什么啊!要立即对他们加以管制,确立军纪!”(31)「前田吉彦少尉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67頁。日军航空兵军曹井手纯二在回忆录中写下身处下关码头等大屠杀现场时的观感:“日本军的军纪为什么会如此堕落呢?……且说在现场,哨兵和宪兵都不在,行动很自由,甚至拍照都是可能的。”(32)井手纯二:《我所目睹的南京惨剧》,王卫星编,叶琳、李斌等译:《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页。一些日军官兵的日记中记载了宪兵失职的现象,如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看到一个宪兵欲制止军官酒后喧闹却反被其扑倒的窘状,暗讽宪兵的软弱。(33)「山崎正男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09頁。1938年1月26日,美国驻南京领事馆官员爱利生在前往日军军营调查一起强奸案时遭到日军官兵殴打,是为“爱利生事件”。指挥殴打爱利生的军官天野,还犯下强奸、伤害、掠夺等多种罪行,宪兵对其亦无可奈何,“可以理解,法学士、律师钻了法网的空子。对于宪兵的调查答辩颇为巧妙。未必可见会受严重处分”。(34)「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94—295頁。
南京沦陷之初,华中日军中上层沉浸于“膺惩中国”、炫耀战功的狂热气氛之中,并未对淞沪会战以来军风军纪紊乱的问题加以重视,由此导致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在日军中的“权威”进一步失坠。无论是留守外侨,还是现地日军官兵,均认为宪兵对于底层官兵缺乏基本的约束力,面对暴行几乎无所作为,其无能与怯弱助长日军官兵的作恶气焰,致使军风军纪更为败坏。
三、南京沦陷后日军宪兵参与暴行
尽管普通官兵对于随军宪兵的观感不佳,一些原华中日军上层军官却对其高度赞誉,如原华中方面军发言人宇都宫直贤在战后称:“宪兵在南京城内的举止的确优秀,他们军纪严明,就连外国记者也很佩服。”(35)宇都宫直贤:《黄河、扬子江、珠江——回忆在中国的工作》,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第13页。为了维护日军形象,随军宪兵在与外侨的接触中往往表现出较为温和、友善的一面,有时也会劝止士兵对外侨的骚扰,从而获得一些外侨的好感。但是,大量史实表明,随军宪兵对待中国民众表现出蛮横、凶残的另一面,其参与对中国民众的诸种暴行,同样为军风军纪的破坏者。
日军宪兵以“检举”抗日力量为名义,肆意屠戮南京军民。战后,“宪友会”关于大屠杀期间日军宪兵是否参与“检举”工作表述模糊,称“日军在检索便衣士兵之际,若由宪兵为之则较为熟练,然而一般部队官兵并无此经验。故而对于一般民众与便衣士兵的辨别就很困难,超过必要程度的严酷检出与处置,由此留下了很大祸根”。(36)全国憲友会連合会編纂委員会『日本憲兵正史』、510頁。显然,“宪友会”的说法,意图通过否定随军宪兵参与“检举”工作而为其开脱罪责。大量资料表明,随军宪兵不仅参与“检举”或搜捕工作,而且大开杀戒,其凶残与普通官兵无异。如12月15日步兵第七联队队部命令全队官兵次日向难民区出发,彻底搜捕歼灭国民党残余士兵,要求随军宪兵队协助联队。(37)歩兵第七連隊「戦闘詳報」(1937年12月7日—12月24日)、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622頁。值得注意的是,步兵第七联队的战斗详报说明当时南京城内并非没有随军宪兵。显然,宪友会的说法有误。又如一些外侨所见闻的,在1938年元旦当日,“‘举止似乎文明一些’的宪兵今天抓捕了一些普通士兵,理由是有严重的不轨行为。据说这些士兵被枪毙了”。(38)[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66页。事实上,华中日军上层并不否认宪兵参与搜捕工作,如饭沼守在日记中记载,南京沦陷后宪兵即开始在城内大肆搜捕“抗日力量”,“宪兵不断逮捕潜伏于南京难民区域或外国大使馆等地的不逞之徒,主要包括保安队长、八十八师副师长等”。(39)「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33頁。松井石根的副官冈田尚在证言中亦提到,“也有进入难民区对中国士兵的搜捕。搜捕由宪兵来执行,据说中国兵从帽子痕迹上就能被发现”。(40)「松井軍司令官付·岡田尚氏の証言」、阿羅健一『聞き書 南京事件』、図書出版社、1987年、28頁。另外,日军宪兵不仅参与“检举”或搜捕工作,而且直接策划惨案。据曾根一夫记载,因怀疑南京郊外某个村庄具有“很强的抗日情绪”,在随军宪兵的策划下,日军部队趁村民午饭之际偷袭并屠戮了整个村庄。(41)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第306页。
日军宪兵参与对“慰安妇”的暴行。宪兵强征中国妇女为“慰安妇”的行为,在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述:“寺田中佐指导宪兵,在湖州设置娱乐机关。宪兵透露,要征集百人左右。”(42)「山崎正男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11頁。山崎所述的强征之地虽非南京,然可证实宪兵强征中国妇女的暴行确实存在;宪兵维持慰安所“秩序”的场面,在第十六师团卫生兵上羽武一郎的日记中有详实记述,“妓女也出来迎接了,但是70名妓女接待500名士兵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只好算了。士兵们排成两队哇哇乱叫,宪兵吃力地维持着秩序,面对这些女人谁不想大干一场呢!”(43)上羽武一郎:《上羽武一郎阵中日记》,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86页。诸如此类宪兵维持慰安所“秩序”的场景,在东史郎日记中也有记载。(44)東史郎『我が南京プラトーン——一召集兵の体験した南京大虐殺』、青木書店、1987年、120頁。
大屠杀期间日军宪兵从事强奸、掠夺的暴行,在外侨的记述中屡见不鲜。英国外交部驻华官员豪尔在报告中谈及1938年初南京城内日军宪兵参与抢掠的情况,“‘恢复军纪’的确是极度漫不经心,甚至宪兵也强奸、抢劫,无视他们的职责……有好几天,我们一个宪兵也没有看到。最近,将特殊的袖章发给日本兵,称他们为宪兵,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不端行为拥有特殊的保护,并且不必履行某些日常的职责”。(45)《豪尔致外交部128号电报》(1938年1月10日),陆束屏编译:《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英国外交文件与英美海军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第65、68页。魏特琳观察到,“今天(1938年1月13日),我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46)[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78页。中方人员也记载了日军宪兵参与暴行的事实,如避难于难民区原美国大使馆内的国民党军军医蒋公榖揭露,“使馆自前几天屡被敌人抢劫,经国际委员会及美侨向敌方提出抗议后,敌方派中岛部队宪兵四人来守卫,各房间都来看了一次,遇到有妇女的,就嬉皮笑脸地进去坐坐,还要讨香烟吸。进出都被限制,反而不方便起来。一到晚上,他们还不是同样的跑出去做那抢劫奸掳的勾当。吓,倒算是宪兵呢!”(47)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日军官兵在日记中同样记载宪兵恣意戕害中国民众的暴行。上村利道在日记中提到一起令人不明所以的“宫崎宪兵事件”,“宫崎宪兵大尉存在越权行为……宫崎宪兵的行动越听越感到其非常识且违规行为很多。实在令人难办”。(48)「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90頁。若参看第十六师团参谋木佐木久的日记,大概可知这一事件的端倪,即宪兵宫崎为掩盖自己的失职,恶意迫害两名无辜的中国女子,木佐对此评价道:“我对于所谓的宪兵者,未尝带有恶感,然而就本次事件,感到极度憎恶。使我军的名誉、南京的军纪失坠的究竟是谁?甚而要剥夺这两个可怜女子的生命。不得不感到强烈义愤。”(49)「木佐木久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31頁。
大屠杀期间日军宪兵对中国民众滥施暴行的现象,成为此后日本统治南京的常态。这一期间随军宪兵所表现出的残暴性,也为日后的南京宪兵队所承继。曾根一夫切身观察到南京宪兵队对当地民众施暴的肆意性:
这儿所谓的“大扫除”,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室内室外的清扫。宪兵队的“大扫除”指的是把作为嫌疑犯抓进来的关押人员全部处死。
“这么随随便便就把人杀了,如果有冤枉的人怎么办?”我这样问道。对我的提问,成濑(宪兵名——引者注)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傲慢地说道:“凡是被宪兵队盯上抓捕来的人,不分有罪无罪,全部作有罪处理。就算你没有罪,拷问之后就作有罪处理。顽固的家伙就严刑拷打。拷打致死的,就编造一份有利的调查记录作为有罪处理,这样案子就结了。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处死他们,所以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有罪。”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之所以本国人和外国人都惧怕“东洋魔王”,就是因为日本宪兵队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以前我就听说,只要被抓进宪兵队,就不可能活着回来。现在看来的确如此。(50)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第326页。
从曾根的这段记述可见,南京宪兵队专以拷掠为能事,毫无法纪观念可言,其残暴性、肆意性与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对暴行的参与可谓一脉相承。然而,与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分散化、小规模的作恶活动不同,南京宪兵队对中国民众的暴行更具组织化、常态化,刻意营造出宪兵政治的恐怖气氛及其对沦陷区民众的威慑力,由此成为沦陷时期南京民众与外侨闻之色变的“魔窟”。事实上,南京宪兵队的所作所为,可谓战时日军野战宪兵对中国沦陷区实施恐怖统治的缩影。
四、华中派遣宪兵队的编成与宪兵“权威”的树立
南京沦陷后华中日军制造各种惨案,严重破坏日本军政当局历来所宣传的军纪严明形象。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对此不无感叹:“不料我军南京入城之际,发生诸多暴行夺掠之事,乃至于我军有不少损伤威德之处。”(51)松井大将「支那事変日誌抜粋」、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8頁。在大屠杀经历一个阶段后,参谋长塚田攻在向各部队的通牒中强调:“希望此际对军风军纪的维持振作投入最大努力……其中军纪军风方面,令人顾忌的事态近来渐渐频繁发生。”(52)「軍紀風紀ニ関スル件」(1938年1月9日)、『支受大日記(密)其2 昭和13年自1月14日至1月26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110。鉴于“(南京)令人顾忌的事态业已发生”,在攻占杭州前夕,华中日军上层要求随军宪兵入城后要切实履行职能,尤其当日军官兵因战斗需要而侵损到在杭外国人权益时,“要尽可能讲求当地解决之手段,同时不失时机地向集团司令部及最近宪兵报告与通报”。华中日军上层认识到增加宪兵数量的必要性,要求参与攻城的第十八、第一○一两个师团各派出一个中队作为补充宪兵,至日本驻杭州领事馆附近加强巡视。(53)「杭州占領に伴う秩序維持及配宿等に関する件」(1937年12月20日)、『陸支密大日記 第49号 2/2 昭和15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26-221。
1937年11月,华中方面军成立。考虑到日军将长期驻屯华中沦陷区,日本军部在攻陷南京之前即仿效伪满关东宪兵队,筹备成立专门的华中日军宪兵部队。军部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华中派遣宪兵队”,规定其在组织上隶属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设总部于上海,在职能上主掌华中方面军行动区域内的治安工作及军事警察业务。(54)「中支那派遣憲兵隊臨時動員要領、細則の件」(1937年12月9日)、『陸支機密大日記 第7冊 2/2 共7冊 第12号の2 昭和13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機密大日記-S13-19-109。在编成规模上,军部将原配属于华中日军的102名随军宪兵扩充至400名后就地编入华中派遣宪兵队,并将该部队司令官的阶级定为与联队队长同等的大佐级。按日本军部的规划,华中派遣宪兵队下设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宪兵队,其中南京宪兵队设队本部与三支分队,含官兵共计119人。(55)「中支那派遣憲兵隊ノ編成配置及服務ニ関スル件報告」(1938年1月12日)、『支受大日記(密)其4 昭和13年自2月1日至2月2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111。1937年12月18日松井石根下达指令,上海派遣军于南京宪兵队管区内设军律会议,处理由该管区内违反军律者引起的案件。然而,直至1938年1月10日,华中派遣宪兵队方告编成。
伴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事的失败,日本陷入战争泥沼。如何动用一切军政力量,形成对中国沦陷区的长效殖民统治,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开始思考的课题。伴随华中派遣宪兵队的正式编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随即出台《华中派遣宪兵队服务规定》,进一步明确该部队的职能细节与业务范围,如第四条规定“宪兵要注意区域内诸情况,将必要事项不失时机地报告、通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及各军司令官”、第六条规定“宪兵协助治安及宣抚工作,使其目的易于达成”、第八条规定“宪兵要经常视察军人军属之行为,警戒预防其非法行为”等。(56)「中支那派遣憲兵隊服務規定」(1938年1月10日)、『支受大日記(密)其4 昭和13年自2月1日至2月2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111。
松井石根还向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作出训示,强调这支部队对于华中日军维持占领区内社会治安以及下一步作战的重要意义,“事变爆发以来已历数月,我军给予敌军致命打击,现已攻陷首都南京,如今我军欲使行动区域安定,进而充实战力,准备下一期作战。此际迎来精强之华中派遣宪兵队,可为我军于实力上增添一大战力”。或许松井已注意到南京沦陷后宪兵的失职问题,他特别强调“宪兵的行动必须作为一般军队及所在民众的模范”,在业务方面要充分“自省自戒”,尤其要注意避免引起国际纠纷:
目前之状况,要牢记保安及军事警察之业务特别重要,对于所在民众致力于警防绥服之同时,要无遗憾地使军队之统率及行动变得更为容易。为能以寡少兵力而尽其任,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业务重点……对于如陷入职权滥用、受到军民弹责等,不可马虎对待。要严格自戒自律,且在我军行动地域内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列国的权益错综,鉴于此,要经常以公正妥当态度处理之,不可酿造事端。(57)「中支那派遣憲兵隊長に与ふる訓示の件」(1938年1月13日)、『支受大日記(密)其2 昭和13年自1月14日至1月26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110。
从如上《服务规定》与松井训示中可见,华中派遣宪兵队自成立之初,即被授予极大的权限,其职能并不仅限于约束军风军纪,而且涉及日本对沦陷区民政工作、特务工作等多方面;其业务范围可视其活动区域的实际情况而变动,具有很大灵活性。以隶属南京宪兵队的常州宪兵分遣队为例,在1938年1月下旬驻屯常州日军的卫戍会报中,详细记载该分遣队要求当地官兵必须注意的事项,除“防止未发之犯罪”“严格管制非法行为,尤其是掠夺”“绝对不许进入禁止入内的房屋”“不得对妇女施暴”“严格要求外出者的服装及敬礼姿态”“各部队一般外出时要向宪兵分遣队通报”等整肃军风军纪方面的事项之外,还包括“协商小卖部商品价格”“特别注意通信上的防谍”“对于身体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娼妓,不使之从事交易行为”等方面的内容。(58)「陣中日誌 自昭和13年1月1日至昭和13年1月31日 独立攻城重砲兵第2大隊本部(4)」、『独立攻城重砲兵第2大隊 陣中日誌 昭和12年12月1日—13年1月31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上海·南京-230。
日本军部与华中日军上层在华中派遣宪兵队编成后,有意识地树立其“权威”。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特别指派一批宪兵进驻南京、镇江、上海等地船舶运输机关,严格检查归国日军官兵携带的物品,尤其禁止他们将从南京等地掠取的中国货币、有价证券、金银器件、药品、鸦片等携带回国。作为加强宪兵“权威”的重要措施,“各部队长要讲求万全之处置方式,不得使部下回避以上检查,私下将物品出售、隐匿、破坏等,若发现有如此情况则处以严惩”。(59)「鹵獲及押収品引継並内地携行貨物に関する件」(1938年2月8日)、『支受大日記(密)其8 昭和13年自2月24日至2月27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5-114。宪兵严查归国官兵携带的物品,使不少官兵在南京等地所犯的掠夺罪行暴露,由此引起他们的恐慌。当时日军官兵对宪兵的恐惧心理,如早尾虎雄所分析的:
按当时战士思考角度,认为如对敌地物品加以占据,即可随意自由处置,此亦无可奈何之情况。金银财宝、被服、绒毛类、中国衣服等,大量被作为私物寄回国内。故有回国之际私物检查之流程。在中国所得之物、所购之物一概禁止带回国内。此完全系宪兵之工作。因存此实情,士兵心中对于宪兵之恐惧超过想象。故其在病态中对于军法会议、宪兵、处刑、死刑、自首等词多有交织。此种情况在国内未尝可见。(60)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231頁。
此外,通过使宪兵严厉查处官兵酗酒、殴斗、失仪等违反军纪的行为,进一步强化其“权威”。在上海方面,据早尾虎雄观察,1938年1月初,日军占领区内酒馆彻夜狂欢,醉步蹒跚的士兵哼着小曲嬉笑逐闹,毫无军纪意识。尽管街头有不少宪兵巡视,“然而眼中相当宽大不加咎责,只要深夜不喧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妨碍他们去享乐”。华中派遣宪兵队成立后不久,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即向上海派遣军下达《上海市内(不含南市)军人军属管理规定》,要求当地巡察及宪兵要严格监视态度不良的军人军属,对于过分者现场加以纠正,且要警视敬礼规范,将不良者通报所属部队。(61)「中支那方面軍軍法会議陣中日誌」、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133頁。2月,上海宪兵队加大整治官兵酗酒斗殴等行为的力度,对于寻衅滋事者,“结果必然毫不客气对之检举”。(62)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230頁。在南京方面,“爱利生事件”发生后,日本外务部门遭到美方严重抗议,南京宪兵队队长小山弥即向华中日军上层提出增加辅助宪兵与增设城内宪兵派出所等建议。(63)「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43—244頁。不久,南京日军特务机关宣布设置打给宪兵队的报警电话,并在主要马路出入口安排宪兵监视士兵举止等,以此加强对驻南京日军部队军风军纪的约束。(64)「被占領側から見た日本軍の南京占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776頁。据拉贝观察,1938年1月末以后,南京主要街口已有宪兵把守,禁止日军士兵随意在街上游荡。在某些案件中,一些日军士兵被宪兵当场逮住并拘捕,“宪兵的数量正日益增加,治安状况也将随之好转”。(65)[德]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第448—449页。
华中派遣宪兵队对军纪的整肃工作自2月“开始活跃起来”,至4月徐州会战前后宪兵在华中日军中的“权威”得以完全树立,“全军全面紧张,面目一新。所谓宪兵之观念开始浸入士兵们的头脑中,大概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66)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227、229—230頁。然而,伴随华中日军宪兵“权威”的树立与强化,底层官兵对宪兵的恐惧心理也在不断渲染,曾根一夫注意到“当时日军士兵普遍恐惧宪兵队的介入”“宪兵队成为士兵们最厌恶的地方,士兵们都畏惧、憎恨宪兵。即使没做亏心事。见了宪兵都会避开”。(67)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第301、326页。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华中日军宪兵“权威”的树立,特务工作逐步成为战地宪兵的核心职能,监察军风军纪的本职反而日渐淡化。井上源吉作为原华中派遣宪兵队队员,曾经对战时华中宪兵职能上的这一转变有所说明:“说到其任务,在战地宪兵本来任务管制军纪之外,情报搜集、思想战对策、中国民众对策、宣抚宣传、对第三国人的保护、对交战国人的监视等,几乎掌管所有部门。因此,除重大的掠夺暴行、强奸事件之外,必然处于马马虎虎应付原本任务的状态”。井上还提到,作为华中日军基层形态的野战宪兵,在从事特务工作中获得不受监督、独断专擅的执行权与处置权,“特别是对于被派遣到远隔之地的派遣队长、分遣队长,因被授予法的范围内的某种独断执行权,故而根据不同情况,甚而连作为特务机关的任务,或属于军政方面的施策,也通过宪兵之手来进行”。(68)井上源吉『戦地憲兵』、図書出版社、1980年、123頁。志村毅描述了野战宪兵从事特务工作的场景,“在某个战场上,宪兵只是乘坐着跨斗式摩托车或是骑马来到驻扎地,听取情况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而间谍则由宪兵拷问”。(69)志村毅「戦争を知らない世代に語り継ぐ」、創価学会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会『揚子江が哭いている——熊本第六師団大陸出兵の記録』、189頁。联系上文所述南京宪兵队对中国民众“生杀予夺”的肆意性,就不难想见日军野战宪兵手握何等无羁的权力。
结 语
南京大屠杀期间诸多惨案的发生,与华中日军宪兵存在密切关联。淞沪会战结束之后,华中日军宪兵面对军中滋生的酗酒斗殴等违纪行为采取漠视态度,对于官兵掠夺、强奸等战争暴行怯于阻止、揭露,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军中树立作为“军事警察”的“权威”。南京沦陷后,仅有少量随军宪兵进入城内,他们对于日军官兵制造的暴行,依旧采取熟视无睹甚而姑息纵容的态度,导致宪兵的“权威”进一步失坠。需要指出的是,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不仅未能成为维护军风军纪的表率,且与普通官兵同流合污,同样扮演战争暴行制造者的角色。
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华中日军宪兵“权威”的失坠,应被视为一种反常现象。淞沪会战以来,华中日军上层为尽快实现攻陷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目标,利用各种手段强化部队战力,甚而通过牺牲军风军纪,以激发底层官兵的蛮勇。随着战事的平靖,树立宪兵在军中的“权威”,成为日本军部与华中日军上层加强其对部队统制力、重塑日军“军纪严明”形象的重要举措。南京大屠杀期间随军宪兵出现的失职问题,又促使日本军部与华中日军上层加快这一进程。
随着华中派遣宪兵队的编成,华中日军宪兵在组织和职能上发生明显变化。华中派遣宪兵队一改原日军随军宪兵临时、松散的组织形态,逐步形成“华中方面军—华中派遣宪兵队—主要都市宪兵队—基层地区宪兵分队(派遣队)”的垂直隶属结构,其组织严密性大为提高。至1945年时,华中派遣宪兵队下属分队数达35支,宪兵网络基本涵盖华中沦陷区内主要城镇(70)参见荻野富士夫『日本憲兵史 思想憲兵と野戦憲兵』、255頁。,野战宪兵成为战时日本对华中沦陷区实施殖民统治的基干力量;在职能上,华中派遣宪兵队被授予更为广泛的权限,其业务逐步集中于特务工作,行政、司法警察的职能凸显,军事警察的职能弱化。
华中宪兵“权威”的树立,是否改变了华中日军军风军纪的面貌?南京大屠杀之后,华中派遣宪兵队在一份关于南京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驻屯各地的日军官兵仍沉浸于战胜之势头,遂致军风军纪涣散,敢于从事各种犯罪活动,给居民生活带来不安。因各上司、机关给予适当的指导和管理,目前军风军纪趋好”(71)《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1938年2月19日),庄严主编:《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62页。,以此说明在短时期内宪兵的整肃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1943年7月,华中派遣宪兵队教习队制定《军事警察勤务教程》,其中较长时段地考察了华中日军军风军纪的变化:
中国事变爆发之初,即南京陷落不久之际,华中军人军属的恶行犯罪颇多,特别以对上官冒犯等恶性军纪犯为首,辱职、掠夺、强奸等令人厌恶的犯罪频发,其后因上司的指导得当与官兵的自觉而逐渐减少……虽然犯罪渐减的倾向如前所述,然而若观察其恶质程度,则难称良好。即逃亡、企图免除兵役、自伤等战争倦怠厌恶乃至观望凯旋等,志气战意消沉,或基于破坏军纪军秩以下犯上的思想意识,冒犯长官之类行为有所增加,尤其是出现内容恶质化的倾向。另外,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等相关犯罪不绝其迹。(72)「軍事警察勤務教程」、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447—448頁。
从这段记录可见,南京大屠杀之后宪兵突击性的整肃工作,并未使日军官兵形成对军法军纪敬畏的心理。虽然官兵的犯罪数量有所减少,然而其所犯罪行的性质更为“恶劣”。军心涣散、“下克上”等问题在华中日军中日益突出,底层官兵对中国民众的掠夺、强奸等战争犯罪行为频繁发生。这一报告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后华中日军宪兵基于官兵恐惧心理所树立的“权威”,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地日军军风颓废、军纪败坏的实相。
然而另一方面,在日本军部的扶持下,以野战宪兵为形态的华中日军宪兵却掌握了不受监督、独断专擅的执行权与处置权,其在沦陷区基层肆意作恶、横行无忌,通过制造各种惨案,营造恐怖气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威慑沦陷区普通民众、镇压抗日力量的“爪牙”。战争时代,华中日军宪兵声名狼藉,不少人战后成为国民政府指名的战犯,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日军宪兵作为法理上的军风军纪维护者,在现实中则是军风军纪的破坏者,这一矛盾性事实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即已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