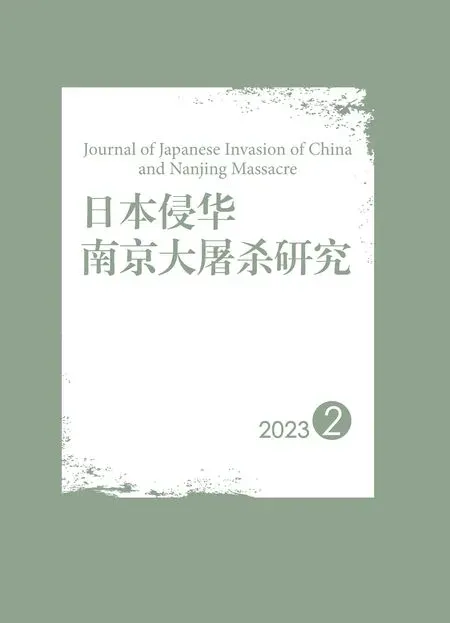两难的困境:抗战时期的难民回流问题(1938—1940)
万振凡 何金华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难民向后方(1)目前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后方的概念并未统一,在地理视角、空间视角、政治视角下后方都有不同的阐述、解释。本文所指的后方既包含了政治视角下国统区的范畴,也包含了地理视角下的中西部等地理单元。关于后方概念的讨论可参见周勇《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研究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迁徙,在难民的跨区域流动中(2)本文所说的难民回流,具体是指在战时由后方返回沦陷区。而沦陷区区域内的流动,如从农村重新回到城市,亦或是各乡村、城市之间的地域流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由沦陷区向后方的迁徙是难民的主要流动方向,学界围绕难民的迁徙背景、对难民的救济以及难民迁徙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方面已有较为系统的探讨。(3)如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张根福:《抗战时期人口流迁状况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6期;常云平、刘力:《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但战时难民跨区域的流动并不只是由沦陷区向后方的单向流动,1938年初即开始出现了难民从后方返回沦陷区的人口流动现象,即战时难民的回流问题。早在1938年,叶朔中就曾对难民回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4)参见叶朔中《伤兵问题与难民问题》,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63—66页。,此后学界对此虽有注意但并未给予较多的关注,鲜有专文论述。(5)如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279页)与程朝云的《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9页)都对此问题有所提及。此外,张根福的《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57页)以浙江杭州、嘉善、吴兴、桐乡等县市为个案,以战时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探讨了战时人口回流的问题。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都是以其专著中的某一小节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关注了战时难民回流的现象,至于社会对回流难民的讨论、国民政府的应对以及难民回流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并未进一步的探讨。
事实上,随着战时难民回流现象的普遍出现,社会上随即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应对难民回流的讨论,国民政府也在战时颁布过相关条令与措施,应对、阻止难民的自由回流。难民的回流不仅是抗战时期的人口逆流动现象,并且由于难民回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特殊性,该现象也引申出了政治立场上“义民与顺民”的气节之争,同时也牵涉到后方为长期抗战储备人力的现实问题,交织着国民政府与返乡难民生存处境之间的现实矛盾。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不仅是对抗战时期难民迁徙、流动上的研究作一点补充,也希望通过探讨战时返乡难民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回乡行为,呈现国民政府与回乡难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存在的矛盾与差异,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思考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间接的战争苦难与基本生存权利的侵害。
一、战时普遍的难民回流现象
全面抗战期间,国统区与沦陷区并存,全国范围内人口数量的变动并无精确统计。若从战时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来考察难民的回流,存在一定客观困难。因此,本文主要通过解读梳理重点档案史料与报刊史料,来考察战时难民普遍的回流现象。
1938年初,难民的回流就普遍引起了社会关注,《申报》《抗战》等主流报刊频频对该问题进行了报道。当年2月《抗战》就报道称,“最近流亡在内地各大城市的江南战区难民都纷纷地准备回乡去”,报道还提及了“集体回乡”的方式及回乡的三条具体线路:
一条是走粤汉路经广州、香港再换海船到上海,再由上海进入战区各县;一条是走浙赣路到金华,再经浙东海口到上海;一条是先到九江再步行过马当山封锁线,坐外国江轮赴下游各埠。(6)倪锡英:《可注意的难民回乡问题》,《抗战》第49期,1938年2月,第6页。
同年3月,《申报》也对难民回流的现象给予了较大幅度的报道,3月15日《申报》香港版就刊发了简讯,“难民约二三万人,陆续由汉南下,经港回籍”(7)《难民陆续过港回籍》,《申报》(香港版)1938年3月15日,第4版。,这与此前《抗战》所报道的第一条线路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申报》汉口版则在3月8日就发表社评《难民回乡问题》,提到“近来关于难民回乡问题,颇引起社会之注意。除一般刊物上,关于此项文章多所披露外,政府当局以及公众团体,亦皆纷起研究”。(8)《难民回乡问题》,《申报》(汉口版)1938年3月8日,第1版。随后不久,3月14日《申报》香港版继续将此文以社评形式刊登,并在卷首强调,“救济难民与防止难民回乡问题,本报曾于八日有所论述”。(9)《难民回乡问题》,《申报》(香港版)1938年3月14日,第1版。从《申报》特意将该问题重复刊发这一点不难发现,此时难民回流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及政府当局的普遍注意。同年6月,《抗战》仍对该问题关注不减,“发现有不顾离去而宁愿冒险重返陷落敌手家乡的很多!这个问题实有深切加以注意的必要”。(10)王哲民:《关于难民返乡问题》,《抗战》第83期,1938年6月,第7页。此后,社会对战时难民回流现象持续关注,就笔者所见的报刊资料而言,迟至1940年,社会各界对难民回乡问题仍有较多关注。(11)如范式之:《减少难民与防制顺民问题》,《全民抗战》第5期,1938年7月,第56—57页;蒋玉麟:《解决难民问题的建议》,《轴心》第14期,1938年8月,第13—14页;沈威:《政治进攻声中的难民回籍问题》,《大风》第72期,1938年12月,第5—6页;《振委会通函各省市劝阻难民回籍》,《新闻报》1939年3月15日,第14版;《港地难民陆续回乡》,《中国商报》1939年11月15日,第1版;彭文应:《难民回乡问题》,《抗战月报》革新特大号2卷1期,1940年7月,第29—30页。
在时人所留下的私人记述中,也发现了战时难民返乡的记载,其内容在时间与地点上与上文的报刊资料有一定旁证关系。原清华大学教授浦薛凤曾记载,1937年11月常熟沦陷后,他大姐一家从常熟逃难至武汉,但1938年2月初浦薛凤收到书信得知,“大姊同儿女已离汉搭车由港返沪”,“瓞农住汉不久,亦合伴归乡,一行五六十人”。(12)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册,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70页。北大教授郑天挺在1938年9月经香港乘船回乡吊唁时记载:“旅客多江浙人,大多逃难由皖、赣、鄂、湘转道粤东以归。”(1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9页。这与1938年2月《抗战》所报道的线路和集体回乡的方式都有所印证。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在日记中也曾记载自己的儿子原已迁至重庆,但在重庆政训处的工作解散后,便从重庆回到了浙江老家。(14)《张棡日记》第9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372、4380页。
此时国民政府为应对战时难民回流所采取的措施,则再次表明了难民回流现象的普遍。1939年3月《申报》报道:“国府鉴于近来各地由战区逃出之难民,因日久旅居,生活困难,一般贫民,拟回籍度日,为纠正此种错误思想起见,特饬由振济委员会切实劝阻。”(15)《振济会劝阻难民回籍》,《申报》1939年3月5日,第9版。大约一周之后,多家主流报刊也报道了同样内容:振济委员会劝阻难民回籍。(16)如《振委会通函各省市:劝阻难民回籍》,《新闻报》1939年3月15日,第14版;《振济会劝阻难民回籍》,《时报》1939年3月15日,第5版;《中央劝阻难民回籍》,《救济旬报》1939年3月21日,第5版。据此,作为难民救济主要机构的振济委员会应该是在1939年3月向各省市下达了有关劝阻难民回籍的正式指示。1939年行政院在关于救济工作的报告中也提及了难民的回流问题:“敌伪近月以来,对于各地难民多方诱惑,故订颁回籍难民处理办法及难民组训办法大纲,现各地报告成立难民组训委员会者,计有四川、陕西、湖南、湖北、山西等省共十八处。”(17)《行政院关于救济工作之报告》,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社会建设(二)》第97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90页。从这则史料分析,难民的回流现象在各省应均有发现,国民政府也统一颁布了关于难民回籍的处理办法。在1940年《湖北省政府公报》所刊发的《难民回籍处理办法》,文尾就注有:“本办法由军事委员会会政治部、振济委员会分呈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核准施行。”(18)《难民回籍处理办法》,《湖北省政府公报》第399、400期合刊,1940年1月,第35页。同时该办法也收录在《中央战时法规汇编》,具体详见《处理难民回籍办法》,《中央战时法规汇编》下,1939年,第267—269页。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一项训令,也印证了国民政府的确正式颁布过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前曾会同拟定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呈奉钧座核准施行在案。”(19)《关于废止难民回籍处理办法的训令》(1940年8月),重庆市档案馆藏,0053-0002-0149-0000-0003-000。从此处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应对层级上看,难民的回流在此时应是一个颇为普遍且备受国民政府重视的问题。
部分地区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也基本与上文的分析相佐证。1938年11月军政部曾抄发了第五战区关于防止回籍难民的办法,“拟呈‘防止敌人在豫皖边境欺骗利用我民力物力办法’及对过境回籍难民宣传纲要各一份”,“各战区同时施行以利抗战”。(20)《军政部兵工署关于抄发防止敌人在豫皖边境欺骗利用我民力物力办法》(1938年11月),重庆市档案馆藏,0191-0001-0103-1000-0038-000。1940年11月,江西省临时参议会也提出过“制止难民回籍以免资敌案”。(21)《许参议员提制止难民回籍以免资敌而利抗战案》(1940年11月),江西省档案馆藏,J017-1-00204-0027。1942年万县的一份报告则反映了难民回流的具体现象:“此地难民时有逃回沦陷区者(据调查,数月以来,已逃回四五千人),实抗战建国中之危机。若不亟为补救,倘效尤成风,后患实堪虞也。”(22)《李运昌关于万县难民组成情况的报告》(1942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管藏。转引自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万县作为此时陪都重庆的近邻区县,其材料所反映的回乡问题颇具代表性和说服力。从以上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难民的回流现象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广泛性。
张根福和徐旭阳两位学者分别依据浙江、湖北的一部分日伪资料,论证了难民回流的现象。张根福以浙江杭州、嘉善、吴兴、桐乡等县市为个案,指出全面抗战初期与中后期沦陷区都存在“人口回迁”现象,并整理出了具体的回迁人数统计,特别是全面抗战中后期的难民回迁,应该包含大量从后方返回的难民。张著引用了伪浙江省政府印行的《浙江省政概况》,伪警务处于1943年对杭嘉湖及萧绍等17县市控制区人口进行了统计,“计自三十年九月份起,至三十二年六月份止,人口总数已由1544975人增至2331100人”。(23)参见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54页。徐旭阳对一部分由湖北武汉返回东部沦陷区的难民人数进行了统计。武汉沦陷时滞留了大量难民,伪政权建立后为了恢复武汉的社会秩序,采取了遣送外地难民回乡的举措。1939年1月伪《武汉报》就报道武汉治安维持会通知社会局,对“长江下游如安庆、大通、芜湖、南京、镇江等地,因事变逃避来汉之难民”,经登记查实后“设法觅具船只遣送回籍”。这基本与上文张著分析的回迁地域相近。并且徐著还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的一部分资料,统计得出1939年5月至1940年1月期间,“由伪武汉特别市社会局协助转请日军特务部颁发长江中下游各埠乘船许可证、自费购票返乡的难民,共计11090人”。(24)参见徐旭阳《灾难·屈辱·倒退和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沦陷区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页。两位学者对回乡难民的数量统计,虽然只涉及部分地区、部分时间段,但两者作为流入地与流出地在地域上有一定的直接联系,从难民流动的具体数据上给予了本文一定佐证。
通过档案史料与报刊史料的解读梳理,基本可以确定,战时难民的回流是一个从1938年初就开始并持续的普遍人口流动现象。但与全面抗战初期人口内迁不同的是,人口内迁的流动规模大且集中,而难民的回流主要是呈分散、独立的小群体式流动特征。
二、难民回流原因的分析
难民历经艰苦逃亡到后方,为何又选择在战时返乡?从此时社会讨论反映的信息看,难民回乡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在后方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二是日军在沦陷区实施所谓的“怀柔”政策,主动招引流亡在外的难民返乡。
籍贯对难民具有特殊意义,就如难民自己所言,“人是生下来先有了籍贯才有了名字”,“离开了自己的家,人就如飘在大洋上的小舟”。(25)《难民》,《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8月26日,第8版。实际上,籍贯所衍生出的社会关系或许是普通人最为仰仗的,除此之外,大部分普通人并不具备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杭州沦陷时,丰子恺逃离家乡时就曾感叹:“石门湾镇上的人,像他们这样生活托根在本地的占大多数,像我这样糊口四方的占最少数”,一般人“逃出去,也是饿死!”(26)《桐庐负暄》,《丰子恺全集》文学卷4,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丰子恺的感受或许间接道出了普通难民逃离后方后的困境。因此,难民出于避难求生的本能逃离家乡,并不仅仅只是对“场所”的告别,也意味着脱离家乡熟悉的生活经验以及身份的变化。或者说“从流离的那一刻起,经验、成熟和社会的时钟都在滴答作响,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变化”。(27)〔美〕萧邦奇著,易丙兰译:《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理解籍贯对难民的特殊意义,就为探讨难民战时的返乡行为提供了一定参考。
难民战时的逃离行为并不具有任何的计划性和前瞻性,逃往哪里,能逃多久都是未知数。这也就预兆了大部分难民在后方艰窘的生存处境及返乡行为,就如此时《申报》社评对难民回乡行为的分析:
难民流落异乡,大半失业,收容所之待遇,自远非平日家庭所可比。甚且徘徊道左,收容所亦不得入,既无物质足够其典质,又无亲友足供其凭依。瞻念前途,战事之结束何日,生活之寻觅无方,于是乃发生“终死也,与其死于异地,毋宁死于故乡”之心理,而况异地之饥寒必死,故乡之冒险,尚有九死一生之望乎?(28)《难民回乡问题》,《申报》(汉口)1938年3月8日,第1版。
1938年两位江苏籍难民逃至重庆后生活无继,不得已向政府请求救济,两人的救济状描述了他们此时流落后方的生存状态:
惟目前囊空如洗,生活发生问题,既以人地生疏,告借无门。又无收容所可资容身,艰苦困迫,难以言宣,现寓民生寄宿社,已欠数日房金。每日专特少许稀饭充饥,身体已感难以支持,在此特殊困迫之下,不得已具呈。(29)《重庆市政府关于救济江苏难民陈鸣一、吴壮游的批》(1938年6月1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0098-0002-0003-6000-0032-000。
无积蓄、无工作、无住所、无亲友可凭依,是此时大部分难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难民便有可能沦为乞丐。1939年11月《大公报》就报道港九地区露宿街头行乞之人“总有一万人以上”,而这部分人“除一部分为本港原有贫民之变相外,其余有不少为内地逃难到港之难民”,并指出“由战区中逃难到港,因港中生活程度极高,所带生活费用,瞬息告罄,在港既无生产,而故居又不能返回,不得已沦落为乞丐,藉延残喘,其境遇至堪怜悯”。难民虽然处境引人怜悯,但仍会被香港当局以维持社会治安及整肃市容为由予以肃清、驱逐。(30)《当局整饬市容,肃清街头乞丐》,《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29日,第2版。而难民迫于生存,不得已乞讨的现象并不鲜见。1940年重庆市警察局就曾发布训令,“近来本市,有类似难民乞丐,结队在各大商号乞讨,态度强硬非达到要求数量不去,殊属妨害市容秩序,仰饬严予取缔”。(31)《重庆市警察局关于取缔类似难民乞丐强硬乞讨的呈、训令》(1940年5月),重庆市档案馆藏,0061-0015-0336-6000-0020-000。香港与重庆的两则材料,可以基本说明一是确有逃到后方的难民沦为了乞丐,二是沦为乞丐又面临着被肃清、驱逐的境地。郑天挺1938年9月回乡吊唁时,对于沿途难民的一段记载则更加详细地说明了难民越逃越难,迫于无奈行乞的穷困境地。船抵汕头时,他曾这样记载,“有少女操吴音登舟求乞,自谓与母逃难至此而资斧绝,困居旅舍,不得已而出”,这里不难看出难民逃亡无以为继的现实状况,而郑天挺形容该少女“衣履敝而周整,不似下流”,(32)《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89页。则反映出了逃难途中难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无奈乞讨的状况。
面对战时大量集中的内迁难民,国民政府事实上实施过诸多措施进行救济,诸如短暂保障难民食养的收容所,诸如难民移垦、创办难民工厂、开办难民职业介绍所等积极的长期的救济措施。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对后方难民实现普遍的救济,即使是短暂保障难民食养的难民收容所也是有限的救济。就如前文所引收容所“自远非平日家庭所可比”,客观环境上收容所多是以“当地之祠堂、庙宇及公益场所”组成(33)《各级党部难民救济工作实施办法》,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社会建设(一)》第9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85页。,生存环境较为恶劣。1940年江西的一份议案就指出,“各县收容所诸多指定祠堂、庙宇,男女亲处彼此不分,以至奸淫盗窃之事时有”。(34)《制止难民回籍以免资敌而利抗战案》(1940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藏,J017-1-00208-0022。其次,收容所也只是“日图三餐,夜图一宿”依赖式的寄生生活,而且据湖北省的一份资料显示,对于难民的收容还秉承着“随时收新随时疏散”的原则,“难民收容不得超过三个月”。(35)《湖北省振济会宜都县难民收容所关于难民痛苦请继续收容救济的呈》(1942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LS006-002-1185-0004。虽然各地收容办法、原则有所差异,但普遍来说,收容所的客观环境以及战时收容所的救济性质,并不能实现对难民的长期救济与安置。
从难民自身来说,面对收容所的食养救济,并不愿意长期滞留于此。战时收容所的混乱或多或少让难民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战时收容所屡被指出对难民侮辱打骂,“据说有些难民收容所里面的管理员,对待难民,简直有如狱卒对囚徒一般,稍不如意,便会拳棍交加,打骂相随”。(36)蒋玉麟:《解决难民问题的建议》,《轴心》第14期,1938年8月,第13页。1939年一位逃难至江西的难民就曾因为在收容所的困苦遭遇写了一份状呈,“自逃到兴国之后,不料该县收容所,视难民若乞人,待遇形如乞丐任意侮辱,或迫令难民操作苦工,否者停止给养,且对于上令规定菜费分文不发,种种惨状不堪枚举”。该状最后还写道,“原为拥护领袖长期抗战,不将人力物力资敌,争取最后胜利之大计,自愿舍乡别祖丢去家产逃难后方,藉表爱国图存之真诚,何其竟受压迫似此”。(37)《桂仁风、张善茂为枚举难民收容所种种惨状乞彻查依法办理的呈》(1939年8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J008-1-01217-0001。这已反映出了此时难民颠沛流离下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也就不难理解难民的返乡动机。所以逃亡的种种苦楚,已使最初抱着及汝皆亡之心的难民失去了信心。就如艾芜在逃难途中,对湘江一带回乡难民的描写,“还逃什么呢,拖都把人拖死了”,“一句话啰,死还是死在自己地方上好!”(38)艾芜:《难民还乡》,《艾芜全集》第1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同时日军在沦陷区以“怀柔”政策主动招引,也是难民选择回乡的原因之一。1938年8月《全民抗战》就报道日军“以传单标语等印刷品广为散发我前线”,宣传在日军的统治下,地方“安居乐业,各执其务,向着王道乐土迈进”。在多方宣传之外,日军还以实物引诱,“在接近我前方公路两侧,间并预置若干耕牛和食盐,诱致我无知难民回乡”。(39)范式之:《减少难民与防制顺民问题》,《全民抗战》第5期,1938年7月,第56页。《湖北省政府公报》也披露1940年前后日军招引难民回乡的具体举措,“据报近有奸人煽动难民”,“家乡亲友来信,告以今年丰收且敌倭优待民众”,并提及“沿途有人招待拟在秋凉结伴回乡”难民的方式路线:
自芷江起程用民船经滤溪赴常德改坐汽船(半价),到长沙后乘火车过株洲到萍乡(此段有人招待车可免费),再步行经宜春分樟树、临川、东乡、金华至上海(沿途均有人招待不需路费)。(40)《电发难民回籍处理办法仰即遵照》,《湖北省政府公报》第399、400期合刊 ,1940年1月,第24页。
报道还指出,“上列情形闻各处均有同样事情发生”。四川、江西的两则档案史料就印证了这一点。1938年四川省就传达过要注意敌人引诱难民回籍的训令,“查敌方以怀柔政策诱惑战区难民回籍,资其利用,自属严重”。(41)《关于劝止敌方诱惑战区难民回籍并拟定统筹救济办法给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署的训令》(1938年5月),重庆市档案馆藏,0081-0003-0040-4000-0009-000。次年江西省九江县党部也报告称,“接有本籍未流亡之亲友来函,谓地方安靖,并言产业急待登记,嘱即回籍办理,否则失其原有权等语”(42)《敌在沦陷区域假藉产业登记威胁难民回籍请核议研究对策的笺函》(1939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藏,J016-3-03049-0233。,与《全民抗战》的报道内容基本相似。还有如前文所引,在伪《武汉报》所报道的消息中,日军主动“赈济”“遣送”难民回乡的举措,对“长江下游如安庆、大通、芜湖、南京、镇江等地,因事变逃避来汉之难民”,经登记查实后,“设法觅具船只遣送回籍”。因此,难民在自身逃亡无以为继的生存状态下,面对日军“积极”主动的宣传、鼓动以及胁迫,“多数意志不甚坚定的难民,便在这诱骗的宣传下都动了归乡之念”。(43)倪锡英:《可注意的难民回乡问题》,《抗战》第49期,1938年2月,第6页。
战时难民的逃离行为是面对战争威胁本能的仓促行为,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但抗战区域扩大与长期抗战格局形成后,大部分内迁难民却不具备长期逃亡的现实条件。若要继续在后方长期流亡,那此时的逃亡就必须带有重建的意义。而如果在后方不能实现重建的意义,对于难民而言,回乡便成了此时必然无奈的选择。就如时人所言,难民逃亡是希望“后方能保着生命及前途生活的出路,但是事实的教训,只有使他们焦虑悲愤,失望,丧气!”(44)王哲民:《关于难民返乡问题》,《抗战》第83期,1938年6月,第7页。所以,难民在后方的生存危机与日军的主动招引、胁迫是难民回流的表层原因,大部分难民不能将后方的逃亡转化为重建,返乡就成了“必然”。
三、义民与顺民:社会对回流问题的讨论
战时难民回流现象的普遍,随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围绕如何看待、应对难民回乡问题的讨论。主观情感上,社会舆论对于难民的返乡行为抱有同情,普遍认为被难同胞因生活困难而返里,深堪同情,但实际行动上对难民回乡行为持以坚决否定的态度。首先在政治意义上难民的返乡行为上升到了“义民与顺民”的气节之争。难民本身基本不含政治意义,但此时难民的返乡行为则被赋予了政治意义。难民的回流在时间上是发生在战时,空间上是从后方返回到沦陷区,因此,难民的返乡行为即被视为“顺民”,甘当难民则被视为是“义民”。“宁做难民不做顺民”是社会舆论的主流,也被认为是政治人格的体现。舆论认为,“敌寇和我们的国族,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大决斗,我们积极上不能尽其所有以贡献国族,就该在消极上不妨碍抗战建国的进展”。(45)《顺民做不得》,《政治旬刊》第68期,1938年12月,第31页。即使难民的返乡行为主要是迫于生存的无奈,但此时返乡已经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返乡即被视为“顺民”,并不被社会主流舆论所接受。社会主流舆论的导向是“没有勇气去反抗,那么与其做顺民,我愿意做一个难民”。(46)闲人:《难民和顺民》,《大美晚报》1938年4月3日,第6版。甚至有观点表示,“顺民做不得,一做顺民,思想言行,在客观上就和汉奸没有多少分别”。(47)沈威:《政治进攻声中的难民回籍问题》,《大风》第27期,1938年12月,第6页。相反,甘当难民则被高度肯定和赞扬,1940年就有观点提议“难民应该改为义民,借以提高难民人格”。(48)《难民应改称义民》,《前线日报》1940年7月3日,第4版。不难看出,此时社会舆论对政治意义上“义民与顺民”的讨论推崇的是义民,自由返乡做顺民的行为客观上并不被社会所包容和接受。
其次,在具体如何应对难民返乡的问题上,基于难民返乡对抗战的利弊出发,社会舆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难民返乡对抗战有害应该阻止。该观点认为国家构成要件为土地、人民与主权,抗战以来中国对于土地实施焦土政策,因此人民也应“随焦土政策之施行”,疏散于内地。而“难民在敌之占据期中,仍纷纷返其故乡”,“敌人自必利用其生产,以增加侵略之力量”,使“焦土抗战之意义,亦遂丧失无余”。(49)《难民回乡问题》,《申报》(香港)1938年3月14日,第1版。与该观点相似,还有观点认为政府、人民、土地三者是立国的基本要素,现在一部分土地虽被敌人暴力占领,但若没有人民帮他生产,供他驱策,那么即使占领的地区再大一点,也没有用处。人民是“活动的资源”,在艰苦的抗战中“不能轻易把大批的活动资源去奉送给敌人”。(50)倪锡英:《可注意的难民回乡问题》,《抗战》第49期,1938年2月,第7页。该观点强调的是,“顺民多一人,即敌寇可用之力多一分,而其崩溃的时间,亦迟一刻,于是我国的最后胜利就淡一度,这是资敌卖国的叛徒行为”。(51)《顺民做不得》,《政治旬刊》第68期,1938年12月,第31页。所以难民的返乡行为被视为对抗战有害无利即应阻止。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若难民返乡对抗战有利,则应遣送而非阻止。该观点从难民与后方的现实处境为考量。一是认为难民仅仅迁居于安全地带,生活并无长期保障,一味强行制止,恐难收效,徒使无数难胞痛苦不堪,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为自己造怨民,为敌人造顺民的行为。二是认为在长期抗战的背景下,战事延长,战区更为扩大,后方并不能对难民给予普遍的救济,并且长期抗战正需人力,难民关在收容所里,是徒然消耗国力。因此,难民回乡不仅对自身有利,使难民“有屋可住,有田可耕,有业可操,生活有保障,流离后方的痛苦,可以避免”,也能“减轻政府及后方人民重大的负担”。(52)丘云甫:《难民回乡问题的检讨》,《抗战时代》第6期,1940年12月,第14页。
从实际角度上看,若难民返乡对抗战有利,则应遣送而非阻止的观点,正视了难民与后方的实际,也冲破了返乡即为顺民的政治束缚。该观点中的遣送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帮助难民返乡,而是基于难民返乡对抗战有利的基本立场,对返乡难民予以组织与短期训练,期望他们返乡后能发挥一定的抗战作用。所以该观点认为,难民返乡本并不是一个坏现象,甚至有舆论认为,“我们不应阻止难民回乡,我们唯恐难民不回乡”。(53)彭文应:《难民回乡问题》,《抗战月报》革新特大号2卷1期,1940年7月,第30页。该观点认为难民深受痛苦,反抗情绪浓厚,并熟悉家乡环境,与当地民众非亲即友,因此,若能对回乡难民予以组织与短期训练,难民回乡后可人地相宜地从事组织沦陷区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刺探情报等抗战工作,在沦陷区与敌人作长期抗争,从而将回乡做顺民的局面,改变成“武装回乡,收复失土”的大运动。(54)倪锡英:《可注意的难民回乡问题》,《抗战》第49期,1938年2月,第7页。
社会舆论对难民回流问题的讨论,对于难民回流总体持否定态度。难民的返乡行为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返乡即为顺民,社会舆论号召的是“宁做难民不做顺民”。但在具体讨论上,则有经组织训练后的遣送与阻止的两种意见。实际上,社会舆论对难民回流问题的讨论,中心围绕着难民返乡与抗战的利弊关系。
四、服务抗战为根本:国民政府的应对
难民回流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具体的应对措施,措施与此前社会讨论的主要观点基本保持了一致。国民政府同样对返乡难民主观情感上表示了理解,“被难同胞,颠沛流离历经艰苦,渴念家乡自属人情”。(55)《对过境回籍难民宣传纲要》,《中央战时法规汇编》下,1939年,第269页。但实际行动上对自由返乡的行为在名实上都予以坚决否定。1939年3月,赈济会通函各省市劝阻难民回籍,就表明难民返乡是“错误思想”,并采取了阻止措施,“各地军警在各交通口岸切实劝阻难民回籍”。(56)《振委会通函各省市:劝阻难民回籍》,《新闻报》1939年3月15日,第14版。1939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的《救济难民运动纲要》也指出,“不作汉奸不做顺民”,“当汉奸固然永不齿于人类,就是甘做顺民也不啻自掘坟墓”,“现在一时的牺牲和痛苦,应认为是抗战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无可避免”。(57)《难民本身应有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社会卷》第2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不难发现,国民政府也将难民的返乡行为赋予了政治意义,返乡即为顺民,并强调此时难民应当为抗战作一时的牺牲和忍让,实际上也是在号召“宁做难民不作顺民”,基本表明了国民政府在主观意识上对于难民自由返乡的否定态度。
在具体应对措施上,国民政府采取了阻止与组织训练后的遣送两种方式。首先在阻止的措施上,1939年江西省所颁布的“防止难民回乡办法令”颇具代表性,主要原则是从引导与防范两方面入手,阻止难民回流。引导方面:一是加大收容使难民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各地收容所对到境难民务须尽量收容”;二是“扩充难民生产事业”,如“增加工厂”“扩大垦殖事业”“积极举办小本贷款”,使难民皆有生计;三是“举行职业调查与介绍”,使难民“身心有所寄托,生活得以安定”;四是对难民给予关怀,“经常进行劳慰工作”“召集难民及当地人民举行联欢会籍以联系感情”“纠正当地人民鄙视难民之心理”;五是切实加紧对难民的宣传工作,“指导各报馆及宣传团体,尽量暴露敌人残酷行为,同时极力宣传政府救济难民工作之情形,籍以把握难民信仰”,主动防止难民回流。(58)《江西省政府关于准省动员委员会函送修正防止难民回乡办法令仰遵照的训令》(1939年5月),江西省档案馆藏,J023-1-00454-0016。
在实施引导措施的同时,再辅以防范措施阻止难民回乡:一是以布告的方式劝阻难民返乡,“张贴各交通要衢及难民收容所内”,“尽量暴露敌人之暴行,使难民有所畏惮”;二是检查邮电,“沦陷区内来往信件一律严加检查,如发现含有诱惑难民回乡情事,即予扣留”;三是严密户口调查,加强难民管理,对收容所难民“予以组织,严行管理”,“自由避居内地者”,“当地政府须严密户口调查,编入保甲组织”,“如户口有异动时,事先应报请当地政府核准,否则不许迁徙”;四是“随时派员化妆在各收容所或交通要道侦查,如发现难民有可疑行动应予扣留”。此处之所以强调是阻止难民的“自由”返乡,是因为国民政府在1940年8月以前试图允许并支持一部分难民经组织训练后返乡从事一定抗战工作,即社会讨论中若难民返乡对抗战有利则应遣送而非阻止的观点的实践。这一设想在1939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难民组训计划大纲》中得到了说明:“使战区及接近战区之难民,人人不离乡土,并能切实做到自卫自养,以增加抗战力量,而减少政府对难民之负担”,“使后方回籍难民”,“不做顺民,不为敌用,并能发挥各个人或集体之力量,摧毁敌人一切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侵略设施”。(59)《难民组训计划大纲》,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社会建设(一)》第9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72页。《对过境回籍难民宣传纲要》则更详细地说明了国民政府期望这一部分回籍难民所发挥的作用:
吾人回籍之后,即应联络亲戚朋友,与本城本镇或本乡村之同胞组织严密之侦探网侦探敌情,报告国军。组织多数之破坏队,破坏公路桥梁,机场仓库,使敌人运输补充陷于绝境。组织广大之游击队,牵制敌军之后方或侧翼,使其不敢锐意前进。组织宣传队,向同胞宣传,敌人之暴行与欺骗之阴谋,并宣达我政府对沦陷地区同胞眷怀之德意。报告政府抗战到底,复仇雪耻之决心与我愈打愈强,敌愈打愈弱之事实,则丰功伟绩,实可与前线抗战将士相比伦,而无愧色。(60)《对过境回籍难民宣传纲要》,《中央战时法规汇编》下,1939年,第270页。
国民政府对遣送这一措施的施行,是期望回籍难民利用对家乡熟悉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在沦陷区发挥一定的抗战作用。在此后所颁布的《处理难民回籍办法》中,国民政府对这部分回籍难民予以了极大支持,“回籍难民,应依其程途之远近,由救济机关或呈请政府酌给路费”(61)《处理难民回籍办法》,《中央战时法规汇编》下,1939年,第268页。,“难民回籍途中之振济机关对于难民之食宿应予以招待”(62)《难民回籍处理办法》,《湖北省政府公报》第399、400期合刊,1940年1月,第35页。。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国民政府对该措施的高度期望。所以,国民政府在阻止难民自由回流的同时,又允许支持一部分经组织训练后的难民回籍。这实际上还是从对抗战是否有利的角度出发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国民政府希望经过组织训练后的回籍难民能在沦陷区发挥一定抗战作用,达到“里应外合”的效果,主动将返乡做顺民的局面,转变成“武装回乡,收复失土”的大运动。
对难民回流问题的应对若能按照以上措施进行,那么难民回流无疑对抗战有极大帮助,不仅能适当弥补后方对难民救济的不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全民抗战,难民回流也就不至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却废止了此前颁布的《难民回籍处理办法》:
前曾会同拟订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呈奉钧座核准施行在案。嗣后军政部为断绝敌区交通,至敌死命计,复经订定封锁敌区交通办法,呈准颁布。兹查以上两种办法,大有抵触之处,曾有关机关一再研讨佥认为敌人正在企图安定我沦陷区域,引诱难胞回籍,吾人应即依照封锁敌区交通办法严厉执行以资抵制,至原订之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应予废止等语。(63)《关于废止难民回籍处理办法的训令》(1940年8月),重庆市档案馆藏,0053-0002-0149-0000-0003-000。
此训令在湖北、广西、云南、浙江、江苏五省的政府公报上均有刊发。(64)详见《奉令废止难民回籍处理办法电仰知照》,《湖北省政府公报》第415期,1940年9月,第13页;《饬废止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广西省政府公报》第869期,1940年9月,第9页;《奉令废止难民回籍处理办法一案令仰知照》,《浙江省政府公报》第3245期,1940年9月,第19—20页;《奉国民政府令为准将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废止等因一案令仰知照》,《云南省政府公报》第74期,1940年9月,第8—9页;《奉军事委员会令难民回籍处理办法应予废止一案令仰知照》,《江苏省政府公报》第38期,1940年9月,第15页。训令中“抵触之处”即指断绝地区交通式的全面阻止难民回流,与此前颁布的《难民回籍处理办法》中允许一部分难民经组织训练后回乡相矛盾。而采取实施封锁敌区交通的办法全面阻止难民回流,应该是此前对回籍难民予以组织训练后“武装回乡”办法收效不佳。其实在此前社会对难民回籍问题的讨论中,就有观点质疑难民返乡后是否还能发挥原定作用,“前方所做应做的工作,如敌情通讯,内向宣传,反间谍等等,在敌人强力的监视之下,如何能与后方联络,发生效力?”(65)丘云甫:《难民回乡问题的检讨》,《抗战时代》第6期,1940年12月,第15页。如果回籍难民没有发挥武装回乡的作用,国民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全面阻止难民回籍的措施。除了社会讨论中认为难民回籍是资敌行为外,更为客观的现实是在抗战的背景下,难民回流的背后还牵涉到后方为长期抗战,储备人力的现实问题。
国民政府阻止难民自由回流的措施,日军主动招引难民回乡的举动,以及社会讨论中将难民视为“活动的资源”,都直接表明了难民作为潜在人力资源的实际价值。而国民政府在后方实施人力管制,则更为确切地反映了后方一定程度上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现实问题。(66)例如江红英就指出战时实行人力管制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直接关系到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坚持抗战。参见江红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罗玉明、李勇也指出后方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实问题,参见罗玉明、李勇《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探析》,《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在《第二期抗战与军队政训工作的改进》中就指出,“国家处此时机,危急万状,人力物力俱感极大困难,人人都应抱定一人要作二人事,一物要作二物用。”(67)《第二期抗战与军队政训工作的改进》,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92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这也表明了此时后方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和重视。在1939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救济难民运动宣传纲要》,则直接指明了难民群体作为后方人力资源的潜在价值,“前方无时不需要大量兵员之补充,至于前后方的军事运输,伤兵的救济和治疗,汉奸及敌情的侦察,以及各地的游击队等等”,“这一批源源不绝的补充人员,除依法在各地抽调外,难民群中也是最好的来源”。“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后方“处处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和技术工人及普通工人,这一批人员无疑的难民群中能供给一部分”。(68)《救济难民之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社会卷》第2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页。国民政府在战时也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难民服役计划纲要》《难民组训计划大纲》等,力图充分组织、调动后方难民的劳动力价值。在1940年7月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一项救济案,也表明救济难民的出发点之一即为“增加我方之人力,而免资敌用”,“国家战时资源得借以充裕,而与敌作长期经济斗争”。(69)《宽筹救济费用利用移运后方之难民以发展生产事业而宏救济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社会建设(一)》第9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01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将后方难民纳入到了抗战的序列之中。
国民政府对难民回流问题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是以对抗战的利弊为根本原则。阻止难民自由回乡的一贯原则,则是因为难民回流与后方储备人力长期抗战的现实需要相矛盾。在长期抗战的背景下,后方难民大量自由地回流的确是后方潜在人力资源的流失,于长期抗战不利,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难民自由回流。与此同时,本着对抗战有利的角度,也试图允许并支持一部分难民经组织训练后回籍从事一定的抗战工作。但这一构想在1940年被军事委员会正式否定,转而实施断绝敌区交通的方式全面阻止难民自由回流。
五、结论
战时难民的回流是1938年初即开始并持续的分散、独立的小群体式的人口流动现象。
因此,抗战时期难民的流动,并不只是向后方迁徙的单向流动,而是呈现双向流动的特点。难民之所以在战时选择返乡,表层原因是难民在后方的生存危机与日军的主动招引、胁迫。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战时难民的逃亡更多的是出于避难求生的本能,基本属于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的仓促行为。长期抗战格局的形成后,脱离籍贯“庇护”的难民却不具备长期逃亡的现实条件,又很难将逃亡转化为在后方的重建,返乡或就成了此时无奈的必然选择。在如何应对难民回流的问题上,国民政府的措施与社会讨论基本一致,即主观上对回籍难民怀有同情,但在实际行动上对返乡行为在名实两方面都予以坚决否定。同时,本着对抗战有利的原则,也试图允许并支持一部分难民经组织训练后返乡,期望他们人地相宜地在沦陷区发挥一定抗战作用。但这一构想在1940年8月被军事委员会通告废止,转而实施以断绝敌区交通的方式全面阻止难民自由回流。
战时难民返乡的行为已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和抗战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上,此时的返乡行为与国民政府、社会舆论所呼吁的“宁做难民不做顺民”,举国抗战的爱国热情相悖。现实意义上,除了主观认为难民回乡后易被日军奴役、利用,是“资敌”行为于抗战不利外,客观上在长期抗战的背景下,后方一定程度上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难民作为后方潜在人力资源的价值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所以,难民回流问题既是政治意义上“义民与顺民”的气节之争,也牵涉到后方储备人力抗战的现实需要。
难民回流问题交织着国民政府与返乡难民生存处境之间的现实矛盾,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从难民的立场上来说,战时的逃离是期望规避战争对生存的威胁,但是全面抗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大,难民逃亡陷入无以为继、越逃越难的现实境地,出于生存的再次考虑,又不得不选择返乡,这是难民“逃”与“回”之间的两难。再则,国民政府一贯否定、阻止难民自由回籍的基本原则,也并不是完全无视难民的现实处境,事实上国民政府实施过诸如难民移垦、建立难民工厂、开办难民职业介绍所、对难民实施小额贷款等救济安置难民的具体举措。但面对大量集中内迁的难民,这些措施实难起到普遍的救济效果。若任由难民自由回流,的确也是后方潜在人力资源的流失,于长期抗战不利。所以国民政府也处于两难的困境。此外,难民的返乡行为本是出于生存的考量,国民政府的应对则是基于后方长期抗战储备人力的现实需要,难民一定程度上已被国民政府主动纳入抗战的序列之中,因此难民的生存立场与国民政府的抗战立场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两难困境。
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境之下,该如何看待战时的难民回流问题?对于难民而言,返乡是基于生存的选择,是否也应当给予更多的历史关怀与客观理解,就如江沛在分析华北“治运”时期不同战时群体心态所指出的,对无奈状态下民众的选择应该“超越民族主义及政治话语的视角”(70)江沛:《华北“治运”时期诸群体心态考察:1941—1942》,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基于尊重人性的理念,远离政治。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应对措施虽与难民的生存处境有所冲突,但坚持的是抗战立场,最终出发点还是服务于抗战。在难民生存立场与国民政府的抗战立场的矛盾与差异下,是否也启迪我们应该在直接的战争暴行之外,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思考日本侵华战争对普通民众所造成的间接的战争苦难与基本生存权利的侵害。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人民在全面抗战时期以各种方式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
——聚焦各国难民儿童生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