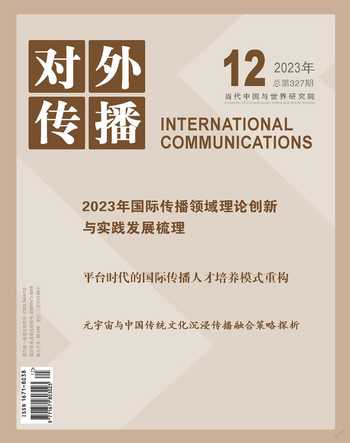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相德宝 曾睿琳


【内容提要】本文对过去41年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历史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整体模式,总结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方向。整体说来,传统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典型的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是以国家需求导向,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内容,复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模式。在培养效果上,该模式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性和表层需求,但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也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结构性失语,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当下媒介技术引发的全域性、生态性、颠覆性变革,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亟需走向分散枢纽模式(hub),通过在不同专业、学科复合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实现从“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从不同专业、学科赋能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赋能不同学科、专业,实现因校、因专业制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養模式创新和专业、学科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国际传播在专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语。
【关键词】国际传播 人才培养模式 权威 枢纽 平台时代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是人才①,而人才培养的核心是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基地,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 ②。高校国际传播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直接决定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同时,新媒介技术对全球国际传播格局带来全面、深刻变革,国际传播进入“深度媒介化时代”和“平台时代”③。深度媒介化社会和平台时代的最核心特征是传统媒介权力的解构,人人权力的上升——人人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角。平台时代,内容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平台本身并不从事生产,转而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为相关内容生产主体提供连接、交互、匹配与价值创造等服务。
从1982年中国国际新闻专业的创建算起④,国际新闻专业建设至今已经走过了41年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5·31”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随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伟业重任的国际传播人才也成为当下国家的迫切需求,高等教育中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更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议题。
在此宏观背景下,如何顺应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形势,适应媒介变革的需求,重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成为当下国际传播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尝试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41年的历史进行全面回顾,同时深刻理解平台时代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提出平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路径。
二、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41年形成的主要人才培养模式、特征及问题
纵观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41年的发展历程,形成“外语+新闻”模式、立体培养模式和个性化地方模式三种模式。
(一)“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新闻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国际传播人才早期被称为对外报道人才。早期的中国对外报道人才培养没有系统的专业学习和学科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作为一种常识,通过一堂课或两堂课介绍一下。后来提出应该“考虑设置专业,或开出一系列课程,从对外报道的理论、原则、直到采访与写作的具体要求,以及外语等方面给学生予全面的训练”。⑤
国际新闻教育的诞生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视国际报道工作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门开启之初,对外报道成为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但是国内的对外报道人员极缺,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国际新闻教育旨在培养更多能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⑥。而从社会宏观视角来看,改革开放直接催生了该专业。⑦
新中国的国际新闻专业始建于1982年⑧,为了解决人才需求的缺口,特别是为了给我国新闻机构培养合格的驻外记者,有关部门和单位联合从1983年起在一些高校中开设国际新闻专业五年制本科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从而正式开始了我国的国际新闻专业化教育⑨。北京广播学院于1982率先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本科专业⑩,最早开设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包括厦门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11。在课程设置上,该模式强调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外语新闻采写”、“英语新闻编译”等课程,培养具有较高外语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鼓励具有小语种教育背景的学生进一步学习新闻传播知识,打通多语种国际传播赛道12。采用“双轮驱动”策略,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有机融合13。另外,还有部分高校与国外的教育机构搭建了合作平台,选送优秀学生前往海(境)外高校学习深造,或开设双硕士学位项目联合培养,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外语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总的来说,早期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模式,通过语言能力、新闻生产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复合14,实现培养讲外语、会传播、懂多元知识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目标。
(二)五校“国传班”:国际新闻传播的立体培养模式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硬实力的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愈益重要。2009年,以提高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支持和协调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五所高校统一开设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设立的“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践”立体培养模式应运而生。
该模式旨在为中央级主流媒体培养国际新闻传播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爱国情怀。同时,该模式强调国际传播教育要坚持“价值引领”,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强化国情社情认知15,熟悉并实践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伦理及相关政策法规。面对当今世界日益清晰的全球化格局,大连外国语大学在其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增加了“世情教育”16,培养学生洞察世界、监测全球舆情的能力。另外,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和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17,合理应对国际传播中的逆境,游刃有余地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格局。
伴随“一带一路”合作的推进,国家越来越需要掌握多语种的国际传播人才。北外、上外、广外等外国语大学利用自身多语种资源,纷纷开设多语种国际新闻传播实验班,合作开展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和研究,力图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传播人才,服务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但从英语+新闻的国际传播培养到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本质上还是一种语言+传播的复合型教育模式。只是语言数量的变化,而国际传播深层次的专业领域知识培训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改变。
就教育类型而言,当前该立体培养模式已经形成了四大类型:一是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重视外语教学高于重视新闻教学的“外重于新”类型;二是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的将外语教学和新闻教学置于同等地位的“外新并重”类型;三是以厦门大学和四川大学为代表的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教育,强调新闻专业与人文学科结合与互补性学习的“新重于外”类型;四是“外新专”并重类型,学生在四年的大学时间里,不仅要学好新闻专业和英语专业,还要额外掌握另外一门专业,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专业,将学生培养成专业复合型的国际传播人才。有学者认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需要实现语言能力、新闻生产能力、知识结构与多种意识的多维度复合,并且需要经历从本科基础阶段、硕士提高阶段到就业深化阶段的进阶式培养过程18。
(三)地方个性化国际传播培养模式
国际传播的地方培养模式主要是指地方高校依托自身学校特色、区位优势、学科和专业优势,深耕某一领域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小而精、个性化培养的特点。例如,近年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利用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加强东南亚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该校明确了其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定位,把握其区位优势,积极了解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国情民情19,制定“一国一策”的定制化国际传播策略,以提升國际传播效果。
同时,伴随近年中华文化“走出去”,一些拥有武术、中医药专业的高校通过创立学科融合的全新专业20加强国际传播。例如,首都体育学院加强中国武术人才的国际传播培养,规定武术国际传播人才要在英语能力、武术技能和文化底蕴三个方面下功夫。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中医+”、“+中医”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中医国际传播能力人才培养。
(四)集中权威: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国际传播+”模式
整体说来,过去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该模式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特点:
1.根本任务。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以服务国家需求为根本导向,从最初的应国家开放之需,到今天担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软实力建设任务,整个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历程紧紧瞄准国家需求,以为国育才为根本指针。
2.培养主体。国际传播人才的“国际传播+”培养模式,强调政府、媒体、高校三者联动,以满足政府需求、媒体需求。高校培养对象主要集中于新闻专业的学生,为媒体国际传播或政府国际传播培养人才。
3.教育内容。过去40多年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以传播能力为轴心,复合外语能力为根本内容。无论是最早的英语还是到当下的多语种,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一种传播能力培训,属于为国际传播赋能的“国际传播+”模式。
4.社会效果。满足了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之需(传播和语言问题),表层之需(语言问题)。可以说,过去的模式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培养模式同样暴露了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只有沟通技巧,缺少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不利于中国在经贸、法律、国际政治、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科技等重大性、专业性问题上占据主动。
三、当下国际格局、媒介技术对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冲击与挑战
当下,全球国际格局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化浪潮深刻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今天的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担当不断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21因此,顺应当今全球国际格局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构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培养符合新时代国际传播需求的人才,成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变革也推动着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随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5G、大数据、云计算、量子科技等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的传播生态发生了颠覆性影响。这场新传播技术变革,是一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其所释放的效果是裂变式的,影响范围是全域性的22。一方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数字技术释放了人的主体活性,为个体的传播活动赋能,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统的专业内容生产(PGC)的边界得以延伸,用户生产内容(UGC)极大地增强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了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信息传播的高效使得“全时”传播成为现实,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彻底打破了国际传播以政治组织、对抗对话机制等要素为主的传统格局,更打破了专业新闻从业者对国际传播实践的某些刚性约束。
四、平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顺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需求以及平台时代的传播特征,本文尝试提出以“分散枢纽(hub)”模式重构传统“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提出面向未来的学科构建基本路径、培养模式与思维创新,尝试解决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结构性失语。
(一)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
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平台时代不同专业与国际传播的逻辑关系厘正。国际传播活动的多年实践证明,“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充分重视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该模式将目光局限于新闻专业的学生,虽然鼓励学生对外语和其他专业进行辅修,扩充知识面,但是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传播内容单一、专业程度浅薄的问题。而“+国际传播”能够推动不同学科领域与国际传播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通国际传播的不同专业赛道,扩大国际传播声量,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占据主动。
“+国际传播”模式的本质聚焦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对象的扩散与延伸,通过在各个学科专业、各大特色高校中开设“国际传播”相关课程的方式,鼓励学生修习国际传播理论知识,搭建各个学科专业与国际传播之间的有机互通。一方面,信息技术引发了新闻领域的互联网革命,新闻生产活动逐渐从职业性的活动转变为社会性的活动23 24,不同专业的学生参与到国际新闻传播活动中来的难度降低、积极性增强;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在国际传播的叙事框架中融入更多学科理论知识,如金融学、国际法、农学、医学等,从而为“讲好中国故事”丰厚内涵,增加底气,提高声量。
(二)从专业教育到素养教育
在中国传统媒体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平台时代,这样的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在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新闻业不断下沉,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得以突破,新闻专业教育的模式也随之不断更迭。如今,我们需要解放国际新闻传播与职业化的密切捆绑,建立针对所有学生的新闻素养教育,实现国际传播技能的下沉与扩散;与此同时,还需不断深化新闻专业理论教育,达成多元协同的传播格局。
為实现这种多元协同的格局,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建构“金字塔模式”。首先,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科培养应继续深耕理论研究,引领学科宏观发展方向,保障专业生产内容(PGC)持续稳定输出,始终承担“小而精”的行业“领头羊”角色。同时,国际传播素养教育应当深入全国各大高校,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搭建起人人参与、百花齐放的国际传播平台。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有能力、更有义务掌握基本的国际新闻传播知识和技能,从而强化用户生产内容(UGC)的质量,提高其专业度,打造“新闻职业共同体”25。
(三)从其他学科赋能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赋能其他学科
在过去的集中权威模式的国际传播中,各个学科作为分支围绕着国际传播这一中心节点,为国际传播赋能,从而出现了其他学科赋能国际传播(“empower me”模式)的学科格局。在这一传统格局中,主角始终是国际传播本身,其他的交叉性学科处于依附地位,为国际传播活动服务,满足国际传播在各个领域的基本需求。这样的学科格局适应于中国国际传播第二次浪潮,用以实现媒体能力纵向提升与多元主体横向扩充26。然而,平台时代推动传播生态系统变革,通信、信息和媒介基础设施都成为全球性产物27,国际传播活动无处不在,无所不传,而以国际传播为中心的集中权威模式对各学科分支不够重视,从而导致国际传播实践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
在此基础上,国际传播学科格局应当转变为国际传播赋能其他学科(“I empower”模式)的分散枢纽新模式。化“人人赋我”为“我赋人人”,让国际传播为其他学科专业走出国门、传播专业化中国故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范·迪克构想的平台化树(platformization tree)28一样:这棵“树”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根,通往由国际传播平台形成的树干,然后再分枝到枝繁叶茂的各个其他学科领域。树干中的国际传播平台仍然是平台力量的核心,是数字基础设施和各个学科之间、各个社会大众之间的中介。众多分枝则代表了各式各样的学科领域,比如中医药学、艺术学、体育学等等,它们与“树干”(国际传播)互相汲取养分,并刺激向上、向下和侧向的生长。
实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集中权威型模式(Authority)到分散枢纽型模式(Hub),有利于不同专业、学科开展复合型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形成因校制宜、因专业制宜、百花齐放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学科体系,有利于从根本上推进解决我国国际传播中结构性失语的难题。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大学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研究”(2023SYLZD010)前期研究成果。
相德宝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睿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司久岳、吕鸿、商旸:《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之路》,《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第23版。
②冯向东:《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7-71页。
③姬德强、杜学志:《平台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兼论媒体融合的外部效应》,《对外传播》2019年第5期,第13-15页。
④唐艾华、尚京华、路永民:《国际传播人才教育类型与阶段刍议》,《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55-157页。
⑤白国良:《对外报道随谈》,《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第47-48页。
⑥郭可:《国际新闻教育谈》,《新闻大学》1994年第2期,第62-63页。
⑦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当代传播》2010年第4期,第97-99页。
⑧黄勇:《广播学院增设国际新闻专业》,《新闻战线》1982年第8期,第44页。
⑨同⑥。
⑩同⑦。
11同⑥⑦。
12刘滢、姜飞、盛阳:《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探索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新模式》,《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8期,第45-47页。
13文秋芳:《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7-23页。
14钟新、崔灿、蒋贤成:《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多维度复合与进阶式培养: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十周年毕业生调查》,《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2期,第147-168页。
15高晓虹、冷爽、赵希婧:《守正创新:中国特色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中国编辑》2022年第7期,第4-9页。
16张恒军:《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传媒》2017年第11期,第76-78页。
17钱锦宇、郭淼:《全媒体时代人权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战略定位与可行性探索》,《人权法学》2022年第5期,第100-111页。
18同14。
19左小麟、廖圣清:《传承党媒红色基因 推进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培养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人才的探索与思考》,《传媒》2022年第5期,第16-18页。
20谢粤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策略》,《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1年第9期,第96-97页。
21孙吉胜:《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人民日报》2022年9月22日,第9版。
22张涛甫、姜华:《新传播技术革命催生“拟现实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5日,第13版。
23何塞·范·迪克、孙少晶、陶禹舟:《平台化逻辑与平台社会——对话前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主席何塞·范·迪克》,《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第49-59页。
24杨保军、李泓江:《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8期,第5-25页。
25庹继光、吕柠芯:《新闻职业共同体中学界功用探析》,《新闻界》2015年第20期,第48-52页。
26姜飞、张楠:《中国对外传播的三次浪潮(1978—2019)》,《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第39-58页。
27同23。
28Van Dijck. 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Visualizing Platform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3, no.9, 2021. pp. 2801-2819.
責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