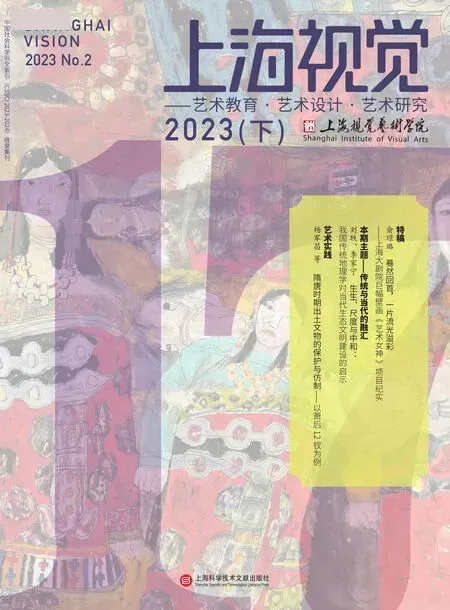生生、尺度与中和:我国传统地理学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刘轶 李家宁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 20162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200025)
我国传统地理学曾经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展现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奇异的魅力。自近现代以降,随着西方科技、文化及制度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或提倡“西体中用”,或提倡“中体西用”,其背后的逻辑实际都是以西学为出发点。在此大背景下,“渊源于西方的近代地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一元化,使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本土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大陆上几乎变成了‘绝学’,导致许多方面令人难以见到它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1]“此后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成就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牾的中国学术传统,包括地理思想在内,往往被蔑视,甚至斥之为‘迷信’”。[1]传统地理学不但学界乏人问津,在主流社会中也常遭嘲讽贬低,似乎以此态度方能证明“科学”与“进步”在这一时代的正当性和高尚性。但是,如果拨开“封建”“落后”“陈旧”“腐朽”“迷信”这些遮蔽在传统地理学之上的简单粗暴的标签,以客观、全面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地理学,便会发现它的诸多思想和方法至今依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传统地理学的概念厘定及相关问题
首先要明确的是,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地理”之名起始甚早。《周易·系辞上》就提及“地理”之名:“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此处依孔颖达之疏,“地理”的意思就是:“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此外,先秦经籍亦多记有“地理”之名。如《礼记·礼器》:“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管子·形势解》:“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不过,有学者认为“至汉代,以山川大地及其形态特点成为地理,才较为明确”。[2]如《淮南子·泰族训》:“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又如《汉书·郊祀志》:“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这都是以“地理”指山川大地。后来者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说:“人物咸沦,地理昭著。”也是这个意思。葛洪《抱朴子》说:“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也……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此“地理”的含义,则从最初的观察、勘探、研究大地山川之道,补增了人类采取某些措施和方法与大地山川进行交流、互动,从而获得超越客观世界的神秘的回应等意义。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它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地理学有什么不同?于希贤教授较早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做了较全面的回答。他认为,近代西方地理学这一学科体系兴起于欧洲,在19 世纪上半叶由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戴尔(Carl Ritter)奠定基础,然后逐步走向世界,慢慢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元化。它可以分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其中,自然地理又细分为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植被等;经济地理又细分为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地理、城市地理等;人文地理又分为文化地理、人口地理、政治地理、行为地理等。而中国传统(本土)地理学是指近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以前发生、发展于中国的地理学。他强调:“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个根本论点为:西方现代地理学传入我国是20 世纪20 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长达数千年间,中国自有一套地理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学术系统。以此作为观察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选择不同的人应当居住、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布置和创建自己的生活空间,处理生产和生活中的地理问题,选址布建人居环境,如国都、城市、村镇和宅居等等。这一套地理学的思维在中国萌芽、产生、形成、发展,行之有效地指导中国人认识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一套地理思维系统有自己的概念、术语、理论、方法,也建立了一些规律和法则。在中国乃至于在东亚的汉文化圈运用了几千年,解决了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从中创造出若干灿烂的地理科学成就。”并且,中国传统地理学与西方现代地理学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两套系统,“我们可以把西方地理学科学思想体系传入到中国之前的中国古代本土地理学称之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即如医学在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两套系统,中国的传统地理学就相当于医学中的中医系统。这一套地理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学科体系、学术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1]
从上述摘引中可以发现,于希贤教授所界定的中国传统地理学与西方近代地理学有着较大的不同,它有着自身较为明显的特征。我们可以从时间、思想、重点、效果、影响等几个维度,归纳出中国传统地理学独有的、区别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特点: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传统地理学是近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以前发生、发展于中国的地理学;从指导思想来看,中国传统地理学是如何处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来看,中国传统地理学是如何在客观的自然环境中,布置和创建自己的生活空间、处理生产和生活中的地理问题;从实践效果来看,中国传统地理学产生了一套独有的关于大地、自然、人类、社会等相互运行的思维模式,有自己的概念、术语、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些规律和法则,行之有效地指导中国人认识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影响来看,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化圈有着上千年的影响力,为这一区域的人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由此创造出若干灿烂的地理科学成就,等等。
由此可见,传统地理学与近代以来的地理学有着根本上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根本上的区别,与其说是对“地理”这一对象在认识上的不同,毋宁说是其背后文化、思想体系的不同。西方近现代地理学是冷静而客观地研究、分析“地理”这一对象及其有关的现象,背后充满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精神;中国传统地理学则将主观的情感注入到“地理”这一对象及其有关的现象之中,一方面关注这一对象及其有关的现象,另一方面更相信自己与这对象之间不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能在与它的互动中,获得超越客观世界的神秘的回应(“感应”)—这恰恰符合中国传统上“道始于情”的思想:这种回应既是“情”作用于“道”的本有之义,也是“道”呼应于“情”的自然体现。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其知识的本质属性,以地理术数(地理术)称之”。[3]那么,这种“知识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以为这种“知识属性”实则包含了诸多的内容,不但有今日之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知识,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植被、农业、交通、城市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是涵盖了礼仪、民俗、宗教等知识体系的复合体。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传统地理学则不应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机械的知识体系,而应看作是在这一复杂而复合的知识体系中,寻求“人”与“人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及人的价值体现。
二、传统地理学蕴含的生态智慧
在我国传统地理学中,蕴含着诸多富有价值的生态理念,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生生不息的生态哲学,顺时节用的生态道德,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中久经不衰的生态智慧,长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固然丰富多元,但“天人合一”是诸种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如钱穆先生就认为,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他指出:“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即是天人合一。”[4]儒家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是谈天时运行四季变化中体现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天人合一”;宋代张载则直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明代王阳明则把张载的意思稍作变化,讲“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讲在天、地、人、道、自然这一逻辑中呈现出的“天人合一”的关系。庄子说“与天为一”“人与天一”也是此意。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提倡“天地一旨,万物一观”,讲“青山是我身,流水为我命”“物不异我,我不异物”,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理念,集中体现了古典美学的本体论范畴和价值观理念,内蕴了万物生生不息、自由的诗性生态精神,不仅彰显出自然本体的‘元’‘始’整体话语,也体现出万物相互联系且‘太极化生’的人文景观”。[5]
在传统地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如《重校正地理新书》就明白无误地提出:“若宅兆,则有山岗胜负,三鉴覆临,六道抵向。三鉴者,天鉴、地鉴、人鉴也。六道者,天道、地道、人道、鬼道、死道、兵道是也。”[6]直接点明了“天人合一”在传统阳宅选择术中的核心地位。再如,《地理发微论》开篇就讲:“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邵氏曰:立地之道,刚柔尽之矣。故地理之要莫尚于刚柔。刚柔者,言乎其体质也……水则人身之血,故为太柔;火则人身之气,故为太刚;土则人身之肉,故为少柔;石则人身之骨,故为少刚。合水火土石而为地,犹合血气肉骨而为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二理也。”[7]又讲:“夫地理之与人事不远,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见。”[7]它在这里提出了宇宙生成和天人相类的观念,将宇宙生成与人的身体联系起来,亦即是汉代董仲舒的宇宙图示:天地通过与人及人类社会的相互感应而形成一体,强调了天地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性关系。清代范宜宾则提出:“夫地理之学……我所据之地足以承天,而天不隔我,则地与天交而为一,天地形气即合而为一,自然和谐。则所葬之骨,亦与天地之气为一,其福应之来,若机张括也。”[8]他在这里指明天地与人能够“合而为一”,能够“自然和谐”,人因此能获得吉福。
“生生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观念。很多学者对“生生”哲学已经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论述,如“梁漱溟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将孔子学术之要旨归结为‘生’”“方东美明确地将中国哲学精神概括为‘生生’,即‘生命的创生’,并认为一切艺术均来源于体贴生命之伟大”。[9]“生生”来源于《周易》,其核心就是对于宇宙万物和生命的创始和变化,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认为宇宙自有生机,即认为宇宙是由它自己的生机,生生不已地繁育而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外在的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二是认为万物皆有生命,即认为万物皆禀赋着宇宙之生机,皆具有生命之灵性,而不是静止状态的死物。”[10]西方地理学认为,无机界如大气、岩石、土壤、水圈等是没有生命的,只有有机界如生物圈等才是有生命的。但中国传统地理学背后是“生生不息”的生态哲学,它不仅认为生物圈有生命,而且在天地人等系统之间就是一个更大层面的生命体。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言,中国文化的宇宙观是将“自然人文合组为一个空间系统,从上有天、地、日、月延伸到人间,然后又深入到人体内部,建构一个四个层次的大网络……将广宇长宙看作一个各部分和各因素互动的秩序”。[11]如传为郭璞所作的《葬书》就特别指出:“葬者,乘生气也。”这实则就是从具体的微观地理环境来强调这种各部分和各因素互动的秩序,认为只有把握住这种规律或秩序,才能获得“生气”的庇护。传统地理学还强调要顺应这种“生生”,认为只有顺应了这种“生生”,才能与“天道”相呼应,然后才能获得吉福。例如传为黄帝所作的《黄帝宅经》说:“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是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这是把人的身体和天地万物的形态相对应,要求顺应“生生”规律,才会是“上吉”。
在中国传统地理学中,还蕴含着顺时节用的生态道德。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节用”和“顺时”的思想。“节用”是顾惜生态均衡,不肆意破坏自然的均衡发展;“顺时”则是不违背生态规律,要根据自然的趋势来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儒家反对过度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强调的是“节用爱人”,要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2]《孟子·梁惠王上》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认为人类应该按照天时季节安排生产劳动,不要违背时令;在进行生产劳动的时候,要注意节度、适宜,不能过度摄取自然资源。换而言之,这种顺时和节用即是李泽厚先生高度重视的中国哲学中的“度”的问题。“度,就是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人类是靠这个东西生存下去的”“我既不把黑格尔的‘有’,也不把‘质’,放在一位,而是把‘度’放在我哲学认识论的第一范畴”“中国上古极重音乐……它有各种不同的‘度’,它不仅使人际和谐,而且‘神人以和’,人与天地宇宙和谐一致,协同共在”[13],这都是在论述“度”的重要性。中国传统地理学对这种“尺度”的重视,正显示出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中顺时节用的生态道德观念。如《发微论》讲:“自有宇宙即有山川,数不加多,用不加少,必天生自然而后定,则天地之造化亦有限矣……截长补短,损高益下,莫不有当然之理。”[7]强调宇宙自然自有它的规律,人不能过多地进行干涉和掠夺,而是要顺着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合情合理的准则,实质就是一种“尺度”,就是在人与生态的关系之中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
中国传统地理学还提出了“中和共生”的生态理想。首先要看到,中国的“中和观”与西方的“和谐观”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照曾繁仁先生的意见:“这种中国古代的‘中和论’是迥异于西方古代‘和谐论’的。‘中和论’是一种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宇宙万物诞育运行理论。而‘和谐论’则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具体事物比例对称理论。”“中国古代‘中和论’思想是一种人生哲学,关涉到宇宙社会人生,以‘善’的追求为其目标……‘中和论’思想绵延5000 年,诞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14]其次,《中庸》讲“中和”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以为这里一方面讲“中”,就是讲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方面讲“和”,就是讲合乎自然及社会的规律,具有包容性和发展性,因此才能够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要求。再次,“中和”与“共生”是紧密不可分的。由于有着“中和”的恰到好处、包容发展,因而有万物的共生共荣,“中和”促进了“共生”,“共生”反过来丰富了“中和”。《乾·文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也正是描绘了人与万物中和共生的理想状态。在中国传统地理学中,“中和共生”既是一种完美的地理环境,也是一种环境与人相互成就的生态理想。它对此观念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强调地理和人的“有情”关系。在传统地理学看来,一个好的环境,不但自身优美、均衡,同时也会对人类表现出“有情有义”的状态。如《发微论》讲:“其向我者,必有周旋相与之意;其背我者,必有厌弃不顾之状……向者不难见,凡相对如君臣,相待如宾主,相亲相爱如兄弟骨肉,此皆向之情也;背者亦不难见,凡相视如仇敌,相抛如路人,相忌如嫉冤逆寇,此皆背之情也……故尝谓地理之要,不过山水向背而已矣。”[7]再如,《水龙经》讲:“大河类干龙之形,小河乃支龙之体。后有河兜,此即荣华之宅;前逢池沼,允为富贵之家。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前后萦回无破,财富田丰。地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15]又如,《地理人子须知》讲:“或左边朝山无情,或左山破碎之类,凡此则宜穴依于右,或向扦顾右,以避其凶而趍其有情吉美之山水;若右宫砂水有如此者,则穴宜扦依左,或向扦顾左,以就左边山水有情美好者。”[16]这都是讲环境和人的“情义”问题。看得出在传统地理学中,人们自觉地把环境人格化,让环境有了“人”的主体性。在这种人与人化的环境“中和共生”“有情有义”的关系中,不但表现了人对生态环境的充分尊重,也表现出人对生态理想的自觉追求。
三、传统地理学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首先,当代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大工业时代以来,西方以人类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生态观,多从合乎于人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自然生态,并不把人之外的自然生态作为值得尊重和保护的对象。直到进入20 世纪,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并意识到造成这种危害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工业科技使用上的问题,其后还有着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和信仰问题,是人类把自然生态当作工具、视自然生态从属于人类社会的逻辑结果。重建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形成“人与自然在‘人-自然’复合整体层面的平等与统一……并将自然界的生命、有机物和无机物都纳入‘大地’的宏大领域,思想崭新的‘生命共同体’景观”。[17]毋庸置疑,在这一方面,传统地理学其实已经给予了我们相当多的启示,尽管它显示出的这种“平等与统一”的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还是不自觉的和幼稚的,但它在实践中已经探索、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其次,传统地理学中的中和观、生生观、节用观,给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发。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是探索和创新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平衡问题。因为没有人类活动的自然生态,就没有所谓的“文明”可言;而仅仅重视人类的文明,则又回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因此,如何在实践之中既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又不违背生态的发展规律,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传统地理学的经验来看,节制人对自然的索取欲求、对自然的生机(包括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予以共情、根据自然的规律安排人的生产活动等等,以此来建构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均衡性,努力实现一种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物我一体的生态理想,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有效回答。
再有,在传统地理学看来,保护生态的目的不仅是让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均衡发展,更是让人类自身能由此达到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在此世界中得以诗意地栖居。古人曾经充满诗意地讲:“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18]人在青山绿水之间,不但沉浸在自然风光之中得到愉悦的心境,更在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一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从这种充满感情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它表达了古人对生态文明的某种理想;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地理学蕴含的生态观不仅仅是“生态的”,更是“文明的”;不仅仅是“自然的”,更是“心灵的”。另外,它也提醒了我们:人类如何对待生态,实质也就是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生命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