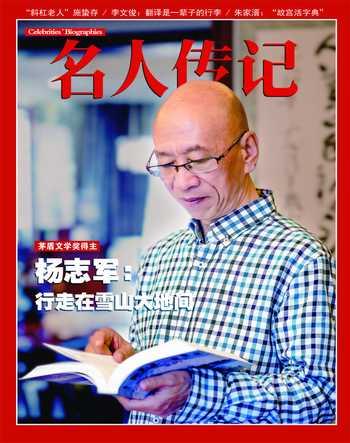陆晶清与王礼锡:抗日烽火中的诗坛伉俪
段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在中国大地迅速蔓延。远在欧洲,一对夫妇的身影奔走在抗日援华战线上。被迫流亡的几年里,祖国的命运时时牵动着他们的心。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再次携起手来,创办报纸,募集款项,以笔为枪,为抗战呼号。
丈夫叫王礼锡,以诗文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东方的雪莱”;妻子陆晶清,是李大钊和鲁迅的高足、石评梅的挚友,曾是“五四”新文学星空下的一颗璀璨之星。因为诗,他们结缘;因为共同的革命信仰,他们珠联璧合。
是诗人,是作家,更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在中国文学史和反法西斯的历史上,他们写下了自己的热血诗行。
小女敢言志,立志奔前程
遇到王礼锡之前,陆晶清的人生充满悲苦。她是白族人,1901年1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的一个古玩商人家庭,原名秀珍。因父亲喜好古诗和历史,四五岁时,她便跟着父亲背诗。父亲有丰富的想象力,能把诗讲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或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她听得心驰神往。
辛亥革命后,女子教育蓬勃发展。十几岁时,陆晶清考入云南女子初级师范学校,身形纤小的她,鬓绾双髻,每日提着布书袋走读。教国文的老师古典诗词造诣颇高,这更加激发了她对诗词的兴趣。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读到胡适的新诗和鲁迅的小说时,她“全身被活跃的思想和力量所占据”,对新诗开始热衷起来。
陆晶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量进步刊物,对旧礼教、旧道德,她骄傲地蔑视着。当“五四”的风吹到西南边陲时,她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积极参与到云南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对父亲提出的“毕业后在本地做一名小学教员”的要求,她断然拒绝:“小女敢言志,狂诞孔仲惊。木兰御外侮,红玉抗金兵。清照词千古,班昭史有名。我岂甘落后,立志奔前程。”
1922年秋天,陆晶清以西南女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意气风发时,她的人生突遭变故——母亲因长期疾病缠身,不堪忍受,选择了自杀。
从此,陆晶清“跳出了幸福篮”,内心“蕴藏着辛辣的悲剧”。泪别父亲和幼弟,由一家旧式旅行社“包运”,她由昆明北上。初到北京那晚,在新月繁星下,她初识了北京的美。负重晚归的骆驼,小胡同中清脆的梆声,都是诗,都是画。满目都是新奇。后来,她这样形容:“那时我真是一个由僻乡进城的‘乡大姐。”
新的人生即将开启,满怀着向往,她不仅将名字“秀珍”改为“晶清”,还把出生年份说成1907年。多年后,她不无得意:“那时我把年龄往后推几年,感觉自己心灵年轻点。”
学校名师云集,一切都令人鼓舞。可是,新鲜感过后,便是孤寂。远离家乡,人地两疏,因为想家,陆晶清“愁苦到万分”。除了上课,她总是偷偷地躲起来哭,靠念诗、写诗排遣烦闷。
那时,李大钊教哲学,周作人讲欧洲文学史,后来,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也受邀来上课,每每听讲,陆晶清都受益匪浅。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她才气尽显,笔下的“青灯”“寒月”“落花”清澈凛冽,自成一格,其新诗开始在《语丝》等刊物上发表。
更令她欣喜的是,她收获了友谊,石评梅、庐隐、许广平、刘和珍都成为她要好的朋友,她们亲昵地称她“小鹿”。在校舍“红楼”,她们互相鼓励,齐头并进,课外,还经常相约到鲁迅居住的“老虎尾巴”去“吃小灶”。
有了朋友们的陪伴,陆晶清渐渐活跃起来。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她和好友许广平、刘和珍奋起反抗校长杨荫榆的奴化教育;和石评梅共同编辑《妇女周刊》,以犀利的笔触抨击黑暗的社会势力。在给鲁迅的信中,许广平以赞许的口吻说:“晶清虽则自己未能有等身的著作,除新诗外,学理之文和写情的小说,似乎俱非性之所近,但她交游广,四处供献材料者多,所以《妇周》居然支持了这些期。”
然而就在母校风雨飘摇之时,云南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那个暮春的傍晚,见到“父逝速回”四个字,陆晶清惨叫一声便昏厥过去。家中只有弱弟和继母,满怀悲痛,她南下奔丧。再回来时,学校已经解散了。
命运没有怜惜她,紧接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她亲眼看到好友刘和珍倒在血泊之中。那些日子,只有泪,只有恨,只有凄怆。
在一处破败的房子里,陆晶清和石评梅相依为命,她们将屋子用绿纸裱糊,再摆上几盆花草,谓之“绿屋”。在“绿屋”里,她们一起哭悼刘和珍,一起撰写《梅花小鹿》的集子,一起编辑《世界日报》副刊。她们约定,要“相伴着,相慰着,走完崎岖的生之旅途”。
因从小敬仰孙中山,受“救国救民”思想的影响,陆晶清加入了国民党。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她决意投入革命的洪流。在《出征》一诗中,她斗志昂扬:“从今后,荷枪实弹作个长征人,只拼着这一腔热血前去冲锋杀阵。”
1927年,受李大钊委托,陆晶清去武汉送一份文件给当时的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武汉,她协助邓颖超编辑刊物,创办学校和贫民医院,忙碌中,伤痛渐渐远离。可是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因营救一位共产党员的妻子,她被列入“准共”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抓捕。无奈之下,她踏上了漂泊之路。此时给她安慰的,仍是石评梅,在一封封信件里,她们靠文字取暖。
1928年秋天,残酷的命运再次降临,在上海,陆晶清接到了石评梅的死讯。那一刻,犹如有一把利刃骤然插入心房,她“伤极了,昏惘了”,只有痛哭!忍住淚水,她登上北上的轮船。愁云惨月下,她回忆着“红楼”和“绿屋”中的种种往事,酒醉醒来,忍不住悲呼:“绮宴散了,人影逝了,只天际孤雁在哀鸣……”
所有的散碎篇章,无一不流露出凄婉。人生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拯救她的人出现了。
在诗的生活中,爱成长起来
回到北平后,陆晶清一边处理石评梅的后事,一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回炉深造”,兼任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她的内心仍然是苦闷的,而这苦闷,只能在笔下倾诉:“归来了,我依然血迹斑斑带着沉重创伤。心境是凄怆,胜利的旗帜只在远处微笑、飘荡……”
爱她护她的“梅姐”舍她而逝,蘸着眼泪,她写下一篇篇怀念之作。
一个冬日,陆晶清正在报社当班,这时,有人来送稿件,是这人自己的诗作,上面的署名是“王礼锡”。简单寒暄过后,陆晶清接过稿件。面前的青年穿长衫,戴礼帽,温文尔雅,黑框眼镜背后,一双眼睛透着友善与真诚。
交谈后两人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王礼锡童年丧父,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后来去南昌心远大学旁听,得到名师指导,诗文素养极高。再后来,他做过教师,当过报社记者,主编过《青年呼声》《新时代》等进步刊物,参加革命后,还担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1928年,他来到北京教书,一边带领学生参加工人运动,一边在业余时间用诗歌描摹时代。
窗外,暮色已四合,他们却浑然忘我,彼此相见恨晚。
此后,王礼锡便经常来找陆晶清,既谈诗,也谈革命。陆晶清的编辑室,四壁裱糊得像草一样绿,电灯罩则红得像一团火,这青春的环境成为王礼锡“恢复疲劳的处所”,而陆晶清也会在忙完工作之后,借故拖延时间等候他的到来。
那时,王礼锡正在编写《物观文学史丛书》,陆晶清被吸引,他写《李长吉评传》时,她开始撰写《唐代女诗人》。后来,这本小书出版,为女性文学研究填补了空白。
“物观文学史丛稿,本来是我一人唱独脚戏,而今成为我与晶清两人的合奏曲了。”对坐在破方桌的两旁,他们一写就是半天,在研讨与切磋中,心灵越来越默契。编辑室的窗上、壁上,貼满了王礼锡写的诗句;漫步清华园中,面对一派肃杀,他们触景生情,即兴唱和;短暂别离时,又在诗中写尽缱绻与怅惘。
友情升华为爱情,甜蜜驱散了忧伤,陆晶清不再哀怨,笔调变得绮丽奔放。在《沉醉的一晚》中,她记录了一次对饮后的情景:“妆台上的桃花分外妖慵,眯着眼窃笑我双腮泛红。他的醉态惺忪,醉眼朦胧,像是进了魔宫,入了幻梦!这纵然是个梦,梦也新鲜,但愿,浸在这梦里年复年。花影已由西边移到东边,月儿是何时悄渡过中天?”
她的诗中,有了温馨与缠绵,《低诉》中的诗句像波浪一样在王礼锡的心上翻腾:“这是一首迷人的诗,这是一首动心的诗,至少是我已尝到这诗篇的迷人的滋味,至少是我的心被它打动了,不,是正在骚动的心被骚动得更利害了!”
那段时间,王礼锡用真情挚语写下几十首表达爱的诗歌,后来全部收录在《风怀集》中。
“我们的诗与爱就在这诗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了。”在《市声草》中,王礼锡这样回忆“在很忙碌而枯燥的生活中,每天晚上总有一两小时沉醉于晶清的编辑室里红色灯光的温波里的清谈。最初仅仅是清谈而已,借这微温的清谈来润泽这沙漠中的旅行者的心。而狡狯的爱神就悄悄地一天天窜进我们的清谈生活中,好象茑萝在墙上攀援,不知道几时就滋蔓满墙了。”
然而,他已有妻有子。王礼锡出身于清末一个官宦家庭,早早就被安排了一桩封建婚姻,二十七岁的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王礼锡的坦诚换来了陆晶清的理解。作为婚姻自由的倡导者,她无惧世俗的藩篱。挚友石评梅的爱情悲剧让她痛恨封建礼教,更何况,好友庐隐的婚姻、恩师鲁迅的婚姻,无不是冲破桎梏才走到一起的。当王礼锡妥善处理好家事后,她接受了他。
因多次组织示威游行,王礼锡的住所受到监视,门缝里多次被塞进恐吓信。为了安全,应爱国将领陈铭枢之邀,他前往上海,出任神州国光社总编辑。
1930年冬天,王礼锡前往日本办事,几个月后,陆晶清也来到东京。在一间小出租屋里,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因身高悬殊,有贺客在婚礼上起哄:“快给新娘子搬个梯子来!”
享受着新的生命之宴,王礼锡的诗句里满含喜悦:“雾开新月眉初舒,盖地青毡春渐苏。山半小楼客意艳,一灯浓酒醉红炉。”
纵然前路仍有坎坷,但从此,他们有了生死相依的伴侣。
“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
蜜月里,带着新奇感,陆晶清感受着日本的社会和人情。然而,她是失望的,“上野的樱花真不及北平中山公园的榆叶梅,她没有榆叶梅那样娇艳的姿色,也及不上我们‘红楼内的几株梨花”;对于男女同浴,“赤诚相见”,她更是难堪不已。在她的内心,祖国无可比拟。
异国的境遇和体验触发了陆晶清和王礼锡关于中国社会的思考,一回到上海,他们就携手创办了《读书杂志》,邀请各界人士在这个园地展开论争。陈独秀等人纷纷参与,他们对中国社会史的讨论一度引发震动。随着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的相继爆发,他们又推出专刊,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
“是你转变了我固有的许多僻性,是你把我从‘游戏人间的惰性中拯救出来。”在王礼锡的影响下,陆晶清跳出个人情感的小圈子,把目光投得更远。他们一起组稿,一起连夜推进杂志下厂印刷,《读书杂志》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情感也越来越浓烈。
没想到,因为讨论敏感问题,杂志被当局没收。面对查禁,陆晶清大声疾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猪被杀也要叫几声,我们被杀,连叫几声的权利都没有,成何世道?”
像个战士一样,在何香凝领导下,她冒着炮火上前线慰问将士,救护伤员。在给弟弟的信中,她豪迈地说:“关于我们的生命请你不要过虑!因为我们自己并不重视,在昨夜今日的血战中不知牺牲了多少忠勇的战士,被难的同胞的尸骸埋葬在火光弹雨下的也不知有多少为了争国家民族的生存,他们能牺牲,我们也一样的可以赴死,死在手刃敌人的血泊中,是多么的悲壮呵!”
在共同的战斗中,王礼锡始终和她肩并肩,他不断撰文批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出版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和左翼文艺作品。其鲜明的立场惹恼了当局,他上了“黑名单”,以“出洋考察”为名被“限期出国”。
1933年,陆晶清随王礼锡远赴欧洲,踏上了长达五年的流亡之路。
在伦敦,他们蜗居一隅,以卖文为生。“一室兼食宿书房之用,食物与鼠子共之。”在鼠患成灾的环境下,王礼锡作诗遣愁:“老子一生五千言,蝇头自笑日五千。凄惶竭作成何用?入市难酬乳酪钱。”
即使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五千字,低廉的稿酬也仅够几杯牛奶的钱。唯有爱,能抵挡愁苦和劳累,有陆晶清的陪伴,王礼锡骄傲地说:“天天过的是蜜月生活。”因诗作在欧洲颇受欢迎,“东方的雪莱”响亮一时。
煮字疗饥之余,他们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在世界和平大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上,王礼锡的声音振聋发聩:“不抵抗不是和平,乃是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听到日军进攻北平的消息,犹如一个霹雳瞬间在头上炸响。陆晶清和王礼锡放弃写作计划,联合友人筹资创办《抗战日报》,发起成立援华会,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仅在英伦三岛,他们的演讲就多达数百次,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洪流中,那执手相依的身影如浪花般奔腾着,一路向前。
城市一个个沦陷,守在收音机前,陆晶清心急如焚。她为延安捐钱捐物,并致信邓颖超:
邓大姐:
武汉分袂以来,弹指十有余载。二十年代前期,我在北京女师大,受到恩师李大钊、鲁迅先生的培养教育,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二十年代后期在武汉妇女部,受到领导何先生与邓大姐的关怀指导,增强了革命的意志。三十年代初来到欧洲,投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洪流。
七七事变以来,更加努力投入抗日援华工作。现在我国不少城市已沦陷,而延安却岿然不动,不断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为了表达我个人对延安军民的崇高敬意,特将我个人的一些稿费与饰物,捐献给延安抗日军民,竭尽个人绵薄,聊表全民抗日之微忱……
1938年10月,一封信件远渡重洋落在案头,这封信是郭沫若和老舍联名写来的:“礼锡兄、晶清嫂:你俩在欧洲为抗日援华做了大量工作,贡献良多,有口皆碑。现抗战已进入最艰巨階段,兹代表全国文协热烈欢迎你俩返国,共纾国难。”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针对他们的通缉令被撤销,二人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抗日。临行前,在和朋友们的告别会上,王礼锡朗诵了他新写的诗歌《别了,英国的朋友们!》:“我去了/我去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他语调中的苍凉与悲怆,闻者动容。时任驻英大使郭泰祺说:“这样感动人的诗句,可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古今中外所闻所见不多。”一位英国女诗人也动情地说:“我是含着骄傲的热泪听它的,读它的,撼人心魄。”
异邦五年,诗文就是王礼锡和陆晶清的武器,是他们的“百万雄兵”。
“执着火把狂奔”
1939年初,夫妇二人抵达重庆,王礼锡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国民外交协会常务理事,被委任为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
不久,作家战地访问团成立,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推荐下,王礼锡担任团长,他将带领这支“笔部队”去前线搜集材料,真实记录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以便“供给无数的现在及未来的诗人、小说、戏剧、散文家,让他们去歌颂,去记述,去表演”。
在日记里,王礼锡写道:“残酷的仇人啊,是谁使得我对母亲不能尽为儿子的责任,对妻子不能尽为丈夫的责任,对儿子不能尽为父亲的责任,无论是为家,为国,为世界人类,我们只有牺牲一切反抗侵略者。”
为了取得南北方战场的全面资料,王礼锡把陆晶清分到南路,自己则随北路出发。他叮嘱她,一定要每天写日记。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重庆一别,竟成永诀。
兵分两路后,他们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两个月后,陆晶清已经写下了六万多字的战场记录。遥望北方,她期待着与王礼锡的胜利团聚。
与此同时,王礼锡也一路走一路写《笔征日记》。尽管条件恶劣,几次遇险,但他始终充满激情。在洛阳,他与老舍重逢。在老舍眼里,“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病容,还是那么胖,那么精神,那么和蔼,嘴角上老微笑着”。
然而,长期沐雨栉风,王礼锡积劳成疾,于中条山战地访问期间,一病不起。数日后,在去医院的途中,因一位特派的勤务员给他服错了药,王礼锡猝然离世,年仅三十八岁。他的死因被诊断为黄疸病,而在他留下的箱子里,三封恐吓信赫然入目,上边说,如果“不悬崖勒马”,就让他“有去无还”。
一周后,远在浙江金华的陆晶清收到了噩耗,她一路恸哭着回到了重庆。后来,她在悼念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凄惨:“锡!请想想这晴空霹雳会把我震到怎样地步!我仿佛从高山绝顶跌落到万丈深渊底,我仿佛中了重磅炸弹,全身都化作了飞灰!……我本不信命运,命运这魔鬼却不断戏谑我。我纵然是铁汉,也难承受这样残酷的打击。”
他是知己、导师,是理想的情人和丈夫。他逝去了,她的世界只余下一个“空”。可是,他的老母、幼子需要照顾,他的遗稿需要整理,侵略者的脚步还肆无忌惮地踏在祖国大地上,她唯有坚强起来,“执着火把狂奔”。
1939年10月8日,在王礼锡去世百天之时,陆晶清写下《给礼锡》,刊发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你的声音犹在我耳边,你的笑貌犹在我眼前,到今朝,我们别离了才整一百天——‘死,已把我们分割开人间、黄泉!……日月有时灭,我们的爱不终。海可枯石可烂,此恨啊无穷!”
她把悲痛埋在心底,一边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一边在中学任教,同时主编《扫荡报》(后更名为《和平日报》)副刊。同事评价说:“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妇人,虽然长得特别矮小,头脑灵活得很。她的谈吐与她的新诗一样,充满机智。讨论问题,每能切中事理,兴致高的时候讲几句幽默话,总会引得大家笑不可抑。”
夫妻八年,王礼锡对革命的坚定乐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陆晶清,她早已不再是那个笔下只有哀怨的小女子。后来,她以《和平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再度赴欧,以如椽之笔采写了许多重大事件。故地重游,她仿佛又听到了王礼锡在为抗战呐喊,仿佛又看到了他们在斗室里伏案合写《望乡情》时身边有硕鼠自由穿行。
新中国成立后,陆晶清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古典文学,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她没能幸免。厄运中,她不断告诉自己:“人生有泪不轻流,要坚强。”
那十年,她的两大箱资料,包括在战时前线写的日记,被付之一炬。唯一欣慰的是,王礼锡的《笔征日记》手稿被她藏在臭不可闻的咸菜缸底,最终躲过一劫,成为珍贵的抗战史料。
晚年,陆晶清深居简出。尽管眼疾严重,视力模糊,但她仍然坚持整理王礼锡的遗稿,对他的每一首诗作,她都能背诵如流。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各种质地的小鹿,“小鹿”,是王礼锡最喜欢的爱称。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冬日,他和阳光一起闯进她的生命里。
“努力使你的精神永在”,灵前致祭的誓言,她始终牢记着。古稀之年时,她仍笔耕不辍,连续撰写了《在何香凝身边》《鲁迅先生在女师大》等多篇回忆文章。
1993年,陆晶清走完了坎坷而传奇的一生,而她和王礼锡的诗与爱,将永恒地留在这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