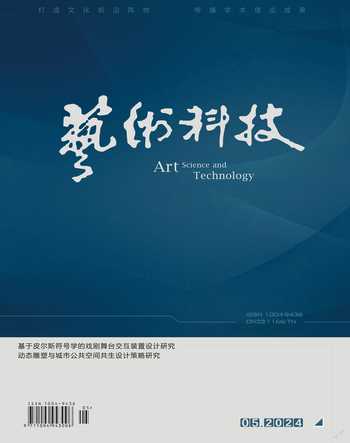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策略
摘要:目的:当下,直面时代变迁、关注社会边缘群体、满足观众情感需求成为现实主义电影须实现的目标。温暖现实主义理念的提出有效回应了时代召唤,相关电影大量出现,但如何实现作者性与类型化的有效缝合成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困境。新生代导演领军人物文牧野成功突围,其导演的《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两部影片均获得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佳绩。文章以其电影为例,重点分析类型化叙事手法下导演自我美学体系的构建,研究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类型化叙事如何实现作者论视野下主题倾向与理性克制的平衡,实现电影叙事策略的美学升级。方法:文章从美学特征、自我美学体系、主体倾向与理性克制三方面入手,对其导演电影进行探究。结果:导演继承了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传统,作品呈现出极强的现实感,表达了对边缘群体的现实观照。其一方面赓续戏剧性类型的叙事策略,在戏剧化冲突中呈现社会现实、抚慰焦虑;另一方面通过以喜写悲的叙事调性演变和动态叙事空间转变,完成自我美学体系的建构与作者性的艺术表达。此外,导演始终保持客观的叙述态度、克制个性的影像呈现,以达成創作者主体倾向与理性克制的二元平衡,完成社会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结论:文牧野以多维度革新姿态表现出类型化与作者性在现实主义题材中对立调和的可能性,体现出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创作自觉,为我国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树立了美学范式。
关键词: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文牧野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5-0-03
目前,以满足观众娱乐需求从而达到情感纾解为终极愿景的影片主宰市场,观众渴望电影发挥补偿与疗伤的作用。温暖现实主义理念[1]的提出有效回应了新时期观众的呼唤,彰显了人文情怀,体现了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影片情感与精神的传承,以及以反映时代内核为支点的创新性传承。
然而在中国市场掀起一股创作热潮之后,如何实现作者性与类型化的有效缝合成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困境。新生代导演文牧野“用类型片的讲述方式去讲一个相对作者性的内核”[2],其电影《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在商业类型与艺术个性的制衡中成功突围,以边缘化视角展现两个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永不言弃、不断追求幸福的强大信念,将温暖贯穿始终并使其成为人物的终极救赎方向。
1 文牧野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
“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本体概念继承于现实主义美学,主要包括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等。”[3]文牧野导演的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在继承了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传统的同时,又完成了对新视野的开拓,结合时代需求,努力寻求能够与当下受众有效交流的方式,积极调动受众的情感,促使他们从自我关怀走向他者关怀。
1.1 对边缘群体的现实观照
客观真实呈现底层生活是现实主义电影的第一要义,也是文牧野电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文牧野导演的两部长片讲述了底层人物于阵痛中坚强地追求幸福,于生活中不断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同时导演也完成了对新价值判断的阐释,即边缘群体不等于弱势群体也未必弱势。
《我不是药神》根据时事新闻改编,讲述了程勇沉沦物欲惊醒后的人性激活与自我救赎的弧线转变。影片中社会底层人物被揭开的现实伤疤与叙事主题呈现的人性力量戳中众多观众内心,引发其情感共鸣。《奇迹·笨小孩》拆解城市底层,以刻画底层众生相来观照现实,以描摹景浩兄妹及其团队面对生活考验的精神力量来激励大众,使其燃起斗志与希望去追求美好生活。
“我们可以将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4]文牧野导演在洞察生活本真后,以现实主义笔触阐述自身的真知灼见。通过对社会底层群体生存现状的真实再现,直击人性善恶,打破大众对底层的刻板印象,彰显卑微人物战胜苦难的强大人性力量,于人物抗争与救赎中启发观众深入思考相关社会问题。
1.2 彰显现实感的影像类型
尽可能再现与还原现实,一直是许多导演渴望达成的视觉创作目标。在置景上,无论是位于狭隘巷子的简陋门店内的各种印度神像、手里攥烟且胡子拉碴的颓废中年男子、墙上暴露的美女照片以及在印度的游客照,还是满墙的儿童蜡笔画与识字帖、生锈铁床、褪色的工作服、街弄随意晾晒的被褥、朴素的棕色凉拖与起皱的牛仔中裤,都最大限度展现了上海与深圳地缘性的时代感,同时交代了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处境,于细微之处体现真实生活质感。
在拍摄上,采用晃动式带有自然感的手持摄影。摇晃镜头更贴近真人视点,镜头本身未介入演员表演,毫无保留地呈现摄影机所能窥探到的一切东西,凸显出导演纪实性展现真实世界、直面真实的意图,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此外,跟拍的手持镜头具有代入感,能使观众不自觉地参与到跌宕起伏的叙述情节与情绪变奏中,更易引发观众共鸣。
色彩是电影中的重要元素,有强烈的情绪性,诉诸的不是意识和知性,而是表现性和气氛。两部影片虽前后部分影调相差较大,转折处冷暖的两极变化推动了剧情发展,但究其整体情感性表达,还是以带有能量感的亮色调为主,以温情基调歌颂希望与生命,激励奋斗者不断创造更多可能,永不言弃地追求幸福与美好生活。
2 类型化文本演绎下的自我美学体系构建
中国不缺现实题材,缺的是类型化的现实题材。文牧野导演通过对类型叙事公式的工整运用,以类型片的外壳阐述作者论视野下底层如何拯救个体命运,将个性与共性、艺术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完成了自我美学体系的建构。
2.1 戏剧性类型叙事策略的赓续
“金羊毛夺宝团队”模式的采用体现了导演类型化叙事的策略。无论神药小队还是奇迹小队,成员虽身份、性格与处境各不相同,但都以情感为中介构建起统一向上的精神导向与行为动机,统摄成为全景式呈现时代底层命运的集体镜像。导演以温暖的笔触歌颂了各司其职的典型符号式角色乐观积极的精神品质,在揭示生活真谛的同时传递温情,也为底层个体命运的改变提供了现实且可靠的捷径。
此外,导演以亟须处理的经济危机作为主人公的驱动力,以医疗业与手机制造业的微小触点揭露隐藏于当今金字塔式社会阶层下的边缘层困境,引发观众深思。其点线面叙事逻辑也同样展现了文牧野在赓续类型电影叙事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现实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其在戏剧化冲突中更为写实地呈现社会现实、抚慰焦虑,达成创作主体类型诉求和现实关切的圆融与自洽。
2.2 作者论视野下艺术表达的探赜
客观来说,当下导演掌握着电影整体风格与艺术表达的主导权。文牧野在迎合大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召唤的同时,采用独特创作策略,展现出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
其一,以喜写悲的叙事技巧与影片主题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于叙事调性演变中指向时代变迁下社会所忽视的裂痕。“底层悲喜剧不仅是底层叙事的亚类型书写与情感策略,而更应作为呈现社会现实复杂性的方式。”[5]如《我不是药神》里程勇、吕受益二人在欢快音乐中开启购药之旅,其中程勇与印度轮渡商操持各色语言鸡同鸭讲的桥段实在引人发笑。在喜剧因子的加持下,事情似乎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不仅让病患吕受益的绝望与沉重得到了合宜的缓解,也讓观众暂时放下了对饱受疾病折磨的人物的担忧。然而隐藏在叙事背后的冷酷事实于笑声消退后,以摧枯拉朽之势重返银幕。又如《奇迹·笨小孩》里汪春梅愤怒于省吃俭用为儿子购买的助听器被砸碎而拿起斧子大喊:“老子砍死你们!”这一情节使叙事基调由悲转喜,将暴力打斗喜剧化,将观众从沉郁氛围中拉出。但如导演所言,镜头始终指向小人物的无奈与困境。类型元素已然盖过个体苦难,真实展现工厂劳保措施不到位的社会问题。
其二,电影创作者对空间的多层面感知及其对电影空间的独特处理和表现,最终指向的是广阔深蕴的文化空间[6]。《奇迹·笨小孩》以多重的动态空间转变展开叙事,角色在空间中不断争夺话语权,终极指向依旧是倡导人文关怀的社会主流文化。出租屋内的兄妹二人为解决食不果腹之常态跳脱家庭空间转向城市空间谋生。城市的AB面推动主角突破既有的群体划分,在厂房的小社会空间里创造自己的乌托邦,最终跻身金字塔高层的城市空间。底层人物瓦解权力空间构型,夺得被长久压制的时代话语权。影片于动态隐喻空间下赤裸地讽刺城市褶皱处被遮蔽的权力秩序,精准触达“直面苦难,永不放弃追求幸福”的积极社会主题,向大众传达了温暖向上的地缘文化精神与主流价值观。
3 主体倾向性与理性克制的二元平衡
横向比较国内外现实主义影视作品,会发现其创作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影片总会不经意流露导演想要表现的立场或态度。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既满足大众审美需求与表达社会关怀,又兼顾创作者的自我表达,游刃有余地平衡作者性与类型化,成为当今电影创作者乃至电影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文牧野娴熟处理个性表达与社会性呈现、商业化与类型化的关系,取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佳绩,其成功之处正是恰当把握主体倾向性与理性克制[7]。
3.1 客观叙述
导演始终保持客观的叙述态度。虽与第六代导演一样,主观上倾向于展现现实主义题材,以底层视角窥探大时代,但也注重克制表达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一方面,导演从底层生活小切面入手,揭示褪去光鲜外表后的社会伤疤与隐蔽于动态空间内外的阶层与话语权,但不作过多批判,而是温和、积极地引导,最后将这种时代症结的处理权交付给观众。
另一方面,无论角色身处何种困境,始终展现温暖的基调。《我不是药神》中,程勇最终锒铛入狱,街道两旁围满自发前来送别的病患。镜头来回切换,病友深情且带有尊重崇敬之情的目光犹如一束光照亮了阴暗的押送车,温暖了主角,更感动了全体观众。景浩无法支付房费而被赶出门外,敬老院热心护工梁永成夫妇伸出援助之手,暂时提供了住所。
3.2 克制的个性化影像风格
导演会刻意克制个性化的影像风格。一般而言,运用手持摄影往往倾向于表达某种主观意愿,但导演选择消解作者性,不刻意追求精致画面和拍摄角度以及工整构图,而是使摄影机自然地参与叙事。他让镜头跟着演员一起呼吸,捕捉演员所有的情绪。《我不是药神》里众人因被查购买印度仿制药而被抓进警察局,老奶奶与警察对话,手持镜头以曹斌主观视角“俯视”这个无助的老人。导演试图将观众放到与执法者同等的位置,引导观众深入思考法与情。
另一方面,为使观众不出戏,导演选择重点展现演员表演,突出故事主体,甚至要求摄影师在有限空间内自行寻找立足点,在空隙中捕捉表演细节。程勇与吕受益于医院门口售药时,摄影机只进行普通的放大与缩进,以旁观视角展现主角启程售卖仿制药受挫的经历。少量的奇观化场面也仅是为了呈现时代变迁下现代化的地缘风貌,如深圳大都市景观。
4 结语
对囿于社会现实的边缘人群表达人文关怀,成为当下电影亟待演绎的主题。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出现不仅响应了时代召唤,还以有限的生活半径为切入点,直面文化症候,书写普通人的命运变迁。文牧野导演作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者的阶段性代表,继承现实主义电影观照现实与尽可能还原现实的美学传统,以多维度革新姿态推动电影工业的美学探索,实现了作者性与类型化的完美结合,达成了创作主体与观众的深度情感共鸣,也为我国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树立了美学范式。
参考文献:
[1] 胡智锋.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现实[N].光明日报,2022-03-30(015).
[2] 文牧野,谢阳.自我美学体系的影像化建构:《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1):61-69.
[3] 贾冀川.现实主义电影的困境与出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3(4):162-163.
[4] 刘坛茹,王文敏.当代中国底层电影的寻找叙事研究[J].当代文坛,2011(4):144-147.
[5] 刘思齐,李春雷.底层“悲喜剧”电影的叙事逻辑研究[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21(5):54-58,63.
[6] 海阔,罗钥屾.电影叙事空间文化研究范式[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2):67-72.
[7] 王坤,曹颖.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源流与艺术嬗变[J].电影文学,2023(23):63-68.
作者简介:周茜(2000—),女,江苏常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