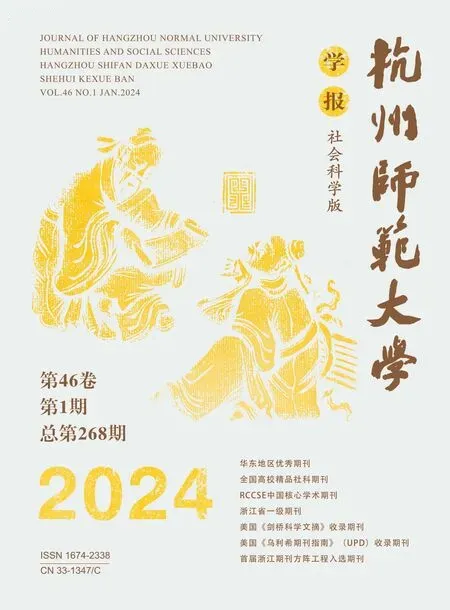佩特的审美批评原理
王柯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维多利亚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1839—1894),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始作俑者。在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立场时,佩特看似着力强调艺术与各种形式的美所给人的快乐享受,实则着力追求艺术化人生的审美趣味与理想价值。尤其在目的论意义上,佩特十分看重艺术与人生的互动融通关系,一再强调艺术对人生质量的催化与优化作用,不惮其烦地鼓励和引导人们在追求光彩瞬间的艺术欣赏过程中,尽力提升各自的艺术鉴赏力与审美敏感性,力求实现艺术化人生的终极目的。
为此,佩特身体力行,通过自己对艺术鉴赏和审美批评的实践活动,为读者提供某种可资借鉴和具有实效的参照模式。那么,在关乎艺术的审美批评方面,佩特在相关原理与运作实践领域,到底有何独到之处?有何值得重视的论说?本文试从佩特推崇的审美批评具体化原理出发,结合其对文艺复兴艺术、希腊雕刻艺术与柏拉图美学思想的解析,尝试彰显佩特作为古典艺术批评家的特殊视野与阐释效度,同时说明佩特如何从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汲取“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根源与理论支撑。
一、审美批评的具体化
佩特在《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Renaissance:StudiesinArtandPoetry)和《鉴赏集》(Appreciations)等著述中,一直关注艺术与诗歌之美,但对美的抽象定义或普遍使用的公式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类定义或公式,虽然费尽心力,言之凿凿,但对鉴赏艺术与诗歌的精华而言,其启发性与助益性则令人失望。他就此断言:
美,如同作用于人类经验的其他品质一样,是相对的;其定义越抽象,越无意义,越无用处。因此,要采用尽可能最具体而非最抽象的术语来界定美,而不是探寻美的普遍公式;要设法找到最充分地表现美的这种或那种特殊显现的公式,这是美学研究的真正目标。[1](P.xix)
上述观点既涉及“审美研究的真正目标”,也关乎文艺批评的有效原理。这两者随之融贯于“审美批评家”(aesthetic critic)的专业特质之中。其中至为关键的基点,就是要遵循阿诺德的说法,“按照对象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对象”(to see the object 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1)Mathew Arnold. “On Translating Homer.”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hew Arnold. ed. Robert H. Sup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1977, vol. I, p.140; Mathew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hew Arnold, 1864, vol. III, p.258.。 这就是说,审美批评家面对艺术品或其他形式的审美“对象”,要依据其“本来面目”进行评价,要凝神观照其自身结构、表现情境、内在价值和蕴涵意义,继而借助“尽可能最具体的术语”(the most concrete terms possible),对其逐一进行深度的审视、阐释、评判和鉴赏。
可见,佩特在此引用阿诺德的这句名言,意在强化审美批评家的基本素养和原则立场。这是因为佩特一方面赞赏阿诺德的言论和做法,认为借此方法可将批评对象(文艺作品)从个人纠缠不清的奇思怪想中解救出来,从而更为客观和清晰地审视和鉴赏对象;另一方面,佩特十分关注反思事物的本性,同时也十分看重美学在人生中的地位。这便使他轻视那种基于抽象思辨或普遍笼统的哲学或美学,断言任何将绝对视为梦境的形而上学追问,在审美批评领域都是毫无意义的。譬如,在论及歌德这位“审美天才”时,佩特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容易沉浸于平庸的形而上学本能,如若我们想要以艺术的完美性来熔铸我们生活的话,那么,喜爱形而上学的品位就会是我们应该放弃的东西。哲学服务于文化,不是通过绝对或超越性认知的神奇馈赠,而是通过帮助人们去发现激情、陌生世界与生活的戏剧性对比。” [1](PP.183-184) 有鉴于此,佩特反其道而为之,极其重视基于具体分析和精准描述的审美批评功能,并为归于哲学名下的美学,设定了上述如何“服务于文化”的特殊功能,即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功能。
在佩特眼里,真正的“审美批评家”,务必将其审视的对象,即一切艺术品和人类生活中较优美的形式,看作产生快感的动力或力量,因为这些对象都或多或少有其独特属性。在此,佩特通过具体分析,将自己的感受简化为各种元素,继而对其加以解释。对他来说,无论是一幅绘画、一处风景、一类香草、一种葡萄酒、一块宝石、一位讨人喜欢的人物等等,都会因为各自具有使人产生独特快乐印象的特质而弥足珍贵。结果就是,伴随着人们对这些印象的感受力逐渐深入,人们所受到的教育也相应变得完善起来。所有这些审美对象,皆通过其优美而使人产生独特的美感或快感。
说到底,佩特认为“审美批评家”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区分、分析和呈现这些优点,将这些优点同其他附属物分离开来,指出美感与快感源自何处,在何种情况下能被人感知。据此,当“审美批评家”在挑选和阐释这些优点时,就像化学家对待各种自然元素一样,既能对自己也能对别人叙说清楚之后,他的目的才算达到。[1](P.xix)总之,真正的“审美批评家”,若要不玷污自己的名声和职责,那务必具备足够的能力,采用审美批评具体化的方法,精准明晰且发人深省地描述和分析其所面对或凝照的对象,由此完善广大观众或读者的艺术教育或审美教育。可见,佩特在倡导审美批评具体化原理的同时,旗帜鲜明地贬斥形而上学的抽象批评或空洞无物的玄言高论。因为前者有助于人们解读、感知和鉴赏审美对象,后者则恰恰相反,属于既无意义也无益处的无效劳作。
二、文艺复兴的艺术解析
那么,在鉴赏艺术的过程中,佩特是如何运用审美批评具体化的方法呢?我们不妨先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为例。在佩特看来,米开朗基罗的艺术风格代表一种有别于古希腊雕塑的体系。其真正的典型之处,就在于“甜美与力量”(sweetness and strength)以及惊与喜的彼此交错之中。这里,思想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好像要从标致的外形中突围出来,将一种可爱的品质一点一滴地覆盖上去,所有这一切通常只在最质朴的自然事物中才会被人发现。这就是他所标举的“强健中的甜美”(exfortidulcedo)。(2)“甜美”有被译为“甜蜜”,见佩特《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张岩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笔者根据原文译为“甜美”。原文中先用英文表述——sweetness and strength,后用拉丁文注解——ex forti dulcedo,后者可英译为sweetness out of strength。参见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Donald L. Hill. ed.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57。正是采用这种方式,佩特总结了中世纪艺术独有的特征,也就是那些与其他古典作品截然有别的特征。 譬如,在米开朗基罗的手中,石头仿佛有了生命,雕塑作品变得鲜活起来。这位雕塑家通过对生活的深刻暗示,将作品中甜美型的奥秘呈现出来。于是,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人们可以从极其强大的力量中发现甜美的源泉。《创世记》《新生》《母爱》等作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其实,奇妙的甜美与雄健的力量,以其惊喜交加的互动方式,富有诗意地融会在《夜》《昼》《晨》《昏》这一组象征性的雕刻形象里。佩特认为,这一组形象与其作者的心灵和精神极为接近,与那些仅仅蕴含象征性的观念相比,它们更为直接地表达了米开朗基罗的思想。在这里,与其说是通过确定的概念予以表达,不如说是通过一种碰触和喧闹的激励方式予以表达。不管思想以什么方式试图使自身专心于非肉体的精神性条件和环境,这里表达和关注的所有模模糊糊的幻想、疑虑和预感,总是处在变换、混合、被确定又重新消失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既无宽慰也无恐惧思想的地方,其所富有的只是模糊和愁闷的思索。准确地说,在所有情感领域,米开朗基罗是一位诗人,一位仍然活着的诗人,一位活在我们丰富思想最深处的诗人。在一首十四行诗里,这位诗人曾发出如下叹谓:
幸福的精灵,
以热烈的爱情,
使我垂死衰老的心,
保持生命。
在其雕塑作品中,米开朗基罗借助明亮、灵敏、准确的技能,采用精妙、含蓄和富有启示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于爱情和生命的眷恋、沉思与遐想。可以说,他的相关思想,是一种对于先于生命、死后重归无形状态的默然无语的要求,是对变化的要求,是对从变化到不变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修正、神圣化和同情性冲动的要求。最终,这一思想已然远离原点,是一种既稀薄又模糊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其模糊程度甚于那种曾经与人心如此接近的最明确的思想。当新的身体产生之时,这一思想是一缕飞掠而过的光照,是一种不可能触摸的外在结果,相继挂在那些过于严谨、过于无法定形的脸庞之上。这一思想,是一种梦想,稍作徘徊,就在黎明时分消退了;它既未完成,亦无目标,也很无助;这种思想是一种事物,有着柔弱的心灵、模糊的记忆,却没有多大冲击力;它是一种呼唤,犹如门口的一束火焰、风中的一片羽毛。[1](PP.75-76)佩特的相关审美分析,颇为具体和细微;其诗性化的描述,不仅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且丰富了这组雕塑所表达的深刻内涵,譬如模糊玄思的哲理性、形态变化的戏剧性、生命时间的循环性、梦境神游的奇幻性等等。
令人惊异的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时,佩特对死亡的关注似乎如影随形,在具体化的审美批评中更注重某些关键细节。譬如,观看《美杜莎》这件作品,他发现只有达·芬奇将其画成死尸的头颅,借此表现一种“腐朽的魅力”,表现一种精妙绝伦的美。画中那些细软的蛇群,进行着惨烈的缠斗,似乎要通过互相扼杀来躲避美杜莎的脑袋。[1](P.83)如果躲之不及,任何生灵都会在瞬刻之间化为“僵石”。面对《蒙娜丽莎》这一名作,佩特认为这幅肖像隐含这一标题——“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据他观察,蒙娜丽莎的眼皮显得有些倦怠,看似比她置身其中的岩石还要苍老。她就像吸血鬼一样,已经死过多次,熟知坟墓的秘密。[1](P.99)
无独有偶,佩特还将死亡的意识贯注到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之中。他曾感慨说,这位伟大艺术家就像拥有高贵心灵的其他意大利人一样,心里装满死亡的念头,连他真正的情人也与死亡同伍。死亡,最初是所有悲伤和耻辱中最坏的现象,后来竟然获得很高的荣誉,从粗俗的需求与生活中、令人愤怒的污点中剥离出来,飞遁而去。[1](PP.69-70)这种表达死亡的论调,无疑有悖于当时的主流生活观念,必然遭到正统派人士的抨击。但要看到,佩特热衷谈论死亡的初衷,意在提醒读者人生苦短的事实,借此促使他们追求一种在精神与情调上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某种佩特式向死而生的暗喻。
值得注意的是,佩特每谈艺术,必言生死。在他的深层意识中,人的生死总要涉及“瞬间”这一概念。在佩特的人生观中,他所宣扬的“瞬间”概念,通常被引申为关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瞬间哲学”。在《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一书的“结论”部分中,佩特尝试超越生死的局限,尽力捕捉可能的瞬间,甚至将其当作生活的本源和唯一的实在。面对人生经验中五光十色的短暂时刻,他建议人们必须抓住任何强烈的情感、任何认知的契机、任何形式的感官刺激、任何奇异的直观对象,这其中无一例外地包括艺术品。所有这些必将组成的一连串富有审美意义的独特瞬间,只要把握得当,只要欣然敏悟,只要扩展有方,就会逐一转换成丰富多彩的、活力十足的、诗情画意般的人生。在此戏剧性的经验过程中,佩特十分在意的是如何将粗陋的文化变成高雅和优美的文化,如何将那些瞬间转化为审美的瞬间和精神的狂喜。在这方面,他依然看重的是艺术魅力,认为艺术会通过自身坦率的表达,将最高的质量赋予人们所获的那些精妙绝伦的瞬间。[1](P.190)如此说来,真正组成人生的那些绝妙“瞬间”,应当蕴含在高雅的艺术魅力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艺术杰作,正是富含这种艺术魅力的典型代表。
的确,佩特敏锐地洞察到艺术魅力的瞬间特性与现代思想发展中的相对性相。于是,他以生命的不确定性、短暂性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断然扬弃了绝对主义的原理,有意强化了相对主义的宗旨。如其所言:我们有一短暂时期,使得我们的伫留之地,不再属于我们。这让人不由想起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说,即万物流变,无物常驻,世界如同一条水流。虽然我们可能两次涉入同一条河,但我们不可能两次都将自己的双脚涉入同一水流,因为再次涉入的水流,在转瞬之间已非原来的水流。[2](P.15)不难看出,佩特的瞬间学说,与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说具有潜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佩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赫拉克利特的启发。不过,佩特使用自己的阐述方式,试图为人们走出人生的困境和参悟人生的意义指点迷津,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人们的敏锐感,以便把握或鉴赏自然和艺术时展现给人们的奇特感觉和印象。[3](P.35)由此推断,佩特强调“瞬间”的特殊意义,对于真心热爱生活的人们来说,就是期待他们在艺术鉴赏中积极地探索瞬间、创造瞬间、感知瞬间,最终在把握瞬间的审美体验和敏悟中,有滋有味地快乐生活,艺术化地享受生活。唯有这样,生活才是本真而丰富的生活,而不是黯然被生活所遮蔽的生活。
三、古希腊雕塑的鉴赏方法
那么,佩特又是如何论述古希腊雕塑的艺术特质及其鉴赏方法的?依据具体化的审美批评原理,佩特着意通过揭示相关细节,来助推古希腊艺术鉴赏活动。在这方面,佩特虽然深受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学思想的影响,注重从神话、宗教、爱美意识和社会政治文化等视域出发,探索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基本特质,但与此同时,他力图独辟蹊径,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从神话传统与石铁工艺等角度切入,昭示古希腊雕塑不同凡响的审美价值。
尤为有趣的是,佩特在《古希腊雕塑的开端》一文中,在论述英雄时代的古希腊雕塑艺术特征时,率先提出“三重隔离说”,借此表明现代人要想真正欣赏古希腊雕塑艺术,首先应当注意和识别下列现象。如其所言:我们所拥有的最高级的古希腊雕塑,是在一种三重隔离状态下呈现给我们的。其一,古希腊雕塑与伴随性的诸艺术相隔离——譬如,帕特农神庙殿壁饰浮雕上的骏马,没有原先所戴的金属笼头,大理石浮雕上只留下原来的穿孔;其二,古希腊雕塑与建筑群相隔离,这等于失去经过精确估算与设置的观察距离和点位,而神殿壁饰带在设计时就属于这一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其三,在我们现代的展览馆里,古希腊雕塑与明朗的希腊天空和富有诗意的希腊生活相隔离。[4](P.167)
读者不禁要问,这“三重隔离”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导作用?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在此处或彼处看到这些作品,他会自以为看到自己所期望看到的真品;如果他不假思索,努力将自己完全投身于那种特定的氛围里,认为这样一来他就会像原来的希腊观众一样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神奇魅力,那他肯定不会取得预想的效果,反倒陷入自作多情或自以为是的陷阱。也就是说,无论你在大英博物馆里,还是在法国卢浮宫里,当你看到这些作品时,你是在三重隔离状态中观看,已然落入伪装或失真的环境之中。古希腊雕塑一旦展示在这种虚假环境中,就等于切断了这些作品与纺织匠、木匠、金匠、诗人、哲学家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其感受力大受折损。因为希腊雕刻家都是有思想、有理智、有情感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想要表达希腊人的内心生活、精神特质和思想境界;同时通过自己超绝的技艺,想要表达希腊人的情感世界、审美意识以及神性虔诚,等等。因此,欣赏古希腊雕塑,要具备充分的知识素养,要知道环境的真伪,要了解作品的缺失,要追思历史的情境,否则人们就会顾此失彼,甚至以假当真,那样就会忽略或错失希腊雕刻艺术的原本魅力与感染力。
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现代人在博物馆观看古希腊雕塑时,通常会将呈现于眼前的黄色大理石视为作品的本色。实际上,原来的雕塑涂有不同颜色,有的还点缀着贵金属(如黄金)或象牙装饰品。无论是帕特农神庙的宙斯雕像,还是米洛斯岛的爱神雕像,原本都有华美的装饰和色彩。现代考古学家从所发掘的雕像中,多次看到上面涂抹色彩的痕迹。实际上,佩特早先在论述“雕像时代”(the age of graven images)的古希腊雕塑时,就曾十分确定地表明:
古希腊雕塑的批评家们经常谈论这一艺术时,就好像古希腊雕塑总是在没有色彩的石头上成形,总是依据一种几乎没有色彩的背景。如我一直尽力表明的那样,古希腊雕塑的真实背景,是一个技艺精湛的世界,借助精美与技艺,触及日常生活中最微末的细节,与人生特有的动态发展密切应和,所表现的内容包括典型高贵人体的充满活力的运动与微动;这些人体的衣着相当适宜得体,其周围的景致,就像巨人周围的景致那样富有诗意。倘若那些没有色彩的石头形状进入到雕塑的背景之中,那是让没有遮盖的人体进入到某些巨人的图景之中,其目的只是为了以冷静和庄严的方式,来表现或凸显后者的精美罢了。[4](P.200)
当然,佩特此处所言的色彩,除了衣着所需的涂色之外,还有色调丰富的金属饰物,譬如闪光的黄金、黄铜以及洁白的象牙等。菲迪亚斯所雕塑的宙斯神像,分别供奉在奥林匹亚和雅典帕特农神庙,均采用了贵重的象牙和黄金等有色金属,突出展示了“英雄时代”金匠的工艺水平。再者,诸多古希腊雕塑家在装饰其作品时,更喜欢使用某些色泽各异的黄铜,或者使用考林斯所产的那种金光闪闪的合金(bright golden alloy of Corinth)。[4](PP.200-201)
至于希腊明朗的天空和富有诗意的生活际遇,那的确是鉴赏希腊巨型神像雕刻与建筑门楣浮雕的重要背景。现如今,我们在博物馆里所看到的那些雕刻作品,无法同其原先设置的自然环境相提并论。不过,我们在雅典帕特农神庙遗迹观赏那些女神形体雕刻立柱时,借助当地明净晴朗的蓝天,依然可以追溯当年历史情景和艺术氛围的某些光影。但要想比照当时雅典人富有诗意的生活,显然就比较困难了。在古代,不少雅典人,无论是在剧场里观看演出,还是在消夏酒会上坐以论道,抑或是随军外出征战,他们随口都会朗诵《荷马史诗》或雅典悲剧杰作的某些著名段落。甚至在极端条件下,有的雅典战俘是通过吟诵悲剧诗人的作品度过牢狱之灾的。俱往矣,这些都只能借助历史描述去追忆和想象了。
需要指出的是,佩特在分析“英雄时代”的古希腊雕塑艺术时,还特意关注希腊的次要艺术,也就是金匠、铁匠或工匠的工艺品。他认为在这些次要艺术精品中,可以折射出古希腊雕塑艺术的精致和细腻之处。譬如,他曾列举的典型例证,就包括浮雕图案错综精妙的“阿喀琉斯战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和弗阿克斯国王富丽堂皇的“阿尔卡诺俄斯宫室”(the house of Alcinous)。[4](PP.171-172)这两个例证均来自《荷马史诗》。对于前者,《伊利亚特》第18卷里有过细致的描述[5](PP.468-608);对于后者,《奥德赛》第7卷里有过详尽的描述[6](PP.37-132)。这些描述在遣词用句上,或许蕴含诗人的夸张、美化或想象,但其所依据的相关景象,终究是原物的直观形态。事实上,所举战盾上浮雕的景致,宫室里摆设的装饰,均属于空间艺术范畴,均离不开各类工匠的手艺和当时的冶炼制作技术,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英雄时代”古希腊雕塑艺术的精湛工艺和表现方式。
在论述希腊艺术、神话、宗教和人生之间的关联时,佩特在相当程度上因循的是温克尔曼的基本思路,但其中也穿插着个人的一些见解,彼此之间形成某种互补关系。根据佩特所言,希腊宗教是一种重要的仪式系统和诗歌观念的展示。作为诞生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则,宗教总是随着人类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在玉宇晴空下宗教变得明亮,在社会宽厚时宗教变得自由,在人类生活发生断裂、精神遭到限制和世界黑白颠倒时,宗教也就变得严酷和紧张不安。在希腊宗教里,有不少观念来自神话。不过,神话本身完全不是宗教的源泉,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宗教观念的载体。于是,在神话中,就涌现出人类的形象和性格。当神话变成不再变化的仪式因素时,其自身就给宗教观念带来一种具有永生性的精致和上升的因素。在通常情况下,固定的因素成为宗教仪式,流动易变的因素成为神话,继而转化为宗教观念。乍一看来,希腊艺术是与宗教纠结在一起的。我们习惯于认为希腊宗教是艺术和美的宗教,是以奥林匹亚的主神宙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为偶像的宗教,是以《荷马史诗》为民众教育“圣经”的宗教。[1](PP.159-160)当然,古希腊的多利安人崇拜日神阿波罗。日神不仅拥有理智、明耀、和缓、快乐和不灭的阳光,而且拥有奋勇向上、恒久不竭的力量和精神。希腊宗教借此提升了自身。这便使希腊艺术在一种快乐的氛围中,从希腊宗教中产生出来,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希腊宗教的独有特权,就在于能使自身转化为理想的艺术。正是在古希腊雕塑中,希腊式的理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希腊神话与希腊宗教之外,古希腊雕塑与古希腊传统的爱美意识密切相关。对于古希腊人的爱美意识,佩特与温克尔曼所见略同,概括起来就是:没有人像希腊人这样给予美如此多的尊重。年轻宙斯与阿波罗的祭司们,永远是一些荣获美的奖章的年轻人。有的城邦市民因为一位外乡人美貌异常,而为他树立起一座纪念碑,随后还在纪念碑下为其献祭。有一首古代歌曲,吟唱过四种愿望,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美。由于美如此令人渴望且受人嘉赏,所以每一位拥有美貌之人,都努力寻找门径,让全体人民知道他的优胜之处所在,以便由此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模特,使得艺术家拥有永远面对至美的机遇。美甚至赋予人们获得荣誉的力量。在希腊历史上,最美的人有着很高的声誉。一些人因身体某一部分的美而出名,法列里的迪米特里阿斯就是因美眉闻名,因而被称作“美眉公”。人们似乎认为生出漂亮的孩子也是值得嘉奖的“壮举”,这一点时常通过有关美的争论得以展示。在斯巴达和雷斯宾岛,在朱诺庙里,在柏拉西人中,妇女们之间流行着关于美的争论。对美的普遍性的尊崇,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为了能生出漂亮的孩子,斯巴达妇女在她们的卧室里,都要种植一株漂亮的水仙花或一朵风信子。[1](P.166)
这里所言的“四种愿望”,可能源自西蒙尼得斯的一首诗,一般认为这四种愿望包括健康、美、力量与财富。柏拉图在《法礼篇》(Laws)里,也曾提及这几种被视为善好之德的愿望。不过,相比之下,位列第二的“美”,实则同位列第一的“健康”,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希腊人委实崇尚美,但他们崇尚的是健康美或健壮美,从不喜欢病态美或羸弱美。这不仅与他们习以为常的审美理念相关,而且与他们喜好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运动)和争冠意识相关。另外,在当时的冷兵器战争年代,健康或健壮的公民应召入伍,对于保护城邦的安危至关重要。更何况斯巴达的子女育养传统,通常把健康作为先决条件,否则宁愿弃之不养,以免给家庭和社会造成额外负担。
总之,希腊人看重美,特别看重健康美。通常,角力学校的美与艺术家工作间的美彼此映照,相互转换。在围绕体育训练学校或场地四周的走廊里,艺术家与哲学家经常光顾、散步和交谈。在相关话题中,有关人体美的讨论,通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举凡拥有健康美形体的年轻人,往往志存高远,尝试着与神比肩量力。他们身上不断增加的美,相继传导给诸神塑造的完美形象。他们甚至会不无自豪地宣称:“我证明了神的存在。我宁愿选择美的身体,也不选择国王的皇冠。”[1](P.167)这便是那个世代年轻人所选择的更为高雅的生活。
另外,在希腊人的思维中,盛行一种神何以成为人和人何以成为神的思维模式。因此,赫拉克利特曾言:“凡人是神人,神人是凡人。此方生彼方死,此方死彼方生。”这兴许是说,人希望成为神而认识这个世界,确定这个世界,安居在这个世界。[7](P.19)按照我的理解,神何以成为人,是就外形而言,是通过人赋其形而成。人何以成为神,也是就外形而言,那是通过摹仿神而成。如果说神是完美的,神的雕像就是体现这种完美的象征。于是,希腊艺术家通过把神雕刻成人形,由此造就凡人可以直观的形象,以便让人可以摹仿,并在教练的指导下追求塑造美善兼备(kalokagathia)的形体和内外应和的境界。如果说人是在摹仿神的过程中成为完美之人,那么,希腊艺术家通常以神的完美形象为样板,依此造就完美的人体形象。如此一来,在直观的艺术形式中,除了个别代表神祇的象征装饰或独特神器(譬如智慧女神雅典娜手中的神杖、日神阿波罗头上的光环、酒神狄奥尼索斯发髻的葡萄叶等)之外,用大理石雕刻的神与人的形象,在直观意义上是彼此类似的,在审美意义上是难分伯仲的。当然,在柏拉图那里,人之为人,在于像神。这涉及完美形象的塑造与完善德性的修为,涉及内外双修的道德伦理学或道德人类学的目的论追求。
应当承认,以古希腊雕塑为代表的希腊艺术,实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话题,以上所陈只不过是删繁就简的提示而已。这里,我们不妨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话作为结论。这段话是佩特亲手译自黑格尔的《美学》第2卷,足见他不仅赞赏而且认同黑格尔的如下归结:
在希腊,这种完美地塑造了神性和人性的感觉,是十分内在和卓越的。从其诗人和演说家身上,从其史学家和哲学家身上,是无法从一个中心点上来构想希腊的;将目光投向雕塑的完美形式,将其作为理解希腊的关键之处,以一种艺术的观点,对政治家和哲学家表达一种与史诗和戏剧中的英雄们一样的敬意,只有这样,才能构想希腊。这是因为,在希腊的那些美好时光中,他们扮演且创造,思考着这一可塑性的角色。他们伟大且自由,从自己个性的土壤中生长起来。他们自我塑造着,且能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伯里克利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伯里克利本人、菲迪亚斯、柏拉图,尤其是索福克勒斯,另外还有修昔底德、色诺芬和苏格拉底。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他们都是一些完全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就是自己的艺术家,每个人都被置于一个没有缝隙的模子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神一样不朽的艺术品。那些表现奥林匹克运动的胜利者的身体的艺术品,也是这样塑造的。是的,甚至是在希腊人的聚会中,从水中出现的最美的裸体妇女也是这样
这一论断可谓理解希腊精神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希腊艺术的一把钥匙。无论佩特或温克尔曼,还是黑格尔本人,他们各自都掌握着这把钥匙,并且从这一视域出发,多向度地观照着希腊人的文化、生活、思想及其秉性,在探幽入微的过程中,深入揭示了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内在奥秘和审美价值。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为当时和后世的广大读者,开启了理解和鉴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有效途径。
四、柏拉图的美学定律与目的论追求
在我看来,佩特的美学与艺术思想底色,包括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所热衷的古典研究,尤其是他对柏拉图与古典艺术的研究。从学术史上看,在19世纪的古典学界,佩特是关注柏拉图美学的少数学者之一。在《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这部论集里,最后一篇文章专论柏拉图的美学定律。其所聚焦的柏拉图对话文本,主要是《理想国》《会饮篇》与《斐德若篇》等。
佩特通过研究发现,在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智或精神生活中,耸立着“两座伟大地标”(two great landmarks):其一是理想城邦,其二是理式世界。这两个领域既涉及“辩证的精神”,也关乎“哲学的禀赋”。[8](PP.195-196)更为重要的是,美的理式对柏拉图而言,已然成为核心理式(central idea)。美作为呈现理式意涵的典型例证,用以彰显理式与特殊事物的关系,表现思想行动对事物自身的影响。举凡爱美之人,既要凝照视觉所及的肉身之美或可见之美,也要探寻思想所及的绝对之美或美自体。个体对美的自我发现,具有某种不可预测的特性,其间所凭借的是一种亲和力法则,即一种介于审视者与被审视对象、认知过程与认知对象之间的亲和力法则。[8](PP.170-171)这里若就可见之美与绝对之美的各自特性及其内在关联而言,前者意指美的现象或外显,后者象征美的实在或真相;前者易变,后者永恒;前者为果,后者为因。也即是说,天下美之为美的原因或成因,在于后者而非前者。不过,对此原因或成因来说,可见之美虽是特殊现象,但最接近美的原型或永恒范式。如此一来,两者的关系尽管有本末之别,但是彼此相互印证、须臾不离。
事实上,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里,借助苏格拉底之口,对爱美欲求与美的阶梯喻说,进行了颇为翔实的阐述。其中不仅谈到人的形体美与心灵美,而且论及社会的制度美、真正的知识美与绝对的美自体。当柏拉图将美作为爱欲的对象时,就等于把全部身心倾注于美的发现与创造。这里面所隐含的有机多义向度,不仅涉及基于多种形态美的爱欲现象学,而且涉及基于道德与智慧的人类本体论。[9]
有趣的是,佩特认为美的永恒理式出于某种缘由,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类似这一理式的拷贝或摹本,或者说是相关的影像或相似的类型。它们彼此之间虽不完全相称或应和,但真实而妥帖,从中显露出公正与完美城邦的摹本特征。美的永恒理式,促使人们用心沉思、不断求索,一方面贯穿全部理式学说,另一方面贯穿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在持续的探索中,造就一批理想城邦的重要基石或管理城邦事务的“哲学家”——“热爱真理与真实存在的哲学家”(tou ontos te kai aletheias erastas, tous philosophous)。[8](P.171)
在这里,美自体的拷贝或摹本,令人联想到柏拉图的摹仿说(theory of mimesis as imitation)。通过研究《理想国》的第3卷和第12卷,佩特发现柏拉图的美学与其伦理学关系密切。或者说,在我们周围世界里被视为审美特质的东西,与我们道德品质的塑形过程之间,存在某种密切关联。[8](P.269)人生本身,也就是人的行为与品质,会受到艺术的影响或熏染,会从不可抑制的艺术良知中获得某种益处。譬如,作为主要德性之一的克制精神,就会步入人生的基本发展过程之中,会浸入人生充满活力与慷慨激昂的行为之中。[8](P.282)实际上,柏拉图作为西方历史上最早的艺术批评家,十分重视诗乐艺术(诗、乐、舞等)中的审美要素及其情感效应,坚信这些东西会对人的品行或人格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有鉴于此,柏拉图宣称诗乐艺术教育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早期教育阶段或蒙学阶段,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培养和塑造“美善兼备”的城邦卫士这一目的论追求。
谈及艺术的摹仿行为(包括舞台上或想象中的身体摹仿行为与心灵摹仿行为),柏拉图认为这一切均发端于早期生活阶段,随后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持续不断,最终成为人类习性的组成部分,通常蕴含或反映在身体的运动、声音的语调和思维的方式之中。总之,通过悦耳悦目的摹仿行为,必然会对人性、习性与德性产生某种影响。公民作为理想城邦的主体,理应自身追求完善,拥有人性的质朴特征。这就要求音乐、诗歌和艺术,持守克己奉公的法令,传达符合道德的价值,力助公民养成艰苦朴素的品格。柏拉图假定,人类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易受影响的感情脆弱性(susceptibility)。故此,艺术品用于表现的形式、色彩、音响、语词、景物和主题,加上准确、质朴、节奏、多样化或与之相反的种种审美特性,都会在听众与观众的秉性中,各自转化为某种伦理品质,继而进入到欲望与意志的领域。其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效应,自然会造成影响城邦公民情操和意志的条件,而不会只是无动于衷或毫无影响的存在物。[8](PP.271-272)
概括起来,佩特对柏拉图美学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大定律。第一是考虑和设定理想城邦艺术的适宜定律。鉴于人在年少时,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就像某些昆虫一样,惯于参照身旁的植物颜色,因地而异地改变自身表象。为了培养合格的城邦公民,就需要构建适宜的艺术氛围,借此规避恶性或负面的离心趋向。在适宜的艺术氛围中,诗、乐、舞等艺术务必经过完美训练,在道德和审美意义上适合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鉴赏能力,从而爱其所应爱,恶其所应恶,习其所应习。在祭神的礼仪中,在城邦的节日里,在戏剧的舞台上,这些符合道德与审美的艺术表演或表现,有望营造出城邦所需的文化氛围,借此促使人们在身体与心理的各种摹仿中,汲取有益于自身品质与人格发展的成分或要素。
第二是保持传统艺术形态的恒定定律。在诗乐艺术与多样性的趣味领域,务必恪守自我克制的法令,遵循适合道德的规定,切勿单纯追求音乐或审美效果,切勿随意改变诗、乐、舞的节奏、韵律、动作、声音、方法与结构等。至于那些像转动镜子一样可以映照四周外物的艺术家,也就是那些擅长摹仿或炫技的艺术家,他们也许能激发观众的审美快感,制造魔幻的娱乐活动,却会对青少年的习性和品质产生消极影响,诱使他们更多地寻欢作乐,而不是更多地修身养性,以期塑造“美善兼备”的人格。有鉴于此,艺术就像法律一样,旨在助推心灵的构建,也就是依据正确的理性来塑造良善的心灵与质朴的人性。为了净化理想城邦的艺术与文化氛围,为了借此除恶存善,城邦艺术务必得到相应的净化、道德化与高贵化,务必避免夹带任何“道德毒药”(moral poison),务必区分出无视城邦规定的“坏艺术家”(bad artists)。所谓“坏艺术家”,实则是技巧高妙、无所不能却自以为是的摹仿型艺术家。他们虽然擅长摹仿一切,表演起来惟妙惟肖,但是不符合城邦的艺术教育目的,甚至有些背道而驰或唯名是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可能的困境,城邦最好以礼遇的方式,将这些自以为是的“坏艺术家”送到其他城邦,不得让他们进入理想城邦。
第三就是通过艺术精神气质来培养勇武和节制德行的平衡定律。考虑到理想城邦的构建与城邦卫士的培养,柏拉图十分重视艺术的精神气质(art ethos),高度警惕艺术的情感力量(art pathos)。按照他的说法,诗人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善好的品格,应当引导人们效仿英雄人物。画家也是如此,其作品应当在部分程度上符合审美要求,在部分程度上符合伦理规范。但就城邦卫士的人格塑造而言,多立克艺术中的建筑与诗乐,具有男子气概或勇武的精神气质,这有助于塑造勇武的德行,成就果敢的卫士;与此同时,多立克建筑中柱式的特殊规矩和形状,遵循的是严格的尺度与比例,实属将逻辑与理智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一艺术特征有助于孕育节制或审慎的德行。建筑艺术的这些法则与特征,也可以运用于或体现在雕刻结构、绘画形象、诗乐韵律与舞蹈节奏之中。总之,柏拉图依据自己的美学方案所推行的文学艺术,要求观众或听众全神贯注,专心体悟诗人与艺术家作品中的表现力及其丰富内涵,以便在不同精神气质的和谐互补中,构建勇武与节制的美德和卓越品行。
值得注意的是,佩特认为柏拉图笃信古希腊流行的这一谚语:美是难的(chalepa ta kala)。这意味着美委实难以界定,难以把握,难以创构,甚至难以欣赏。但是,所有古希腊人都离不开美,不管是艺术还是生活,不管是教育还是宗教,美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过,佩特认为柏拉图教导我们所要热爱的美,主要是“不形于色的美”(dry beauty)。[8](P.283)现代人容易将这种美等同于数学家所说的那种“冷静与严肃的美”。实际上,柏拉图所推崇的“不形于色的美”,在本质上是会通道德、审美与理智等维度的综合美。当然,在至为“抽象”的意义上,这将会指向理智化的绝对美或美自体。
佩特上承柏拉图的观点,认为美与善、审美特性与道德品性、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8](P.269)的确,美的理念在柏拉图至为抽象的思辨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其数篇对话中,柏拉图十分重视美与善的本体特性,经常标举美即善的互动关系学说,甚至多次将美与公正这一综合性德行并列起来加以比照。(3)Plato. Republic. Loeb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 pp.476-480,505-509a; Plato. Philebus. Loeb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 pp.64c-65b; also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John M. Cooper. ed.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尽管柏拉图声称美与善两者的形态存在趋同与别异现象,但在美自体与善自体的本体论意义上,因善而美的因果关系是确然无疑的。[10] 据此,佩特因循柏拉图的理路,秘而不宣地站在审美立场上,似乎遮蔽了美所内涵的道德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佩特唯美主义思想中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虽然在当时的理论氛围中不乏法国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因素,但是在佩特自己的深层意识中,这一论点主要是从柏拉图的艺术思想中脱胎演变而来。按照佩特的理解,柏拉图是“最早的美术批评家”(the earliest critic of the fine arts),是最早预测出“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念的古代哲学家。[8](P.267)在这里,佩特所引用的古希腊文是Ar’oun kai hekaste twn technwn esti ti sumpheron allo e oti malista telean einai,其在柏拉图笔下的用意是“艺术自身没有目的,但只求自身的完善”。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柏拉图都十分关注可见之美的可能作用与真实之美的重要意义。在构造其理念论的过程中,柏拉图在反思可见之美时,高度重视这种美在我们经验中的作用或地位。因为在人们周围的可见世界里,节制、果敢与公正等主要德性并非是肉眼可见的,而是透过各自引人注目的“形象”展示出来的,或者说是透过人类个体及其卓越行为得以直观表现的。于是,在教育领域,这些德性的兴发与养育,均始于和终于具有对称性、适宜性和审美性的音乐或诗乐。有鉴于此,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本身是对“源于事物本性的某种音乐的共鸣式鉴赏”(sympathetic appreciation of a kind of music in the nature of things)。[8](P.267)这意味着以音乐或诗乐(即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艺术,不仅关系到审美鉴赏或艺术教育,而且关系到人格德性与心灵教育。
的确,柏拉图一再强调诗乐关乎人类心灵,认定艺术的审美要素是城邦公民心灵塑造或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艺术如同法律一样,“是按照正确的理性,对心灵的一种构建”,人们总不能期望少年儿童仅像鸟儿一样唱歌吧。[8](P.275)这等于说,人类不应是头脑简单的本能型摹仿者或鸣叫者,而应是具有人文修养和审美情趣的创造型鉴赏者或表演者。佩特个人深信,柏拉图所倡的艺术观,是奠定艺术地位的重要基石;艺术鉴赏或艺术教育,是建构理想城邦和公民德行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出于这一缘由,柏拉图才从道德与审美教育的角度,反复阐述如何创构适当艺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目的论上看,柏拉图在论及早期教育时,特别强调诗乐(mousikē)艺术与体操(gymnastikē)艺术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两者关系到青少年日后的德行发展,关系到培养“美善兼备”的整全人格(whole being)或“完善公民”(perfect citizen)。一般说来,诗乐艺术呵护心灵,诗乐中对神明和英雄的颂扬,对高尚德行与品格的表现,能教化民众,使其心灵“爱其所应爱,恶其所应恶”(misein men a chrē misein, stergein de a chrē stergein)。[11](P.653)相应地,体操艺术关照身体,通过游戏、舞蹈、田径、狩猎与军训,能使人体魄强壮,身材健美,能征善战,有助于保家卫国。
有鉴于此,柏拉图强调道德修养的艺术教育思想,可称之为一种道德诗学。这种诗学主要基于道德理想主义(moral idealism)和政治实用主义(political pragmatism)的原理,主要由心灵诗学(psycho-poiēsis)和身体诗学(somato-poiēsis)两个有机联系的维度构成。从原理上讲,道德理想主义基于至善的理念,将智慧、勇武、节制与正义等德行所构成的城邦伦理基础完全理想化了,不仅认为这种伦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僵化的法律体系,而且坚信通过正确教育会使这种伦理要素内化在公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最终培养出具有优良德行的完善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想国》里,这种伦理或道德至上的学说,显然超越了法律至上的传统。但在《法礼篇》里,柏拉图虽然持守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原理,却回归到了法律至上的传统界限之内。至于政治实用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我曾说过的政治工具论,该理论基于“为城邦而生,为城邦所用”的信条,从维护城邦的共同利益与和平秩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把对公民实施的艺术教育视为手段,就如同把对公民的法治教育视为手段一样,最终是要把公民培养成保家卫国的战士和遵纪守法的楷模。从构成上讲,以诗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旨在培养健康的心灵、敏锐的美感、理性的精神、智善合一的德行,以便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旨在练就健美的身材、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武功、优秀的品质,以便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从目的论上讲,心灵诗学以善心为本,身体诗学以强身为用,柏拉图正是想通过心灵诗学与身体诗学的互补性实践,来达到内外双修、文武全才的教育目的,造就身心和谐、美善兼备的理想人格。[12](PP.91-92)
对于这一点,佩特的论证既不充分,且显矛盾,前后难以自圆其说,无法从柏拉图注重道德化艺术教育的立场一跃跳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然而,佩特在理论上似乎“我执法执”,刻意抛开柏拉图的思想语境,不惜断章取义,将柏拉图的相关言论当作“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的理论支撑与历史依据。这实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是其唯美主义思维惯性的产物。不过,如果我们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主张悬置起来,将其纳入佩特念兹在兹的柏拉图主义艺术理论中予以审视,就会发现佩特的唯美主义是一种异类,是一种既关注艺术审美又关注人生完善的混合体。正因为如此,贯穿佩特美学思想中的主线如下所示:艺术是完善人生的唯一形式,艺术的存在有赖于自身的审美价值。在艺术鉴赏中,感性取代了道德,审美创造了快乐,体验丰富了人生。
五、余论
综上所述, 佩特所推举的审美批评具体化原理,分别呈现在他对文艺复兴艺术与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解析与鉴赏之中,也体现在他对柏拉图美学原则的归结之中。无论是艺术的细节还是理论的原则,无论是艺术的人生化还是人生的艺术化,佩特均提出一些相对独到的观点,这对我们现在品鉴古代艺术或古典美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笔者认为,佩特对于艺术与人生的思索,与其古典研究关涉颇深。如若追溯其古典研究兴致及其理论初心,就会发现他自己似乎从一开始,就怀着宗教膜拜式的热情,竭力在古典文学、哲学与艺术中,着力探寻一种有望发掘人生价值或真谛的行为准则。在其所有作品中,佩特最为专注的主题,均涉及人生如何度过或人应如何活的关切。最终,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试图设定一套与艺术和审美理论相应和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人类个体应为自身生活,生活应以艺术鉴赏为乐。艺术是直观的现实存在,有别于遥远空幻的目标。针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庸俗的生活方式,针对英国物质主义的泛滥现象,佩特在尖刻批评的同时,尝试将人们的生活兴味与审美态度,引向文艺复兴时期和希腊古典时期的艺术盛况,借此来激发人们鉴赏艺术美的情趣,鼓励人们在物质和政治领域之外寻求雅致与高贵,以便过上更有价值和更有品位的人生。